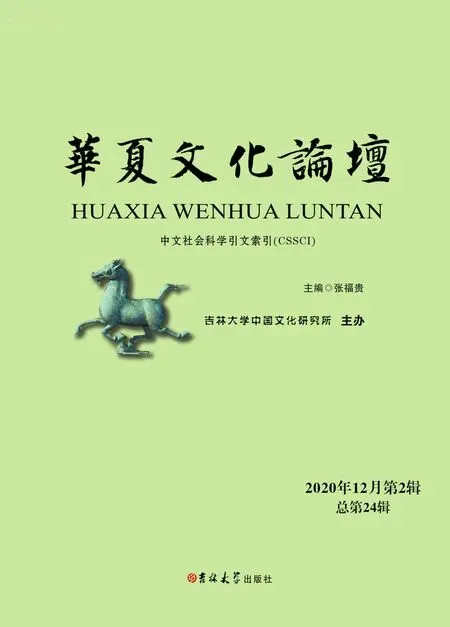悲美之趣:日本汉文小说的美学范式
——以《本朝小说》为例
【内容提要】江户时期,东传日本的中国古代诗歌数量巨大,包括《唐诗选》在内的众多诗集受到日本汉学者的推崇。日本作家川合仲象的汉文小说《本朝小说》,将《唐诗选》及《和汉朗咏集》等作品中诸多诗句融入小说创作,体现出日本特有的“物哀”“幽玄”“寂”三大文学审美意识。这种“诗入小说”的书写方式,及由此体现出的“日本式悲美”情怀,是中日异质文化融合时所出现的汉文化本土化现象,也是日本汉文小说创作的一种美学范式。
日本江户时代,中日交往频繁,中国商船舶载大量汉籍入日,这些汉籍在日本流布广泛,加之幕府掌权,大力推行汉学,汉文学占据日本文坛半壁江山。随之涌现出诸多日本汉学者,他们通晓汉语,熟读汉诗文,能够吸收中国文学精华进行汉诗、汉文小说创作。江户时期作家川合仲象的汉文小说《本朝小说》,就是中日异质文化融合背景下,日本汉学者进行汉文小说创作的一部典型作品。该小说对《唐诗选》《和汉朗咏集》等作品中诸多诗句进行接受与变容,巧妙穿插于小说故事情节发展中,与日本古典美学思想相融合,体现出了日本文学特有的“悲美之趣”。其作品,对于研究中日文化传播与交流,以及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受容助益颇多。
一、《本朝小说》对中日汉诗的受容
(一)对《唐诗选》的接受与变容
《本朝小说》除叙事性、对话性语言外,运用中国古代诗歌、骈文偶句、俗语典故等一百余处。其中诗歌94处,已知出处诗歌64处,整首引用的为31首,摘引部分对句的有25首,从多首诗中摘引一句或数句融合成一首诗的有8处,日本汉诗有10首。另有20处诗句未知出处,可能是前代日本文人所写,也可能是作者川合仲象所写。
全文94首诗中,共出现33位唐代诗人62首诗中的诗句。这一现象与江户时期中国诗集大量传入日本有关。经考察发现,川合仲象在创作《本朝小说》时,极有可能受到江户中期传入日本的《唐诗选》的影响。笔者将《本朝小说》的《自序》与《唐诗选》的序文进行比较,发现《本朝小说》序文中许多语句,明显仿效了《唐诗选》序文;考察《本朝小说》已知出处的64首诗,有47首为《唐诗选》收录,而且多集中在《唐诗选》卷六“五言绝句”和卷七“七言绝句”中,这也佐证了《本朝小说》确实受到《唐诗选》的影响;《唐诗选》在江户时代中期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汉学者的重视与喜爱,当时这本书被认为是“形成日本人中国文学修养和趣味之重要部分”①[日]日野龙夫:《〈唐诗选〉国字解·解说》,《〈唐诗选〉国字解》,东京:平凡社,1982年。的一本书。由以上几点看来,川合仲象创作《本朝小说》时,会受到《唐诗选》的影响也不意外。
分析小说中的诗句,可以看出作者并非随意摘引《唐诗选》中的诗歌,而是对其进行了巧妙的接受与变容。例如:小说开头,写石川五门夫妇八月十五夜在庭院中饮酒赏月,妻子原氏吟咏:“古人秉灯夜游,何不布筵设燕,赏青天一美人。”②王三庆、庄雅州、陈庆浩、内山知也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第122页。这里的“赏青天一美人”化用李白《拟古·高楼入青天》中的“高楼入青天”以及“遥夜一美人”两句。之后写夫妇二人对酌:“女夫对酌月徘徊,一盃一杯复一盃。我醉欲眠君且眠,有意抱琴来,何必明朝。”③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22页。化用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中的“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再如,旅馆馆主把长半介绍到坂田公时家作看护时,作者写到:“馆主与公时讲,将长半托身:今日不知谁计会,春风春水一时来。情如水不舍昼夜,姿似山易移春秋。”④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31页。前一句出自白居易的《府西池》,后一句出处未知,或为作者自己所写,或为前代日本诗人所写。作者将中日诗歌杂糅,使诗入小说,是对中国诗歌受容的一种体现。
《本朝小说》除去对《唐诗选》的接受外,也选取了未收于《唐诗选》的中国诗歌。有白居易三首七言绝句、元稹一首七言绝句、李白两首七言绝句、杜甫一首五言律诗、曹松一首五言律诗。除唐诗外,还有三国时期曹植的《七步诗》、东晋陶渊明的《四时》《饮酒二十首·其五》以及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可见作者选诗时,也参考了其他诗集,并根据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将不同诗歌的诗句糅合为一首诗。例如:小说写女主人公阿岩为父报仇,外出寻敌的艰险以及对家乡的思念时,引用诗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⑤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39页。前一句出自《饮马长城窟行》,原诗表达独居妇人对丈夫的思念,而此处用来表达阿岩对家人的思念;后一句出自李白《送友人入蜀》,原句表现的是蜀地崎岖难行,这里用来表现阿岩外出寻仇的艰难险阻。川合仲象巧妙地将中国诗歌穿插于小说情节中,丰富了小说故事情节,侧面表现出人物的心理感受。这种“诗入小说”的书写方式,使《本朝小说》具有叙事性与抒情性双重特征。
(二)对《和汉朗咏集》等其他诗句的受容
除去中国古代诗歌,小说还引用日本诗人写作的汉诗10句。这十处诗句,多出自日本平安朝中期佳句集《和汉朗咏集》,此外还有著名汉学者菅原文时、小野篁、都良香等人的名句。这是《本朝小说》对日本汉诗受容的一种表现。仔细考察发现,川合仲象引用《和汉朗咏集》中的诗句,与当时社会风气不无关系。《和汉朗咏集》自日本平安中期一直到江户时期,受到统治者和各阶层文人的欢迎,在当时起到了汉文教科书的作用。《本朝小说》同样也受其影响,例如,小说描写入冬时节,引用《和汉朗咏集》中藤原笃茂的诗句:“池冻东头风度解,窗梅北面雪封寒”。①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32页。在写阿岩外出寻仇,母亲姥氏送别女儿时,引用其中的名句:“杨贵妃归唐帝思,李夫人去汉皇情”②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36页。表达母亲对女儿的不舍与担忧。小说结尾,写阿岩报仇后,剃发出家,亦引用其中庆滋保胤的名句“长生殿里春秋富,不老门前日月迟”③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47页。对生命发出感叹。
除《和汉朗咏集》外,小说还选用一些日本汉学家的名句。如写男主人公长半被流放到浪华,见到贾船齿并,商家鳞列,娼家荡子云集时,引用平安时期诗人都良香的名句:“三千世界眼前尽,十二因缘心里空”,④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29页。表现长半初见浪华繁荣景象的心理感受——感叹人生如梦如幻。又如:小说写发狂后的阿岩,寻仇途中遇到已成乞丐的婢女阿林,引用平安时期诗人藤原义孝的诗句:“朝有红颜夸世路,暮为白骨朽郊原”,⑤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41页。表现二女悲惨经历,以及人生无常的佛教思想。
日本汉学者创作汉诗时,能够巧妙融入本国特有思想精神,做到将中国文化本土化。基于此,作者特别选取一些日本汉诗来表现本国特有的“无常观”,这正是川合仲象推崇的佛教思想在小说中的体现。
二、《本朝小说》对日本古典美学的受容
《本朝小说》不同诗人诗歌数量的选择与安排,体现出对日本古典美学的接受与变容,这是中日异质文化融合时所出现的汉文化本土化现象,也是日本汉文小说创作的一种美学范式。
小说选用李白诗12首,白居易诗11首,杜甫诗4首,岑参诗3首,王维、孟浩然、刘希夷、陶渊明诗各2首,其余诗人如张继、王之涣、杨炯、贾岛等人诗各1首。仔细分析所选诗歌,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均为抒情性诗歌。这些诗歌几乎只是抒发小说中人物或叙述者对外在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其次,政治性不强。所选诗歌很少涉及社会现实、政治以及个人志向。最后,题材的单纯性。诗歌题材绝大多数是描写眼前之景,表达心中之情。包括四季变幻、思乡、怀古伤今、表达个人心境与人生无常。这些特征,与日本岛国根性、日本人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相吻合。日本人多注重抒发个人纤细多愁的情感,抒发对外在事物的细腻感受。正是由于岛国环境和独特气候使得日本人的情感富于起伏变化,对自然、生命有了独特认识,内心体验着万物的生死轮回,在春去秋来四季变幻、自然界的生机与衰飒中,体味着生命的美好与无常。所以,日本学者久松潜一在《日本文学的风土与思潮》一书中,将日本文学定义为“季节的文学”。这些特征也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逐渐形成日本古典文学注重情绪感受、注重对个人苦闷哀伤心情的宣泄与表达的审美基调,最终确定了日本三大古典美学思想——“物哀”“幽玄”与“寂”。
笔者在分析《本朝小说》后发现,其受到日本本土文化的沁润,无论是情节、人物行为及心理,还是外部环境的描写,都通过精心选取的诗歌表现出来。诗句中融入了“物哀”“幽玄”与“寂”的美学思想以及作者本人对人生的诸多体悟与感怀。相比于越南、朝鲜等地的汉文小说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文化上对中国有高度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言,①朱洁:《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35页。《本朝小说》更多地展现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这样看来,小说外在采用的诗歌“样式”是中国的,但其内在所表达的“情感”却完全是日本的。
(一)物哀之美
日本“物哀”是受中国“物感”影响形成的一个美学范畴。所谓“物哀”,即人由于外在客观事物、客观环境的触发,内心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低沉、悲愁、伤感、缠绵悱恻的情感。这一概念,很容易与中国古代文论“物感”概念相混淆。二者的概念表述与理论内涵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毕竟它们是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生发的概念,还是有所不同。
首先,二者所面对的客体,即“物”不同。“物感”中的“物”可以是外在客观事物,也可以是内在主观意识,即想象中事物的表象。“物哀”中的“物”主要指外在客观事物、景物。
其次,从艺术创作论上讲,“物感”与创作主体的想象构思密切相关,除去外在物象,它更侧重于意象的形成以及主观意识的表达,具有间接性。“物哀”主要是创作主体因亲见之景、亲历之事触动而产生的直观感受,更具有直接性。
再者,情感表达上,“物感”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儒家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作品反映的思想情感要符合儒家政治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通常要使情感的表达与哲理性思考相契合,力求做到“情”与“理”的统一。“物哀”则更为单纯,强调文学应直面内心,抒发个人纯粹、真实的感受,很少掺杂政治因素。
最后,主客体融合的状态不同。“物感”从文学发生论上讲,主体被动接受外界事物的感召,激发出内心情感,同时在思想、道德、学识、情志等因素影响下,达到“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融合状态。“物哀”更多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讲,通常创作主体主动感受外物,选取能够代表主体情感的外界事物,将情感完全融于外物,使之彻底情化,最终用“物”的生命形态取代“我”的生命形式,从而体现“我”对生命无常的感叹,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通过比较,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物哀”,它是一种具有纯粹日本精神的美学思想,是一种建立在直观感受上的美学理论,并且受到佛教“无常观”的影响。《本朝小说》引用的许多诗句中,同样表现了“物哀”这种情感。小说写石川五门以及阿岸父女被公府抓走后,引用唐代诗人苏廷硕的《汾山惊秋》:“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①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25页。原诗表达的是一种岁末迟暮之感,这里作者借以表达三人被抓后愁苦哀伤的心绪。“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一句,既可以表现出妻子原氏内心的担忧,同时巧妙暗示出时值秋末,万物凋零,人的命运也如此捉摸不定。小说写命案了结,婢女阿岸落发出家,罪魁祸首长半被流放浪华时,引用两处诗歌:“观身岸额离根草,论命江头不系舟”,以及“群山眼头飞,碧水鼻下极。掉(棹)水疑山动,扬帆觉岸行。山复山,河工削成青苔岩;水又水,谁人染出碧水潭?”②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25页。前一处引用日本《和汉朗咏集·无常部》中的诗句,“离根草”和“不系舟”正是对阿岸、长半二人命运的形象表达,一个剃发出家,一个流放异地,从此相隔天涯。这句诗是对世事瞬息万变的无奈和感叹,同时也是小说前后两个故事的分割线,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后一处诗句中的“掉(棹)水疑山动,扬帆觉岸行”化用唐代诗人曹松《秋日送方干游上元》中的“汲水疑山动,扬帆觉岸行”描写行船时的景象。这是长半流放途中的所见所闻,“山复山”与“水又水”的浅吟低唱中,暗含着长半内心的哀伤落寞。舟在水中行,长半放眼四周看到“群山眼头飞,碧水鼻下极”,不禁感叹世事无常,人生如梦。接着作者写到:“大公江上,吟耴之古,英雄言气,使人奋起,取之目前,‘吴楚东南折(坼),乾坤日夜浮。’顾之心,天涯去往,顿觉断肠。”③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26页。这里引用杜甫《登岳阳楼》中的诗句,表达长半的感慨——历史浮沉尚且如此,个人命运更难以把握。舟到浪华,作者引用张继的《枫桥夜泊》和卢僎的《望南楼》两首诗。由于亲见之景、亲历之事的触动,使长半产生了身处异乡的惆怅哀伤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因此选取此二诗表现长半的心绪感受。
《本朝小说》借用诗歌,将原氏面对自然万物荣枯凋零和人的命运捉摸不定的哀伤愁苦,长半流放前对未知前途的担忧惆怅、流放途中的怀古伤今、抵达流放之地时的思乡之情细致地表达出来。小说笼罩着一层深深的“物哀”情调,使读者随着小说人物的心绪,感受着日本独有的“物哀之美”。
(二)幽玄之境
“幽玄”一词,本为汉语词语,“幽”字有隐藏、不公开,沉静偏僻之意。“玄”字有深奥不易理解、虚幻不真实之意。公元6世纪,佛教禅宗思想传入日本,在日本极为盛行。源于禅宗的“幽玄”契合了日本人民细腻敏感、崇尚自然、注重因缘的心理性格而受到推崇。日本民族吸收中国思想,结合自身传统文化,将“幽玄”发展为具有本土文化特质的美学思想。
日本的“幽玄”,通常对于所要表现的对象及其含有的某种深刻难解的思想境界,并不进行直接露骨的描写,而是追求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在的神秘性,含蓄委婉、优雅柔和地表达出来,引发欣赏对象的联想和想象。它与中国的“妙悟”说极为相似,都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通常选取幽深朦胧的自然景物,表达一种深远淡雅的情思,追求意在言外的委婉含蓄的境界。但仔细比较会发现,二者实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美学思想。
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对“妙悟”的追求,是作家通过对外在客观世界的细致观察,结合自身哲理性思考,选取符合自己情志表达的意象,描绘出富有韵味的形象画面,从而形成禅韵无穷的境界。对于读者而言,只有动用自己的直觉、情感体验、学识素养、想象与联想等要素,并联系客观现实,才能把握作品的神妙境界。正如叶燮所倡导的“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
日本的“幽玄”不讲求哲理性,而重视“心”的感受。主张用“心”去主动感受、欣赏自然万物,通过冥思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内涵和发展规律,追寻纯粹的精神世界,领悟一种精神自由。它认为人贵在内省,无需过多言语,用心便可感受到一种“无中万般有”的境界。这种“‘无’的思想使人们产生了忽略艺术形式的独立审美价值的倾向,强调超越形式去显现真如,要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要求‘得其意而忘其形’”。①周建萍:《儒道佛思想对日本“幽玄”范畴形成之影响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创作者无需直陈事物表象,而要抓住事物之本质,通过写意的手法,反映“心”的感悟与冥想。接受者亦通过“心”的感悟与思索,打通与创作者之间的心灵桥梁,在一种纯真自在的状态中,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进入“幽玄之境”。
川合仲象通过诗歌将“幽玄”的审美意识在小说中表现出来,将中国诗歌之美与日本古典美学有机融合。《本朝小说》中将一些含蓄优雅的诗歌安排在小说情节关键之处,使读者通过诗歌便可以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内在情感变化,无需过多直白的刻画。如长半因盗取公时家钱财,杀死公时逃走,公时之女阿岩外出寻仇路遇盗贼,设法逃脱后,作者引用陶渊明《饮酒·其五》中的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②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38页。此诗原写山中傍晚景色,而阿岩此时处于凌晨,无论是时间还是心境都与原诗大不相同,紧跟着这句诗,作者写到:“闲雅无比,姑坐慰心”。③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38页。说明阿岩此时恐惧感已经消除,心境由紧张逐渐平缓。通过“悠然”“闲雅”等词,可以感受到阿岩内心的淡定超脱,报仇之心更加笃定,更加坚韧。作者未直接描写主人公心理变化,却通过诗歌将一些“言外之意”更好地表现出来。
“幽玄”的抒情并不是直抒胸臆,而是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由此生发出一种无常感,咏叹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体现出一种“宿命论”的思想。可以说,“幽玄”是比“物哀”更深一层的审美意识。川合仲象通过诗句,表现出“幽玄”中蕴含的“无常观”。比如,长半初到浪华,见到美人林列、荡子云集、人肩相摩的景象时,忽生出一种人生无常,如梦如幻之感。此时,作者引用刘希夷的《公子行》,郭震《子夜四时歌六首·春歌》中的“陌头杨柳枝,已被春风吹。妾心正断绝,君怀那得知”以及白居易《长恨歌》中刻画李杨爱情的诗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①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30页。川合仲象借这三首描写男女爱情的悲歌,来表现长半一系列所思所感:初到浪华,看到美人林列、荡子云集的景象,想起自己背叛委身于己的婢女阿岸另娶新欢,导致新婚妻子被杀,阿岸剃发出家的种种感情纠葛,体悟到世事无常,自己对男女之情也捉摸不透。此时,一种缠绵悱恻的哀愁弥漫在小说中,让读者从“心”出发,通过“心”的感悟与冥想,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与爱情。这种诗意化的写法,有效地强化了小说人物哀伤、凄怆的内心情感,引起读者对世事无常的感伤,促使其用“心”去追寻纯粹的、纯真的爱情,达到了“幽玄”的审美效果。
(三)风雅之寂
“寂”是从日本中世纪的“幽玄”进一步发展而来的美学理念,是日本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寂”本指事物古旧之貌或荒凉冷凄之景,正因为这种景象能够激发出日本人的审美情趣,符合他们“自然即美”的思想,所以成为日本独特的审美观。在日本人潜在思维中,自然本真是一种生命充实感的享受,自然本身的荣枯变幻能激发出他们本能的感官性审美体验,促使其去追寻纯粹的、精神性的美感。人应该感受自然之美,直视纯粹的自然,使自然与“心”直接相通,使人与自然同生共灭。这是一种日本式的“风雅”精神,当这种精神建构与禅宗思想巧妙结合时,便生发出日本之“寂”。它比汉语中的“寂”有更深广的意蕴,表达出一种“以悲哀和静寂为底流的枯淡和朴素的美,一种寂寥和孤绝的美。”②周建萍:《“趣”与“寂”——中日古典美学范畴之比较》,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中文系,2012年,第9页。
“寂”追求一种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它与中国的象外之“趣”相类似,都追求一种“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趣味。但本质上,二者是异质文化土壤中生发出的不同审美感受。中国之“趣”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儒释道思想相结合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中国文人在潜意识中都有一种“积极入世”思想,心怀抱负,想要建功立业。当“入世”受挫后,他们只能无奈选择“出世”,通过参禅悟道、修身养性来找寻心灵的寄托,但即使归隐深林,依然很难完全摒弃世俗,内心深处还存有“入世”的渴望或信念。这种“积极入世”思想,使中国之“趣”带有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精神态度。文学作品中,既表现出空灵含蓄、自然淡雅之美,也体现出豪放刚烈、大气磅礴的雄健壮美。日本之“寂”则更趋向于一种阴柔美。文学作品在选词描物上,都偏爱“冷”“清”“淡”“枯”“素”的情调和色彩,追求一种冷寂枯淡的审美情趣。由于日本民族特有的心理性格,使之形成了崇尚阴柔、枯淡、闲寂之美的民族风尚。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淡化了政治,淡化了人的理性因素,多抒发个人内在隐秘的情感心绪,追求一种哀伤唯美的悲情色彩,读者能从作品中获得精神的慰藉和美的享受。这是一种“日本式的悲美”,是日本民族自然观的体现,是日本人与自然独特的相处方式。他们将孤独的自我投身于大自然中,感受自然,直面心灵。这是他们对生命的一种尊重与肯定,是主动融入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他们流连于悲欢离合的哀伤中,忘情于世事无常带来的空寂虚幻,享受着“寂”中蕴含的悲美乐趣。
《本朝小说》所引诗句中,也体现出日本“寂”的古典美学思想。仔细分析小说所引诗句会发现,其中包含的“寂”,符合王向远教授在其论文中阐释的“寂”的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寂之声’(寂声),第二是‘寂之色’(寂色),第三是‘寂之心’(寂心)。”①王向远:《论“寂”之美——日本古典文艺美学关键词“寂”的内涵与构造》,《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小说在描写阿岩从盗贼手中逃脱后,深夜恐惧奔走时,引用王维的诗《鹿柴》。这首诗表现了“寂”的第一层意思,即听觉上的“寂静”。用盈耳之“声”来表现“寂静”感受,给人一种空寂幽深之感。此处作者用“寂之声”反衬阿岩逃跑时的恐惧心理,“空山”“深林”“青苔”等词汇也符合日本人所追求的冷寂枯淡的审美情趣。再有,小说写阿岩外出寻敌,夜晚行至山间,山中无宿,集草卧,久久难眠,化用李白《静夜思》中的诗句:“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②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37页。当阿岩得知仇人长半的下落,准备报仇,勇位小说为她设宴践行,作者引用白居易的诗句:“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③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丛刊》第一辑 第五册,第142页。这两处诗,表现了“寂”的第二层含义,即视觉上的“寂”。两句诗都写到了“月”,月之色可以说是一种“寂之色”,给人一种苍白朴素之感。比起中国人喜爱具有喜庆热闹之感的大红色而言,日本人对朴素、古旧、浅淡的颜色情有独钟。此两处,通过“寂之月”,表达阿岩内在隐秘的心绪感受以及对家乡的思念。再者,长半初到浪华,看到商家林立,人群络绎,市场喧嚣的情景时,作者引用日本诗人都良香的名句:“三千世界眼前尽,十二因缘心里空。”此处表现了“寂”的第三个层面,即一种抽象的精神姿态,称为“寂心”,这是心理上的一种主观性感受。有了这种“寂心”,整个人会达到一种平静洒脱、自由放松的状态。身处繁华的浪华,长半看到的却是人生如梦,变幻无常,想要自己内心平静下来,这便是“寂心”的一种态度。当读者看到小说前后两个故事的女主人公阿岸和阿岩最终都选择落发出家也会明白,这是她们经历了世间悲欢离合,感受过世事无常对心的冲刷涤荡后,归于寂然纯粹、淡泊宁静的表现,是主动融入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读者亦可以从小说中,享受到日本之“寂”带来的悲美之趣。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日本“物哀”“幽玄”与“寂”之间有着层层深入、不断发展的关系。“物哀”是人由于外在客观事物的触发,内心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低沉、伤感、缠绵悱恻的悲美情感,是人对自然、生命的最为直接的感受,抒发对命运虚幻无常的慨叹。“幽玄”是“物哀”之情的精神内化,当人们在外界的触动下产生淡淡的哀伤,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时,“幽玄”要求人们通过冥思去发现事物的本质内涵和发展规律,发现生命的真谛,用心追寻一种闲寂超脱和纯粹的精神自由。“寂”是从“幽玄”进一步发展而来的美学理念,是日本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当人们进入“幽玄之境”后,可以体会到作品所蕴含的一种哀伤唯美的悲情色彩,获得心灵的超脱和精神的慰藉。当这种情感进一步深化,转化为一种享受与乐趣时,“寂”便产生了。“寂”是日本民族自然观的体现,是日本人与自然独特的相处方式,是他们感受到世事无常后,对生命的一种肯定与把握。由“物哀”“幽玄”融合发展而来的“寂”是一种“日本式的悲美”,它使人流连于悲欢离合的哀伤中,忘情于世事无常带来的空寂虚幻,享受着“寂”中蕴含的悲美乐趣。
川合仲象的《本朝小说》,巧妙地将汉诗穿插于小说情节发展中,以此彰显出的日本古典美学思想,正体现了平安时期汉学家菅原道真提倡的“和魂汉才”思想,同时也为日本汉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种美学范式。笔者对《本朝小说》进行了美学视角的分析,希望可以对当下日本汉文小说的研究,以及日本江户时期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交流提供另一种角度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