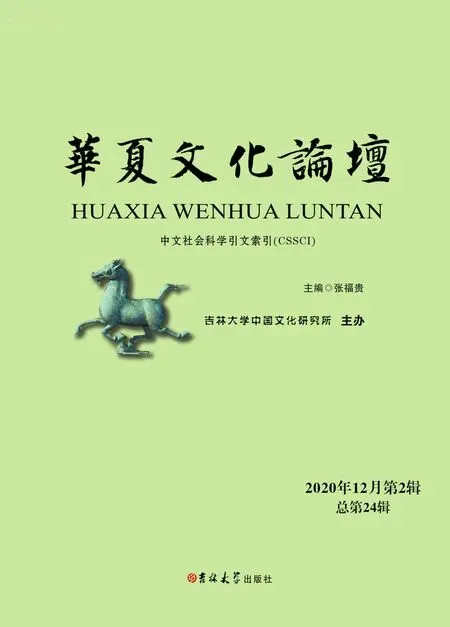中国近代科学防疫第一人:华人医学家伍连徳与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
【内容提要】1911年召开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是近代中国开始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防疫体系的标志性事件。但其首倡者并非是国内的伍连德等人,而是最早来自俄国方面,清政府担心列强插手损及主权,转而积极争得主办权。在会议的筹备和举行过程中,伍连德被委以重任,领导了会议的顺利进行,他本人也在会后受命负责落实会议决议,筹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并长期主持工作,成为这一地区及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推动者和标志性人物,从中也可看到近代华人华侨在回国参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特殊历史面相。
伍连德(1879—1960),这个出生在英国殖民地马来亚槟榔屿的首位华人剑桥医学博士,因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素享“鼠疫斗士”、“防疫先驱”等盛誉,并于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候选人,其生平和事迹已受到广泛的关注。①有关伍连德的研究情况可以1995年为界,此前主要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台港等地以其传记为主的记述,之后开始受到大陆学界的注意,相关的情况可参见黄贤强:《史料、时空与史观:伍连德传的比较研究》,《现代传记研究》2014年第1期。然而与伍连德对近代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相比,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最明显者莫过于相关论著主要集中在医学界,重点也在于总结和概括他对中国近代医学和卫生事业的贡献,而从华侨华人及历史研究角度的探讨尚不多见,不但众多关键性史实尚待厘清,而且研究的资料也多依赖伍连德的自传,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以本文探讨的伍连德参加1911年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活动为例,在这场近代中国首次举办的国际医学会议中,伍氏既是筹办与推动会议的核心人物,又从此开创了他之后二十余年的防疫生涯,可谓改变其人生轨迹的分水岭式事件,目前尚未引起应有的注意。因此有必要在重构相关史实的基础上就此做一专门的考察,也希望借此讨论伍连德在近代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构建中的作用,以及近代华人华侨在回国参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殊历史面相。
一、承担会议筹备重任
1911年4月3日,由清政府外务部和东北三省地方政府联合举办的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开幕,与会的正式代表主要由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一流医学或防疫专家组成,时人称其为中国“空前未有之学术大会也”①陈垣:《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广州:光华医社,1911年,第1页。。以历史之后见观察,此次会议也应视为中国医学开始参与国际医学活动及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卫生防疫体系的重要标志。
对于具体是何人、出于何种动机发起会议,现有的研究却存有不同看法。一种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伍连德是首倡者,但持此论者均未给出相应的史料依据。②邵宇春:《沈阳历史上的首届国际学术会议》(《兰台世界》,2009年11月,高龙彬在《伍连德与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创立和演进》一文中也持同样意见(《南方论丛》2014年第6期。此外,袁熹的《清末我国举办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档案史料》,新华出版社2001年)、王银的《1911年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略论》(《红十字运动研究》2007年卷)提出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是会议首倡者,焦润明、焦婕在《清末万国鼠疫研究会考论》(《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一文中则持清政府说,但均未给出相应的史料依据。其实伍连德在本人的自述中曾明确表示,并不清楚谁是会议的最早提议者,他自己在接到外务部的开会通知后也觉得“出人意料”。很显然,会议的发起者不可能是他本人。③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程光胜、马学博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以笔者所见史料,会议的最初发起并非出自中国方面,而是来自俄国人的提议。1911年1月19日,俄国向英美等列强发出照会,声称东北的鼠疫不仅威胁到俄国,而且有传入欧、美的危险,但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既不合理又无效率,要求各国联合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也有必要邀请各主要国家的医学专家前往疫重之区做一次国际调查。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中美往来照会集(1864一1931)》(第1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00页;《俄使照会派医研究鼠疫》,《顺天时报》1911年1月21日,第2版。清政府判断俄国此举虽以防疫为名,实则包含其借列强之力介入中国防疫内政之意图,遂决定接受提议,主动向列强发出照会,邀请各国选派医生前来,并负责差旅、保险等项费用。但俄国又节外生枝,提议各国医生抵达东北后在哈尔滨召开一次万国防疫会议,且会议要由俄方主导。中国政府再次由外务部向列强表明:希望各国医生尽快到达东北,并由中国组织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这一倡议很快获得英、美、法等国支持,俄国随后也表示愿意派代表团参加,德、比、意、奥、日等国也同意选定代表。⑤参见管书合:《国际合作与防疫主权: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再研究》,《史学月刊》2020年第6期。
可以看出,此次鼠疫研究会的最早提出者应为俄国人,中国政府因担心其节外生枝、干涉主权,才力争会议主办权。在此过程中,外务部曾特地致电时任哈尔滨防疫局全权总医官的伍连德,就会议的地点和时间问题征求意见。伍氏在召集各医生会商后,建议会址选在受日俄势力影响较小的奉天省城,并拟定于三月初五(4月3日)开会,会期两周到五周,均为外务部所采纳。①《外部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6。
不过,中国政府虽然争得了万国鼠疫研究会的主办权,但以当时国内对传染病的认识与研究水平而言,能否成功筹办这样的会议,国内外舆论普遍并不看好,俄、日两国也均抱有凭借医学优势以凌驾于中国之上而主导会议之意图,因此如何准备会议的学术议题至关重要。②陈垣:《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第43-47页。为此,外务部经过讨论,决定将此重任交由伍连德负责。2月22日,外务部特地致电锡良,“所有会中应议事件,已饬伍医官先事准备”。③《外部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廿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6。为慎重起见,外务部还专程从北京派出英国医生礼耳到哈尔滨,面见伍连德请示相关事宜。2月26日,受外务部指派,伍连德又携同礼耳等人从哈尔滨赴奉天拜会锡良,面商会议筹备事项。3月17日,在哈埠疫情已基本肃清后,伍连德再次启程赴奉,全力筹备会议,直至大会开幕。④《哈尔滨郭司使等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廿八日)、《长春孟道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廿九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15-23;《医学博士赴奉之宗旨》,《远东报》1911年3月18日,第2张。
从当时情况来看,清政府之所以指定伍连德负责准备会议的学术议题,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他的医学造诣和防疫成就。自1908年从槟榔屿归国后,他以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资历被聘为北洋陆军医学堂帮办,待遇优渥。但1910年12月下旬在东三省疫情日趋严重之际,伍连德临危受命,到疫情中心哈尔滨调查疫情并协助当地防疫在他的主持下,哈尔滨防疫局先后制定和实施了诸如断绝交通、焚烧尸棺、隔离检验等医学干涉措施,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即成功控制了当地疫情,乃为扑灭这次鼠疫大流行的转折性事件,也赢得了中外舆论的一致赞誉。⑤参见管书合:《伍连德1910-1911年在东北防疫中任职“全权总医官”考》,《史学集刊》2018年第6期。外务部委任他来筹备会议的学术议题可谓众望所归。
此外,伍连德的华侨及留学生身份应该也是外务部考虑的重要因素。从上文所述会议的发起经过可以发现,中国政府能够争得主办权,实际上离不开英美等国的支持,而要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尤其面对俄、日两国的可能挑战,同样需要争取这些国家的合作。而伍连德虽自1908年开始任职于北洋陆军医学堂,但从身份上说仍是英国殖民地的公民,又长期在英国留学,在北京可以经常出入已颇为国际化的使馆区,“经常在这里能够遇上许多来自于他们留学国家的外国朋友”⑥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下),程光胜、马学博译,第368页。。再加上他本人乐于交游,回国后很快与京、津、沪等地的欧美医学、外交界人士相熟稔,如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英国驻华公使馆医师格雷博士(后被提升为公使)等都保持着良好的友谊。⑦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下),程光胜、马学博译,第9、10章。从协调英美国家的关系并争取支持的角度来看,伍氏也是十分恰当的人选。
从后来的情况看,伍连德也的确不负众望。在他看来,当务之急应该详细调查各地疫死人数,“分别造册以备将来开会研究”,并决定从哈尔滨附近各地开始着手进行调查。鉴于满洲里是中国境内最早发疫之地,对研究疫情具有特殊意义,伍连德又派遣天津北洋陆军医学堂解剖教授、时任哈尔滨防疫局医官全绍清前往实地考察,“以为会议张本”。此外,黑龙江地区因开发较晚,缺乏专门卫生人才,也由伍连德等人订立调查项目,遴选深明医理、卫生的统计学人员驰往调查,或协助当地调查,“事关国体,预备宜周,勿稍大意”。①《饬哈尔滨郭司使电》、(宣统三年正月廿二日)、《饬哈尔滨郭司使电》(宣统三年正月廿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15-22。此次对疫情的详细调查为近代中国以来首次,不但成为此次会议讨论的基本材料,会后又经东三省行政部门连同各项防疫规则、会议相关资料等,汇编一书,即《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共三大册、数百万字。并经批量印刷,分送全国各处,对后来国内防疫和研究均具典范意义。②(《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纂修题名》,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一册;《函送驻奉各国领事疫事报告书由》,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档号:C10-12311。)
为了展现中国学者的医学水平,伍连德经与哈尔滨防疫局各医生会商后认为:此次疫症直中肺脏,哈埠的俄国医生已经做了解剖研究,中国医生尚未进行,恐怕开会时“于研究上实为缺点”,亟需立即着手。因事属创行,特电请东三省总督核夺。锡良总督立即回电表示同意。③《哈尔滨郭司使等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初四日)、《饬哈尔滨郭司使电》(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15-23。哈尔滨防疫局接到回复后即遵照进行解剖,还准备了鼠疫细菌标本,配以详细说明书,以供会议研究使用。④《东省疫症警告》,《吉长日报》1911年3月22日,第一张第5版。伍连德自己也从哈尔滨的病例中提取了细菌培养物,随身带至奉天后,专门安排了一间单独的实验室进行研究。⑤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程光胜、马学博译,第58页。
除认真准备之外,伍连德等人还重视与欧美医学界人士的合作。美国参会代表斯特朗(R.P.Strong)和奥斯卡·蒂格(Oscar teague)在会议开幕前半个月携带细菌检测仪器到达奉天,中国方面特意提供了实验场地以及奉天鼠疫医院数十例新近疫死者供其解剖。⑥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程光胜、马学博译,第58、76页。英国先是派出地方自治部医官雷金纳德·法拉(Reginald Farrar)作为参会代表,后因印度当时也发生了鼠疫,亟需研究,又以印度政府名义派出细菌学家皮特雷(G.F.Petrie)为代表⑦《吉林行省为准驻英钦使函英政府现派医官来哈尔滨研究疫病的札文及东三省总督的咨文》,吉林省档案馆藏,档号:J101—37—5112。。中国方面为此特意从满洲里捕捉12只旱獭,用快车运至奉天以供英国代表研究⑧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程光胜、马学博译,第82页。。
对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伍连德等人也力图寻求英美的合作。起初,奉天方面拟定代表遴选的标准是“学有专门”的“在事防疫医员”,据此推举了10名代表人选。⑨《致外部电》(宣统三年二月廿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8;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二编第2-7页。除司督阁是在奉天行医多年的苏格兰传教士外,其余均为中国人。不过,外务部收到这份名单后却并未立即同意,而是交由赴奉专门筹办会议的外务部右丞施肇基会同伍连德和奉天方面进一步讨论,在会前两周,才最终确定9名正式代表,除保留最初名单中的伍连德、全绍清、方擎、王恩绍、司督阁外,又加入英国人希尔(公共卫生学博士、北京协和医院讲师)、格雷厄姆·阿斯普兰(医学博士、北京协和医院讲师)、阿瑟·斯坦利(医学及公共卫生学博士、上海工部局卫生官员)、俄国人保罗·B·哈夫金(哈尔滨俄国防疫医院院长),其中数位就是由应伍连德邀请而来的。①《外部来电》(宣统三年二月廿五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8;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二册,第三编第一章第2页;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会议的筹备工作紧张忙碌,直到大会开始前一天,伍连德还在为朝廷特使施肇基的讲稿作最后的润色,为会议作了充足的准备。
二、伍连德在会议中的双重身份
经过精心的筹备,1911年4月3日(三月初五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省城小河沿惠工公司正式开幕,伍连德被公推为大会的主席,这就意味着对于接下来近四周的会议,伍连德既有领导之责,须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同时作为中国的代表团长,又要尽力展现中国的学术水平,并且要谨慎应对任何可能对中国主权有损的言论和提案。
对于大会主席之职,会前俄日两国均有意争得,以便于主导会议。上海《申报》对此评论称:“鼠疫研究会之开办,以吾国为东道主,无如吾国医学不见发达,会长一席,遂惹起他人艳羡,以某国为甚。其某博士之来东,最在事先,即为此也。”②《东三省通信》,《申报》1911年4月22日,第1张第5版。这里所指是俄国早早派出了以医学博士查伯罗特尼(Zabolotny)为首的代表团一事,该团于1911年3月初即抵达哈尔滨,并于3月17日先期赴奉天,并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俄方舆论宣称,查氏已由中国政府请为奉天万国瘟疫研究会议长,显系为争取会议主席制造舆论。③《医学博士赴奉之宗旨》,《远东报》1911年3月18日,第2张。日本代表团为首者是曾师从德国著名细菌学家科赫、并在鼠疫研究方面而享有世界声誉的北里柴三郎博士。3月23日,北里甫从日本抵达大连,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日本处在鼠疫研究的世界前列,中国只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无权为此次会议设置议题。他警告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日本代表将予以坚决抵制。④《北里博士行程》,《盛京时报》1911年3月21日,第5版。伍连德和负责会议筹备的奉天中国官员们也感觉到:北里颇有意争取大会主席位置,以压服中国医生作为会议的领导者,日本人将是会议的“最强不和谐音者”。⑤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程光胜、马学博译,第58-59页。另据当时国内报纸报道,会议开始之前,为杜日、俄觊觎,“幸有美医士深恐喧宾夺主,不第不甚雅观,且与中国主权亦形丧失,遂不惜周折,与吾交涉司说明,且与各医士关说,同举伍连德为会长。”①《东三省通信》,《申报》1911年4月22日,第1张第5版。另据当时在上海出版的《中西医学报》的报道称:“众意皆以伍连德为会长,某国阴梗其议,伍亦谦让未遑,卒从众议,推伍为会长”。(《医事新闻》,《中西医学报》1911年第13期。)因此,大会开幕当天,伍氏才顺利被推为主席。
为争取俄、日代表的合作,在伍连德的主持下,俄国代表团团长查伯罗特尼博士被安排在开幕式上代表各国专家发言,日本代表团团长北里教授也主持了细菌学与病理学部分的会议。这些安排显示了伍连德富有经验和卓识,后来在整个会议期间,俄国代表团表现得“颇为友善和长于交际”,北里等日本代表也对会议的顺利进行“贡献良多”。②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程光胜、马学博译,第58、71页。不过作为大会主席,大部分的会议还是由伍连德主持。据当时报载,会场上各国代表发言踊跃,“互陈意见,甲论乙驳,议论沸腾”③陈垣:《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第30页。。或因争论过于激烈,竟有代表因受刺激于会后服毒自杀,所幸抢救及时,亦可见场面之热烈。④《德医自杀》,《顺天时报》1911年5月7日,第2版。对于这种场面,伍连德均能及时的裁定或引导,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大会主席的身份之外,伍连德还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不但要经常就学术问题发言,以彰显中国的学术水准,更须时时警惕和防范会议上有可能损及中国主权的提案和言论,其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大会最后阶段(4月24日-28日)的讨论。按照议程,这一阶段主要是商定和表决会议决议,以作为大会报告提交给中国政府。但在欧美等国代表主持拟定的草案中,关于对中国防疫行政意见的部分内容,让伍连德等人感到侵及内政、逾越大会主旨。其中较为突出者是草案D部分第3个问题,英、俄等国代表根据欧美的经验和惯例,分别建议清廷在中央政府建立专门负责公共卫生的部门、在全国各县建立卫生机构并配备一定数量的医生和卫生工作人员、在全国建立死亡登记制度。对此,中国代表伍连德、司督阁等人都明确反对,并与英、俄等国代表反复争持不下,他们反复强调这些建议已超出了会议职责范围之外,并且不符合中国实际,即使在欧美国家也不见得能够完全实施。会场连日讨论因此也异常激烈,“大有敝唇焦舌以向争之概”。⑤《万国鼠疫研究会闭会》,《盛京时报》1911年5月1日,第5版;《防疫会中之中国医士》,《顺天时报》1911年5月4日,第2版。相关讨论的内容和具体情况可见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417-446页。最终,在英国驻华使馆医官并充任该国代表的德来格等人的协调下,草案绝大部分内容经修改讨论后达成一致意见,个别争议较大问题以会议表决形式决定,最终形成决议45条,以作为会议临时报告,于4 月 28 日(三月三十日)下午大会的闭幕式上提交给中国政府。⑥《万国鼠疫研究会闭会》,《盛京时报》1911年5月1日,第5版;会议决议可参见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二册,第三编第一章第3-14页。
对于大会过程和结果,中国方面自然极为满意。大会闭幕当天,锡良、施肇基二人联名向军机处、外务部报告称:各国代表一致认为中国政府此次办理防疫事宜“俱中肯綮”,会议决议主要内容也是关于隔离、检验疫病、疑似病院及交通运输的防疫设施等方面,不涉主权,“各员以防疫大会,环球创举,宣扬仁,著为美谈。复以待遇优备,力陈谢悃。①《致军机处、外部电》(宣统三年三月三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4-46-19。而伍连德作为大会的主席也备受各方赞誉,尤其在英美各国,“声名藉甚”。经外务部推荐、学部奏请,清政府授予其医科进士;又经陆军部奏请,授予其陆军正参领,以备军医之用,舆论也称其“身价十倍”。②《伍连德身价十倍》,《盛京时报》1911年5月6日,第2版。另外,清廷还选派其为三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1911年12月在海牙举行的第一次鸦片会议。③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下),程光胜、马学博译,第647页。
三、被会议改变的人生轨迹
可以看出,万国鼠疫研究会能够顺利举行,伍连德是居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而在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对伍连德本人也影响巨大,乃至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会后不久,按照大会的建议,清政府授命伍连德负责筹办东三省防疫总处,并于翌年开始运行。在此后二十余年里,伍连德长期担任这一机构的领导职务,其主要的防疫和学术活动,也基本上是在这里展开的。
还在研究会的大会讨论时,各国专家就一致认为:“防疫之举重在发生之时,执行防治尤重在瘟疫扑灭之后从事预防”。④伍连德:《东三省北境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全书》,第二册第37页,1917年。因此,在研究会向中国政府提交的会议决议中,首要强调的就是对鼠疫的研究与预防工作,前8条即开宗明义指出:应当就地研究而收其成效。特别是在满洲里,每年应在猎取旱獭季节设立医务部、隔离所以及临时病院,以作监测和预防的准备。⑤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二册,第三编第一章第4 页。此外,决议第13条认为肺鼠疫预防最主要的措施是隔离,因此建议常设传染病医院;第42条建议中国政府设立常设卫生机构,“一遇疫病发生,可以扩充办事,”并能迅速提供防疫专家的名单以备随时调用。⑥张元奇等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二册,第三编第一章第7页、14页。
甫经肺鼠疫大流行之创痛巨深,中国政府对于这些建议高度重视,在会议结束不久,即由外务部委派伍连德负责具体落实,并饬令东北地方政府拨给其所需建筑、人员经费及常年费用。⑦《致吉江两省电》(宣统三年四月二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锡良档案,档号:甲375-16-29。1911年5月中下旬,伍连德带领两名助手为此专程再赴东北,先后到奉天、哈尔滨、满洲里等地同地方官员会商并实地考察,初步拟定在哈尔滨、满洲里两地设立医院、隔离所。⑧《伍医官来哈消息》、《伍医官来哈》、《伍医官北赴满洲里》,《远东报》1911年5月18日、21日、25日,第2版。同年7月9日,伍连德又偕同曾普(北洋医学堂毕业)、陈祀邦(剑桥大学毕业)等医官和俄国医学专家查伯罗特尼博士等人组成中俄联合考察团,先后赴俄境之博杂、中国境内之满洲里、齐齐哈尔,专门考察各处旱獭与肺鼠疫的关系。所到之处,不但随时捕捉旱獭化验并种植疫苗实验,还冒着危险掘开獭穴深入观察,基本弄清了旱獭的生物特性、生活习性、寄生蚤类及常见疾病等情况。①《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伍连德赴满洲里等地考察旱獭等咨行黑龙江巡抚周树模》,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21-3-52。
此次考察结束后,伍连德继续筹备工作,在东北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相继在哈尔滨、满洲里、三姓、拉哈苏苏等地设立医院,1912年10月正式合称为北满防疫事务管理处,直接隶属于外交部,常年经费由哈尔滨关税项下拨付,伍连德为该处总办兼总医官。②《吉林行省为哈尔滨防疫医院报开用关防日期的批文》,吉林省档案馆藏,档号:J101—21—0657。1918年又应营口地方和海关邀请在当地开设医院,该机构下辖医院已逐渐扩展至整个东北地区,更名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伍连德也长期担该处负责人,直到九一八后东北沦陷才被迫撤离。
在其存在的二十余年里(1912-1932),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不但在东北地区多次成功组织防治鼠疫、霍乱等疫病的流行,而且长期致力于传染病及公共卫生学研究、培植医学教育、促进地区公共卫生建设、进行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等方面工作,成就斐然,在近代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在当时就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组织之一”。这些成就当然与伍连德的努力密不可分,而他本人亦孜孜不倦地工作和研究,也赢得了广泛的中外赞誉。1924年梁启超评论称:“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③伍连德编纂:《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大全书》,第4册,1924年。;1931年《良友》杂志评价他:“为近世医界有数之人物,其学识之深造,久为中外所共仰”。④《得之于人,用之于世——医学家伍连德自述》,《良友》1931年第58期。在世界范围内,伍连德也以“鼠疫斗士”为人熟知,并于1935年获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候选人。
结语
伍连德与1911年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之关系至此已大致廓清,但仍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这个回国不到三年的年轻华人,何以能够在中国近代举办的首次国际医学会议上被委以重任,并在此后二十余年里孜孜矻矻,成为近代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有力推动者和标志性人物。通过本文的梳理可以看出,作为中国近代以来首次举办的国际医学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并非是国内医学进步的自然结果,而是晚清政府在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时为防止列强插手并损害国家主权的所采取临时危机应对措施,也标志着近代中国在传染病频繁跨区域流行的新变局和西方医学的冲击之下,因关系到民众健康与政府责任,建立与世界接轨的卫生防疫体系已刻不容缓。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伍连德作为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精通西方医学并具备世界眼光的专业人才,以及因华人留学生身份与西方国家的特殊关系,自然能够脱颖而出。此外,伍连德始终“热情关注自己国家”,当被外务部征询是否愿意到哈尔滨扑灭疫情时,他认为这既是难得的科学研究机会,也是“真正为伟大的祖国服务”,所以毫不犹豫的表示接受⑤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程光胜、马学博译,第346-348页。。这样的信念也让当时外务部主持其事的施肇基及地方的锡良等人印象深刻,从而给予坚定的支持,应该也是重要的原因。
然而与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从海外归来的华人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在伍连德回国的三十年里,虽然相继服务于晚清、民初北京政府、东北的奉张、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外各方均能维持良好关系,但他担任的一直是实际从事防疫卫生方面的职务,与政界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极少卷入当时的政治纷争。在这个意义上,伍连德及所代表的这类知识分子,或许可以称为福柯所说的“特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场所虽然主要在于实验室、医院、学校等具体的场所,以实际的工作影响了普通民众的健康、国人知识结构的质变以及与世界接轨的科学体制的建立,理应受到更多地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