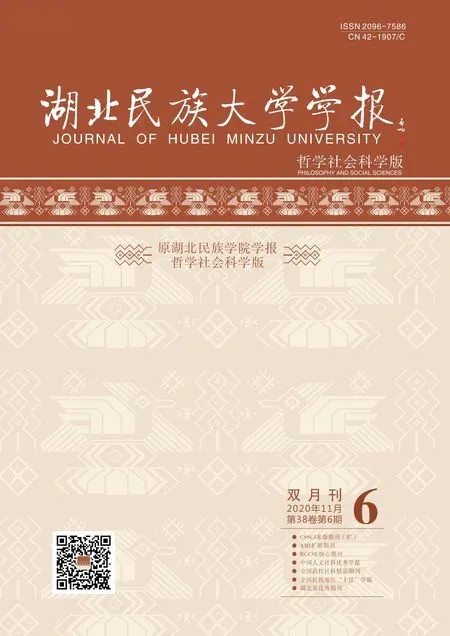明代汾州地区乡贤文化的形成机制与影响特征
黄永林 任 正
明代是我国传统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学者们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视角展开讨论,或从宏观透视,或聚焦一地深入研究,探寻官民互动下的明代社会。(1)参见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潘星辉:《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杨国安:《明清时期两湖地区乡村社会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明代官方与民间在不断博弈中实现了双赢,诸多社会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纷纷兴起,积极参与到民间秩序维护和地方社会发展之中。其中,乡贤群体崛起的意义重大,有了乡贤参与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政治运转、文化传承等都出现了有别于先代的特征。
“乡贤”是空间与人的集合,是某一区域内贤达群体的集聚,是该地社会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乡”是特定的空间,指县以下的区域;“贤”原意指财物多,后引申出指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再后来又指有较高文化水平、道德素质,对社会贡献较大,名望较高的人。(2)先唐时期并无“乡贤”一词,“乡”和“贤”二字各有含义。许慎《说文解字》载:“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乡,六乡治之。”“贤,多才也。从贝臤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啬夫别治:别治谓分治也。百官公卿表曰:县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贤,多财也。财本作才,今正,贤本多财之称,引申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申之义而废其本意矣。”“乡贤”一词作为正式词汇出现,最早可溯源到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杂述》:“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3)刘知几 :《史通》卷十《杂述》,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刊本。唐宋时期的乡贤尚无籍贯的特殊要求,只要是德才兼备,名望颇高的名士即可。明代以降,乡贤的属地性特征日益明显,乡贤在地方社会的影响逐渐增强,乡贤文化由此形成。关于古代乡贤的研究成果颇多,学界主要通过方志、碑刻等资料对乡贤的历史渊源、内涵外延、社会功用等进行阐释。(4)牛建强:《地方先贤祭祀的展开与明清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赵克生:《明清乡贤祠祀的演化逻辑》,《古代文明》2018年第4期;赵克生:《明清乡贤考据述论》,《古代文明》2019年第3期等。但这些研究多数过于宏观且对古代乡贤文化的探讨不够深入,对乡贤文化的区域性研究尚少。本研究以明后期的山西汾州府为中心,对汾州府乡贤文化的形成、作用机制进行探讨,以期对乡贤文化的研究提出一些思考。
一、乡贤的历史形成与认定过程
(一)祭祀政策:从先贤祠到乡贤祠
乡贤的形成与国家祭祀政策的演变密切相关。古代圣贤的祭祀由来已久,(5)春秋时期的《周官·春伯》:“有道有徳者使敎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到秦汉时期,士大夫认为祭祀先贤是移风易俗,教化百姓的重要方式。各类祭祀先贤的祠庙曾广泛散落于中国的乡间村落,也有一些存在于城市甚至皇家庙宇之间。这些先贤既有本乡名人也有外乡贤达,总的来看大部分祭祀属于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寄托着民众对该先贤的怀念与尊敬。
将先贤祭祀上升到国家层面,对先贤进行广泛祭祀始于唐代。唐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6)吴兢:《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贞观四年(630)“壬午,令自古明王圣帝、贤臣烈士坟墓无得刍牧,春秋致祭。”(7)刘昫:《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太宗下》,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同年,唐太宗又下令全国各州、县学皆建立孔子庙。(8)欧阳修:《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第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孔子成为全国性先贤的同时,其他一些古圣先贤也得以进祠庙,入祀典,成为地方祭祀的一部分,由州县官员定时致祭。唐天宝十三年(754),玄宗下令在地方设立“先贤祠”,祭祀地方先贤,(9)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八六《帝王部·赦宥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28页。“先贤祠”之名始见,地方官府开始建祠庙以祭祀包括名臣、义士在内的先贤,而建祠庙的地点则是其活动的特定区域。(10)雷闻:《唐宋时期地方祠祀政策的变化》,荣新江:《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9-294页。宋承唐制,在全国各地亦设有“先贤祠”,这些地方祭祀的先贤有籍贯在此的本土乡贤,有遗爱一方的外乡官员,还有与本地毫无关系但声名显赫的贤达之士。到元代以后随着科举仕途受阻,不少士人经营地方,造福乡里,逐渐形成了地域色彩浓厚的地方乡贤群体。明代以降,日益完善的科举制度与户籍政策,(11)明代科举制度较唐、宋已相当完备,此时的地方学校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平台,祭祀乡贤的乡贤祠与名宦祠成为地方学校的标配。此外,明代户籍制度较宋代严苛,官员致仕、丁忧必须回到原籍,这使得这些地方精英的家族势力在乡土得以沿续,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都占据了优势地位,成为地方权威。随着明朝政府对地方祭祀政策的改革,这些地方士绅的权威日益显现。使以地方乡贤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与地方的结合更加紧密。“地方先贤祭祀,从宋代的先贤祠到明代的乡贤祠的变化,反映了宋明两代地方社会势力的强弱差异。”(12)魏峰:《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先贤祭祀看宋明地方认同》,《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从唐宋到元明时期,随着国家祭祀政策的不断调整,先贤的属地性日益增强,地方在祭祀先贤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被祀者的籍贯,“先贤祠”也逐渐演变为“乡贤祠”。
明代是乡贤祭祀制度完善的重要阶段,国家权力通过乡贤祭祀这一手段延伸到了地方,由此形成的乡贤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效果显著。地方精英则通过控制乡贤祭祀的各个环节,不断增强了他们在地方的影响力。据《大明会典》载,明初,朱元璋曾下令:“凡应祀神祇,……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具实以闻,著于祀典,有司岁时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尝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祭、其祠宇禁人毁撤。”(13)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九十三《群祀》,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1466、1467页。到嘉万时期,明政府对祀典进行了修改,“嘉靖九年,令各处应祀神祇帝王、忠臣孝子、功利一方者,其坛场庙宇,有司修葺、依期斋祀、勿亵勿怠。……凡各处乡贤名宦祠,万历二年令各抚按官查勘釐正,有不应入祀者,即行革黜。”⑨明代,国家积极引导地方祭祀品学兼优、利国利民的地方贤达,“有功德于一时者,一时祀之,更代则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逾境则已。”(14)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奏考正祀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时,乡贤祠成为地方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明万历《汾州府志·学校类》中载有汾州府乡贤祠及所辖一州七县乡贤祠,共计两级九所,祭祀有历代汾州府乡贤60余人,这些乡贤祠均位于学校戟门西边,与戟门东边的名宦祠相对应。(15)王道一:《汾州府志》卷四《学校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9-54、48页。
“按化名成俗,必繇学校,则学校非贤士之关治化之府乎?……汾风气淳厚,士兢好修,固将出为名世、处为真儒,以增学校光者,宁直裨益民俗已哉!”乡贤祠与名宦祠并列于学校之中,前者祭祀生于本地的乡贤,注重籍贯的本土性,后者则祭祀仕宦当地的官员,侧重对地方的贡献性,二者泾渭分明,但又形成合力,共同净化地方风气。“仕于其地,而有政绩,惠泽及于民者,谓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徳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果有遗爱在人,乡评有据,未经表彰,即便及时兴立祠祀,以励风化。”(16)俞汝楫:《礼部志稿》卷八五《严名宦乡贤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让官方支持,深孚众望的乡贤入祀乡贤祠,是一项多赢的施政手段,其本人得以光前裕后,其家族获得了地方声望,为当地百姓树立了乡土榜样,也是地方官员劝民向善,教化百姓的手段。
(二)真正乡贤:从精英认可到百姓认可
明代乡贤的遴选入祀有一整套程序,乡贤入祀乡贤祠需获得三方面的认可。
首先,入祀乡贤要获得乡土精英认可。这是国家的祭祀乡贤政策落地的开端。这些乡土精英包括本地官宦、鸿儒硕学、生员、乡老等,他们熟悉地方风土人情、历史典故,深受百姓和地方官员的认可,他们的举荐在乡贤入祀过程中极为重要。所以“能否列入乡贤,有赖于此人长期在地方县学读书、其道德文章得到本地生员和乡老的一致认可。”(17)魏峰:《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先贤祭祀看宋明地方认同》,《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汾州府的乡贤亦如此,他们深受乡土精英的认可。如宁乡庞辅,“成化十四年仕,……退居林下,力持清约,乡评重之。”(18)王道一:《汾州府志》卷十一《人物类·乡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5、202、212、201、206、202、203、198页。同县陈谟,“万历二十年入祀,敦厚清简,……历官五任,囊无长物,月旦高之。”②
其次,入祀乡贤要获得地方政府认可。这是国家的祭祀乡贤政策深入基层、精准实施的关键。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官员求访有功于国家社稷,惠爱于一方百姓的忠臣烈士、孝子贤达。经过乡土精英初步推举后,地方官员加以核实,最后乡贤候选人方能被认可,入祀典,进乡贤祠或其他祭祀专祠。若得不到政府认可,这些祭祀场所就成为淫祀,被捣毁的风险很大。陈宝良认为“乡贤祠尊奉出于本地的名贤,因此学官成为具体主持祭祀、增入受祀者的主管官员。某人是否能列入乡贤、名宦祠,学官拥有很大发言权,……学官再考其行实,予以认可。”(19)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从《汾州府志》中关于汾州府乡贤的相关记述也表明了学官在乡贤选择、认定方面的重要性。汾阳张更化为“嘉靖乙丑科进士。万历辛丑,督学吴公会檄本府从祀乡贤祠。”②孝义霍冀是明万历重臣,官至兵部尚书,“带管提学道成公宪行,入祀乡贤。”②同县赵讷是“嘉靖己未进士……年七十九卒,门人私谥文直先生,提学佥事周行入祀乡贤祠。”②临县袁克良由“提学陈行入祀。”②这些汾州府的乡贤顺利入祀乡贤祠,地方学官功不可没。
除入祀乡贤祠之外,入祀典也是获得官方认可的重要标志。《汾州府志》中有许多关于汾州府乡贤的祀典赞语,如汾阳张益,“正祀考赞其‘家传科第,世业师儒。’”②介休宋隐,“祀典云:‘天性孝友,问学遂精,丧母禄不求荣,训子言必重道。’”②同县郝质,“正祀典赞云:‘御军有纪,约己甚严。’”②入祀典的地方乡贤,成为正式享受国家香火的祭祀对象,有司将严格按祀典要求,春秋致祭。
最后,入祀乡贤要获得百姓的认可。这是政府访求乡贤,祭祀乡贤的最终归宿。乡贤所拥有的无形影响力、巨大感召力是当地百姓赋予的,只有人民信服、尊崇乡贤时,乡贤才能发挥出强大的力量,进而推动社会风气的改善。明代汾州府诸乡贤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如汾阳柳诚,“乡人称为学士”;②汾阳田耔,“乡邦推重,为立忠孝祠,与辛彦博并祀之”;②平遥李颐,“立志诚笃,孝闻乡闾。”②乡土精英推举、地方政府认可、乡党百姓崇拜的乡贤是三方力量博弈的产物,尽管百姓在这一过程中处于弱势,但若无民心向背,乡贤只是没有灵魂的权力衍生物。只有深孚众望的乡贤才是拥有灵魂的地方榜样,才能最终成为地方官员推动地方教化的无形工具,为官方的乡贤祭祀政策画上圆满的句号。
二、明代汾州乡贤群体的时空分布与品格特征
汾州初设于北魏太和年间(477-499)。隋改西河郡。唐武德三年(620)改浩州为汾州,天宝元年(742)改西河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汾州。宋金元时期直到明初皆称汾州,到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由州升府。汾州府“西控黄河、东驭太岳、南临河东,当山西南北向交通要路之冲,成为地缘意义上举足轻重的统县政区。”(20)韩磊:《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与地方控制》,《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汾州人杰地灵,“汾才素甲晋邑”,(21)王道一:《汾州府志》卷四《学校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9页。走出了诸多名宦贤臣、孝子义士,他们中不少人成为汾州乡贤,得以入祀典,入乡贤祠,享受家乡香火。介子推、郭泰、狄青、文彦博、霍冀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明万历《汾州府志》载:“其人士私窃唐虞之遗化,藉资文学之陶熔,类多休懿可范,虽显晦竖立各殊,然所谓乡之善士者一而已矣。”②这些在明代汾州享受地方香火,名列方志乡贤传的“乡之善士”即汾州乡贤。他们传承着三晋大地的上古遗风,或以道德文章著称,或以嘉言懿行流芳,是汾州地区培养出的社会精英,是本地乡贤群体中的代表。他们散落在汾州府下辖的各个县中,享受着地方香火,呈现出鲜明的分布特点和群体特征。
(一)明代汾州乡贤群体的时空分布
明代汾州乡贤概况可从万历《汾州府志》卷四《学校类》及卷十一《人物类·乡贤》中一窥究竟。统县政区级的乡贤祠位于汾州府学戟门外西,共祭祀历代汾州乡贤20位,下辖的一州七县也均建有州、县级乡贤祠。永宁州祀唐宋务光等6位乡贤;汾阳县祀晋王延等20位乡贤;平遥县祀北魏郭文恭等3位乡贤;介休县祀介之推等7位乡贤;孝义县祀汉辛庆忌等6位乡贤;临县祀元袁湘等1位乡贤;灵石县祀北宋师范等6位乡贤;宁乡县祀元陈资寿等12位乡贤,合计62人。(22)王道一:《汾州府志》卷四《学校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54、55-56页。而从《人物类·乡贤》部分的记载来看,汾州府所辖各州县的乡贤除《学校类》中包含的62人外,另有《人物类·乡贤》中的45人,合计107人。(23)王道一:《汾州府志》卷十一《人物类·乡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8-215页。综合万历《汾州府志》中的《学校类》与《人物类·乡贤》两部分资料,制表1如下。

表1 万历《汾州府志》中汾州府所辖各州县历代乡贤统计表
由表1可知,汾州地区乡贤分布最大的特点是时空分布不均。而这与汾州地区不同时代在整个山西地区的重要性及内部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从历时角度来看,汾州地区乡贤分布呈现出从先秦时期到宋元明时代人数逐渐递增的趋势。(见图1)以宋代为分界线,宋代之前的一千年,汾州地区乡贤人数较少,合计18人,占历代乡贤总人数的不到20%;而宋代之后的一千年,汾州地区乡贤人数较多,合计89人,占汾州历代乡贤总人数的80%强,其中尤以明代为盛。有明一代,乡贤人数占汾州历代乡贤总人数的近50%。宋代以前,汾州地区在整个山西地区存在感较低,长期分属多个统县政区,到北魏太和年间才正式设州,汾州夹在山西北部并州和南部蒲州两大重镇之间,长期属于山西地区的弱势统县政区,辖县较少,综合实力有限。宋代以后,汾州地区经过千年积淀,其重要性日益显现。有明一代,尤其是明万历年间升级为府以后,汾州府成为与太原府、平阳府并列的重要统县政区,各项事业发展较快,各类人才较之前代有了井喷式的涌现。当然,乡贤数量由远到近的增长趋势也与前代历史久远,政区调整频繁,乡贤籍贯难以考据有关。所以,越是靠近明万历《汾州府志》编修之年,乡贤数量越多。此外,明代地方政府编修地方志其主旨是记述明代该地区的各项成就,彰显本地区的人杰地灵,所以乡贤数量到明代为盛,也在情理之中。

图1 万历《汾州府志》中的汾州府历代乡贤统计图
从共时角度来看,汾州下辖各州县的乡贤人数分布不均。汾州地区乡贤集中分布在府境东部以汾、平、介、孝、灵为代表的平川五县中,五县乡贤总数合计86人,占汾州乡贤总数的80%强,其中介休有27人,乡贤人数甲汾州。而位于汾州府西侧吕梁山区的永宁州、临县、宁乡县等三州县虽辖境广阔,但仅有21人,占汾州乡贤总数的不足20%,其中临县最少,仅有3人。明万历时期,汾州府“府属共户四万一千九百一,口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二十六”,平川五县自然条件较好,经济富庶,人口繁盛,五县人口共计45万多,占汾州府总人口的近90%。山区三县位于境西,多山地丘陵,经济落后,人烟稀少,总人口不足7万,仅占汾州府总人口的10%强。①可见,人口多寡对不同县域的乡贤人数影响颇大。但也有例外,宁乡县万历三十四年(1606)仅有五千余人,但县内入祀乡贤竟有12人,比人口远超其的灵石县、永宁州、临县都多。《汾州府志·风俗》谈到宁乡县“土瘠民穷,俗尚敦朴……士崇礼节,知名间出,有陶唐氏之遗风。”(24)王道一:《汾州府志》卷二《风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页。加之邑侯积极推动,汾州府内最贫弱的宁乡县乡贤数量反而较多,这与地方贫弱但民风淳朴、渴望人才有关。
(二)明代汾州乡贤群体的品格特征
汾州众多的乡贤组成了乡贤群体。这一群体的品格特征十分突出,集中体现在个人业绩、人格魅力、家庭背景、民众口碑四大方面,这些鲜明的品格特征构成了汾州乡贤文化的重要内涵。
1.个人业绩
明代进方志、入乡贤祠的汾州乡贤群体大多数都是饱学之士,不少人通过科举入仕,走上了传统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一些人道德文章颇为出名,还有著作流传。后唐平遥薛融“以文学名,初仕唐为补缺,直弘文馆。”(25)王道一:《汾州府志》卷十一《人物类·乡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3、199、211、201、198-215、202、212、200、203-204、210、208、215页。宋代汾阳王嗣宗“少力学,开宝八年登进士第一,补泰州司寇参军。”其著有《中陵子》三十卷。①宋代孝义赵昌言“太宗时举进士,……卒赠吏部尚书,谥累肃。①”元代汾阳张益“举进士第一,仕至国子司业。”①有明一代,汾州地区科举兴盛,入选《汾州府志》的明代汾州乡贤,绝大多数是正途出身,尤以进士为多,达20余人。另有举人10人,岁贡生7人,三类总人数占明代祭祀的本朝乡贤的七成强。①汾阳柳诚“有德行,能文章”,“乡人称为学士”。①同县刘尚义“好读书,著《柏山集》四卷”,擅长五言诗,有汉魏风骨。①孝义赵讷是明代汾州府乡贤中著作最多的一位,他“性嗜读书”“刻语录诗文三十卷,杂著纂次七十八种,郡县续志其一也。”①
2.人格魅力
汾州乡贤德才兼备,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是地方忠孝楷模。他们居家时孝顺父母,教子有方,团结家族,友善乡党;为官则廉洁奉公,耿介不阿,能力超群,造福一方。宋代汾阳王嗣宗“居家能睦宗族,著遗训,戒子孙勿得析居”,居官则“转运多劳,有称职之誉,谋猷茂著,见匡国之才。”①明代汾阳田耔“居官鲠直,一介不取”,在家“事亲孝养诚至”。①明代平遥李颖、李颐、任义、任良才等诸贤,都是“孝思纯笃”,“孝闻乡间”的孝子。①明代介休石瓒“刚毅笃学,慈孝性成”,任河南罗山县令时,“清廉抚民”,当地百姓为其立生祠,巡抚尚维特表其坊“光生冀北,名著汝南”,提学杨胤贤题匾云“忠臣第”。①汾州乡贤,文者为谦谦君子,武者则冠勇三军。北宋汾州名将狄青“善骑射,少好将帅之略”,官至枢密使,是北宋少有的名将。明代平遥乡贤温恭“骁勇刚毅”,任征西大元帅。同县霍韬“义勇刚毅”,拜总兵。
3.家庭背景
汾州乡贤中有不少父子同列乡贤祠,共入乡贤传的例子,家风传承可见一斑。元代汾阳人杜丰及其二子杜思明、杜思敬三人同入乡贤传,皆拜高官。同县张益及其子张大猷勤学好读书,均举进士,正祀考赞其“家传科第,世业师儒。”①明代汾阳人董龄登进士,选庶吉士,后任职地方,“有廉能声”,其子文奎“由乡举知玉田县事,有父风。”①平遥任良才、任良弼为亲兄弟,良才举成化进士,忠孝双全;良弼为弘治进士,不阿权贵,清廉有声。南北朝时期介休的宋氏家族自宋隐之后6人皆入乡贤传,宋隐兼入汾州府与介休县两级乡贤祠。介休文彦博官至宰相,教子有方,“公八子皆历官要,……皆荣及三代。”①金代永宁州吴氏家族家学深厚,吴永广藏万卷书,子吴希尹力学,大定间登进士第,孙吴子章亦举进士,为翰林学士,三人皆入乡贤传,希尹入祀永宁州乡贤祠。
4.民众口碑
汾州乡贤为汾州百姓尊敬、爱戴,地方所推重,不少人还进入正史之中,为史家所称道。如汾阳柳诚,“乡人称为学士”。①汾阳田耔,“乡邦推重,为立忠孝祠,与辛彦博并祀之”。①平遥李颐“立志诚笃,孝闻乡闾”。①宁乡王友贤“万历三十二年入祀,……居乡若处子恂恂如也,疾言怒色,终身不见,乡人大服其伟度。”①同县庞辅“成化十四年仕,……退居林下,力持清约,乡评重之。”①陈谟“万历二十年入祀,敦厚清简,择地而蹈,……历官五任,囊无长物,月旦高之。”①这些汾州乡贤的忠孝之举深受当地百姓推崇,地方官员也通过春秋致祭、嘉奖提倡,在本土弘扬这些乡贤的嘉言懿行,以教化百姓,改善风俗。中央政府则在编修官方史书的过程中,将其中一些乡贤收入其中,为其立传,让他们名留青史。如汾州乡贤中的狄青、文彦博、霍冀等诸多乡贤得入《宋史》《明史》等正史之列,其芳名懿德,昭煜千秋。
三、乡贤文化的形成机制与影响特征
乡贤群体是乡贤文化的生产者,这些乡贤品德高尚,能力超群,造福一方,为官方所重,受民间信赖,成为官方与民间沟通的重要纽带,政府政策需要他们的影响力深入到基层,民众意见需要他们的关系网传递到上层。乡贤文化在政府主导、乡贤参与、民众互动中形成发展并发挥作用,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中,乡贤文化逐步形成并以乡贤濡化圈、濡化网的形式发挥作用。
(一)乡贤文化的形成机制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26)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人民论坛》2020年第3期。乡土社会就是这个基层,而乡贤在协调国家与民间的关系方面扮演着桥梁角色。乡贤与乡土社会的联系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生前亲自参与乡土社会治理,这是乡贤文化形成的第一阶段;二是身后成为官方社会治理的榜样,这是乡贤文化形成的第二阶段。乡贤参与乡土社会的方式从生前到身后,从直接到间接,这使传统伦理道德旗帜的挥旗者实现了从乡贤本人到地方官员的转移。乡贤也从具体的人转化为了抽象的精神符号,成为地方的文化记忆,乡贤文化也得以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迈进,最终确立下来并能在地域上扩散,在代际上传承。
1.第一阶段:乡贤贡献与乡土社会
乡贤文化的第一阶段离不开乡贤直接参与乡土社会的治理。乡贤在地方文化传承方面的贡献最突出。不少汾州乡贤积极参与汾州地方文化建设,主要通过撰文著述、开塾讲学等方式传承发展地域文化。地方名胜古迹的修建,离不开他们的撰文;地方志的修撰,他们是作序者与编修者。如石州乡贤张珩是明正德间进士,官居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他关心乡里,《汾州府志·艺文志》留下了他的《明州倅陶公传》《宁乡县增修城池记》等大量有关家乡的文章,对汾州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军事地理等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27)王道一:《汾州府志》卷十四《艺文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0-262页。孝义乡贤张冕、赵讷二人致仕回乡后,均投身于地方文化的整理传播中,先后编撰了两部《孝义县志》,赵讷对孝义文化研究最深,有各类著述70余种,“性嗜读书”“刻语录诗文三十卷,杂著纂次七十八种,郡县续志其一也。”(28)王道一:《汾州府志》卷十一《人物类·乡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2、215页。一些汾州乡贤因丁忧或致仕回到家乡,开塾讲学成为他们教化乡里的最直接表现。明代宁乡乡贤杨昇“有学有行,虽退居林下,教授生徒,成才接踵。”②同县高崧“谨饬正大,非礼不蹈,迪多士,桃李竞爽于门”,②他们在家乡人才培养,风气改善方面居功至伟。此外,这些乡贤及其家族在地方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婚丧嫁娶的礼仪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方民众,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准则,时至今日,不少乡贤家乡还有“某府家宴”“某家菜”的饮食文化流传。
乡贤在参与社会救济、调解社会矛盾、主持公共设施修建等领域贡献也很突出。“明末名士大部分在罢官或退隐期间在故乡推动地方慈善活动,”(29)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1页。如明末宁乡乡贤陈谟、王友贤等在家乡出现饥荒时,积极奔走,救济乡民。明孝义乡贤霍冀官居兵部尚书,当家人因宅基问题与邻人发生纠纷时,霍冀千里传书劝说家人,晓以利害,说“让他三尺又何妨”,最终留下了“仁义巷”的佳话。明孝义乡贤梁明翰致仕回乡后,深感乡民受疾病之苦,出资并主持修建了三皇庙(包括药王殿),祈求神灵免除百姓病痛。这些都是乡贤直接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表现,在此过程中民众对乡贤的敬重逐渐积累,乡贤文化亦初步形成。
2.第二阶段:官员推动与乡土治理
乡贤文化的第二阶段与地方官员的推动密切相关。《明太祖实录》载州县官负有:“宣扬风化,抚安其民,均赋役,恤穷困”等职责。(30)《明太祖实录》卷161·太祖洪武十七年四月壬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实录》校勘本。《明太宗实录》重申朱元璋时地方官员的《到任须知》,要求地方官劝课农桑、劝勉学校、诚敬祭祀、旌表孝义。(31)《明太宗实录》卷194·太宗永乐十五年十一月壬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实录》校勘本。重视表彰乡贤本身就是地方官的职责所在,这些乡贤的高风亮节、义举雅行被政府认可,被允许列入乡贤祠,享受民间祭祀。乡贤的文化遗产被官方充分利用,成为地方官员教化民众,进行社会治理的法宝。政府认可引导民间认可,政府对乡贤行为的认可并对其高德善举进行宣扬,让百姓认识到这种行为的正义性,向这些乡贤们学习,才能够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从而向上向善,得以修身,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利国利民。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乡贤在民间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乡贤文化最终形成并随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丰富。
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普及教育让人民得到教化,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统治角度来看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通过扶植以乡贤群体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提倡乡贤文化,政府不仅可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而且还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此过程中政府、乡贤、百姓实现了多赢。对区域影响巨大的乡贤群体是联系上层统治者和下层老百姓的重要纽带,政府对他们行为的表彰,不仅使这些乡贤群体得以光前裕后,实现不朽于世间的人生理想,更向民众传递了以他们为榜样,努力修身便可获得社会认可,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信号,劝导百姓向上向善,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即巩固其自身统治根基。在乡贤个人感召示范与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乡贤文化最终形成。这些乡贤成为地方的文化符号,关于他们的嘉言懿行、忠孝之举乃至趣闻轶事都是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形成的乡贤文化在传承中不断丰富。
(二)乡贤文化的影响特征:一圈一网
1.一圈一网的形成机制
乡贤文化的累代影响是以文化濡化的形式进行的,濡化过程中形成了乡贤濡化圈,进而构成了复杂的乡贤濡化网,这是乡贤文化影响特征的重要体现(32)本文的乡贤濡化是指乡贤在地方文化累代传承中的一种文化作用机制,它既包括空间的扩散,也包括时间的延续,分为乡贤濡化圈和乡贤濡化网两个层级,与文化濡化密切相关。文化濡化这一概念(enculturation)最早见于美国人类学家浴赫斯科维茨(M. J. Hoskovits)于1948年出版的《人及其工作》一书中。此后的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历史学等领域的诸多学者都受其影响。文化濡化强调文化的代际传承。。乡贤濡化圈是以乡贤本人为圆心,以该乡贤影响范围的空间距离为半径的圈层结构。这个圈层结构由核心区(县级政区)、次核心区(统县政区)、边缘区(高级政区)、辐射区(全国)组成。一个县域内以不同乡贤为核心形成辐射范围不同的乡贤濡化圈。以明代汾州乡贤数量最多的介休县为例,就有介子推濡化圈、郭泰濡化圈、文彦博濡化圈、宋隐濡化圈、张翼濡化圈等27个乡贤濡化圈,这些濡化圈影响范围各异,彼此相交,互为补充,进而构成了复杂的乡贤濡化网,它们与乡土社会中的其他机制、制度产生共振,共同在乡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便是乡贤濡化圈与濡化网的形成机制。在一圈一网中,乡贤文化以群众自发的方式或政府推动的方式在乡土社会中累代传承。

图2 乡贤濡化圈与乡贤濡化网示意图
2.一圈一网的地域影响
乡贤在核心区(即该乡贤老家)影响最大,其形成的乡贤文化作用最强,持续时间最久。核心区里的乡贤文化在该乡贤在世时已形成,其子孙及家族成员通过祖先祭祀、家风家训传承等途径传承乡贤文化,并在村镇内部乃至相邻村镇发扬光大。如明代汾阳人田耔“居官鲠直,一介不取”,在家“事亲孝养诚至”,在其孝行感染下,族人“多孝顺者”,当地乡党也深受感动,为其设立忠孝祠。(33)王道一:《汾州府志》卷十一《人物类·乡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1-202页。灵石静升镇王氏家族,以“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病”等十四条家训传家,绵延500年,在静升镇及灵石县影响最大,是当地乃至山西的名门望族,灵石百姓以王家为标杆,尤其是在教育方面,希望自己的家族也可以像王家一样人丁兴旺、人才辈出。
乡贤在核心区以外各个圈层影响力的形成,除自然扩展(包括口碑传播,家族成员、乡里熟人等的传播)外,还与政府的倡导密切相关,旌表是地方官治理地方的重要手段,(34)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0页。政府的介入使乡贤文化能历代相传,也极大地推动了其在地域上的扩展。次核心区对应府州一级的统县政区,府州官员的提倡可使乡贤入祀府州乡贤祠,位列府州地方志,其影响力也从乡贤原籍所在县扩展到了同属一个统县政区的其他各县,从而在政府的引导下作为地方的模范参与到地方治理中去,享受后世乡人绵延不绝的香火。汾州府下辖各州县乡贤原本的影响范围仅在本县或者扩展到邻县,但随着其中一些乡贤入祀府级乡贤祠,成为《汾州府志》的记述对象后,这些乡贤的影响也相应扩展到了汾州府治所在的府城及附郭的汾阳县,又从此地向汾州府下辖的其他各县传播开来。如入祀汾州府乡贤祠的乡贤分别来自汾州府下辖的汾阳县、介休县、永宁州等多个州县,其影响随着官方推动而扩展到汾州府下辖的其他各县。
乡贤文化对边缘区、辐射区产生影响的模式也类似于次核心区,但离核心区越远,该乡贤的影响力越弱。当然,因乡贤的家境出身、官职品级、名声大小、政府支持力度等因素的不同,其辐射范围也不尽相同。以不同乡贤为核心构成的乡贤濡化圈形成的交集便是诸多乡贤共同的作用范围,这些区域的民风会更加淳朴。如介休乡贤介子推同时也是邻县灵石祭祀的乡贤,两个乡贤濡化圈的交集在绵山附近,这里是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民风淳朴,寒食风俗至今流传。乡贤濡化圈和濡化网有着不同的范围,就汾州府而言,可分为县域乡贤濡化圈、濡化网与府域乡贤濡化圈、濡化网,而一地不同的乡贤濡化圈共同构成了该地乡贤濡化网。汾州府下辖的永宁州、汾阳、介休、平遥、灵石、宁乡等各州县的乡贤濡化圈数量不同,共同组成汾州府乡贤濡化圈,这些乡贤濡化圈如同蜘蛛网一般相互缠绕,共同构成汾州府乡贤濡化网,错综复杂的乡贤濡化网为地方人才培养、文化事业发展、民风民俗改良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四、结语
明代汾州乡贤是联系政府与民间的重要纽带,也是乡贤文化承载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乡贤通过文化濡化这一机制参与地方治理,所形成的乡贤濡化圈、乡贤濡化网促进了乡土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乡贤文化对明清时期的乡土社会影响深远。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剧烈变革,乡贤在民间慢慢失语,乡贤文化日渐衰落,但乡贤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乡贤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乡贤及乡贤文化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不容忽视。当前,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35)吴心欲:《基本本体性逻辑的乡村振兴战略内涵辨识》,《江汉学术》2018年第3期。振兴乡村应从乡贤文化中探寻乡村治理的智慧经验与合理因子,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借鉴古代乡贤的忠诚、孝义、仁爱、亲民等优秀品格及良好的家风,培育社会主义“新乡贤”,树立新榜样,发展新文化。与此同时,还应深入挖掘古代乡贤留下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乡贤故事,传承乡贤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实现新时代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