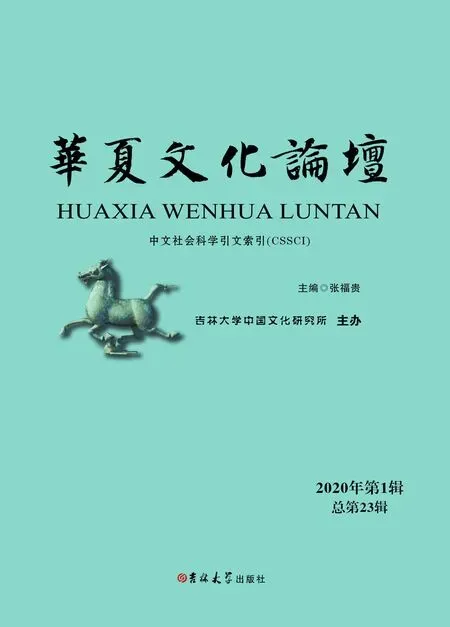异文、通假与经典化
——以毛诗《关雎》“芼”安大简作“教”为例
华学诚
大家知道,“诗经”这个概念是到汉代才有的,秦汉之前叫“诗”或者“诗三百”等,安大简测定为战国早中期,所以称名“诗经”并不是很合适。
安大简《诗经》有58首,我们以《关雎》的一个字为例来谈谈相关问题。诸如如何正确对待异文,怎么去使用通假,如何认识古书的经典化,等等。今天想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来谈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它们涉及对出土文献的认识,对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包括文献的二次利用。出土文献的初次整理与研究如果出现偏差,就会误导利用这些材料所进行的研究,就会给后续研究带来新问题。
《诗·周南·关雎》毛诗第三章:“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安大简《诗》“芼”作“教”。整理者注释说:“上古音‘教’属见纽宵部,‘芼’属明纽宵部。二字韵部相同,声纽有关,当为通假关系。毛传:‘芼,择也。’”安大简整理者“教”通“芼”的说法,在训诂上缺乏依据,在先秦找不到用例,在语音上也有窒碍。
先看看训诂材料。《说文·攴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释名·释言语》:“教,效也,下所法效也。”《广韵》平声《肴韵》“古肴切”,释曰“效也”;去声《效韵》“古孝切”,释曰“教训也,又法也、语也。《元命包》云:‘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谓之教,教之为言傚也。’”《集韵》平声《爻韵》“居肴切”,释曰“令也”;去声《效韵》“居效切”,异体字有“学”等,引《说文》为释。从这些古辞书提供的训释材料可见,教化、效法、教育、传授、使令等是“教”的本义和主要引申义。“芼”的本义是指草铺地蔓延,《说文·艸部》:“芼,艸覆蔓。”毛诗的底本应该是很早的,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尔雅·释言》就已经有了“芼,搴也”这一训释,郭注明确解释说:“谓拔取菜。”《尔雅》和郭注都是以《诗》“左右芼之”这一句作为依据的,毛传“芼,择也”则对“搴”这一动作义作了进一步概括,以使之更切合自己所理解的《诗》意。可见,“教”和“芼”在意义上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既没有发现“教”可训“择”的任何故训资料,也没有见到“教”与“芼”相通的古注辞书依据。
再看看语言事实。先秦文献中,“教”字的用例非常多,但并没有一条是作为“芼”的通假字来使用的。比如《左传》,书中“教”的用例不是动词就是名词,其意义基本上是在前文所引故训范围内。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中,“教训”“教诲”作为双音词单列词条,“教”作为单音词列了两个义项,一是“教育,教训”,二是“指教,教导”,没有其他解释。例如《左传·隐公元年》:“称郑伯,讥失教也。”《左传·隐公三年》:“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也。”《左传·桓公六年》:“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毛诗里面,“教”的全部用例只有7条,也没有一例通“芼”。例如《小雅·小宛》:“教诲尔子,式榖似之。”《小雅·车舝》:“辰彼硕女,令德来教。”《小雅·绵蛮》:“饮之食之,教之诲之。”
最后看看语音。一般来说,通假关系的确定并不能单纯依据语音相同或相近这一条,换句话说,语音相同或相近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以通假关系的确定还需要故训资料、文献用例等方面的证据。如上所说,在故训资料和文献语言方面,都没有材料为“教”通“芼”的说法提供佐证。即使单纯从语音上来看,整理者认为“教”通“芼”也是有问题的。“教”和“芼”的上古韵部虽有一二等之别,但同属宵部,与下文的“乐”构成宵、药合韵,也就是说,叠韵是没有问题的。但声纽则颇为相隔:“教”是见纽,属牙音清音;“芼”是明纽,属唇音鼻音。两个声纽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差别很大。“教”和“芼”连邻纽也算不上,整理者说二者“声纽有关”,既无论据,也无论证,让读者很难理解如何“有关”。整理者把差别如此大的两个声纽看成“有关”,也许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以往的研究已经有人指出中古晓母字与明母字在上古有联系。其实这个研究结论目前只在特定的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并不能简单类推,比如中古晓母字与帮滂並诸母就不存在与明母字同样的联系。反之,也不能据此作如下推理:既然中古晓母字与明母字在上古有联系,那么中古见溪群疑诸母与明母字在上古也应该有联系;更不能不加论证就理所当然地认定它们“有关”。
有了上面这些理由,我们认为安大简说“芼”和“教”是通假就难以成立。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了异文,这个异文怎么解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诗”的经典化。
众所周知,《诗》很早就广泛流传,上古文献中用《诗》是很常见的现象,单是一部《左传》,用《诗》就有277条,其中赋诗68条,引诗181条。《诗》曾经是孔子所用的教材,并经过孔子整理,这一整理是《诗》的学者经典化。
安大简被测定为战国早中期,那个时期《诗》在实际流传中的抄写本应该不少,孔子的众多门人和再传弟子都应该有经过孔子整理的抄写本,安大简《诗》是不是属于孔子整理本的传本并不清楚,当然也不能排除。包括孔子整理本在内的各种抄写本,在战国时期流布地区很广,传抄代代不辍,比如齐鲁一带就定然有不少抄写本,说不定在今后的某一天我们又能发现一个新的简本。既然古书那个时期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的传布方式主要是传抄,而且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那么传抄过程中就既可能有抄错的情况,也可能有凭意改动的情况。传抄出现的错讹是不自觉的,而凭意改动则可以视为《诗》的民间俗本化。
无论是传抄错讹,还是凭意改动,结果就是,先秦古书包括汉代来源不同的古书,文句歧异、异文较多,《帛书老子》甲乙本与传世《老子》之间的歧异就是显著的例子,阜阳汉简《诗》不属于齐鲁韩毛四家诗的任何一家也是明证。秦始皇帝焚书坑儒之后,《诗》《书》等禁书的传播方式被迫改变为口耳相传,后来据此记录的书又增加了更多歧异。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诗》则有齐鲁韩三家立于学官,稍微晚出的古文诗学毛诗则私学相授并于东汉盛行。四家诗和其他“经”学一样,在汉武帝之后经历了一个“官”“学”经典化的过程,《诗》的传本经典化定型于毛、郑之手,此后就是版本经典化的过程了。
正因为先秦古书包括《诗》,都有上述复杂的流传过程和经典化过程,所以今天看到的战国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存在大量的文句歧异和异文,毫不奇怪,这些文句歧异和异文,有些是正误性质,有些就未必如此了。譬如“教”,这是安大简《诗》的用字,而“芼”则是毛诗所据古本的用字。如果这两个字都是代表该字所记录的词,也就是说,这两个字的不同,并不是一个词的用字不同,而是不同古本的用词不同,那么我们千方百计用“通假”来沟通,就会距离本来面貌越来越远。整理者为什么会坚持用通假来沟通安大简《诗》与毛诗呢?笔者猜测,没有顾及如上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可能是一方面,更主要的可能还是整理者有一个预设:毛诗的用字、用词是正确的,与毛诗不同的安大简《诗》异文应该是通假,因为简帛中存在的通假现象比传世文献要多得多。
现在再回到《关雎》这首诗本身。这首诗不管是分三章还是分五章,其内容都可以分为四层。第一层起兴之后说“君子好逑”就是“窈窕淑女”,接下来三层抒写了“君子”思慕追求“淑女”的过程和结果。如果我们把安大简《诗》和毛诗的文字不同,首先看成是本字本词,也就是说,不把“教”与“芼”视为通假,那么,诗意的呈现会有所不同。这首诗后面三层所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以下,是说“君子”求之而不得所经历的思念折磨;“参差荇菜,左右采之”以下,是说“君子”将如何“有/友”之;“参差荇菜,左右教/芼之”以下,是说“君子”将如何“乐”之。
“流”和“芼”的本义都不训“采”,但《毛传》曰“流,求也”“芼,择也”,这是把“流”“芼”视为“采”的同义词,这当然是毛诗所理解的诗意。朱熹《诗集传》说:“顺水之流而取之也。”陈奂《毛诗传疏》说:“流本不训求,而训诂云耳者,流读与求同,其字作流,其意为求,此古人假借之法也。”朱熹、陈奂对毛诗的理解是准确的,毛诗把“流”“采”“芼”的意义训为求取、采择、选择,那么这三层的意思就形成了一个同义平面,达到循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效果。
安大简《诗》与毛诗“流、采、芼”相同位置上出现的三个字是“流、采、教”,按照毛诗的诗意,“教”当然无法理解了,所以整理者就讲通假。如果不把安大简《诗》与汉代经典化之后的毛诗理解成同一个传本,那么具体字词就可以不受毛诗的束缚。荇菜属于浅水性植物,叶子漂浮于水面而根生于水底淤泥中。参差不齐的荇菜,叶子会随流左右漂荡,以此设喻,所以《关雎》说“左右×之”。这个“×”,安大简《诗》分别为“流”“采”“教”,结合下面对应位置的“求”“有”“乐”并以其自身的意义来解读,是可以讲通的,这样去解读安大简《诗》也许才能真正接近这个本子所要表达的《诗》意,即与毛诗不尽一致的《诗》意。
明白了《诗》的经典化过程,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这个“教”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了。
《说文》所云“上所施下所效也”,即“教化”之意。上古常常特指乐教。《礼记·乐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郑玄注:“教,谓乐也。”《礼记》原文的大意是:天地的道理是这样的,寒暑不合时令就会发生疾病,风雨无法调节就会产生饥荒。乐教,如同寒暑一样,不适时宜就会危害时世;礼制,如同风雨一样,不加调节就会劳而无功。郑玄云“谓乐也”,这是以狭义的乐教来解释广义的教化,也就是说,在这一句里“教”特指“乐教”。《礼记·乐记》:“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孔颖达疏:“谓宽广乐之义理,以成就其政教之事也。”“广乐以成其教”说的也是“乐教”。
“乐教”有很古老而悠久的历史,古圣贤都非常重视。下面这些都是关于乐教的重要记载:《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礼记·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孔子家语·问玉》:“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郭店楚简《语丛一》:“乐,或生或教者也。”又《尊德义》:“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得争将。”又《性自命出上》:“凡古乐动心,益乐动恉,皆教其人者也。”孔子看待“乐教”的作用和意义所站的高度更是无以复加。《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今天一般把《关雎》看成普通的抒情诗,认为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男子对一位女子的思慕与追求。这一解读还原了原生民歌本来的面目,但未必符合先秦两汉文献经典化过程中对这首诗的理解。换句话说,对先秦两汉《诗》的各种传本做文献整理和解读,应该置于诗教、乐教等语境之下,应该充分重视这种语境对《诗》经典化的深刻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先秦两汉上层人物眼中的《诗》,才能解释《左传》《国语》等古史记载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用《诗》的现象,才能理解战国诸子在论著中喜欢引《诗》的现象。
“诗言志”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诗论,而《毛诗序》无疑是中国最早的系统诗论,所以理解先秦两汉《诗》的经典化,《毛诗序》自然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参考文献。《毛诗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这句的主要意思是说,《关雎》这首诗表彰的是后妃美德,目的是教化天下而正夫妇之道。又曰:“《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这句话的大意如下:《关雎》赞美得到贤淑的女子来匹配给君子,忧虑如何进举贤良之人而非贪恋女色;怜爱静美娴雅的美女,思念贤德良善的人才,却没有伤风败俗的邪念。这就是《关雎》的要义。《毛诗序》这段话是在揭示《关雎》的主题,而这一观点显然本自孔子。《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然孔子与毛诗对《关雎》主题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对于春秋以来《诗》的各种传本进行解读时就不能不重视这一观点。
安大简《诗》有关的几句摘录如下:“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有之。参差荇菜,左右教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结合上文的论述,我们这样来理解安大简《诗》这几句:长短不齐的荇菜(如同美女)啊,忽左忽右漂流之;美丽善良的女子啊,(君子)睁眼闭眼都想着她。长短不齐的荇菜(如同美女)啊,从左从右采摘之;美丽善良的女子啊,(君子)弹琴鼓瑟拥有她。长短不齐的荇菜(如同美女)啊,在左在右教化之;美丽善良的女子啊,(君子)敲钟击鼓乐教她。上述理解,是基于如下认识。“参差荇菜”是比喻,故可以括注“如同美女”来理解。第一层表示美丽贤淑的女子像荇菜一样漂流不定,故而要“求”;“流”用本字解,不用毛传之“求”训。第二层表示美丽贤淑的女子像荇菜一样可以采摘,故而说“有”;“有”用本字解,不视为“友”的通假,毛诗作“友”是后来经典化的结果。第三层表示美丽贤淑的女子可以教化,故而能够进行乐教;“教”用本字解,“乐”应是“乐教”之“乐”而非“快乐”之“乐”。这三层从“流之”而“求之”,到“采之”而“有之”,再到“教之”而“乐之”,层层递进,尤其是最后一层,画龙点睛,直白表达“后妃之德”说。
荇菜有“左右流之”的特点,荇菜也能“左右采之”,说荇菜可以“左右教之”并不合事理。笔者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几位与我有交流的专家也重点提到了这一疑虑。笔者所以作如此解,是基于如下两点考虑:第一,“教”与下文乐教之“乐”是完全对应的,这是诗旨的体现,直言乐教、不假修辞是安大简《诗》作为早期民间俗本的特征;第二,表达了诗旨而没有顾及“教”与荇菜的特点,这种顾此失彼的瑕疵正是战国早中期民间俗本所以为俗本的原因之一,不必为之“完善”。毛诗用“芼”并训为“择”,既有对荇菜择取所长、舍弃所短之意,又有比喻教化使人去俗就雅之功,在表达上比安大简《诗》胜出一筹,由此也能让今人看到了毛诗经典化过程的一斑。
总之,依照“教”本字作解,能客观反映出安大简《诗》和毛诗的不同,从而反映出处于经典化早期的《诗》与完成经典化的毛诗之间的不同。安大简整理如能够全面客观地呈现并解释这些不同,而不是一味地将简本往经典化之后的毛诗上附会,不仅可供研究历时条件下文献用字的不同、语言修辞的推敲,而且可供研究先秦至汉代经典化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如果说汉代之前的经典化是文献的经典化,那么汉代之后四家诗的不同则属于版本的经典化。文献的经典化与版本的经典化,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是另外一个论题,这里就不再谈了。
安大简《诗》“教”“乐”作如上解释,还有一些旁证。
“钟鼓乐之”之“乐”,《毛传》《郑笺》都解释为快乐之“乐”;后人沿用之,以为使动用法,意谓使快乐。这样解释符合毛诗的上下文语境,但并不适合安大简《诗》。安大简《诗》的“乐”与上文“教”对应,我们理解为“乐教”之“乐”。陆德明《释文》说“音洛又音岳”,陆氏又音就是“乐教”之“乐”的音。《韩诗外传》有两则材料能够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佐证,其中一则是《韩诗外传》卷一第十六章:古者天子左五钟,右五钟。将出,则撞黄钟,而右五钟皆应之。马鸣中律,驾者有文,御者有数。立则磬折,拱则抱鼓,行步中规,折旋中矩。然后太师奏升车之乐,告出也。入则撞蕤宾,而左五钟皆应之,以治容貌。容貌得则颜色齐,颜色齐则肌肤安。蕤宾有声,鹄震马鸣,及倮介之虫,无不延颈以听。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然后少师奏升堂之乐,即席告入也。此言音乐相和,物类相感,同声相应之义也。《诗》云:“钟鼓乐之。”此之谓也。
《关雎》四家诗异文,可以旁证安大简《诗》所属古本系统不同。四家诗《关雎》依次有如下异文:关关雎鸠/关关鴡鸠;在河之洲/在河之州;君子好逑/君子好仇;参差荇菜/槮差莕菜;辗转反侧/展转反侧;左右芼之/左右覒之;钟鼓乐之/鼓钟乐之。“钟鼓”与“鼓钟”,词序不同,没有文字、词汇的差异,不予讨论。其他各例可以看看如下材料。
鴡:《说文·鸟部》:“鴡,王鴡也。从鸟,且声。”毛氏《关雎》题下陆德明《释文》云:“依字,且旁隹……旁或作鸟。”《尔雅·释鸟》:“鴡鸠,王鴡。”陆德明《释文》:“鴡,本又作雎。”《玉篇·鸟部》:“鴡,亦作雎。”王筠《句读》:“鴡,毛诗作雎。雎鸠,王雎也。”据此,“鴡”“雎”异体字,《说文》无“雎”字,“雎”盖俗字。
洲:《说文》无“洲”字。《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曰州。”“州”字下引《诗》作“州”。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此毛氏古文也。加水旁作洲,乃今文俗体也。”李富孙《诗经异文释》:“州从重川,本州岛渚字,又为九州岛,已取水周绕其旁意,俗复加水旁以别于九州岛字,失其义矣。张氏弨曰:自唐天宝间以隶写六经,遂杂用俗改字,如州复加水……之类。”
逑:陆德明《释文》:“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郑云‘怨耦曰仇’。”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孔颖达正义云:‘《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今据郑君以‘怨耦’释‘仇’字,则《诗笺》本不作‘好逑’也。”李富孙《诗经异文释》:“据许氏,逑为正字;其作仇,或三家本相传如此。”
参:《说文·木部》“槮”字下引《诗》作“槮差荇菜”。参差,连绵词,或写作槮差(《说文·木部》)、或写作篸差(《说文·竹部》),许氏所见《诗》作“槮”,毛诗作“参”。
荇:陆德明《释文》:“荇,本亦作莕。”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尔雅·释草》:‘莕,接余。其叶苻。’《尔雅》是鲁诗之学,则作莕者,鲁诗异文也。”
辗:陆德明《释文》:“辗,本亦作展。”李富孙《诗经异文释》:“吕忱《字林》从车、展。《后汉书》注、《淮南□□》注、《楚辞·九叹》王逸注、《文选》注并引作‘展转’。案,古本皆当作展,《说文》云‘展转也’,今从车旁,则《字林》所加也。”
芼:陈乔枞《诗经四家诗异文考》:“顾野王《玉篇·见部》:‘诗曰左右覒之。覒,择也。覒,本亦作芼。’案,覒,毛诗作芼。”《说文·见部》:“覒,择也。从见,毛声。读若苗。”李富孙《诗经异文释》:“毛诗多假借,此当为‘覒’之借字,三家多从本字。”
从简单梳理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异文有些是四家诗所据传本的区别,也有些是毛诗经典化之后形成的异文,前者可以说是文献经典化过程中的异文,后者则是版本经典化过程中的异文。这些异文的形成虽然有阶段的不同,但有一个根本性质并无区别,即这些异文都是同一词的用字不同。那么,我们能否据此作出如下推论:四家诗虽然各有师承,用字有不同,但都源自一脉,而安大简《诗》与四家诗则不属于同一个传本系统。
总结
华老师这个题目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怎样认识异文,第二个是怎么来使用通假,第三个是怎么认识典籍在经典化过程中的用字变化。不同时代、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出土文献材料、传世文献材料的情形也千差万别。我们做历史语言文字研究,首先要把材料弄清楚,要有历史发展眼光,要讲究方法,否则我们的研究基础就不牢靠,我们的结论就可能是建立在沙滩上。华老师最近多年来一直着力推动文献语言学学科建设,本文就是文献语言学的一个精彩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