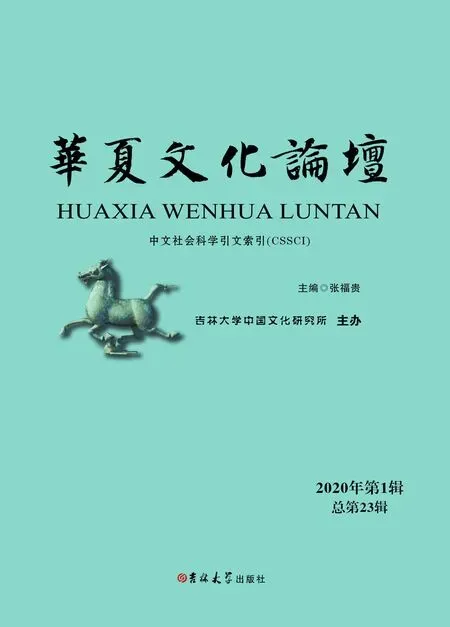论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体例
王海宾 孙赫男
【内容提要】《八朝名臣言行录》开创了以记录“名臣”言行事迹为中心的“言行录”体例。朱熹“有补世教”的编纂目的及审慎的纂史态度,促成了《八朝名臣言行录》别具一格的体例。该书收录北宋“名臣”104人,其以时系人,以人系事,提纲挈领,以叙人臣之迹,以寓“八朝”之史。该书的“体裁”源于正史列传,经朱熹改造后形成了新的史书体裁,每位“名臣”的传记由小传、正文、注文组成,体现了其不同于列传的编纂结构。《八朝名臣言行录》以“编纂”代“著述”,直录原文,自注出处,取材浩博,考证精当,其内容上具备“征实”和“善叙”两个特点,兼具故事性和教育性,易于接受和传播。
《八朝名臣言行录》是朱熹编纂的一部重要史书,该书取材审慎、考证精当,文献价值极高。今人郑骞、王德毅、裴汝诚、顾宏义、叶建华、李伟国诸先生对《八朝名臣言行录》进行了专门研究,为进一步探究该书奠定了基础。①参见郑骞:《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原本与删节本》//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宋史研究集》(第四辑),台湾编译馆,1969年,第1-16页;王德毅:《朱熹〈五朝及三朝名臣言行录〉的史料价值》//王德毅:《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鼎文书局,1972年,第65-70页;裴汝诚、顾宏义:《两种版本,不可偏废——郑骞先生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原本与删节本〉读后感》//朱杰人:《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2-323页;裴汝诚、顾宏义:《〈八朝名臣言行录〉琐考》,《宋史研究论丛》,2018年第23辑,第277-295页;叶建华:《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初探》,《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第25-30页;李伟国:《朱熹〈名臣言行录〉八百年历史公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第89-99页。诸位学者对该书的版本和文献价值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充分,然而有关该书编纂体例问题的研究略显滞后。《八朝名臣言行录》是“言行录”系列史书的开创之作,其在编纂“体裁”和“义例”方面多有创新,独具特色。本文试图对该书的编纂目的、体裁、义例及总体体例特征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以期充分认识该书的编纂特色。
一、《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目的
史书的编纂体例,一方面体现着篇章的组织结构和编写格式,一方面又体现着著者的编纂目的和思路。朱熹编纂《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目的与该书呈现的体例息息相关。该书序文中称:“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全,而又汩于虚浮怪诞之说,予常病之。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尚恨书籍不备,多所遗阙,嗣有所得,当续书之。”①[宋]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朱杰人等:《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页。观此段文字及朱熹全书可知其编纂该书有三个目的:
一是“有补于世教”。史书皆有“劝戒”之功,“古之史《尚书》《春秋》是也,二经体不同而意同……然《尚书》记治世之事,使圣贤之所为,传之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善之效,安得不说而行之,此劝之之道也……《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辩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②[宋]孙甫:《唐史论断·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68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43页。从《尚书》和《春秋》起,史书便承担着对世人“劝善戒恶”的社会教化功用,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正是应史书劝善之功用而生,正所谓“列传善善恶恶,而言行录善善之意长”。③[明]黄宗羲、陈乃乾:《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页。这一点完全符合朱熹的治史态度,即对史学价值的判断,他认为史学具有劝善惩恶价值,无论“著史”还是“读史”都要本着劝善惩恶这一目的进行。④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2000年,第69-104页。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辑录近世文集、笔记、杂史、别传等各类文献中所记名臣“嘉言懿行”汇为一书,以此教化世人,正是其历史观的体现。《四库提要》评价该书,称:“宋一代嘉言懿行略具于斯”。⑤[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7),中华书局,1965年,第520页。后世代有续、仿朱熹之作,如宋李幼武纂《皇朝名臣续录》、元苏天爵纂《元名臣事略》、明尹直纂《南宋名臣言行录》、清徐开任纂《明名臣言行录》等,历代编纂皆有此目的。明人张采指出:“言行录者,所以教人学为人也。夫为人莫大乎畜德,故受之以前言往行,使夫知所乡方,则可以与人道矣。”⑥[明]张采《〈宋名臣言行录〉题辞》//朱杰人等:《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79页。张采此言道明了古人作“言行录”的目的即是教化世人,使人们按照先贤的言行行事。因此,朱熹“有补于世教”之目的使其选择了以“名臣”言行之迹为写作对象,促成了“言行录”体裁的创立。
二是纠正史籍“虚浮怪诞”之病。朱熹倡导史官应秉笔直书,据实著史。汤勤福先生在研究朱熹史著编纂思想时称朱熹有良史之风范,对显贵不隐讳,不虚美,不受权贵操纵,不以自意取舍,反对著史附会谶纬迷信。⑦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2000年,第168-175页。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中即有很多体现其不徇私情的例子。如他记好友吕祖谦之先人吕夷简传,能“瑕瑜互见”。对此,《朱子语类》明确记载了朱熹的态度,《语类》云:“《涑水记闻》,吕家子弟力辨,以为非温公书。(原注:盖其中有记吕文靖公数事,如杀郭后等。)某尝见范太史之孙某说,亲收得温公手写稿本,安得为非温公书!某编《八朝言行录》,吕伯恭兄弟亦来辨。为子孙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从己,则不能也。”①[宋]黎靖德、王星贤:《朱子语类》(卷130),中华书局,1986年,第3104页。朱熹在此表示了对好友吕祖谦的同情,但仍坚持史实,不为私交而曲笔,这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良史风范。另外,朱熹极力反对附会迷信和以成败来论符瑞灾异的史著。他在解答学生疑惑时曾说:“如高帝(斩)蛇,也只是脱空。陈胜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为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为符瑞。”②[宋]黎靖德、王星贤:《朱子语类》(卷83),中华书局,1986年,第2151页。在当时神化皇权的社会背景下,朱熹能有如此见解,实属难能可贵。“秉笔直书,据实著史”在他的史著编纂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③关于朱熹史著编纂思想相关内容参见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第168-175页。在朱熹如此科学严谨的史籍编纂思想指导下,其在《八朝名臣言行录》辑录“嘉言懿行”过程中删剪了近世文集、小说等文献中的“虚浮怪诞”之说,这种严格考订材料、审慎纂史的态度成为后世著史的典范。
三是将“散出而无统”之文献聚为一书“以便记览”。朱熹深知修史之弊,他曾经撰写过《史馆修史例》,提出了很多关于如何修史的真知灼见。《朱子语类》中关于朱熹批评修史之弊的记载有很多,例如,他称:“今之史官,全无相统摄,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头在第一年,末梢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认分年去做,及至把来,全斗凑不著。”④[宋]黎靖德、王星贤:《朱子语类》(卷107),中华书局,1986年,第2665页。又指出:“近世修史之弊极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关,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杀处在二年,前所书者不知其尾,后所书者不知其头。有做一年未终,而忽迁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复修者。有立某人传,移文州郡索事实,而竟无至者。”⑤[宋]黎靖德、王星贤:《朱子语类》(卷107),中华书局,1986年,第2666页。朱熹所论正是造成文集及记事之书“散出而无统”的原因,因为史馆中按年分人去修史,致使一事首尾不相连接,常又因人事变迁而造成修史中断,终而导致文献“散出而无统”。于是朱熹辑录文集、碑志、家传、小说、别史、杂史200多种文献资料,聚为《八朝名臣言行录》一书“以便记览”。
源于“有补世教”,纠正史籍“虚浮怪诞”之病,“以便记览”之目的,朱熹编纂了《八朝名臣言行录》,以促成该书特殊体例的形成。
二、《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体裁
清代学者姚永朴指出:“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二曰例。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⑥[清]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史学研究法》,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此处“体”指的是体裁,“例”指的是义例,“体裁”与“义例”互为表里,缺一不可,不能相互混淆和替代。董恩林先生《历史编纂学论纲》一文指出不能将史书体裁同史籍分类法、史书性质与作用、文章体裁等混为一谈。所谓史书体裁,是指一部史书内容的基本结构形式,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而史评体、史论体、史考体等是就史书的文章体裁而言的,记言体、记事体等是就史书的文字特点而言的,典制体、方志体等是就史书内容而言的。史籍分类是多样的,可以按照史书体裁来分,也可以从其他方面分类,但史书体裁分类只能按照史书编纂结构来分类。①参见董恩林《历史编纂学论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9卷,第4期,第123-128页。这一论断对于我们认识《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体裁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八朝名臣言行录》共二十四卷,其中“五朝”部分十卷,收录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60人,其中穆修、种放、李之才、魏野、林逋附录于卷十之一《希夷陈先生》传之后。“三朝”部分十四卷,收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44人,“八朝”共收录“名臣”104人。
《八朝名臣言行录》以时系人,以人系事,提纲挈领,以叙人臣之迹,以寓“八朝”之史。该书以人物为中心,采取小传、正文、注文的结构形式。一般认为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起源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为纪传体史书,从体裁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的综合。本纪,记帝王;世家,记诸侯和贵族;列传,记各方面代表人物;书志,记典章制度;表,记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八朝名臣言行录》的体裁正是起源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列传体裁。有学者指出:“《太史公自序》谓《春秋》主乎作,故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主乎述,故一则曰论载名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再则曰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此开《名臣言行录》之先声,非为司空城旦书也。”②[清]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第221页。此语点明了“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的正史列传开“言行录”之先声。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以北宋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名臣”为写作中心,对列传体裁进行了改进,精心选择和编排史料,首创了“言行录”体,以发挥其社会教化功用。
明季黄宗羲说:“史之为体,有编年,有列传。言行录,固列传体也。列传善善恶恶,而言行录善善之意长,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洁当年,一言一行,足为衣冠准的者,无自而入焉,则比之列传为尤严也。”③[明]黄宗羲、陈乃乾:《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第317页。黄宗羲言明“言行录”属于列传之体,且侧重于善言善行的记录。他指出“言行录”出于列传,而别于列传的特点。《史记索隐》曰: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④[汉]司马迁:《史记》(卷61),中华书局,2009年,第2121页。从有清以来的评介和朱熹的编纂事实看,“言行录”与列传都以人物为中心载叙史事,其殊异之处在于,“言行录”专以汇聚名臣美言善行为其设传,或专取德备才具者置传,而汇为一书以褒善戒恶;列传则善恶兼载以劝善惩恶。“言行录”与列传皆为人物立传,“言行录”多汇数众为一帙,列传则附正史而不具备独立地位;“言行录”重辑录和自注,而列传重剪裁和整合。列传因史体所限,减省文献载录,势所必然;“言行录”援采富赡,正可补其体例之憾,自有其编纂形式上的优长。从编纂基本结构形式上来看,“言行录”每篇“传记”由小传、正文、注文三部分组成,而列传无“小传”部分,也很少注明史料来源。现代学者叶建华先生指出:“言行录竟成为一种特殊的列传史体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①叶建华:《朱熹〈宋八朝名臣言行录〉初探》,《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第28页。顾宏义先生也说:“观是书(《五朝名臣言行录》)体例,即将辑录相关史料分载于北宋前五朝五十五位名臣下,或为正文,或作注文,从而形成一特殊的史书体裁”。②顾宏义:《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未注出处之引书试析》//朱杰人、严文儒:《〈朱子全书〉与朱子学——2003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确如他们所认为的,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是一种在列传基础上改造的特殊史书体裁,从宋至清,续仿《言行录》的史书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言行录”体史书系列。
三、《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义例
义例,或称笔法或称类例。刘知几说:“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③[唐]刘知几、[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8页。足见“义例”在史书编纂过程中的重要性。“编纂史书,在结构—体裁确定之后,还需要就材料如何取舍、组织和表述等问题确定宗旨、原则和方法,这就是义例的内容。体裁是史书的基本框架,义例则是组织这一框架的方式方法。”④参见董恩林:《历史编纂学论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9卷,第4期,第123-128页。该书是一部与列传相关具有独特体裁的史书,其编纂“义例”亦呈现出与列传不同的特点。
第一,“直录原文,注明出处”是该书在编纂义例上最显著的地方。朱熹编纂《八朝名臣言行录》正文部分辑录史料1984条,28万余字,基本是直录原文不做改动。朱熹采用此种方法编纂史书,是受到了《春秋》编纂思想的影响,朱熹对《春秋》的认识,即体现了朱熹的史书编纂思想,如朱熹说:“《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又说,“(《春秋》)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尔。”⑤[宋]黎靖德、王星贤:《朱子语类》(卷83),中华书局,1986年,第2145页。朱熹此言表明孔子作《春秋》是“直载”鲁史,不加主观按断。朱熹编纂《八朝名臣言行录》也要“直载”史事,直录原文,让“史料”说话,这是朱熹该书的最大特点。他还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朱熹认为《春秋》并不是如先儒所说的有一套褒贬义例,只是取“史文”,据史事展现历史。朱熹将此种观念融入《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中,他在该书中几乎没有对历史人物、事件发表意见和评说,只是选择排列史料,记录“名臣之迹”,以此彰善戒恶,探究历史。此如明代杨以任所说:“(《八朝名臣言行录》)是书各胪列事实,亦春秋劝惩之旨”。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7),中华书局,1965年,第519页。此外,注明史料来源,是该书的另一显著特点。该书所辑录的1984条史料中,只有109条未注明史料来源,占比5.5%,所占比例很少。清代学者全祖望称:“但晦翁《宋名臣言行录》每所援据,必注其书之所出于下,此最是著述家一妙例。”②[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1),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07页。
第二,该书史料来源广博,且选择精当。全书征引文献种类繁多,包括家传、别传、语录、行状、碑志、文集、笔记、小说等各类文献。如《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寇准传》的正文部分所用史料共三十九条,约四千七百多字,来源于《遗事》《政要》《记闻》《莱公传》《谈丛》《东轩笔录》《闻见录》《掇遗》《名臣传》《倦游录》《归田录》《旌忠碑》《麈史》等文献。据统计,该书参考五种以上材料写成的传记有五十八篇,占55.7%;十种以上的有十五篇,占14.3%;其中最多的一篇参考书竟达十九种之多。③叶建华:《朱熹〈宋八朝名臣言行录〉初探》,《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第24页。叶建华先生指出:《八朝名臣言行录》不仅采摭浩博,而且取舍精审。对众多的材料,朱熹进行了筛选,然后采取增补、并存、考证、存疑、互见、解释等方法,加以编辑。④叶建华:《朱熹〈宋八朝名臣言行录〉初探》,《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第23-25页。此处所论的六种方法体现了朱熹对史料选择的精审之功。朱熹编纂该书时对一些错误的记载进行考证或存疑的例子有很多,如《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一《中书舍人曾公》辑录了一条来源于《温公日录》的记载,朱熹对其进行了考证,于此条史料后加按语云:“案:曾公父死南都,杜祁公为治其丧,时惟公在侧。今文集有谢杜公书可见也。又荆公作墓志,亦言至南京病卒,此云不奔丧者,温公传闻之误也。”⑤[宋]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朱杰人等:《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51页。朱熹此编选取材料的审慎态度以及所用材料的广博,给后世续仿之作树立了典范,成为了“言行录”类史书的一大特色。
第三,该书的材料组织和内容安排独特。
首先,该书每篇传记的正文之前都设有“小传”,主要介绍传主的生卒年、籍贯、任职情况、谥号等,小传一般约为二百字。不同于正文部分直接辑录原文,小传部分是朱熹依据各类文献总结撰写的,通过阅读小传即可清晰地了解传主的基本情况。
其次,该书在人物排列上亦有独到之处。该书所收录的人物并非全部为“名臣”,亦包括朝堂之外学术、教育等名流。因此该书的编纂顺序是优先排列治国理政方面影响力大的名臣,大致按北宋皇帝在位的先后,名臣则按照官阶大小为主进行排序。其后再排列一些次要名臣及草莽声名显赫者。例如:“五朝”部分,前八卷按照皇帝在位先后,名臣在朝官位大小排列了四十一位,有赵普等治国名臣,有曹彬等军事名臣等,从太祖朝至英宗朝共五朝。然后第九卷又从太宗朝开始排列,第九卷收录的九人中太宗朝二人,真宗朝二人,仁宗朝五人。第九卷和卷十所录的十九人多为文教方面的官员或山林隐士等,有以谏言知名的田锡,有以教学知名的胡瑗、孙甫、石介三先生,也有陈抟等方外隐士。此外,该书正文在内容排序上大致按照人物个人事迹的先后顺序排列。
再次,该书采取了附传的形式,记载与传主相关的一些重要人物,如《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陈抟传”后,即附录了穆修、种放、李之才、魏野、林逋五人的传记。另外,也有少部分传记中记载其兄弟的事迹材料,如《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之四《窦仪传》中记载其弟俨、侃、偁、僖的相关事迹。
最后,该书注文部分采取自注形式,基本上正文的每条材料后用小字作注文,主要是注明史料来源,有一小部分“注文”用于补充材料,或用来进一步解释说明等,也有少部分材料没有注明史料来源。简言之,“言行录”体例的史书,取材广泛,采用辑录原文的方式编纂,且注明史料来源,是以记录“名臣”嘉言懿行为中心的人物传记资料汇编。
四、该书呈现的总体体例特征
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以“编纂”代“著述”,对所用史料考证精当,同时具备“征实”和“善叙”两个特点。
《八朝名臣言行录》及其续仿之作在古代目录文献中位于史部的传记部分,与其他同在史部的传记类(家传、别传、名臣传、行状、碑志等)题材相比,其在编纂方法上更规范,在编纂观念上更显理性,更好地发挥了史学编纂著作的劝惩功用,其“征实”性较强,更为接近正史。清人赵翼指出:“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①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3),中华书局,1984年,第500-501页。赵翼此说之“言行录”为单传“言行录”,其与家传、别传、行状和碑志多为传主的子弟或亲友所撰写,其多以标榜、夸饰传主为能事,与朱熹“名臣言行录”据史实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如上文提到的朱熹在史料选择上注重存疑和考证,其在序文中也以“虚浮怪诞”为非,他在编纂《名臣言行录》选择史料时,即已排除了违背史实的材料,以审慎的态度来编纂史书。《八朝名臣言行录》以“编纂”代“著述”,实现史书的教化功能。此如宋陈傅良所说:“以臣所见,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②[宋]陈傅良:《止斋集》(卷2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50册,第723页。朱熹以特出的史才、史识,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八朝名臣言行录》在辑录家传、别传、名臣传、行状、碑志等各类庞杂的文献过程中去除了“虚浮怪诞”之说,但是却保留了传记“善叙”的特点。与正史列传相比,《八朝名臣言行录》叙事更为流畅,语言生动,可读性强,易于传播和流通,使其成为经典史著,对后世影响深远。朱熹编纂《言行录》既注重史实考辨,又注重审视史料,选用材料既注意语言又注意内容。他多选取记叙流丽,又包含国政大事、军事战争、民族团结,及个人修为等方面的史材入传,“昔晦庵朱文公修《宋名臣言行录》,凡其立朝事君之节,施政行事之宜,与夫议论答问之大关系无不具载”。③[明]郑岳纂、吴伯雄:《莆阳文献》(卷10),广陵书社出版社,2016年,第137页。观《言行录》所载名臣事迹,其兼具故事性和教育性的特点,适合大众读者,相比朱熹所纂其他理学书籍,易于传播和得到认可。宋人黄震说:“此录名臣之言行备焉,《近思录》诸儒之讲明详焉,彼此参验,环循阅习,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进其所行,晦庵之望后学者其庶乎?”①[宋]黄震《黄氏日钞》(卷5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708册,第344-345页。尽如朱熹所愿,《八朝名臣言行录》得到了广泛传播,与其他理学书并行流通并互为参考,为朱熹理学思想的广泛传播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言行录”不仅体例别具一格,内容上也可谓具有征文考献之资。《八朝名臣言行录》是一种特殊的列传体例,具有人物传记的属性,同时该书辑录原文的方法,保存了大量文献资料,亦具有史料汇编的属性。“言行录”辑录原文的编纂方法使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得以保留。经初步统计,《八朝名臣言行录》征引各类资料多达200余种,如:其所征引的单篇行状24篇,墓志铭43篇,神道碑24篇,征引语录类文献10种,单篇言行录6种,文集20余种,笔记近40种,杂史、杂传20余种,奏状、序、记等近20余篇,还有百余条未注明史料来源而待考者。这其中包括了一些早已亡佚的篇章,如《范属公蒙求》《宋圣掇遗》《王荆公日录》《巵史》《范祖禹家书》《王沂公言行录》《陈忠肃公遗事》等;也包括很多传至今日已非足本的书籍,如《后山谈丛》《王文正笔录》《温公琐语》《丁晋公谈录》《张乖崖语录》《倦游杂录》等。因此,《八朝名臣言行录》是辑佚与校勘北宋历史文献的一部重要书籍,今之学者在辑佚和校勘北宋杂史、别传、笔记时对朱熹该书应多加参考。朱熹这种编纂“言行录”的方法对后世人物传记的成书影响至深,如元代的《元名臣事略》、明代的《南宋名臣言行录》、清代的《明名臣言行录》等都具有史料汇编的性质。例如,《元朝名臣事略》全书引文达 123篇,这120余篇文字,就史料学来说,都是第一手资料,是《元史》编撰的重要史料来源。②姚景安:《苏天爵及其〈元朝名臣事略〉》,《文献》,1989年第3期,第101-111页。可见“言行录”体史书的文献价值。现代学者一致认为编纂“言行录”体史书意义非凡,有重要价值。如郑骞先生称:“(《八朝名臣言行录》)是一部很好的宋人传记资料,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③郑骞:《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原本与删节本》//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宋史研究集》(第四辑),台湾编译馆,1969年,第1页。
以上通过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目的、体裁、义例及其呈现的总体体例特征的探析,展示了该书的编纂特色及朱熹的治史之才。如有不当之处,祈请学界宿儒指正。
——艺术体裁的修辞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