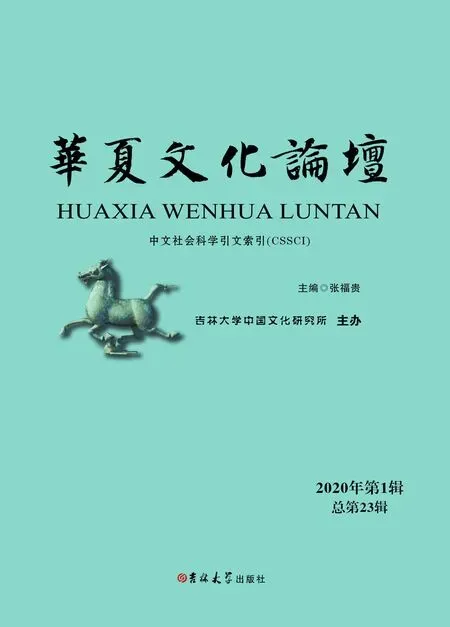汉代经学视域中的文艺创作论
郭明浩
【内容提要】天人学说是汉代感物论产生与发展的沃土,《乐记》首论艺术“感物”而生并已臻成熟,阐明了心性之动源于外物触发,导致乐的产生,影响乐的风格与基调,《乐动声仪》还专论诗人感物作诗。汉儒高扬“美刺”有显著的政治意图,但其创作论属性不容忽视,它不但揭橥了“美刺”系诗人的创作动机,还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诗》的创作情境。韩《诗》提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已明确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生命体验、生活经历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深刻影响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
在先秦诸子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论或为缺无,与之相关者多为与艺术创作有“同然之理”或为其奠定理论根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庄子》以梓庆削木为鐻、庖丁解牛、庄周梦蝶等谈心斋、坐忘、虚静、物化,虽然从根本上讲,《庄子》所言以体道为归宿,其宗旨并非论述文艺,但毫无疑问,其思维模式、言说方式与艺术创作确有同然之理,进而被视为中国美学史上艺术创作论的滥觞,特别是要求主体摆脱一切外在束缚,进入自由无碍、空静澄明、物我合一的心境,无疑为探索艺术创作规律提供了理论基础。严格来说,真正意义上对文艺创作规律进行初步探索的是汉代文士,其中,汉代经学叙述中更是不乏有关文艺创作的相关论述。
一、感物说
感物说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极富民族特色的文艺创作理论。感物美学认为,艺术创作的动因乃主体受外物触发、感召而产生情感、情绪的变化,这种变化作为一种心理能量以审美的方式疏泄并呈现出来,艺术创作由此发生。简言之,感物是艺术创作的动因与前提,故有研究者认为,“感物是艺术创造的门户”,“又是艺术创造的基础和材料”。①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267页。
感物说的哲学根基是天人合一,更确切地说是天人感应,天人感应又基于古老东方的万物有灵论,天人感应作为探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强调天人交感、主客融通。在政治权力的助推下,天人学说在汉代大行于世,甚而可以被视为汉代学术的主潮,尤其是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春秋繁露》中于此有相当深入的阐发,劳思光指出,“董仲舒所倡‘天人相应’之说,实为汉儒之‘宇宙中心思想’之总枢”②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6页。。总而言之,天人之学为感物美学(或称感应美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天然土壤,并由于其与经学的密切勾连,使感物说大量存在于汉代经学文本中。
《礼记·乐记》被视为汉代感物美学的代表,也或许是最早提出艺术创作“感物”说的文本,李健注意到,“《礼记·乐记》在讨论音乐问题时最早提出这一观念,指出音乐的产生是‘感于物而动’,也标志感物范畴正式形成”③李健:《天人合一:感物美学的哲学根基》,《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6期。。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感物说首见于此,却已经相当成熟、完善,这在中国美学范畴史甚至世界美学史上都不多见。
一方面,《乐记》提出,人性之本然为静,性之动源于外物触发,感物所生好恶需通过礼乐进行调控、限制。即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④[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14页。此处既言“静”为人之本性,但又敏锐地觉察到或警惕地意识到“感于外物而心遂动是性之所贪欲”⑤[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14页。,而“性之欲,即所谓情也”(朱熹)⑥[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84页。。如果说《乐记》作者未对本然之性进行善恶评判的话(朱熹赞其为“纯粹至善”),那么“感于物而动”(即朱熹所谓“情”)便有善恶之分,而且“恶”似乎居于主导,并最终导致“大乱”:
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⑦[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14页。
人受外物之诱而生情,情如果无法有效管控、节制便导致“灭天理”“穷人欲”的恶果,邪恶之心、作乱之事也由此滋生,社会秩序、道德伦理自然陷于混乱,因此,不受节制、规范的“好恶”最终必然酿成“大乱”。从表面上看,《乐记》乃言人性感物而动的“恶果”,实则是为“制礼作乐”张本,故下文即言“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⑧[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15页。孙希旦亦总结说:“盖人之好恶之失,乃大乱之所由起,此礼乐之所以不可不作也。”①[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985页。由此观之,《礼记》确已相当深入论及感物而动之情是“制礼作乐”的因由,其政治伦理意图十分明显,但无疑已经直接触及艺术创作发生的实质,这不仅是对先秦至汉代感物论的总结,也应被视为中国感物美学的里程碑。此后,类似“性本静,感物而动,情生焉”在中国文艺心理学史上并不鲜见,故钱锺书指出,“先秦以来的心理学一贯主张: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情’是平静遭到了骚扰,性‘不得其平’而为情”。②钱锺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2页。
另一方面,《乐记》还明确指出,乐产生于人心感物而动: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③[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10页。
孙希旦直言“此言乐之所由起也”,④[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976页。即作者心性受外物触发产生心理波动,主体将这种心绪通过复杂的心理活动形之于五声,五声交错杂比而为音,加之乐器吹奏、舞蹈搬演,最终形成乐,由此观之,《乐记》相当完整、深刻地呈现了乐的产生过程与机制,即“物→心→声→音→乐”。当然,在感物生乐的过程中,创作主体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换言之,人心之喜怒哀乐决定了“声”的风格、基调: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⑤[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11页。
乐系主体心理与外物交感的结晶,但人心多变无常,有所谓“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诸多形态,它们从根本上决定了“感物”之声有不同艺术风格与道德色彩。可见,在《乐记》作者看来,感物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心之善恶,声音之美的产生与呈现最终由感知主体决定,且主体的“情志最终走向了被约束、规范化或单调化的狭窄天地,扼制了情志的丰富多彩”⑥张峰屹:《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4页。。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感物美学体系中,“人心”的主导地位意味着中国文学必然走向重视抒情言志,因为所感之物只是触媒或载体,呈现主体精神世界才是艺术行为的最终目的,文学艺术从根本上便被视为一种主体情感意志的宣泄而非外在世界的再现,只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要求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必须“合乎礼义”。当然,《乐记》认定人心善恶决定“声”的风格色彩,根本目的还是为统治者干预“人心”提供依据,因为人心好恶决定声之善恶,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他们试图通过礼乐刑政钳制人心,使之向善,防奸止邪,即“先王慎所以感之者……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⑦[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11页。
《乐记》的物感说在纬书(尤其是《乐动声仪》)中得到了发展,赵在翰《乐纬叙录》有言,“一曰《动声仪》,言咏歌舞蹈,揄扬雍容,德盛物感也”①[清]赵在翰、钟肇鹏、萧文郁:《七纬》(附论语谶),中华书局,2012年,第747页。。《乐动声仪》除论及乐之化人如“物之动人”以外,还专门论述了诗人感物作诗之过程:
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②[清]赵在翰、钟肇鹏、萧文郁:《七纬》(附论语谶),中华书局,2012年,第340页。
此处未言明诗人所感对象,即省略了“物”,但却相当深刻地“指出了诗人由感而作的具体过程,即感→思→积→满→作”,虽然其说多沿袭《诗大序》,但却较之“提出的‘情动于中而形与言’之说更加具体明晰”③孙蓉蓉:《谶纬与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第97页。。同时,《乐动声仪》对诗人感物为诗过程的描摹较之《乐记》也更为深入、精微,更为重要的是,《乐动声仪》未对诗人所感的结晶进行道德伦理审查、判定,其所“歌咏”之作无疑较少政治钳制,自然也具有更高的创作论价值,魏晋南北朝的感物说无疑于此多有受益。此外,《诗纬·诗推度灾》还进一步讨论了“感物”的根基乃天人感应:
十月之交,气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
及其食也,君弱臣强,故天垂象以见征。辛者,正秋之王气。卯者,正春之臣位。日为君,辰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为臣,秉权而为政,故辛之言新,阴气盛而阳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④[清]赵在翰、钟肇鹏、萧文郁:《七纬》(附论语谶),中华书局,2012年,第239页。
依据今日的科学眼光看,日食是正常的天体运动现象,但在《诗推度灾》作者眼里,《小雅·十月之交》则是诗人将“反常”自然现象与现实政治联系的产物,这既涉及天(日食)与人世(君弱臣强)的感应关系,还关涉诗人有感于天之异与政之坏而作诗。
由此可见,虽然以《乐记》为代表的汉代感物说最终不免陷入政治牢笼、伦理审判,但毫无疑问,汉儒已经对艺术创作中的感物现象有相当程度的认知,这既是对前代感物理论(如《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的吸收与总结,也是真正为中国古代感物美学奠基,而《乐动声仪》中的感物论已明显摆脱政治束缚,直接推动魏晋南北朝感物论的兴盛,陆机、刘勰、锺嵘等正是沿着《乐记》《乐动声仪》开辟的理论路径踵事增华,并最终使中国感物美学蔚为大观。
二、美刺论
统治者的施政得失既关乎社会稳定、政权盛衰,又直接影响每个人的生活状况、生存境遇,故百姓对时政表现出明确的好恶顺理成章。如果人们的政治评价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便可简言之“美刺”,文学艺术家或在字里行间颂扬美政,甚而成为政治的吹鼓手;或以笔为武器指斥其流弊,甚而诅咒政权坍塌、更迭。《诗经》便对文学创作之“美刺”二端予以清晰的呈现,如《大雅·烝民》之“吉甫作诵,穆如清风”,《魏风·葛屦》“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诗人美刺指向显露无遗,由此观之,诗人作《诗》或实有其美刺之志。
与此同时,作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常被统治者或儒生披上道德伦理面纱,甚至成为“劝善惩恶”的工具,使后世论《诗》者(尤其是汉代经生)不得不竭力在《诗》中寻绎诗人美刺的蛛丝马迹,甚至不惜牺牲《诗》旨妄生美刺。当然,汉儒以美刺言《诗》旨可谓渊源有自,从某种程度上讲,孔子“诗可以观”意味着《诗》中寄寓善恶、得失,“诗可以群”暗指《诗》有“群居相切磋”之善言(“美”),“诗可以怨”更是隐含着一个基本前提,《诗》暗藏诗人的怨愤之情,否则便无怨刺上政之效果(“刺”)。《荀子·大略篇》更有“《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①[清]王先谦、沈啸寰、王星贤:《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511页。“疾今之政”便可简言之“刺”。汉儒承先秦旧说且变本加厉,将美刺说发展到完全成熟甚至极端,且使以“美刺”论《诗》成为汉儒释《诗》最为突出的特点,故陈廷焯直言“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②[清]陈廷焯、宋效永:《青溪集》,黄山书社,2004年,第38页。闻一多更是批评“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③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总之,“美刺”为汉代四家诗释《诗》的共同特征,也体现了其作为文学创作驱动力的面向。换言之,美刺说在汉代文学评论中兼具创作论与批评论双重属性。此处仅言其创作论属性。
鉴于文艺创作的美刺传统与前代解《诗》的美刺立场,汉儒多以“美刺”论诗人作《诗》之旨。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中,对诗人出于美刺目的作诗有相当关注,其《举贤良对策》提出“诗人美之而作”及“诗人疾而刺之”: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④[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第2499-2500页。
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⑤[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第2521页。
在董子看来,周宣王为圣明君主,他希望重振周代雄风,故承续先王之道,并攘外安内、补察时政、整顿朝纲、任用贤能、兴兵征伐,故有所谓“中兴”之称,其时诗人颂其功德、赞其勋绩。而在周王朝衰颓之时,臣民重利轻义、争讼并起、纲常大坏,诗人不满国家政治崩坏、纲常失节,故讥刺之音作,《小雅·节》(毛《诗》名《节南山》)便是其例,其说虽未言明讥刺对象,但明确指出《节》寄寓诗人对政治现状、社会风气的不满。当然,董仲舒言诗人美刺绝非是为了探索艺术创作规律,而是希冀统治者正其身,并以此教化百姓:
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①[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第2521页。
诗人所刺,当为警示统治者,因为上行下效,作为权力拥有者当规范言行,如此便可为万民效仿,进而有利于维护政治统治稳定。可见,董仲舒言美刺一则是希冀统治者规范言行,一则是为教化百姓、维护统治,这体现了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特性,即儒生与统治者间的斗争与调和,或称“学”与“术”的斗争与共谋。一方面,儒生希望传承先圣之道,并以之为武器成为帝王师,另一方面,道的实施必须依附、依赖于统治者,故不得不在理论上抬高统治者地位甚至进行神秘化,且以儒家之道教化万民,维护政治统治的稳定。反之,统治者既需要儒生维护政权,故授以官位爵禄,同时又要防止儒生势力过度膨胀以致失控,故必须予以限制、打压,最终结果是作为知识精英的儒生与政治统治者之间达成妥协、实现折中。此处董仲舒言《节》之“刺”既要求规范统治者的言行,又希冀实现政治稳定,便是儒生之“学”与统治者之“术”调和折中的产物。
我们清楚这事实,也尊重这些读者对期刊的选择。国内文学报刊有数百种,《星火》只是中国文学报刊联盟56家理事单位中的一家而已。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以《周颂·敬之》具体阐释“诗人美之而作”,即“圣人事明义,以炤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诗》云:‘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②苏舆、钟哲:《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265页。,臣民受圣人、先王之功德的恩泽,故称颂之,并将这种尊崇、喜悦以诗歌表达出来,这无疑属于“美”。当然,如前所述,董仲舒言《诗》之“美”旨在以《诗》为教:
说而化之以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从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圣传授而复也。③苏舆、钟哲:《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265-266页。
百姓效仿圣人、先王,精神世界受到感化,有移风易俗之效,万民遵循先圣之贤德,无违法行为,故刑法不用,最终实现天下大治。这与《举贤良对策》所言并无二致,即其论诗人所美,旨在化民、治国,其政治意图于此可见。董仲舒所言直接为《诗纬·汎历枢》承续,即“圣人事明义者,以炤耀其所闇,故民不陷,《诗》云:‘示我显德行’”。④[清]赵在翰、钟肇鹏、萧文郁:《七纬》(附论语谶),中华书局,2012年,第249页。由是观之,董仲舒已对美刺作为创作动机这一文学创作心理机制有相当深入的体察,只是美刺对象集中于政治领域,其旨归也直接服务于政治统治。
以美刺解《诗》是四家诗的共同特征,这必须基于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诗人作《诗》本来便暗含美刺之意,后世阐释者才能以《诗》之意逆作者之志,这表明阐释者对能够深入了解、准确把握作者意图相当有信心,当然,按照新批评的说法或许已经陷入意图谬误的泥沼,但是中国古代阐释者认为,以意逆志是可能且有效的。因此,虽然四家诗以美刺论《诗》本意在解析《诗》旨,但也言明了诗人的创作意图,具有创作论意义。此处举齐鲁《诗》解《小雅·六月》、鲁《诗》释《小雅·斯干》为例:
齐说曰:宣王兴师命将,征伐猃狁,诗人美大其功。鲁说曰: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曰:“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故曰中兴。又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猃狁,威蛮荆。”①[清]王先谦、吴格:《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607页。
鲁说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宫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②[清]王先谦、吴格:《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648页。
齐《诗》、鲁《诗》阐释者都认为,《六月》《斯干》都是赞美宣王功德之作,虽然齐、鲁之说未必真正符合《诗》之本事与宣王时代的历史事实,但它们无疑为探索《六月》《斯干》的创作情境提供了线索,尤其是为了解诗人创作意图提供了可能。
以“美刺”解《诗》影响最深远者当属《毛诗》,尤其是《小序》对大多数《诗》篇都进行了美刺判定,有学者统计如下:
《毛诗序》明标“美”(或“颂”)、“刺”(或“恶”“伤”)字样的有157篇,而虽未标明“美”“刺”字样,但从内容上看仍可归为言“美”的有37篇;虽未标明“刺”,但内容上仍可归为言“刺”的有16篇。若以此计,则《毛诗序》中涉及言美、刺内容的就有210篇,占《诗经》总数的2/3还强。③梅显懋:《〈毛诗序〉以美刺说诗探故》,《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1期。
《小序》为诗篇贴上美某公、刺某王的政治标签,历代均有批评者斥其“妄生美刺”,但“美刺”说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诗人创作寄寓政治倾向这一维度。同时,完全从文学角度考察《诗经》是近代以来的事,如果我们试图深入历史现场,《诗经》中完全称得上抒发一己私情之作或许不能占据主体,因为在文明轴心期与文学滥觞期,诗歌与社会政治、宗教祭祀的关联无疑更为密切,我们不可以今人文学观念裁决古人之作,因此,美刺说虽未必尽合历史现场与诗歌本事,但或许在相当程度上呈现了当时的诗歌创作情境。此外,虽然以美刺言《诗》是四家诗的共同特点,但在“美刺”判定及具体所指上常有分歧,如四家诗对《关雎》或“美”或“刺”及其所指并不一致,毛《诗》以为“美”,而齐鲁韩三家则判定为“刺”,但它们都在阐明《诗》旨的同时,关涉到诗人作《诗》意图,且四家《诗》的言说方式并无根本区别。
四家《诗》以美刺论《诗》奠定批评实践基础,郑玄则在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其《诗谱序》从整体上概括了《诗经》创作的美刺特征,所谓“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④[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554页。,换言之,风雅之道不过美刺二端,诗人职责亦在以美刺反映时世、臧否政治。他还在《六艺论》中言作诗者“诵美讥过”,即“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⑤[清]严可均、徐振生:《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50页。与此同时,郑玄承袭变风变雅说,治世诗人美之,衰世诗人刺之: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①[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555-556页。
文王、武王、成王之世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故百姓歌之以美;幽厉之时天下大乱,政教纲常不存,故民歌之以刺。这种以时代先后、篇第顺序分正变、生美刺的做法自然为后世论者所讥,但是也从侧面触及当时诗人创作的美刺指向,且这一认知多为汉儒及后世论者所宗。
此后,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白虎通义》亦言诗人在诗中美刺时政:
合曰《大武》者,天下始乐周之征伐行武,故诗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②[清]陈立、吴则虞:《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103页。(《礼乐》)
古者师出不逾时者,为怨思也。天道一时生,一时养。人者,天之贵物也,逾时则内有怨女,外有旷夫。《诗》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③[清]陈立、吴则虞:《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209页。(《三军》)
天下百姓憎恶商纣之恶,周兴兵伐商得天下可谓救万民于水火,深得民心,故诗人以诗颂周灭商,四家诗也均视《皇矣》为“美”。军旅杀伐之事,事关家国安危、家庭聚散,一旦戍边时限延长,旷夫怨女自然甚为愤懑,并以诗抒发怨刺之情。此外,《白虎通义》在论述“五谏”(即五种进谏方式)时有言,若帝王施政不当、统治衰微,百姓受其荼毒,并引起灾异不祥之事,诗人作诗刺之,以求君王醒悟并弃恶向善,即“若过恶已著,民蒙毒螫,天见灾变,事白异露,作诗以刺之,幸其觉悟也”④[清]陈立、吴则虞:《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237页。。
由此可见,美刺作为诗歌创作论在汉代经学叙述中极为盛行,甚至被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也正因为如此,其旨归在引导文艺创作必须受政治伦理约束。换句话说,政治话语凌驾于文学话语之上,文学只是政治的工具。汉儒囿于文化语境与政治环境,倡言文学创作之“美刺”的政治性自有其弊,摆脱政治束缚的批评使命只能在经学偏枯之时,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忽视“美刺”说的创作论价值,因为它不但揭橥、梳理了中国文学创作的美刺传统及合理性,而且为后世以文艺讥刺社会、干预时政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精神指引。
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文艺创作的发生与普通民众的生存环境、生活遭际密不可分,尤其在艺术的萌芽期,百姓将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喜怒哀乐诉之艺术便是早期艺术创作发生的基本形态。《弹歌》所谓“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有异文),无论被视为“古孝子之歌”“军葬战歌”,还是狩猎之歌,无疑都是百姓生活场景最为生动、浓缩的描绘与再现。此后,有强烈现实主义特色的《诗经》更是有大量反映民生之作,大凡战争之伤、稼穑之艰、剥削之酷均颇为常见,甚至在一段时间里,讨论《诗经》的“人民性”成为诗经研究的关键词。
关于《诗经》创作与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汉儒早有论及,尤其是韩《诗》提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一极精妙、深刻的论述,为我们呈现了人民歌咏生活(尤其是疏泄怨情)这一文学创作现象,这也意味着汉儒已经注意到普通百姓在文学创作中扮演的角色。何休对韩《诗》此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其云: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户牖而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①[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4965页。
何休本意在言天子不出户而知天下事是因为采诗制度,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②[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第1708页。。但与此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诗歌创作乃人民(男女)对现实生活不满(“天下所苦”),故将这种愤懑之情诉诸诗(“歌”),早期文学创作图景于此揭示得颇为形象、深刻。由此观之,“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刺《诗》的一类,此类诗歌主要关注下层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并以之警示统治者。在汉代《诗经》阐释中,不惟韩诗准确洞察到这一点,四家诗都注意到反映民间疾苦之作,此处试举毛诗《小序》解《鸨羽》《大东》《楚茨》:
《鸨羽》,刺时也。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而作是诗也。③[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774页。
《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④[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987页。
《楚茨》,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⑤[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03页。
在《小序》作者看来,《鸨羽》《大东》之诗均系讥刺乱世劳役、征战之苦及其引起的“不得供养父母”“损伤于民财”(孔疏);《楚茨》之作者意在抨击幽王时代诸多乱象:统治无道、赋税繁重、田地荒芜、饥馑荐臻、病疫不断、流民四起、祭祀辍止。三首诗虽借“君子”“大夫”之口道出,但从根本上讲是“劳者”“饥者”诉求的表达。换言之,“劳者”“饥者”的生活遭遇、生命诉求才是这些诗歌创作的根本原因。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于中国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就文学创作而言,关心民瘼之作不断涌现,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一脉,并表现出中国文人强烈的社会关怀与责任意识。如白居易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①顾学颉:《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30页。其创作精神、写作旨归与表现对象无疑延续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传统。就文学批评来说,其隐者乃对关心民间疾苦、讽喻时事之作评价甚高,如历代论者对老杜之诗、白居易讽喻之作多有赞誉;其显者则直接赓续其论,并直接成为后世文学批评引用的范本与言说的凭借,如嵇康《声无哀乐论》便有“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②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98-199页。简言之,诗乐均为创作主体内心悲痛之情的呈现,劳者歌其所历之事,以哀切之言杂比而为诗。此后,《太平御览》引《古乐志》、《文选》李善注潘岳《闲居赋》及谢叔源《游西池》,均引《韩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之说,如李善注《游西池》引《韩诗序》:“《伐木》废,朋友之道缺。劳者歌其事,诗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为文。”③[清]王先谦、吴格:《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569页。王先谦认为此处有阙文,文义不通。
此外,汉儒还注意到文艺创作中的想象问题。在《楚辞·远游》中便有“思旧故以想象兮”,此处“想象”已有遥想、回望之意,却并非艺术创作中的想象。但《西京杂记》中的“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则无疑是对汉代赋家创作过程中驰骋想象、天马行空的归纳概括。此后,《乐纬·乐动声仪》于想象有更为生动、深入的论述:
神守于心,游于目,穷于耳,往乎万里而至疾,故不得而不速。从胸臆之中而彻太极,援引无题,人神皆感神明之应、音声相和。④[清]赵在翰、钟肇鹏、萧文郁:《七纬》(附论语谶),中华书局,2012年,第339页。
《乐动声仪》作者注意到神的诸多特性:源自于心,自由无碍,打破时空的限制而无往不至,这正是文学创作想象活动的典型特征,六朝神思说之风行(如宗炳、王微、刘勰、萧子显),其与《乐纬》此论之关系不可不察。
综上,虽然汉代文艺创作观念多寄生于经学中,常为政治伦理所限,未取得独立地位,但其滥觞意义、发端价值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