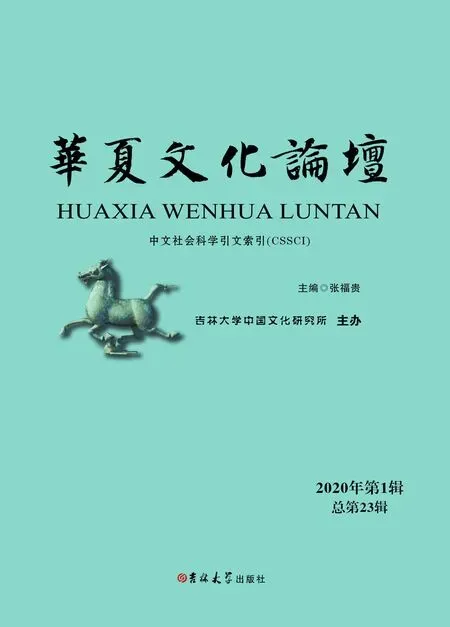中古文士精神之演进①
陈引驰
【内容提要】如果要了解中国文学,除了要对文学文本下功夫,对文学本身要有很深入的了解,了解的方面越广、越深,越好,包括宗教信仰、学术思想等。所谓“中古”的时段,一般中文系的同学可能考虑的都是魏晋南北朝或者六朝。但是这样的理解实际上比较狭,只在研习文学史的群体里有这么一个认同。如果走出去,到历史学界,包括到海外的学术界,他们所讲的“中古”包含的时段范围比我们更广,简单说,从汉魏之际一直到唐宋之际都可以是所谓“中古”。讲中古史,往往是将隋唐史都包含在里面的。
如果要了解中国文学,除了要对文学文本下功夫,对文学本身要有很深入的了解,了解的方面越广、越深,越好,包括宗教信仰、学术思想这些,有更多了解可能更好。今天我想谈的是中古文人的精神世界的演进。
首先,所谓“中古”的时段,一般中文系的同学可能考虑的都是魏晋南北朝或者六朝。但是这样的理解实际上比较狭,只在研习文学史的群体里有这么一个认同。
如果你走出去,到历史学界,包括到海外的学术界,他们所讲的“中古”包含的时段范围比我们更广,简单说,从汉魏之际一直到唐宋之际都可以是所谓“中古”。讲中古史,往往是将隋唐史都包含在里面的,很多的前辈老先生,如陈寅恪先生,从国外回来,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逐渐转向中古史研究,范围基本上就是魏晋南北朝唐代,当然隋唐部分他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专书,形成清楚的学术系统,而对六朝他也有很多论文,可惜没有著成专书,但是对他而言,“中古史”涵括了魏晋南北朝唐代或者说汉魏之际到唐宋之际这样的一个范围,是没有疑问的。这是我首先要做的一个说明。
那么所谓的“精神演进”,为什么要了解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了解一个时代文人的思想世界或者他们的精神世界,对我们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的文学表现、他们的文学文本,是有很大帮助的。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了解,其实会有很大欠缺,有的时候会看不进去。这里简略地勾勒一下中古时代的情形,大家可能都知道的部分,就不再多说了。
一、从经学、子学到玄学
就早期来讲,大家知道先秦时代的战国有所谓“百家争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儒、道两家。如果把西汉和东汉的学术思想流变视为一整个的过程的话,基本上它是腰鼓状的:初期继承了战国以下的那样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然后儒、道相争,然后就是所谓“独尊儒术”,经学成立,于是,子学时代终结,经学时代来临——冯友兰先生最初写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就是这么称呼的;经学时代,所谓“五经”或“六经”都是以儒家学术为中心的,到了东汉,儒家经学当然继续在发展;而到了东汉后期,经学逐渐瓦解,多元的各种各家的思想又重新出来,首先出现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又重新关注子学,比如说《墨子》,早期的墨学在西汉初年就没落了,但是墨子的研究在东汉后期又重新起来,当然还有《老子》《庄子》,包括像《孙子兵法》,我们今天都能看到曹操注的《孙子兵法》——所以基本上东汉末期这样的状况越来越清晰,随着经学的瓦解,子学重新兴起。
子学兴起以后,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所谓玄学的成立。玄学的兴起,一般会认为它与道家有莫大的关系。冯友兰先生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课,讲稿的英文本20世纪80年代才翻译回来,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对于魏晋时代的玄学,用的英文就是Neo-Taoism,这意谓着在冯先生的理解之中,道家是玄学的关键因素——这当然是对的;不过,另一方面,你如果进入那个时代,仔细看那个学术展开的具体过程,便可以说:玄学是从儒学或者说从经学转出来,而兼纳了道家的很多成分,是儒、道两家结合的一个结果。这里只讲最简单的事实,这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人、文学和文学史也很有关系。大家都听到过当时有所谓“三玄”的讲法,《易》《老》《庄》三部重要的玄学经典——大家往往这么说,也没错,但如果是你们学生写论文,我就要批评:你不能这么写,因为还不够严谨,实际上“三玄”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在《颜氏家训》的《勉学》这一篇,“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显然,所讲的“三玄”指的是南朝萧梁时代的风气,并不是直接指魏晋的时代。当然,魏晋时对《易》《老》《庄》“三玄”也是非常关注的。为什么要从玄学所关注的经典来谈?以往的研究有从思想的侧重谈,比如从“有”“无”的讨论来谈,这是哲学史的一般近路;有从“自然”“名教”的关系来谈,历史学家多从此角度进行梳理。我们之所以从“三玄”来谈,是因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往往是借助于对前代经典的阐发。思考学术思潮的起伏变化,你关注它注释什么经典、阐释什么经典,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
玄学的第一个阶段,核心人物是何晏、王弼,这个大家都知道。何晏、王弼的学问,聚焦在哪里?他们关注的经典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三部:《周易》《老子》《论语》。
《周易》:何晏没有什么著作留下来,但是他很乐意谈《周易》,这在《世说新语》里有清楚的记载;王弼是注了《周易》的,那是一部极重要的注本。
《老子》:何晏曾想注《老子》,不过他后来遇到王弼,两人倾谈之下,何晏非常吃惊,感觉这人年纪那么轻,却真正能论“天人之际”,然后他说我就不注了,“退而著《道》《德》二论”,写了两篇论文——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来,在当时的学术著述层级中,“注”是第一位的,今天,“注”可能不算学术著作,不如专著,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观念,那时“注”可是居第一位的——何晏不注《老子》了,退而著《道》《德》二论,那《老子》的注是谁做的呢?是王弼。我们现在都知道,也很重视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本,乃至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郭店简本,但之前很长时间大家读的八十一章《老子》,就是王弼注的,王注本最为流行了。
《论语》:何晏的《论语集解》大家都知道,今天常见的《十三经注疏》就收了;王弼关于《论语》没有像他《周易注》《老子注》那样的专门著述,但他有《论语释疑》。
所以,由以上的情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何晏、王弼他们最关注而下功夫的主要是《周易》《老子》《论语》这三部书。《老子》比较特殊,没有问题是道家的经典,而《周易》虽有玄旨,但无疑首先是儒家经典,是“五经”之一,《论语》早期在汉代属“传”,后来也进入“经”的行列——从何晏、王弼他们对经典的关注,可以说他们是兼合儒、道而展开他们的学术的,他们的玄学是从经学转出的。
玄学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文学史上熟知的文人,他们的玄学被称为“竹林玄学”,也就是嵇康、阮籍这些人的玄学。嵇康、阮籍他们实际上是文人,今天在哲学史上或者思想史上也未得到浓墨重彩的刻画,不像王弼留下了完整的著作,可供深入讨论,但他们在玄学的发展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从他们开始特别关注《庄子》。嵇康特别喜欢谈《庄子》,他的系统见解,今天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你打开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逍遥游》开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一上来就有嵇康的意见被摘录在那里。阮籍则是最典型的代表,他写了三篇重要的文章:《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我们讲文学史经常会谈到《大人先生传》,然后说它受到庄学怎么样的影响;而从这三篇文章——当然现在留下来已不是完整的全篇——你可以看到他对《易》《老》《庄》三种经典都有讨论,是真下过功夫的。当然最重要的要数向秀,他最初要注《庄子》,嵇康虽然对《庄子》很喜欢,也下了功夫,却不主张向秀注它,说这书大家聊聊心得便很好,何必去注?但是向秀不管朋友的劝阻,也幸好他没听嵇康的话,他注成之后,《世说新语》里讲因此而导致“玄风大畅”,庄学一下子就为大家所关注了。向秀的注基本应该是保留下来了,后来一个著名的公案,就是向秀的注是不是被那位“口若悬河”的郭象剽窃了。《经典释文》记说向秀大概注了二十六篇共二十卷,我们今天读到的郭象本是三十三篇,那时候有一个说法,向秀的二十几篇可能都被郭象囊括到自己的注里边去了。现代也有人尝试做离析的工作,要分清哪些是向秀注哪些是郭象注,这恐怕很难。简而言之,我们今天看到的当然是郭象注本,但郭象注文里面肯定有相当部分——虽然很难估计——是向秀的见解,对这些注,有的学者就合称为《庄子》“向郭义”,这可能是比较周到的。讲得可能有些细琐,但意思就是说向秀在《庄子》成为重要的玄学经典过程中有关键的作用。
回头来说,从何晏、王弼的《易》《老》《论语》到竹林文士的《易》《老》《庄》,这一经典关注的变化趋向显示,玄学从经学里面转出来,加入了《老子》,再是《庄子》,道家老庄的思想融入其中,这是玄学主要的发展线索,也是主要的演进脉络。
二、玄学对于文士的意义
玄学是魏晋时代非常重要的新思潮,那玄学对于文学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我们研究的是文学,所关心的还是文学,梳理玄学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个人觉得能帮助我们对某些文学的问题、文学的文本有不同的认识和了解。不少学者关注到道家的思想、庄子的思想在魏晋时代对文人和文学的影响,这样的考察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个人觉得庄学对于文人最重要的启示,一个是关于自由,一个是关于生命。
生命观的问题,今天不能展开,简单谈一谈自由的问题。所谓自由,那个时代最突出的表现是基于对自己个性的尊重而做出自己的人生抉择。首先就要提到嵇康,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想很多读中文系的人都读过,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文章,大家都知道有个背景,当时已经出来做官的山涛,是嵇康早先的朋友,也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劝嵇康也一起来做官,嵇康不同意,然后就写了这篇文章给山涛,算是回应他。大家很容易注意到文章里面提到的各种放荡不羁的言行,比如嵇康说我不能做官,我这个人很懒,懒到什么程度?实在太不像话了,假设说要上洗手间,要“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实在憋不住了,我才去,所以我这种人是不能做官的。可能大家看到这一类事情觉得很有意思,觉得嵇康这个人很好玩。但他绝不仅是这样,嵇康是一个特别能持论的人,当时写“论”一类的文章,他是非常厉害的,老爱跟这个人辩论,又跟那个人辩论,关于养生问题,关于音乐本身是否有哀乐的问题,等等。那么《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文章仅仅是在讲自己如何奇怪异俗的形象吗?他没有一点理据吗?其实不是的,这篇文章里面最重要的理据,在我看,是一句话,叫“循性而动,各附所安”。什么意思?以大白话讲,每个人都应该按照他的本性来行动。你如果通篇仔细看下来,这是他立论的根据。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行动,来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而我与你山涛个性不同,自然不能与你一样进身魏阙。
嵇康讲的这个“循性而动”的“性”是哪里来的?其实“性”这个概念是《庄子》里非常重要的概念。对古人来讲,这整个宇宙、世界,它有其精神、有其“道”在;而天道在人间、在现实世界当中,它落实在哪里?《庄子》的《天地》篇里有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很有条理,“天道”就落实在“性”上,落实在nature上,落实在世间万物的性上。这是基本的观念,不仅是道家的观念,而且可以说是古人讲天人关系的普遍的观念,像《中庸》里面一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这就是“天”落实到“性”上;再比如《孟子》讲要“尽心”——“心”就是他所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而后知“性”,知性而后知“天”。由“心”可以推到“性”,然后推到“天”,为什么能够推上去?因为心、性就来自于天,天道就落实在性上。这么说来,儒家和道家都是这么讲的,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庄子》也是这么讲的。为什么要依循于各自的本性而为?因为天道就落实在万物包括人之性上,你依循于你的本性就是依循于天道自然。“性”这个概念在《庄子》外篇的最初几篇比如《骈拇》《马蹄》《胠箧》里不断出现,非常重要。比如说“马,蹄可以被风雪,毛可以避风寒”,说马生活在一个自在的状态下,“饥则食,渴则饮”,本来很好;而伯乐来了,一定要将马训练成为千里马,施以种种严苛的办法,违逆了马的本性,最后可能万里挑一,“一将功成万骨枯”,出了一匹千里马,却有很多马被弄死了。《庄子》里面讲这样意思的段落很多,比如说鲁国(今天的山东包含古代的齐、鲁,齐更靠海,鲁国离海远一些)的国都之外飞来一只海鸟,可能因为这样的海鸟比较稀奇,国君就把鸟捉去,给它吃好的,还同时为它奏乐,结果这只海鸟从来没见过这架势,目瞪口呆,不敢吃,不敢听,三天就饿死了。《庄子》里讲这叫“以人养养鸟”,不是“以鸟养养鸟”——你这样的方式,对人来讲是很尊重的,钟鸣鼎食嘛,但对鸟是不合适的。所以要尊重各自的本性。从《庄子》这里转回去看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文章,就非常清楚了:嵇康说,读了《老》《庄》以后,我本来很自由自在的性格,就更加趋向于放旷这一路了。可以说,“循性而动”的“性”,应该就是庄子思想脉络之中的“性”。综观全篇,这个“性”不断出现,贯彻始终。嵇康对山涛说,我们两个人的相知是偶然相知而已,实际上你并不了解我的本性,让我来告诉你我是什么样的性格,我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语境之下,他讲了一大堆他自己怎么懒怎么不好,像身上有很多虱子等等,实在与做官的道路不合,最后讲到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走魏阙的路,我志在“长林丰草”之间,你不能逼我,逼我的话,违逆了我的本性,我会发疯——所以说,嵇康的这篇文字,背后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理论依据,而这个“循性而动”的观念来自于庄学。
但前边讲到的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再分析下去,复杂在哪儿?《与山巨源绝交书》又绝不仅是一篇从某个理论观念出发来表达我不愿做官意愿的文字,这后面有很激烈的政治斗争:嵇康的太太是曹家人,当时曹氏与司马氏处于激烈争斗的情境之中,所以他不可能去依附司马氏的力量。其实山涛一开始也很犹豫,山涛的表姑嫁给了司马懿,他与司马氏有了更多的关联,但是他也一直不愿出山,直到高平陵之变曹家的皇室力量受到致命打击以后,格局已定,他才出来做官,然后他再想把嵇康也拉出来,嵇康当然断然拒绝。我想在嵇康和山涛的背后,是一整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环境,从这个环境里看,《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文章所表达的姿态,说到底是一个政治的选择,非常现实的一个政治选择。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当中,嵇康这一政治的选择,有很多话是不能直接讲的,直接说你是那个集团的,我是这个集团的,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那恐怕早就被杀了——嵇康最后被陷害致死——不能讲,怎么办?嵇康借一个玄理,借所谓“循性而动”的理据,给你讲一套道理。所以,看上去这篇文章它确实是在讲道理,我们个性不同啊,所以你可以去做官,我不行啊,所以算了吧,从此我们分道扬镳,等等,对吧?当时不管政治立场怎么样,玄学义理都是大家所了解乃至熟悉的,可以为各方面的人物所认可的。比如,大家知道锺会,就是最后进谗言害死嵇康的那个人,也是位玄学家,能文能武,在灭蜀之役中也是重要的人物,他也很有学问,《世说新语》里很有名的一个故事,锺会拿着自己写的文章去给嵇康看,嵇康在那儿打铁都不理他,弄得锺会很难堪。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中,即使嵇康有非常清楚的政治选择,但当他不能直接说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玄理——不管在政治上与我同道还是异路,哪怕是我的对头,你们也是共有这些玄学理解的人——来写这样一篇文章,你们也能在玄学理论上了解它的意旨,最后嵇康曲折但坚定地给出他的结论:我不能跟你一起,我不愿出来做官。这个时候,玄学的理论对嵇康来讲是有实际作用的,而不是抽象的。一般想象,那时的人们讲玄学,讲“有”“无”之辨,似乎很玄妙,但你应该知道这些人都不是跟政治无关的人,何晏、嵇康这些人都是深深卷入曹氏和司马氏之间政治冲突的,在这样一个很残酷、非常紧张的形势之中,他们有自己的选择。但如何表达呢?像嵇康就借助了玄学,借助于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玄学义理来谈。单就文章而言,它确实是基于玄理对自己个性的一个说明和表态,这是玄学对于嵇康这样的文人的第一重意义;而在因为外在局势不允许你做出实际的政治选择的宣示的时候,嵇康这样的文人借助都能为双方了解和接受的玄理来传达自己的立场,玄学理念具有了实际的作用,这是玄学对他们的第二重意义。
如果可以再延伸一点儿,我觉得陶渊明跟嵇康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今天讲陶渊明是一位退出江湖,退出万丈红尘,返归自然的超脱的诗人,对他做了田园诗般的理解。但陶渊明哪里是?你看他的生平就可以知道,他根本不是这样的。陶渊明一辈子有起码五次入世的经历,入世经历里面最长的一次是跟桓玄,大概有两年,可能跨了三个年头;后来他也跟过刘裕,在他手下做官。桓玄、刘裕是两个什么样的人物?是当时东晋后期前赴后继,要壮大自己力量,甚至要推翻东晋政权,要篡位的人,桓玄已经称帝,但最后没有成功,被刘裕打败,而刘裕最后是成功了——他们是对头,但是在推翻东晋夺取天下方面,他们是一路人。陶渊明在这样两位一代枭雄手下做过事,眼见过风云变幻,你说他是一位心境纯净、非常天真淳朴的人,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我无法相信,残酷的政治斗争他都见过,所以他完全明白。
陶渊明最后离开官场、离开政坛,他退隐田园是非常自觉的一种选择,这个自觉的选择,我相信不仅仅是他自己讲的那些理由。陶渊明很有意思,他做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其实很多人也都做过人生的重大选择,但陶渊明是对他的人生重大选择进行了最多说明的人。我们今天基本都认同了陶渊明的讲法,他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所以他回去了;而且,在田园的环境里诗人说他自己感到很高兴,对不对?什么“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等等话语,对吧?他讲了很多这样的话,包括《归去来兮辞》里也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你们想想看,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人生重大的选择讲得太多——我可能有点儿过度诠释——好像有点儿过分,似乎他一定要讲出一个令众人信服的理由。从陶渊明早年的实际政治经历来看,我相信他绝对有非常现实的理由,绝对有实际的考虑;但那个时候他不讲或不便讲,他用什么来讲呢?还是这个“性”:“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本性是喜欢自然环境的,包括《归去来兮辞》中提到自己“质性自然”。他用这些玄学的理论来向大家解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离开官场仕途,是因为这才是真正符合他本性的,这才是他真正希求的自由,这样一种选择令他开心快乐。诗人借讲论众人能懂、人所共知的玄理来为自己的人生选择做辨说,但我想他有他非常实际的政治背景和现实的考虑。
三、佛学进入与多元信仰
玄学之后,最重要的思想潮流当然就是佛教,它与源自先秦古典时代的儒家和道家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最主要的三个精神脉络。佛教起源于印度,大家知道,大约是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而佛教真正对中国的精英文化、对我们文学史上的那些文人发生影响,基本上是在东晋以后。明代的何良俊有一部《四友斋丛说》,就提出过这么一个观点,他说晋室东渡以后佛教才真正对中国的士人有影响;现代的研究也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比如你们看荷兰非常有名而重要的研究佛教史的学者许理和所写的《佛教征服中国》,它比较全面地处理相关材料,可以看到东晋之前文人跟佛教相关的材料很少,他们之间的关联非常有限。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你们去读《世说新语》的《文学》篇——《世说新语》是非常重要的书,但是你不能仅仅看里面的故事好玩,实际上这些片段背后有一整个的历史背景、文学史的背景、思想史的背景,读《世说新语》可以读出很多内容,有时候一两条材料都足以引发你切入丰富而深远的中古世界,帮助你理解那个时代。《文学》篇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它讲的是学术的发展和文学的起来,全篇一百多条,大致分了两部分,从曹植七步为诗的故事之后大抵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但之前部分的“文学”,其实还是“孔门四科”所谓“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文学”的概念,指广义的文献和文化——《世说新语》的《文学》篇一上来讲经学,主要是马融、郑玄等这些经学大师的事情;接下来记述的是玄学人物何晏、王弼的故事;再往下是嵇康、阮籍;然后就是佛学,这些有关佛教的条目,时代基本都在东晋以后。
晋室东渡之后,士大夫才开始认真而深入地研读佛经,我们不妨以一个故事来说明。最初佛教僧侣的地位比较低,像最有名的支遁即支道林要和王羲之聊聊,作为高门士族的王羲之理都不理他,不跟他接话,端着架子;支道林没办法,但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僧人,专门去找王羲之,趁着王羲之正要出门,支道林堵住他,硬拉着要谈庄子、谈“逍遥”,花言巧语,玄妙异常,王羲之听得入迷,一高兴便“披襟解带”,把准备出门而穿得整整齐齐的衣服都解开了,他不走了,与支道林聊开了。所以一开始,应该是佛教僧人去迎合士人的,像支道林就是以庄学的“逍遥”玄义来接近王羲之。随着士人研究佛学的深入,情况有了变化。那时候有一位殷中军殷浩,读佛经读到《小品般若》,他是当时有名的玄学家,智力超卓,遇到他有疑问不懂的地方,就标记一处,积累了百余处吧,然后他就去找支道林讨论。这次轮到佛教僧人不与士人接谈了,支道林不跟他谈。怎么回事呢?原来竟是王羲之劝阻支遁的,他的说法是殷中军是玄学名家,非常厉害,谈起玄学滔滔不绝,别人很难辩倒他,现在下了那么大功夫研究《小品般若》,他搞不清楚的,你支道林说不定也搞不清楚,你们对谈,如果他问难你,你答上来,这是天经地义,你是佛教僧人嘛,你当然得答上来,万一你答不上来,一世英名可就毁了,所以你一定不要去和他谈《小品般若》。故事很有趣,但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看出来士人真正对佛教经典、佛教义理下很深的功夫,基本在东晋以后。
东晋以后,佛教进入了精英士人的主流。从东晋,一直到唐代,对中国的精英文士来讲,他们的精神世界、思想世界之中,儒、道、佛三者清楚地构成了一个多元结构。传统的经学和儒家经典,他们不会不读,这是他们看家的东西,从一开蒙,最早都是学这些的;然后有道家的、玄学的、道教的、佛教的,这些都在他们的头脑中盘旋,都成为他们的精神资源,在他们的为人处世、人生选择一直到文学文本的书写里边,都会留下这些交错而复杂的痕迹。
在整个的这一历史时段中,你都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精神传统互相之间的交织、冲突、平衡、融合,几乎所有重要的文人身上都有这样的一种表现。比如刚才提到的王羲之,你读他的《兰亭集序》,这是名文,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一死生”就是把死生看成一体,相通相贯;“齐彭殇”——彭祖活了七八百岁,殇就是未成年而夭折的小孩子——长寿的和夭折的都差不多是一样的。王羲之对这样的说法很恼怒,说这样的观点真是胡说八道。那么所谓“一死生”“齐彭殇”是谁讲的呢?是庄子。王羲之这里是在骂庄子,说庄子你胡说八道,什么“一死生”“齐彭殇”!现在的人会觉得奇怪,那个时代老庄不是几乎所有士人都倾心相向的吗?他王羲之怎么会这样批评庄子呢?其实很自然,因为王羲之是个道教徒,而道教的一个基本追求就是长生久视,这是与主张自然主义的道家庄子截然有异的,而那个时代,《庄子》属“三玄”之一,与唐代以后被纳入道经系统、与道教打成一片还不同,当时它是属于玄学的。王羲之是站在了道教的立场上,对庄子的生命观念提出严厉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奇怪,你了解了当时的那些文人的精神状态,他的思想脉络,就好理解了,道教和道家固然有很多相关的地方,但起码在中古时代尤其是早期的中古时代,在如何理解生命的问题上,两者之间的认识和态度并不相同。玄学脉络之中的道家庄子是讲自然的,文人之中,陶渊明领会了真正的庄学思想,他讲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我随着自然流程随波逐流,该终结时就终结,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道教不是,道教是要追求长生,采药也好,炼丹也好,种种的修炼都是为实现长生乃至永生。所以,起码在这一点上道家和道教不同,王羲之正是站在那个时代道教生死观的立场上,对道家庄子的“一死生”“齐彭殇”,展开了他的批判。
类似的复杂情形其实不少,我们有必要审慎对待。比如谢灵运,今天很多人研究,特别关注到他与佛教的关系。但谢灵运的一生,佛教对他来讲固然很重要,他也介入了当时最重要的佛教的争论,有《与诸道人辨宗论》这样的重要文章,不过就整体而言,不能讲谢灵运是一个佛教徒,不能过高估量佛教对他的意义。谢灵运作为当时的高门贵族子弟,拥有各种知识储备和精神资源,你看他的诗文,引据的经典什么样的都有,《周易》《论语》《老子》《庄子》等等,当然也有源自佛经的;而且从谢氏的家学来讲——南朝人讲究家学,很多士人的信仰不完全是个人的选择,这与后来的唐宋时代不一样,后世的信仰往往是个人的选择,我信什么是我的选择,现代人也是这样;但谢灵运那个时代,家族信仰的因素很重要,像王羲之所在的就是道教世家,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等等,老子和儿子都叫什么之,看着奇怪,其实那是天师道;有些家族则是信佛的,跟佛教的关系很密切——绝对不是佛教世家,当时高门贵族基本还是以玄学综合各家,儒、道、玄兼合,对佛教也有新锐的了解。所以你看谢灵运文字书写里边的那些引据,甚至你扩大开去看他们谢家其他人文学书写里边的引经据典,佛教也都不是最突出的。这样,回过头去,就能帮助你去理解谢灵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种种言行和思考,到底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思想资源。简而言之,那个时代里的文士如谢灵运一样,拥有的都是一种多元的信仰和精神世界;这个多元的信仰和思想,相互之间可能是冲突的,有待他们的选择,当然也能够是兼容的,共同支撑和支持他们的人生和文学。
我想接着提到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是后者的典型。白居易非常有趣,我非常喜欢白居易这个人,他看起来不像陶渊明那么高洁,而是比较俗,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俗,然后他直言不讳地表现出来,但是他对于生活呢,非常热爱,对自己的人生也很清楚。我觉得中国文学史上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清楚,能够很好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样生活,这样的文人并不很多。李白、杜甫可能是最伟大的诗人,但他们对自己的实况恐怕都不太清楚,李白觉得自己很牛,“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说自己可以“为君谈笑静胡沙”,其实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杜甫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你给他一个官做,马上就跟人闹翻了,做不成事。陶渊明对自己的人生非常清楚,苏东坡渐渐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白居易也是这样的一位,清楚自己能干什么,然后自己活得很有趣。白居易以他自己的生活为中心,什么儒、道、佛,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只要是他觉得能够让他快乐,能够为他所受用的,他都接受,都包容。所以,他将儒、道、佛都混在一处,没有隔碍,他有一首诗叫《味道》——不是我们吃东西的“味道”,这个“味”字在这里做动词解——里面写“叩齿晨兴秋院静”,“叩齿”是道教的一种修养方式,现在还有人实践,他说早晨起来我在安静的院子里叩齿,练这个功夫;“焚香冥坐晚窗深”,点一支香,“冥坐”就是静坐了,在窗边静坐到深夜,你看,他是早晨修道,晚上念佛;下边两句话是“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檀经》说佛心”,道经、佛经他都有研读、体味。白居易还有诗说到自己跑到庐山里面建了一个房子——今天大家都会背《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说花开得晚,为什么呢?因为山里面天气暖得迟一些——他住在山里面的时候,把和尚、道士一起找来,其乐融融。对各门各派各家各流,白居易都是包容的,都是接受的。
四、回向儒为宗主的世界
最后,再简单地做一个回顾:从东汉后期经学瓦解开始,诸子学复兴,接着是玄学的起来,再是从东晋以后佛教进入精英士人的精神世界,那个时代的文人便处在这么一种多元的精神和信仰的状态之中。
我还是想再表达一下,之所以观察这个时代的思想或学术的演变状况,最后还是想在文学的立场上来看当时的文人拥有一个怎样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对他们的为人和他们的为文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从汉魏之际,经六朝直到唐代,起码到唐代中期,那个时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从那种单一的状况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可以说是一个自成段落的时代。我们回过头去看,时代的精神和思想,难说永远都是多元,也不可能永远都是单一的,我们所谈的这个多元时代是不是显得特别?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在这个时代里,文士们面对多元的精神世界,似乎大多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这个时代里,多元的信仰和思想不成其为问题——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如此。那些文士有时候也意识到,多元的同时就是差异乃至冲突,但他们觉得可以啊,我可以自由、圆融地出入,人生的不同时刻,可以具有多面性和各种可能。
真正要重新对精神世界进行调整,大家都知道,从中唐的韩愈开始。文学史上所谓的“古文运动”,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一个部分。韩愈们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原道》直接讲到了,人都是要修身的,儒家《大学》里面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从修身始,道家也讲修养自我,佛教也是,但韩愈说这里面有个重大的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不同就是,儒家在修身之后“将以有为也”,你修身以后,要推展开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释、老就是佛教和道家,则放弃了后边这些。道家的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开玩笑地讲,在先秦诸子里面,老子的官做得不小,他是中央大员,周天子朝廷的人,其他很多人像孟子,都没做什么官,庄子最多是漆园小吏,孔子也只是鲁国的官员,地方大员而已;但《史记》里讲老子“见周之衰”,便跑掉了,看东周不行了,就自己一甩手走了,典型的不负责任嘛。所以,从韩愈这些人开始,精神世界的多元性,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严肃的问题。不是说韩愈以后包括宋人对于道家、佛教就是完全的排斥,而是在多元的精神传统之中,你要立一个宗主。宗主是什么?宗主就是儒家,要重新回到儒家。当然唐宋以后建立起来的所谓的儒学或者道学或者理学——不管它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名称——已经与之前的早期儒家传统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重新确立传统儒家的核心地位,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
这代表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过去的中古时代,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那样的一种文人精神世界多元化的时代结束了,多元的时代已经从兴到衰,走过了这样一个相对自成段落的历程。对此,我们需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在这个时段里,多元思想在交织冲突,当然也有融合,形成各种各样的姿态。你进入这个时代,要有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这是这个时代的文人和这个时代的文学最重要的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