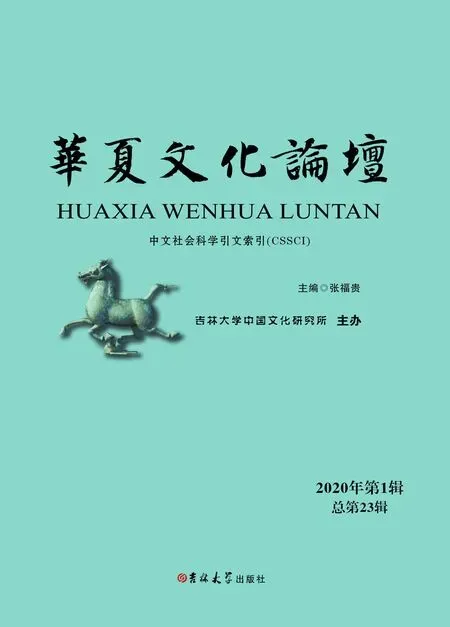“慎言观”视域下孔子的情感传播观念研究
林 凯 谢清果
【内容提要】在语言传播方面,孔子主张“慎言”,而这种“慎言”观念背后是各种德性情感在主导:有天道之情的敬与孚,也有人道之情的仁与信等,这些德性情感支配着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慎言”传播。语言作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是天与人和人与人沟通的媒介,孔子用譬喻的语言传播风格以及使用雅言的方式来传递德性情感,实现德性情感的互动、共鸣。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在这种德性情感传播中,孔子的目的在于通过“慎言”来培育个体德性的修养,强化阶级之间的互动交流,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固,建构新的理想社会。
《论语·季氏篇》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74页。文中《论语》的引文均来自此版本。作为继承周公思想、延续周礼制度的孔子面对这种“礼崩乐坏”、僭越社会规矩的行为是厌恶和抵制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论语·雍也》又言: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面对社会失序行为,孔子试图用其仁政思想来扭转这一局面,建构新的符合周礼的社会秩序。从语言方面上看,“祝鮀之佞”就是巧言,而“宋朝之美”就是令色。那么祝鮀之佞与宋朝之美便很少有仁的品质,但却可以大红大紫,十分显赫。②毕宝魁:《〈论语〉“不有祝鮀之佞”章本义辨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这违背了社会礼的规范,也就是损德缺仁的表现,正如孔子所言“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语言作为日常交往的符号,是天人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交流传播的重要媒介,它能够表达人的思想和观念,也能够传递人的情感和态度,由此改变对世界的认知、提升人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水平。我们通过孔子周游列国及其对弟子教诲的历史实践来看,语言成为其游说君王、教化弟子、传播仁政思想的主要媒介,由此体现了语言强大的说服力和教化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主要是通过语言表达的内容、语言传播技巧等来完成的。这种渗透于日常交往的语言传播功能对人的思想和品德的塑造往往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常常具有看似细微而殊难抗拒的影响,①沈立岩:《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1页。正如孔子所言:“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论语·颜渊》)因此,他在交往中是极其注重语言的表达和运用的,整体上看是一种“慎言”观念。从表面上看,孔子所倡导的“慎言观”是对语言传播功能的认知和重视,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孔子对社会等级制度的维护,也就是说,语言传播不仅不能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而且还应该成为恢复周礼、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进一步看,“慎言观”是孔子顺应天道、修行人道的德性情感的体现。我们从“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可以看出,语言和仁这种德性情感是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的表达是内在情感的一种外在表现,在笔者看来,孔子的“慎言观”背后是德性情感的促动,德性情感成为语言传播和人际交往行为的基础动力。基于先秦儒家这种思想背景,本文也将从语言和情感传播的角度入手来考察孔子“慎言观”对语言的运用及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传播(交往)的内在理路,从本质上探讨孔子仁政思想的传播内涵。
一、“慎言”交往观及其情感沟通功能
语言作为人类沟通的媒介符号,具有明显的情感沟通功能和社会传播效应。而孔子对待语言和使用语言传播具有特定内在逻辑,形成“慎言”的交往观念。
(一)孔子的“慎言”交往观念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版),中华书局,2016年,第1220页。这是孔子对语言的媒介性质、传播功能以及语言传播的谨慎态度。从社会传播效应来看,《论语·子路》载: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如果说,语言能够像上文所说的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则有可能产生“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效果。《系辞上传》有言:“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③黄寿褀、张善文:《周易译注》(新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05页。面对语言强大的社会传播效应,孔子一直都主张在交往中慎重对待语言的传播。《艮》卦六五爻辞曰:“艮其辅,言有序,悔亡。”④黄寿褀、张善文:《周易译注》(新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79页。语言传播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则才能消除悔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正如《周易折中》引龚焕云:“艮其辅,非不言也;言而有序,所以为‘艮’也。”⑤黄寿褀、张善文:《周易译注》(新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79页。也就是说,这里体现的不是不言,也不是妄言,而是要根据一定规则慎重对待语言传播。《说苑·敬慎》曾记载孔子关于慎言的故事:“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鸣其背曰:古人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必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孔子顾谓弟子曰:记之。此言虽鄙,而中事情。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这告诫人们慎重对待言语,这里反映出春秋时人际关系中传播的复杂性。①郑学檬:《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31页。《论语》中也记载了大量孔子关于“慎言”的言论,譬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而已”(《论语·学而》)、“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从根本上说,这是矜慎内敛、克制自省的精神的体现,更是先秦儒家维护周礼、践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礼乐制度中的德性情感的反映。②沈立岩:《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二)语言作为情感沟通的媒介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③[晋]范甯:《春秋谷梁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34页。也就是说,人能够运用语言符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人可以传播接收语言符号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从口语传播的角度来看,语言依靠声音的表达,承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而声音的高低起伏则能反映和表达人的内心情感。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语言在社会交往,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功能上,沈立岩认为,“它可以以经验或神秘的方式影响言者个人和国家的命运,而旁观者也可以从中窥见这一命运的征兆;它是人格修养和思想情感的不可缺少的表现方式,也是鉴别一人之德行高下和智能贤愚的重要依据。”④沈立岩:《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 观念及其文学意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8-399页。笔者以为,在遵从周礼、修己体仁的春秋时期,语言的情感功能是尤其明显的,这是由于春秋社会人际交往的双方是在严密的等级制度下,以相应的社会身份进行交流,语言传播活动都须遵守一定的规范和约束,而这种遵循实际上是一种内心情感的体现,或者说是内在情感的约束促进语言规范化传播和表达。而春秋时期这种内在德性情感的外在表现就是孔子所倡导的“慎言”,也就是说它体现了一种慎重的态度,正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由此看来,情感可以渗透到整个语言系统,语言系统的几乎任何可变的方面都是表达情感的渠道和载体。⑤Elinor Ochs and Bambi Schieffelin:Language has a heart,Text,1989(09):7-25.
其实,按照卡西尔的说法,“语言最初并不表达思想或观念,而是表达情感和爱慕的”,⑥[德]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44页。“言语有不同层次,最初和最基本的层次显然是情感语言。人的全部话语中的很大一部分仍属于这一层”。⑦[德]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49页。也就是说,语言承载情感的信息要先于语言表达思想和意义,诚然如斯,语言尤其是口语表达,语言的声音、词汇、句子等都是情感表达的有效形式,交流双方通过识别语言中携带的情感信息进而协调自己的行为,从而进行顺畅的交流。“人情不同,其辞各异”,饱含情感的语言能够在不同场合、时间和对象上进行入情、合情的传播,提高语言的传播效果,实现交流目的。①尚爱雪:《语言的情感化和情感化的语言》,《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刊),2002年第1期。可以说,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媒介,更是人类情感沟通的桥梁。
不过我们也看到,孔子也曾表达过“无言”的思想,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用四季更替、万物生长这种“无言”现象来阐释天道运转的规律。语言是桥也是墙。“言”可以传情达意,也会阻碍交流。②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页。这也许可以解释“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语言的重要性在立德、立功之后。笔者以为,对于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孔子对于道的认识更多在于“体认”,而思想和情感的表达更需要语言作为媒介和载体,语言传播成为体道、悟道的一个阶段,对于孔子所倡导的顺承天道、仁爱人道的理解和感悟需要自身的沉浸式体悟。
二、“慎言”交往的情感动力
情感可以作为社会行动的触发因素。③Du Bois,John W.and Elise Karkkainen:Taking a stance on emotion:affect,sequence,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dialogic interaction,Text and Talk,2012(32):433-451.孔子主张“慎言”就是在一定情感的支配下形成的社会行为。张景云认为“慎言”作为儒家传播的一条重要原则受到“五常”的约束,其中,“仁”对言论要求:隐恶扬善、谦逊忍让,主张木讷、反对巧辩。“义”对言论要求:传播者内心和谐中正,言谈的内容、程度、方式以及时机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将“义”作为选择传播对象的依据。“礼”对言论要求:恪守禁忌、符合社会角色的要求、言谈态度谦恭、反映“仁”的内在的要求。“智”对言论要求:传播者的条件、传播内容的准确性、传播时机的确定、传播效果。“信”对言论要求:真实、恰当,“言”与“行”相匹配。“慎言”的实质是通过“五常”伦理制约传播,维护社会秩序。④张景云:《“五常”与儒家“慎言”传播思想》,《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2期。这是张景云从“五常”的德性情感这个角度进行的归纳总结。笔者以为,“五常”是从人道或者说社会伦理道德层面推动人与人之间的“慎言”行为。在本文中,我们结合孔子承延周公礼制思想以及孔子倡导的仁政理念,将孔子“慎言”行为背后的情感推动力归纳为天道之情和人道之情,从与天沟通和与人交流两个层面揭示“慎言”交往观念及其背后的情感动力。
(一)天道之情:敬与孚
这里的天道之情指的是孔子对上天和对君王敬畏的德性情感。这里的“敬”应该要追溯到西周初期周人敬畏上天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尚书》中多有记载,譬如“在后之侗,敬迓天威”,“以敬忌天威”,①[唐]孔颖达:《尚书》,中华书局,1998年,第103页。“尔尚敬逆天命”,②[唐]孔颖达:《尚书》,中华书局,1998年,第113页。等等。徐复观指出:“‘敬’是始终贯穿在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的,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是主动的、反省的,因而是内发的心理状态。……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察照、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而此种人文精神,是以‘敬’为其动力的。”③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2-23页。“敬”成为了推动周初人与上天沟通的情感推动力,也只有这种敬畏的德性情感才能承受天命。孔子承延了西周这种对上天的敬畏之情,如《论语·季氏》中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种对天的敬畏之情可以说是人与上天的互相确认:“上天的意志最终在人的行为和成就中实现自己,但它不是一种确然无疑的恩命;人通过时刻敬畏、戒惧的自我反思、自我校准去接近它、领会它——天命其实是关于自己道德能力和人类崇高价值的信念,它是由人的道德行为去显明和成就的。”④李宪堂:《“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文史哲》,2017年第6期。除此之外,这里的“敬”也体现在孔子在等级分明的阶级中,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应该遵守等级中的礼制,对社会这种等级制度抱有敬畏之情,不能逾越和破坏,诸如始终恪守君臣之礼等。这种对上天对等级礼制的敬畏之情使得在与上天和人际交往中慎重运用“语言”。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敬畏的情感应该来自于内心的真诚,也就是说不管是与上天相互确认的敬德保民的行为还是遵守等级制度的遵礼行为,都需要发自内心去实践,应该始终如一地遵守天道和人道。这种真诚的情感,笔者以为就是“孚”的内涵。
孚在《周易》的二十五个卦中都有出现,其以“孚”“有孚”等形式出现,其主要意思是“孚”是一个君子的内在德性,是一种美德。《周易·观卦》“有孚颙若”,马融释曰:“孚,信;颙,敬也。”⑤黄寿褀、张善文:《周易译注》(新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70-271页。《说文》“信,诚也”“诚,信也”⑥[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52页。。所以“孚”具有“诚信”的意思,但是这里的“诚信”在笔者看来是一种心中始终秉持的德性情感,是至真至诚的情感,而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信任情感(这种含义将在下文探讨),朱熹曾经辨析“孚”字与“信”字意义的区别说:“伊川云:‘存于中为孚,见于事为信。’”⑦[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3版),中文出版社,1984年,第2969页。也就是说“孚”更强调内心真诚的情感,而如果体现于外则是一种“信”的情感。《中孚》卦的《彖》传可以解释这一点,《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也就是说,中心诚信,譬如柔顺处内能够谦虚至诚,而刚健居外又能中实有信;于是下者欣悦而上者和顺,诚信之德惠化万邦。⑧黄寿褀、张善文:《周易译注》(新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652页。“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其业。”①黄寿褀、张善文:《周易译注》(新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83页。言辞的传播要出于诚挚的情感,这是积累功业的一种体现,“敬”和“孚”是君子承应天道、积累功业所应秉持的情感,更是在与天人沟通中主导“慎言”的内在德性情感。
(二)人道之情:仁与信
“仁”与“信”就是仁爱和信任(也包含诚信的含义)的情感,这是人道之情的主要体现,在本文中人道之情是从人际交往层面去重新划定的。从“仁”的角度来看,“仁”是孔子治国理政的核心,在本文中“仁”是一种仁爱情感,它是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情感,是德性情感的一种。《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从二。臣铉等曰:仁者兼爱,故从二。”②[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61页。这也就是所谓的“仁者爱人”,也就是说“仁”需要体现在人与人的相互交流之中,相互关爱才能体现这种情感,而且在孔子看来,“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基于这样的爱憎分明的情感,因此,在语言上应慎重表达意见和看法。可以说,“仁”是人性固有的一种温情和暖意,这种温情和暖意只有施之于他人才获得实现,……在孔子这里,仁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相互敞开、相互成就的群体行为,这种群体行为共同构成了人类整体存在的超越性。③李宪堂:《“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文史哲》,2017年第6期。仁爱情感是贯穿于孔子一切社会交往行为中的,这是推动人际交往和传播的核心情感。而关于“仁”的内容,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其中,“信”的情感也是属于仁爱情感的范畴,但是因为“信”与语言传播有更直接的联系,“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④[晋]范甯:《春秋谷梁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34页。语言与人的诚信和信任之情是紧密相关的,它能体现一个人的内在德性情感。因此,本文单独对这种情感作阐释。
晁福林就《诗论》的简文分析过孔子诚信的语言观念——言所当言。上博简《诗论》第二十八简中记载:“《(墙)又(有)荠(茨)》,慎密而不智(知)言。”晁福林认为《墙有茨》反映了夫妻之间应该慎言,但同时也应该“知言”,也就是说夫妻之间的言语交流也要有诚信。对此晁福林引用郭店楚简《六德》第三十七号简加以论证,第三十七号简的简文讲道:“君子言信言尔,言炀(诚)言尔,设外内皆得也。其反。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⑤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这里强调了君子应当讲诚信之言,这样对人对己皆好。如果不讲诚信之言,那就会出现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不协调的违礼局面。夫妻的枕席之言虽然还不能说就是“慎独”之言,但却是与之接近的。孔子认为就是夫妻之间也应当讲诚信之言,而不可以随意胡说。……但是孔子认为怕泄露于外而慎言,并非达到了“知言”的标准。君子应当做到的操守之一,就是慎独,就是言所当言,即诚信之言。①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43页。笔者以为,夫妻之间的交流害怕泄露而慎言,但是语言传播终会泄露,所以孔子认为,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讲求诚信。应该说,“慎言”是诚信交往的一种体现,诚信和相互信任之情更加要求交流双方应该“慎言”而不是用“巧言”进行传播交流。
可见,在人际交往中“知言”——诚信地运用语言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孔子强调的“信”是建立人际信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诸如《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同时“信”也是决定人在社会生存的重要条件,如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信”意味着,“自我”与“自我”之间通过对共同信用机制的维护,减少人际的摩擦和内耗,最终建立起一种人生道义上的相互承诺关系。故而孔子说“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②李宪堂:《“天命”的寻证与“人道”的坚守:孔子天命观新解——兼论孔子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文史哲》,2017年第6期。因此,人的诚信之情也是推进人际“慎言”交往的重要内在德性情感之一。
三、孔子情感传播的语言路径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在与君子交往中应该注意时机、察言观色、要充分表达等传播技巧,当然也需要规范语言表达的内容,谨慎地使用语言进行情感交流。在孔子遵从周礼、以德性情感为基础的人际交往中,德性情感作为一种内在动力规范着语言的表达和传播,在这种规范中,语言作为一种修辞符号自然形成了外在的表达路径和传播方式,引起双方的情感共鸣,促进交流。
(一)“譬喻”:情感传播的语言表达方式
孔子的“慎言”传播观念,其实也包括善于运用语言进行交流传播的内涵。我们知道,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具有意义模糊性和解释性等特征,它总能在具体的语境中被使用并且产生直接意义(denotative)和隐含意义(connotative)。③胡春阳:《人际传播学:理论与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8页。这说明了语言的传播功能,它能够直接表达一个事物,也能够以一种暗指或比喻④[美]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9页。的方式来表达,也就是说为了能够更好地传达思想,扩展语言的传播功能,就必须采用修辞。⑤钟肇鹏:《孔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43页。比如,在《论语》中我们看到了孔子在使用语言时经常运用譬喻的手法,譬喻的交流乃是孔子教育的主要方式。《论语·子罕》记载,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为政》篇载,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以此来比喻为学要持之以恒,君王要用德治才能实现人心归附,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比的修辞手法,如: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我们通过《论语》发现,孔子大量通过比喻、对比等譬喻的形式来传递他的思想,这扩展了语言的表意空间,更有利于受众进行联想和解读。
孔子使用“譬喻”的语言表达方式,一方面以自身作为类例推己及人,把“譬”提升到“仁之方”的高度(郝大维与芬格莱特等认为这种“推己及人”的譬的方式,含有一种推己及人的“恕”的情感,是一种敬意的行为①[美]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4-355页。);另一方面从“德”的视角视察自然,将温润缜密的美玉对应君子“仁”“智”“义”“礼”“忠”“信”的美德,对应“天”“地”与“道”“德”的本性。这样,“譬”就不再是一种以类相喻的普通表达手段,而是一种充满象征意味的言说方式,由此形成“君子比德”的话语传统。②崔炼农:《孔子思想的传播学诠释》,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5-147页。这种话语传播方式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话语隐喻的方式来表达对上天、君王的参照学习,以及对上天和君王的美德颂扬,以此为参照不断提升自身的德性水平,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孔子试图在沟通行为中通过敬意行为再现历史或当下的美德。这一再现不是借教义和信条,而更多依靠的是经验的古老资源——行动及其情感氛围。③[美]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3页。在榜样或参照对象的激发下,传受双方建立一种呼应和共鸣,这也揭示了譬喻的另一种含义,也即隐喻的形式,这种形式运用于沟通行为就会唤起交流者独特的情感体验。
进一步来看,这种隐喻表达情感体验的“真”体现在沟通者之间:“让有耳能听者自己倾听。”④[美]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6页。一方面这种“真”能够在现实中有可以参照的榜样,另一方面这种参照榜样用譬喻的方式能够让每个人都能理解和接受,从而将上天或圣贤的德性真实地落实到倾听者的身上,可以说,这种譬喻的话语传播方式能够实现撒播效应,这一点与耶稣的布道有相似之处。耶稣在三篇对观福音(《马太福音》13、《马可福音》4和《路加福音》8)中都以布道者的形象出现,并以“播种者的寓言”进行布道。耶稣认为,播种者撒播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地上,大部分种子不会结果,只有少数能结出果实。这种“撒播”的传播方式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由此,耶稣说:凡有耳者,皆可听,让他们听吧!⑤[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75页。这里的撒播显然需要传播受众发挥主体性去接收信息和自我解读其中的含义,实现与他者互动。因此,在孔子“譬喻”的传播方式上,能够将德性情感撒播在话语交流中引起受传者的互动,而且隐蔽地将社会等级思想融入其中,在无形中起到规范和引导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引导和激发传受双方关于德性情感的共鸣,从而调整他们的社会交往行为。
(二)“雅言”:情感传播的语言材料
《礼记·王制》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⑥[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全三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360页。,不同地区语言是不相通的,因此,孔子主张应该学习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郑玄注:“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①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中华书局,1958年,第93页。雅言,就是为了克服语言不相通而制定的标准的语言、语音、语义等,当然对孔子来说,这是为了传播他的仁政思想,推广礼乐制度。
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孔子鼓励弟子们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字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而且如果不学诗,则无以言。(《论语·季氏》)一方面,孔子在教习诗、书、礼仪和执行礼仪的过程中采用雅言;另一方面,孔子传承了西周雅言赋诵的方法,不仅诵读,而且弦歌。②崔炼农:《孔子思想的传播学诠释》,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2-143页。在这些学《诗》的诸多功能中,我们主要考察学习《诗》这种雅言材料对于情感的激发和传播的意义。诚如上文所言,诵读和弦歌的方法能够将《诗》这种雅言的情感功能发挥出来。《诗》可以兴,也就是《诗》能够激发人的内在激情和心志,这是情感表达和传播的起点。《诗》可以群,也就是诵读和传播可以让众人一起参与诗歌的创作和诵读。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述而》),也即教育的普遍化和仁爱的广泛施与,《诗》为百科知识的渊薮、人生经验的教科书,对于知识的增进、性情的陶冶、意志的引导具有极大益处,能在一个“无辞不相接,无礼不相见”③[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全三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1299页。的社会环境里产生合群亲众的效果。而且作为艺术的诗歌,还特具一种情绪的感染和共鸣机制,沉吟涵泳之间,足以令人心动神驰、潜移默化以臻于思想、情感的同化与调谐之境。④沈立岩:《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4页。这里的“群”不仅是表明《诗》的学习和传播对象具有广泛性,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在群体的学习中引起情感共鸣,由此,《诗》中的内涵以及所蕴含的德性情感得以传播和内化。
与此同时,《诗》可以“怨”,也就是可以抒发不满的情绪,《说文》有言:“怨,恚也。”⑤[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21页。孔子虽以“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论语·述而》)自励,但并不主张掩饰个人的真实情感,正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在他看来,情感只宜善加引导和调节,而不能强行去压抑,所以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⑥[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全三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1281页。,诗歌则为情绪的宣泄提供了理想渠道。⑦沈立岩:《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5页。通过诗的语言抒发和传播情感,实际上也是能够让情感在礼的规范下得到合情合理的传播和抒发,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是有积极意义的。总的说来,雅言的运用能够让相应社会阶级在社会交往中应付自如,实现有效交际,应该说,雅言的运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社会交往的空间。
四、结语
孔子“言传身教”并且“述而不作”,可以看出,言说式的口语传播是孔子所倚重的一种传播形式。在当时书写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语言对于信息传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语言传播方面,孔子主张“慎言”的交往观念,这是孔子对于语言传播的深刻认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在先秦时期担负着特殊社会整合沟通功能,在孔子遵循的尊王忠君的先秦社会背景下,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慎言”需要对社会秩序进行反思:语言传播不应对礼制造成冲击,不能造成社会失序,换句话说,慎言的目的在于通过口语传播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社会秩序。而在孔子的观念中,慎言始终是与德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德处于基础和首要的地位,德引领着语言的传播方式和语言内容的选择,以此传播礼乐制度和仁政思想以及达到双方德性情感的互动和交流。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慎言观”对于孔子关注语言的社会传播效果及其作为人际交往媒介具有重要意义,在语言媒介作用下促成传受双方德性情感的交互传播,从而塑造言行合一、具有圣贤人格和德性情感的君子或圣人,以此通过语言传播和情感交往来建构甚至维持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