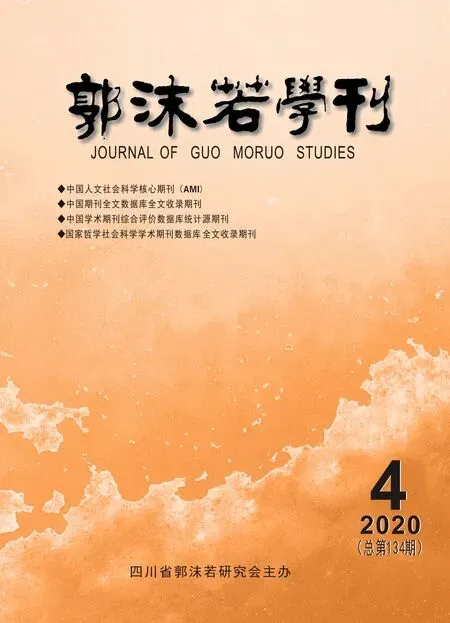小角色 大作为
——《棠棣之花》酒家女形象解读
刘 蓉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作为一种戏剧样式,悲剧是社会生活中悲剧现象的艺术反映。剧作家从悲剧冲突中表现主角的苦难和死亡,以显示作者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评价。①陈瘦竹,沈蔚德:《论喜剧与悲剧》,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9页。《棠棣之花》作为郭沫若先生抗战时期六大历史悲剧之一,以其感人的故事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在我国戏剧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郭老综合《史记·刺客列传》《战国策·韩策(二、三)》《竹书纪年》等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在此基础上加以想象生发,创造出这一经典之作。作品塑造了聂嫈、聂政、酒家女、韩山坚、侠累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形象,其中酒家女春姑一角甚是出彩。长期以来,学界对《棠棣之花》的研究多集中在聂氏姐弟的形象和作品主题的探究上,而对次女主角春姑给予关注的仅有李闰月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利弊与价值缺失》与陈荣阳的《意图与表现的龃龉——郭沫若〈三个叛逆的女性〉新观察》等少数文章,这些文章将春姑与《卓文君》中的红萧与《王昭君》中的毛淑姬放到一起进行分析,而对春姑形象作专门分析的文章则是少之又少,可见学界对春姑形象的分析尚有空白。基于此,笔者试图从三个不同角度对酒家女的形象进行解读。
一、与众不同的叛逆者
作为《棠棣之花》的次女主角,酒家女春姑的身上承载着作者对新人殷切的期盼,她是郭老借以传达新思想新观念的敢于抗争的重要载体。郭老笔下的酒家女首先是一个具有鲜明反叛性的人物。春姑的反叛是全面的,多层次的,其叛逆首先体现在她有新思想。春姑第一次出场是在第二幕《濮阳桥畔》,她与母亲讨论齐国女子改着男装,并大胆抨击孔夫子,要求去读书。春姑与母亲据理力争,她不再认同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她认为女性只有接受了教育才会识廉耻,才能更好地教导子女,而这种教育并非孔夫子的那套传承千年的观念,春姑所说的教育内容是指全新的、与传统不一样的新思想。春姑的身上有着新人渴求知识的品质,而这也正是五四运动所大力提倡的,作者借春姑之口对时代女性发出呼吁,号召女性追求思想上的大胆解放,勇敢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去争取接受新事物的权利。邓颖超同志曾评价郭沫若先生说“他举起锋锐的笔,真理的火,向着中国妇女大众指出光明之路。他吹起号角,敲起警钟,为中国妇女大众高歌着奋斗之曲。”①邓颖超:《为郭沫若先生创作廿五周年纪念与五秩之庆致祝》,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显然,春姑就是郭老吹起的号角。
春姑的叛逆还体现为她敢于追求平等。在与母亲论争女孩子也可以上学求知之时,她以周武王后妃为例,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后妃与普通人家的女儿是没有区别的。这种不将后妃与普通人之女区别对待的态度既是对平等权利的大胆追求,也是对人权的大胆追求,春姑敢于否定皇权,发惊世骇俗之语实质上也更是对传统等级观念的彻底否定。
春姑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不愿意做男人的玩物。在酒馆生意冷清之时,母亲劝她对客人殷勤一点以招揽生意,春姑质问母亲“难道你要叫你的女儿学那些不三不四的娼妓吗?”②郭沫若:《郭沫若戏剧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第287、289、269、288页。春姑认为“男子汉我是最恨的”,她不肯对那些举动“不好看”的客人假以颜色③陈荣阳:《意图与表现的龃龉——郭沫若〈三个叛逆的女性〉新观察》,《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4期。,她向往外面的世界,大胆向母亲喊出心声。春姑不愿一辈子待在男子整日饮酒取乐、女子则谄媚取悦男性的“火坑”濮阳桥。“良禽择佳木而栖”,在春姑看来,生活在濮阳桥这样的地方一辈子只能像娼妓一样依附于男子,而这种失去自我的生活对于春姑来说,是比死更危险的。春姑不服务于男人的反叛姿态是对男权的不屈从和对女子权利的争取,亦是对男女不平等思想发出的强烈不满与抗议。
春姑的叛逆还体现在她大胆追求自由的爱情。当聂政出现在酒馆时,向来不愿意给男人好脸色的春姑主动给聂政斟酒;春姑对聂政芳心暗许,待聂政动身去行刺之时,她又主动赠与聂政桃花并衷心希望对方平安归来。春姑勇敢打破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大胆表露自己的感情,真挚感人。郭老极善于运用极富诗意的语言表达人物情感,在《棠棣之花》中,他穿插引用了《湘累》,春姑对聂政真挚的情感在“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我们从春望到秋,从秋望到夏,望到海枯石烂了!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④郭沫若:《郭沫若戏剧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第287、289、269、288页。的唱词中展露得淋漓尽致。这样坦诚直白地表露感情在当时的人看来无疑是离经叛道的,是为社会所不容的,也正是这种与众不同更彰显其难能可贵。
在《棠棣之花》中,郭老没有将这新思想新观念通过女主角聂嫈传递,而是借由酒家女之口表达出来,反而收到了更明显的效果。我们知道生存环境往往会影响到个人的见识,春姑作为一个清贫的酒家女生活在偏僻之地,却敢于跳出生存环境的限制,勇敢追求平等,勇敢表达爱慕。作为小角色的她身上积聚着进步的思想诉求,较之女主角聂嫈,这种诉求更凸显社会渴望新思想的迫切性,愈加体现郭老思想的强烈性,所以酒家女的叛逆就更显珍贵,故其感染力也就被无限放大开来。
二、义无反顾的追随者
作为叛逆者的酒家女形象已然让读者印象深刻,但郭老似乎并不满足于此,除了赋予春姑大胆的反叛精神之外,还赋予了春姑强烈的正义感,让她成为聂氏姐弟忠诚的追随者。酒家女既追随聂政,也追随聂嫈,她“之所以追随他们,主要是他们身上那种反抗强权的精神”⑤唐敏:《〈三个叛逆的女性〉配角的异质性体现》,《郭沫若学刊》2013年第3期。。与其说春姑追随的是聂氏姐弟,毋宁说她追随的是为民众的“大义”。
素来厌恶男人的酒家女在与聂政第一次见面时,聂政与严仲子的谈话慷慨激昂。聂政直言:“我是把我自己的生命看得和自己身上的任何物品一样,只要用在得当的地方,我随时都可以送人。”⑥郭沫若:《郭沫若戏剧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第287、289、269、288页。这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气概与素日那些“见了姑娘们便要怪眉怪眼,摸手摸脚,一点也不庄重”⑦郭沫若:《郭沫若戏剧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第287、289、269、288页。的男人们形成鲜明对比,二者高下立判。作为一个渴求新思想的人,春姑内心的天平此时无疑是倾向了聂政这边。当听到聂政要凭借一己之力前去刺杀韩相侠累之时,春姑更是为聂政高尚的人格和大无畏的精神所折服,春姑自己作为一个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反叛传统的人,其素日的举止与聂政的选择不谋而合,于是春姑对聂政芳心暗许。这不只是一般青年男女的爱情,春姑倾慕聂政,因为她也是一个纯洁善良“有正义感”的少女,两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⑧陈瘦竹:《现代剧作家散论》,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页。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春姑在思想上选择紧紧追随聂政,在聂政启程后整日为他祈祷,期盼其平安归来。
心理学认为人在欲望得不到满足之时,会将着重点从重要处移向琐细的无关紧要之处,用一种思想代替另一种多少相关的思想。①[美]斯佩克特:《弗洛伊德的美学:艺术研究中的精神分析法》,高建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在得知聂政已经慷慨就义,聂嫈为传播弟弟的英勇行为以大无畏的勇气前往韩城去为弟弟收尸之时,酒家女为其精神感动,将对聂政的倾慕转移到了其姐姐聂嫈的身上。她要求同聂嫈一同前往韩城认尸,她对母亲说“我的心已经许了人了,我就算配不上他,我就替姐姐做个丫头,陪姐姐去死,我也心甘情愿的。”②郭沫若:《郭沫若戏剧全集》(第一卷),第 302、313、305、304页。此时的春姑由先前的追随聂政转而追随聂嫈,在春姑看来,不能盼到聂政平安回来,那去为其收尸不失为另一种精神安慰。春姑在思想上与聂嫈要去认明聂政尸体的想法是契合的,春姑热爱自由的性格,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崇拜英雄的志向,使她毅然和聂嫈一起走上十字街头。③高国平:《“血淋淋的纪念品”——读郭沫若历史剧〈棠棣之花〉》,《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6期。弗洛伊德认为,在认同机制中,自我有时模仿他不爱的人,有时模仿他所爱的人。④[奥]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车文博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二者此时勇敢前往韩城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为烈士敛尸,更是对聂政舍生取义行为的模仿。一方面,酒家女与聂嫈都是聂政的追随者,另一方面,聂嫈此时又是此次行动的领导者,春姑在此时又扮演着聂嫈追随者的角色。
在第五幕十字街头,春姑与聂嫈来到韩城,眼见聂政已经就义,聂嫈痛呼“你姐姐没有你连一刻时候也是不能活在世上的呀!”⑤郭沫若:《郭沫若戏剧全集》(第一卷),第 302、313、305、304页。聂嫈明白弟弟的毁容是为了保护她,但此时她对统治者的深切仇恨让她不愿意苟活,她要抛下一切为弟弟殉死。聂嫈用一种决绝的姿态向社会发出抗议,这一举动深深震撼了春姑,心慕之人的死更是让酒家女伤痛不已,她拔出短剑欲以身殉情。春姑与聂氏姐弟相识甚短,与聂政仅有一面之缘,却为其崇高精神所感动而愿意追随他们慷慨赴死,这也从侧面展示了对聂氏姐弟行为的认同。
聂嫈为亲情、为正义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去追随弟弟的行为深深震撼了读者,但较之于酒家女,其震撼力又有所削减。春姑为仅有一面之缘的聂政倾注了全部的爱恋之情,正是这种强烈而纯粹的爱让她甘愿与聂嫈一同赴义,她深知此次行动的危险性却毫不畏惧,这种大无畏精神比起聂嫈毫不逊色,也正是通过对春姑这种举动的描写,聂氏姐弟行为的强大感染力得到了彰显。可以说,春姑是社会新起力量的化身,春姑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强大张力远超出了郭老对春姑这一形象的配角定位。
三、身先士卒的引领者
仅仅让酒家女作为聂氏姐弟的追随者似乎还不足以完全传达作品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奋起反抗的精神,于是郭老又赋予酒家女以引领者的身份。在聂嫈自杀后,春姑接过聂氏姐弟手中的接力棒,由原先的追随者转而承担起引领者的责任,借由宣传聂氏姐弟的大义精神,春姑引导大家觉醒进而奋起反抗。
酒家女作为最先觉醒的一批人之一,其感召力首先体现在她说服母亲允许自己与聂嫈一同去韩城认尸。春姑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自然不愿意她前去冒险,但她用执着和坚韧感动了母亲,母亲后来转变了看法。在酒家母看来,女儿前去韩城为聂政殉死是高尚的,可以让女儿成为“有名的烈女”,此“烈”是革命烈士之“烈”,而非传统的“贞节”之“烈”。⑥罗雅琳:《危机时刻的美学与政治——以郭沫若历史剧〈棠棣之花〉为中心》,《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她对聂嫈嘱托道:“他假如能够同着你一道死,也是不枉白活了一世,我也乐得人家称赞说:一只野鸡生出了一匹凤凰呢。”⑦郭沫若:《郭沫若戏剧全集》(第一卷),第 302、313、305、304页。酒家母的这种转变与之前要求女儿放下架子去替酒客斟酒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正是春姑的坚定决心让母亲愿意支持她追随聂嫈去完成自己的志向,去成为“一匹凤凰”,去成为捍卫正义的“烈女”。
酒家女的感召力其次体现在感动盲叟祖孙。盲叟与孙女玉儿靠卖唱为生,从韩城带来聂政就义的消息,在目睹春姑欲与聂嫈慷慨赴义之后,盲叟感叹聂嫈与春姑的举止比娥皇女英还要感人。他感慨道:“两位女子一齐要去殉死一位英雄。老人以后就专心唱出这曲歌来,也就可以使我这剩下的残年有点意义了。”⑧郭沫若:《郭沫若戏剧全集》(第一卷),第 302、313、305、304页。正是被聂嫈与春姑的行为所感动,盲叟愿意将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宣扬她们的故事,在这里,盲叟已然成为二位女子的追随者,而春姑引领者的形象也渐趋明朗。
当酒家女提出要为聂政殉情之时,聂嫈对她说“我希望你留着不死,把我兄弟的故事传播出去,使天下后世的人都晓得有我兄弟这样一位英雄,也使天下后世的暴君污吏知道儆戒。”①郭沫若:《郭沫若戏剧全集》(第一卷),第 314、321、322、325页。剧情发展到这里,酒家女接过聂嫈手中的接力棒,其引领者角色已然鲜明。此时的酒家女身上承担着宣扬聂氏姐弟英勇事迹的重任,她要让聂氏姐弟的故事流传开来感染更多的人奋起抗争,于是有了后来春姑向卫士们讲述聂氏姐弟故事的一幕。在被卫士抓住带回受审之时,她告诉卫士们:“你们应该知道:这位英雄正是为国除害,为民除奸,他的死是为的我们大家呀!”②郭沫若:《郭沫若戏剧全集》(第一卷),第 314、321、322、325页。在春姑看来,向群众“介绍一位真正的英雄,原是值得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的”③郭沫若:《郭沫若戏剧全集》(第一卷),第 314、321、322、325页。。只要英雄的故事能够得到传播成为人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个人性命原是不足一提的,能为正义出一份力,生命会变得更有意义。在酒家女的感召下,群众们积极响应,杀死了士长,这群“有良心的人”抬着三位义士的尸首向山上走去。正是在春姑的影响下,群众们觉醒了,他们高唱着“中华需要自由”、“中华需要兄弟,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把主人翁们唤起,快快团结一致,高举起解放的大旗”,让自由之花开遍中华。④郭沫若:《郭沫若戏剧全集》(第一卷),第 314、321、322、325页。他们追随的是死去的三个人,他们继承的是聂氏姐弟与酒家女为正义事业不惜性命的无私精神,酒家女与聂氏姐弟是他们精神上的引领者,是他们奋起抗争的强大动力。
笔者认为春姑后来对聂氏姐弟事迹的宣传不仅仅是受聂嫈所托,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价值认同,正是出于对这种高尚行为的认同,她愿意将其当做人生理想去实现,愿意以一己之力去唤醒更多的群众奋起抗争。她甚至不惜以死明志,其态度之坚决令人惊叹。酒家女以“放逐生命的决然姿态,显示了妇女争取自我解放之路的坚强决心,其抗争的激烈程度符合挣脱现实牢笼的需要”⑤李闰月:《〈三个叛逆的女性〉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利弊与价值缺失》,《淄博师专学报》2019年第1期,第66页。。她的身上有着与聂氏姐弟相同的“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的献身精神,但这种精神在春姑这一配角身上显然更具震撼力。
酒家女春姑以配角姿态向观众传达了郭老对于社会时代的呼求,多重身份的叠加使其在剧中承担起传达作者思想、凸显主人公气质、唤起剧中群众以及现实接受者奋起抗争等作用。每一个角色都会发光,小角色也可以有大作为,正是郭老对这个角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使得这一形象丰满感人。作家常常借角色之酒浇自我心中之块垒,郭老也曾说过他的历史剧是借古人的生命吹嘘一些新的东西进去,酒家女这一形象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作者的意图,是郭老传达“新东西”的极好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