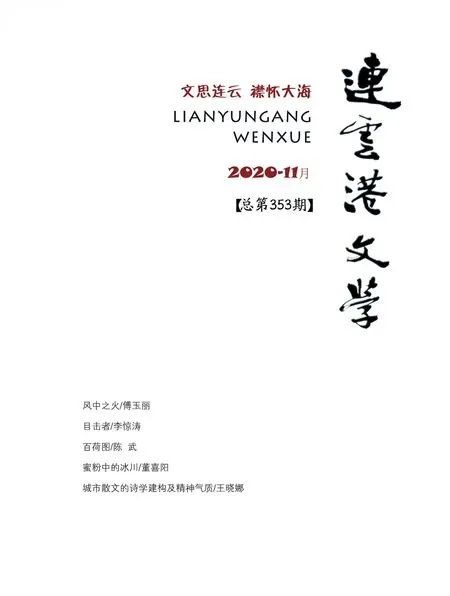孤独的言说
孔灏
读诗
群 羊
一只羊必定是孤独的,而一群羊
更孤独!在呼伦贝尔
我看到一群羊的孤独
加重着白云的分量
远方是大河,是浸润在羊的眼睛里
清亮亮的沉默。风吹草低呵
青草弯下了去年的腰身
羊群按住了牧歌里的大风……
从眼前到天边,从今夜
到明天。谁的流浪被草原遗忘
谁的身影被草尖的露珠
交还给一只羊?
一只羊必定是孤独的,而一群羊
$result = socket_bind($sock,$address,$port)or die(“socket_bind()fail:”.socket_strerror(socket_last_error()).“/n”);
更孤独!在呼伦贝尔
有一只羊平静地看了我一眼
有远方的大河平静地
流逝在我和羊群身边
注:此诗发表于2008 年《诗刊》,并入选2008 年中国年度最佳诗选和2009 年第17期《新华文摘》等。
孤独的言说
亚里士多德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这句话,还有另外一种译法,即亚里士多德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圣贤。神灵也罢,圣贤也罢,讲的应该都是同一个意思:抛开了人身上的动物性之后,孤独,必然与人在精神上的超越密切相关!
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看来,孤独,不仅仅是人类追求精神上的超越所要必经的某种状态,更让他们念兹在兹的是:孤独,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在其《飨宴》里写到:太古之时,人类都有两副面孔,两对眼睛,两个鼻子,两对耳朵,两张嘴,四只手,四条腿,四只脚……身体强壮,行动有力。于是,人类的优势不断壮大,甚而对天上的诸神都形成了威胁。这样一来,众神之王宙斯经与众神商定,将人类截开一分为二,并分别置于不同的地方意图使他们永远不再相见。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被劈开成两半的一个不完整的个体,他们都终其一生在寻找着自己的另一半;也所以,当两个自认为找对了的人相爱之后,会拥抱在一起不停的挤压,想要进入对方的身体再合二为一,这是人做爱的原因,更是人想要找回自己的方式。这样,人和人的相爱,可真的不是两个个体的人之间的私事了,而是整个人类回归本来的族群之大事!然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被一分为二地劈开的,数量太多了,相距太远了,他们之中的有些人能够顺利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有些人,终其一生,也不能够!所以,柏拉图的寓言最终想要说明的是:孤独,是人类的本质。
中国古代哲学家里,讲“孤独”讲得最通透者,莫过于庄子。说起来,他应该是中国古代最孤独的哲学家了!纵观《庄子》一书,他好像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惠施。而且,其实这位“朋友”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是他的论敌。他太挑剔了!你看,他对朋友的要求可有多高啊: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庄子·大宗师》)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个人在一起聊天说:“谁能够把无当作头,把生当作脊柱,把死当作尾椎,谁是能够通晓生死存亡本是一个整体的人,我们就可以跟他交朋友。”然后,这四个人都相视而笑,心心相印,于是相互之间成了朋友。
庄子这是讲,做朋友首先要在理念上“三观”相合。这还不够!在行为上,庄子又有自己的标准。再看: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穷终!”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庄子·大宗师》)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个人在相交为朋友时说:“谁能够相互交往于不相互交往之中,相互帮助于没有帮助一样?谁能登上高天巡游雾里,于无边的境地里回旋,忘掉了生之为生,而永远没有终结和穷尽?”然后,这三人相视而笑,心心相印,于是相互结成好友。
与庄子交友,须当如此方可!我说亲爱的庄子哥哥呵,叫你怎能不孤独?不过,我所说的孤独,在庄子看来,也许不值一说,更加算不上孤独!庄子哥哥一定会这样想:既然人和万物皆从大道中来,所以每个人都是和万物完全不同的自己,那么,为什么不让这个独特的自己率性成长?同理,既然人和万物皆从大道中来,所以每个人都是和万物共为一体,那么,为什么不让这个独特的自己率性成长?同样的意思,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中是这样一句诗:
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
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唯其如此,这样的“孤独”,才有力量,也有意义!于庄子自己而言,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是“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哪怕是过了一万代之后才遇到一个知音,那也没啥,这个时间上的差距不也好像是早晚相见一样吗?也唯其如此,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才有理由;李白《独坐敬亭山》时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才有深情;柳宗元面对江雪时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才有意蕴!
十多年前,承《连云港日报》副刊部主任杨帆老师青目,让我在日报“花果山副刊”刊载过一年时间的摄影配诗。其中《群羊》一诗,即是为了彭朋先生的一幅摄于呼伦贝尔的图片所作。后来,这首诗发表于《诗刊》,并入选了当年的年度最佳诗选和次年的《新华文摘》,得到了国内一些诗歌界朋友的认可。写完此诗十余年后,我去了新疆,有位新疆诗人对我说:希望新疆的草原,给你如呼伦贝尔草原一样的灵感。我说,写《群羊》时我并没有去过呼伦贝尔。他听了之后,有点怅然。我知道,我能懂得他的怅然,我也知道,我说不清楚他的怅然。那,也像是一种孤独感吧。
就像,就像我懂得一只羊的孤独,是的!那种感觉,就像我懂得一只羊的孤独。
一只羊必定是孤独的。而一群羊,更孤独!一群羊的孤独,也是白云的孤独,也是大河的孤独,也是风的孤独,也是露珠的孤独,也是草原的孤独……也是,我的孤独。如果,如果你刚刚看到了这首诗,或这篇文字,那么我知道:这些孤独,也都是你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