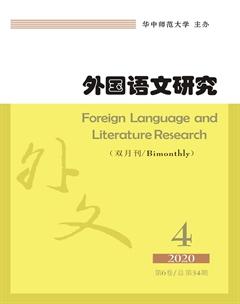“理论”背后的诗意人生:陈永国教授访谈录
刘芳 陈永国
內容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的研究热情一直居高不下。作为国内译介和研究西方文论的先驱者之一,陈永国教授丰富的著述和理论译作为中国学者的文学研究道路拓宽了视野,其对理论研究的坚持、对文学批评的深思和对诗歌创作的热忱同样格外引人注目,发人深省。为深化学界对西方文论研究以及其与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关系的理解,促进对当下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的思考,这次访谈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首先,陈教授回顾了自己早期的学术经历,分享了自己对文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心得,并谈论了对文论的跨学科性质和中国学者“失语”问题的看法。然后,陈教授对其基于当下的文学研究现状而提出的文学生态阅读、文艺的社会科学等概念做了说明,就诗歌鉴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最后,结合自身诗歌创作的感悟,陈教授探讨了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割裂的常态现象,并勉励青年研究者以兴趣为引领,坚持前行。
关键词:陈永国;西方文论;诗歌创作;生态阅读;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CCNU19TD016)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美国现当代小说中城郊书写研究”(项目编号:CCNU20A06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芳,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和美国文学的研究。陈永国,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翻译理论和外国文学。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Chinese academia. A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translating and studying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Professor Chen Yongguo has helped Chinese scholars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by his research articles and translation of numerous theoretical works.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s impossible without his persistence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passion for poetry writing and insights into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interview aims to unveil the approach to literary theorie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 between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and creation, and to facilitate reflections on current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interview, Prof. Chen first shared his gains about literary theory studies while reviewing his early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talked about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literary studies and Chinese scholars “aphasia”. Professor. Chen then elucidate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reading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ed the future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ience, and talked about his thoughts about poetry appreciation. Finally, Professor. Chen commented on the disparity betwee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reation based on his own poetry writing, and encouraged young scholars to cultivate their own interest and pursue literary studies with perseverance.
Key words: Chen Yongguo;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poetry creation; ecological reading; social sciences
Authors: Liu F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carmenliu@126.com. Chen Yongguo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t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His recent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iterature. E-mail: chenyg@mail.tsinghua.edu.cn
一、西方文论与我的学术之路
刘芳(以下简称刘):陈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我的访谈邀请。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您就一直在外国文学研究这个领域里耕耘,而且是译介和研究西方文论的先驱者之一。您能否谈一谈中国的文学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是怎样一种状态?您是如何走上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道路的?
陈永国(以下简称陈):这次访谈被耽搁了很久,本该在疫情之前就完成的。疫情不仅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还开始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往大里说,如何对待疫情之后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往小里说,如何对待我们今天这样的采访?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重新审视。说心里话,我对这次采访思考了很久,首先是我不想随便应付一下了事,同時更不想把它变成一种“名人秀”或“权威话语”。
我从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从字母开始学习英语。四年后主动支援边疆去了拉萨的西藏师范学院(现西藏大学),开始教英语。1982年回到吉林大学继续从教,一点一滴地从非常有限的英美文学阅读中接触到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那时候,正值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绝大部分人(专业和非专业的学外语的学生和年轻教师)都把精力放在语言应用上,力主经济商业往来方面的交往,很多人乘经济改革之风下了海,很少有人喜欢“不赚钱的”文学和理论研究。而且,由于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相关方面的书籍和阅读资料也并不多,直到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等连续出版了“美学译文丛书”、“文艺美学丛书”、“当代中国美学思想研究丛书”等,才算真正接触到偏重美学的西方理论译著。而就我个人而言,真正开始阅读西方文学理论及相关领域的原著,还是从1990年去佛罗里达大学访学开始的。
刘:对比您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习条件,当下中国学者开拓学术视野的途径非常多,但对很多人而言,文论研究仍是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除了语言障碍带来的困难,还因为现当代文论既有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有明显的跨学科性,与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这些知识构架如果薄弱,就造成了更大的研究障碍。您在学术成长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能否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心得?
陈:文学理论确实很难,是典型的跨学科领域,涉及到你提到的和没提到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的认知。不仅涉及各方知识的交叉和融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种建基于感性的文学阅读经验之上的理性思维和分析能力,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精力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切不可急于求成。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书也要一本一本地读。
我个人的理论之路开始于文学的爱好和对不同文化的接触。最早开始的文学阅读和翻译还是在拉萨期间(1979-1982),曾为当时的《西藏文艺》翻译过包括叶芝在内的一些英美现代诗歌,同时为西藏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翻译过关于西藏的民族文化、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农奴制度等三种书籍(内部出版),虽然这几部书的内容与文学相对较远,但从文化认知和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却开启了我持续至今的另一条学习道路,即翻译,也拓宽了我对文化的了解,加深了对人本身的认识。回想起来,在拉萨的三年是我青年时代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表面看起来似乎与现在的我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对于一个来自大东北乡村的青年来说,接触西藏文化、与藏族人民共饮青稞酒、同跳踢踏舞,这是我当时接触到的除东北乡土文化、大学里的所谓“学术”文化之外的第三种文化,除了我所熟悉的朴实、豪放之外,藏族人民特有的情感结构和忠厚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再经过我在翻译相关书籍时对藏族文化的精神内化,这对我后来对西方文学的理解和对理论的接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因为无论是文学的理解还是理论的阐释,都离不开对人自身、对物自身、对世界自身的理解。恰恰是一些看似不相关的知识和思考,能够帮助提高自己认识世界、认识人的能力,所涉及的不是学科领域内的知识,而是一种综合性思维方式的形成。
刘:我大致统计了一下,您在西方学术思想的译介方面发表的各类书籍有近40部,很多都是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您在介绍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在选择书目时,有着怎样的学术考量?
陈:如果加上合作的译著,四十部肯定是一个保守的数字。但是,我早期翻译的理论著述其实并不成体系,虽然数量较大,但谈不上重要贡献。回想起来,早期翻译的一些著述确实像有些人所批评的,非常粗糙,基本上是应出版之需和急于发表而作,并无明确的学术考量。与当时(甚或现在)的一些年轻学子一样,能够得到出版者的青睐或老一辈学者的器重,能在有限的学术发表资源中分一杯羹就已经是福星高照了,还去管什么体系。但对于我而言,还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除非是文学以及相关领域的著述,其他领域(如经济、商业、旅游等)概不涉及。总结起来,我所译著述的学科领域大约包括:文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史、思想史等。在这些著述的翻译方面,尤其在入门阶段,我参加过王逢振老师、刘象愚老师、罗钢老师、申丹老师以及汪民安教授主编的系列书籍,这些是基础的基础,为我后来自己主编或参与主编的书籍框定了范围。
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有什么学术(其实我非常不愿意用“学术”这个词)成长途径的话,那就是翻译。尽管所译看起来零零碎碎,不成体系,但一旦达到一定的量,在翻译过程中所细化和内化的东西就会自行组合,按其学科分类进入大脑中的不同储存库,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的库存也会越来越多,构成一个可随手使用的百宝箱,虽然残破不全,但用于“修修补补”还是很有效用的。
刘: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些虽然是陈老师的个人经历,却同样是那个“理论热”的时代的写照。从宏观上来看,那一段时间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并非是盲目的,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去译介、引进和调用一些西方理论资源,以便更好地阐释全新的文化现实。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大家实际上参与、推动和见证了这一实则功在千秋的事业。您曾经提出用话语(discourse)代替理论(theory),理论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创一种话语形式。①您认为当今的青年学者在介绍和研究西方文论的时候,应该关注哪些问题,采用怎样的态度来建构中国的“话语形式”?
陈:的确如此。中国学者的译介确实不是盲目的。首先,所译介的都是国内短缺的,这是供需关系。其次,多年来,西方理论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总是有新思潮出现,必须及时译介,否则无法参与讨论,争不到话语权,也就没有参与讨论的资格。但是,理论跟风的现象也是有的,尤其是欧陆理论经过美国人的改造,顺道被拐进了中国,有很多是打了折扣的,所以,不负责任的跟风给我们国内的译介和研究设置了障碍,甚至导致了“失语”。其实,所谓的“失语”并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错误的理解、错误的接受,有些“学者”为了打快拳,甚至不读原文,不读全书,见书名、目录便随即望文生义,致使在真正参与国际对话时,各说各话,驴唇不对马嘴。我们都有说话的能力,都能表达思想,但说什么话,表达什么思想,在不在一个轨道上,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文论而言,并不存在“西方文论家”或“东方文论家”之别。我们谈论的文论是世界性的,西方文论、中国文论、各个国别文论,本应是一家,既然文学是没有国籍的,关于文学的理论也就同样没有国籍。更何况文论是思想史的基础,我们利用相似性和差异性来区别文化的异同,人种的异同,国族的异同,但文学归根结底是以人、人性和人的生活为对象的,不管异同多大,最终关于文学的话语、关于人性的话语,都应该是一致的,它所构成的是人类的思想宝库。我们可以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讨论国别文学的理论,但理论始终是理论,是关于某一命题、母题或主题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以话语的形式进入思想史。所以我并不赞成建构所谓的中国的话语形式。我们可以说自己的话,讲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但就文学话语而言,最终应属于世界文学。
二、文学阅读与批评的哲思
刘: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文化和学术语境总在不断改变,对理论的探讨要始终立足于当下的变化和问题,要用新的理论视角来践行我们的文学批评。您在这方面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比如您在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提到“文艺的社会科学”②。刚看到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学艺术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想象性再现,文艺研究必然关注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其次,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汲取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您提出的“文艺的社会科学”似乎并不是上述的文学社会学批评,也不是简单的文学研究与社会学的交叉。您能否谈一谈这个概念?
陈: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谈。首先文学本身属于人文学科,因此自然离不开哲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但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和反映论而言,文学是给社会照的一面镜子,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反映到文学文本中来。就19世纪中叶以来的整体社会发展来看,我们先后经历了三个时代。首先是马克思本人所生活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这个时期典型的特征之一体现为金钱对人性的扭曲,文学艺术则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接着我们转向本雅明所生活的资本主义工业高度发展时期,其重要特征是技术官僚对真理的遮蔽,文学艺术则趋向于机械复制,导致原作光晕的喪失。随之进而转向当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数控时代,信息符号导致了语言的沉默,即对语言自身的遮蔽,文学艺术则趋向于生物控制式的复制,智能、克隆、机器翻译、机器写作等。
实际上,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社会已经不是文学艺术理论所侈谈的那种解构,而恰恰是其反面,即空前高度的结构化,人正经受着史无前例的技术控制,而一旦人工智能真的取代了人类大脑、机器翻译和写作取代了人工翻译和写作,那么现行的理论视角,即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等一系列视角批评还能行之有效吗?这就是我所说的文艺的社会科学批评的另一方面,即从社会发展的技术层面思考人自身的未来,进而思考文学艺术的命运。其实这种思考在马克思那里、甚至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被过多的传统、过多的意识形态、过多的主义所淹没。所谓的文艺的社会科学无非就是从当下的技术控制来思考当下的文艺,进而回归人的科学自身,如果还有这个可能的话。
刘:从2013年以来,您以“阅读”为题发表了数篇论文,从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文学阅读和批评。③在2018年,您在不同场合都提到“阅读的生态”和“生态的阅读”。这两个概念似乎与生态批评密切相关,与当下的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有关,这种理解是否正确?
陈:所谓阅读的生态或生态的阅读不外乎指文学批评的一块清净之地。文学和作品本身是干净无瑕的。但多年的“理论热”把文学这块净土变成了各种主义的竞技场,变成了理论的兵家必争之地。任何一种文学的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被事先框定某种“视角”或“框架”,或被想方设法引入某种“主义”的歧途,这直接违背了文学和批评的本质,即批评必须自文学的文本阅读而来,而非相反。因此,文学的生态阅读简单说就是祛除各种先知先觉的理论的阅读,不是戴着理论的有色眼镜的阅读,而是回归文本本体的阅读。
刘:您曾经也提出“阅读中包含着可读性和不可读性、可译性和不可译性”④,这句话是否包含了您对作者、读者、文本和世界的关系的思考?文学批评者如何对待您所提到的可读性等?
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说,按照本雅明的观点,可读性就是可译性,指的是语言之间可以互译互通的部分;而不可读性通常也是不可译性(但不可译性并非不可读性)指的是语言之间不可互译的部分,称之为纯语言。纯语言也是诗歌语言。朱光潜先生说读译诗就是读诗,其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意即:诗歌是不可译的;翻译的诗是诗,也就是用译入语写的诗,因此已经不是原文的诗了。严格说来,文学批评所要关注的恰恰是这部分。一般而言,上面括弧中所说的不可译性并非不可读性,指的就是语言中不可互译者,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读。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即:可言者,言;不可言者,沉默;或:可言者,言;不可言者,展示。对于艺术家或诗人来说,沉默或展示的方式各有不同,这或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象、图像、隐喻等,或空白、删节甚至破折号(如狄金森的诗),甚或是颜色的涂抹、抽象的图案或重拾的物品。对这种不可读性或不可译性的读解只能是读者与诗人或艺术家的一种心灵契合,也即瞬间发生的灵魂震颤,而绝不是事先规定好的各种“视角式”批评。
刘:相对于小说和戏剧,我觉得诗歌的鉴赏尤其难,特别符合您说的不可译性和不可读性。一般来说,我们会从诗歌这个文类的基本元素入手,结合文学流派的知识和运用文学批评方法来解读。您在诗歌批评方面更多地思考什么?
陈:诗歌的确与小说和戏剧不同,因此对其阅读和阐释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就文学总体而言,其区别于视觉艺术的最大特征是语言再现,因此就文学内部的要素而言,语言才是形式和内容本身。在我看来,诗歌最大的特点是形象的完整性和语言的破碎性。形象的完整性体现在意象的应用。一个完整的形象可能会以不同的意象表现出来,以便讲述一个故事,或揭示一个主题。但语言却不是完整的,拆解的句式,零碎的短语,不连贯的断片,要想读懂一首诗,首先必得把这些破碎的语言残片贯穿起来,使其与意象达成逻辑关联,才能看到诗的思想和情感所在。一首诗与一幅画一样,写在纸页上的文字只是出现在画框之内的画面,它由各种色彩、线条、形状构成。但画的真实含义或许不在画框之内,而在画框之外,就如同诗的真意不在所说出的言语之中,而在未表达的沉默之中,在文字间的空白之中。这就是之所以字面意义不能读作诗之真意的原因之所在。
三、作为自我表达的诗歌创作
刘:据我所知,您在从事文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之余,同样还进行诗歌创作,并出版了三部诗集。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的诗歌创作?
陈:写作诗歌是中学时代起就有的爱好。大概是由于少年时阅读了许多古诗、古文所致。学了英文后,业余时间也尝试译一些英文诗,但没有发表。遗憾的是,我既不是文学理论家,也不是诗人。我写过一些文学批评和讨论西方理论的文章,但大多是介绍,很少有阐述自己独到的观点的。我一向觉得,对于理论这东西,只要能说清楚了,也就不错了。我多年来坚持的译法基本是直译,力主保持原文的风格和原意,初译时尤其如此。后来学会了拆解长句,表达略微顺畅,但也不敢苟且转译,所以读来还是略显生硬。但无论如何,我自觉吃透了原文的思想,长年累月的积淀以及对诸种理论的深入认知,使我感到一个文学批评者和译介者,如果自己不懂如何写作,就难以谈论写作;如果自己没有创作的经验,就没有资格对别人的创作说长论短。于是,就在译介和讨论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尝试诗歌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之后,再拿起笔来书写文学问题,觉得很多问题自然通畅了,比如诗歌写作中的情感宣泄问题、思想深度问题、文字与图画的关系问题,以及现行文学理论所讨论的身份、族裔、性别等问题,其实在诗歌写作之时几乎是零度,也就是说,都是后来读者或批评者读出来的。诗歌和其他艺术一样,重要的是一种吸引,一种唤起,一种要说话的冲动。思想也好,情感也好,艺术中的一切都扎根于坚实的大地,而大地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就是你周围被人忘记、被人忽视但却依然快活地或悲伤地存在的那些事与物。一旦它们吸引了你,你就有话要说,有欲望要表达,有快乐或悲伤要分享。一件简单的物或极其平凡的事就会唤起无数的联想,导致无数的可能性,从中你会发现你自己,以及你自己所寻找的,所追求的,所要说的。对于我,这是人生的真谛。
刘:我认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创作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三者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又互促共生。您能否谈一谈您的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您会有意识地遵循文学原则来创作诗歌吗?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陈:独立和互动是非常恰当的描述。但我只能说写诗的過程是认知的过程。没有哪个诗人会在诗歌理论的指导下去写诗,除非那些所谓的实验派。如前面说过的,一物的吸引令你产生写作的欲望,你要发泄这股力比多,在一定的互文状态下和思想与情感的召唤之中,你挥笔成诗,达成对该物的认知,欲望得以满足。
就自己而言,我从不字句斟酌,大幅度修改,充其量事后对个别字句细究一番,免生笑话,仅此而已。就写作而论,过程是重要的,结果并不重要,因为我并不是为了读者而写,也不是为了发表而写,只是表达一下当时当地的心境而已。况且,我不认为刻意遵照某项原则或原理去写,会写出好诗来。译诗也是同样。不论原诗多好,经过译写之后,它依然是译诗;读者读的是诗,但却是以译诗身份出现的诗。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关于文学/诗歌的研究与写诗并不冲突,虽然不受理论的指导和干扰,但思想和情感的深度或学识的渊博或短浅,却可以直接决定创作的深度和广度。
刘:大部分理论家和批评家热衷于阐释文学现象和作品,高屋建瓴地探讨文学问题,但并不从事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批评实践和文学创作似乎被割裂开,您认为这是否是在当今中国文学研究者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陈: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我在译介和理论研究方面用力比较多,这在那个“理论”相对匮乏的时期有着重要的意义。我的大半学术生涯都致力于理论译著,直到最近十年左右,我开始自己的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写作。但这不意味着理论没有用了,也不说明我放弃理论的译介和评著,最近我还收到了达姆罗什的一部关于文学之比较研究的新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买了版权,并已开始翻译。我对理论和翻译的热情有增无减。但是,如果一个人把一生都献给了译介和评论,而不去走一走对自己来说最能发现自我的路径,也会是件很遗憾的事。
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割裂是常态,也是必然。单纯从事批评和理论研究同样会很出色,很优秀,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眼界放宽一些,看一看我们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文学家,比如伍尔夫、艾略特、叶芝、雪莱,甚或但丁、彼得拉克、贺拉斯等,更或如哲学领域的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他们之所以思想深邃,人生理解入微,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认知独到,既能理性地探知,又能感性地体味,是直接从事创作的思想者。我不认为每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都可以是作家,但我以为尝试一下肯定是有益的。
刘:最后,对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以及从事文学教育的青年教师,您能否谈谈您的期待和建议?
陈:我其实只是停不下来。谈不上贡献,更不能说是什么楷模。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方向,并发生了兴趣,那就随心去做,尽力去做,能否修成正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我想对青年学者所说的,是为共勉。
刘:非常感谢陈老师在全球疫情肆虐的特殊时期接受这次访谈!
注释【Notes】
①参见聂珍钊、吴笛、陈永国,“外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前沿问题”三人谈,《山东外语教学》3(2018):70-77。
②参见陈永国,经济、技术和数字:文艺研究中交叉的社会科学视角,《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020):108-118。
③有关的论述请参见陈永国,阅读的意义和阅读的艺术,《外文研究》6(2013):43-49;陈永国,再现不再:只为阅读的写作,《文艺研究》5(2017):5-17;陈永国,回归物本体的生态阅读,《江西社会科学》1(2020):150-156。
④参见陈永国,再现不再:只为阅读的写作,《文艺研究》5(2017):5-17。
责任编辑:何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