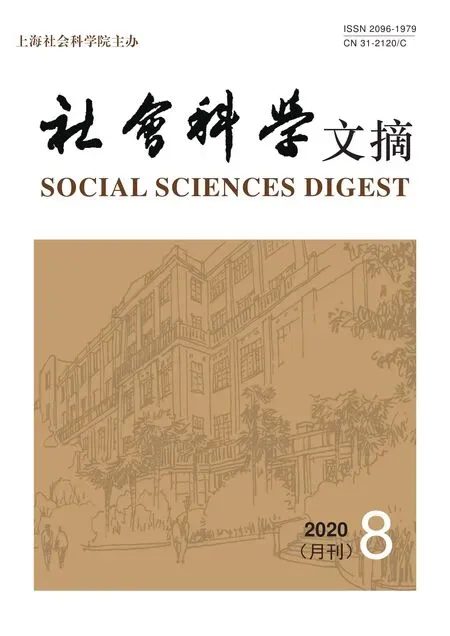大成若缺
——中国传统艺术哲学中的“当下圆满”学说
文/朱良志
大成若缺,是老子哲学的名言,后来成为传统艺术创造的一条定则。最圆满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残缺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强调在当下直接的生命体验中,超越残缺与圆满相对的知识见解,从而达到处处圆满、无所欠缺的境界。
显然,“大成若缺”的核心意涵不是重视“残缺美”,不同于西方美学由断臂维纳斯引发的关于残缺美的讨论。它认为任何奠定于知识基础之上的“大成”——圆满——都是残缺,不存在一种知识分别之下的圆满之美。圆满只有在超越残缺与圆满相对性见解前提下,于当下直接的生命体验中实现。传统艺术哲学将此称为“随处圆满、无少欠缺”。传统艺术以其支离、萧疏、残缺、破碎等形式创造,打破部分与全体、狭小与广大、破碎与整全等相对性知识计量,创造出世界上殊为独特的艺术面貌。“大成若缺”,是老子哲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传统中国艺术创造的一条定律。
传统艺术哲学认为,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每一个生命存在都是自足圆满的,都是大全世界。当下即是圆满,小中可以现大,不在于体量上的扩大、声色上的圆满、构造上的圆熟,而重在心性的推展,只有归复生命的真性,在直接的生命体验中,才能有真正的圆满俱足。万物皆备于我,若胶着在知识或目的性的控制上,世界万物永远不可能“备”于你,永远不可能有“圆满”,所以,“大成”于“不成”——残缺——中得之。
支离与大全
支离,是唐宋以来艺术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对它的重视,显示出中国艺术发展中的一些重要倾向。
这个概念由庄子提出。在庄子的哲学系统中,支离,是与“全”——整体性——相对的。它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支离其形,散漫无章,无法拼合,构不成整体,因而它不是整体中的部分。我们说一个存在,总是在某个整体中的存在,由整体存在方使此存在获得秩序。而支离,就是铲除这样的秩序,打破常规,斩断人们“完型”的冲动。如支离疏,“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云云,超越了人们关于人的整体性的认知。第二,因无整体的归属,存在的意义只能从自身获得。支离,就是互不隶属,所谓“四支离析”,各各自在,互不关联。如果我们由整体角度去看,它们是零散的;由一个“完全”的视角去审视,它是凌乱的。我们说它不合某种规矩,而无“理”;说它不合美的准则,而露出“丑”,由此剥夺它的存在意义。第三,是它的无目的性,支离其形,如散木不能做桌子而为人所用,不能打造成车轮用于交通,无法被利用,因而被弃置,进而逃脱人间戕害,得以终其天年,因其不“全”,故而能“全”其生命也。
庄子假托一个人的“支离其形”,来说“支离其德”的道理。支离其形,是他所说的堕肢体;支离其德,就是他所说的黜聪明,也即老子所说的“上德不德”。以支离的方式,撕开知识和秩序的面纱,直面生命本身,建立生命新秩序。部分与整体、支离和大全,这种相对性的思维,是知识的见解。支离与整体相对而论,但不意味庄子强调的是部分,他的主要意思在突破整体和部分相互依存的关系,撕裂知识的罗网,如禅宗所说的,做一条“透网之鳞”——游出鱼网的小鱼,自然而然地优游。庄子“相忘于江湖”的哲学,就是这支离。
“支离”思想深刻的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道路。唐宋以来艺术的发展,在形式构造上,一变汉魏以来的传统,体量的追求、形势的营造、秩序的谨守、绚烂色彩的渲染,到了中唐以后,渐渐被一种超越秩序、小中见大、平淡悠远、支离萧疏的创造理想所碾压,如果不是被取代的话。艺术开始走上一条知白守黑的道路,水墨的出现就是典型表征,以无色而具五色之绚烂的思想基础正是这种“支离”哲学。文人艺术重视“以曲求全”的智慧,园林中曲径通幽的形式创造中,就潜藏着超越对称、打破秩序的思想根源,绘画中枯木寒林的流行,也与此一观念有关。
艺术是需要法则的,而支离的重要特点是脱略秩序、淡化人工痕迹,在无法中得天地之大法、之大全。中国艺术重视“散”的境界。萧散,是对人工秩序的背离,它与庄子的“支离”思想密切相关。庄子给支离起了个名字叫“疏”,所谓支离疏,传统艺术推崇“萧疏”境界,“萧疏”与“萧散”意近,都强调脱略秩序、在不全中追求大全。疏,有解意,所谓“疏解”。支离疏举一把剑器,解开知识扭结,与外在声利世界划出一条鸿沟。疏,也含有“通”意,所谓“疏通”。所谓路明寒月在,山静宿云收,萧疏中有一条通往真实世界的大道。
残缺与圆满
支离,重在非联系性,各各自在,不在整体中追求意义。而残缺,虽然也是不全,也具有非整体特点,然其重点则在构成的不完整上,习惯中我们认为一个物体存在该有的部分,缺失了,如缺月挂疏桐,就是一种残缺,又如印章线条和边际的残损等。
残缺,在中国艺术的形式构造中具有很高位置。老子说,“大成若缺”——最高的圆满是残缺的。印家话,“与其叠,毋宁缺”——与其重重叠叠,左旋右转,线条允宜,整饬充满,还不如断其线,蚀其面,如水冲岸,如虫食叶,缺处就是全处,断时即是连时。
中国人对残缺美感的斟酌,极易使人想到西方美学中有关残缺美的欣赏。古希腊的断臂维纳斯,就是残缺美的典型。有人认为,这比身体完整的维纳斯更美,人们在其断臂中,想到完整的手臂,产生一种视觉压强,由此激发更强烈的审美冲动。但如果这样理解中国审美观念上对残缺美的追求,就有些南辕北辙了。这不是形式美感的斟酌。我们常说动人春色不须多,花开十分不算好,需要减一点,损一点,这与重视残缺的思想倾向了无关系。这种大成若缺的观念,体现了传统艺术哲学的重要倾向——对知识的超越,突破残缺与圆满的斟酌,从长短高下、圆满残缺的外在形式走向内在的生命体验中,如九方皋相马,在骊黄牝牡之外,去追求它的真精神。重残缺,是为了破追求圆满的妄念,破秩序计较的迷思。
我们说缺,或者意味数量上的欠缺、标准上的不足、形式构成上的不完满,残缺的基本特征是不完满、不圆融、不全面、不规则。因此,我们说残缺,就意味着先行有一个完全的、完满的、完美的、完整的“原型”存在;就意味着对某种秩序的认同。我们从某种秩序出发,去绳之律之,从而分出高下、美丑,残缺和圆满的种种斟酌,是分别的见解。如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矣,斯恶已”——天下人都知道美的东西是美的时候,就显示出丑来了。美丑是一种知识的见解,是某种秩序、标准的产物。残缺和圆满的思虑也是如此。
传统艺术哲学有“随处圆满,无少欠缺”的定则,核心意思就是超越残缺和圆满的妄念。它认为,从当下直接的生命体验出发,就是俱足的、周备的,没有需要补充的东西,没有什么缺憾。意义不须由外灌注,动能不需填补。当下体验,就是意义的实现,它是天之足。自己是当下境界的唯一成就者。一句话,从真实体验出发的生命创造,并没有残缺。
破碎与浑一
破碎和浑一,是一对矛盾,传统艺术哲学追求浑一的境界,但并非以浑然一体为最高审美理想,更不意味躲避细碎。这里有值得注意的两种理论主张:
(一)超越浑一与破碎的分别。老子的“大制不割”观念,其立意在以浑一的智慧,做分别的文章,但并不意味他反对分别、分散。《老子》第二十八章云:“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老子的守道抱一,不是要守住浑然不分的状态。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之以为利,有之以为用,有与无不可偏废。以无作有的文章,以有呈现无的真实。所以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徼,同皎,明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就是“散”,万物都是“道”(或“无”)的皎然呈现,万物(器),都由真朴散而使之成。所以,道是浑一的,但不能不分,不能不说散,不能不说一而二、二而三的滋生万有的过程。道是无为的,但不能不说作,说有为。所以,有为、分别、分割、分散、细碎,都是必然的。天下的雌与雄(由生物特性上说)、白与黑(由色相上说)、荣与辱(由价值上说),都是说“割”,说“分”,说“有”。所以老子的“大制不割”,又可以说是“大制若割”,也就是以“不割”的智慧做“割”的文章。
在老子大制不割中,有两种不同的“浑”,一是作为无分别智慧的浑,一是作为与“散”相对的形式之浑然。老子绝非推崇浑然未分的原初形式。其根本旨归,是以浑一的智慧,去超越作为知识的浑、散分别。理解老子此一思想精髓,对把握中国艺术的精神极为重要。
清李修易说:“发端混仑,逐渐破碎,收拾破碎,复归混仑。”这是以混仑的原则,做破碎的文章,此正是老子“大制不割”说的正解。
(二)生辣中求破碎之相。在浑一哲学影响下,中国艺术特别推重浑然一体的整体感,这几乎成为传统艺术的定则,诗文中的整体回荡之势,书法的笔势说,以“书写性”为基础的绘画的笔情墨趣,如追求一笔书、一笔画的美感,都是这种整体性的体现。浑一整体,是建立在联系基础上的,强调形式内部的流动回环,重视由整体性所导致的激荡和变化。这些激荡和变化都是由联系所构成的,没有联系,就没有“势”。“浑然一体”,是对达到很高艺术水平的描述,是对一种潜在秩序的肯定。
然而,正是整体性的追求,对联系性的痴迷,使艺术滑入一种定则和平衡之中。它不是形式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心灵的忸怩作态所造成的。由此,传统艺术论中出现一种刻意追求破碎、通过破碎来破浑一之弊的倾向。
南宋词人张炎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这一评论在后代传为佳谈,其中包含重要的道理。张炎所指出的,正是梦窗词过于追求整体的流弊,虽整体看来颇佳,然典实过多,用语晦涩,雕刻痕迹历历在目,看似浑成,实则细碎质实,失清空流动之韵,既陷细碎,又未达浑成。
重破碎,是对此浑一整饬秩序的回避,对秩序的消解。《艺概·书概》云:“孙过庭草书在唐为善宗晋法,其所书《书谱》,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刘熙载对《书谱》书法之论,极为贴切,其笔多破,而气愈浑,于破碎中见周章,气韵流动不在形,而在内在的势,在贯通一气的内脉。
黄公望之画几乎就是“浑沦”二字的代名词,世人以“浑厚华滋”评之,但不能想当然认为,他的画是一片浑沦,恰恰相反,他的画往往于细碎缺断处用力,碎处就是全处,分处亦是合处,此为大痴画最难及处。
局促与自足
局促与自足也是一对概念,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万物皆备于我”的理论与此有关。
心性的推展,是宋元以来艺术发展中的重要倾向,重视内觉的艺术将心性的拓展作为其秘器。宋元以来中国艺术的内倾化越发明显,艺术越来越重视内觉的智慧,而非留恋于外在形式上的描摹。在形式构造上,不少艺术家一方面尽量简化形式,压缩空间,淡去声色,有意创造一种局促、偏狭的世界,刻意渲染外在世界对人存在空间的威逼。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从中转出一种从容回荡、优游徘徊的精神,于偏狭中见广大,由逼仄中出圆融,由此成就“万物皆备于我”的心灵境界。
道家哲学,是艺术哲学中此类“备物”思想的直接源头。《庄子》将“备物”与对美的把握联系在一起讨论。《天下》篇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这段话从对美把握的角度,谈如何“该”“遍”,也就是如何备于物的问题。这里有两种对美的感知方式,一是“备于天地之美”,一是“判天地之美”。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是知识的分别途径。庄子认为,这是对美的破坏,真正的美的体验,必须超越知识,美是不可“判”、不可“析”的。只有超越“判”“析”的分别,兼怀万物,与物一体,于此生命体验中,才能“备”万物之美。也就是说,拆除知识的屏障,是获得美的完满体验的根本途径。
说到宋元以来艺术哲学中的“备物”理论,就不能不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学说。应该承认,艺术理论中的此种“备物”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孟子发端而来的。但在深入研习艺术哲学此方面思想后会发现,此一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渐与儒家思想拉开距离,而过渡到以释道观念为中心,以超越知识、重视体验的无分别见为根本原则,进而形成与儒学这一重要学说的不同进路。
儒家心统万物的“大心”之推展,与道家“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备物说,有重要差异。我们在苏轼的“造物初无物”的论述中,在《二十四诗品》“具备万物”的浑一学说中,乃至在祝允明的“初不物于物”等理论中,都可以看出这种差异性。若以一言来概括,可以说:儒家“万物皆备于我”重在“理”的会通,道家“兼怀万物”重在“理”的超越。一始终有一个主体的存在,一倾向于呆若木鸡的“全德”之境,二者不可等而视之。
小结
大成若缺,作为传统艺术哲学中的一条定则,包含着极为丰厚的理论内涵。以上四个方面的讨论,都立足于传统艺术的具体形式创造。一是支离与大全,传统艺术创造中对支离、萧散、疏落等的强调,旨在突破整体和部分相互依存的外在计量,归复生命真性。二是残缺与圆满,超越残缺和圆满相对的妄计,从当下直接的生命体验出发,臻于“随处圆满,无少欠缺”的境界。三是破碎与浑一,传统艺术有一种对联系性的强调,这是使艺术滑入僵滞和平衡的重要原因。传统艺术重破碎的境界,要于“生辣中求破碎之相”,这是对浑一整饬秩序的超越。四是局促与自足,如在艺术形式构造上,尽量简化形式,压缩空间,淡去声色,有意创造一种局促、偏狭的空间,刻意渲染外在世界对人存在的威逼,从中转出一种从容回荡的精神,于偏狭中见广大,由逼仄中出圆融,由此成就“万物皆备于我”的心灵境界。
四个方面,第一在破整体,第二在破圆满,第三在破联系,第四在破充足,四者都在超越外在的知识计量,臻于体验心灵的“大全”,这是“大成若缺”艺术哲学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