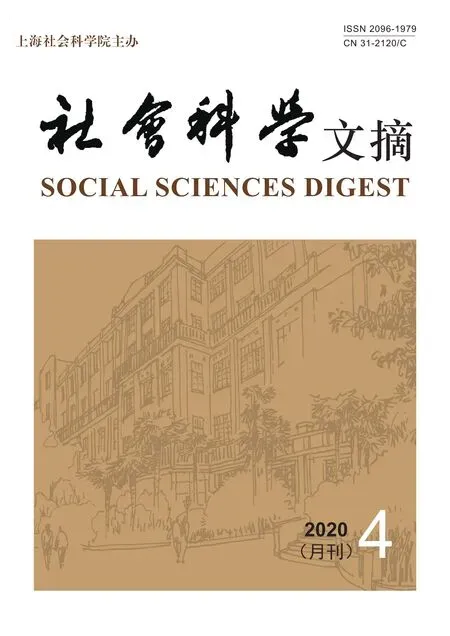鲁迅晚年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预感与忧思
文/王彬彬
鲁迅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距“七七事变”爆发尚有八九个月。如果说,“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是一种局部霸占,那“七七事变”则意味着日本是以侵占全部中国为目标了。鲁迅没有看到“七七事变”以及后来的情形,但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鲁迅便预感到日本会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国土全面沦陷,人民都成为亡国奴,是鲁迅晚年深重的担忧。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华民国诞生才20年。中华民国是推翻满清统治后建立的。满清作为异族侵略者,入主中原,统治中国260多年。鲁迅生于1881年,30岁以前,都是满清统治下的草民,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作为汉人,是满人的奴隶。当作为满清的奴隶时,鲁迅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满清统治中国260多年,不但以暴力迫使汉人在身体上屈服,还以各种手段对汉人“治心”,即在精神上愚弄、麻醉汉人,使汉人在心理上和在精神上认同满清的统治、奴役。当辛亥革命发生时,极力要捍卫、维持满清统治者,并非全是满人,也有许多汉人。甚至当满清政权已然垮台、民国已然成立,还有些汉人以遗老身份无限怀恋满清王朝,时刻梦想满清皇帝的复辟,也真有汉人主导的复辟闹剧发生。这情形,鲁迅在书上读到过许多,在现实生活中也曾见识过许多。摆脱此一异族的统治才20年,又要成为彼一异族的奴隶,这怎能不令鲁迅有无尽的哀伤?满清统治者费尽心机对汉人进行“治心”,手段也不可谓不高明,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而日本如果全面占领了中国,也必然会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上的愚弄、麻醉,让中国人民不但在身体上臣服于日本统治,在精神上也认同甚至迷恋日本的统治——而这,才是晚年鲁迅最为深切的忧虑。
一
“九一八”之后,鲁迅便清醒地意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决不会停止膨涨,国联的调解也好,日本国内自由主义者的呼吁也好,中国军政要人和学界名流的劝告也好,都不可能让日本停止、放弃对中国的侵略。鲁迅预感到日本的野心是将整个中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以日本其时军事力量之强大,这种野心是可能很快实现的。人民成为亡国奴,当然令鲁迅痛心,而最令鲁迅担忧的,是人民普遍在精神上被日本侵略者所奴役、渐渐地身为奴隶却不自觉为奴隶,甚至以奴隶生涯为幸福。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武力征服,固然令鲁迅愤慨,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必将进行的精神麻醉、心理征服,则更令鲁迅忧心。帮助日本侵略者在武力上征服中国的中国人,鲁迅固然对之痛恨,而帮助日本侵略者在精神上、心理上征服中国人民的中国人,则令鲁迅百倍憎恶。
正因为感觉到日本人已经在对中国人施行“治心术”,正因为担忧日本人“治心术”的成功,或者说,正因为预料到日本人“治心术”必然大有成效,所以鲁迅对日本人针对中国人的“治心术”极其敏感警醒,而对身为中国人有意无意地帮助日本人“治”中国人之“心”的行为,则更为敏感和警醒,也报以最大的憎恨。
二
“九一八”之后,鲁迅频频地谈论金元时期汉人的悲苦境遇,谈得更多的,则是明末的正义之士惨遭迫害以及满清统治者对汉人“治心”方面的殚精竭虑。
鲁迅认为,两次奴于异族,是国民性弱点的重要成因。而所谓两次奴于异族,当然是指金元时期和满清时期了。“九一八”后,鲁迅频繁地在文章中谈论金元和明清时期汉人遭受的压迫、凌辱,频繁地谈论以异族而入主中原者怎样既残酷地对汉人“治身”,又以种种方式对汉人“治心”。这当然是因为预感到金元和明清的历史又将重演。鲁迅长期致力于对大众启蒙,长期致力于国民性改造。脱离异族奴役才20来年,国民性改造还未见成效,却可能第三次整体性地奴于异族,而如果这第三次整体性奴于异族的时间足够长,那国民性的弱点必定进一步加剧。想到这些,鲁迅如何不痛心不己?如何不寝馈难安?频频地谈论前两次奴于异族时期的事情,是在抒发忧虑,更是在试图警醒国人。
1931年10月23日,“九一八”之后一个多月,鲁迅在上海《文学导报》上发表了长文《“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的行文让我们感到,当时国民党官方扶持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确激怒了鲁迅。鲁迅所尖锐批判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作品《黄人之血》,以所谓“剧诗”的形式,歌颂13世纪时蒙古帝国对欧洲的侵略。《黄人之血》中,西征的大军由汉、鞑靼、女真、契丹等黄色人种组成,而统帅大军的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拨都元帅。《黄人之血》在“黄人”的名目下,在“亚细亚”的旗号下,把汉人与汉人的征服者、奴役者说成是一家人,而家长则是蒙古人。拨都元帅统帅的黄种人大军,本来所向披靡,节节胜利,但后来虽肤色相同却种族相异的几类人,不懂“团结”的重要,竟自相残杀起来,终于“为白种武士所乘”,这是令作者十分遗憾和痛心的。《黄人之血》把那时的汉人与蒙古人写成一家人,这令鲁迅感到巨大的荒谬,也令鲁迅有着巨大的担忧。鲁迅写道:“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拨都,不是中华人赵构,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拨都的统驭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黄人之血》歌颂“亚细亚”的人民在蒙古人统驭下的联合,这自然而然地令鲁迅想到现实中的情形。所以,鲁迅尖锐地指出:“拨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现实是,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入中国,已在东北为所欲为,并且大有统驭整个中国的野心。依照《黄人之血》的逻辑,中国的人民应该甘当日本侵略者的顺民,而如果日本统驭了整个亚细亚,那亚细亚的人民都应该团结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下。这样的文学作品,是在明目张胆地替日本侵略者“治”中国人民之“心”。
三
在日本侵略者正对中国鲸吞蚕食、日夜不止的时候,鲁迅频频想到金元和明清之际。鲁迅留日时期就认为,中国国民性弱点的成因,在于历史上两次沦为异族的奴隶。身为奴隶而忘记自己的奴隶处境,甚至在奴隶生活中感受到幸福;身为奴隶而认同主人对自己的奴役,这种奴隶人格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统治者精心对被统治者“治心”的结果。统治者用各种方式,对被统治者的头脑进行改造,才使得被统治者视统治者为亲人、为父母,才死心塌地当着奴隶、奴才,并且誓死捍卫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奴役。鲁迅晚年的不少文章,都揭示了金元时期汉人的悲苦状况,而谈得特别多的,却是明末。说鲁迅晚年有一种“明末情结”,也并不为过。因为明末中国的社会状况,正是满清入主中原的根本原因。正是明末的腐朽黑暗,正是明末统治者对正义之士的摧残,为满清的侵入准备了条件。
日本人突破山海关、向华北挺进后,鲁迅便时时提及明末。鲁迅对国民党政权是极其不认可的,甚至可以说是痛恨至极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在鲁迅看来,其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与明末十分相似。明末的朱家王朝在国内的种种行为,正为满洲人的侵入扫清了障碍,而国民党政权眼下的所作所为,也正为日本人的侵入创造着条件。鲁迅写于1933年4月29日的《文章与题目》中就指出,在明末,“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国内的草菅民命、杀戮清流,当然十分有利于满洲人的入侵。鲁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屡屡提及明末,或明或暗地把明末与现实相比照。而在私人通信中,则谈明末的情形更多。公开发表的文章,说话还有所顾忌,私人通信则把话得更为明白。鲁迅多次提到明末的杀戮清流实际上是在为满洲人的侵入开辟道路。
四
明末与清初是连在一起的。有了明末的腐败、黑暗,重用奸佞而剿除清流,才有了满清的入主中原。所以,鲁迅在频频提及明末的同时,也常常说到满清统治者在精神上控制、驾驭汉人的用心和伎俩。有时候,他则是把明末和清代一起谈。关于清代,鲁迅谈得最多的是以文字狱为典型表现的文化专制。满清入主中原后,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实行文化专制,当然是为了有效地控制汉人的思想,是为了让广大汉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满清的统治。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预感到日本人很快将入主中国,而日本人统治中国后,也必定会实行文化专制,必定会大兴文字狱。总之是,清代的历史又将重演。清代的文字狱,往往是汉人搜罗证据、深文周纳地向满清统治者告发的结果。鲁迅说,此类事不久又会出现,当然是说当日本人统治中国并实行文化专制后,又会有中国人向日本统治者告发自己的同胞犯有思想罪,而满清的那种文字狱则也会再现。写下这样的预言时,鲁迅内心当然是沉痛的。
1934年7月17日,鲁迅写了杂文《算账》。每有人谈及清代的学术成就便眉飞色舞,以为是前所未有的。而清代的学术成就,是满清以异族统治中国并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的产物,是一种畸形的东西。鲁迅说:“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所谓清代的学术成就,体现在训诂考据上,这是一种没有思想的学术。在清代统治者严酷的文化专制下,便有了这种学术的畸形发展。中国的士大夫、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要统治者做出尊孔崇儒的姿态,便愿意与其合作,不管这统治者是不是异族入侵者。鲁迅接着说:“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鲁迅又一次提及胡适所谓的“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鲁迅深刻地指出,满清统治者做出尊孔崇儒的姿态,不过是一种征服汉人之“心”的策略。满清统治者的“治心术”当然是有成效的,能够以少数人而奴役中国近300年,就证明了这种成效。所以鲁迅说:“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这些大门面。”满清统治者的“治心术”,把中国民族的“有些心”治得麻木而奴性,以至于到了民国,还是那样冷漠、愚妄和扭曲。文章最后,鲁迅写道:“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当然是指日本人即将主宰中国、清代的历史又将重演。在这样的时候鲁迅算这样的账,心情肯定是复杂的。
清代的文化专制,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的“治心术”,是鲁迅晚年非常留意的事情。1934年7月10日,鲁迅写了《买〈小学大全〉记》,这也是鲁迅上海时期特别重要的文章。鲁迅揭示了清代文学狱的种种看似匪夷所思实则大有深意之处。鲁迅指出,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也仅仅是允许人们尊崇,并不允许人们真以朱子为榜样。说白了,尊崇朱子,不过做做样子、装点门面,当然,更深层的用心,则是为自己的政权找到更多的合法性。如果有不明事理的书呆子在尊崇之余,还以朱子为榜样,那可就要遭殃了。因为一学习朱子,就不免在思想学术上开宗立派,就不免聚众讲学,就不免有门户林立,这就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何况,以朱子式的“名儒”而出仕,就成为受人景仰的“名臣”,就可以以道抗势了。满清皇帝当然不愿意有这样的“名臣”整天戳在自己眼前。因为文字狱的严酷,士子便不敢治史,尤其不敢问津近代的事情,许多书被销毁、禁绝,使得读书人根本不知曾有这些书存在。“文化统制”,说白了就是愚民政策。满清统治者为了愚弄汉人,为了有效地对汉人“治心”,既采用了消极的策略,也使尽了积极的招数。作为消极手段的文字狱,是禁止士人发表不利于专制统治的言论。而如果士人仍然在思想,不利于专制统治的观念、看法就仍然可能从士人的头脑中源源不断地产生。虽然士人不敢把这些观念、看法表达出来,但只要它们存在于士人的头脑中,就仍然对专制统治是潜在的威胁。文字狱只能对付已经形成文字的东西,而无法消灭隐藏在头脑中的思想。所以,文字狱再严酷,也不过治标而已,要治本,则必须让天下士人的头脑中根本不产生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思想。而要做到这一步,便必须断绝天下士人的思想资源。编纂四库全书,决非为了弘扬、发展中国固有文化,而意在以阉割、篡改已有著作的方式,摧毁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思想产生的资源。对汉人著作进行取舍,使被舍弃者成为禁书,久而久之,就无人知晓了。即便留下来的,如果有涉及金元之处,也要进行修改,而将修改过的作为定本。特别忌讳涉及金元处,自然很好理解。金元对汉人的凌虐,性质正与满清相同,容易让人发生联想。被阉割、篡改的著作,也不限于语涉金元者,总之是只要认为不利或无益于满清的专制统治者,都要删除、改纂。
鲁迅进而说,不但消极的文字狱和积极的禁绝、篡改汉人著作显示了满清统治者对汉人“治心”的良苦用心,即便是那些宫廷起居注或奏议、谕旨一类东西,也时时显示着满清统治者宰制汉人的心机。鲁迅早年认为两次奴于异族,是汉人性格中奴性生成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看法至晚年仍未改变。在专制统治下,在严酷的文字狱面前,文人的崇尚所谓“性灵”,是不得己之举,是借以避祸偷生的手段。鲁迅之所以认为对那些奏议、谕旨一类清廷文献加以整理、钩稽,让人看到清代统治者驾御汉人、对汉人进行文化专制、对汉人“治心”之“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却也十分有益”,当然是因为中国又将面临异族的统治、奴役。
“九一八”以后,日本的侵华问题,其实成为鲁迅时时关注、经常思考的问题。鲁迅预感到日本决不会满足于仅仅霸占东北,而必定有将全中国归于治下的野心,而这种野心极可能实现。金元和满清的历史又将重演。除了对现实中种种与抗日有关的问题发言,鲁迅还频频论及金元,谈及明清,而谈金元、谈明清,也无非是间接而更深刻谈论现实。鲁迅对时局的观察,未必事事都十分准确;对现实的批判,也未必句句都完全在理。后来的历史进程,当然有些也是鲁迅没料到的。但鲁迅所预感的大事情,的确发生了,而鲁迅的担忧,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