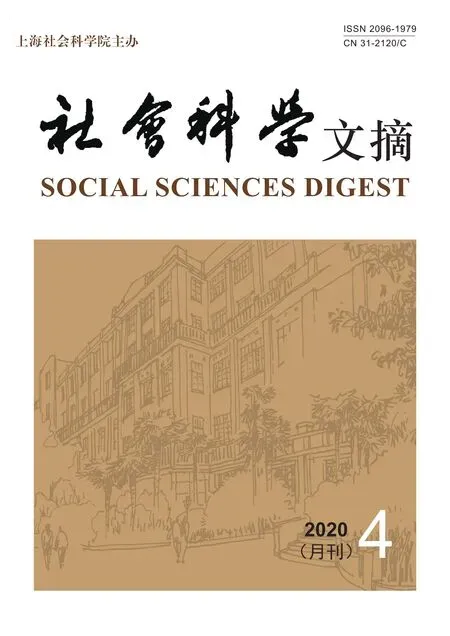论《边城》的“诗语”风格与结构模式
——基于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视角
文/龚刚
小说《边城》问世多年,至今仍有众多读者深深迷恋其中乌托邦式的田园风情,同时又为翠翠在绝望与希望中的内心挣扎与一往情深所触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是结构的艺术。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组合、结构安排,造就了一个遗世独立、饱含情韵的“边城”世界?这是沈从文艺术创造的“达文西密码”。在本文中,笔者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视角,剖解沈从文内在的写作发生过程及呈现形式,重捕《边城》核心符号,揭示《边城》的隐性复调叙事,以期“解码”沈从文艺术世界的奥秘。
《边城》的“诗语”风格
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而言,是创作手法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最终决定了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比如炒茶,不同火候的炒法,就不可逆转地决定了茶叶的品位和形态。形式主义学派创始人什克洛夫斯基声称:“在文学理论中我从事的是其内部规律的研究,如以工厂生产来类比的话,则我关心的不是世界棉布市场的形势,不是各托拉斯的政策,而是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很明显,对什克洛夫斯基来说,“文学形式的变化问题”才是文学艺术的内在问题,所以他把创作手法看成艺术的本质。在他看来,“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这段话广为传诵,影响极大。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的“文之悦”理念即是其翻版。如果深入体会什克洛夫斯基这一说法的语境就会意识到,“把形式艰深化”不等于故作深奥、故弄玄虚,也绝不是提倡晦涩的语言和繁冗的表达。“形式的艰深化”与“事物的奇异化”不可分割,而使事物“奇异化”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也就是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这就是艺术的目的。
那么,如何在形式与事物的对应关系中,恢复生活体验,“使石头成其为石头”呢?这就要看创作者能否从“一般语言”中破茧而出,以有助于“加强印象”与“增加事物实感”的“诗的语言”再现事物,演绎生命体验。一般语言与诗的语言的对立,凸显了日常表达与艺术表达的对立,日常表达依赖于说话习惯,艺术表达依赖于创作手法。创作之为创作,就是要在习惯中创新。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沈从文有其独到的“纺织方法”,这是他的“达文西密码”。任何人在解析“边城”世界的时候,都不应忽视他的“纺织方法”——创作手法——这一动态过程的决定性生成作用。只有读懂了他的“纺织方法”(“诗语”风格、结构方式),才能破译他的“达文西密码”。下文且以《边城》第一段为例,解读其“诗语”风格: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个黄狗。
先从词与词的组合来看,作者尽量减少前缀,非用不可时,也多选功能性的修饰语,而尽量避免情感性的修饰语,如“官路”的“官”,“湘西边境”的“湘西”,“小山城”“小溪”“小塔”的“小”,“单独的人家”的“单独”,“老人”的“老”,“女孩”的“女”,“黄狗”的“黄”。它们简约地指明了人与物的基本性质与特征,主观色彩很淡,留给读者的回味空间却很大。
修饰语可以区分为三种:一种是关于事物的形态与方位的,如大、小,方、圆,东、西,左、右;一种是关于事物的声色与气味的,如轻、响,明、暗,黄、白,香、臭;一种是关于事物的情感效果的,如“忧郁的天空”中的“忧郁”,“热情的火焰”中的“热情”,“欢乐的溪流”中的“欢乐”,都属此类。它们都不是事物固有的属性和客观的存在方式,而是主体移情的结果,具有明显的情感色彩。我们从《边城》第一段就可以看到,作者绝少使用第三种性质的修饰语。无疑,全文那种平静而又隐含深情、从而具有极大情感张力的叙述语调,是和作者上述对修饰语的有意识提炼和取舍密切相关的。
除了多用功能性的修饰语,作者对数量词的运用也很有特色。在不到一百字的文字中,数词“一”连续出现了七次,数量词“一个”出现了四次。在汉语中,“一”和“一个”都是很常见的数词和数量词,但沈从文这样的大文豪却如此频繁地使用这些几近平庸的语辞,一定有些门道。在我看来,这是沈从文“大道至简”的简约化思维的体现,这和他喜用功能性修饰语一脉相承。另一方面,连续出现的人与事,都是单数个体,也给人以孤寂之感:年老的祖父与年幼的孙女,在遥远山城的小溪边相依为命,确实是清冷寂寞的。此外,“个”这个量词,一般用以表示人,沈从文却用以指称“黄狗”,这是动物的人化,就算不能因此得出在山野田园之中天人合一这种学究化的结论,至少也表明了在这户单独的人家中,黄狗不是异类,而是给人以温暖的家庭成员。
本文采用田口方法对切削参数进行分析优化。田口方法(Taguchi method)是由日本田口玄一博士(Genichi Taguchi)根据统计学原理和方法创立的一种实验方法。借助田口方法,工程人员可以通过最少的实验次数,快速获取最佳的参数组合,从而大幅减少实验次数,降低实验成本。田口方法的两大工具为正交试验和信噪比(S/N)。根据期望目标,信噪比分别具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如式(3)~式(5)所示:
再从句式来看,作者尽量避免造句冗长,且非常注意表达上的连贯性,我们还是看第一段,“靠东有一条官路”,下接“这官路”如何如何;“有一小溪”,下接“溪边”如何如何;“溪边有座白色小塔”,下接“塔下”如何如何;“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下接“这人家”如何如何,这可以说是用了一连串的顶真格,有如溪流一样的连贯流畅。
由于语言组合只是作者组合语言的结果,是组合语言这一动态过程的静态形式,因此,如果我们要追踪活生生的创作手法,从而将文本的生成过程清晰地揭示出来,就必须从对语言组合的静态解析上升到对组合语言的动态描述。可以想见,当作者在构思时,一定是千头万绪,意乱情动,种种画面浮现眼前,种种体验回荡胸中,如何将它们围绕某一情节内核(我至今坚持认为,情节是小说文体必不可少的因素,只不过那些在人们眼里更像“小说”的小说作品,乃是以情节吸引人,而那些在人们眼里不像“小说”的小说作品,则竭力避免让情节明显地浮现出来,而是浓缩沉淀为一个情节内核,成为整部小说的根。《边城》的“根”,就是天保、傩送、翠翠之间的爱情纠葛)导入某一叙述流程,如何在导入的过程中不丧失既有的感觉,如何在保有感觉的同时尽量贴近人物本身、事物本身,以“增加事物实感”,这一切的一切,都依赖于特定的创作手法,都要在组合语言、安排结构的动态过程中得到解决。且看组合语言的过程,作者以三个同样的前缀“小”,捕捉住了对山城的感觉、对溪的感觉、对塔的感觉,也捕捉住了对整个故事、整个作品的感觉,作者显然摒弃了诸如幽静、潺潺、玲珑等未必不准确,但一旦运用必然破坏行文语气并烙上醒目的主体色彩的修饰语,从而迅速贴近了事物本身,取得了与读者平静对话的姿态;其他如“单独”“老”“女”“黄”,也有同样的效果。
综观整部小说,由第一段文字所显示出的两大特点,即,多用功能性修饰语和常见的单数个体数量词,以及避免造句冗长并注重表达上的连贯性,贯穿始终,摇曳出一个宁静淳朴、情思悠悠的“边城”世界。
《边城》的核心符号
托多罗夫曾提倡诗学研究,因为“诗学是一种既抽象又内在地理解、掌握文学的学科。这门学科关注的不是实在的文学,而是可能的文学,换句话说,它所关注的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抽象属性”。这种结构主义的抽象思路,用在小说研究中依旧驰骋如意。
如果要进一步解开《边城》的“达文西密码”,就要抓住整篇小说的核心符号,以揭示其结构的奥秘。在我看来,左右着“边城”世界的的核心符号不是翠翠,也不是纯真的初恋,而是一个容易为人忽视的节日——端午节。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段落,提到了“两个中秋节”“两个新年”,但对翠翠来说,都比不上“那个端午(节)”:
这两年来两个中秋节,恰好都无月亮可看,凡在这边城地方,因看月而起整夜男女唱歌的故事,皆不能如期举行,故两个中秋留给翠翠的印象,极其平淡无奇。两个新年却照例可以看到军营里与各乡来的狮子龙灯,在小教场迎春,锣鼓喧阗很热闹。到了十五夜晚,城中舞龙耍狮子的镇筸兵士,还各自赤裸着肩膊,往各处去欢迎炮仗烟火。……翠翠同他的祖父,也看过这样的热闹,留下一个热闹的印象,但这印象不知为什么原因,总不如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
在中国民俗中,新年、中秋、端午应是最美好的节日,既寄寓着美好情愫,又各有一番温馨热闹,所以格外让人期待。小说中的湘西山城也不例外,“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过年喜庆,中秋相思,端午吃粽、赛龙舟。那个让翠翠感到“甜而美”的端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就在这个端午节,祖父带了黄狗同翠翠进城,过大河边去看划船,结果遇到了掌水码头的龙头大哥顺顺的次子——“眼眉秀拔出群”“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诨名“岳云”的傩送。虽然只有寥寥数语的交谈,他却已让翠翠暗生情愫,挥之不去。每到端午,这份情思就会格外强烈,也就平添了翠翠的忧伤。如果没有端午节,不会有翠翠和傩送的邂逅,不会有翠翠的情窦初开,也就不会有故事的开始。
端午节的邂逅,端午节的情思,一个是情节的枢纽,一个是情感的枢纽。情节只是背景,情感氛围的营造才是用心所在。沈从文的散文化小说向以优美而哀伤的情致动人,曲折离奇的情节构造从来都不是他的关注重心。对于翠翠和傩送(二老)的爱情故事,沈从文更注重在闲言淡语中旁敲侧击地加以刻画,而不会像言情小说一样浓墨重彩地加以描摹。
这样的描写,好像不着边际,实质上是在轻描淡写中推进情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这部散文化小说中,正是因了这份端午节的情思,一直若隐若现的情愫才落到实处,并不断深化,直到翠翠的灵魂在睡梦里为傩送的歌声轻轻浮起,直到傩送的哥哥、同样爱着翠翠的天保黯然离去、溺水而亡,直到无奈的终局。
《边城》的隐性复调叙事
苏联文艺理论家M·M·巴赫金曾开创性地提出“复调理论”,将音乐中的复调概念引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文学评论,至今声名显赫。巴赫金在其著作中写道:“各种独立的不想混合的声音与意识之多样性、各种有充分价值的声音之正的复调,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征。但这不是多种性格和命运在他的作品里在统一的作者意识这层意义上的统一客体世界里被展开,而正是多种多样的具有其世界的平等意识结合成某种事件的统一。”正是这颇为拗口的后半句话启发了笔者,如果以复调理论分析《边城》的文本,会在叙事结构与涵义上获得新的发现。
从深层结构来看,沈从文的《边城》其实讲述了两个爱情故事:一是翠翠与天保、傩送兄弟的爱情纠葛,这是主体;一是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这是淡渺的背景,就像萦绕在山间的悠悠笛音。
这两种爱情都是超世俗、超功利的,却以两种不同形式来表现。一种是以罗密欧朱丽叶式的双双赴死作为结束,反映出来的是人对爱情的渴望和执着超出了现世的藩篱——既然在现实中寻求不得,便转向另一个世界。这种爱情观念,是老船夫不想让翠翠效仿的。
翠翠的爱情是含蓄矜持的,从一开始的害羞,到此后交往中的欲语还休,就像溪流边的一朵雏菊,静静等待着傩送来到自己身边。而就在这样的等待中,翠翠错失了一次又一次邂逅幸福的机会,直到天保的悲剧发生,直到傩送黯然离去。但翠翠还是在等待,不知归期地等待。
翠翠母亲却是为爱情而燃烧的性格,爱得热烈,死得也热烈。她爱上了屯防的军人,并怀上了孩子,当淳朴的军人在荣誉和爱情的两难抉择中服毒死去,她也在生下翠翠后随之而去。他们的爱情如火一般烈,刀一般决绝,留下了一段哀婉的传奇,也给翠翠的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
作者将翠翠母亲的爱情故事作了淡化处理,令其只是若有若无地浮现在人们的传说中。作为前奏,小说中仅以一段故事梗概般的文字极简练地描述了翠翠父母的惨烈爱情及其结晶。
从叙事结构上来看,将翠翠母女的两段爱情在现实中衔接起来的,是翠翠的爷爷。翠翠的爷爷经历过丧女之痛,为了不让外孙女重蹈覆辙,思索再三,既没给托人求亲的天保一个明确的答案,也没告诉傩送翠翠的真实心意,被傩送认为“弯弯曲曲,不利索”,后者还认定,“大老是他弄死的”。客观而言,翠翠爷爷的模棱两可的确间接造成了天保之死,但他是害怕外孙女重演其母的悲剧,所以在婚嫁之事上格外慎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整部小说淡渺背景的上一代人的爱情悲剧,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下一代人的爱情故事。至此,在结构上翠翠母亲与翠翠各自的爱情经历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沙漏的形式”,更为抽象的说法是,形成了一个“X”的式样。而中间交汇的一点,正是在《边城》这篇小说里种种美好之下,隐含着的那个微苦的内核——生命的延续必将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在反复捶打中挣扎成长,得以存活与否尚不可知,但努力过、深爱过便存了希望。
通过比较两代人的故事可以发现,翠翠的柔情似水与翠翠母亲的热烈似火,是两个极端,但在情深意重这一点上,却一般无二。翠翠的父亲与翠翠的心上人,一个因放不下军人的荣誉而自杀,一个因放不下对哥哥死亡的愧疚而出走,淳朴近于傻。沈从文通过这种隐性的复调叙事,刻画出了他理想中的化外世界:唯美,纯情,重义轻生,虽然不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