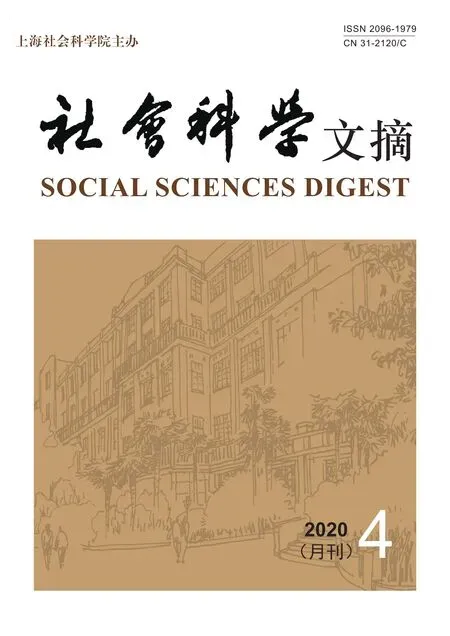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古文观
文/郭英德
清乾隆年间朝廷组织、馆臣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学批评内容。由于《总目》由总纂官纪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因此《总目》的文学批评无疑渗透着纪昀个人的文学思想。但更重要的是,《总目》“实是钦定之书”,而且凝聚着四库馆臣的集体智慧,集中体现了清代前、中期以朝廷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思想和意识形态。
近十多年,学界对《总目》的骈文观多有研究,精义纷呈,但对《总目》的古文观却未见系统论述,仅在探讨纪昀与《总目》的文学思想、文学批评时略有涉及。其实,《总目》对“古文”的基本性质和形态特征的论述相当丰富,且颇为精彩,足以从一个侧面揭示清前、中期以朝廷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思想,及其所根基的文化传统和所宣扬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值得我们深入考察。
“古文”的基本性质
《总目》中“古文”一词,用例数以百计,核其大要,可以归结为二义:第一,“古文”指上古时期的一种文字类型,在小学语境中与“籀文”“小篆”等并举,在经学语境中与“今文”对举;第二,“古文”指中唐以后渐趋成熟的一种文体类型,在文学语境中与“诗”连称,在散文语境中与“时文”“骈体”“语录”等对举。
《总目》运用第二义的“古文”,有时称为“古文词”,如卷一八一清法若真《黄山诗留》提要:“若真诗古文词少宗李贺,晚乃归心少陵,不屑栉比字句,依倚门户,惟其意所欲为,不古不今,自成一格。”或称为“古体散文”,如卷一七三《御制文初集、二集》提要:“惟我皇上心契道源,学搜文海,题咏繁富,亘古所无。而古体散文,亦迥超艺苑。”(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19页)。
本文集中论述在散文语境中与“时文”“骈体”“语录”等对举的“古文”。《总目》虽然从未直接阐释何谓“古文”或何为“古文”,但是在与“时文”“骈体”“语录”等文体的比较中,却深刻地揭示了“古文”的基本性质。
首先,《总目》总是明确地辨析“古文”与“时文”的异同。《总目》中所谓“时文”,亦称“时艺”“今文”“制义”“制艺”“八比”“馆课”等。《总目》中常以“古文”或“诗古文”与“时文”对举。如卷一七八明郑心材《郑京兆集、外集》提要云:“心材老于场屋,必欲一第而卒不可得。年五十始就铨,平生精锐之气,已消磨于时文中。诗古文特偶试为之耳。”(第1608页)
大要言之,《总目》认为“时文”源于“古文”,因此“时文”与“古文”自有相通之处,二者皆应根柢于经术,崇尚“典雅遒洁”的文风。卷一七一明王鏊《震泽集》提要云:“鏊以制义名一代,虽乡塾童稚,才能诵读八比,即无不知有王守溪者。然其古文亦湛深经术,典雅遒洁,有唐宋遗风。盖有明盛时,虽为时文者亦必研索六籍,泛览百氏,以培其根柢,而穷其波澜。鏊困顿名场,老乃得遇,其泽于古者已深,故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也。”(第1493页)正是有见于此,《总目》认为,如果不能“得古文之源本”,无论是“古文”写作还是“时文”写作,必然“皆不入格”(第1648页)。
虽然“古文”与“时文”二者均可以载入集部,但是《总目》却更为倾向于在“古文”与“时文”之间“区分体裁”,将“时文”剔除出集部。卷一七三弘曆撰、蒋溥等编《御制乐善堂文集定本》提要指出,依据两宋以来的“古例”,“制义”自然可以载入别集或总集,但是为了“区分体裁,昭垂矩矱”,“时文”还是以不入集部为宜,因为这更便于彰明“古文、今文之分”,由此体现出弘曆“睿鉴精深”的文学观念(第1519页)。
因此,《总目》在根本上并不认可“时文”是“古文”之一体。《总目》对“儒者率殚心制义,而不复用意于古文词”的辨析,明确地显示出“时文”和“古文”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文体的看法(第1620页)。而且,《总目》更不赞许“明人文集以时文为古文者”(第1508页)。《总目》认为,“以古文为时文”,因其追本溯源,因此堪称“八比之正脉”;而“以时文为古文”,则因其本末倒置,“非古文之正脉”,故而应当避忌(第1727页)。
其次,《总目》也明确地辨析“古文”与“骈体”(或“骈体之文”)的异同。《总目》中所谓“骈体”(或“骈体之文”),亦称“俪体”“俪偶”(或“偶俪”“俪偶之文”“比偶之文”)、“骈偶”(或“骈俪”“骈偶之文”)等,而更常见的称呼是“四六”(或“四六之文”)。《总目》中常以“古文”与“骈体”对举。如卷一八九《梁文纪提要》云:“然古文至梁而绝,骈体乃以梁为极盛。残膏剩馥,沾溉无穷。唐代沿流,取材不尽。”(第1721页)
《总目》明确地认识到,“骈体”与“古文”同源,二者自有相通之处。卷一八九明王志坚《四六法海》提要云:“大抵皆变体之初,俪语、散文相兼而用。其齐、梁以至唐人,亦多取不甚拘对偶者。俾读者知四六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于兹体深为有功。”(第1719页)就其本源而言,“古文”与“骈体”虽有“文章正变”之别,但皆为“文”之一体,都属于“文”的家族成员,不可以“判若鸿沟”(第1732页)。
然而《总目》更为强调“古文”与“骈体”自有不同的“文格”。在语体上,“古文”以散语见长,“骈体”以俪词取胜;在风格上,“古文”以朴质为尚,“骈体”以雕饰为华。“唐之古文”与“六朝之体”相比较,“斫雕为朴”,“文格”判然有别(第1285页)。如果随意将二者相互杂糅,甚至“以骈体为古文”,则有乖“典则”与“文格”。卷一七三清吴伟业《梅村集》提要批评吴伟业:“惟古文每参以俪偶,既异齐、梁,又非唐、宋,殊乖正格。”(第1520页)
就其深层意蕴而言,《总目》认为,“以古文为骈体”固然可取,而“以骈体为古文”则必当避忌。这是因为,明清文人普遍认为,“古文”为源而“骈体”为流,“古文”近古而“骈体”趋今,“古文”体尊而“骈体”体卑,二者各有其内蕴的文化价值,不可混为一谈。对文学类型、文学体裁进行源流、古今、尊卑的价值判断,这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重要传统,《总目》继承并强化了这一传统。
再次,《总目》中也常以“古文”与“讲章”对举。如卷一八四清黄越《退谷文集》《诗集》提要云:“所著《四书大全合订》,及选刻制义如《明文商》《今文商》《墨卷商》《考卷商》之类,皆盛行一时。盖平生精力注于讲章、时文。此集所著诗古文,乃以余暇兼治者。”在《总目》中,“讲章”亦称“语录”“讲学”(或“讲学家言”)等。
《总目》中对“古文”与“语录”的辨析是非常严格的。《总目》认为,与“弇陋粗鄙之状”的“语录”相比较,“古文”更为讲究“修饰章句”,追求“文质相宜”(第814页)。而且,“古文”还追求“平正醇雅”(第1433页),“雅健有格,无抄撮语录之习”(第1510页)。
综上所述,《总目》认为,“古文”不是“时文”,虽然可“以古文为时文”,但切不可“以时文为古文”;“古文”不是“骈体”,虽然“骈体”源自“古文”,而且“运意遣词”也“与古文不异”,但“古文”切不可掺杂“骈体”,更不可以“骈体”为“古文”;“古文”不是“语录”,不可以有“弇陋粗鄙之状”。
“古文”的形态特征
既然“古文”不同于“时文”“骈体”和“语录”,那么,作为一种性质独特的文体,“古文”具有哪些形态特征呢?大要言之,《总目》分别从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方面,明确标举“古文”的形态特征,即散行单句、华实酌中、法度谨严、醇朴雅正。
在体制层面,《总目》认为,与“时文”“骈体”相比较,“古文”最明显、也最易于辨识的外部形态特征,就是它以散行单句为标志,而不以骈语俪句为范型。因此,“古文”也可通称为“散体之文”(第1586页),切忌“俪句与散体间用”(第1577页)。
在语体层面,《总目》认为,作为典范的“古文”,应达臻“体裁尽善,华实酌中”(第1519页)。与“语录”的一味俚语鄙词不同,与“骈体”的过度丽藻雕饰也不同,“古文”既避忌语言俚俗,也避忌辞藻华丽。如果行文兼用“表启骈词、语录俚字”,则有悖“古文”的“文格”(第1543页);如果行文“喜雕琢新句,襞积古辞”,也难免“流为别派”(第1669页)。《总目》认识到,就“古文”自身的形态演变而言,自然而然地呈现出“由质实而趋丽藻”的审美趋向,但即使是“格律遂成”“体裁大判”之后的六朝“骈体”,仍然与古文“面目各别,神理不殊”,“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第1719页)。
在体式层面,《总目》强调“古文”应谨守“法度”(或称“法律”),而不是仅凭才气驰骋,率意为文。所谓“法度”(或“法律”),表现为“折矩周规”“意态波澜”“高简”“安章宅句”等体式特征,以“严密”“谨严”“严谨”为宗尚,而有别于“讲学支离冗漫之体”(第1338页)。以此为前提,如果再加以“边幅”稍广,“酝酿”稍深,“崭崭有笔力”(第1508页),“脱然于畦封”(第1657页),那就更能达臻“古文”之佳境。在这方面,明唐顺之的“古文”批评堪称深中肯綮。卷一八九《文编》提要称唐顺之:“深于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别择,具有精意。”尤其擅长辨析文章法度,“妙解文理”。因此唐顺之选评《文编》,“所录虽皆习诵之文,而标举脉络,批道窾会,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以蕲至于古。”(第1716页)
在体性层面,《总目》提倡古文醇朴雅正的文学品格。《总目》认为,娄坚的“古文”之所以堪称“真古文”,是因为在文学品格方面“具有古法”,即“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鲜明地体现出“正始之音”(第1515页)。《总目》称许蔡世远编撰的《古文雅正》“以理为根柢,而体杂语录者不登;以词为羽翼,而语伤浮艳者不录。”(第1732页)
“雅”及其相关词组如“古雅”“醇雅”“雅正”等,是清前中期评文论艺的“关键词”,代表着清廷不可移易的核心价值观。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玄烨撰《御选古文渊鉴序》,宣称其衡文标准是“辞义精纯”“归于古雅”。康熙四十一年(1702)颁行《御制训饬士子文》,强调:“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乾隆元年(1736)、十九年(1754)、二十四年(1759)、四十三年(1778)、四十四年(1779),上谕多次重申“清真雅正”的为文宗旨(《高宗纯皇帝实录》)。
就清代以朝廷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思想而言,“崇雅黜浮”应是基本的文章理念,无论是“古文”还是“时文”“骈体”“语录”,莫不以此为归趋。但是与“时文”“骈体”“语录”相比较,“古文”的书写策略是“不为雕饰藻绘之辞,而皆有以合乎仁义中正之旨”(蔡世远《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序》),因此就其体性而言,“古文”更能体现清代帝王“崇雅黜浮”的文章理念,更便于推进道统与文统合为一体的文化建构,因此更值得大力提倡。
“古文一脉”的正传
《总目》之所以明确地标称自成系统的古文观,实际上是针对明末“古文”两大流派的弊端,有所见而发的。卷一七九明邓渼《大旭山房集》提要引邓渼之语指出,明末“古文”流派中,“七子派”“摹拟工则蹊径太露,构撰富则窠臼转多”,而“公安派”“竟陵派”则标尚“肤浅之法,畏难好易”。其实,这两种“古文”写作之弊,不仅泛滥于明末,甚且贯穿于有明一代。
《总目》认为,明代“古文”脱离“前辈法度”,流行“畏难好易”的“肤浅之法”,肇始于前期“肤廓冗沓”的“台阁体”文风(第1472页)。至明中叶,则流溢为“时文”“语录”一派的文章,“于文格多所未合”(第1590页)。晚明则有“三袁”等人,“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以致“破律而坏度”(第1618页)。直至清初,“畏难好易”的“肤浅之法”仍然流风不减,为文难免“纯以天资用事,往往或失之粗豪”(第1643页)。
而明代“摹拟工则蹊径太露,构撰富则窠臼转多”一派,则以正、嘉之际“前七子”发其端,以隆、万之时“后七子”继其后,绵延百年,蔚然成风。《总目》卷一七九明袁宏道《袁中郎集》提要云:“盖明自三杨倡台阁之体,递相摹仿,日就庸肤。李梦阳、何景明起而变之,李攀龙、王世贞继而和之。前、后七子,遂以仿汉摹唐,转移一代之风气。迨其末流,渐成伪体。涂泽字句,钩棘篇章,万喙一音,陈因生厌。”(第1618页)因此,《总目》称许王慎中尽焚旧作,转而“一意师仿”“欧、曾作文之法”,并影响了唐顺之、茅坤等人(第1504页)。
然而,尽管“唐宋派”有意矫正“七子派”文章之弊,追求“演迤详赡”的文风,足以“卓然成家”,但仍然残留摹拟的痕迹,难免成为新的“窠臼”。卷一七七明茅坤《白华楼藏稿》《吟稿》提要云:“坤刻意摹司马迁、欧阳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选《史记钞》《八家文钞》《欧阳史钞》,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拟有迹。秦、汉文之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则自坤始。”(第1592页)因此,《总目》认为,学“古文”者,即使“根柢仍出八家”,甚至进而宗秦、汉,又进而宗六经,也难免有行偏走差之虞(第1666页)。
于是在治弊纠偏的意义上,《总目》认为,“七子”的“肤滥”,“三袁”的“纤佻”,皆偏离了由“唐宋以来之矩矱”所延续的“古文一脉”正传,从而造成明末“古文”的极弊。入清以后,侯方域、魏禧、汪琬等人起而救弊,倡行“古文”。但魏禧濡染“三袁”风气,“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侯方域秉承“骈体”积习,“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二人皆未能符合“唐宋以来之矩矱”。唯有汪琬深于学术,为文“大抵原本六经”,因此“气体浩瀚,疏通畅达”,足以“接迹唐(顺之)、归(有光)”,成为“古文”正传(第1522页)。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九《爱鼎堂遗集序》指出,在文学发展史上,有“趋风尚”与“变风尚”两种选择。“趋风尚”者,或“厌故喜新”,或“巧投时好”,或“循声附和,随波而浮沉”,凡此皆不可取。而“变风尚”者则有二途:一为“乘将变之势,斗巧争长”,一为“于积坏之余,挽狂澜而反之正”,纪昀更为赞许后者。《总目》倡导“古文一脉”在清前中期的传承,也更多地瞩目“于积坏之余,挽狂澜而反之正”。《总目》认为,清初以来尽变明末“纤仄之体”,文坛风气从康熙时的“沉博绝丽”,雍正间的“舂容大雅”,到乾隆朝的“佩华衔实”,奏响了“沨沨乎治世之音”(第1728页)。由此可见,《总目》“拨乱反正”而标举的古文观,恰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前中期以朝廷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思想。这一古文观承续了源远流长的古典审美理想,并为姚鼐等桐城学人发扬光大,引领清中后期的古文风尚,描绘出一幅“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满天”的绚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