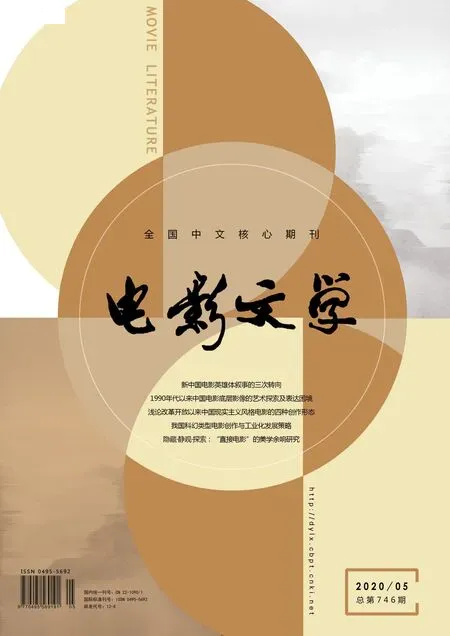生态电影的叙事机制与文化认同
卞祥彬
(安徽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生态电影衍生于文学的生态批评,将电影批评的关注焦点从“人”转向与人生存紧密相关的空间环境,以期通过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视点转向重建失衡的价值观念体系。美国学者斯格特·麦克唐纳(Scott MacDonald) 2004 年在《建构生态电影》(Toward
an
Eco
-Cinema
)一文首提了“生态电影”(Ecocinema)的概念,确立了生态思潮和电影批评的联系,以期建构一个能使观众从消费主义的旋涡中抽身的精神花园。生态电影以其长镜头与舒缓的剪辑节奏、非对抗式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像化表达、长时间的凝视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生态电影”美学。史蒂芬·吕斯特(Stephen Rust)在《分隔渐隐——对生态电影研究的定义和定位》中提出“在实际效果中,对先锋电影的感受可以抵御商业媒体对精神和环境产生的破坏”。再次确认了“生态电影”对消费文化的抵抗,提出了精神和环境净化的功用。“生态电影”所建构的新时期公共文化空间,实现了公民意识的表达,恰恰契合当下观众对生态意识的内在诉求,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大众生态焦虑的文化体现。生态电影通过影视语言的自然表述强调生态启蒙的意义,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自然的关系。当前好莱坞电影末日情节和英雄救赎的震惊美学成为电影类型化生产的强势叙事机制;而生态电影《哪啊哪啊神去村》(又译《爱上春树》)却专注于自然生态治愈与人性修复的成长论述,呼应了生态电影对消费指向的怨怼。生态电影在父权式微的图景下,通过电影的叙事机制实现了对主体身份的“寻唤”与自然生命的质询,成为生态电影的经典叙事范式。
一、生态电影的叙事机制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认为主体的形成经历了“镜像阶段”三个过程,即将自我指认为他者、自我的出现、接受了社会文化结构与语言系统的主体的最终形成。通过自我的“凝视”与异化为社会关系中的主体,最终实现价值观念的认同。电影《哪啊哪啊神去村》在一系列的影像程式遮蔽下反复展示平野勇气所面临的现实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将现实意义的成功横亘于平野勇气与爱情、友情和亲情之间。平野勇气所面对的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脆弱而是现实价值观念对其的边缘化,即形成了镜像的第一阶段:主体的迷失。而在选择做林业实习生的逃避中,远离城市文明的平静林场使平野勇气对大山产生了认同并治愈了其内心创痛而实现了主体重获,并最终在大山与平野勇气的认同互动中进入了主体的自我迷恋阶段。平野勇气也实现了落榜高中生——林业实习生——大山之子的主体蜕变。
(一)欲望对象的缺席与主体的迷失
拉康认为欲望对象始终是一种缺位,形成了“存在/在场/满足”与“匮乏/缺席”的关系。电影中平野勇气遭遇了高考落榜、女友分手的接连人生打击,形成了欲望对象缺失与理想自我死亡的双重缺席状态。电影将人物异化于现实价值体系,在一系列的人生挫败之中平野勇气逐渐在现实的都市生活环境中丧失了自己。欲望对象的缺席造成了主体迷失的创痛,形成了电影被言说的多重交叉的语义维度。
平野勇气与石井直纪的互动关系成为电影生成多重含义和感触性的佳例:石井直纪的前男友成为平野勇气的镜像,而石井直纪亦是平野勇气前女友的镜像。两个人物被遗弃的创痛产生了对自我与他者的怀疑。平野勇气带着对宣传册里女孩的完美想象而重获欲望对象,然而石井直纪对其若即若离的关系形成了欲望对象的匮乏与缺席。欲望对象的匮乏与缺席给予了平野勇气走进山林的勇气,并在自然生态的治愈下获得新生,二人关系的确立成为互相认同的获得。城市来客同样是平野勇气的自我镜像。城市价值体系中的“慢生活”将神去村想象成理想生活的镜像,带着奇观欲望的观赏态度终将无法到达“理想世界的彼岸”,成为两种价值体系不可调和的隐喻。城市来客的新奇与初到林业学校的平野勇气的乖张成为互为映照的镜像。不同的是平野勇气对城市价值体系的“反叛”成为其走进自然生态价值体系的必经之路,也是获得新的认同的基础。在这种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平野勇气实现了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双重丧失,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与理想自我重建的双重获得,重申了欲望与匮乏、创痛与治愈的主题。
(二)心理创痛的治愈与主体的重获
拉康认为在与另一个完整对象的认同中构成自我。被现实世界抛弃的平野勇气在神去村重获认同。自然的治愈不仅治愈了欲望对象缺席所造成的创痛,还使平野勇气在枯燥的林业生产中产生了对山林的认同。平野勇气在自我救赎中重获人性的精神空间,逐渐以爱之名学会责任与担当的生命意义。最终在祭祀山神的大典中平野勇气的名字被收录进祭祀名单,姓名的确认既是新人际关系的确立与再平衡,也是新的价值观念体系的认同,完成了主体的获得。在此,成长于森林深处的百年树木净化了被功名利禄困扰的城市人的心结,给予了他们新生活方式的可能,浸润进对生命意义的新思考。电影中没有将平野勇气异化为英雄,远离城市文明的林场成为生态理想社群的生活模式,完成了都市观众对没有贪婪、懂得感恩的理想生活的投射和想象,映射了现代人群现实生活和精神空间的矛盾与危机。
电影所建造的生态空间中主体的重获成为人性治理的新途径。自然环境的独特描绘承载了更为重要的“自然治愈”功能。生态环境从被动呈现到成为电影叙事的主动因素,由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改造征服发展成为自然生态对人性的保护与修复。生态电影重新建立起自我、他者、自然及社会的诗意审美关系。电影虽然未将平野勇气塑造成“无父子”或“无母子”,但其家庭与现代价值观念共同离弃了他造成了一种匮乏。人生低谷的平野勇气并未获得父母的关注和救助,其最终选择出走以逃避这种匮乏造成的创痛。影片结尾平野勇气站在家门却被原木的味道吸引,正揭示了现代价值观念意义中的家甚至是城市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归宿而成为要逃离的空间。主体被自然生态再次召唤,自然生态观念选择与对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反叛,成为主体确立的重要标志。
(三)理想自我的镜像与主体的自我迷恋
电影《哪啊哪啊神去村》充斥着对男性气质的彰显。电影中以对饭田与喜为代表的男性角色健硕身体形象的长时间、多角度的凝视,使电影语言充满了诠释与再诠释的开放性。祭祀山神的大典中所有男性赤裸的身体凸显着男性阳刚,恰如与现实都市价值观念中被资本消费逻辑裹挟的性别弱化和男性气质的衰落形成镜像的对比。太阳、大树都被影像赋予了男性力量的肯定与宣泄。祭神用的大树被刻意塑造成男性生殖器官的造型。摒弃了现代文明的机械工具,重返传统时代的斧砍,巨型锯与男性性器官在画面构图中的重合,都隐喻着主体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叛和对自然生态中男性精神的回归。电影中对男性形象的选择和叙事中反复强调的男性气质成为主体自我迷恋的经典寓言。借助影像语言表现的逆光中饭田与喜砍伐参天巨树的身型,大树倒下,粗放、刚强的男性魅力得以彰显,正是主体理想自我的镜像。
男性主体的建构与差异性他者的出现成为主体对自我的另一种迷恋。男性的存在以被女性的需要而得以彰显。平野勇气帮助石井直纪洗净了青春的创痛,勇敢地在乡野间举起“爱罗武勇”(I love you)的情爱宣言。这种全能的主体性身份赋予了主体占有欲和控制欲的极大满足感,呈现出主体建构镜像阶段的指认方式和想象性的满足。女性作为差异性他者的形象填补了男性行动客体和欲望客体的匮乏,使男性主体获得再次确认。从理想主体的被遮蔽到彰显,电影以多重视角和对话的形式完成了生态电影的叙述范式。
二、生态电影的文化认同
麦茨(Christian Metz)将精神分析引入电影受众研究,“对视影片获得意义的观众的深层心理结构,以及产生和接受影片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论述电影这个造梦机器是如何运用想象性手法和技巧,通过制造出特有的观看情境,刺激、缝合了观众产生认同的幻觉和欲望,来说明电影实质上是一种迎合了观影主体的内在欲望和需求的想象性的建构。”与好莱坞生态灾难视觉奇观贩卖生态焦虑不同,电影《哪啊哪啊神去村》以非灌输语言和寓言空间,在自我身与心、自我与环境相互认同的和谐共振中使人得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启发感恩、责任与担当的共情。投射并回应着观众对传统生活空间的记忆和想象,将清新的乡野故事带入生态叙事中。生态电影能够跨越文化差异实现自然生态中人类生命的身份认同,将个人与社会、生态环境的权力关系重新思考。
(一)绿色生态与恋母情结
电影《哪啊哪啊神去村》将神去村塑造成现代城市文明之外的精神“桃花源”,成为现代都市精神荒原的想象家园。电影中不仅将女性对平野勇气的引领和感召与自然生态空间融合形成了母爱的呵护,呼应着人性的俄狄浦斯情结,给予了被以父权形象出现的现代城市文明价值观念所威胁的主体以包容和抚慰。对生态环境的母性化处理,以纯净的自然生态的治愈实现了被都市现代文明感染的人性净化和感召。电影在影视语言的语义中凸显了男性气质的刚强和赞美,却将女性的力量包裹成虽为隐秘却更为强大的精神动量。
平野勇气在浓雾的山林寻找孩子中获得山林神灵的回报,神的形象被刻画成柔美的女性身体局部,手作为引领的肢体寓言,再次凸显女性在人生迷惘时刻的引领作用。这种“超自然”的浪漫主义处理完成了人与自然的互动交往,将现实经验与电影叙事的“割裂”拓展了自然生态的“他性”内涵,升华了自然生态的母性气质。林场的生态空间彻底摆脱了电影寓言发生的空间场域,进化出电影语言的寓言功能。
让人引以为傲的木材品质、被饭田与喜撞死的野鹿以及蝮蛇,影片充分肯定了山林给予人们的一切,对生命尽情地赞美的同时还对山林——母亲的感恩。电影中流露出对森林巨大生命力的震撼与感叹,满山的树木从现代价值观念的“经济财富”意象转化为“精神财富”的生命精灵,成为生命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家园。对森林的认同内化成为对生命的认同,并将森林的巨大生命力注入枯竭了的现代人的躯壳,抚平焦虑而重获自我。山林教会了所有人重获爱的本能,如何让人内心充盈,因此山林同时被赋予了给予人类生命和精神原动力的母性特质。影片结尾平野勇气重回城市的不适与眩晕终究抵挡不住街头木屋的原木气味,亦是自然生态的召唤。平野勇气笑,不再迷惘,重回自然空间,成为绿色生态与恋母情结的完美诠释。
(二)山神崇拜与男性复归
现代工业文明的野蛮扩张,不断侵蚀农业文明的文化现实,揭示着社会变革对人类生存空间和情感体验的强烈震荡。市场经济的现实价值取向,城市空间的现代文明与乡野山林原生态的生活习惯和信仰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冲突,更是人类对现实生存空间和精神生态的痛苦挣扎。现代文明依赖于资本的消费逻辑,全然抛弃了自然生态的生长认知。现代性别意识展现出无性别或者中性发展的趋向,当前电影中中性气质的流行即是受众资本消费逻辑反向作用的产物。此时,中性不再是被阉割的、匮乏的、不完整的生命个体,而成为两性之间共趋的“第三性别”。男性气质的中性化美学指向遮蔽或回避了男性气质缺损现象背后的根源性问题。
美国电影理论家史蒂芬·沙维罗(Steven Shaviro)批判当代媒体抛弃了电影的认知性,青睐利用影视语言的感触性完成震惊美学的追求。而电影《哪啊哪啊神去村》将个人救赎与生态治愈融合,在生态环境对人性的净化中完成男性的成长蜕变。影片中不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有限索取与自然丰厚回报的良性互动。更为关键的是全片对山神的敬畏以影射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影片传递出‘人并非自然界中的暴君和全能的领主’‘人必须与大自然相对和谐地相处,否则将招来灾祸’。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转换为对生命的普遍尊重,并因此升华出生态电影特有的生命之美。在对自然的凝神关照和深邃思考中所生发出的思想,会贯穿在具有生态意识的电影作品之中”。
生态电影将生态意识充分融入到视听语汇中,将自然生态空间移置成电影的叙事空间。电影的生态空间摆脱扁平故事背景的僵化状态,从物性空间上升为男性成长的情感空间和精神空间。平野勇气进村时的框架式构图实现了都市空间与自然生态空间两个不同场域的隔断,更将神去村塑造成都市空间外的世外桃源——现实与理想的跨越。特别是片尾祭神大典上赤裸粗犷的男性躯体与庄重的行进仪式,点点火把不仅照亮了浮躁的现实世界的心理暗角,更成为一颗颗纯净安静的内心的象征。对“久久能治大神”的信仰成为人们对自然生态的敬畏,亦在自然生态中重新建构了现代社会式微的父权。影像语言中一个个健硕的男性躯体所呈现的不再是征服,而是以臣服的男性姿态,惶惶祈祷。这种非对抗式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俯视角画面构图的人与树的对比中凸显了自然生态的无穷力量。自然生态感召了无父之子的迷惘与彷徨,完成了古老的男性成长的主题。
(三)生态美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期的生态电影美学建构的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具有现代性的表达公民意识、实现精神皈依、顺应生态自然规律的非对抗性的精神空间,契合了当前观众的生态意识的内在诉求,并在生态美学观念上实现了跨种族、地域和意识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文与共振。国内学者陈阳认为,“生态电影研究首先反对的是消费主义。对资源无可遏制的贪欲,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且是生态的问题”。将生态电影批评引入对生态现实的关照,在生态电影的多重镜像的寓言中,穿过生态环境的表象进入人类社会和精神危机反思的美学指向。
“关注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涉及社会公正、正义以及种族、性别等大量社会现实生态问题,并探讨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关注生态公正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联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生态电影将自然与社会双重交叉的生态维度承纳于戏剧化情节结构之中,在理想生态空间与现实生活空间之间延展着复杂的生态视域,指涉了大量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态问题,迫使观众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八十万一棵的百年树木与亿万富翁的美好憧憬不仅刻画了初到林场平野勇气所代表的现实价值观念对生态环境的价值考量,也体现着对现代经济发展短视观念的批判。城市青年对慢生活的不同理解:城市对自然的新奇、奇观化表达 “原来不是用斧子砍的”,隐喻城市文明与自然生态观念的鸿沟而产生对城市的疏离并转向自然生态的价值观念认同。平野勇气的发怒成为价值观念转向的标志,既获得了村民的认同,也成为其对城市文化的反叛与现实价值观念体系的怀疑。饭田与喜对平野勇气的评价:既修不好树,也不会用大型机械,种树也不行,但平野勇气却获得了神去村的认同成为大山之子。这正是与现实价值观念对应的自然生态价值观念的反照。两性和谐、自然调和,充分地尊重自然生态的规律,少了战胜自然的豪迈而产生了敬畏之心,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也与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的长远发展观念契合。
结 语
生态电影《哪啊哪啊神去村》通过自然生态的治愈完成主体迷失与重获的人性救赎,实现了被现实价值压抑的自我认同的重建与满足,在自然生态叙事空间中寻唤跨文化、跨地域、跨种族的主体。“其超越族群,跨越国族,试图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其他物种关系中重设议题,重新感觉的恢宏态势”。独特地域性的空间生态景观与全球化语境的融合,将生态环境生产与个人生命的成长形成互文。人类对生态自然环境的价值观念最易跨越地域、文化、种族将人类形成命运共同体,实现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价值取向。生态电影呼吁调整人类的索取与付出的比例,使自然生态以可持续发展状态满足人类的欲望。这不仅关乎人类共同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将生态环境提升至了人类精神文明的神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