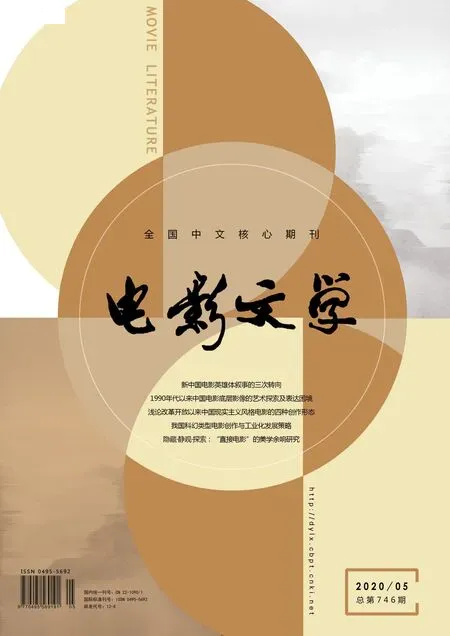景观再现与空间想象:《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媒介地理学凝视
高 尚
(滁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媒介地理学是一种关于人类与媒介、地理、社会等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的学说, 它既研究人与自然和媒介的相互关系,也研究人之间和媒介之间的空间关系。”媒介地理学的发轫可以追溯至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学说,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波兹曼的“媒介场景与社会角色变化”、梅罗维茨“情境理论”等,这些学者均或多或少地提及“媒介传播”与“地理空间”的关系问题。但彼时的媒介传播与地理空间依然存留在理论论述的层面上,随着网络传播的裂变式发展,“媒介形式的扩张,触角的伸展,传统的地域界限无可避免地被打破,原本异域的风景也借助全球化的媒介而被更多人所欣赏,虚拟与现实的情境更是相互渗透,建构起全新的地理空间”,这无疑是当下媒介传播与地理界域此消彼长式关系的真实写照。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媒介地理学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理论,由于自身的学科交叉性使得媒介地理学具备了被广泛运用的现实可能,而电影中的媒介地理学考察则使得理论学说在实践运用中具备了更加丰富的意义呈现。
一、影像再现下的媒介景观
“媒介地理学的核心议题在于既关注地理因素对媒介内容、传播符号和媒介形态的影响,也关注媒介对社会环境、地理样本、地理尺度的建构”。作为都市电影的宠儿,上海一直是人们乐于展开想象与叙述的对象。从张艺谋导演早期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李安导演的《色·戒》、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无一不在叙写着这个充满繁华与欲望的都市,既令人心向往又令人心生厌恶。人们通过影像再现的手段,将一幅幅历史画卷展现在观众面前,《罗曼蒂克消亡史》无疑也是其中的一员。“电影作为一种将真实和幻想用光影呈现的电子媒介,将原本想象的地图和真实的场景交会,从而形成独特的媒介地理景观”。高耸的楼宇、豪华的轿车、考究的服饰、精美的首饰、华丽的寓所甚至令人炫目的灯光,将这个具有“魔都”之称的十里洋场一览无余地映现出来。
(一)高耸的楼宇
故事开始的场景是淞沪会战前的上海——这个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大都市,影片虽然没有点明都市的繁华,但却给予了高耸的楼宇长达几十秒的运动俯拍。高楼大厦似乎是繁华都市的标配,这里是故事发生的场域。只不过这样的景物印象并没有存在多久。光影照射大厦的背后,那一片片不见光明的阴影似乎预示着战云密布在城市上空。在其后的镜头中,楼宇这一实物景观却也曾再次呈现,只不过这次却是战后崩然倒塌留下的残垣断壁。这种极具视觉张力的对比性手法也将上海这个在战乱年代中风雨飘零的都市形象传递给了观影受众。同时,这也呼应了影片的主题“消亡”,“消亡”的不只是罗曼蒂克,还有罗曼蒂克发生的场域。
(二)豪华的轿车
提及城市的繁华,自然少不了对车水马龙的刻画。然而,在影片中却并没有对此进行呈现,取而代之的却是干净的街道上留下为数不多的豪车、名媛。陆先生(葛优饰)与小六(章子怡饰)第一次的谈话场景设定在豪华轿车中,而在正式谈话之前电影镜头给予的却是车标的特写。这一举动则昭示了故事的主人公是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物。权力、财富与声望这些抽象性的社会分层概念,此时却无须过多地着笔。人物身份与城市繁华形成了相互辉映的态势,豪华轿车验证了人物的社会身份,而人物的身份地位又进一步映衬了城市的繁荣。
(三)考究的服饰
在正式进入影片没多久,出现了这样一段对渡部(浅野忠信饰)的描述:“他终年着质地考究的长衫,说着地道的上海话,跟沪上时髦的中产阶级一样又是喝茶又是泡澡堂子,经年累月,再看不出日本人的样子。”长衫这种极具时代特征的服饰在影片中已不单单是对历史面貌的还原,更进一步说它是人物个性、阶级、地位以及立场的象征性载体。渡部虽然常年穿着长衫以示众人,但在不见人影的背后却立马以和服的样貌呈现,他表面上是个上海人但骨子里却是日本人。除长衫外,影片中也涉及对西服、皮袄、长袍马褂、旗袍的描叙,每种服饰的出现则各自代表了不同人物的群体归属。以王先生(倪大红饰)为代表的长袍马褂和日本谈判代表的西装,则形成了强烈的中西、新旧视觉对比。“跳脱出电影本身,服饰文化反映的是特定历史大环境下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思潮”,不同人物的服饰设定也将彼时上海时局的复杂性与各方势力的交错性推到观众面前,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其中的剧情。
(四)精美的首饰
如果说服饰是本片最具有象征性的物质载体,那么影片中对于首饰的着墨则将电影提升到另外一种高度。精美首饰,贵妇人的用于装扮自己的饰物,与衣着相似,一般它可以凸显穿戴者的社会身份,成为炫耀财富的资本。但影片中涉及首饰的桥段并没这样简单化处理,而是将暴力美学的画面传递给观影者。被砍断手掌上所戴的玉镯以及樱花耳环,这些精美的饰物却与流淌的鲜血联系在一起,给人造成感官上的强烈刺激,从而使人对暴力的解读产生一种另类的想法。在这个充满繁华与富庶的地方,同样也会视人命为草芥,伴随财富名望的是随之而来的喋血暴力。
(五)华丽的寓所
寓所这个场域空间也是电影着力刻画的对象,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美好、浪漫、中产式小资生活的代言词。影片中寓所里所发生的场景多为吃饭,但这里的用餐却不是字面上的意义。食色性也,吃饭的场景却是为展现大都市里的生活与人性而服务的,通过寓所这个封闭的空间,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也得以丰富饱满起来。陆先生的内敛、王先生的老成持重、渡部的狡诈都发生在寓所中,寓所这个私密的空间元素为故事人物展现各自的性格特征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平台。影片结尾的时刻,陆先生回到已经破败的、被查封的寓所门前,经历战火的摧残,寓所已不复当年的华丽,这也验证了罗曼蒂克的消亡。
媒介所构建的影像景观给予了观影者自身想要的东西,实现了个人对作品的内容消费与符号解读,也实现了对现实地理景观的重建与延伸。《罗曼蒂克消亡史》不仅对旧上海地理景观进行还原与想象,也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与传统的角度对旧上海的地理意义加以重构,从而达到突破原有时空限阈的功效。影片中的楼宇、轿车、服饰等媒介景观承担了中介的角色,通过这些景观桥梁人们可以进行相应的观影仪式,这些特定的媒介景观也将特定时期下的地理样本呈现出来。通过媒介景观再现的手法完成对消逝年代的追忆以及历史的想象,这也正是媒介对于地理环境所能挥发作用的体现之一。
二、跌宕年代的城市想象
媒介总是在特定的地理基础上组织内容的,媒介信息传达总是带有地理特征烙印的。学者邵培仁在华莱坞电影发展史研究中曾做过这样的表述:“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它是地理与文化天然的融合。而江南影像正是在这样一种地理空间与文化形塑中诞生的对江南景观的建构与表达。”换言之,媒介地理学中所强调的地理空间是承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时间、空间等诸多要素的载体。地理区域作为表象的背后,对其空间意义挖掘才是内核。《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所描绘出的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道德地理以及性别地理,大致勾勒出人们对特定时期背景下的城市想象,也完成了对旧上海空间意义的开拓。
(一)政治地理
影片在政治地理上的发展主要有三条线索:家国政治、帮派政治与人情政治。淞沪会战前夕的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背景设定将故事的所有人物都拉进了战争的机器中。以陆先生为代表的爱国人士,借以时局太过敏感的理由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作为此时上海滩风云般的人物存在,陆先生并非不知断然拒绝的后果,为此他也付出了家人被杀的代价。同样,作为反派的渡部,原本是一个安逸的上海寓公,由于自己的偏执的家国信仰毅然投入战争,最终落个家毁人亡的结局;作为一部帮派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除了教父式的帮派枪战场面,它也兼有利益交换下的妥协让步。陆先生为了弥补自己的结拜兄弟曾这样说道:“银行的事情他好像有些不高兴,事情解决以后,我想把番禺路的厂子给他。”由于陆先生不同意与日本人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张先生(马晓伟饰)的利益,陆先生想通过馈赠的方式加以弥补。除了利益交换之外,其实这其中还裹挟一层更深的含义——张先生有可能为了牟利而去做汉奸。为了张先生也为自己的脸面,这是陆先生不愿看到的。同时,这也将故事中的人情政治——“脸面”给牵引出来;“脸面”不是故事的主线,但它却贯穿王先生的始终。王先生在面对小六与电影明星的奸情时,并没有下令杀掉他们而是让人把他们送到北方。这位饭桌上谈杀人没有丝毫畏惧之色的人并非害怕,而是那样做会有损自己的脸面。常年在身的长袍马褂验证了他是传统的代表,某种程度上脸面比生命重要,由此确立了属于他的人情世故。
(二)经济地理
美国人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新口岸的开放和对新贸易的无限的期待,招得世界各处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人除去靠他们的‘机智’(应当是诡计多端)为生而外,别无任何行当或职业。”民国时期的上海滩也并未逃脱这样的窠臼,它既是犯罪者的天堂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影片中,陆先生手下的一个马仔(王传君饰)问另一个马仔(杜江饰)来上海的原因,对方这样答道,“世道不好,想到上海来学做生意,赚点钱”,其言外之意无不透露着这里是财富获取、机遇寻得的好地方。同样,在面对工人罢工时,陆先生有着这样一番话:“这些人(罢工工人)没有正常人的情感,他们不喜欢现在这些,高楼啊!秩序啊!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他们都不喜欢,或者有着其他什么目的,毁掉上海也不可惜。”其实这段台词足已验证此时上海的繁华,高楼、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这些都是城市外化的物质象征。也正是这些繁华造就了上海滩的帮派林立、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人人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进而在人脑部世界中建造起一座符合弱肉强食法则的城市空间。
(三)道德地理
“不同的地理空间具有特有标准的约束,而且,在个人身份定位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相对的影响因素。”陆先生的爱国行为是道德,陆先生的杀人行为也是道德,可以完美验证上述论断。在外寇入侵的状态下,拒绝与日本人的合作是其民族气节的表现,枪杀日本谈判代表是其为亡者复仇的义气使然。中国人与帮派大佬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在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传统的道德方式对其似乎并没有约束力。或许,乱世下的大上海,遵从自己的道德标准才是最好的标准。王先生不愿意杀小六,他有着自己的处事标准;一心向往爱情的小六,不顾传统伦理的约束,不惜以身犯险也要与男明星在一起;日本间谍渡部,在自己妻儿面前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转身背后又成为实施性虐的变态。或许是战争造就了这一切,但道德这个命题本身就与人性紧密相连,与其说这是关于道德的描述倒不如直接称之为人性的呈现。
(四)文化地理
吃讲茶、地方小吃、方言……这些极具地域文化色彩的空间存在,似乎支撑起了整部电影的文化地理图景。吃讲茶是旧时流行江南的社交风俗,民间裁决纠纷的一种方法,它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门程序:约定的地点、具有社会威望的仲裁者、相应的吃茶仪式。吃讲茶如经调解不成,则往往酿成凶斗。电影开始时渡部与北方客(赵宝刚饰)吃讲茶桥段便是这种地域文化的鲜活展示。为了表现地域文化,除了吃讲茶这种形式,地方小吃也是影片的另一亮点,如上海汤包。正如酸甜苦辣咸具有地域之分一样,食材也有地域之分,北京烤鸭、兰州拉面、西安羊肉泡馍、重庆酸辣粉……地域小吃脱去食材这个外衣,其实质却是一座城市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汤包这张地域名片,以及在电影中反复的出现,仿佛无时不在提醒着观众的认知。如果说地方小吃不具备典型的文化意义,那么影片中的方言呈现则显得惊艳许多。某种程度上来说,方言更能代表地区文化特色,方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语言使用的过程其实也是社会性、关系性体现的过程。”方言中所蕴含的文化性与社会性成为地域十分凸显的外在表征。在一定程度上,方言这种强势的方式为给大家营造一个更投入、更真实的旧上海提供了便利条件。
(五)性别地理
影片将性别这一兼具生理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向概念,使用视觉化与情节化的方式进行了处理。光鲜的旗袍与考究的长衫,通过服饰差异化的视觉呈现本身就能代表人物性别上的差异。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中,旧社会是没有性别平等的概念的。故事伊始,大多的女性人物设定多为一种附庸般的存在,她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小六也好,小五(钟欣潼饰)也罢,包括吴小姐(袁泉饰)与王妈(闫妮饰),她们都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但随着故事情节的推动,这种人物印象逐步得以修正。向往爱情的小六试图突破既有生活的枷锁,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原本安静温顺的小五突然有了自己的爆发;吴小姐在接受被丈夫抛弃的同时,也勇敢地接受了戴先生的追求。这些女性人物身上所展现出的自我意识觉醒作为故事情节的一部分,本身也强力地推动了故事的情节发展,进而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
“空间作为媒介的体验与实践渗透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感知和想象中,空间的生产也成为一种媒介,展现出空间奇妙而丰富的人文与社会内涵,呈现出空间媒介化的特征和作用”。由政治、经济、道德、文化以及性别交会而成的地理图景构筑起了作为旧上海大都市的空间地貌,其中所呈现的人文社会景观完成了人们对魅力之都的社会文化想象。影片所表达的家国、爱恨、情欲等相关主题,深刻赋予了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以鲜活的生命力,同时,也将特定时期下的社会历史给予揭示。
三、对都市影像再现的反思
《罗曼蒂克消亡史》作为一部艺术商业片来说,它完成了自己在艺术造诣上的任务,但在唯票房是从的标准下,作为商业片,它又是失败的。这其中固然与电影的营销方式以及非线性的叙事手法有关,诸如宣传不到位、非线性的剪辑造成一定的观影障碍等相关因素。但从都市电影的角度来看,它的出现为我们思考都市影像再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一)都市影像的中心化
影像作为都市再现的手段与方法也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而在诸多影像方法中,电影却是最为润物细无声的一种。相比较城市宣传片,电影并没有那么直接与生硬,后者往往在城市宣传中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在都市影像再现的问题上,作为都市区域描述的电影也出现了属于自身的问题——中心化。所谓都市影像的中心化,实指电影在都市呈现的过程中其集中程度比较严重,往往发达城市的影像呈现概率要远远高于欠发达地区。致使这种结果的因素有很多,如故事的背景的设定、对历史客观事实的尊重以及影视创造的偏好等都能够造成这样的结局,但这并不符合价值多元以及区域协调的社会理念。每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故事,镜像式的影视呈现不应该成为某种偏好。在某种程度上,北上广及港澳台,这些都市影像的宠儿,它们是影视与资本合谋下的结果,而不应该成为都市影像的全部。都市影像的中心化其实质反映的是一种媒介呈现的选择性以及地域选择上的偏见,这是种典型的“精英史观”应当值得人们留意。
(二)都市影像的区域性与整体性
如果说都市影像的中心化是一种理念问题,那么都市影像的区域性与整体性则是一种操作问题。它讲述的是都市电影如何走出都市的框架走向全国乃至全球的问题。在媒介地理学中,“媒介尺度主要表现为媒介的本土性、区域性、全国性、全球性这四个特质。其中本土性和全球性是联系媒介与地理最最重要的两个尺度。本土性与地方密切关联,而全球性则与世界紧密相关”。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都市影像所反映的已经不是单个的地理城市,它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影像化的某个地区性都市它不但是一种区位上的指涉,还应该做到不同政治、经济、文化间的融合,实现媒介与社会、媒介与地理之间、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共鸣与溢散。因此,在都市影像的区域性与整体性的整合问题上,可能颇费精力,这里既包括都市题材影片的创作也包括其后传播方式的选择。
(三)都市影像的刻板印象
都市影像中心化的后果除了都市呈现的选择性以及地域选择上的偏见,其实还囊括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都市影像的刻板印象。由于在都市呈现的过程中的高度集中及反复使用相同主题的城市表达加剧了人们对相关都市的刻板印象。提及上海仿佛它就应该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但过去与现今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存在,媒介地理学所强调的流动性与相对性却并没有得以体现,造成繁华假象的背后免不了都市影像的“功劳”。有学者指出,造成刻板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权威的顺从,对传统的顺应”。对于都市影像的刻板印象而言,顺从权威做法、顺应传统规范,只是表层的理由,其实质却是内生原创力的不足。当然,笔者这里并非鼓动大家去颠覆传统否定权威,而是期盼在未来的都市影像作品创作中能够融入更多的思考,能够产制出更多公正客观的作品。
结 语
用镜头反映历史,用景观书写想象。媒介是反映社会的镜子也是人们感知日常生活环境的信息来源,而影像媒介的出现让人们有了突破时空限制展开思维的可能性。媒介是流动的,不单单是指地理空间上的流动,也可以是时间发展上的流动。通过电影叙述展现历史风貌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手段,《罗曼蒂克消亡史》这部兼具黑帮题材与谍战题材于一体的民国群像戏,在镜头、台词、服饰道具等元素的烘托下展现出现代人对旧上海大都市的空间想象。它实现了媒介地理学中的媒介、地理与社会等诸多要素血脉式的联动,它为人们的空间想象提供了诸多的样本。“媒介传播与我们对地理乃至对民族国家的判断和认识从来都是依赖媒介(文学的、新闻的、图像的等)的描述。我们所有的地理观念,更多的是媒介帮助我们建构起的一个“‘虚拟的实体’和‘想象的共同体’。大众媒介作为这种‘想象’的媒介,它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与过程。使千百万陌生人形成同为一族的印象,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地理’”。电影中所呈现出的实物景观也好,地理空间也罢,“其指涉并不只是简单一一对应地表现既存现象,而是传达了更为活跃的信息,最终目的在于让人们从中选择和重组地景中的文化意义”。换言之,虚拟影像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折射,人们在其中可以找到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从而对既有的道德价值与社会秩序展开合理的想象与认同。本文以《罗曼蒂克消亡史》作为蓝本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媒介地理学的解读,以此而引发了对都市影像再现的中心化、区域性与整体性以及对于城市空间的形象塑立问题的相应反思与展望,希冀这些能为人们的后续研究与实践提供些许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