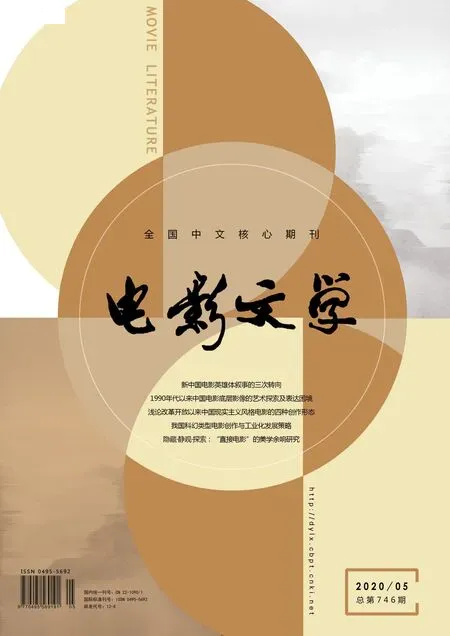试论横店影视城影视旅游消费中的图像迷恋现象
徐开阳
(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 洛杉矶 90007)
一、引 言
横店影视城坐落于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作为中国最大的影视基地,横店影视城每年吸引大量剧组前往拍摄和制作影视剧。横店影视城以导演谢晋拍摄《鸦片战争》为契机而建成,并随着中国影视产业的振兴而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有广州—香港街、明清宫苑、秦王宫、清明上河图、红军长征博览城等13个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仿真建筑群以供影视剧拍摄和游客游览。目前对于横店影视城的研究多集中在影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方面,尚未就图像在横店的流行及其与旅游消费的关系展开讨论。
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横店影视城是以观光娱乐休闲为导向的欢乐王国,也是经影视图像切割而成的以视觉为主导的图像王国。许多游客在仿真古代建筑前身着古装拍摄照片或者个人微电影,成为影像世界中的主角;商家渴望通过与知名演员合影造就明星效应,从而招徕顾客;影视剧照被包装成促销广告,吸引游客购买影视主题的纪念品和食品。这些现象可以被归结为“图像迷恋”。
“图像迷恋”包括迷恋事物的图像或迷恋成为自己的“仿像”。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其著作《仿像与模拟》(或译为《拟像与仿真》)中谈到 “仿像” 与“模拟”两个概念。“仿像”(simulacra)意为像、幻影、模拟物。“模拟”(simulation) 在书中语境下意指仿像的形成过程与机制,有模仿、仿拟的意思。美国左翼批评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解释道,“仿像” 是 一 种 “没 有 原 本 的 东 西 的摹本 ”。“摹本”是对原作的复制。在现代社会,正如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所述,随着摄影、印刷等技术的发展,艺术著作能够被拍照,而照片可以被大量复制。这些照片虽然是对原作的完全复制,但正是因为这种可复制性,它们失去了原作的独一无二的气韵(aura)。本雅明实际上指出,复制品能使人感触到某种真实,但它无法替代原作的价值。与复制品不同,“仿像”是对本身就不存在本源的事物的摹制。因为没有本源进行对照,仿像无法被置于“真”与“假”的二元评判标准当中,它构成的是消解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超现实”。游客在浏览横店影视城时对仿制建筑群的信以为真,以及影视城中基于图像的营销与消费,体现的正是对超现实时空的幻想与沉溺。
为游客拍摄微电影的项目则体现出“图像迷恋”的另一方面,即对于完美主体性的迷恋与对自我的他性的欲望。人们看到镜头中自己的图像,就如同看到了镜子中的“另一个自己”。拉康(Jacques Lacan)在阐释其镜像理论时提到,镜中像是构建个人主体性的重要机制,而认出镜中的自己同时也是一种错乱的认识,因为这种“认出”实际上是把“那个人”认作“自己”,而那个镜中人是自己更完全、更完美的像。镜像机制表达出对于理想自我的欲望,同时也制造了主体性的自我疏离。影视图像制造虽与镜像制造不尽相同,但在“制造另一个自我”方面有较高关联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图像迷恋也是对更完美的自我的渴求,也可以说是对于作为自身仿像的他者的追求。这个另外的自我与真正的自我以图像为媒介共存,导致主体意识也变得超现实。
横店影视城中的“图像迷恋”一方面带来一些机遇,一方面则掩盖了许多问题。比如,聚焦于图像的旅游模式使得横店很容易成为“打卡”剧组取景地与“明星聚集地”的代名词,而游客与影视产业之间的互动并没有成为横店影视旅游的关切点。本文围绕横店影视城内游客对仿拟时空、饮食、微电影体验三方面的消费,通过分析影视城内仿像的生成与“图像迷恋”现象,探究“图像迷恋”对横店文化景观与旅游体验的深刻影响, 并厘清这种旅游体验与消费是如何既与“图像迷恋”现象相辅相成,又构成对于“图像迷恋”的反思。最后,本文试从图像与影视旅游消费的关联方面对于影视城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二、图像穿越:消费仿拟时空与现实的退场
在横店影视城,在同一空间内往往排布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宫殿与街道的仿制品,身着不同历史时期服装的群众演员常常围坐在一起就餐,餐厅里也经常提供仿制古代宫廷风格的食物,重建的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之外是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以视觉复制为准则的空间逻辑打破了时间(历史)秩序,使得游客能够轻易产生一种跨越时空,超然于现实的乌托邦式体验。
图像是这种乌托邦体验的核心。海报、照片、视频、主题公园……图像锚定了游客对于所见本身的认知,使得他们不再透过图像去追寻事物本身的意义。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仿像是难以抗拒的人造的蒙太奇与无意义的折叠”。正是因为仿像的无意义在图像的复制与拼贴中变得似乎有意义而为人所难以抗拒。影视剧的制作正是基于对真实存在的复制与加工,或者更确切地讲,是对已经被叙事所复制、加工过的社会现实的影视技术再复制。这种对现实的双重复制并非虚假,因为在复制之中,真与假的界限被消解,也就不再存在相对于“真实”的“虚假”,只存在一种“超现实”。但不可忽略的是,因为这种超现实往往说服观众不再去深究仿像制造与银幕/镜框之外的多层次的社会现实,它带有乌托邦式的虚无和欺骗性。
对图像的迷恋是一种新的空间意识。正如迪士尼乐园本质上是乌托邦一样,横店影视城打造了一个完美空间,它消除了对现实的怀疑,实现了对时间流逝的逆转。横店影视城的设计正如朱利安·穆尔菲特(Julian Murphet)对后现代建筑的评论中所言, “超越了精神价值……和人文主义的范畴,进入了一个自由浮动的、短暂的、抽象的、多重映射的世界”。这是因为横店影视城中的建筑群可以在影视拍摄中随布景的变化而改头换面。这些能够被快速改造、消费和抛弃的空间的价值在于它们在电视和电影银幕上制造的仿像。然而,游客们并未感觉他们被充斥着仿像的空间所愚弄;相反,游客们喜欢在仿制建筑前身着古装拍照。他们只需要把仿制的“紫禁城”当作真正的紫禁城,为自身的仿像和“紫禁城”的仿像的结合体进行消费,并从中体验快感。从一则视频采访中可见,在2018年度热播剧《延禧攻略》《如懿传》播出后,大量游客来到横店影视城中的“紫禁城”,想要寻找剧中的场景,甚至带着剧照来现场比照,再拍下手举剧照在该拍摄场景的照片。许多游客根据电视剧中的宫殿名寻找延禧宫、长春宫等,有两位游客还想要寻找《如懿传》中的冷宫,然而却发现那个冷宫作为临时搭建的布景早已被拆除。这类“打卡”式游览以影视剧为导向,追求的是将影视剧中的虚拟空间和叙事具象化,实则最终归于对影视剧仿拟空间和仿制的“紫禁城”的双重图像迷恋。清宫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清代宫廷文化如何在影视中被表达等文化性内容并未能在横店出场。
横店影视城也具有历史时空的跳跃性,使得旅游体验基于但不限于对仿像的消费。在影视城中,游客能够一次性浏览民国时期风格的广州—香港街、秦汉风格的秦王宫、宋代风格的清明上河图宫殿群、按照故宫比例修建的明清宫苑、战争年代布景的红军长征博览城以及互动性很强的梦幻谷。梦幻谷中有大型游乐设施,以及火山喷发、山洪暴发等自然现象体验区和夜间游览项目。多层次历史时空的仿制与铺陈吸引了游客购买景区通票,可供游客在以上景区中任选3个外加梦幻谷进行游玩,票价在450~520元之间浮动。梦幻谷的存在使得游客对仿像的消费延伸与变化,它如同一个进出仿像时空的节点,提示着图像迷恋之外的现实性娱乐消费,而后者作为图像迷恋主导的旅游消费的补充性旅游产品,往往自成一体,无法为横店影视城的仿拟历史时空提供切实的内容补充。
三、品味图像:饮食消费与阶层问题的失语
横店影视城中有关饮食的图像复制背后充满资源流动和一定程度上的阶层关系隐喻。需要注意的是,“阶层”与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多种因素有关,在这里暂且只讨论其作为基于收入水平和社会资源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社会动态,而非政治概念。在影视剧制作中,食物作为道具不可或缺,通常由道具师提前购买原材料或准备好菜肴。如果演员们不需要真正在拍摄中进食而仅仅是表演进食,即“假吃”,那么菜肴只需要外观良好,不需要真正煮熟或者制作精良。诸如面粉、大米、蔬菜和面包等一般性食物,因其通常不需要被特写镜头拍摄,往往被多次使用,直到变质。如果演员们确实要在镜头前食用食物,那么剧组通常会精心准备菜肴,有时还会从当地的星级酒店订购菜品,或者专门聘请厨师随时制作菜肴以供拍摄。出于经费考虑,剧组也常使用塑料模型食品。另外,剧组中何人接触、安排食物与剧组中的等级关系与人力资源分配息息相关。处于较高职位的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通常与食物道具保持一定距离。道具师和场工主要负责安排、放置与收捡食物道具,他们有时还会让群众演员帮忙。总之,食物的重要性与它们在镜头中的形象有关。当食物出现在镜头特写中,并与主要角色和剧情密切相关时,它们的地位则得到升级,成为涉及主要故事情节的重要标志。然而,经过银幕传递后的食物图像,其位于观众想象中的色香味已经掩盖了其背后的人力资源分配和影视剧拍摄过程中所隐含的一定的等级意识。
影视拍摄过程中对食物的应用充满表演性,同理,横店“影视菜系”的营销也是一场基于仿像的制造与流传的展演。“影视菜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与被拍摄的菜肴相关的仿制菜品,明星经营的餐馆,以及首先在明星中流行,然后在大众中流行的食品。“影视菜系”的流行是跨越现实和网络虚拟空间的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现象。电视节目、照片等传统媒体,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点评网站、外卖软件等,已经成为“影视菜系”营销与消费的重要渠道。例如,“美团”和“饿了么”订餐平台上有诸多商家打出以“××明星最爱/推荐”为名的菜品,吸引游客或者当地居民订购。广泛流传于各类媒体平台上的“影视菜系”的图片也推动了兼具现实性与虚拟性的食物消费。
“影视菜系”营销搭建了明星和所谓“普通人”之间的桥梁,但这种联系只是一种基于仿像的想象,承载着对于阶层跨越的渴望。许多餐厅店主在店门口的屏幕上滚动播放自己接受电视台节目采访的画面,也有许多店主挂出与前来就餐的明星的合影。一家主营东北风味的餐厅甚至用店主与明星的合影照片装饰了所有的墙壁,构成了一场大型“明星合影展”。餐厅老板与明星合影的那一刻是他们生活轨迹重叠的唯一的点,照片产生的一瞬间也是二人阶层交叉的结束。尽管如此,正如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对于照片的分析,“摄制的图像无须在‘真正的现实主义’与‘伪现实主义’之间挣扎”,因为照片的内在逻辑就是——它就是原型本身。这些照片因对当时状况的复制,而使人相信该餐厅在横店餐饮业中的明星地位。但是,这种对于照片的利用却无形中将其对现实的复制转化为了一种表演性质的仿像,其所指已经不再是合影这一事件本身,而是现实中并不一定存在的事物:该餐厅的高品质或者名望。这种仿像在巴赞所提的现实主义与伪现实主义之外,更类似于詹明信所说的“照片现实主义”(Photorealism),也就是说照片中店主与明星的亲密关系在“真实世界”中无迹可寻,因为照片“本身就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真实世界,并对这个自我制造进行仿拟”。
另外,当堆砌着照片的墙壁变成了集体仿像的制造场域,店主在墙上贴出的一条“禁止拍照”的警告却表明这个场域拒绝被再一次复制。拒绝再复制体现出“图像迷恋”背后对阶层跨越的欲望。通过阻止游客拍摄墙上的照片,店主把自己打造成一位不可复制的明星,一个更完美的自己,并保持着其与“普通人”之间的微妙距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不断的图像迷恋和复制中,人自身变成了另一种媒体,进一步复制着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并说服自己应该迷恋、奉行“成为强者”的阶层跨越逻辑。
需要补充的是,本文基于阶层与图像之间的联系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并将阶层暂且划定为以收入和社会资源为导向的一种评判标准。但当今社会划分阶层的标准越发多元化,单纯的收入和社会资源增加并不能代表阶层的提升。另外,个人对于阶层的认知可以具有自由性,并非统一以收入为导向,也就是说,现今“阶层”越发成为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甚至可能是伪概念。横店图像迷恋现象背后对提升收入、获得社会资源、实现“阶层”跨越的渴望,其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社会资源流动与分配的复杂图景的“仿像”。
四、成为图像:微电影消费与“深度游”探索
在对影视旅游的内涵进行阐释时,周伟斌指出:“早期的影视旅游着重强调影视作品拍摄基地作为旅游吸引物而形成的旅游经济形态,是影视旅游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的影视旅游产品较为单一,旅游体验以静态的基地观光为主。”而近些年的影视旅游开始拓展游客与影视基地之间的动态关系,引导游客成为影视基地和电影文化的活跃参与者。近年来,横店影视城推出了“深度体验游”项目,为游客拍摄微电影,让游客体验成为主角的乐趣,而不再仅仅行走于仿古建筑群中或者期待偶遇明星。在拍摄现场备有专业的化妆师、造型师、摄像团队、后期剪辑团队,还会提供剧本供游客选择,并配有导演执导游客入戏。作品可分为MV、约30分钟时长的体验版微电影,以及私人定制版微电影,价格从几百至几千元不等。
从游客的角度来看,微电影消费体现着对于成为不同情境中的“另一个自己”,或者说“自我的他性”的迷恋。除此之外,微电影消费还隐喻着暂时切换社会角色的猎奇心态,以及成为个人生存环境中的主角,掌握现实社会资源的渴求。然而,当这个另外的自我本身就是一个超现实的仿像时,自我便无法与仿像最终成为一体,那个看起来更完美、有趣的仿像便只能禁锢于影视旅游这段特定的时空记忆里。
个人微电影拍摄项目一方面使得游客了解到影视剧制作的基本流程,获得了更丰富的旅游体验,另一方面则面临着模式化的问题。虽然游客可以根据喜好增加台词或者场景,甚至可以以较高价格拍摄私人定制微电影,但从整体上来讲,为了迅速制作出成片,微电影拍摄以及后期制作会套用固定模板,这也就将游客个人的主观性和创造性排除在影视制作、创作之外。这并非意味着游客任剧组摆布,而是意味着个人微电影拍摄并没有为影视行业之外的个体提供了解、参与影视行业的真正机遇。微电影拍摄以图像的制造仿拟出一种并不切实存在的个人与影视行业的接触途径,这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影视行业的封闭性。微电影项目的宣传口号之一是让有着电影梦的普通人实现“演员梦”,这个宣传暗含了影视行业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较为显著的一条是影视行业背后巨大的资本利益链条,而这样的距离并不能凭借“成为图像”而得到弥合。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对影视城的时空消费、饮食消费,还是微电影消费,都呈现出以影视城图像制造为主导,游客围绕图像迷恋展开消费这一特点。那么游客与影视、影视城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在以资本交换仿像的逻辑之外,横店影视旅游怎样才能真正成为“深度旅游”,还有待深入挖掘。
结 语
对于仿像的迷恋是横店影视城中的旅游营销与消费的重要特点。当游客身着古装、旗袍在建筑群中穿梭留影或者拍摄个人微电影时,这种图像生产是对原本不存在的事物的复制,因为在真正的历史时期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位民众,但这种穿越了时空的仿像制造却为游客带来了自我满足。又比如,商家与前来就餐的明星合影,这种照片是对当时状态的复制,但是当商家利用这些照片来证明其餐厅的品质时,这些照片就成为带有象征意义的仿像,因为它并不是对餐厅品质的直接证明。无论是游客古装照还是与明星的合影,都吞噬了真实与非真实、自我与仿自我的界限,也模糊了仿像之下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文化动因。由此可见,横店图像王国对图像以及由图像所呈现的表面化感知高度依赖,从而掩藏了图像制造机制之下的消费逻辑和社会阶层动态。正如朱利安·穆尔菲特所述:“文化对象缺乏深度与消费主体缺乏深度相匹配:两者都是从无底洞般绵延不绝的图像的碎片中捡拾而来的。”这种影视旅游模式的问题在于其高度依赖表面化的图像,从而引导游客不再关注图像边框之外的规训着他们的消费模式,也模糊了图像迷恋所代表的对阶层跨越的渴望。在这种迷恋之下,身体被银幕解构并转化为图像信息这一事实被封禁在无意识的身份危机中,也使得与此相关联的阶层症候被简单化为“明星效应”的话语。
横店通常被称为中国的好莱坞或宝莱坞。从某种程度上讲,横店影视城与其他一系列影视城也是互相不断复制的仿像,但谁是谁的仿像,这个仿像又是什么,仍有待探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横店影视城以“图像迷恋”为主导的运行模式拉动了影视城的发展,也掩盖了图像生产、复制与旅游消费、阶层分化等社会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从以下几方面为横店影视旅游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1.提升景区文化内涵,重视影视产业的现实功用,以影视制作为基点,开展文化推介、博物馆建设、影视史展览与教育等活动。
横店影视城以仿像为主导的消费模式并非与充盈影视旅游的现实意义相矛盾。如果能够以建筑群仿像为切入点,引导游客在体验仿真历史时空的同时真正获得历史文化知识的熏陶,那么,横店影视城可以成为兼具旅游休闲功能与现实社会效益的场所。
2.规范景区餐饮行业管理,解构对于“明星效应”的盲目追求。
“影视菜系”市场的红火以及餐饮业利用仿像制造明星效应,获得经济利益的现象,本质上是将明星置于“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社会阶层,从而引导游客对明星餐饮进行消费,制造出以餐饮为媒介的阶层跨越的心理满足。然而,这很容易为餐饮行业的不规范操作提供空间。因此,打破明星神话,正确对待、定位影视产业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角色是必要的。
3.开拓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深入互动关系,提升游客参与度和主动性。
如前文所论,微电影体验并不足以成为景区发展“深度游”的灵丹妙药。如果游客能够真正参与到个人与影视产业互动关系的书写与调试中,比如提供机会让游客自己言说“我与横店”的叙事,那么游客与影视城便能够形成良性对话,既提升了旅游体验,又能够促进影视城更好地服务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