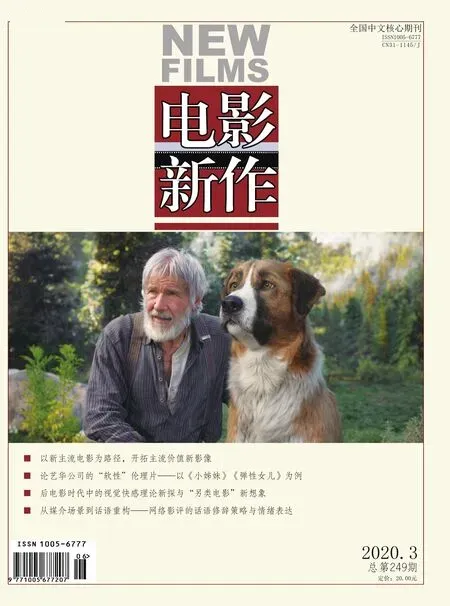虚拟现实电影:“洞寓”的坍缩与观者的再塑
潘璋敏 汤雪灏
VR技术究竟是为电影艺术带来了新的可能,还是如电影之于摄影一般,分化为一种新的影像艺术类别,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虚拟现实电影(VR电影)的问题上,持乐观态度者普遍认为是现有的技术水平与电影语言制约了VR电影的进一步发展,而反对者则旗帜鲜明地指出“VR不是电影艺术的未来”,而只是由技术商人推动的一次电影技术伪革新运动。作为一种新兴的影像技术,现在对其盖棺定论还显得为时过早,电影艺术在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中,一直以包容性的姿态完成了数次自我迭代。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洞寓”的坍缩、“完整电影”神话的建构,以及观影者的地位等角度对虚拟现实电影进行考查,试图探求虚拟现实电影在当下发展中所遭遇的症结与对策。
一、虚拟现实:影像技术的新变革
“虚拟现实”一词出自法国戏剧家翁托南·阿铎在20世纪30年代写就的《剧场及其复象》一书中,阿铎对虚拟现实的定义是“精神的复象,可以帮助观众、参与者进入另一种精神的世界内”。当下的“虚拟现实”一词则更多地指借助VR头显、沉浸式外设等技术手段实现的沉浸式、交互式视听体验的影像设备。追本溯源,我们可以发现“虚拟现实”的设想动力与技术积累更为久远。业有学者已经指出,《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这一物件,“同今天的虚拟现实设备实在是太接近了”。而基于双目视觉产生立体效果的VR设备的技术雏形,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立体视镜设备。1820年代晚期,生理学家发现了视束交叉(optic chiasma)的生理现象,在科学意义上解释了双目视差的原因,立体镜随之诞生。这些文学幻想与技术积累,为VR影像的诞生在历史脉络中埋下了伏笔。
近年来,再度兴起的虚拟现实技术热潮,给电影、游戏甚至工业领域等诸多行业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但是在它是否适应已经发展了百余年的电影艺术,仍旧是一个疑问。VR电影指的是使用虚拟现实(VR)技术制作的电影,需要佩戴VR眼镜等设备进行观看。在体验上,这种形式能够给予观看者很强的参与感,甚至得到戏剧的临场感体验。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全新的电影形式融合了戏剧与电影的优点于一体,在真实感、沉浸感与体验感上,VR电影可以说是强于传统的平面电影与立体电影。但是VR电影究竟是电影技术的变革,还是诸如之前“4D电影”“5D”电影等电影技术演变中的昙花一现,学界与业界尚无定论。
VR技术本身的“中心化”与“视点化”,并不能很好地与成熟的电影语言相结合,传统电影中历经数百年才发展完善的视点、焦点、景深、景别等电影语言在所谓的VR电影中近乎失效。在现有的一些以短片为主的VR电影中,对视点的处理一般都采用了具有参与感的第一人称视角,如《救援》(HELP,2015)、《紧张症患者》(Catatonic,2015)等作品,均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制作,能够给观众带来极强的临场感与参与感。而在焦点与景深的问题上,由于人眼的生理结构制约,以及技术水平的限制,暂时还没有可能做出真正的全景深电影,现有的VR电影几乎都是将焦点固定在叙事空间以内,这样做即是对观者的一种视觉引导,同时也是对客观因素的一种遮蔽。在景别的问题上,VR电影同样面临的十分严峻的考验。在传统的电影语言中,特写展情绪、近景看动作、远景造氛围几乎已经成了固化的定律,而VR电影由于自身的开放性与观察者的可移动性,固定景别的概念近乎消失。更有甚者,观众可以自主地取景、推拉眼前景物,这对没有接受过专业视听语言设计训练的广大观众来说,无疑将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众甚至还会在专业人员营造的影像环境中“取景”出一些“劣质影像”,这些“劣质影像”无疑会妨碍叙事的流畅性与画面的美感。但如果将观众固定在某一位置被动地去接受影像信息,那么VR电影又将存在退化至“环幕电影”与“360球型银幕电影”的境地,失去了虚拟现实语境中最为重要的互动感、参与感与不确定性。
我们可以假设或者展望,在未来成熟的VR电影影片中,将会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视听体验。如果说未来的VR电影可以达到成熟的“沉浸戏剧”那种临场感与参与感,VR电影或许能给观众在观看电影之时带来更多自主的可能。毕赣导演的处女作《路边野餐》(2016)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镜头,在陈升与卫卫在结束在小镇的游荡之后,他们将乘坐摩托车去往河边离开荡麦。在这一段的处理中,导演没有选择让摄影机紧跟着陈升与卫卫做一个跟随镜头的处理,而是在隐隐的雷声中,让摄影机突然向路边的一个巷道转去,“抄近路”式地到达主路之上与骑着摩托的陈升叔侄相遇,然后摄影机继续跟随纪录他们的荡麦之旅。在笔者看来,未来的VR电影至少要能完成这样的技术,让观众有权力自主地选择从哪条道路跟上电影的叙事内容,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成熟”。
二、“洞寓”与“完整电影”的神话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开篇明义地指出:“人类无可救赎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桑塔格借此评述摄影影像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而电影的造梦机制更加的强化了这种“洞穴之寓”。现代电影院在结构上与“柏拉图的洞穴”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说现代电影院是“洞穴”的话,那么以VR为代表的虚拟现实设备,则是“柏拉图洞穴”的2.0版本。
传统的电影形态,无论是从幻灯时期的煤油灯、电灯投影,还是当下的激光技术,其本质都是使观众看到发光体投射在幕布上的反光影像。而VR则是直接注视作为“发光体”的屏幕设备,这是一种可以类比为在“洞寓”中走出洞穴的人类直视太阳的观影形式。在“洞寓”中,柏拉图称走出洞穴的人类在适应太阳的光照之后,终于看清了这个“真实”的世界。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了鲍德里亚在《拟象与仿真》中的论断,“拟象从来不是要隐藏真相——它就是真相,它要隐藏的是没有真相”。虚拟现实中的影像,不再是对物质现实纯粹复原,而是出现了许多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拟象”,这些“拟象”在脉络肌理、运动轨迹与视觉感受上与真实视觉体验相符,即是人们在戴上VR设备之前“先验的”已经获悉他们所观看与体验到的将是一个虚假的世界,但是在生理反应与心理感受上,依旧会认定这种“拟象”已然成为“真像”,这意味着,以柏拉图的“洞寓”为哲理基础的电影观看机制“坍缩”了。“坍缩”一词原是天文学用语,意指由外而内的收缩与挤压,从而形成新的物质。在天文学的概念中,“坍缩”发生的时候,星系向外射出的光将会失去它的全部能量,从而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光逃逸出去。VR影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电影艺术进行的此类“改造”。在传统的电影理论中,无论是“画框论”还是“窗户论”,都存在着一个“此在”供观看者在现实世界的观看环境中站定。VR设备所带来的沉浸式体验,剥夺了观众与电影空间之间的安全距离,从而只能置身于影像世界的挤压之中,一切都是内向收缩的,与此同时,观众也被因“坍缩”产生的力被吸引到影像所形成的拟态仿真环境之中。
VR影像所带来视觉与知觉的仿真感受,在某种意义能正在创制一个超越“电影”、属于“拟象”的拟态影像世界。2020年2月6日,韩国MBC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与你相见》,讲述了一个技术团队利用8个月打造的VR(虚拟现实)系统,帮助一位母亲与已去世女儿重逢的画面故事,场面十分感人。抛去这种技术带来的进步与感动不谈,而是去对其所生成的影像本身进行关照,就能发现这种VR影像对“电影”本身的一次冲击。安德烈·巴赞曾经说过,电影是满足了人类的“木乃伊情结”,因为满足人追求对时间的纪录与凝固而伟大。电影与摄影的区别在于,人类在观看照片的时候会下意识的认为自己是在看“过去的事”,而在看电影的时候则会认为是在看“正在发生的事”。在VR影像降临之后,人类所掌握的影像技术,已经不仅能重现时间,甚至还能还直观感受上“生成”共时的时间。电影的非线性时间、现实时间与影像时间之间的巨大裂缝,会撕裂观众观看电影时的临场感与经历感。而VR影像,则是给予观众/参与者一种共时的体验效果。VR影像中的共时性来源于可交互的互动体验,交互带来了“对话”的可能与空间,与“互动式电影”所带来的伪交互体验不同的是,VR电影中的交互体验才是真正的、实时的,不需要脱离叙事语境与视听空间的。在《黑镜:潘达斯奈基》(Black Mirror:Bandersnatch,2018)等自我标榜为“互动电影”的电影形态中,观众对剧情的选择与控制需要进行手动操作,这种操作造成了观众对剧情体验的间离感,无法达到沉浸体验的效果预设。
巴赞认为,如果电影还没有到达“完整电影”的程度,是“因为它的守护女神在技术上还力不从心”。电影技术在有声、彩色、立体的进化中,都曾遭到无数次质疑的声音,但是电影经受了这些考验,吸纳了新的技术语言,使自己愈发朝着“完整电影”的方向走去。与此同时,巴赞对电影的思考还存在另外一个维度的解读,即“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所谓渐近线意味着无限趋近却永不相交。同时VR影像设备带来的触感体验填补上了视听之外的知觉感受,这是否会导致未来的“电影”终究会逾越过巴赞预设的这条界线?VR影像也许真正地带来巴赞曾经梦寐以求的“段落-景深”镜头(长镜头),以此来完成对“真实”的再现。
三、观影者地位的再塑
早在电影的幼年时期,就曾出现过不同观影模式的争论与实践,这其中包括卢米埃尔兄弟的大银幕集体观影与爱迪生团队的私人观影模式。一般意义上来说,当下的电影史叙事是将卢米埃尔兄弟于1895年巴黎在大咖啡馆的公开放映视作电影史的开端,而将爱迪生团队的电影视镜推到“失败媒介”的范畴。近年来,媒介考古学的兴起启发了学界应当摒弃传统的、线性的媒介进化史,而是将“考掘历史上那些失落已久、转瞬即逝、止于想象的媒介物”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通过这种研究思维可以探访VR电影的多种“前身”——电影视镜(Kinetoscope)与立体视镜(Stereoscope)的视觉原理,从而观照当下VR电影技术的渊源与前景。
VR电影与爱迪生电影视镜的亲缘性,源于他们所共有的“私人观影”模式与沉浸视听体验。电影在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中,仿佛更适合在大众聚集的环境下于大银幕进行观看,而在网络观影的方式兴起之后,私人观影的模式再次兴起,VR电影作为一种可以享受“极致”影像体验的观影模式,未来又是否会对电影院线的发行模式造成冲击呢?事实上,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传统的电影院观影模式已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电影发行模式被迫重新洗牌。电影院闭门数月,以《囧妈》为代表的传统院线商业大片网络发行,传统的电影节开始尝试线上展映这些都对电影的观影模式的悄然移动。鉴于目前VR设备的价格依然居高不下,观看VR电影的主流方式,仍然是在线下商业中心的VR体验馆中,VR影片数量少、价钱高,观看场景固定,目前还很难吸引观众养成观影习惯。这些“痛点”,也曾是电影视镜失败的重要原因。抛去这些市场与商业因素不论,VR电影在观影体验上,与爱迪生电影视镜同样有诸多相似之处。
作为一种“观察者技术”的暗箱世界体系,曾影响了人的视觉观察模式数世纪,直至19世纪早期摄影术成熟才逐渐退位。与摄影影像的视觉逻辑不同,暗箱将观察者的地位封闭在其内部的范围内,迫使观察的主体从现实世界退出,进入暗箱中呈现的影像之中。VR电影同样有着这种的要求,即使观看者完全退出其肉体所处的空间,从而进入一种虚幻的影像世界中。德勒兹所说的“电影不仅将运动带入影像中,还将它带入心灵中”与“大脑即屏幕”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被再次验证。大脑成为播放影像的屏幕,原本应当投射在银幕之上的光影,直接被视网膜接收,并在直接成像于眼底。与暗箱、电影视镜相比,基于双眼视差所形成的立体视觉,更是强化了这种沉浸感与具身感。乔纳森·克拉里曾指出“立体视镜——其实是以视觉经验的彻底抽象化与重建作为基础”,并认为“立体视镜动摇了观者和观看对象之间的布景关系,此关系乃内存于基本上属于剧场架构的暗箱装置”。VR眼镜作为一种在原理上与立体视镜近乎相同的视觉工具,同样继承了它的这些特点。另一方面,身体是暗箱视觉体系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在暗箱视觉体系中身体与影像所形成的沉浸环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摄影术的诞生,曾经将观察者的身体从暗箱之中抽离,摄影影像生成的再现实践使得观察者不再需要“置身其中”,但是VR影像却在某种程度上又将观察者重现拉回暗箱视觉体系之中,形成了一种观众调动整个身体与VR影像装置进行互动的模式,从而获得“剥夺性”的视听体验。
传统的电影,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始终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行为,即使在一些具有多重解读意味的“烧脑电影”也不例外。而VR影像对电影的侵入,将会重塑观众/观察者的地位,给予观众更大的参与性。诸如在《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2018)、《超时空同居》(苏伦,2018)等以“时间迷宫”为主题的电影,是否可以在VR技术的加持下生发更多种可能。在一种理想的VR电影或者说是VR影像形态中,观众应该化身为一个观影体验者的角色,自由地在电影所塑造的视听空间中翱翔。
结语
技术是电影变革的重要动力,在将虚拟现实看作是一种“电影语言”之前,首先要意识到它是一种“影像技术”,作为一种技术类型的虚拟现实,是包含着电影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的重要技术手段。传统的电影行业需要正视虚拟现实技术的崛起,这是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电影院线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闭门歇业,在此期间流媒体放映大行其道。疫情期间家庭观影与单人观影的模式被再度点燃,这原本应该是VR电影的一个发展契机,但困于片源、设备、市场等诸多原因,虚拟现实电影的热潮并没有再度袭来。时至今日,虽然虚拟现实电影仍未探求到适合其自身体系的电影语言与叙事形式。但是可以期待的是,虚拟现实技术将会给以电影为代表的影音娱乐形式带来深刻的冲击,虚拟现实电影会使电影艺术朝着“完整电影”的神话继续演进。
【注释】
①刘帆.VR不是电影艺术的未来[J].文艺研究,2018(09):91-98.
②[法]翁托南·阿铎.剧场及其复象[M].刘俐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51-57.
③ 严锋.假作真时真亦假:虚拟现实视野下的《红楼梦》[J].中国比较文学,2020(02):2-17.
④[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M].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7.
⑤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Selected Writings. Ed .Mark Pos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66.
⑥[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8.
⑦ 施畅.视旧如新:媒介考古学的兴起及其问题意识[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07):33-53+126-127.
⑧[法]吉尔·德勒兹.大脑即屏幕[J].杨尚鸿译.电影新作,2018(03):13-16.
⑨[美]乔纳森·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论19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M].蔡佩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5、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