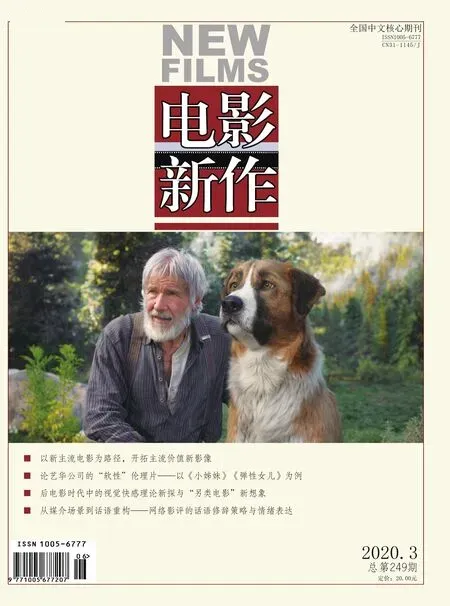重叠、表现、力度感:流媒体时代影院观影体验的再思考
曾 洁
自电影诞生以来,影院就是其最重要的放映平台,甚至可以说脱离影院的电影是不完整的,缺乏其原始规范下的多重属性。在很多观众的心里,影院本就是电影的一部分,是获取电影内容,开启电影奇幻旅程的闸口,圆满的观影体验的起始点来自于影院。
纵观整个电影史,影院的发展一直道路坎坷。最初爱迪生在“开源节流”的商人思维下用箱状电影视镜“孤立”着每一位观影者,观影并不是一种即时共享的活动,而后来出现的豪华电影宫,在提升受众观影体验水准的同时也担负着高昂的成本。进入21世纪,借势于商业空间,充分展示规模经济优势的多厅影院模式已经在全球得到推广,可是近几年来以奈飞为首的流媒体平台来势汹汹,传统院线似乎难以招架,一场疫情更是把全球院线拉入了严酷的寒冬。
回望影院发展的一路波折,面对流媒体的硬核攻势,在疫情之下,正是电影行业特别是实体院线进行思考和布局的重要关口。而笔者认为和电影史上影院的突围和重生一样,转机的密钥依然在受众手中。如何摸准受众观影心理,营造不可替代的观影空间,触发受众独特而难忘的观影体验,才是影院应对危机的源头活水。
在当下这场流媒体与实体影院之争中,于受众而言,流媒体的主要优势来自于观影成本低、观影行为更为自由便捷、片源丰富且自主选择性强。然而,身处纷繁多样的媒介世界,受众选择将自己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交付给电影这种艺术形态,绝不是仅仅是去置换那种单一的,与日常观看电视行为无异的“疏松的活动状态”。
受众对于电影提供的非日常的紧张感及快感的痴迷其实由来已久。当1895年12月28日法国巴黎大咖啡馆的地下室被建成一个小型影院时,面对从银幕中驶来的火车,观众瞬间集体倾倒惊呼。卢米埃尔兄弟赋予电影的生命力不仅仅来自商业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标注了观影体验的多维性和公共性,颂扬了于极致观影体验而言,影院格局的绝对价值。在此之后,电影的每一次进化也都离不开影院,而受众在影院提供的多重观影方式、特殊观影空间的培养下,形成了既定的影院观影心理和审美方式,成为更纯粹的观影人。
一、静穆的狂欢:影院观影心理的重叠性
“和宗教仪式相似,电影的信徒也从四周聚集而来,同赴圣殿,宛如巫术,宛如梦境,甚至如弗洛伊德所言的‘强迫性神经症’。”“强迫”受众不辞辛劳前往影院接受电影洗礼的驱动力本身并不单纯,受众兴致勃勃借由旁观一个故事的名义奔赴群集的现场,在路途中要经受各种公共程式的检验,这些程式是交际的、互动的、仪式性的。但是在观影过程中,黑暗的笼罩下,受众却往往沉迷于一种独处的状态,任凭自己不为人所知的一面被引诱出来。这种重叠的,看似互斥的心理体验勾勒出影院观影最神秘且动人的肌理。
(一)外向的群集归属需求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人的延伸”,影院媒体不仅是视觉、听觉的延伸,更是人身体的综合延伸。影院在召唤受众感官功能上的效用不等同于电影本身。人们从得知电影信息,选择影片、影院、观影时间、观影同伴、选位、购票、奔赴影院、进入影院环境、在黑暗的影厅中寻找座位、落座、直到观赏电影,几乎启动了整个身体的器官机能,在不自觉中被裹挟进影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议程中。而这种规范性并非绑架式的、压制性的,受众反而乐在其中,因为这整个过程中同样也充斥着人际与群体互动的快感与安全感,是人社会性的集中体现。
在数百人聚集的观影现场,每个人都笼罩在一个大的“意义场”之下。“不断的心理递接终究会形成不同程度的心理交融。”和所有仪式一样,在相同目的的驱使下,陌生的身体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同一情境、同一文本的召唤下共同震颤,虔诚且专注。于是人们与其他观影者产生奇妙的心理勾连,致使这些陪伴在周围,排布整齐的黑影瞬间也有了温度。然而构成此意义场的不仅有显在直接的内容信息(主要来自于影片内容),同样也包含隐晦间接的关系信息(主要来自于受众自身)。观影者在一种协作关系中共同编织着完整的意义场,以确保人们可顺畅地接收且体悟影片内容。如若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挣脱这种协作关系,意义场将出现破口,噪音侵入,不断把受众从影片构筑的“梦境”中拖拽回现实,令其惊慌失措、惴惴不安。
影院观影行为对于受众群体归属感的满足,得益于影院环境所营造出的一种陌生感。“艺术的本质在于通过形式的陌生化,使人们习而不察的事物变得新奇而富有魅力,进而唤起人们对事物敏锐的感受。”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其观看形式和导演的呈现手法同样重要,两者都左右着人们对于电影内容的吸收和消化。影院观影方式的仪式性呈现,提供给人们一种完全区别于日常的陌生感。醒目的影片海报、繁复的灯箱广告、个性化的影院陈设、精心设计的“彩蛋”、立体震撼的声画效果,这一系列的视听元素伴随着人们进入影厅的行动路线依次铺开,环绕出一个与受众生活空间全然不同的共享情境。人们面对随机组成的观影同伴,陌生的光影环境,陌生的剧情,一种犹如冒险般的兴奋感扑面而来,人们极致的观影情绪在影片未开始时已经被调动起来。在这种陌生感的刺激下,人们急不可耐地想要逃离现实,投入电影奇观的怀抱。
(二)本我释放欲望
弗洛伊德认为完整的人格由本我、自我及超我三部分构成,而本我是“人出生时就有的固着于体内的一切心理积淀物,是被压抑、摈斥的人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生命力、内驱力、本能、冲动、欲望等心理能力。”人们为了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往往要受到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的规训,所以本我的部分总是处于压抑隐藏的状态。而正如弗洛伊德所言:“被压抑之物必将重返。”虽然本我总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重返人们的身体,但它重返的路径是需要条件来铺设的。在很多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看来,区别于艺术家和精神病患者,普通人利用自身的无意识能量唤醒本我最常见的路径就是做梦。
弗洛伊德把梦看成是愿望的实现方式。电影受众把本我触发的难以满足的欲望,被现实压抑的感性冲动,以及现实身份的缺憾投射到了屏幕中的角色身上。他们看似安坐在坐椅上,表面波澜不惊,实际内在的本我已经被剧情勾引出来,蠢蠢欲动。他们透过镜框偷窥着别人的生活,放任自己的本性不断描摹度量影片中复杂的人性。
这隐秘的释放、内在的狂欢是否进行地尽如人意,自然也与观影环境有莫大的联系。当受众走入影厅,身体遁入黑暗,面对镜框式的舞台,随即成为让一路易·鲍德利描述中柏拉图式洞穴中的囚徒,“放映和映射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而呆在里面的人,无论他是否意识到(或者根本不会去意识),就像是被拴住、俘获或征服了一样……无论如何,那所谓的‘现实’乃是来自观者的背后,如果他回过头看一下的话,除了一个来自隐匿光源的闪动的光束之外,他什么也看不见。”密不透光的封闭性、隔音墙壁造就的寂静、舒适且私密的单人坐椅,此时精心排布的影厅环境是一种强效的催眠术。前方屏幕是唯一的光源,配合高品质的环绕立体音响,受众的意识完全被操控。此时身体仿佛融入坐椅当中,已不能自拔,灵魂随着光影摇曳迅速入梦,从而体验真身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的快感。
二、“注意”的再凝结:影院空间唤醒的审美表现欲
“注意”是最基本的审美机制之一,是诸如联想、情绪等机制发挥效用的必要前提,“注意”的持有也是人最原始的感官效能之一。然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功能日趋强大,人们获取内容变得越来越容易,但对于“注意”的分配却越来越被动且乏力,注意力总是在无意识之下被绑架。海德格尔说:“常人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而存在”,就是在批判人们以“注意”为基础的审美能力在琐碎且慵懒的日常状态下被禁锢、消解。与瘫软地背靠沙发,木讷地直视银幕,寻常无味的家居观影环境相比,影院可立即将受众的注意力和审美冲动唤醒。影院中造型醒目的立牌、展架,精心设计的海报,品类繁多的食品零售窗口,创意十足的电影周边产品……这一系列显在的视听元素不断给受众的“注意”进行热身。而作为自由消费的客体,它们也在提示着受众,你们是受宠的上帝,你们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当受众入座影厅之后,黑暗的环境,唯一的光源营造的隧道效果不允许其注意力涣散。受众的“注意”此时被提炼成了“随意注意”,它“使鉴赏主体得以在相对稳定的注意中,保持各种心理活动的积极运转,在艺术鉴赏中得到充分的审美享受。”在审美活动中,“随意注意”更能激发受众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随意注意为观众留出了主动参与的心理空间。”在观影的过程中,被“随意注意”支配的受众不仅更能沉浸于剧情,甚至可以反客为主,进行文本再造式的自我表达。
罗兰·巴特提出过“作者的死亡”的概念,即当视听行为发生时,一个文本才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一部电影存在的意义绝大部分来自于受众如何解读它。“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带着自身特有的结构式——我们所有生命体验的成果——来看每一部影片的。”影院观影过程中,受众的看是一种聚焦的看,是一种侵入式的看,是一种创造性的看。然而看和被动接收已不是现代受众的全部诉求,受众的作者身份被影院不断地形塑出来,他们总是意犹未尽,兴致勃勃地欲以自己的方式再造电影文本。
三、感知的力度:影厅布局触发的沉浸式快感
“人类对自身生命的判断,都是以真实性感知和力度感知为底线的。这种生存心理底线也就自然地投射为审美心理底线。感知力度,是人们以审美方式感知世界和感知自身的一个重要坐标。”艺术家在创造过程中总是倾尽全力搭配组合各种艺术元素,使其呈现出最佳“张力结构”,可使艺术品之前的受众不由自主地注目、共情。具体到电影,其“张力结构”不仅来自于文本内的语法策略,如演员表演方式、场面调度、剪辑节奏等,也由呈现文本的媒介形态而构建。
基于人眼的生理结构,两只眼睛能看到的水平视角能达到200度。标准的现代影厅屏幕大约覆盖受众前方45度的范围,也就意味着屏幕周围的大部分视野被浪费。回望过去,院线为了应对电视的强劲攻势,将改革的着力点放在受众观影视觉感知力度的强化上。3D立体电影、多银幕维馨体的出现都是通过深挖大屏幕的潜能从而重构影厅的视觉结构,不断强化电影视听元素在受众感官上的作用力度。
实际上,当下流行的“沉浸电影体验”和ScreenX等技术都是以影厅空间为基准,对于屏幕进行多方位扩延,让影像可以更为自由的流动,与受众达成更亲密的接触。除此之外,现代影厅也在不断开掘受众感知的其他维度,比如“4DX”和“Smell-O-Vision”电影,分别召唤出受众触觉和嗅觉的感知经验,培养出更为敏感、投入、主动的电影受众,使他们更容易排除现实的干扰,全身心地沉浸于虚幻的梦境。在影厅多维度立体式综合布局下,电影文本苦苦经营的节奏、层次、重心、平衡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此时,对于受众来说,审美的力度感知才真正成了一种整体感知。
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影厅的技术布局营造出的沉浸感,与VR技术标榜的沉浸式体验截然不同。“身临其境感觉虽然奇妙,但是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当你面对一个心不在焉的讲述对象时,哪怕你有全世界最棒的故事,也没有人专心去听。”这是Facebook旗下 Oculus Story Studio的创意总监对于VR电影提出的担忧。受众在VR电影中所拥有的是一个交互式的身体,自带游戏属性,甚至一个微小的举动都会对剧情产生影响。所以受众原本藏匿于黑暗之中的“偷窥者”的快感被VR电影营造的互动真实所剥夺,受众不能轻松自如地去旁观别人的故事,反而要不自觉地承担叙事的重任。
结语
在电影诞生后的百余年间,影院都是电影垂直产业链的重要构成,票房收入是评价一部电影优劣的重要指标,更是不断循环滋养电影艺术革新的实际力量。立足于受众观影体验的视角,从其最根本的审美诉求出发,对于影院应对此次腹背受敌的危机有着巨大的提示作用。首先,技术的发展对于强化受众感知力度,优化观影体验的确有显在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附属屏幕呈现的内容,是否会让观众注意力分散,通过多屏幕实现的同场景多视点叙事是否破坏了故事的悬念感等。其次,影院不能囿于作为观影物理场所的单一定位,应把自己打造为可进行更多意义交流的更具温度的场域。再次,影院应该主动培养受众的影院观影习惯,比如利用艺术电影、“经典重映”等类型和做法挖掘影院的潜在受众,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形式主动走向受众,化身成有内涵、有情怀、有品质、有号召力的不可替代的品牌。
在多元、自由、民主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影院用最深沉且细腻的方式对每一个观影者赋权,给予他们自省、怀旧、宣泄、成长、返璞归真的权力。每一位观影者都如同《天堂电影院》里的多多一样,在影院中无声地成长、蜕变。无数次在黑暗的掩护下,乘着别人的故事回到恐惧、欲念开始的地方,直至遇到那个单薄且纯粹的自己。
【注释】
①李法宝.影视受众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55.
②潘桦、李亚.互联网时代电影的影院本体论[J].现代传播,2019(6):98.
③ 余秋雨.观众心理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57、20、113.
④ 周宪.美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65.
⑤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本我/994438?fr=aladdin.
⑥ 让一路易·鲍德利.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A].吴琼主编.凝视的快感: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9.
⑦[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7:156.
⑧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69.
⑨ 同3.
⑩ 帕特里克·菲利普斯.观者、观众和反应[A].吉尔·内尔姆斯主编.电影研究导论[C].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203.
⑪同3.
⑫谢周浦.VR(虚拟现实)电影中观众的审美体验[J].魅力中国,2017(52):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