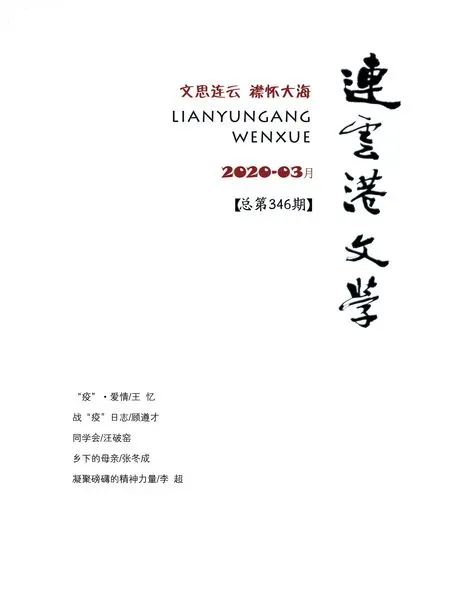早晨从中午开始
梁爽
罗佳始终认为,家里的女人合起伙来干掉了他的幸福。其实,家里的女人不多,只两个,母亲和嫂子。
她们常会让他心烦意乱,譬如此刻。
他狭小的卧室里充斥着肉汤的味道。这味道像个狡猾的入侵者,由细微的浸润到慢慢地蚕食,现在已如污浊的海浪恣意地翻滚,拍打着冲击着他敏感的嗅觉神经。罗佳皱皱鼻子,翻了个身,母亲为“坨坨糖”蒸制汽水肉的功夫愈发炉火纯青。
他讨厌这该死的味道,没有这味道,他可以继续沉浸梦乡。她们永远不会懂,一个疲惫的上班族,一个夜里常常失眠的人,周末的幸福莫过于早晨能从中午开始。
早晨从中午开始。
罗佳的脑袋里灵光一闪,一位大作家的创作谈就是这个名字。彼时他刚进大学,在杂志上初看到这几个字,吓了一跳。古人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医说“天人相应”,人体必须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罗佳认为,一个时间错位的人,他的人生也必然错位。
事实上,没过多久,罗佳也和他的很多同学一样,过起了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日子。学校有严格规定,宿舍每晚按时熄灯。学工科的男生,把宿舍外的电线接成蛛网一般,轻而易举地可以在夜里获得光明。不睡觉的罗佳,看小说、打游戏、看碟,和其他室友差不多。不一样的,他不会像他们那样和女友煲电话粥,他没有经历过那种如火如荼让人奋不顾身的恋爱。
“坨坨糖”和他妈妈几乎分毫不差地进门,每个周末如此。母亲笑盈盈地端上了热气腾腾的汽水肉,眼里像含着蜜一样地看着“坨坨糖”把鸡蛋和肉丸送进圆嘟嘟的嘴里。
“坨坨糖”是哥哥的儿子,母亲的心头肉。母亲开心的时候,会“心肝宝贝坨坨糖”地喊他。母亲常说,他是我们整个罗家的希望。罗佳也曾是母亲的希望,直至今日,他还清楚地记得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激情澎湃地守在电话旁,把他金榜题名的喜讯通知到每一个能想起的亲戚。同样的话,母亲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说到情绪激昂处,会爆发出响亮的笑声,笑到兴头处,又会洒下几滴热泪,说自己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付出没有白费。
母亲的样子,让罗佳反感又难过,甚至觉得考上大学成了一件丢人现眼的事。母亲说得没错,她生他养育他,含辛茹苦地付出太多。但她太多诸如此类的做法,他很小就厌恶,到了中学,这种厌恶更加明朗清晰,他发誓长大绝不找母亲这样的女人,并因此发奋读书。
每天放学进到小区,一楼人家的窗户里会飘出炒菜的香味,他的同学们就会哈着腰把自行车骑得更快,把车铃摇得更响。他却没有那份兴致。
对于大多数的寻常百姓家,晚饭后全家人围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是一件温馨的事。罗佳却不喜欢。母亲永远把频道停留在肥皂剧上,父亲会陪在母亲身边,在茶几上摆上一碟油炸花生米或是一盘卤鸭脖,小半杯烧酒,一会儿抿上一口。记忆里,父亲的头发总是油腻腻的,喝过酒的脸常常在电视屏幕反射的光影里泛着酡红的光,有种说不出来的猥琐。但罗佳并不讨厌父亲,父亲寡言,在家里的地位无足轻重。父亲永远是母亲最好的听众,母亲有说不完的话,东家长西家短,或者占了谁的便宜吃了谁的亏。罗佳不能理解生活里怎么会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事,吃亏占便宜总被母亲算计得无比分明。
罗佳的中学时代,有点像南方的梅雨天,不是暴雨压城,也没有朗朗白日。就那么慢慢被抻着,总有种说不清的惆怅。如果说这梅雨天里有过一束光,那就是省师范的大学生夏梦实习的那段日子。夏梦喜欢穿白衫牛仔裤,总是把马尾吊得高高的,说话的声音不大,爱笑,即使生气的时候,脸上也像带着笑。罗佳第一次知道,女人可以如此温柔恬美。他更加认真读书,并立志要考上大学。他认定,只有读了大学,才能遇到夏梦一样的女生。
“坨坨糖”把最后一点肉汤倒进嘴里的时候,罗佳出了门。接下来的时间,“坨坨糖”要睡午觉,养足了精神,才能继续奋战下午的补习课。在这段时间里,母亲是不允许全家人发出任何声响的,父亲放个屁都会让母亲剜上一眼。
生活变成如此模样,嫂子功不可没。嫂子没工作,把炒股当事业,没见她赚上几个钱,却可以名正言顺地颐指气使,外加好吃懒做。哥哥结婚后,把家安在了汉口,因为嫂子是汉口人。在汉口人眼里,罗家住的红钢城与乡下无异。嫂子骨子里瞧不起乡下人,行动上却没有避而远之。每个周末,她都会打着探望的幌子,携着哥哥和“坨坨糖”雄赳赳地跨过长江,到“乡下”来大吃二喝。最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大半辈子精打细算骁勇善战,却在嫂子面前低眉顺眼,举手投降。罗佳为此不平。母亲说:“我都想得开,你有什么想不开,你哥哥多大的本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孙子。你快点给我娶个回来,哪怕也是这么个主儿,我也照样伺候。”罗佳被母亲说得哑口无言,快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这件事成了母亲近几年最大的心病。
“坨坨糖”的补习班生涯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的,奥数、英语和作文。母亲有些心疼,嫂子振振有词,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别人都在补,我们不补就会落后。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嫂子为“坨坨糖”报的三个补习班都在红钢城。红钢城是武钢最早的家属区,因当年苏联老大哥援建武钢时设计的一片红砖老楼而得名,教育资源和汉口自是不能相比。罗佳问母亲:“还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她到底想让孩子跑输还是跑赢。”母亲淡然地回了一句:“只要她肯陪着孩子跑就行。”母亲掏了三门补习班的辅导费,同时周末的饭菜做得更加用心,不但营养均衡,还要随“坨坨糖”的课程而准确掌握开饭时间。
罗佳没有去网咖,而是公交地铁又公交地铁一路辗转到武汉另一端的H 大,尽管苏琳已不在H 大。
罗佳和苏琳的相识没有特别的浪漫之处。在朋友卖烘焙的微信群里,罗佳看到苏琳头像的第一眼,便去加了她。苏琳并非美得出奇,但有种说不出的味道,特别是她饱满的嘴唇,欲说还休,看了让人心里发紧。
罗佳坐在篮球场边的看台上,点着一支烟,慢慢抽起来。这几天正是倒春寒,打球的学生们却大多穿着背心短裤。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汗流浃背。罗佳竖了竖衣领,年轻真好!从前他也曾这样年轻蓬勃过。十年寒窗,总算走进象牙塔,终于可以大口地呼吸弥足珍贵的自由空气。那时的罗佳像路边花店里罩着塑料网套的玫瑰一样,网套一被剪破,他就“嘭”的一声急急地绽开了。在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中,他始终没忘记寻找一个夏梦般的女生。
罗佳的第一个女朋友媛是在老乡会上认识的。媛童花头,大眼睛,着一袭白裙,罗佳看她第一眼便有了好感。美中不足,媛爱用日本卡通片里蜡笔小新一样的腔调讲话。罗佳几次提醒她好好说话,媛依然故我。虽然反感,罗佳还是把这场恋情继续着,他知道在如今这样开放多元的时代寻找一个恬美纯净的女孩无异于水中捞月。但是那天晚上在阶梯教室后面的合欢树下,罗佳第一次握住媛胀鼓鼓的乳房时,媛却扭动着身子喊不要,不要——她喊第二句“不要”时,罗佳抽身而去。他喜欢清纯的,但不是装清纯的,这比幼稚愚蠢更加可憎。
大马的电话打断了罗佳的沉思。大马约罗佳晚上一起吃饭,还有陈铭。这是他们三个人的传统节目,哪儿有新开的馆子,想了什么口味,他们都会约着一起去。不会吃就不是武汉伢。起初几次吃过饭去K 歌,大马都嚷嚷着找小姐。罗佳和陈铭一起拒绝。有一次大马喝高了,说陈铭肯定是个童男子,罗佳你不会也是吧?陈铭抢白大马,说他不想过早地葬送自己的自由。陈铭的家庭条件好,眼光也高,普通女孩子入不了他的眼。陈铭休假时会变身成背包客,短假登山徒步,长假自驾旅游。他在无比珍爱着他的自由,惬意地享受着他的人生,与女生无关,与风月无关。罗佳对大马的话不置可否,他怎么可能是个童男子,不过不像大马那样不辨优劣剜到筐里便是菜罢了。大马有大马的生活哲学,结婚了再去哪儿找这样的自由,他要痛快淋漓地挥霍他的自由。
罗佳第二个女朋友叫米诺,一个和名字一样充满现代感的女孩。那是大四下学期,工作已经尘埃落定,大把的日子无事可做,他空虚无聊,还有种说不清的惶恐。他的很多同学是急着毕业的,急着工作,急着赚钱,甚至急着结婚。他不急,走出大学校门将是血雨腥风的江湖,有多少事要独自面对。他渴望在校园里呆得久一点,再久一点。米诺就在这个时候闯进他的生活。他们迅速地同居,一起躲在出租屋里看碟,或者连续地做爱。对于这两件事,米诺始终充满兴趣,尤其是后者。每次罗佳进入她的身体,她都会夸张地喊叫。毕业后,米诺去了南方的一座海滨城市,罗佳没再联系她。说来也怪,他竟一点都不想她。但在很多个夜深人静的午夜,罗佳会把这段记忆重新掏出来认真地审视,审视的结果让他的心底涂满忧伤,说到底还是和爱情无关。陈铭和大马把自由标榜得至高无上,罗佳觉得那是一种矫情,一种心智不成熟的表现。他想要的,是一场爱情,一场真正的、纯粹的爱情。但他不会跟他们说,他们会笑疯的;他更不会跟家里人说,他们更不会懂。
坐得有些冷了,罗佳起身时还没想好要去哪儿,拐到路上,竟打听起机械学院来。两片嘴唇似乎不受大脑支配,见到路人张开便问。
机械学院的大楼现代、庄严、气派,站在高高的台阶前,罗佳心里有如万马奔腾。认识苏琳半年多,这是第一次来她曾经读书的地方。对此,苏琳没说过什么,但他知道,她不愿意他来。台阶上,一个清瘦的穿着黑风衣的女人正拾级而下,罗佳觉得自己的眼睛在一点点地潮湿。苏琳也喜欢穿黑风衣,如果此刻走下台阶的是苏琳,她绝不会走得这样拖沓无力,她小腿的肌肉一定是紧绷的,她顺直的马尾一定是晃动的,如果除掉风衣,她的腰肢一定是在灵活地摆动。陈铭和大马不会知道,腰肢灵活的女人才真正的性感。
晚饭的位置大马选的,一家土菜馆,羊肉火锅和牛蹄子做得地道。罗佳鲜有的抢着倒酒,还不住地劝酒,三个人都喝得有点高。转战KTV 的时候,大马又要找小姐,陈铭第一次没反对,罗佳说,要个陪酒的。包厢里光线很暗,角落里的帕灯在不甘寂寞晃头晃脑地闪烁。大马叫了一打啤酒,说句上洗手间后迟迟未归。陈铭一手举着话筒,一手搂着陪酒女,声嘶力竭地唱着刀郎的情歌。女人微胖,黑色的紧身裙,把赘肉勒出起伏的沟壑。陈铭细长的手不安分地在沟壑间游走。
眼前的一切恍然如梦,苏琳第一次约他的时候罗佳也有过这样的感觉。
那次苏琳选的酒店在郊外,罗佳打了的士一路狂奔而去。拐进酒店细长的走廊,如同走进一节卧铺车厢,罗佳甚至清晰地听到耳边有节奏地响起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他不知道自己将要行往何处。苏琳的皮肤蜜一样的颜色,她的腰肢灵活轻盈,她的港湾水润柔软。罗佳似一叶扁舟拼命地划着,很快被彻底淹没。事后,罗佳趴在苏琳的身上呜呜大哭,这才是女人。他欢喜,他忧伤,他无法表达,他唯有哭。
五个月后,苏琳去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她的男友在那边留学。
临行前的见面,苏琳选的位置是星巴克,罗佳坚决改在茶馆,一向说了算的苏琳依了他。那天的天气好得出奇,艳阳高照,像跟人较着劲一样。罗佳两只手使劲握着细高的茶杯,贪婪地看着苏琳。苏琳饱满的唇上涂了一层淡淡的玫色,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更加俏丽动人。是梦吗?如果真的是梦,罗佳想长醉不想醒。苏琳被他看得两颊微红,“干吗一直抓着杯子,你冷吗?”罗佳看着苏琳的眼睛不说话。苏琳说:“别这样,一开始就说好了的,我们只是陪伴,不能相爱。”罗佳鼻子发酸,“我也没想到,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爱上了你。”罗佳把头转向窗外,广玉兰刚刚绽放,没有树叶衬着,一大朵一大朵开得稀稀落落,窗玻璃上浅浅地浮着他的影子。窗外似乎没有风,他苍白的脸的影子却在微微地抖动,他多想给苏琳一个笑,可是眼泪却不争气地汩汩而出,他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那么多个孤单的日子,两个人一起走过,这一别,也许此生都不能再见。苏琳把手指伸进他浓密的卷发,“对不起,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罗佳把苏琳的手拉到脸旁蹭了蹭,问:“睡前还能聊天吗?”苏琳眼圈儿红了,低下头吹了吹杯里的茶叶,“差多少时差呢,我们现实些吧。”一芽芽在水里站着的茶叶,被苏琳吹得东倒西歪。
罗佳回到家时,已快十二点。客厅没有开灯,母亲还在守着电视。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罗佳一边换着拖鞋,一边打着哈欠。
“小佳,陪妈坐会儿。”罗佳愕然,二十九年的生命里,似乎第一次听到母亲这样温柔地跟他讲话。
“今天你嫂子跟我说,五一想带孩子去泰国旅游,说老师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得带孩子见世面。”
罗佳一听就火了,“她又让你出钱吧?!夏天不是刚去香港见过世面,她要带孩子去火星见世面也没人拦着,她倒是自己出钱啊。”
母亲叹了口气。
“小佳,你自己上点儿心,快谈个女朋友结婚吧。你结婚了,她再想惦记我的钱,我也没有了……”
卧室里已经嗅不出肉汤的味道。苏琳走后,罗佳有了失眠的毛病,除非把自己喝个酩酊大醉。结婚的前提不是得找到相爱的人吗?人生的旅程那么漫长,没有个爱的人陪着,靠什么支撑走下去?罗佳的眼前又晃动起苏琳俏皮的笑脸。刚认识苏琳时,苏琳刚好在西藏旅游。她问罗佳,你会藏语吗?罗佳说,我会武汉话和英语。苏琳笑,说,在藏语里,“亲爱的”发音就是“罗佳”。随后,她在话筒里轻轻地喊了两句“luojia,luojia”。罗佳,亲爱的?亲爱的,罗佳?罗佳,罗佳?亲爱的,亲爱的?罗佳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泪水涌了出来。苏琳,这四种组合,你喊得是哪一个?
luojia——luoj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