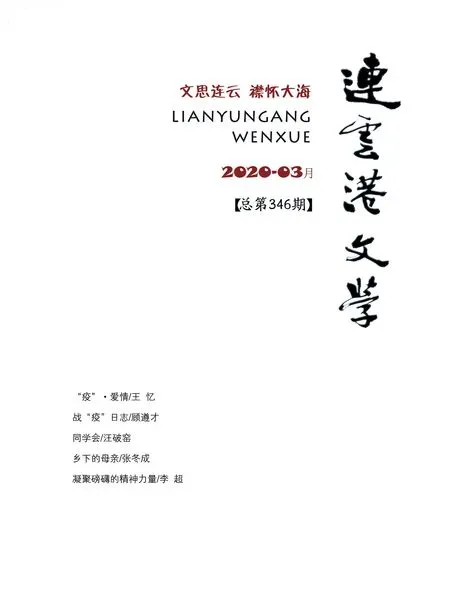瓜事
王文岩
对于生吃瓜,我有着近乎病态的迷恋。若追根求源,这种病态可以追溯到20 世纪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出生在20 世纪60 年代末,那个时候温饱问题还未解决,一切都以粮为纲,而我家乡的黑土地又是长庄稼的沃土,于是,家乡的大小片田,种的都是小麦、玉米、黄豆、水稻之类的粮食,家门口那块小得可怜的菜园里也几乎统一地栽种大葱、白菜、萝卜等能放进锅里的菜类,就连篱笆墙上缠绕着的也是能炒菜的豆角、冬瓜、丝瓜、葫芦之流。至于那些能生吃的瓜类,统统被看成是不抵饥不抵饿的消费品。村上偶有败家老娘们在菜园隐蔽处栽上几棵黄瓜,往往是刚刚结出指头大的瓜牙转眼工夫就不知进了自己孩子还是别人家孩子的肚里,因此种种,村上人家的菜园子就好像复制一般,一家一家的都一个样。要想见到黄瓜、酥瓜、甜瓜,那就得竖起耳朵,一听见“卖瓜喽,卖瓜喽”的吆喝声就尥蹶子朝外跑,一准看到推着交通车高声叫卖缓缓走来的侉子卖瓜人。交通车的长框里多的是黄瓜、酥瓜,很少见甜瓜的。瓜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粮食换。于是有的孩子便气吁吁地跑回家,哭闹着让大人买瓜,可大多数的大人都无视孩子的哭闹,硬着心肠不买。也有的孩子哭闹成功了,破涕为笑地跟在妈妈后面仰着小脸端出半米箩小麦、玉米抑或是山芋干,一番讨价还价后买了几根黄瓜,乐滋滋地端着奔回家去。大多数的孩子们知道哭闹无用,便叽叽喳喳地围拢着卖瓜人的瓜框,似乎看一看瓜儿嗅一嗅瓜味也能解馋,当然,也有的孩子忍不住诱惑会悄悄地将脏乎乎的小手伸进瓜框,企图去摩挲一下瓜儿那清嫩嫩的皮儿。
买瓜解馋的可能性不大,孩子们的希望在田野里呐。背着背篓三五成群的身影游弋在乡野的每一个角落:玉米高粱地、黄豆山芋田、大河滩小树林。名为割草,眼睛似鹰鼻子似犬,最常猎获的便是野生喇叭瓜,一根藤蔓拉开来,能摘到好多鹌鹑蛋大小的喇叭瓜,其中熟好微黄的喇叭瓜又香又甜。有时候,运气好也会在人迹罕至的隐秘处发现悄悄生长的野酥瓜,但大多数情况下,最大的野酥瓜也只有鸡蛋大小,此时的野酥瓜正在酝酿苦味,浅浅的啃一层皮,脆鲜鲜甜津津的,稍咬深些便苦得人脑仁生疼。因此,孩子们都会强忍着口水,将四周的藤蔓野草聚拢来严严实实地掩盖住野酥瓜秧子,并相约多少天后一起来摘瓜。只是往往事与愿违,几天后再来看时,瓜早已被后来者摘走,懊恼之余恨恨地咒骂几句怏怏而去。
所谓“狼多肉少”,好不容易发现一棵喇叭瓜,惊喜还在心头跳动呢,可拉起瓜蔓一个个试过去,满满的全是失望,熟好的喇叭瓜早已进了先行者的肚里。黄豆地里喇叭瓜多,可自从豆荚起鼓后生产队的看青便看得紧了,看青的来回巡视,冷不丁的就会在哪儿冒出来,吓得人魂飞魄散,因此,孩子们轻易是不敢进黄豆地。
不过,孩子们智慧多多,解馋的方法也多多。譬如我与我的好朋友小荣就偷吃过东河滩霞家的冬瓜。那天太阳亮亮的,我与小荣在河滩上割草,中途提起过好多棵喇叭瓜蔓,可没找到一个不苦的喇叭瓜,天近晌午,又饥又渴的我们发现了一个个圆嘟嘟的冬瓜静卧在瓜叶下,我与小荣的想法不磨而合:我们挑一只乳白色绒毛覆盖的鲜嫩冬瓜,削掉嫩绿的皮,一人一半,坐在树荫下大快朵颐。冬瓜肉不太甜但汁水很多,瓜瓤部分则有点别样的酸,很是可口,只是吃过冬瓜后嘴巴里有点涩涩的异样感。
小荣说冬瓜有些像西瓜,我没见过西瓜,可小荣吃过。小荣家与我们家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巷口,小荣的父亲在大队部干点什么,母亲是代课老师,他家总会有稀罕的东西。有一次我在小巷里发现一块碧绿的瓜皮,翻过瓜皮,瓜皮上还带着薄薄的一层瓜肉,瓜肉上还隐隐见到淡淡的粉红。平常我们吃瓜是不留瓜皮的,我跑回家夸张地向父亲描绘那块瓜皮,父亲说那是西瓜,吃西瓜只吃里面红色的瓤子不吃瓜皮的。我使劲地在脑海里琢磨着西瓜的样子,可想的全是红红的瓤子咬进嘴巴的爽快,不由地猛咽口水。
一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教授我们汉语拼音,老师带读“X 西瓜的西”,X 拼音下配图:一块切开的西瓜,碧绿的瓜皮,红艳欲滴的瓜瓤,黑亮的瓜籽。我一边大声跟读一边悄悄地吞咽口水。这时候,我对西瓜总算有了形象感官的认识了,不过我憧憬着的是什么时候能看到真的西瓜,咬一口蜜汁样的西瓜红瓤。
做梦一样,一天放学回家,我真的见到了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并且真得吃到了西瓜瓤子,只不过我吃的西瓜瓤子是淡粉色的。那年我十岁,好像大人们也不在为温饱问题发愁了,以粮为纲的口号似乎也不再喊了。我们固村临县的郭庄悄悄地种了一片瓜田。郭庄与我们村隔着一条大河,郭庄的几乎所有都在东河岸,可偏偏遗留一块河滩地在西河岸与我们村的田地相连,郭庄人便在西河滩上种起了香瓜,自然这块地从瓜秧扯藤起就吸引了我们村大孩子小孩子垂涎的目光。郭庄人当然知道这块瓜地的诱惑力,他们村派出了粗壮似虎奔跑若飞的大刁二刁两光棍兄弟看瓜,兄弟俩在瓜地头搭个瓜棚,吃住都在瓜棚,整日虎视眈眈地守护着瓜地。慢慢地随着瓜的成熟,瓜的甜香随着微风飘进了孩子们的睡梦里,大小孩子白天黑夜都在琢磨着香瓜的事。孩子们的鬼点子多的是,何况参与的还有许多大孩子。俗语说“好汉难敌双锤”,况且几乎是整个村庄的乌泱泱一片的孩子,他们有的是从电影里学到的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扰”“多方向多角度进攻”。结果是大刁二刁顾头难以顾腚,面对各个方向真真假假的偷瓜者茫然不知所措,自然,孩子们得手的机会就很多了。这一次大刁二刁追赶几个偷瓜的大孩子去了,姐姐他们便趁机跑进瓜地,瓜地种的都是香瓜,只有瓜棚旁种有几棵西瓜,姐姐没见过西瓜,看到这么大的一个便摘下抱着跑回了家。哪知道抱回来的西瓜还是个生瓜蛋子,不过我们捧着这没熟的西瓜也是十分的欣喜,自然也啃得津津有味。
日子真是不经过啊,几乎是一转身的光景,我们已近中年。不知从几时起,生吃瓜不再是夏日的专利了,一年四季,只要你想吃,超市里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瓜,黄瓜、酥瓜、香瓜、哈密瓜……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瓜。就是西瓜也有眼花缭乱的品种,八四二四、黑美人、蜜宝、特小凤……红壤的、黄瓤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我仍然喜欢吃瓜。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吃瓜了,可再稀罕的瓜也激不起自己那份吃瓜的急切了,即使是特甜特香的瓜塞鼓肚皮,仍觉得瓜味里少了点什么,而淤积于心的馋瘾却一直都在。有时候依然怀念野地里喇叭瓜的香甜,舌尖存留的仍是第一次遇见的那半生熟西瓜的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