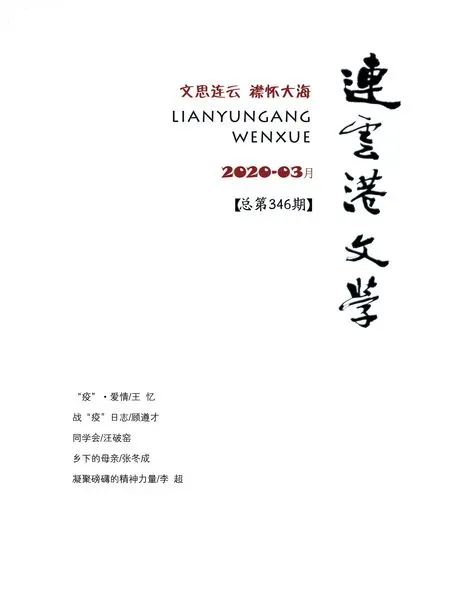摇曳的烛光
皇甫卫明
电梯门从中间往两边移开,志军习惯性迈步出去,觉得有点异样,去路被什么东西挡着。莫非只顾着低头拨弄手机,按错了楼层?两排按键,“16”闪着幽蓝,没错。要不,走到另一栋楼了?那几乎不可能,虽说搬到这里不到半年,从地下车库停车位到过道,熟门熟路,闭着眼睛都认得。
志军,志军吗?电梯门自动关上的瞬间,有人唤他,苍老而熟悉,是奶奶的声音。志军再次按开门,挡在门口的是架空的竹榻。竹榻对面探出一个脑袋,白发稀疏蓬乱,遮住了大半个脸面。志军恍然明白了什么,从竹榻上翻过去。奶奶坐在板凳上,手扶着竹榻,眼神无助望着志军,大孙子,奶奶要……住你家里。
志军站了一会儿,开门进屋,还能觉得奶奶无助的眼神跟着他,落在他的后背上。妈,怎么回事?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音量开到极致,对儿子的询问毫无反应。在厨房忙乎的父亲,拉开移动门探出半个身子,你甭管,这不是你孙辈的事。志军说,你准备让奶奶住楼梯间吗?父亲说她爱住就住,随她。
你们不要脸面,孙辈也要脸面的!志军狠狠道。
母亲从沙发上蹿起来,这是我的房子,你要脸面你管,你拿什么管?
志军蔫了。
今天早上,志军父亲祖兴接了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小叔龙兴问,在家吧?父亲刚想问什么事,小叔挂断了。小棺材,又动啥歪脑筋?父亲嘀咕了一句。
不过一支烟工夫,隔着门,杂乱的脚步声,硬物与墙壁地面的碰撞声,窸窸窣窣的不知名的声响,打破了过道一向的寂静。父亲开门出去,过道里堆满了破烂。小叔气喘吁吁道,今天是1 号,这个月老娘搬你家住。父亲刚想说什么,小叔已经窜入电梯,咔嚓一声关上门,哗哗哗一路下去。父亲从破烂中挤过身,按下另一架电梯,追出底楼过道,但见那小子的电瓶三轮影子一般消失在拐角。
父亲一路追到小弟家,不在。打他手机,关机。父亲只好拿老太太出气,又不敢太过分。父亲说,讲好住小弟家的,干吗呢你?老太太瘪嘴瘪脸的,嗫嚅道,大也是儿子,小也是儿子。声音不大,语气不软。父亲说,你还有一个儿子呢。老太太眨巴着干枯的眼睛,道,要我死,我偏不死,活着看看有啥不好!父亲说,你一天到晚死死死,掐也掐不死你。老太太一句不让,你掐你掐呀。
父亲与他老娘之间,已经多年没有一句好话。毕竟是自己亲娘呢,撑不了几年了,自己也是老人了,他也想跟其他家庭一样和和美美。可一见面,一开口,老娘那刻薄的言语,那刻毒的眼神,咳,总之想孝也孝不起来。
志军母亲在门口看了一眼,把人关在门外。婆媳俩斗了大半辈子,谁都没摆服帖对方。后来再也不吵了,两人形同陌路。志军母亲不再直接参与是非,只在背后撺掇。这次,母亲提醒父亲坚持原则,千万不可心软,进门容易,再赶她走就难了。父亲拿定了主意,而且,孙子大学马上放假,小房间得留着。
志军不敢擅自把奶奶迎进家。按理说,父母的房子也是他的房子,但还不是一回事,产权明摆着不是他的名,他无权做主。眼看着儿子马上毕业工作,他在市里,严格说在市郊买了90 平方米,刚凑够首付,父母也出了一部分,月供近万由他小两口担着。奶奶说,你不做主,你爸也不做主,帮我把蚊帐挂起来。奶奶你真想住过道?志军看着地上一堆灰不溜秋的东西,袖手不动。
奶奶扶着竹榻,强撑着起身。似乎被神秘而持久的力量摁住背部,奶奶的背愈发弯曲,整个身子到头部,在干瘪的屁股那里形成一个夹角,与地面基本平行。看人的时候,只能偏转头部。不知道她是怎么把这张床支起来的,但亲手支起蚊帐,把蚊帐的四个角挂住拴在床架的竹竿顶部,她万万办不到。奶奶唯一没变的是嘴巴,不服输。
志军知道,奶奶不过作势唬人,就像她被二婶欺负后,几次三番,举着农药瓶大闹,或者解下裤带在树杈绾个圈伸进头哭闹。奶奶与母亲关系不睦,就像蛇与蜈蚣上辈子的冤家。可这丝毫不影响奶奶对大孙子的疼爱,尤其是还没堂弟志强的时候。奶奶常说,孙子才算高家人,将来为高家立门头的。奶奶把一团蚊帐抱到竹榻上,翻来覆去找到帐顶,比画着,身子一滚,哼哼唧唧上了竹榻,把自己缩成一团,两手撑住竹榻,试图站起身,把老竹榻折腾得吱吱嘎嘎。
志军于心不忍,说你下来吧,我帮你挂上去。奶奶嘻嘻了一声,看不清乱发下脸上的表情,应该在哂笑,她知道大孙子不会真不管她的。
志军,你在干吗,给我进来!母亲在门后招呼。奶奶摇手示意,分明在说,蚊帐还没支好呢。
电梯间比通道宽敞,奶奶这张床占用了大半个电梯间,堵住了一个半出口。志军把床往自家挪过半米,让出一个出口。对门还没回来,等会儿打个招呼,毕竟靠一部电梯进出多有不便。现在,自家通道有一截被竹榻占据,志军扁着身子从狭缝中过去,好在他家都是瘦肉型的,敦实的母亲通过就吃力了。
真癞我家门口,小儿子那里多舒服?母亲存心让奶奶听见,大嗓门教训志军,你还帮她挂蚊帐,你准备陪她睡?
父亲胸腹吊着大红塑料围身,把菜端上桌,招呼老婆儿子开饭。志军媳妇回娘家了,饭菜马虎一些。母亲气呼呼道,没胃口。父亲说,都怪小棺材(对小弟的蔑称),晚饭后我找他去。父亲的话有潜台词,不怪罪老娘,也不能拿自家儿子出气。母亲说,你现在就找他去,这件事不解决,谁都不准吃饭。
父子俩好说歹说,把志军妈拽到餐桌前坐下。
一阵敲门声过后,老太太断断续续的话音隔门传来,我要……吃晚饭……祖兴……志军……母亲停住了咀嚼,怒目直视门口。父子俩互相瞅了一眼,只顾低头扒拉。餐桌安静,吧唧声显得夸张。母亲把碗筷狠狠往桌上一顿,说,宁可倒垃圾桶,喂狗,看你们谁敢给她吃。
晚饭后,父亲无果而返,又平添了一肚子火。小叔依然没在家。父亲找到小区边上小叔常去的麻将室,也不在。走到小区门口,那里已经围了不少人。老太太从电梯下到底楼,出电梯口后,把板凳当拐杖,坐在小板凳上,撅起屁股,双手移动板凳,坐实,再挪动板凳,倒退着挪向外边。老太太在向人诉说,一把鼻涕一把泪。有人说祖兴来了,一群人瞬间把目光围到他身上。有人说,兄弟间再有意见,老人的饭还是要管的。有人嘀咕,毕竟亲娘呐,不怕被人戳背皮。
“南湖苑”是安置房,以前的老邻居都在这里,对他家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习以为常。新邻居不了解,他觉得有必要解释几句,可哪里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事。戳背皮就戳吧,父亲反而不想说啥了,连人带凳子把老太太端起就走。
父亲隐瞒了老太太下楼的事,从橱柜角落找出老太太以前用过的碗筷,冲洗擦干,盛一碗饭,夹了半碗剩菜。怪不得你烧那么多饭!母亲拦在门口,不许父亲出去。父亲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志军。志军说,妈,天热,剩饭剩菜隔夜就馊了,今天就当看我面子。
奶奶坐在小马桶上,裤子褪到膝弯,露出干瘪的屁股。竹榻上的草席已经摊开,志军放下碗筷,说奶奶吃。奶奶艰难拱起身子,慢条斯理拉起裤腰。一阵异臭顿时弥散在逼仄的空间。志军忍住臭味,把小马桶盖好,用脚踢进床底。床下还有古旧的木质脚盆,脚盆中放着破脸盆,脸盆里放着搪瓷杯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样貌都与使用它们的主人匹配。
奶奶坐在小板凳上,以床为桌,开始享用晚餐。过道里延时声控灯暗了,志军跺一脚,灯亮起,过一会又暗了,再跺一脚。志军开了门,让客厅灯照过来,刚转身,门砰地被关上了。志军按亮手机电筒,幽蓝的光打在奶奶侧身,一头蓬乱的白发如带了电荷,奶奶老得不成人样,简直吓人。奶奶几乎不加咀嚼,一口饭塞进去,嘴巴扭动几下,咽喉像漏斗。小时候,志军整天在外疯跑,吃得再饱,不待晚饭肚子咕咕叫,日日空晌去奶奶灶上扒冷饭吃。那时奶奶已经回到岸上,父母在湖里捕鱼,不到天色暗是吃不到晚饭的。饿是最好的菜,半碗白饭,当然佐以冷韭菜冷青菜最好,有冷鱼更好,毕竟是荤腥。后来有了堂弟志强,奶奶似乎更疼爱小孙子。有时冷饭不多,奶奶只许志强吃,志军眼巴巴看着堂弟狼吞虎咽。为这事,母亲跟老太太吵过好几回。
小叔的手机开着,但不接,志军说我试试。那边果然接了,电话中闹哄哄的,咔嚓咔嚓自动麻将机声中,自摸!有人惊呼,接着小叔一声哀叹。志军刚喊出小叔,那边把电话按了。志军改发短信,我爸希望你来我家,有事商量。没反应。志军又发,你把奶奶扔我家门口一走了之,究竟为什么?
问你爸。对方回了三个字。
你回他,都是一个门里爬出来的,亲兄弟之间摊得开卷得拢,你像贼一样躲着,算什么本事。母亲插嘴说。
志军换了平和的措辞,把母亲的意思变成文字。无回应。志军让父亲想想有什么不当之处,被小叔责问。社保卡!父亲说。
前几天,他打我电话,说想核对奶奶卡上的钱数,明摆着不放心我,说话很漂亮,说毫不怀疑我克扣奶奶的钱,只是不放心村委那些人,不仔细对账,吃了亏都不晓得。我多了份心,去银行打了对账单,给他看。他非得看存折。存折到他手里,天晓得会还我,当我猪头三?
南湖开发湿地公园前,自然捕捞完全退化,渔业村百十多户人家,大多改行上岸,仅有的十多户分散在南湖各区域,割一块水面围网养殖。平日不再以船为家,船不过是交通工具和饲料仓库。这十多户人家,在湖边一块突出的半岛上陆续建了平房,发展为一个小渔村。志军家,及两个叔叔家,都分到了南湖苑140 平方米的安置房,一笔补偿款,另外还有水面补偿款。奶奶是孤老,住一间胡乱搭建的小屋,没有资格获得安置房,只拿到两万多赔款。而作为失水渔民,每月有一千多元退休金,直至终老。
奶奶住哪家呢?当时的小叔表现出很高的姿态,主动提出让奶奶随他住,信誓旦旦,如果克扣老娘,被雷劈死!志军母亲一针见血,你也拿他的话当话,还不是图老太太那些钱?父亲倒是反过来劝母亲,平日跟小儿子关系最亲,她愿意住他家。再说,既然他发了毒誓,量他不敢。母亲说,帮他家烧烧汏汏,有甚不好。父亲说,住我家,你愿意不?
母亲当然不愿意老太太来住。母亲出小区,宁可舍近求远走东门,绕过老太太可能出没的地段,怎么可能跟她在一个屋檐下住,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刚搬过来时,小叔家来不及装修搬不进去,老太太在这边暂住过几天。那几天简直可以用噩梦来形容。老太太趿拉着拖鞋,屋里屋外乱跑,鞋底沾满泥巴及乱七八糟的脏物,刚刚拖干净的高级地砖、木质地板印上一串串的脚印。吃菜更不识趣。比如吃红烧肉,一般人从碗面最上层看准了一块下筷子,尽量不碰别的,虽说在同一个碗里夹菜,筷子独立,同桌口水基本无交流。老太太呢,筷子插到碗底,上上下下抄个遍,这块搛搛,那块戳戳,似乎在最大限度地选优,有时夹到筷子半道放回去,换一块。不要说儿媳孙媳,连她儿子孙子都受不了。自从老太太来这边搭伙,志军妻子小静只同桌吃过半顿晚饭。每次开晚饭时,几个人往隔着紧闭的房门招呼一声,小静在里边回应“吃不下”“不想吃”。几天下来招呼变成纯粹的礼节了。
志军妈嘀咕,不是以前胃口挺好的嘛,成仙了?看似质疑,毫无疑的成分。所有人,包括老太太自己,都知道为什么。小静提着大包小包零食进门,第二天一个个包装袋包装盒到了垃圾桶里。志军妈倒不是担心儿媳零食不作顿,影响健康,而是心疼这些本不该支出或不该多支出的钱。这不,小静连续好几天在外边吃晚饭了,说闺蜜生日,同学请客,还有什么群聚会,天知道怎么一下子有那么多聚会。
那一次,老太太连头搭尾在大儿子家住了半个月。这半个月,老太太倒是活得滋润,从她气色上能看出来。志军妈却是苦不堪言,一家人的生活完全乱了。一天夜里,她听到儿媳小静在埋汰志军,说老太太从不刷牙,筷子上的口水不知多脏,想想都恶心……是的,不想不觉得,一想,真的恶心。志军妈提议分食制,跟食堂一样各吃各的。志军妈的意思当然不是全员分食,是让老太太独坐,另外给她夹点菜。志军父亲沉思半日,说算了,熬几天吧,说出去难听的。志军也表示反对。爷俩顾及脸面,不愿背上忤逆的骂名。
这一夜,三个人都不安逸。志军母亲一改早睡习惯,蜷在沙发上看电视,手里捏着遥控,频繁更换着频道。客厅里没开灯,荧屏忽明忽暗的光影里,母亲哈欠连连,却不肯进房间睡觉。志军父亲被指派出去蹲守,把小叔捉过来,母亲说没个结论不要回来。志军借口看父亲,上上下下跑了几个来回。蚊帐里的奶奶打着响亮的呼噜。一个老妇,那么瘦,呼呼的鼾声夸张得不可思议。老竹榻也极不安分,时时发出奇怪的声响。志军第三次回到过道时,奶奶的呼噜变换了调子,似乎喉咙里被什么东西呛着了,突然戛然而止,转而一声咳嗽,震得竹榻吱吱嘎嘎,散架一般。我要喝水……奶奶说梦话呢。我口渴,再给我拿一支蜡烛……志军听清楚了,不像说梦话。
志军从楼下汽车里拿了一瓶矿泉水,拧开盖子。蜡烛,这会儿哪里去找蜡烛呢,有也不行,烧到蚊帐不是好玩的。唉……奶奶咕嘟咕嘟咽喝了几口,长叹一口气。唉……志军也叹了口气。
迷迷糊糊中,志军被父母吵醒。没等到,你回来干什么?有骨气死在外头,不出脓不出血的也算人!真诈我们呢,今天不把她弄走,我走!母亲骂起人来连桑带槐,哪一句对应哪位,哪位自己明白。一般仅止于出口气而已,过会儿气消停了,该干吗还干吗。不过,与她婆婆决然不会。母亲早起看爷俩没弄出什么名堂,站到门口,对已经起身坐在床沿上的老太太吼道,你小棺材(龙兴)死在外头啦,帮他收尸去吧。老太太干瘪的嘴巴蠕动了几下,没说话,狠狠地横了一眼大儿媳。志军母亲以不屑而仇恨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对手,从那短暂的一瞥中读到了久违的内容,残存的一丝丝怜悯瞬间化为乌有,又一次激发起久违的斗志。走到“归一苑”门口的人了,做啥下棺材冤家,你坏良心呢!志军妈越说越心火,恨不得像当年的二妯娌扑过去动手。
坏良心?坏良心人烂肺肚肠。
老太太说话慢悠悠,轻飘飘的。志军妈患过气胸,因肠梗阻动过手术。老太太这句有气无力的话,刻刻毒毒,噎得志军妈跳起来。老头有时奚落她,嗓门大气势汹,其实没卵用。年轻时婆媳之间吵归吵,老太太有个头疼脑热,志军爸几句软话,志军妈还能捐弃前嫌,给老太太端药洗濯。就凭这个,老头觉得她还不错,从不偏心老太太。
老太太三个儿子秉性迥异,三个儿媳决然不一样。二叔子根兴夫妻活着时,好的时候恨不得合穿一条裤子,不好起来拳脚相向。一般夫妻打架,总是从吵骂开始的。他俩懒得吵,直接动手,不需要做铺垫。当然,体力占绝对优势男人还是让着点女人的。二儿媳刚嫁过来那一阵,老太太如法炮制,拿出降服大儿媳的手段。人高马大的女人似乎忍气吞声,比大儿媳绵软。忽一日,男人们都下湖了,老太太(那是还不老)一个人背对着家门补渔网,女人从背后一把揪住老太太头发,使劲按住,劈头盖脸一顿打,转身就跑。整个过程毫无征兆,女人始终没说一句话,老太太没看清袭击者,但从脚步声,从喘气声能感觉到是谁。黄昏时,老太太摸着一头鼓包,向老头和儿子哭诉。女人承认得很爽快,但恶人先告状,说老太太先动的手,无奈之下才还手。没第三者见证,这场战斗成了悬案。老太太吃了哑巴亏,自然不甘心,人前人后说她的不是,又被对方逮着机会修理过几次。老太太自知不是对手,以后看二儿媳,眼神躲闪,不敢直视。仗着那么几次暗算,二儿媳太平了大半辈子。
志军妈年轻时没跟谁动过手,更不要说现在了。那句话实在让她憋屈。叫你嘴硬!她哇哇叫着,冲到老太太跟前,拖出床底下破烂,一股脑儿扔到楼梯里,勒令丈夫,把老太太赶走。
那句话,志军父子都听到了,心里天平更加失衡了。父亲喉头咕哝了一声,摇摇头,叹了口气。
傍晚时分,小叔过来了。一脸倦容堆着勉强的笑意,似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口大哥大嫂叫得亲热。
你不是能躲么,干吗来了?志军父亲冷言相对。
打煞亲兄弟,好煞外头人。小叔嗫嚅道,大哥,是……是我不好。
志军父亲懒得跟他说话,连责备他的力气都省了,也不问失踪的这两天一夜去哪里鬼混了。这个油嘴张三郎,口中没一句真话。
老太太连同所有家当被送到那边,扔在过道。老太太不知道,小儿凌晨就回家了,蒙头大睡,早饭午饭都没开火。好在有志军偷偷给她的一袋面包,还有半瓶夜里喝剩的半瓶矿泉水,才没饿着。黄昏,小叔开门出来,过道乱七八糟的,凳子上点着一支蜡烛,不知哪里来的风把火苗吹得摇摇曳曳,噗噗作响。那不是普通的照明用的蜡烛,而是烧香祭祀用的红烛,一次次重复融制的劣质蜡烛。真不知老太太从哪里捡来的。难怪手气差,触我啥霉头!他骂了一声,却发现老太太不在。
都说天下父母为小子,老太太内心有没有承认过最疼爱的小儿子最没出息?至少场面上没有过,认为是运气不好,比如娶的老婆没出息,养的儿子不争气,总之都是别人的不是。早年,小儿子不想当渔民,进了厂子学电焊。一天到晚油头粉面,衣冠楚楚,狐朋狗友特别多,工厂里那点工资根本不够花,最大的收获练大了酒量。两百多斤体重,肚子大得蹲不下身子,没法干电焊了,频繁跳槽,基本上没有一家超过半年的。找的外地媳妇也是又懒又馋,穿得花枝招展,三天两头往市里跑,莫名其妙失踪几天,终于在儿子志强十岁那年,跟人跑了。龙兴苦啊!老太太经常对大儿子祖兴说,长子为爷,你要多多照顾。花天酒地,过一阵带个女人回家,比我潇洒不知多少倍,像苦的人吗?有一次,这小子请一个外地女人吃饭,醉醺醺地骑着电瓶车送女人回家,摔了一跤。老太太心疼得要命,叫大儿子去探望。志军父亲把事情经过告诉她,她居然毫无责备的意思,肉麻着唠叨着,六十好几的人啦,摔不起。老太太简直瞎了眼睛,对小棺材的迁就毫无理由,毫无原则。你想照顾他,我眼开眼闭只当没看见,还想怎么着?祖兴回应母亲,更多时报以沉默。
志强是老太太的小孙子,可以说,从小到大,基本上是老太太带大了。这孩子,眉清目秀,酷似他外地母亲,嘴甜像他父亲龙兴。由于欠管教,初中开始轧了一帮街痞子,惹是生非,无心读书,最终只上了职教。志强读书不入门,骗细娘却是无师自通。如花似玉的女孩是志强隔专业同学,天知道中了什么蛊,死心塌地跟着志强,赶都赶不走。没花一分钱,白得这么一个媳妇,多牛!酒桌上,龙兴常常以此为吹牛的资本,说大哥不如他有福气。
小叔在外掼派头,在大哥面前,总是矮着身子,一口一个大哥,叫得亲热、卑谦。父亲冷冷地看着小叔表演,看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老娘哪根筋搭错了,偏要到你这里住几天,我说大哥家那么挤,拦不住啊。小叔一脸诚恳。老娘没搭错,你也清醒着呢,是我过分你们了,对吧,老娘吃你的,住你的,社保卡应该还给她,啊,应该给你保管才踏实,否则,老娘随时会搭错筋。志军父亲话里有话。
这……小叔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很快从容起来,不是不是,没这意思,我龙兴怎么可能惦记老娘养老钱,岂非猪狗不如……
如果不看前因后果,龙兴占尽理由,估计十有八九要戳祖兴背皮。大概半年前,小叔在外头喝多了失口,透露自家造房时,老娘曾经资助过他两万块钱。那年头两万块钱马马虎虎可以造三间平房了,难怪他整天吊儿郎当,日子过得滋润。两个哥哥也曾怀疑过,没有凭据仅止于怀疑。问老娘,老太太动不动常唱苦经,拖大带小养大几个子女,手头总是缺一截,哪来钱贴你们啊。老太太说的你们,明显扰乱视听。时隔多少年,瞒得滴水不漏。
这勾起志军妈一段陈年往事。志军妈第一次动手术,实在拿不出押金,父亲涎着脸向老太太借了一千元钱。连带亲情的债务关系没那么泾渭分明,如果老太太有恻隐之心,豁免了,也并非说不过去。老太太像地主逼债,一次次开口索要,口口声声一碗水端平,有一次是在年夜饭桌上。
还有脸住我家啊?志军妈绝不答应。没分到安居房的老人,几个儿子家轮番住,纵有天大困难,都推不了责任。老太太厚此薄彼在先,志军父母无情无义在后,于情不对,于理却占理。
如果不是老太太生病,社保卡的事还不会穿帮。那次要给老太太交押金,志军父亲说老人社保卡上应该有一点钱的,不够兄弟俩再平摊。谁料,到银行一查,卡上只有几毛钱零头。父亲让银行打了一张对账单,不但两万元补偿悉数被取走,连每月一千多三百元的养老补贴分文不留,五日到账,马上被领走,只错时辰不错日期。父亲要小叔说个所以然,小叔期期艾艾,说可能老太太派用场了,可能另外存起来了。问老太太,老太太闭着眼睛,哼哼唧唧,一副被疾病折磨得痛苦的样子,又不忍心逼迫她。父亲对老太太说了句狠话,这次要是我再拿钱出来,等于凭空把钱给这小棺材,大也是儿子,小也是儿子,我不是你亲生的?偏心到这个地步,死活跟我无关。
志军父亲召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家庭会,每家一个代表,叫上了两个姑姑,按说外地工作的堂妹代表已故的父母,她说赶不回来。其实不想掺和,婉言逃避了责任。不要看老太太嘴巴还硬,迈进九十门槛的人,今天不晓得明天,跌一跤,感冒一次,喝水呛一口,都能要她老命。父亲接着说,不是盼她死,照这样下去,死后必有纠纷。大家都知道老太太有些钱,唯恐她东塞西藏。老娘没钱!哪里还有钱啊……小叔嗫嚅道,话音慢慢低下去。父亲心里何尝不明,只是不想戳穿,老娘那几个钱早就被这小子骗走,挥霍殆尽了。一旦撕破脸面,小棺材宰他没有血,剥他没有皮,无赖一个。父亲说,半年多时间,一个足不出户的老太太,用掉那么多钱缺少理由。
大哥这么说,我跟老娘一个锅里吃饭,钱的事说不清了。
父亲没有接小叔话茬,继续道,老娘钱是老娘自己的,也是子女的。常听老人说不要把家底挖空,好歹留些活络钱,小毛小病不向子女伸手,有的甚至连自己开丧的钱都备好了,不给子女增加负担,更有的双亲过世后,子女不但没贴钱,相反每家分了几千几万。小叔插话,子女分这种钱也好意思。父亲继续不理会,说,我不指望分遗产,相反,为父母花再多的钱,做子女的理所应当。只是……钱要花在阳光下,贴在暗处的钱再少也窝心。
父亲所指,在场的心知肚明。老太太哪天突然倒下了,这小棺材两手一摊,说没钱,或者干脆玩失踪,你拆他屋,还是把他卖了?他不想直接捅破这层纸,有些话最好是两个姐妹说出来。志军大姑说,老娘以前有没有库存不知道,但这次有几万块钱,应该有个说法,说不出来龙去脉,休怪大哥多心。小姑也附和着。面对众人,小叔涨红了脸吼道,谁知道,你们去问老娘呢!两个姑姑早就估计到了,老娘不会说实话的,那些钱不一定是被这小子骗走的,而是老娘主动给他的,早打水漂了。
这次讨论的结果,对存疑的那笔钱搁置一边,小叔被迫交出老太太的社保卡,交志军父亲暂管,老太太每次用度记账。父亲本不想为自己找嫌,几个都推荐他管理。反正除了这小棺材,谁管都可以。父亲捏住老太太几个钱,将来少受一点损失。但父亲知道,他拿的是一个烫手山芋,这小子,早晚会寻事。
大哥,跟你商量个事,明天开始志强带孩子回家来住了,房间也紧张,让老娘……我们大家克服困难。
小叔说的是实情,但未必是实话。
志军与志强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堂妯娌之间却有微信联络。女孩很小时父母离异,被判给整天不着家的父亲,跟着酒鬼爷爷长大。缺少亲情滋润的她,早熟,早恋,借此早早逃离名存实亡的家。对这个自己跑来的“儿媳”,一家人萝卜不当菜,就像收留一只流浪猫。女孩做了几次人流,最后一次,医生说子宫薄得再也不能刮了,只得把孩子生下来。孩子都上学了,这边愣自不给办婚礼。志强跟父亲吵,龙兴说没钱,又说,又不是明媒正娶“媒”你的,摆什么谱。小两口一赌气,住到市里去了。可城里没房子,租住在老小区一户车库,等于过着底层人生活。女孩跟小静的聊天充斥着牢骚。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当城里人的,志军说,典型人物聚到一家子了。
小叔话的真伪,志军心里有数,抢在父亲话前说,小叔,应该让他们住家来,哪有爷爷不照看孙子的,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小叔横了一眼志军说,我是你长辈,哪来资格管我卵子大小!
小叔动辄以长辈自居,以长辈口气教训小辈,父亲不悦,调侃道,你是卵大,一夜输二十万,我们高家数你有胆气。小叔恼羞成怒,我……我自己的钱,输赢关你屁事!
拿到新房钥匙和补偿款那一阵,志军一家忙着装修,争取早日入住。小叔整天不见踪影,难得路遇也是来去匆匆。政府买单的出租房马上到期,他怎么一点不急?后来有人透露,小叔这一阵像捡到了钱,没日没夜豪赌,其中有一夜输得很惨,装修的钱输得差不多了。所以他几乎没怎么装修。
各开门头各开户,当然不关我事,有本事不要榨老娘!父亲也火了。
等会儿把老娘送过来,让你去榨。
无赖腔!志军心里骂道。
越听越覅听,高家出你这个末代!母亲站在门口,把一个红色的折子使劲砸向小叔,吼道,老太太的钱一分没动,拿去!省得你睡不着。今朝三明朝四,你屁眼一撅知道你拉什么屎,还不是为这几个铜钿?母亲顿了一下继续道,我量你身上掏不出百元钞,麻将室东欠西借,没有一家待见你,说得再难听些,锅里没有夜饭米。以后不许再踏进我家,还有,老太婆死活跟我家无关。母亲一连说了这么多气话,呼吸显得急促。
三个男人被震住了。志军并不劝止,觉得母亲说得痛快。志军瞟一眼小叔,脸色平静,母亲的话掷在石头上。
小叔手机响了。对方声音大口气急。老太太被汽车撞了,这会儿躺在小区门口。小叔哇哇叫着,说出来时……出来时还在家,怎么眨眼工夫跑门口去啦,不要弄错。对方骂了一句。志军的心揪紧了,问,哪个门口?跨过几步按电梯。志军父亲也跟过来。小叔还在电话这端哇哇叫,问车子跑了没有,有没有记下车牌?
一辆小红车斜停在门口,车门开着,一位戴眼镜的女孩扶着瘫坐在地上的老太太,看样子是车主,苦着脸,吓得不轻,说话打哆嗦。老太太慢吞吞站起身,甩开姑娘的手说,妹子,不关你事,是我钻到你车上的,省得累赘,唉,死了太平。挥手示意姑娘走。小叔发急了,一把拉住姑娘说,想逃?不放一个桩头(一万元)休想走脱!
老太太白了小儿子一眼。
人多嘴杂,有看客打抱不平,说你敲竹杠,还想靠老娘发财?也有说,还是报警吧,万一有什么事说不清。还有人探身往车里看,问姑娘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如果没有,我们给你作证。姑娘擦着眼泪,感激地点头。
光顾着说话,老太太已经蹒跚着走出人群,折倒山墙拐角了。哎,人呢?小叔惊叫一声,妈——跟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