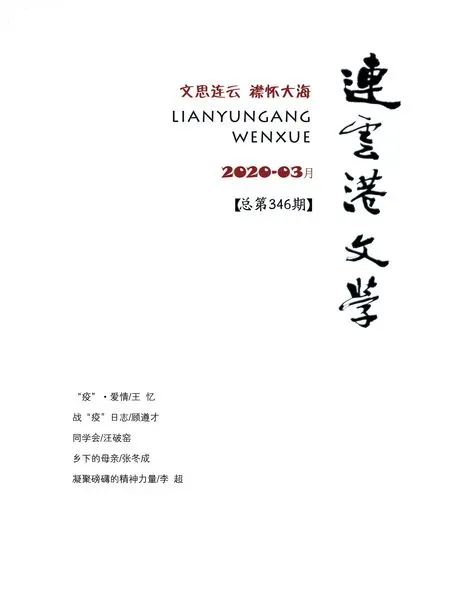最毒的草开最迷人的花
冷紫蔷
一
当我第五次要求换房间的时候,明显感觉到酒店前台的服务员脸色极为难看且露出不耐烦的表情。这是一个年纪二十五到三十之间的女人,因为穿着老气横秋的工作服,头发又被压低盘起,所以年龄看起来有些令人猜测为难。她看似还算礼貌的表情里藏着一股发霉的气息,隔着一个吧台的距离依然能感受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潮湿,令人感觉沉闷烦躁。
像个演员一般,女服务员面露难色的说,今日已无空房间为你调换;并一再强调地说,他们酒店隔音效果是经得起检测的,末了她说如果有人退房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为我调换。我恶狠狠地看向她,本想和她争个面红耳赤,下楼前分明看到有保洁员正在打扫空出的房间,但她最后看似诚恳的承诺让我不得不打消这个愚蠢的念头。平心而论,这个酒店各方面来说还是不错的,价格不贵,房间比较干净,最重要的是位置很好,推开窗子看到的不是喧嚣的车水马龙,而是令人心旷神怡的绿树成荫。暂时我还不想和他们撕破脸皮,我还需要在这里停留几日,直到我找到满意的住处才能搬离。
不过是晚上八九点的样子,隔壁房间里便传来一对情侣争吵声,女人的嗓门很细但很尖锐,从开始的质问到暴跳如雷,再到最后张牙舞爪的歇斯底里。紧接着,便是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有玻璃制品摔倒的声音,也有女人哭喊的声音。我甚至能想象出男子的脸被扭曲暴怒的狮子,青筋在他额头一根根突起,他低沉的声音仿佛从齿缝中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每一个字都说得那样用力、愤怒,后来终于抑制不住,咆哮了起来,如同千军万马直穿墙体,向我扑面而来。我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的争吵了,每次吵架的内容都大相径庭,但剧情却愈演愈烈。起身走到浴室,把花洒打开浇湿我整个身体,从上到下,当湿漉的发丝贴紧脸颊贴上耳朵的时候,我才慢慢地恢复平静。
回到卧室的时候隔壁吵哭喊声也没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激烈的床板与身体之间迸发出来的声响。隔壁女人的声音依然尖锐刺耳,此起彼伏。我拿起枕边那本厚厚的《百年孤独》用力地敲着床头靠着的那面墙,果然,那边的动静消停了一些,不过没过多久又闹腾起来,分不清这次是争吵还是恩爱。这声音足足有一个多钟头,即使我把电视的声音调到最大,依然掩盖不了隔壁房间的骚动。
在忍无可忍的第七天,我毅然决然的拖着行李箱走出了这个害我差点精神恍惚的酒店,当然,许是上天的眷顾,让我在凌晨三点翻找房屋租赁信息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还不错的租房信息。
二
当我觅着地址追寻过去的时候发现它离我并不遥远,不过是穿过几条街。那是一条老街,青石板铺就的小路,幽深而狭窄。积年的石板路早已看不出它原来的颜色,阳光似乎很少光顾这里,偶有几缕光线透过大片的青藤,光和影映在石板上,泛出青色的油光。两侧青砖砌筑的房子略显年代感,每家门前都种有花草,有的攀爬有的垂落,从屋檐到墙壁红的红绿的绿,偶尔风来,禾香沁鼻,溅的人一身春色。当我刚好看到那个门牌号时,天空下起了雷阵雨,青石板被雨滴打的嗒嗒作响,我慌忙叩响了木头门上做旧的铜铃铛。
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身着一袭类似长袍一样的宽松麻料长裙,蓝色的底白色的花,让人顿时联想到青花瓷,很是别具一格。女子个子修长她的头发又密又长、松散地垂于腰际。雨下得很大也很急,那女子竟手持一把老旧的木柄雨伞将我迎了进来。进门后是一个不小的庭院,中间是一条被形态各异的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两旁是郁郁葱葱的藤架,藤架上挂满了果子,个个硕大且饱满。不远处有一方鱼池,里面的小型瀑布流水口甚是漂亮像一座假山,走的近些还能看到里面肥美的水草和几只游的正欢的鱼儿。
女子的笑容很浅,清秀的面孔下给人以清冷的感觉,她的皮肤相当的白,甚至白到有些病态,即使这样依然掩盖不了她的美,凛冽的美,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当她得知我便是今早联系的租客时,她礼貌的带我进了一个收拾得很妥当的房间,房间布置得跟她一样清冷,不过倒是干净整洁。房间不大但却放了一张足够大的木床,床单枕套和一条法式的毛毯都是像刚刚铺上去一样的新,稍稍离近就能闻到那些床品上散发出好闻的气息。
“你先把行李放下,然后洗个澡换身衣服,厨房里正做着饭,我等你一起午餐。”女子的声音没有太多温度倒也不觉得讨厌,正好应了我同样清冷的性格。
洗漱间不大却被女主人收拾得井井有条,许多细节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很有格调的女人,祖马龙香味的沐浴露,花瓣制成的精油皂,就连洗发水都是纯手工制作。浴巾是一块雪白崭新的新浴巾,牙刷牙具也是没有拆开崭新的,看得出女子的细心。
三
用餐的时候,女人依然话不多,当我抬头看她的时候她刚好也在看我。“这个菜很好吃艾,你是怎样做的?”我有些尬聊地找了个话题。“其实就是普通的家常做法,不过是里面加了两味香料。”快吃完的时候女人介绍起了自己,她叫青,今年32 岁,独身,是个园艺师,她说这里很多的庭院都是她设计的,她从事这个行业已有十年之久。她让我叫她青就好。她说她对租客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得带异性回家,房租可以月付也可以季付甚至可以周付。这时我才想起问她租金每月是多少,当时看到这个租房信息的时候是心急如焚想要搬出酒店也没考虑太多其他因素,只看看上面写着只租有缘人限女性。
“每个月租金五百,包括水电,如果同我一起三餐的话再加三百。”我以为我听错了她说的数字,嘴里的饭差点没掉下来,我惊愕的表情应该落入她的眼帘,她依然淡淡地说房租五百,加伙食八百。如果你不忙的时候可以帮我一起修剪花草,这样伙食的三百也是免去的。我慌忙摆手说伙食费我照交,平时我也没其他事可以一起帮忙修剪花草,就当学习了。
青的嘴角稍稍泛起一丝笑意,放下筷子的时候说了声那就这样决定了。“对了,我有些小嗜好先跟你说一下,我喜欢临睡前喝两杯,喜欢煮茶,大约两天抽一包烟。”天哪,我在心里狂喜,至少有一样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我从包里拿出一包宣赫门顺手递了一支给她,她没有接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我习惯了固定的牌子。我识趣的把烟放进烟盒,青从旁边拿了一包我从未见过的一个牌子香烟,单从烟盒看是令人作呕甚至血腥无比的图案,我大概猜得出这是一种小众的国外爆珠香烟。青娴熟的捏碎烟嘴处的爆珠继而点起了那支短而粗的香烟,她抽烟的姿势很是迷人,哦不,应该说是极其销魂,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女人抽烟,但却从未为一个女人抽烟的姿势而着迷,有那么一瞬间我愣愣地看向她,忘记了自己手里也点燃着的宣赫门。
“你呢,你喜欢什么?”青居然和我闲聊了起来。“我比较喜欢咖啡,也会小酌两口,不过已经两个月没再碰酒了。”我如实的回答她。确实,我不是贪杯的人也谈不上会喝酒,对于烈酒我从来都是浅尝辄止,即使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你看起来是我喜欢的类型,否则不会留你下来,在你之前共有过七个租客,其中三个是她们中途退租,另外四个是我被赶走的。”我有些受宠若惊地望向正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人,她此时看起来不再那么拒人千里之外,脸色看起来也不像刚才那样惨白。
四
晚上我早早地进了自己的房间,打开随身带着的笔记本记录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身体的状况。这时青突然推开了门拿了一束插好的鲜花连瓶带花一同放在了我的床头,我连忙感谢青却转过身带上了门。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被花簇包围,阵阵奇香扑鼻而来,这时一个黑色身影向我走来,我努力地想看清对方的脸却怎么也看不清,我意识到这是在做梦,我想挣脱这个梦境却被无数的花藤紧紧缠绕,那个身影有着令人恐惧的气息,我能感觉到他手拿利器,正向我逼近,我想呼救声音却卡在喉咙。
连续几个晚上我都做着相似的梦,我努力让自己在梦中看清对方的面孔都没成功,好几次那个身影差一点就把手里的利器刺向了我的胸口,我甚至意识到有某种力量在保护着我不让那个恶魔接近我的身体。我张牙舞爪地想要夺下恶魔的利器,用尽全力也挣脱不了花藤的缠绕。
白天我开始发烧,我恳请青去附近的医院帮我买一些药,青却给我煮了一壶草药,并告诉我这个很管用。果然,青的草药不仅退了我的烧还治好了我连日的梦魇。我想感激她,却不知道拿什么来回报她,只能在她打理园子的时候去给她打打下手,青依然一副清冷的模样话不多也不会笑,但弯着腰干活的她侧脸真的很美。
五
我跟青说想给她做一顿我家乡的饭菜,青欣然答应。正当我在菜园里采摘蔬菜的时候听到有人敲门声。我和青都是深居简出的人,也未曾听过青提起过她的家人和朋友,还没来得及多想就听到青让我先去开门。
当我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我仿佛掉进了万丈深渊,那个如影随形的恶魔真真切切的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正当我想关门的时候,那个恶魔一把抱住了我,口里念念有词,“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知道我找你找了多久,我找的你好辛苦,快,快,快跟我回家,我日日夜夜都在思念着你……”
我逃也似的拼命从这个恶魔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没跑两步,再次被他抓到,他一双红透了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突然他从怀里拿出一把斧头,猛地就向我身体砍来。
我大喊一声从床上惊坐起来,浑身的汗水早已将睡衣湿透,我慌乱中打开了床头的灯,这时才发现青正杵在我床头,大概是刚才的梦境已经是到了恐惧的极限,青的出现并没让我有多大的恐慌和多想。
“又做噩梦了?”青压低声音幽幽地问。
“嗯……”
“梦到男人了?”青一边说话一边拨弄着我床头柜上的那瓶鲜花。
“嗯,”我一时还没从噩梦中解脱出来,甚至言语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你相信爱情?”青猛地抬起头来问我。
“不信”我脱口而出完全没有任何思考和犹豫。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听听你的故事”青的语气突然温和了许多。
“我以为只要我逃离了那个城市,从此就会一身轻松。那个恶魔是我生活了整整八年的丈夫。那是怎样的一个魔鬼,好吃懒惰不说,连一份正经工作都没有,最重要的是他嗜酒如命,一天三顿酒,顿顿喝到不是摔东西就是掀桌子,他暴躁如雷的性格常常扬言只要我敢离开他他就杀我全家,我知道这个变态完全可以做得出来,所以我一直在忍一直在忍,即使他的暴戾早已让我痛不欲生,但我还是没有勇气逃离他的世界。
你知道吗,他的变态是那样的令人发指。我们在一起的八年时间里我堕胎五次,即使是在我流产期间他的兽欲也从未停止过,长此以往,这使我连做母亲的权利都没有了,我绝望过,自杀过,也逃跑过,每一次都被他像抓小鸡一样抓了回来,而每一次的回来得到的都是变本加厉的暴打和折磨。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生病了,医生告诉我让我善待自己的余生,离开医院我没有回家,直接买了一张火车票。”
六
自从上次的梦魇以后,青每晚都会给我端一碗汤药,并告诉我这有安神助眠功效,喝了它就不会再做噩梦。
果然,喝了青亲自为我熬的汤药后我的睡眠比以往好太多,并且一次噩梦都没做过。半个月后,我的气色明显比刚来的时候好太多,在我的脸上居然能看到一些红晕。晚饭的时候,青突然说了句让我回家的话,我愕然地看向她,不知所措。青放下筷子说,“让你回去不是让你再继续过从前的生活,也不是赶你走,是让你回去跟那个男人彻彻底底干干净净地断了孽缘,然后再轻轻松松地过你自己下半辈子,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不彻底了断你的噩梦还会继续。”
原本我是从来没有过再回去的念头,但青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想彻底从噩梦中走出,必须在法律上跟他断的彻底。青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并告诉我要勇敢地再向前迈一步。
当我回到这个熟悉又胆战心惊的城市时,我浑身开始不自在起来,明明是六月的天气,脊背却泛起阵阵寒意,身上每一寸肌肤都紧缩着,竖起的汗毛在提醒着我的恐惧。这时,一个电话响起,是我的主治医生让我回医院复诊。
当检查结果出来时,我的主治医生竟像个孩子般跳了起来,一边蹦跳一边雀跃的惊喜万千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创造了奇迹,天哪,你简直创造了奇迹,这是我从医二十年以来亲手经历的第一个天大的奇迹,你知道吗,你的癌细胞居然完全没有了,你没有化疗甚至没有后续治疗,居然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这些癌细胞统统不见了。”大概是我听到过最美好最可爱的语言,我抱着这个可爱且美丽的医生我想大声告诉她我爱她,可是我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此时此刻我突然好想青,想同样抱着她,不管她平日里有多冰冷,我想告诉她,我们真的可以来日方长,我真的还可以有大把的时光可以去重来。
七
我从来没有想过办理离婚是那样简单的事儿,当我把病例本扔给那个恶魔的时候他只看了一眼便同意和我一同去民政局,当然,这是当初诊断的时候留下的病例,没想到却帮了我天大的忙。走出民政局才发现家乡的天也是那样的湛蓝,连空气都变得格外香甜。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结束了八年炼狱般的婚姻。此时此刻我只想放飞自己,我想重新开始我的人生,我想当面感激青给予我的勇气。
再次来到青的城市,有种莫名的亲切感,还是那条街那条铺满青石板的小路,还是如同我第一次来时一样下着雨,还是一个人拖着行李箱。
我数着步子来到青的房子前,才发现大门上赫然挂着一把生了锈的铁锁,拔开门缝向里望去,院子里杂草丛生,像很久没有人住过一样,可我从离开到回来不过是短短几天而已。我退回到门口看了看门牌号,以为是走错了人家,但门牌号不会说谎,它印证我确实没有走错。满心的欢喜瞬间变成了慌张,我退出胡同再次确认我没有走错街道。
突然像个被抛弃的孩子,我在大雨里不停地走着走着,最终还是来到了青的房子这里。我傻傻的坐在地上,坐在雨里,想象着青只是买菜去了,一会就会回来。
我忘记了我坐在那里坐了多久,只是雨停了又下,这时路过一位奶奶,我才想起上前询问起青来。我问奶奶知不知道这里的主人去了哪里,她什么时候走的,又什么时候回来。奶奶直愣愣地盯着我看,像在看一个怪物一样看我,她没有走开,直到确认我脑子没有被烧坏才开始跟我攀谈起来。
奶奶问我是哪的人,来这又是找的谁,是不是迷路了、饿坏了、还是被雨淋的有些神志不清了。我一一告诉奶奶我的来历。奶奶再问你要找的人长的什么样子,我大概描述了青的模样,这时才发现奶奶的脸色已经变得相当难看,她紧锁着眉头一副欲言又止,她说孩子你还好吗?你确定你没事?我拼命地点头,然后急切地想要她告诉我关于青去了哪。
“孩子,你要找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这世上的人呀,你怎么要找她又怎么口口声声说认识她啊。你可知道这个房子已经很多年没有住过人了,更别提什么出租了,我们街坊邻居路过这里那也是快步行走不敢停留。虽然这里称不上凶宅但也不利啊,年纪轻轻的姑娘就这样在吊死在里面。听人说啊,这个院子一到晚上就能听到女人的哭声,前两年还陆陆续续有年轻的女娃在这附近莫名的失踪和自杀,听说足足有七个哪。哎,不说了不说了,都是些陈年旧事了。孩子呦,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劝你赶紧离开这里,回你自己的家吧。”
听了奶奶一口气讲那么多,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又在做梦,我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疼痛告诉我奶奶是真实的站在我的面前。这时我才意识到跟青相处的这一个月,除了知道她叫青以外,我对她的一切都无所知。我祈求奶奶再跟我多说一些关于青的故事,我告诉她我不怕真的不怕,即使她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八
“这房子的主人是个年轻的女孩,还没过门就吊死在这里。死的时候只有26 岁,她曾有个大家都知道的未婚夫,这男人是个外乡人,来这里做生意时与她相识相爱,并且在一起住了两三年,就当我们都以为要喝她喜酒的时候那个男人突然消失不见了,后来又听说女孩怀了孕,再后来有人见到有个女人直接找到了女孩家,对,就在那个院子里面她们大吵了一架。没过几天那个男人也出现了,那个晚上旁边的邻居听到她们家有打闹哭泣的声音,大概一周后有人来找女孩去自家的院子设计假山,没曾想那个女孩早已吊死在自己的家中,后来有人说她死的时候肚子已经明显很大了,哎,作孽呀,一尸两命呦。”
我像是在听一个故事,根本无法将故事中的女人与青相匹配。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奶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我就这么漠然地拉着行李箱走出了这个我曾熟悉又陌生的街道。
九
再次回到家乡,我仿佛是大病了一场,我想到了自己年迈的父母亲。
在小区的门口我看见母亲正吃力的提了一篮子菜,她的背有些驼了下去,我大步走了上前,才发现母亲的两鬓早已斑白,这是我未曾料到的。我清楚地记得母亲的头发从未像现在这样发白过,她的背影也从未像此刻这样苍老。这时父亲也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是来迎接母亲的,父亲一只手接过母亲手里沉重的菜篮子,另一只手温柔地挽着母亲的手臂。
我想喊他们,却怎么也发不出声,大概是哽咽了。就这样我走在他们的身后,跟着他们上了楼。
打开房间的门母亲长长地吁了一声,不过是三层而已,但母亲仿佛早已体力不支。
当我走进客厅的时候,我的照片被放在相框里,赫然被放在某个地方,那是我多年前拍的证件照,照片上的人微笑着看着我,像在和我问好。照片的前面放了我平日里最爱吃的水果和糕点。
“以后买菜就让我去吧,你看你现在的身体哪还能到处走动,自从小萍走的这一年多你都没有笑过。”父亲的话就像我照片前正在焚烧的香火一样一点一点烙上了我的胸口,我不明白他们说的什么意思,更分不清楚这是梦还是现实。仅一夜之间,我遇到的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我大声地喊他们,大声地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可是他们依旧旁若无人的在说着话说着我,好像我早已离去,永远的不再回来。
我又回到了那个曾经让我一度痛苦的家,可是大门早已紧锁,当我用钥匙打开门时,我再次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和那个恶魔的照片居然紧紧挨在一起,同样的是照片的前面都摆放了水果糕点。
我踉踉跄跄地跑出了房间挤进了电梯里。“听说了没有,16 楼那家好像要卖艾,傻子才会买那样的房子,就是不要钱也不能要,虽说两人不是死在家里那也是大大的不吉利啊,你说对吧?”说话的这个人正是住在20 楼的胖女人。“哎,别提了,我现在下班都还要我老公来接我,住在这里跟他们成了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你都不知道我这一年多是怎么熬过来的。”18 楼的女人说起话来更是尖酸刻薄。“幸亏他们没有孩子,听说也怪那个男人,烂酒鬼一个,喝完就把老婆往死里打,还不让拉架”
十
我像孤魂野鬼一样游荡在漆黑的街上,没有方向没有思想。我用手机百度了自己的名字,某重点中学九年级四班班主任王某某于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晚二十三时连同她的爱人郑某某一同从家中十六楼坠落身亡,死因不详。经证实,王某某生前已被确诊宫颈癌晚期。
我像个傻瓜一样仰天大笑,我想赶快从这个荒唐的梦里醒来。街头的人越来越多,人群熙熙攘攘。夜灯下的人影被拉得很长,我踩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影不知道该走向何方。猛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身着青花瓷长裙的女子,她的身影在我眼前一闪而过迅速淹没在人群中。我丢下行李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