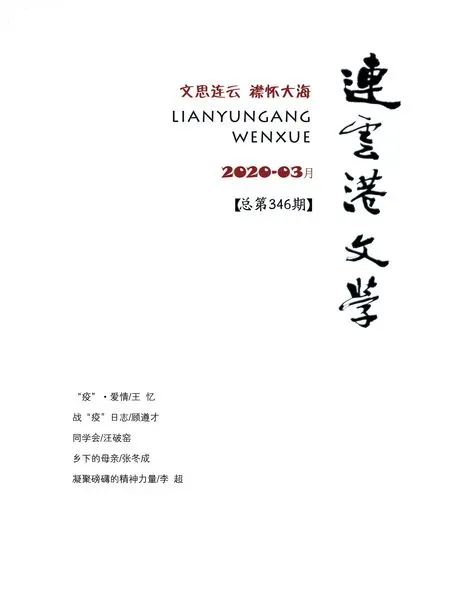鸭司令
钱友红
1
鸭司令,是小叔。
一开始,小叔还不算鸭司令。当然,如果我是一只小鸭,托我的福,小叔勉强可算鸭组长,鸭队长。我呢,自然是他手下的鸭小兵。小叔带着我每周两次往返于糖村和狐镇之间。他读高中,我读小学。
在去狐镇小学读书这件事上,我一直认为是小叔的一个阴谋,是对我的报复。有一段日子,我坚持认为小叔是个阴谋家,糖村的高才生阴谋家。
爷爷有8 个孩子,5 男3 女。父亲排行老大,小叔最小。小叔前面的哥哥、姐姐都没读到几天书,因此爷爷咬牙供小叔读到高中。
那年,小叔参加了高考。拿到高考成绩单,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小叔撕开信封,一下抽出,睁大双眼。慢慢地,小叔的脑袋像烈日下的狗尾巴草耷拉了下来。爷爷一边摇蒲扇赶蚊子,一边端起酒杯,抿一口酒,嘴里发出“咝”的声响。爷爷抿的好像不是酒,而是抿到了树上掉下的洋辣子,被蜇了嘴唇、舌头、喉咙,还有胃。过了半晌,爷爷说,丑媳妇终要见公婆。宏儿,爷爷扁担大的字不识一个。你帮爷爷念念。我瞥了一眼小叔。我读四年级了,马上升五年级,虽不是高才生,成绩也不错,识了好多字。在爷爷面前表现的好机会到了,我读道:语文61,数学63,英语20。小叔挂红灯笼了,小叔挂红灯了!小叔,你高才生呢,还挂红灯笼?!我高声嚷着。小叔的高才生形象像村口的一堵土墙,瞬间轰然倒塌。
不料爷爷说,怎么这样说话?人是铁饭是钢,吃饭。
我瞄了瞄小叔,赶紧端起饭碗。
又过了小半晌,小叔终于说,是我没用。
爷爷说,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没用?好比牛耕田,有的牛一天耕八分田,有的牛一天耕一亩二分田,你说哪头牛有用,哪头牛没用?我看,关键是用没用全力。用了全力,就是好牛。
爷爷的话有点绕,仿佛一下子把人带到云端,让我晕头转向。我只知道,爷爷是糖村公认的种田好手,小叔是糖村公认的高才生。在种田和读书上,他俩是糖村的骄傲。但我困惑的是,种田和读书没有丝毫联系,爷爷却把它们揉到了一块儿。
暑假很快过去,新学期又开始了。小叔继续复读考大学。我呢,准备去糖村小学报名。小叔说,报什么报?你被糖村小学开除了。我虽不全信,却很担忧。不知犯了什么错,得罪了老师或者校长。小叔笑呵呵地说,明天去狐镇小学报名!狐镇小学?我竖起了耳朵,心里像跳进了几只青蛙,在里面蹦跶。小叔解释说,五年级的老师自己才读到三年级,如果他教,一定把你教到一年级去。我认为这是小叔的胡话,因为那位老师我认识,他教过小叔,小叔不是照样读高中,现在不是照样考大学?
狐镇小学离糖村10 里路,那里的老师和学生,我一个也不熟悉,据说晚上还要和小叔一起上晚自修,住学生宿舍。这简直就是被警察抓了坐大牢。于是我更加相信这是小叔的蓄意报复,因为暑假我读了他的成绩单,等于丢了他的丑,他想着法子惩罚我,折磨我。我气得眼睛发红,恨不得用拳头捶小叔几十下。
在我们家读书的事上,小叔有绝对的决定权。他的意见,虽不英明伟大,爷爷却不折不扣地执行,至于其他人,包括我的父母,皆无二话。
我像一头习惯了自由欢奔的小牛,突然被强插上牛鼻栓,绳子一拉,疼得要命,还不得不抬腿迈步。当小叔背着书包、拎着装有米和咸菜的布袋走在前,我背着书包懒懒散散地跟在后,糖村人都笑道,高才生,带保镖了。这还算好听的,有的直接说后面还有个跟屁虫。我发现,无论糖村人怎么说,小叔都眉开眼笑,是那种从心底露出的笑容,灿烂无比。
我暗暗诅咒:英语挂红灯笼的小叔,死也考不取大学。可是,小叔就是死,也要找个垫背的。那个垫背的,就是我。
2
小叔荣升鸭司令,是第二年春天。
我猜想,小叔有做鸭司令的想法,绝不是田埂上的小草,在春风吹拂下才长起,去年的寒冬腊月,或者大雁南飞的时候,就已偷偷冒出了。
我不清楚小叔如何说服爷爷的。我相信小叔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家人不会有任何难度,至多时间迟早的问题。小叔正儿八经告诉我,是一个星期天下午。爷爷家门口多了一对竹匾。竹匾里铺着稻草。稻草上粘着密密麻麻的黑白相间的粪便。竹匾旁边,低矮的细篾栅栏围成了一个椭圆形,里面挤满了小鸭子。它们嘎嘎叫唤,发觉有人走近,赶忙挪远一点,挤缩在一起。
这该有多少只小鸭子啊!如果不细心查看,小鸭子和小鹅长得挺像,都是鹅黄色、毛茸茸的,让人看了想捧着抚弄一会儿。
小叔说,来,帮小叔数鸭子。
小叔在刁难我。鸭子不停走动,哪能数得清?于是我说,250 只,要是不相信,你自己数。
小叔骂我是机灵鬼,然后不无感叹地说,今后天天要数鸭子喽,一天两遍,早一遍,晚一遍。
我皱着眉头。小叔又说,小叔做养鸭专业户了,不能陪你上学了。
我更希望小叔又在开玩笑。可小叔一本正经的,一边清点鸭子,一边继续说,小叔马上就要成万元户了。你帮小叔算算,一只鸭每天下一个蛋,300 只鸭,一天就是300 只蛋,一个蛋一毛钱,每天就是30 元,一个月就是900 元,一年就是10800 元,我再打个折,一年至少8000 元吧;一年后,鸭子可以出售,一只鸭卖8 元,又是2400 元。总共10400元。一年下来,小叔就是万元户。到时,小叔盖了新房,再帮你娶个小婶子回家。
小叔滔滔不绝,沉浸在美好梦想中。我想,小叔一定也是用这套鬼话糊弄爷爷的。小叔这通话糊弄了爷爷,也坑苦了我。他做鸭司令了,以后我在狐镇上学回家都是孤零零的。晚自修在哪里上?还住学生宿舍吗?难道我转学回糖村小学?可是那里的老师和同学,我混得滚瓜烂熟,而且狐镇小学老师上课,比糖村小学老师好玩。真回糖村小学,我舍得?我左右为难。自作主张让我去狐镇小学的,是小叔;现在半路扔下我不管的,还是小叔。小叔就是一个阴谋家!不知不觉,我的眼睛湿了。
小叔像在安慰我,别担心,帮你找人打过招呼了,读书、吃饭、睡觉,都不受影响。泪水从脸颊淌下。不由分说,我抓起一只小鸭,转身就走。小叔嘿嘿笑着,说也好,也好,这鸭算是赔你的。
小鸭子嘎嘎叫唤,声音尖细慌乱。我忽然觉得,我也是一只小鸭子,我们同病相怜。
走出不远,小叔追上,扶住我肩膀,说宏儿,小叔实在学不进。没老师教我们英语,怎么学?再读下去,小叔的英语还是不及格。小叔养鸭,做致富能手,带领糖村家家户户致富。
小叔的大话、鬼话,我一句也听不进。我一定要把这只鸭养得大大的,下的蛋也大大的,超过小叔所有的鸭子,让小叔明白,他英语挂红灯笼,养鸭也照样挂红灯笼。
3
有一段时间,小叔在糖村做他的鸭司令,我在狐镇小学读我的书。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
其实有几次,我差点抑制不住,跑去鸭棚。就差那么一丁点路的时候,我停下脚步,用手死掐脸。我骂自己,皮咋这么厚?怎么不长记性?于是我返回,扛起钉耙到处挖蚯蚓。我要把那只被我唤作小白的鸭子喂得肥肥壮壮的,让它帮我出气,让小叔养鸭挂红灯笼。
不过说真心话,小叔不在身边,我很不习惯,尤其在狐镇小学和中学,有人欺负我时,我特别想小叔。小叔就是我的保镖,有他在,谁都不敢动我一根毫毛。这样想的时候,我尤其希望小叔重新回到身边。而小叔要做鸭司令,做鸭子们的保镖,做他的万元户美梦!
孩子毕竟是孩子。过了大概三个月,一个初夏的下午,我实在熬不住了,还是走近了鸭棚。因为伙伴们告诉我,你小叔不愧是鸭司令。他养的鸭真是神了,和人一样,能听懂他发号施令。
我将信将疑。
鸭棚在涧河边。涧河三四米宽,从横山山沟流淌下来的水,一年四季几乎不断。涧河里有小鱼小虾、河蚌田螺、泥鳅黄鳝。涧河边全是水草,水草里有蚂蚱青蛙。河岸上肥沃潮湿的土壤里,到处藏有蚯蚓。那里的蚯蚓比泥鳅长,比黄鳝粗。小叔还真是选对了养鸭的场所。涧河不远处,有一块宽大平坦的地方,小叔用毛竹和白塑料布盖了两个简易的棚子,可以遮风挡雨,一个鸭子们住,一个他自己住。小叔是位恪守尽职的鸭司令,吃喝拉撒全在鸭棚。
我走近鸭棚,听到小叔在喊,上课喽,上课喽!声音浑厚,在空旷的田野传出很远,撞到了对面的山梁,又回荡过来,上课喽,上课喽!我想难道小叔发现了我,又捉弄我?只见河沿陡坡下,一个个白点,循着小叔“上课喽”的声音,一个劲儿往上爬,往前冲,像涧河里的桃花水一样奔涌而来。我恍然,这哪里是鸭,分明是一个个活泼乱跳的男女学生,听到了叮叮当当的上课铃,从走廊里、厕所间、操场上纷纷乱乱地跑出,慌慌张张去教室上课,以免晚了被老师训斥。小叔端着一只红色的塑料盆,盆里装着鸭食。小叔不断地撒着。他撒食料像是跳舞,一会儿往横里撒,一会往斜里撒,一会儿从上往下撒。鸭子们追着小叔跑,这边位置被占了,那边的位置还空着,不到5 分钟,所有的鸭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都在专心吃食。
小叔忙完才发现我,招招手说,宏儿,你看一下,看到了什么?
我不计前嫌,靠近小叔。鸭子们已经长大了不少,除了身上没有小白干净,和小白大小无几。我狐疑地看着小叔。小叔笑着,一把举起我,放在他肩膀上。你看一下,是不是看到了什么字?我坐在小叔坚硬有力的肩膀上观察着。果然鸭子们埋头吃食时,围成了两个字:二、丫,二丫?二丫是谁?我好奇地问。小叔只是笑,不答话,然后领我去了鸭棚。
鸭棚不大,一张竹床,一张小四方台。四方台上堆放着许多书籍,还有纸张、笔墨。小叔究竟不是一般的农民,不去学校了,还想着读书。小叔好似看出了什么,说这些不是语文数学英语书,是养殖书,这是养鸭的,这是养猪的,这是如何养甲鱼的……小叔一本本的拿着向我介绍。
我不由开始钦佩小叔,他即便是农民,和种田能手爷爷不一样,和我的父亲和其他叔叔也不一样。我心里有了一丝忧虑,小叔有书籍帮忙,他科学养鸭,我的小白能够打败小叔养的鸭子们吗?
4
我和小叔又回到了“蜜月期”。
一到星期天,我就往鸭棚里钻,有时甚至陪小叔在鸭棚过夜。天热了,鸭棚飘散着鸭屎臭,让人喘不过气。我忍着。我喜欢看小叔喂鸭,喜欢他喊“上课喽”后,鸭子们欢快地飞奔而来的热闹场景。小叔照例用鸭食让鸭子站成“二丫”两字。我不再问二丫是谁,这是小叔的秘密,问了也是白问,他绝不会泄露半分。小叔问我,有没有喜欢的女同学?小叔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面红耳赤。小叔说,如果有,我让鸭子们也写出她的名字。说完,小叔咧开嘴大笑。鸭子们被笑声吸引,好奇地伸长脖子四处张望,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经常随小叔去捉活食。所谓活食,主要指鸭子爱吃的新鲜水产品。小叔说,鸭子吃活食,长得身强力壮,下蛋也大。小叔带我到池塘河沿千里湖,用搭网丝网撒网等渔具捉来大大小小的鱼儿,还到沟坝里摸螺蛳。摸了螺蛳,小的直接扔给鸭子,大的用砍刀背一敲,壳破,肉露出了,鸭子张嘴一啄,活吞而下,嘎嘎叫唤,可欢畅了。空闲的时候,小叔教我功课,尤其数学应用题,经过小叔稍微点拨,我豁然开朗,如沐春风。更多的时间,我埋头做作业,小叔捧书细读。四周寂静,除了偶尔几声鸭子的叫唤。
不久的五年级期末考试,我语文87 分,数学108 分。这是狐镇所有小学的一次统考,我名列“探花”。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一下子驰名糖村。爷爷喜上眉梢,直说我们老钱家,坟山选得好,迟早出人。小叔知晓了,一脸喜色,连说不简单,一定好好犒劳我!
我以为小叔说说而已,不想他说到做到。暑假的一个早晨,小叔推醒我。我们在横山脚下的一个小站上车,向凤凰县城出发。车子摇摇晃晃。车里挤满了人,汗腥味刺鼻,比鸭棚还难闻。说了不好意思,我出娘胎第一次来凤凰县城,真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城里人多,车多,好玩的多,好吃的多,简直是天堂。我埋怨小叔没及早通知,急火火的,脚上拖着一双凉鞋。小叔说,又不是做新郎官,穿这么正规干啥?我心想也是。
小叔带我玩了少年宫的旋转木马。乐曲响起,轻悠欢快。我两腿夹紧,稳稳坐着。木马向前跨越,身体随之高低起伏。我有些头晕,生怕摔下。小叔一脸满足,大声问我,怎么样?有没有在草原飞奔的感觉?有没有做大将军的感觉?我想说没有,又怕小叔失望,便借口尿急,急着下马。等上完厕所,想再玩,说还得花一元钱,只好作罢。我懊悔不已,为什么不多坐一会儿?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回糖村后我如何口沫横飞地吹,吹得小伙伴们眼睛发红,心里发痒?
玩了木马,小叔带我来到一个院子前。这个院子,和我们糖村的院子不一样。这院子非常大,住人非常多。小叔说,这个院子叫古道巷院子,里面住的,都是凤凰县里有头有脸的人。我说,小叔,我也有头有脸,不信你瞧。我指着自己的脑袋。小叔说,你有头有脸?有条猴子尾巴还差不多!小叔带我来这个院子,是见一个人,他的女同学,叫王二丫,对,就是那个“二丫”。王二丫的父亲负责看管这个院子。
王二丫瘦长的个子,眼睛亮闪闪的,两条马尾辫乌黑乌黑。她一到跟前,四周开始散发好闻的香皂气息。我暗暗感叹,小叔的女同学,王二丫真美。我狐镇小学的女同学,没有一个比得上。王二丫一定是小叔的相好,长大了,我也要找她这样好看的相好。可是,王二丫似乎并不稀罕我。她自始至终,都没正眼看我一眼。或许,暑假的日子,我和鸭子们为伴,又黑又脏,浑身吸附着鸭屎味,让人一闻就要干呕,至于小叔,也够呛。我为我和小叔这么邋遢,这么不堪而深埋下了头。
小叔、我、王二丫一起吃了午饭,在凤凰县老老少少都知晓的太白酒楼。小叔点了小笼馒头。热腾腾的一笼馒头端上,揭开藤盖,我总算开了眼界。世上竟有如此小的馒头!我夹起一只塞进嘴里,一咬,烫得我差点吐出。这样的吃相实在难看,我担心王二丫笑话,只能强忍着。王二丫拿了一个白色碟子,倒入香醋,夹进七八根姜丝,然后小心地夹起一只小笼馒头,先在装有香醋和姜丝的碟子里浸一下,再身体前倾,张开小嘴,用牙齿咬了那么一丝丝,咬开了一个小口子,王二丫对着小口子轻轻吮吸,吮吸得那么自信,那么顺畅,那么优雅。王二丫以前光顾过,说不定还是常客,至少不像我,完全不知道小笼馒头的吃法。我在糖村听爷爷说过一句话:没吃过猪肉,还听过猪叫。二丫既听过猪叫,还吃过猪肉。唉,凤凰县城和糖村这个穷乡僻壤截然不同,人,也天差地别。我依葫芦画瓢,模仿王二丫吃小笼馒头,毕竟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弄得顾此失彼,乱七八糟。小叔在一旁看我出丑,忍不住笑,又不笑出声,好在王二丫没注意我,只是有滋有味地品尝小笼馒头。结果一笼小笼馒头,她吃了5 只,我吃了4 只,小叔仅吃1 只。小叔说他不饿,早晨吃了蛋炒饭,油腻得很,把饿的滋味也腻溜了。
和王二丫在一起,小叔准是只顾盯着看,看王二丫吃得这么香,小叔就不饿了。回家的路上,我悄声问小叔,那个王二丫,是不是你相好?小叔拍了一下我的脑袋瓜。我继续说,还说犒劳我,你犒劳自己,来看相好的。
小叔忍不住笑了,说你这小子,懂得挺多。快回家,鸭子们要“上课喽”!
5
我把小白带回了鸭棚。
虽和小叔重归于好,但那口气还一直憋着。我要让小白下的蛋更大,比学校的篮球还大,超过小叔养的所有鸭子。我发过誓,要让小叔养鸭也挂红灯笼。为了在鸭群中一眼就看到小白,我在它背上染了红色。喂活食时,我故意往小白跟前扔。
天越来越热,涧河里的水流越来越细,活食也越来越少,一些小池小塘,先后干涸。为了找活食,小叔在淤泥里想办法。小叔指着乌黑黏稠的淤泥,说里面藏着好东西呢。说着,小叔跳入淤泥,双手不停扒拉,果然一条条泥鳅从泥里露出,紧张地藏头藏尾。我也跳进淤泥,和小叔一起挖泥鳅,挖了一条又一条。不到半天,我们逮到了一桶泥鳅,只是我和小叔都成泥人了。小叔看着泥鳅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不久,小叔的情绪一落千丈。这是一封信引起的。早晨,爷爷让我带一封邮局送来的信给小叔。小叔接过,小心地拆开,读着读着,脸越来越黑,好像一阵狂风暴雨就要来临。我从没看到小叔的脸这么瘆人,吓得不敢作声。那天,小叔似乎忘记了喂食。鸭子们饿得嘎嘎直叫,小叔全然不顾。小叔躺在竹床上,用床单蒙着头。快中午了,我端起食盆,学着小叔喊“上课喽,上课喽!”,鸭子们果然从草丛中,陡坡下冲了过来。我一阵手忙脚乱,学着小叔用鸭食撒成“二丫”两字。鸭子像约好了似的,乖巧地站成了“二丫”。我扔下食盆,高声喊道,小叔,你快来看看,我也会让鸭子们写字了,写“二丫”两个字。小叔不但没起床,还朝我吼道,有多远滚多远。我委屈极了。小叔从来不曾这么粗暴地待我。
连续几日,小叔虎着脸,好像我或者鸭子们都欠着他一大笔账。我一开始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想出问题在那封信上,谁来的信?写的什么?我隐隐觉得,与二丫有关。可是,我不敢问。即使问了,小叔肯定不会理睬我,弄急了又得让我滚。整个上午,小叔坐在小四方台前,用笔在纸上写着什么。我猜他一定是写给二丫的。小叔像遇到了什么难题,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停了大半个时辰,撕了,再写,写了一会儿,又撕了。小叔写了一个星期,碎纸屑飘了一地,一张也没写成。
雪上加霜的是,养鸭出了大问题。首先缺水,天越加干旱,涧河彻底干涸了,连鸭子喝的水也不剩一滴,不要说那些靠水养命的小鱼小虾和泥鳅螺蛳。小叔无精打采,从糖村大池塘挑水给鸭子们喝。糖村人说,再不下雨,淘米洗菜人喝的水都没了。鸭子不能缺水,缺水的鸭子,就少了活力。它们的羽毛不再光泽润滑,叫唤不再洪亮娇艳。更严重的是,开始有鸭子耷头耷脑的,连屁股后面一枚蛋都没来得及下,就两脚一蹬,归西了。小叔一声不吭,把死鸭埋进土里。我发现挖起的干土上有了湿痕。那不是汗滴,就是眼泪。
鸭子们得病了?我替小叔着急,胡乱地翻小四方台上书,想在书中找到良策。书里的许多字和术语,我不认识。鸭,还是一只一只地死去。爷爷来了,告诫小叔说,没过不去的坎,把鸭子养好,是天大的事。爷爷的告诫根本不管用,小叔还是那么死气沉沉。鸭子像被黄鼠狼眷顾上了,还是每天少了那么一两只。
我急得直跺脚。小叔,你快快振作起来!小叔振作了起来,就有了斗志,就肯定有办法,鸭子们就会像以前一样生龙活虎的。这样想着,我做出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举动。
6
去凤凰县城前,我温习了上次小叔带我去的历程,包括出行时间、具体线路、须要注意点。我温习了一遍又一遍,像对待刚结束不就的五年级期末考试一样用心。我在鸭棚挑选了20 个大鸭蛋,准备送给王二丫,就说小叔让送的。我又担心万一碰破,弄了一身蛋清蛋黄不说,还把事办砸了。我左思右想,最后咬咬牙,把小白塞进网袋。小白已是成年鸭,挺有分量。我估计那些大鸭蛋,都是小白的功劳。我不再关心小叔养鸭是否挂红灯笼,我把小白也豁出去了。因为我清楚,如果小叔再萎靡不振,鸭子们就完蛋了,小叔也完蛋了。
公交车上,许多人诧异地望着我。或许他们猜测,这个小男孩是去县城走亲戚,还是卖鸭。他们的猜测和我毫无干系。我盼望客车快一点,再快一点。
摸索到古道巷院子的门口,已近中午。门卫处空荡荡的,一个人影没有。小叔说过,这里住宿的,都是凤凰县城的头头脑脑,说不定一不小心,就撞上了县长大人,或者公安局长。我有点发慌,缩在门旁,望着出出进进的人们,不知哪位是局长,哪位又是县长。其间偶尔有人停下,看着网兜里的小白,问卖不卖,什么价?我摇头,把网袋拽得紧紧的。
终于来了一个老头,穿着中山装,洗得有点发白。我试探着走上前,说爷爷,二丫在吗?他没搭理我。我又靠近一点,鼓足勇气大声说,爷爷,我是糖村的。小叔让我给二丫送一只鸭子。小叔病了。我的声音渐低。我真担心小叔。我想,二丫知道后,一定比我更担心小叔。老头转身,厉声说,哪有二丫,哪有二丫?这里没有二丫,从来就没有二丫!快滚!老头怒目圆瞪。我赶紧退了两步。老头凶横的样子,似乎要把小白夺了甩出三里路,甚至会揍我两拳头。我退到不远的梧桐树下,心脏怦怦直跳。小白又饿又渴,气喘吁吁。我没有放弃,紧盯门卫处。我准备着,一旦二丫出现,我就冲过去,把小白给她,告诉她我藏在心底已经一天一夜的话语,尤其是最最关键的一句话:小叔病了,你快去看看。可是,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太阳已经偏西,二丫根本没出现。我的肚子咕咕直叫。小白似乎连叫唤的力气也没了。
二丫真不在?难道老头不是二丫的父亲?我迷茫了。再不回家,将搭不上回狐镇的车。我趁老头不注意,把小白搁在门口,撒腿跑远了。我坚信,二丫会看到小白的,看到小白,就知道小叔对她的好,甚至想到小叔肯定有事,说不定就会来糖村了。二丫一来,小叔哪有萎靡不振的理由?
晚霞在燃烧。
到了狐镇,我疾步回家,累了,便歇一会儿,然后再小跑一段。这条路,我和小叔走过上百趟。走着走着,我唱起了《上海滩》的主题曲: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这首歌是小叔教我的。许多周六的傍晚,我俩唱着它回糖村;许多周日的下午,我俩又唱着它去狐镇。
唱着唱着,我感觉浑身发软,索性在山岗前停下,一屁股坐地上。朦朦胧胧中,我好像看到前方灰尘四溅,土黄色一片腾空而起。远远的,我看到小叔挥举竹竿,赶着鸭群浩浩荡荡而来,而我的小白作为鸭群的队长,一摇一摆,在前带路……
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啪嗒啪嗒往下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