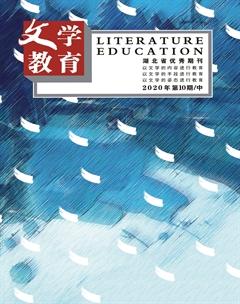尼采《悲剧的诞生》中的“日神”隐喻
内容摘要:在《悲剧的诞生》中,酒神与日神为艺术的二元动力,并在悲剧中达成和解。日神虽不比酒神之强意志力,但在尼采的哲学世界中却为希腊神话之根基,选此根基,采用语言隐喻分析,根据日神一词诞生之三个词根赋予其新的含义和特征,在尼采哲学世界的开端,“上帝死了”的惊人宣言已见端倪,日神后虽为尼采所弃,但仍可窥见尼采哲学之貌。
关键词:日神 隐喻 悲剧的诞生 重估
1872年,尼采出版了他的首部哲学作品《悲剧的诞生》,全称为《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通读可知,这是一首隐含的酒神颂歌,尼采所认为的真正的音乐是酒神音乐,完整的、复杂的,具有丰富的和声,将人席卷其中,或许也因此,人們对于《悲剧的诞生》的研究多偏向于酒神精神。但就篇幅来说,尼采对于日神阿波罗的论述其实并不少,日神与酒神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首先要理解日神,才能真正理解酒神。
一.选择“日神”:真理与隐喻
在具体探讨“日神”这一隐喻的内涵之前,我们首先应当了解尼采的隐喻观,在此基础上方能了解为何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选择了“日神”这一隐喻。尼采的隐喻观与其真理观密不可分。
(一)现实苦痛和此在快乐
一般来说,西方哲学认为真理是与精神紧密相连的,人对于真理仅有发现权和使用权,而无创造权,因为真理是由上帝创造的,“诗灵神授”即是。尼采打破了这样的哲学传统,他认为真理是人对恐惧的回应和应对,人们选择上帝作为真理的创造者,是因为“最令人恐惧的东西、最强烈痛苦的原因(统治欲、肉欲等等),最受人的敌视、被人从‘真正的世界剔除出去了。于是,他们一步步勾销了情绪冲动——把上帝设立为恶之对立面,这意味着,把实在设立为欲望和激情的反面(也就是虚无)”[1]。人世间的苦难诸多,所谓真理不过是对苦难的逃避,借着上帝的名义,虚构出所谓理念的世界,这种由逃避苦难和恐惧的本能激发出的虚构的哲学,也是被奉为具有高价值的真理。真理不过是人的幻想,对真理的崇拜只不过是这种幻想的结果。
尼采看到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在人们深信的真理世界中,一个依凭于神的真理世界中,他找到了日神,一位光明、伟岸、崇高、积极的神,尼采认为日神是整个奥林匹斯山光辉的根基。即便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所谓的真理,但是所有人都学会了用神作为逃避苦难、克服恐惧的“幌子”,只不过为了人生此在的快乐,这一给予人力量的神的代表是“日神”。在这种人生此在的快乐中,神的种种罪恶得以开脱,人仿佛独自成为个体,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依旧能驾驶着自己的小船,为了驶向海市蜃楼般的日神光辉中。
而尼采不想如此,他反对西方哲学传统之逃避苦难的态度,人类所要面对的无尽苦难与随之而来的恐惧应当常伴哲学左右。打碎这样的真理观,即是要打碎人们的习惯与日常,打破哲学传统,从语言开始,让哲学家从语言的网中挣脱,割裂重组已成定式的哲学概念。
(二)语言隐喻本性
真理是人应对苦难幻想的结果,并以此作为哲学的目标和终点,“人们用‘目的和‘手段强占过程(人们发明一种可以把握的过程),而用‘概念强占那造成过程的‘事物”[2]在追寻和把握真理的过程中通过“概念”固定幻想。真理何以打破,首先要将所谓的概念击碎,“尼采认为我们所以为的‘概念形成的方法是同一化,但这种同一化只是因为遗忘而产生的表面现象,它的本质是隐喻。”[3]而语言成为概念后,其隐喻就死去了,每一个概念都掩埋着死去的隐喻的幽灵。
尼采是语言隐喻本性的支持者。关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本性,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思想家们阐述的语言起源理论;一种是结构语言学阐述的语言深层理论。关于源初语言的隐喻性的最有影响力的阐释来自卢梭、赫尔德和尼采。[4]尼采对于语言的发生有他的大胆设想,他认为每一个词与都是经过双重隐喻而形成的,从神经刺激投射为心中的意象,继而转化到声音意象。比如谈论雪花,首先是在心中呈现雪花的意象,想到冬天、寒冷、白色等等,然后才将这个意象转化为/xue214hua55/这样的声音。发声方式是科学的、理性的,而心中的意象是感性的、非逻辑的,因此,语言首先是在感性活动中产生,然后才用理性确定下来,而一旦确定下来就成为一种概念符号,成为人类“知觉隐喻的图式化和固定的习惯”[5],人就不能看到最初的世界,也就是看不到意识之流的世界,而“意识”才是世界的根基。
正因为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真理不过是人们借助神显现的幻想,尼采想要由存在的人自己创造真的真理,这样的真理观点导致尼采在自己的哲学实践中十分重视哲学语言,哲学概念看似已成定时,但却在形成概念的同一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本的隐喻性,导致人永远与真的真理隔着一层纱。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的哲学写作中,将彼时已经成为德国人、或者说西方人头脑中的概念符号——日神和酒神隐喻的幽灵挖掘出来。
这里还可以看出尼采的隐喻哲学转向。一般来说,隐喻是譬喻(譬喻包括明喻、隐喻、略喻、借喻和假喻)的一种,属于修辞学的范围,柏拉图后的语言学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对譬喻、对隐喻的探讨。譬喻作为语言思维中普遍存在且极其重要的部分,可以说一种思维的方式,不同民族之不同的思维方式从其譬喻性的语言中也能窥见一二。譬喻的一大特点即是概念性,但就“日神”这一隐喻来看,尼采抛弃了它的概念性,尽管从语言学的角度隐喻如上位概念譬喻一般可以构建我们的思维方式,但是对于尼采来说这还只是表层的东西,正如在悲剧中“日神”之于“酒神”一样是表象的显现,尼采转向了隐喻的背后,转向了概念的产生,尽管看似仍然是语言学的角度,从“日神”的词根进行探讨和挖掘,但是他又将“日神”置于希腊神话之中,凿开了奥林匹斯山,看向光辉的神之雕像背后的基石,这是隐喻从语言学修辞学领域转向了哲学的领域,不是西方传统哲学,而是诗性的哲学,打碎固有的哲学概念,基于哲学史和文化史创造性地生成新的哲学语言,富有深刻且丰富的隐喻性,尼采是尝试者,后有海德格尔等接续者、发展者。
二.认知“日神”:从光明到幻象
既然尼采选择了“日神”,并将它作为艺术动力之一,也是悲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中他也对“日神”隐喻的内容做了颇为详尽的阐述,让日神这一概念从单一的宙斯之子这一身份和光辉英俊的外表中走出,探索语言这座冰山的水下部分。
(一)“日神”之光
阿波罗(scheinen)意为“光明的人”,日神阿波罗的显现正是光,带来的效果是光明,“光”相比“日神”又向上追溯了一层。“光”是西方世界一个重要的词,甚至可以说开启了西方世界和人类文明,上帝创世纪之初便言“光!”。“光”在西方是一个重要的隐喻,自古希腊哲学开端处便已显现。泰勒斯言“水是万物的本源”,水也是一种“光”隐喻,因为水作为一种透明性的东西,和光一样具有显现的作用。尽管柏拉图十分蔑视华丽的辞藻,将隐喻归入修辞学的范畴而排除在哲学之外,但他本人却是一位隐喻大师,留下了著名的“洞穴隐喻”,亦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命题。“洞穴隐喻”即当洞穴中的人被光照射出的阴影世界所欺骗,只有跳出洞穴才能看到“光”的世界,也就是理念的世界。
而到了1886年的《一种自我批评的尝试》,即对自己早期《悲剧的诞生》的自我反思和批评的小文章,尼采在语言上不仅采用第三人称观照多年前的自己,更是将“日神”抛弃,却又说到要“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用生命的透镜看艺术”[6],“透镜”是“光学”科学中的术语,光学暗含着一种“观点”的隐喻,尼采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日神”隐喻的出发,即“光”。在生命的后程,尼采认为要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主要也是悲剧艺术,他讽刺苏格拉底的眼睛是“巨人之眼”,且只有一只,这一只眼睛“从未燃起过艺术激情之优美癫狂”[7]。尽管尼采还在《悲剧的诞生》中为悲剧的重生与复兴创造条件,但科学主义的滚滚车轮何其迅速有力,时代的知音又是何其少,尼采甚至在《一种自我批评的尝试》中表达了对瓦格纳的失望,这是一位在《悲剧的诞生》中备受尼采尊敬和推崇的艺术家。
在西方“光”隐喻的传统之下尼采找到了“日神”,将“光”扩展到了“光明”,又在最后抛弃“日神”之时,在科学视域下回到了“光”。
(二)“日神”内涵
除了指光明之外,日神的词根schein还有显现或现象的意思,即“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第二层意思;第三层意思为“外表”“幻象”“欺骗”。[8]理解词根schein的含义对于《悲剧的诞生》中的日神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其内蕴,也就是隐喻性正和这三个本源义相关,日神精神基本上正是在这三个方面。
首先是“光明”,阿波罗作为宙斯的子嗣,英俊、光明、伟岸,是奥林匹斯诸神中的绝对正面,在人类生活中,对太阳的崇拜自原始社会其延续至今。光明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正是因为光明的指引,我们才有创造美的冲动,想要将美显现出来。这种光明也正是日神的心理生成,即对快乐的追求。另外,日神之“光明”不仅是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保護,使他们的诸行都有光辉照耀于外,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和照射,当人们意识到日神的幻象之意后,意图更进一步接近时,“恰恰那种透亮的整体可见性又反过来迷住了眼睛。”[9]日神作为艺术的动力之一,其产生的艺术形式总与现实的醒着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高于现实,照耀现实。
其次是“显现”,日神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显现,不仅在日神艺术内,日神冲动对应的日神艺术就是造型艺术,有具体的形象的显现,如雕塑、建筑等,多克立建组规整宏伟,正如日神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在酒神和日神结合产生的悲剧艺术中,日神亦起到了重要的显现作用。尽管悲剧诞生于音乐之中,诞生于酒神精神之中,但作为一种有安排、有形式的戏剧形式,不可能像狄奥尼索斯节日狂欢般一味地“醉”,得益于日神的力量,复杂的音乐也可以显现而被人理解,甚至能形成形象。可见,日神的显现能让神秘不可琢磨的东西变得可感可知,悲剧中日神与酒神在牵制中达到完美的平衡,日神的光辉显现使得悲剧可以“被看到”,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对人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而这种治疗,归根到底因为日神是“幻象”,是“假象”。在悲剧艺术中,观众要在悲剧之外欣赏。现代戏剧,以欧里庇德斯的戏剧开始,悲剧走向了衰落,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观众过渡地参与到戏剧中去。日神的参与让欣赏悲剧的观众保持独立的个体,保持叔本华所言的“个体性原理”。不仅是观众,演员也要在戏剧之外,酒神狂欢让人失去个体而与周围的人一同沉醉沉沦,悲剧的演员应当在舞台上看到自己扮演的角色,这些都需要日神的力量;而悲剧带来的治疗也不过是一种“幻象”,帮助我们免除酒神的过渡冲击,因为痛苦永无宁日,即使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也需要日神的幻象庇佑,才能尽情追求幻象的快乐。也正是“幻象”,尼采一开始就将日神的样态对应“梦”。然而,即便是梦的幻象,也比清醒的生活高出许多,艺术是高于生活的,艺术是至高的。另外,尽管在“显现”中我们看到了酒神对日神的需求,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日神究竟是幻象的,而酒神才是现象背后的存在,即日神离开酒神也无法生存。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尚未将日神舍弃,或许是在他哲学和人生的早期对于人和文化的“可以生存”还保佑希望,因为日神就是整个希腊文化为了对应内在酒神观念而发展起来的,不是任何人的有意为之,也没有任何人能有意为之,对于人类痛苦的本质,必须要有日神追求美和快乐的动力,人才能活下去,生活才能变成一种渴望,文化才能继续下去。也因此,即使做梦的人知道这是梦,也要继续下去。
至此,“日神”在“悲剧的诞生”中已全部走完,既包含了《悲剧的诞生》,也包含了后期的回应,即《一种自我批评的尝试》。“日神”这一隐喻共有三层内涵:光明、显现和幻象,与其词根密切相关,亦是从“光”开始,由“光”结束,我们跟随尼采,再一次认知了“日神”。
三.还原“日神”:重返“日神”现场
重新回到《悲剧的诞生》的写作,尼采在其中对于“日神”隐喻内涵挖掘与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诠释学的方法,尼采不断将“日神”放回到古希腊神话中,将作为艺术动力之一的“日神”放回到诞生悲剧的古希腊时期,回到“日神”发生的现场,并用其他隐喻帮助“日神”隐喻的显现。
(一)返回奥林匹斯山
“日神”是神话中的人物,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的第三节带我们回到奥林匹斯山,以解构“阿波罗文化大厦”的方式,挖掘其立足的根基,也就是将“日神”放回到奥林匹斯山这一诞生源地进行考察。
在希腊神话的现场考察日神,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第一节便指出日神来自古希腊神话。但这种还原历史现场之诠释不能仅立足于历史的发生,还要在历史的发展中做出还原,尼采不仅在古希腊神话中找寻日神,还在人类的活动中诉说日神,看到与古典范例之间的历史距离。在人类活动中,“少女们手持月桂枝,庄严地走向阿波罗神庙,同时唱着一首进行曲,她们依然是她们自己,并且保持着自己的市民姓名。”[10]正如在神的领域日神让诸神成其自己,恣意、浪漫,神庙里的日神也让人成其各自,个性、个体,这便是阿波罗走出奥林匹斯山后之于人类的意义。如果将日神当作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概念来看,这一现场透露出的不过是神的光辉,日神不过是神的概念中的一个。
重组新的隐喻,其发生的现场不止一个,以历史的动态发展的眼光还原现场,继而“收取其从概念的原始内涵中所流传给它的东西”[11],而不是重复概念本身。
(二)梦与纱
“日神”作为一个隐喻,同样有其他的譬喻来丰富它,尼采选择了“纱”和“梦”这两个意象。纱虽有遮蔽但不至完全,日神的光辉虽耀眼,但盯着那光辉我们仍能看到小黑点。然而日神虽然如纱一般将本质遮盖住,它仍是高于现实生活的,尼采用“梦”来证实日神的地位,“虽然给人种种荒谬的假象——对于我们的本质(我们就是它的现象)的神秘根基而言,我们恰恰反而要重视梦。”[12]尼采肯定梦,肯定用艺术的眼光来看世界,即便不是酒神般的强意志力,但也好过醒着的普通现实世界。
尼采的“日神梦”不是个人的杜撰和想象,而是对希腊人的梦的还原,在书的第二节他对希腊人的梦做了有把握的猜测,“他们的眼睛有着难以置信的确定而可靠的造型能力,外加他们对于色彩有着敏锐而坦诚的爱好”[13],在这种对希腊人的梦的还原中,我们再次确定日神的显现这一特征和内涵。
纱这一意象在古代哲学现场亦可寻,只不過跳开了古希腊来到了古印度,并且以其他人的哲学著作为依据和印证。尼采借用叔本华的“摩耶面纱”,认为其同样适用日神的内涵,除第一节直接引用“摩耶面纱”(P23)这个名词外,还有“撕碎面纱”(第二十四节,P172)和“用一种美的面纱演掩饰它自己的本质”(第二十五节,P177)等等,“摩耶”在古印度哲学中意为“幻”,又与日神之幻象相对应。
即尼采在创设日神这一隐喻时,选取了特征相似或相符的其他意象来帮助完善日神隐喻的内涵,使其更加形象化。而这些意象的选择同样来自最原初的哲学现场,饱含历史的厚度。
一方面,尼采如现象学家一般为新的哲学语言的创设还原其历史现场,并在历史的动态眼光下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为了隐喻的饱满与形象,尼采亦借用其他的意象加以说明,而这些意象同样被放置回发生的现场,就内涵而言,与日神的隐喻内涵相吻合。尼采重组与创造新的哲学语言并非空中楼阁虚无缥缈,而是有所根基,小到哲学思想中一个不起眼的“日神”隐喻也是如此。这亦是尼采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其异于传统的哲学观念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历史的还原与流动中进行有根据的创造。
四.结语
尼采选择“日神”这一隐喻,因为他看到了“日神”的快乐的幻象,这层纱始终笼罩,尼采之哲学正是在撕开这层纱,撕裂西方传统哲学之真理的幻象,重新评估真理。《悲剧的诞生》作为尼采哲学世界的开始,我们在仿佛是酒神之“映衬”的日神中就已窥见尼采高呼“上帝死了”的端倪。回到日神诞生的奥林匹斯山,日神之光明的显现,快乐的幻象终究为假,人不应当依凭于假的上帝、假的胜利而存在,因而在《一种自我尝试的批判》中尼采自我舍弃了“日神”,毕竟即使在悲剧中日神发挥其力量使悲剧显现,使悲剧产生治疗作用,但是在酒神的强意志力下日神最终也会以酒神的智慧说话,即假象终会被本质逼迫而改变。
只是,作为脆弱的人类,在日神的幻象中得以窥见“假”真理已实属不易,如尼采般“重估一切价值”而走向“真”虚无恐怕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参考文献
[1][德]尼采.周国平译.偶像的黄昏[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2]王琼.知识作为健康身体的隐喻[D].陕西师范大学,2004.
[3]牛宏宝.哲学与隐喻——对哲学话语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23-33.
[4][德]尼采.孙周兴译.悲剧的诞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美]雷可夫詹森.周世箴译注.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台北:聊经出版公司,2006.
[6][英]道格拉斯·伯纳姆马丁·杰心豪森.丁岩译.导读尼采《悲剧的诞生》[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7][德]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注 释
[1][德]尼采.周国平译.偶像的黄昏[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125.
[2][德]尼采.周国平译.偶像的黄昏[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120.
[3]王琼.知识作为健康身体的隐喻[D].陕西师范大学,2004.
[4]牛宏宝.哲学与隐喻——对哲学话语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23-33.
[5]牛宏宝.哲学与隐喻——对哲学话语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23-33.
[6][德]尼采.孙周兴译.悲剧的诞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6.
[7][德]尼采.孙周兴译.悲剧的诞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1.
[8][英]道格拉斯·伯纳姆 马丁·杰心豪森.丁岩译.导读尼采《悲剧的诞生》[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50-51.
[9][德]尼采.孙周兴译.悲剧的诞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2.
[10][德]尼采.孙周兴译.悲剧的诞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5.
[11][德]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1.
[12][德]尼采.孙周兴译.悲剧的诞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6.
[13][德]尼采.孙周兴译.悲剧的诞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7.
(作者介绍:王雯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