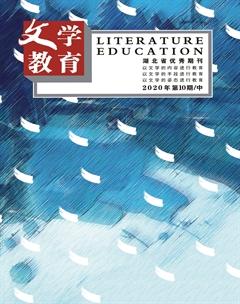黑人族内女性刻板形象表征与颠覆
内容摘要:存在于黑人种族内部刻板形象给黑人女性造成身心伤害,加剧了她们社会地位的恶化。奇尔德雷斯的《荒野葡萄酒》戏剧化地表现了黑人族内强加给黑人女性的刻板形象,并通过女主人公对刻板形象的颠覆抨击了黑人中产阶级的虚伪和偏见。
关键词:刻板形象 表征 颠覆
从美国奴隶制一开始,白人主流社会就给非裔强加上多种负面刻板形象,变成了扭曲和篡改黑人文化及其表征的政治工具。然而,刻板形象还存在于黑人种族内部。上世纪60、70年代的黑人权力运动中,一些黑人男性作家结合白人社会强加给黑人的刻板形象,把黑人女性描写成女家长、不道德、专横、无助的形象,重新定义和缩小了黑人女性的角色。[1]一些黑人女性也内化了这些刻板形象。许多黑人女性剧作家对此做出了回应,奇尔德雷斯的《荒野葡萄酒》是最具代表性的戏剧之一。该剧审视了黑人族内彼此看待对方、反抗白人时出现的贬损女性的刻板形象及其给她们造成的身心伤害,呈现了女主人公对刻板形象的颠覆。
一.黑人族内女性刻板形象表征
该剧写于1969年,正值黑人权力运动高潮阶段,讲述的是1964年的一次骚乱期间发生在一位黑人艺术家比尔的公寓里的故事。比尔计划完成以“荒野葡萄酒”为主题的三幅画,涉及黑人女性身份。他目前已经完成第一幅“黑人少女时代”和第二幅“非洲母亲”,她们“就是那个女性……就是天堂……完美的黑人女性。”[2]
画像中的少女是天堂的体现,代表男性对女性的幻想,暗示比尔理想化意识中的黑人女性形象。这种理想化的黑人女性形象实际上是黑人族内强加给黑人女性的刻板形象,具有明显的欺骗性。比尔并未捕捉到真正的黑人女性特质。而他尚未完成的第三幅则是明显带有黑人族内性别和阶级偏见的女性刻板形象,表现的是迷失的黑人女性,“那种草根小妞……迷失的女人……无知、没有女人味、粗鲁、野蛮、庸俗……一个可怜、愚蠢的小妞……不新潮。”[2]这充分证明了黑人男性的权力和对黑人女性的歧视和贬损。虽然比尔提到社会歧视对黑人女性的压迫,但并不同情她们的困境;这个女性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利用后丢弃。没有受过教育、穿着不得体、外表寒酸的汤米看起来符合比尔及其朋友们的“迷失的女性”标准。但汤米热情、友好、讨人喜欢,有道德,并不是他们臆想的那种刻板女性形象。无疑,剧作家把汤米的良好品性与男性的偏见和自我为中心并置和对比。
对黑人女性的歧视和贬损还体现在比尔对汤米知识的嘲笑上。因为受教育少,汤米就向比尔请教,但比尔却拷问她有关道格拉斯、塔布曼、约翰·布朗这些黑人历史人物以显摆自己知识渊博,并用歧视性言语羞辱汤米和所有黑人女性。“宝贝,为啥要折磨自己?麻烦我们的女性……她们都想有了不起的大脑。把事情留给男人去做吧”的本质是表明女性智力不如男性,暗指她们想以“女家长”姿态削弱男性兴趣,包括求知欲,支配他们。他认为女性只应关心家务,让丈夫高兴,养育孩子。当汤米想穿着不得体的衣服摆造型时,比尔非常生气:“我们的女人该死的没有一点女人味。不知道让步……太他妈的自以为是了。”[2]这证明了男性权力与在培育这种权力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构建女性温顺之间的关系。[3]显然,比尔构建了汤米的身份形象,他要创造的是温驯的女性身体。
这些言论表明比尔已经接受了黑人女性刻板形象:飞扬跋扈、不温柔、渴望阉割黑人男性。他宣称“黑人是美丽的”仅仅指那些符合他的行为准则的黑人女性,仅仅是因为黑人权力运动的政治气候,只想在作品中利用这个概念,他对待汤米以及与她的交流也没有传递该概念。他宣称汤米有一种自卑感,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贬低她的自尊的行为应该为此负责。
歧视和贬损还体现在以辛西娅为代表、内化了社会偏见的黑人女性身上。汤米因为相信辛西娅受过良好的教育就向辛西娅征求建议,后者则给了她一长串有关传统女性的温驯、无私、性感方面的训导,实际上就是黑人女性刻板形象。她指责汤米太过关注自己,丧失了女性的温柔本性,冷酷无情,认为女性必须让黑人男人重新找回他的男子气概,“让他说话。你学会倾听。别太显眼。”[2]显然,她相信黑人女性削弱了他们的男子气概,有必要让他们恢复在家庭和社群中的优越地位。此外,辛西娅还把“女家长”,一个有权力、统治家庭的“当家女人”概念强加给汤米,结果却与汤米的社会现实相矛盾,因为汤米一无所有。辛西娅的话似乎与她生活中的男性的话相呼应,表明她已经接受了黑人女性支配家庭的神话,内化了白人社会和黑人男性社会强加给黑人女性的刻板形象。
二.黑人女性对刻板形象的自我颠覆
在黑人为种族平等和公正而战的同时,他们也在维护黑人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定义和强化黑人女性的刻板形象。该剧戏剧化地表现了以比尔为代表的黑人男性试图通过艺术定义黑人女性的企图,这也是对60年代政治气候的一种批评,对黑人中产阶级虚伪和偏见的抨击,这种抨击体现在剧中汤米对黑人女性刻板形象的自我颠覆上。
首先,汤米对理想化的“非洲母亲”或“明日玛丽”给予了否定。比尔告诉汤米,因为她拒绝达到休斯曾经描述的美丽女性标准,穿着不得体,她就是汤米而不是“明日玛丽”。但汤米以实际行动颠覆了男性认知偏见。明日玛丽和汤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的生活经历。汤米将非裔美国人主体性历史体现在其亲身经历之中。穿着不得体是因为骚乱中“黑鬼”同胞烧了她的一切。受教育少和贫穷并不是因为她懒惰或愚蠢,辍学是为了养活自己,减轻母亲的负担。当比尔炫耀他对黑人历史的渊博知识时,没有受过教育的汤米从她个人历史角度解释了她對约翰·布朗的认知。她告诉比尔,她家人都是一家黑人慈善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买下了布朗的农舍以便建造一个露天剧院来纪念他。她熟悉黑人历史事件和黑人历史人物。这表明汤米的知识源于她的活生生的生活经验,而比尔的黑人历史知识却是源于书本。汤米的表现并不像比尔想象的那样支离破碎或“不新潮”;相反,通过展示她的知识和对非洲女性历史的把握,她表明比尔是支离破碎的,知识贫乏。他在抽象和理想化的非洲女性身上中寻找文化整体性的缺陷被揭示出来,从而彻底颠覆了黑人男性的认知缺陷及其对黑人女性的偏见。
阶级差异也影响着性别政治。辛西娅试图驯服和教育汤米接受中产阶级黑人的意识形态,生活在蒙骗之中。但是汤米拒绝从男性的角度来定义自己,拒绝生活在男性眼中。她让比尔意识到,与“不顶嘴的非常漂亮女士”相反,她是真正的、身体上被赋权的“荒野葡萄酒……明日玛丽,骂人,打架,为自己着想。”[2]她的观点不仅代表了真正的黑人女性身份,也是对理想化和浪漫化的非洲归属感的一种批判。
此外,汤米的知识和观点也是对这些受过教育但有偏见的黑人美学中产阶层的一种批判和颠覆。汤米对辛西娅的训导的反应是“噢,嗯,哼”。这与早些时候她描述白人语言中模棱两可的话语一样,暗示她崇尚自己的话语风格,不喜欢白人语言和辛西娅模仿白人虚假的言语行为。比尔对“黑鬼”一词的无知是对他吹嘘黑人历史和种族知识的明显讽刺。作为一种挑战行为,汤米后来再次使用“黑鬼”这个贬义词语来描述比尔和其他人,暗示她不再想采用他们虚假的言语和行为。比尔认为“黑鬼”指的是“低级的、被降低身份的人”。然而,在湯米要求他查看白人编撰的字典后他发现其定义是“任何黑皮肤民族中的一个成员……粗俗、无礼、怀有敌意和蔑视”,一个明显侮辱黑人民众的轻蔑语。这表明比尔等人的教育是失败的。汤米指出她使用“黑鬼”是出于痛苦,而不是敌意,而白人使用该词时并不区分受教育和未受教育的黑人。因此,如果比尔这些人认为他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以及通过把他们与黑人大众区分开来,他们就更容易被白人社会接受,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汤米认为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懂得多,她才表现得低人一等,逆来顺受。但是他们拥有的只是族内自我憎恨和偏见,只关心自己而没有真正关注黑人的困境,崇拜的只是死了的黑人英雄而不是活着的黑人民众。
汤米也从刚刚经历的痛苦中汲取了一些重要的教训。虽然像她这样的女性因为黑皮肤不符合欧洲审美标准,然而她懂得了自爱,学会了接受自己和看到自己价值的重要性,而不是他人的接受。她承认自己不是比尔绘画中的“荒野葡萄酒”形象,但她对此有自己的定义,把它定义为一种不强调外在,而是强调善良、诚实、同情、宽容等内在品质。比尔问题在于他陷入外部因素、表面特征和刻板形象,这使他丧失了洞察力和判断力,难以呈现一个真实的黑人女性气质的画像。
三.结语
虽然《荒野葡萄酒》以积极的调子结束,汤米不仅主张了自己的自主权,而且对剧中其他人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该剧并没有自认为解决了社会中黑人女性受压迫问题。汤米以为仅仅在熟人小圈子内超越个人受压迫现状。奇尔德雷斯让我们明白,黑人女性不仅面临自己族群之外的种族和性别压迫,她们还面临着族群内部的性别和阶级压迫。
参考文献
[1]Wattley, A. Yonder Comes the Blues: Sexual Politics, Womens Sex Relationships, and the Plays of Contemporary Black Women Dramatists[D].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2001.
[2]Childress, A. Wine in the Wilderness[M]. NY: The Free Press. 1974.
[3]Khuzam, M. “A Black Play Can Take You There”: The Question of Embodiment in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Drama[D]. University of Sussex, 2015.
(作者介绍:白锡汉,陕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非裔美国女性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