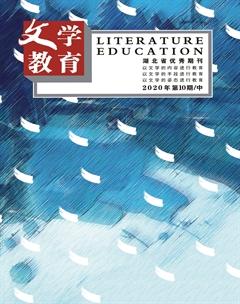叶芝诗歌《记忆》的语言之魅
内容摘要:诗歌《记忆》是叶芝巅峰时的一首短诗,具有鲜明的意象主义诗歌特征。全诗寥寥数行,以山兔以及山兔行迹比喻生活中点点滴滴模糊的过往记忆,形象生动,意象独特。全诗音韵显意、措词简约、句式突显、意象独特,以恰当的音韵、日常词语表述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抽象“记忆”之意,呈现出形象鲜明、特立的意象。因此,无论措词、句式以及用意象等方面诗人都展现出对诗歌语言的极强操控能力和创新能力。本文旨在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读,从语言本身出发探究其中诗歌语言的无穷魅力。
关键词:音韵 措词 叶芝 意象
一.引言
诗歌《记忆》(Memory)是巴特勒·叶芝(W. B. Yeats)一九一九发表在诗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中的一首小诗。其中,语言的简约和富有特色的意象都体现了叶芝创作巅峰时期的风格。众所周知,由于受当时整个欧洲创作之风的影响,叶芝一生的创作随时间的流逝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技法。其大约可以分三大阶段:早期的唯美主义,中期的浪漫主义、意象主义以及晚期的现实主义。其中,1914-1928年间是他创作的黄光时期即:浪漫主义、意象主义以及现实主义相杂合的期间。而这些小诗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现呈现如下:
Memory
One had a lovely face,
And two or three had charm,
But charm and face were in vain
Because the mountain grass
Cannot but keep the form
Where the mountain hare lain. (Yeats, 1997: 150)
这首小诗中所展现出简约特色恰巧体现了叶芝当时在庞德的建议下逐步摆脱他早期诗歌语义朦胧、语言“梦呓”的特点,转向清晰明了、具有民族化特征的口语和选用独特的意象来展现诗歌丰富的内涵。
二.标题题解
标题——记忆(memory)为抽象类名词,它是人类大脑对经验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是一种思维、想象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作为诗歌的标题,其形式简洁、明了、语义概括精炼。《现代汉语词典》对其释意为:“保持在脑子里的过去事情的印象”(2015: 612)。在标题中诗人仅选用了这一抽象名词,没有提供任何附加信息,如何时,何事,何地,何人等相关信息;也没有表明是一种个体性记忆或集体性记忆;更没有使用任何词语如定冠词,不定冠词或形容词等加以修饰。因此,从词的范畴方面可以猜测,诗人可能会描写一种集体性经验结果即:一种对记忆的特征性、整体性描述。从语音学角度看,单词“memory”由三个音节组成,前两个音节的辅音为鼻辅音/m/重复,第三个辅音为流音/r/。根据利奇(G. Leech)的研究,辅音发音时由于气流的强弱不同,读者会感受到不同的语言的强弱效果和对所描写事物产生不同的心理体验(1969: 98)。并且李奇将这两个辅音基本上化分为一类。这意味着单词memory在发音时会让读者有一种相似的语流强弱的重复,一种复现,一种类似生活中事物重复出现的心理暗示。而单词memory中的三个元音分别是前元音/e/、中元音/?藜/、前元音/i/。发元音时,由于开口度由大逐渐变小,气流也渐渐减弱,这会对读者产生一种心理感知上的暗示即:越来越远越来越淡,渐渐消溶最终消失逝的认知印象。辅音与元音合在一起时,一种重复再现与一种渐次变弱相互影响直至结束,这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记忆经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从标题中,读者能够获取如许的一种心理与认知上的暗示。这种暗示与庞德在其诗歌《在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Metro”)所表述的那种模糊记忆相比,似有相似之风又似有迥异之处。
三.音形相合
统而观之,全诗共六句短小诗行,每行均采用抑扬格三音步,押a/b/c//a/b/c韵。全诗形式上,诗人通过第一诗行,第二诗行的行尾二个逗号和第六诗行的行尾一个句号将整首诗从句式上间断相连统一为一个完整的语篇。在诗行之间,诗人选用二个连接助词(and, but)将前三诗行前后承接;第四诗行和第六诗行,诗人选用了二个连接副词:一个表示因果关系的连接副词(because)和一个表示地点关系连接副词(where)连接语篇解释前文;而在第一诗行、第二诗行与第三诗行之间,诗人又采用了词汇复现(repetition)加强诗行间的衔接(第一诗行的face,第二诗行的 charm在第三诗行同时重现);最后,第四诗行与第六诗行中,诗人同样采用词汇重复的手法(mountain)使全诗紧密衔接在一起。因此,全诗无论在语义方面还是词汇形式方面都完美衔接,浑然一体,使读者产生一种整体感印象,即诗中所描述的经验是整体性的体现,并非支离破碎的,是大多数人对生活体验回忆的总体特征。在这一点上,显然它与庞德的那首名诗是不同的。
四.句义相融
从句法角度看,其实原诗六行詩句写成散文体行式仅一个完整的句子,但在诗中,作者将其拆写为六行,诗行间韵步一致,前后押韵,使原本单独的一个句子立刻呈现出一种三维语篇特性,使原本简单明了的一个句子具有了多重可解空间。从体验哲学观讲,它也暗示了一个看似十分明了的人生体验,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明了,其中微妙之处,别有一番洞天。诗歌中,在第一诗行与第二诗行,诗人分别用“one”、“two or three”作为主语,但诗人并没有说明它们分别指代什么。是有生命体还是无生命体,是动物还是人类,是指代一类,还是指代个体?这种不定所指从诗歌一开始就给读者一种不确定的印象,或曰一种整体性确定中的不确定之感。这种在诗歌中使用约数的现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也经常出现,形式与所述虽各不相同但其中有着异曲同工之效,使人读来即有一种熟悉之念,也有一种模糊不定之感。前两诗行完结后,诗人突然笔锋一转意义相背“魅力、美颜皆徒劳”。何以出现这种境况呢?前三诗行中,诗人没有做出任何只言片语的解释,只是一个突兀的结果。一切显得都那么唐突,费解,令人难以释怀。这样一开始就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让读者如跌入了思绪难解的深渊。美学上认为这样的突兀可以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跳、读者的眼球,令读者渴望继续追随作者的言辞。开篇就直接表述所述之物,全无诗歌所谓起承转合之诗法,有着青天霹雳,语出惊人之效果。而与太白之全诗一气贯之,气势冲天不同,叶芝的这首小诗意在设悬,进而突转,最后解释。第四诗行一个连接副词“because”诗歌顺势进入另番境界。如果说前三诗行是对生活体验的实写,那么后三诗行则是与其相对的虚写。但第四诗行中,表面上诗人非但没有解释原因,而是将悬念进一步扩大化,他写道山上的青草,从文字本身看与这似乎与前文毫无关系。在这里诗人第一次使用定冠词“the”来修饰限定大山上的草。但从英语语法上讲,定冠词与不可数名词连用可以表示一类之物,也就是说它表示的也是一种不确定的意义并非指某一特定山上的某一块草地。因此意义并没有变的明确化反而显得更模糊不定。在第五诗行中,诗人继续把悬念扩大化:“仅可存其形”。保存什么的形态?怎样的形态?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在此悬念达到最大化,全诗前后不一致也达到最大化。这一写作特点无疑与庞德的《在地铁车站》相似,从文字表面看都是前后所述不一,但在句法上都具有平行一致的关系。在此,诗人再次使用定冠词“the”修饰抽象名词“form”。在没有下文语境的条件下,它的指向不定。最后一句诗行,诗人告诉了读者一直以来悬而未解之问题。但答案并非直接与题相关,这里体现了意象派诗歌的特征。庞德(E. Pound)曾写道:“一个人在一生中写浩瀚的著作,还不如呈现一个意象”,而意象是“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 (1986: 152)。叶芝在此使用特定的意象来展现诗歌的前三行中所表述的种种经验体验,一种普通语言难以言及至深至彻的人生体验。叶芝理性地选用大山中的兔子作为一个意象,而它在山中草丛中留下的形迹类比人们脑海中可能存留的对渺如烟海的现实经验的模糊记忆。在最后诗行中,这只兔子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是一只还是一类,虽然出现了定冠词但意义却是不定的。解读起来,可谓仁者见人,智者见智。诗人一直把山兔这一意象留到诗歌最后表述出来,形式和意义上立时突显出来,产生了一种形式主义学派所称之为的“前景化”效果,给读者以突显且意犹未尽之余感。
从时态方面考究,全诗共有五处出现动词分别为“had”、“had”、“were”、“cannot but keep”、“lain”。除了一处为一般现在时态,其余四处均是一般过去时态。一方面,一般过去时暗示所述之物、之事是过去的、记忆深处的,并非现实生活中的;一般现在时则表示现在之经验体验。另一方面,以一般过去时态为大背景突显唯一一处一般现在时态,使人类的永恒的过去,与瞬间的现在的主题顿时跃然纸上。对于人类而言,记忆是现在对过去的印象,而过去又是每一秒前的现在,因此人生的记忆其实就是对每一分秒过去的现在的记忆,它如同一只渺小的山兔在绵绵群山中难以计数的草丛中每一秒前所留下的那一丝丝运动的轨迹。因此一切都存在于过去之中,而现在只是过去当中的一瞬而已,诗歌中时态的处理与人类永恒的哲学主题完美结合,并将人生之体验以语言完美再现,使诗歌中以山兔之形迹喻过往之记忆的意象主题进一步深化。
词汇方面,全诗共由32个单词拼合而成,其中仅有五个单词为多音节词分别为:“lovely”、“because”、“mountain”、“cannot”、“mountain”。简单的单音节词配以简短的诗句如若生活中的一朝一夕,平常又无奇,一切显得都那么自然,突然跳跃出来的几个多音节单词如同群山中的山兔一样,给平常带来了一丝丝的异常,给统一的规则带来一点点的破格,让读者在阅读中感知语音的永恒的常态和突然的变异——抽象化表述:这就是记忆——恒定常态中的偶然变异。同时,这种诗语的简单化和日常化展现了当时叶芝的写作特点:以日常语取代后期浪漫主义之靡靡之语,这也印证了庞德所提出的意象主义三原则。
五.意象丰富
诗歌中,最富有特征性的是诗歌的意象:山兔与杂草。首先,山兔的特征是:行踪不定,深藏草丛,快速跳跃着前进,极难捕捉。从认知的象似性(iconicity)看,这与人类的记忆有着相类似的一面——都具有不确定的,跳跃式的运动轨迹。山兔在草丛中跳跃时和短暂地停留时会踩到花草并留下印迹,其真实现场是清楚明了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则渐次变的模糊不清,并渐渐与周围杂草混合一起,难以明确区分出它的行迹。与其相仿,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经历万事万物,其现场真实可见,但随着时间推移,一切会变的模糊不清,模棱两可。正因为如此,虽然人们常称往事“历历在目”但总言说不清。而且人们所经历事件数量之巨如同这难以计数的深山杂草一般,虽然每时每刻人们经历但却永远不能清楚地记住。这一切正如杂草丛中的山兔,虽然每日生活其中恐怕它也无从知晓山草的数量。而山兔过往印迹也只有那种停留伏卧过的才会有模糊的印迹。这不也正是过往事件只有那些特别的才能在在人们内心深处留下印象也即记忆?
六.结语
综上所分析,诗歌《记忆》(“memory”)无愧是叶芝的巅峰之作。从用词、定音、裁句和选意象各个方面,诗人将看似平常无奇的一堆素材黏合成一首风格鲜明、意象新奇的小诗。诗语虽简、诗行虽短以及语法虽平常但整体诗意却丰富无限,将人类对记忆这一抽象的概念具体地体现出来,跃然纸上,如同附于其生命,并从语音、词法、句法方面加以体现。中华先哲老子在描述道的最高境界时曾云:“大方无隅,大器无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里用它来描述叶芝在这首无穷小的诗行里表现无限多的意义的艺术家之才化是不为过分。笔者试将这首诗翻译如下:
记 忆
那一个生的容貌美娇
另两三显的魅力无比
然而魅力娇颜都枉然
因为山上旷野的百草
仅能留存往昔的形姿
在此山兔曾经伏卧过。
参考文献
[1]Leech, G.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69.
[2]Pound, E. 意象主義. 彼得·琼斯 编. 意象派诗选[C]. 裘小龙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6: 150-152.
[3]Yeats, W. B.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 B. Yeats (Vol.Ⅰ)[M]. R. J. Finneran (eds.). New York: Scribner, 1997.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编. 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作者介绍:赵嘏,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翻译学博士,研究方向:诗歌翻译、诗歌研究、翻译学、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