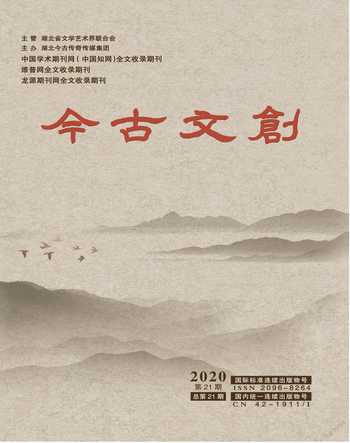以福柯的规训理论解读《一则新闻》
【摘要】 《一则新闻》是韦尔蒂的早期作品,讲述了主妇鲁比,因看到一则家暴新闻(新闻中被害者与鲁比同名同姓)而幻想自己被丈夫殺害的故事。故事中丈夫对妻子的支配与控制方式正好契合了福柯的规训理论。因此从福柯的权力与规训理论出发,围绕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和心灵的规训方式以及女性在规训下的绝望反抗,对故事中夫妻二人权力关系进行深入解读,希望能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找回自我认同与自我价值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一则新闻》;规训;福柯;女性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1-0025-03
一、引言
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是美国20世纪“南方”女作家,同时也是享有声誉的短篇小说大师。她的作品曾斩获美国图书评论家奖、美国图书奖、欧·亨利奖以及普利策奖等美国文学界重要奖项。另外,她的部分作品还被收入美国文学最高成就的“美国文库”系列,由此可见她在美国文学界的重要地位。《一则新闻》是韦尔蒂的早期作品,最早刊登于《南方评论》,后收录于韦尔蒂短篇小说集《绿帘》。同大多数韦尔蒂的作品一样,这篇小说描绘的也是南方社会的生活片段。
小说主要讲述了主妇鲁比,因看到一则家暴新闻而幻想自己被丈夫杀害的故事。虽然故事情节简单,大部分笔墨都在刻画环境以及主人翁的行为与心理变化,但是通过对细节的推敲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淡化了的情节和危险的人物关系。
多年来,专家学者们对韦尔蒂作品的研究不断。这些研究大多联系其南方社会背景,对作品中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畸形心理进行解读,偏向于心理分析、主题探讨、南方情怀以及叙事技巧等方面的研究。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到小人物悲剧命运背后所受到的权力规训。
因此,本文试图用福柯的权力与规训理论来分析故事中夫妻二人的权力关系,以此剖析鲁比悲剧生活的深层缘由、揭露父权社会里女性被压榨、被奴役的事实。
二、双重规训:父权制下的南方淑女文化
“规训”(Discipline)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
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的同时也变得更顺从,从而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
首先,福柯指出,“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因此在规训过程中,只需要“一种监禁的目光,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在故事发生的美国南方,父权制是社会的核心。
因此在这种男性话语主导的社会,女性的衣着服饰、言谈举止,甚至思想道德等方面都要受到男性甚至整个社会观察和检阅。此时的女性既作为男性权力的对象,也成为他们观察和监视的对象。
《一则新闻》里的鲁比就处于这样的监视中:丈夫在家时,鲁比受到丈夫的直接监视。因此原本粗鲁的她开始“轻柔地”准备晚餐,“微笑起来,温柔地低下头”来迎接丈夫望过来的目光。丈夫不在家时,整个社会都成为克莱德的眼睛,人们带着对女性道德要求的目光来观察鲁比的言行举止。而克莱德仅根据他们的“风言风语”就可以间接对鲁比进行监视。男性目光的长期监视在规训鲁比身体的同时也奴役着她的心灵,以至于鲁比内化了这种目光,形成一种“自我监视”效应。她因新闻标题而揣测、幻想被丈夫杀害的场景正是她在丈夫“目光压力”下“自我监视”的有力证明。
另外,除了监视手段,福柯还提到了规训的另一有效手段-规范化裁决。他认为“在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小型处罚机制。它享有某种司法特权,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规定的罪行、特殊的审判形式。”
在《一则新闻》中的南方父权制社会里,淑女文化就像南方女性的道德经,为女性设立了一系列严苛的行为思想规范。它要求女性要恪守道德、严于律己,要像福克纳笔下的艾米丽一样深居简出、恪守礼教。在这样的规范下,鲁比上街搭车的举动自然就被视为一种轻浮、不端的行为。所以克莱德不仅十分排斥鲁比外出,而且一听到“风言风语”就会用肢体暴力来惩罚她。
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家庭暴力在这种文化里被合法化了,成为对女性规训惩罚的最直接手段。此外,除了直接的暴力手段,克莱德对鲁比的规训惩罚还体现在言语态度层面:克莱德刚回到家便对鲁比“大吼”着询问晚饭,接着饭前的第一句便是质问鲁比到底去了哪里。他对鲁比的“大吼”和质问既是一种审判,也是对鲁比心灵的微妙惩罚。其目的是重申规范,使鲁比产生不安与罪恶感,以此来“矫正”她的行为。另外,当鲁比给他看报纸时,他不仅粗鲁地接过并质问报纸的来源,还轻蔑地称呼鲁比“骚娘们”。
福柯曾指出,惩罚不仅是体罚,而是一种能够使人认识到过错的、让人“感到窘迫和羞愧的任何东西:严厉的态度、一种冷淡、一个质问、一个羞辱……”。因此,这种羞辱性的话语不仅是对鲁比人格的侮辱、对其自我价值的否认,更是对其心灵的规训和惩罚。
在层级监视与规范化决裁的双重规训手段下,南方淑女行为规范被逐渐加强。被强化的观念又不断给鲁比带来精神上的压力,使鲁比丧失了自我意识,逐渐沦为被克莱德驯服的肉体。
三、隐藏的“全景敞视监狱”机制
福柯指出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是完美的规训机制,“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这种建筑的结构使得位于中心瞭望塔的权力施加者可以在任何时候看到所有囚犯,而囚犯则彼此无法交流,处于被隔绝和被观察的孤独状态。这就产生了全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由于囚犯目睹瞭望塔的存在却不知道自己是否正被监视,因而产生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即自我监视,继而使得来自瞭望塔的权力得以自动实施。因此,这种机制就造成了一种“精神对精神的权力”,而囚犯的“自我监视”则意味着规训的成功实施。
结合上文对规训手段的分析,从权力空间的角度来看,克莱德与鲁比的权力关系恰如“全景敞视监狱”中的监视者与囚犯的关系。这个监狱以整个父权制社会为建筑模型:父权制社会赋予男性话语权,使这种男性权威成为整座监狱的“中心瞭望塔”;拥有男性话语权力的克莱德则成为瞭望塔中的一员,对鲁比享有监视与惩罚的双重权力;鲁比作为被驯服的肉体,在这种权威的监视下“内化”了男性的目光,使得规训权力在这座监狱里自动实施。
另外,从鲁比和克莱德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状态来看,也与这座监狱的空间模型相契合。从鲁比的生存状态来看,鲁比一直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故事的开始,鲁比不仅自言自语,说话反反复复,而且为各种小事惊讶万分,就连作者都断言:“她一定是孤独惯了。”并且每次克莱德让她伤了心,她所能做的就只有搭车到田纳西,在“储藏松子酒空瓶的窝棚里度过午后时光”
可以看出,鲁比除了克莱德之外无依无靠、孤独无助,所以家成为她唯一的生存空间。反观克莱德,他可以自给自足,自由地在森林中、在社会里穿梭,而不受限于任何人。
为了自己的安全,他任性地用灌木给威士忌酒蒸馏屋搭上厚厚的屋顶,这样雷雨天他就可以独自在里面安逸享受。由此可见,克莱德相对于鲁比是自由的,正如囚犯无法直视中心瞭望塔的监视者,鲁比也对克莱德的行踪无法预见。家就像鲁比无法挣脱的孤独囚室,使她不得不顺服于克莱德。
四、被驯服者的反抗
尽管“全景敞视监狱”被认为是完美的规训机制,但福柯在访谈中指出,“哪里存在着权力关系,哪里就会有反抗的可能性。”虽然男权社会的完美规训使鲁比丧失了自我存在的意识、使她完全沦为被奴役的囚徒,但新闻的出现却模糊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给鲁比指出了反抗的可能。
一方面,如上文分析到的,它引发了鲁比的恐慌与幻想,这是鲁比在丈夫“目光压力”下“自我监视”的表现。
另一方面,“自我监视”之后,鲁比也在这种恐慌与绝望中找回了自我意识,开启了反抗之路。
首先,新闻中的鲁比不仅拥有与鲁比同样的姓名,而且和鲁比一样忍受丈夫的暴力。正如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观点,幼儿从镜像中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总体感知才形成了自我意识,这则新闻就像一面镜子,让鲁比从中看到了被自己视而不见的自我。因此她在幻想中给自己穿上“崭新的睡袍”,即使倒在克莱德的枪下,也要摆出“美丽、动人、死亡的面相。”这种对身体的关注与畅想是鲁比找回自我意识的有力证明。
其次,新闻的出现引发了鲁比对死亡的畅想。福柯认为,“正是依靠生命,通过生命的展现,权力才确立了它的统治;死亡却是权力的极限,是摆脱权力的时刻。”
鲁比作为克莱德权力的对象,她的死亡则意味着权力客体的消失,所以死亡成为她冲出牢笼、摆脱规训权力的一种方法。另外,在幻想中,她得到丈夫的好生安葬,看到丈夫为她“狂乱、呼号、精神涣散。”
可以看出在鲁比的意识中,死亡不仅是种解脱更是对克莱德暴行的惩罚手段。因此,幻想死亡的鲁比,感受到的不再是死亡的恐惧,而是死亡所带来的“遗憾、美好,还有力量”。这种对死亡的美好畅想不仅暗示着她跳出规训机制的束缚,也暗示着她反抗意识的觉醒。
最后,新闻象征着知识,而知识也是一种话语权力。因此鲁比向克莱德指了指新闻中的名字,一方面是对克莱德暴行的痛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自身的存在并从中获得话语权。所以,把报纸拿给克莱德是鲁比对克莱德话语权力的公然挑衅。当克莱德不仅不为所动甚至还大光其火时,鲁比也毫不示弱,用眼神“狠狠地直盯着他”。
这一盯彻底颠覆了与克莱德之间的权力关系,鲁比不再是克莱德观看的对象、也不再是他权力的客体,而是反身成为权力的主体。接着,他们陷入了一种僵局,彼此对视着,“谁都无可奈何,谁都束手无策。慢慢地,两人都红了脸,仿佛一方面感到羞愧难当,另一方面觉得快乐无比。”
从他们对视背后权力抗衡的微妙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克莱德在鲁比“目光”下的羞愧与窘迫,也可以感受到鲁比对克莱德的无可奈何。虽然此时的鲁比仍然无法颠覆与克莱德之间权力关系,但是她解构了克莱德作为权力主体的地位,突破了权力规训的牢笼。
五、女性反抗意识的局限性
《一则新闻》中的鲁比虽然在重压之下绝望反抗,但是,她的反抗只停留在简单的思想意识层面,只是对男性权威的简单试探,并不彻底。
在故事的结尾,克莱德再次否认鲁比与新闻的联系,并且好脾气地拍了拍她的背。他的这些行为一方面是对鲁比个人身份与存在的否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掩饰内疚、对自身权威的维护。而鲁比最终收回颤抖的双手、屈身窗边的动作也反映出她无法扭转局面的无奈。就像最后被克莱德烧毁的新闻报纸一样,她的微弱的女性自我意识也随之熄灭了。
联系故事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笔者认为,这种女性反抗意识的局限性与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相关。
首先,这种女性意识的局限性是由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造成的。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方社会仍然是封闭的农业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塑造了南方人保守的性格。
所以,尽管饱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洗礼,南方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父权主义观念仍然保留着。
另外,在当时奴隶制与种植园经济背景下,南方工业落后导致女性无法工作、更不能独立于社会,因此她们只能依附男性生存。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即使女性意识到了被奴役的事实,也无法摆脱生存的困境。因此,她们的反抗只能停留在细微的思想层面,无法找到切实可行的可靠手段。
其次,雖然韦尔蒂的作品大多以女性角色为主,甚至连评论家乔纳森·亚德里( Jonathan Yardly)都认为韦尔蒂是“女人们的作家”。但韦尔蒂却在南方访谈中声明,她的创作“并不关心与女性主义相关的问题”。她认为,“写小说就是照生活原样描写生活。”
作为一名作家和摄影师,她的作品扎根于南方,像那些影像作品般记录着真实的南方生活。因此,韦尔蒂无意去刻画一个争夺女性权力的新女性,只是按照生活背景记录当时真实的南方女性生活。所以,相比一些拥有较强女性主义创作理念的作家来说,韦尔蒂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反抗意识不够强烈。
六、结语
通过对《一则新闻》中鲁比与克莱德权力与规训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南方淑女规范与暴力惩罚的双重作用下,女性被规训、被奴役的事实。故事中鲁比与克莱德的关系就如“全景敞视监狱”中的囚犯与监视者的关系:克莱德作为监视者,同时拥有监视与惩罚的权力,这就给鲁比造成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力。
在克莱德男性权威的审视下,鲁比内化了他监视的目光自觉形成一种“自我监视”,使得规训权力自动实施。然而,在这样完美的规训机制中,也依然存在着反抗的可能:鲁比不仅从新闻标题中找回自我意识、突破“自我监视”的牢笼,而且还试图颠覆和解构克莱德作为权力主体的地位。她的反抗之举虽具有局限性,但却激励着广大女性,让她们在父权社会的前进之路看到了希望。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2]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韦尔蒂.绿帘[M].吴新云译.江苏:译林出版社,
2012.
[3]Foucault,Michel.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New York:Rout ledge Press,1988:123.
[5]米歇尔·福柯.性史[M].张廷深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6]赵辉辉.“少女”身体意象的文化言说——以尤多拉·韦尔蒂作品为分析对象[J].国外文学,2014,(02):126-134+159-160.
[7]孙素茶.小视角窥探大世界——尤多拉·韦尔蒂短篇小说集《绿帘》解读[J].钦州学院学报,2016,31(09):30-33.
作者简介:
李晓亚,女,汉族,暨南大学201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