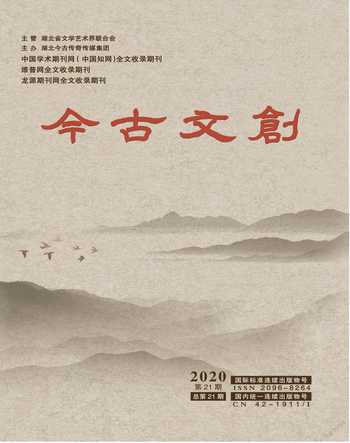李碧华和严歌苓小说中“边缘人”形象比较
【摘要】 李碧华和严歌苓以各自独特的写作方式和题材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地位。她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身上,通过女性的微妙笔触直击“边缘人”的苦痛。相比较而言,李碧华笔下的人物多具有“妖魔化”或疯狂性的生命特征,而严歌苓在展现“边缘人”被欺凌的同时,也不忘展示其自身美好的一面。这与两位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经历以及个性追求有关。
【关键词】 李碧华;严歌苓;“边缘人”形象;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0)21-0009-03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基金项目“女性作家小说中的 ‘香港形象’研究”(编号:2018SJA1534)。
香港作家李碧华用一支诡谲灵异的笔,塑造了丰富多样的“边缘人”形象,并融入自身对女性命运的探究。华裔女作家严歌苓似乎对“边缘”情有独钟,总是主动选择站在与“主流”相对偏远的位置上,用自己的眼睛来打量世界。在她笔下也出现了一系列形态各异的“边缘人”形象。这些人物游走在社会、经济、文化、情感的边缘,所做的种种挣扎和努力,表达了严歌苓对人性的思考和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对李碧华和严歌苓笔下“边缘人”形象的比较,来考察形象创造与文化身份、叙事策略等的互动关系。
“边缘”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指周边部分、临界、沿边的部分。库尔特勒温提出:“边缘人(marginalman)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1]之后,“边缘人”的概念范围不断扩大。一般认为,“边缘人”就是被排除在社会中心之外,和主流人物不同的,而与少数弱势紧密联系的一个群体。包括被社会文化群体孤立的人和具有边缘人格的人。當然,随着时代、领域的改变,它的界定范围也会逐渐改变。
一、社会主流之外的弱势“边缘人”
(一)相同点
李碧华与严歌苓以女性视角为妓女、戏子等社会边缘人物另作新声。在她们的笔下,这些人被欺凌、被强迫,受尽了折磨与屈辱。如《胭脂扣》中的如花尽管是石塘咀当红妓女,却逃脱不了被任意欺凌的命运。与十二少的相恋使她有了追求幸福的可能,但两人身份地位的悬殊让她遭到了陈母的鄙夷与反对。与十二少选择双双殉情,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欺骗。当她发现记忆中的爱人居然苟活于世,才彻底死心。《霸王别姬》中,李碧华将关注的目光放在戏子这类封建社会身份卑微的人物身上。梨园行的学徒们生活中只有练戏和挨打。小癞子忍受不了痛苦几次三番逃跑,甚至自杀。戏子身份的卑微也造成了边缘的处境和认同的困难。台上也许威风凛凛、风光无限,台下却往往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到权贵的玩弄与侮辱。
又如严歌苓《角儿朱依锦》中的名角朱依锦,喜爱她表演的人遍布各地,然而突如其来的政治变革让她成了众矢之的。她没有权力反抗,无法诉说自己的冤屈,甚至连支配自己生命的权利都没有。当她不堪受辱选择自尽后,竟然赤身裸体地被放在走廊上供人围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白蛇》中的舞蹈演员孙丽坤,在“文革”期间被群众强行禁闭并不断地对她进行批斗。她们是社会主流之外的弱势群体,没有能力为自己正声,也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
(二)差异性
李碧华倾向于选取颇具争议性的人物,她故意将笔下的女性“妖魔化”或表现出疯狂的生命特征。她们的痴情疯狂,具有很强的报复性。 如花为了和十二少“同生共死”,竟在对方的酒里下安眠药。又不惜减寿十年换取到阳间七天来找寻前世的爱人,这种超越阴阳两界的疯狂的爱具有一种惊世骇俗的力量。川岛芳子(《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沉浮在政治、权术与阴谋中,成为一个牺牲品。她被养父侵犯后,强迫医生做了绝育手术,剪了男式分头,与女性身份彻底诀别,这种极端的反抗手段震人心魄。《生死桥》中段娉婷为了破坏怀玉与丹丹,竟使计弄瞎了他的眼睛,这样极端的爱着实令人恐惧。
与李碧华的叛逆、反抗、极端人物不同的是,严歌苓对边缘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表现他们被欺凌的同时,也不忘展现其自身美好的一面。她笔下的女性坚韧、善良、温柔,面对生活的苦难默默地承受、包容,在社会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展示出圣母般的美好。
《金陵十三钗》中的十三个妓女,同样是被摧残、被蹂躏的弱者,她们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但当日军丑恶的爪牙伸向自视甚高的女学生时,她们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这群学生。这一刻,她们已经不再是低贱、肮脏的妓女,而是闪耀着崇高、神圣的光辉。《扶桑》中扶桑为了寻找丈夫,被人贩子拐骗卖到旧金山,成了妓女。不论是白人还是同胞,都将她当作蹂躏的工具,甚至被老鸨脱光了衣物,如同动物般吊在称上称重售卖。她没有身份、没有尊严,比寻常的妓女还要悲惨。然而,扶桑却从始至终没有抱怨,没有反抗,她始终是宽容、隐忍的,以一种地母般的姿态承受一切痛苦,展现出向善向美的人性光辉。
二、男权文化桎梏下缺失爱情的“边缘人”
(一)相同点
身为女性作家,李碧华与严歌苓不约而同地将关怀的目光锁定在女性身上,描写她们的痛苦遭遇,揭示她们在男权文化桎梏下的悲剧命运。
《青蛇》中,李碧华将历史文本中白蛇的品质完美地展现出来,她聪慧美丽、德才兼备、妩媚多姿又温婉贤淑,令人无从挑剔。而且道行高深,处处保护书生许仙,为他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可是,这样一个“完美”女性却落得被丈夫背叛、永世镇压的悲惨结局。《生死桥》中,丹丹对怀玉一片真心却被抛弃,由此心生怨恨,决定进入名利场出人头地,报复怀玉,最终染上毒瘾,走上了不归路。《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单玉莲不甘心枉死,拒喝孟婆汤,要转世复仇。前世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人生,在四个男人之间流转;然而转世后依然在男人之间沉浮。她的生命永远都被男人定义,人生无望。
严歌苓《小姨多鹤》中的朱小环能干、善良、尊敬丈夫、孝顺公婆,却因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兵追赶,导致流产,再也无法生育。当公婆带回日本女子多鹤要为张家传宗接代时,朱小环只能被迫接受,把自己的丈夫拱手送人。在朱小环身上,爱情无疑是缺失的。我们无法得知她怀着怎样的心情为丈夫和多鹤的约会打掩护,把孩子视如己出,将多鹤当作自己的亲人。她身上体现了农村女性的坚韧、宽厚、乐观,却也是她生活在男权社会中,不得不放弃自我,屈从、依附于男性的悲剧。
(二)差异性
两位作家笔下女性的爱情悲剧除了来自社会的动荡和男权社会的压制外,女性自身不成熟的独立人格也是重要原因。李碧华《青蛇》中的白蛇、《诱僧》中的红萼公主等女性,她们美丽、独特,本可拥有更自主的人生,却被爱情迷惑,放弃自主权,甘愿成为男性的附庸。读者不免为那些敢做敢当、大胆追求、鲜活丰满的女性叫屈,她们本该美好、精彩的人生葬送在卑劣、龌龊、自私的男子身上。然而,导致她们悲剧命运的,很大程度上是她们自身。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自觉地把自身摆在了屈居于男性的第二位置,最终落得悲剧收场。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在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方面则要比李碧华笔下的女性进步些。她在作品中为很多移民女性安排了来自绅士、温柔、体贴的西方男子的爱情,可最终总以女性的逃离结束。因为这些女性在感受来之不易的爱情同时,始终清醒地明白对方有着对自己充满善意的误读。如《扶桑》中,克里斯对来自东方的扶桑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他喜欢扶桑温柔、包容、母性的微笑,尊重这个流落风尘的东方女子。但当克里斯想要拯救扶桑时,扶桑却拒绝了。因为她清楚地知道,一旦接受了拯救,今后的她将永远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在异国也遇到了一份珍贵的爱情,但如果接受这种夹杂着宽恕和拯救的爱,也就意味着“我”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所以她们拒绝这种本质上不平等的爱情。
三、沉浮在政治變革环境中的“边缘人”
(一)相同点
特殊年代的政治沉浮同样是导致“边缘人”悲剧命运的一大原因。严歌苓与李碧华笔下的许多人物形象被政治边缘化,失去了个人话语权,在风雨飘摇中无力掌控自己的人生。
《霸王别姬》中段小楼和程蝶衣身处乱世不免为时局侵袭,在每一次时局的变动下,人物的命运都会跌宕起伏。而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互相批斗、揭发更是赤裸裸地则将人性中最为隐蔽的恶呈现出来。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美貌的单玉莲被强奸,却被不辨是非的人们斥为“淫妇”。又因送男友一双鞋被定罪为“盗用国家财物”而被批斗、羞辱、下放。她的反抗在特殊的时代宛若浮萍。川岛芳子因父亲的复辟大业被送往日本调教,被洗脑培养成一个以建立“满洲国”为信仰的人。她放弃爱情、家庭,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最终失去利用价值的她穷途末路,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白蛇》《天浴》《角儿朱依锦》等特殊历史时期题材的作品比比皆是。《雌性的草地》中,七个女牧马兵被迫丢掉了作为人的基本天性和女性的需求。在那特殊的时代,一些人的价值观被颠覆,人性遭到扭曲。《天浴》中的女知青文秀用肉体换取回城的机会,《白蛇》中孙丽坤被惨无人道地“改造”,《拖鞋大队》里的女孩们甚至对同龄女孩耿荻进行残忍的性别鉴定……
(二)差异性
李碧华惯有的冷酷、严峻的特点使她笔下的特殊历史时期残酷、暴力。她在《霸王别姬》中写道:“一个女人跳楼了。她的一条腿折断,弹跳至墙角,生生地止步。脑袋破裂,地上糊了些浆汁,像豆腐一样。血肉横飞,模糊一片。有些物体溅到蝶衣脚下,也许是一只牙齿,也许是一节断指。”[3]363这种如外科医生解剖般冷静、客观、缺乏温情的语言,给读者形成一种视觉和知觉冲击。李碧华并未亲身经历过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她对此的印象是参考报纸或别人作品而来。这使得她对特殊历史时期的理解相对浅薄,缺乏内在、深层次的表现。“虽然在感觉方面可以触动读者,但是在表现人的内心方面却很薄弱,以至无法从灵魂深处感动读者。”[4]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正因为直白、浅薄,可以从边缘的人生切面补充这一书写领域。
严歌苓的作品则有意减少血腥的斗争、残酷的迫害描写,而把重点放在人性的分析与展示上。她的移民经历使她能够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待这段时期的扭曲与痛苦。她关注点是这种戏剧性的环境对人性多层面的展现。《梨花疫》中肮脏、来历不明的女叫花萍子不仅被整条梨花街的人鄙视和唾弃,甚至还被人告密,说她有麻风病;《小顾艳情》中未成年的穗子和她的伙伴一起偷窥小顾,并将她的私生活抖落出来……严歌苓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作为一个背景,来展现人性中平时并不会苏醒、但在非正常环境中会爆发出的人格深处的秘密。
四、李碧华和严歌苓小说中“边缘人”形象差异的
原因
(一)社会背景
在为“边缘人”发声时,李碧华表达的是一种质疑、不满、反抗,身份认同混沌。严歌苓则在兼收并蓄中用温和的方式,实现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二者都是处在两种文化之间,表现出的态度却有很大不同,这与她们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李碧华所处的社会环境建立在香港被殖民、缺乏自主权且前景迷茫的背景基础上,边缘化又游离,因此,其作品充满着愤怒、抗拒、毁灭、无望,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多有隐藏的文化内涵;而严歌苓移民则是自己的选择,她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全球化的语境,多元文化交汇,世界经济格局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给作家的文化观念带来了不同于前人的冲击。因而她的边缘人物是包容的。
另外,香港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结合在一起,鼓吹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这样的消费文化环境使李碧华的题材更多选取吸引眼球、与众不同的独特人物形象,叙事风格也独特妖异。而严歌苓的移民身份使她能够站在边缘,关注移民者的生存状况,以一种更为冷静和理性的姿态来思考问题。
(二)个性追求
李碧华素有“香港文妖”之名,她的语言风格泼辣、冷峻、又有妖邪之感,人物大多偏离传统。她偏爱诡异凄美的人物形象,总是将角色的人性、妖性、邪性予以放大,着墨于乱世男女的悲欢离合,书写他们的前世因果与轮回。她还擅长用新的视角拆解传统经典文本,旧事新编。传统文本的改写在李碧华笔下有了剖析人性、寓意当下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在气氛上,她喜欢恍惚沉迷之感,小说中时常出现昏暗绮丽的色调,浮荡的香气。
严歌苓的写作重点在于对人性的探讨。她曾说过:“我对社会上的输者感兴趣,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输法,而赢者都是一个面孔,写作就要写个性的人物。”[5]这种创作追求使她自觉站在边缘,有“他者”的视野和从容不迫的气度。这就造成严歌苓在创作叙事文本时,能以一种较为超脱的姿态进行叙述,具有自嘲、调侃、化沉重为轻松,解庄严于诙谐的特点[6]。并且严歌苓在以博大的政治背景展开叙述时,时常从小人物切入,以小见大映射出时代下人们进退维艰的生存处境。她采取的多是日常化叙述。在时代的政治大背景下,细致地展现他们的生活处境、内心情感,表达出他们物质的匮乏、人身的不自由、精神的无望甚至人格病态。当然严歌苓并没有对这些人物做过多的道德批判,而是冷静、客观地书写人性的多层面。
总体而言,李碧华与严歌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书写身处边缘的人物,表现了不同背景下“边缘人”的生存境况与心理痛苦,并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关注爱情与人性在特定背景下的多样呈现。正是她们风格各异的创作,完善了对“边缘人”形象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姚仁欣.苏童小说的“边缘人”叙事[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2]严歌苓.穗子物语[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李碧华.霸王别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4]李亚萍.一道残酷的风景——解读李碧华小说中的“文革”描述[J].当代文坛,2001,(1):48-50.
[5]刘易.旅美作家严歌苓:美女作家文不对题[N].文学报,2003-3-27(3).
[6]刘俊.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6):30-38.
作者简介:
奚志英,女,江蘇江阴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