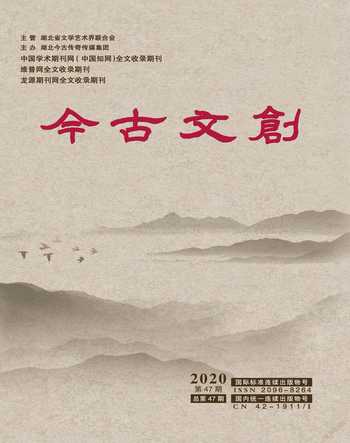试论刘勰对文章“变体”之“度”的把握
【摘要】 作为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系统性文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其“体大虑周”“笼罩群言”的文学思想对中国后世文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十分重视文章的体制规范,《文心雕龙》中的二十篇“论文叙笔”充分体现了他的“变体”观。刘勰认为,各体文章可以在“以本采为地”的基础上,实现“契会相参,节文互杂”之变;文章的“功能”“体势”“体貌”等构成了一类文体的基本特质,这些特质都可以进行“变体”,但不可全变;此外,文章本身所需要传达的“情志”以及“宗经”原则不可变。刘勰对不同文章“体制相参”所做出的评价,看似前后矛盾,实则暗含着对于文章“变体”之“度”的把握。
【关键词】 刘勰;变体;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7-0015-03
《文心雕龙 · 通变》谓“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可见在刘勰的文体观中,文章之“体”是恒定的,文章之“变”只能在保持文之常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另一方面,对于文章之“变”,吴承学先生曾在《辨体与破体》一文中,以《定势》篇“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为例,指出“刘勰既承认文体的相参,又强调文体的本色”“文之大体,也就是文体的‘度’,在这个‘度’内,作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一旦超过‘度’,也就破坏了问题固有的美了”[1] 。
综合以上观点可进行深入探究:刘勰所持之“通变”观与其“契会相参,节文互杂”的观点是否矛盾?其所谓某一类文体的“本采”究竟为何?其所谓的“文之常体”包含了哪些方面?在何种标准下或是何种范围内的文体互参,才能够被刘勰承认为“变体”,而非“讹体”与“谬体”?研究以上问题,能够揭示出刘勰对于文章体制规范“度”的把握,从而促进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深入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对“体制相参”的矛盾态度暗含对
“变体”之“度”的把握
在二十篇“论文叙笔”中,刘勰以大量篇幅描述了各类文体“体制相参”的现象,并且对之持以肯定态度。
比如,在《祝盟》篇中,刘勰提到“祭而兼赞”“策本书赗,因哀而为文,是以义同于诔……颂体而祝仪”,阐述了“祭文”与“赞”的相交,“哀策”以“诔”为内容、以“颂”为主旨、以“祝”为形式的文体特点;再如,在《诔碑》篇中,刘勰以“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以及“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光于诔”,详细论述了“诔”“传”“颂”“碑”“铭”这几种文体之间的互参;同样地,在《颂赞》篇中,刘勰亦论及“赞”是“颂”之“细条”。黄侃先生的《札记》又在刘勰论“颂”的基础上,详细追溯了“颂”的流变,得出“赞”“祭文”“铭”“箴”“诔”“碑文”“封禅”这些文体,“皆与颂相类似”[2]62的结论。这类文体虽然产生有先后,但在内容形式上几乎都有交叉。
对于一些“变体”出色的文章,刘勰亦有所夸赞。例如,在《哀吊》篇中,刘勰以“卒章五言,颇似歌谣”表达了对崔瑗哀辞的认可;而对于潘岳“结言摹诗,促节四言”的哀辞,刘勰更是给出了“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的高度评价;甚至,对于司马相如“吊二世,全为赋体”这类对文体所进行的颠覆性改造,刘勰都没有提出异议。由此可见,刘勰对于文体互参的多样形式,秉持着很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然而,同样是“化而为赋”,刘勰对后世的“吊”却表达了很明显的不满,认为其“华辞末造,华过韵缓”,这似乎与此前对待司马相如之文的态度有所矛盾;同样地,在《铭箴》篇中,刘勰虽然赞赏蔡邕的铭文,但对于他写作“朱穆之鼎,全成碑文”则持否定态度,认为是他只顾沉溺于自己拿手的文体,却不顾对“铭文”与“碑文”所造成的文体混淆;另外,在《颂赞》篇中,对于班傅、马融、崔瑗和蔡邕将“颂”写成“序”“引”和“赋”的体制,刘勰称之为“谬体”“弄文而失质”;对于魏晋时期的“颂”呈现褒贬混杂的情况,刘勰称之为“讹体”。
同样是文章体制的参杂与文体功能的扩展,刘勰为何对某些变体的要求表现得如此严苛呢?这些论述看似与刘勰“变体”观的包容性相矛盾,实则暗含着刘勰对于“变体”之“度”的把握。
二、文体中“可变”的特质
传统文论的“功能”“体势”“体貌”等方面构成了文章能够成为一类“体裁”的基本特质。在刘勰的“变体”观中,不同文体之间的“功能”“体势”“体貌”可以在作家的妙笔之下,得以互相借鉴与融合,在汲取各家优点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一)“功能”之变
例如,在《明诗》篇中,刘勰就论述了从夏商周到汉朝再到建安初年,“诗”的形式从“四言”发展到“五言”的过程,“诗”的主要表达对象亦从政治意义上的“顺美匡恶”转向至《古诗十九首》中的“附物切情”和建安文人的“述恩荣、叙酣宴”,更加注重个人际遇与个体情感的抒发。
再如,在《颂赞》篇中,刘勰以“赞”为“颂”之“细条”。“颂”体内部的种类流变已相当繁多,而“赞”的功能,则是在“美盛德而述形容”的基础之上,扩展为“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也就是在表述对象和表达色彩方面,相对“颂”都有了一定的扩展。
又如,在《论说》篇中,刘勰谈及“论”的“条流”,分为“议”“说”“传”“注”“赞”“评”“序”“引”这八种名目,分别指向“宜言”“说语”“转师”“主解”“明意”“平理”“次事”“胤辞”这八种论说功能。这些“条流”使得“论”的功能有所扩展。
(二)“体势”之变
“体势”者,“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刘勰认为,不同文体之间的体势可以融会贯通,善于作文的人,正是精于通变文章体势之道。
例如,屈骚变“诗”之典雅为艳逸,“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对于其在表现方式上对“典诰之体”“比兴之义”的化用,刘勰认为其达到了忠君规讽的目的,因此对之呈欣赏的态度。
再如,刘勰视“五言”为“四言”的变体,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四言诗因其“持之为训”“順美匡恶”的历史功能,秉持着“雅润”的体势;而五言诗之“清丽”,则表现在《古诗十九首》的“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张衡《怨篇》的“清典可味”以及建安诗歌的“独立不惧,辞谲义贞”……
然而,当刘勰在《定势》篇中论及“赋颂歌诗”的体势时,则称“诗”之理想状态应为“清丽”。也就是说,他已经将原本属于五言诗的“清丽”面貌,融汇到了四言诗的体势之中,实现了诗歌“体势”的流变。
(三)“体貌”之变
对于诗赋体貌的流变,刘勰对屈骚“自铸伟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的盛美风貌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失其实”的写作风格不仅继承了“诗”的风流,也为后世“赋”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及至论赋,刘勰亦认为“赋”能够从“古诗之流”、也即“六义”的附庸地位中兴起,终成蔚然大观,也正是缘于其超越诗体风貌、“极声貌以穷文”的盛大气象。
即便是“本体不雅”的“谐”体,也同样在文体的流变中实现了体貌的渐变。由“谐”至“讔”再到“谜”,文章体貌愈见曲折。“谐”者,“辞浅会俗”,文辞以“微讽”“倾回”为主。“谐”的用辞浅显通俗,或婉转、或诡诈,其目的往往是用于讽谏;“讔”者,“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往往是用隐约的言辞来暗示某种含义,或是用曲折的比喻来暗指某件事物,“谐”与“讔”互为表里,而“讔”之曲折比“谐”更进一筹;“谜”之曲意则更甚,其言辞曲折交错、使人迷惑,“回互其辞,使昏迷也”“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当“谐讔”发展到“谜”时,其文貌更为纤细巧妙,文辞更为含蓄,而一旦悟出谜底之所在,其所喻亦不失明朗。但无论其文貌经历了怎样的流变,“谐”本身“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的箴戒功能并没有消减。
由是观之,刘勰所把握的“变体”之“度”,是尊重并赞赏文章“功能”“体势”“体貌”因时而变的。刘勰所谓“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文章“变”之关键,正是在融通于相对稳定的文章创作法则基础之上,“酌乎纬,变乎骚”,让“文辞气力”顺应时势的发展而变化通达,采时文“雕蔚”之美,酌奇保贞、玩华保实,以期实现文章的永生。
三、文体中不可变的原则
既是“文之体有常”,且须“各以本采为地”,可见文体中那些不可变的因素就是“变体”的关键。其一,文体基本特质虽可变、但不可全变;其二,文章本身所要表达的情志不可变;其三,“宗经”原则不可变。
(一)文体特质不可全变
统观刘勰在文体论中对各类变体所表达的态度可知,虽然刘勰赞赏各类文体“体制相参”的流变与发展,但对于把“吊”写成“赋”、把“铭”写成“碑”、把“颂”写成“序”“引”等现象,刘勰是相当不满的。“文体功能”“体势”“体貌”等这些文体的基本特征可以“相参”,但不可全变。作家不顾文体混淆地任性使才,把文章完全写成了另外一种文体,则是“弄文而失质”,使得文体失去了本身的价值。
另一方面,刘勰之所以对司马相如“吊二世,全为赋体”表达了一定的包容度,关键原因在于相如之“吊”达到了“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平章要切,断而能悲”的境界。尽管司马相如也混淆了“吊”与“赋”的文章体类,但因其文章对主体情志的表达,并未失却“吊”本身所需表达的“哀而有正”的主体情志,因此刘勰对此才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二)“情志”不可变
所谓“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在刘勰看来,文章所要表达的主体情志,应当是文体划分的关键之处,这点可以在刘勰所批判的各类文章中见出端倪。
例如,在《明诗》篇中,谈及晋诗“轻绮”,刘勰认为其“力柔于建安”“流靡以自妍”“溺乎玄风”,失于陈腐浮疏,浮于艳发绮丽,失去了诗体本应有的气度与感染力;再如,在《哀吊》篇中,刘勰就明确表达了对苏慎、张升的哀文“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心实”“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的批判。苏张之文的华而不实、难表情志,正是其难以比肩司马相如之吊文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宗经”不可变
在肯定屈骚伟大意义的同时,刘勰对其中“诡异”“谲怪”“狷狭”“荒淫”之旨持否定态度,因其“异乎经典”而不可取;在评价崔瑗哀辞时,刘勰亦认为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的措辞“仙而不哀”,未能抒发其真实情志。由此可见,在刘勰的变体观中,其所谓“设文之体有常”,关键就在于需要做到“参古定法”。“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刘勰认为,只有做到对“经典之范”之“熔铸”,对“子史之术”之“翔集”,对“情变”之“洞晓”,在取法经书、贯通历史典文的基础上,将经典之要义熔铸于心,将子书史籍之风骨内化于心,将古今情势之演变通晓于心,才能拥有得以新变的“不竭之源”,从而实现与古人情感的交流与共鸣,才能以一种通达的境界为文,创作出跨越时空的经典之作。
总之,在刘勰看来,文章变体之基础,莫过于“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只有根植于儒家经典,文章之树才拥有使其能够常青的灌溉之源。
四、结语
如此看来,刘勰对文章体制相参之“度”的把握便十分明晰了——在保持住“宗经”原则、文章“情志”以及文体基本特征的条件下,不同文体之间在“文章功能”“体势”“体貌”等方面可以互相借鉴,最终实现文体的发展与流变。刘勰的“变体”观既具辩证性也具历史前瞻性,为后世文体的流变勾勒出了一个基本轮廓。
参考文献:
[1]吴承学.辨体与破体[J].文学评论,1991.
[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赵俊玲.刘勰的“破体”观[J].求是学刊,2017.
作者简介:
江俊超,女,浙江宁波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