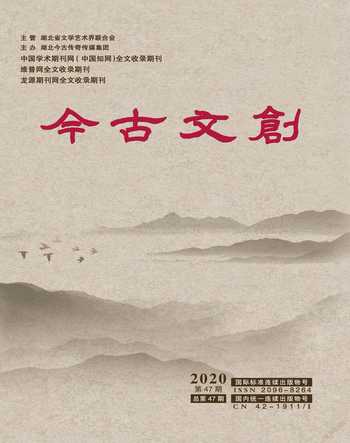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洪水之年》
【摘要】 玛格丽特 · 阿特伍德被誉为“加拿大的文学女王”,她的作品中充满了生态与女性意识,《洪水之年》正是其中的佳作。《洪水之年》是阿特伍德备受赞誉的《羚羊与秧鸡》续篇,“疯癫亚当”系列第二部曲,讲述了一场“无水的洪水”所引发的故事。本文拟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探讨“父权制”社会对托比的压迫、托比的生态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托比的反抗。文章从托比的角度去反思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从而警示人类要与自然、动物和谐相处。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男权制;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I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7-0011-02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佛朗索瓦 · 德奥博纳在她的《女性主义或者死亡》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其目的在于呼吁女性主义者发起一场运动,保护全球生态的生存。[2]在书中,德奥博纳明确指出,父权制体制和男性权利是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不断加剧的根源,“使地球变成了一个不适宜我们子孙后代居住的地方”。[3]一方面,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认为他们是压迫自然和女性,造成生态失衡的根源。另一方面,主张将女性和自然从“男权制”社会解放出来,解构西方男人/女人、自然/文化和理智/情感“二元论”的传统思维模式。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 · 阿特伍德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她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国际文学奖和不计其数的其他奖励和荣誉,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国内外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作品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阿特伍德的《洪水之年》讲述了人类长久以来恐惧的洪水终于来临,这是一场迅速蔓延的疾疫,无法通过生物手段加以控制,如大火般吞没了一座由一座城市,令数千万人命丧黄泉,几乎灭绝了所有人类的痕迹。女主人公之一的托比成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在腐败的统治力量的阴影和新型基因合成物种的威胁下,托比必须尽快决定下一步行动,而不仅仅是把自己反锁在暂时的安全屋里。[1]本文从托比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希望对当下社会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二、“男权制”社会对托比的压迫
在《洪水之年》中,“男权制”社会对托比的压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男权”统治社会这一大环境对托比的压迫。托比一家原本生活安逸,“这里曾经有松鼠栖居,还有一批绿毛兔。还有浣鼠……鹿儿成群出没,偶尔还会闯进母亲的菜园”,后来托比的母亲一直服用大院新研发的维生素药片,成为大院敛财的“小白鼠”,致使病情越发严重,最终丢失了性命,而父亲也在公司警的逼迫下也吞枪自杀,成为孤儿的托比为了生存不得已打工存活。而“男权制”社会下女性的身份地位十分低下,在社会中没有任何话语权,成为隐形的“他者”,托比正处于这样的境地,失去父母的托比要么依靠出卖肉体谋生,要么成为廉价的劳动力。托比为了不沦落为靠出卖肉体为生,她找了份促销的工作。在促销工作中,“而且她(托比)无法忍受自己装扮成熊、老虎、狮子和其他能够听到在自己脚底下被屠杀的濒危动物。于是她直接不干了。”[1]女性和自然无法分割,她们相互依赖。“在她(阿特伍德)的笔下 ,女性几乎天然都有对自然的亲近 、和谐 。女性作为孕育的母体 ,与自然有天然的关联 ,女性天然能从情感上达到对自然的认同与喜爱。”[6]
另一方面,托比受到“男权”代表弗兰克的压迫。后来,托比选择成为废市“秘密汉堡”的服务员。在“秘密汉堡”店,虽然托比每天都可以有两个免费的汉堡吃,但是弗兰克不仅在每日午休时间让托比为他提供性服务,还辱骂压榨托比,致使托比走投无路,在一次园丁游行中加入了屋顶花园。卡罗尔 · 亚当斯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阐释了人类屠宰动物与压迫女性的共同统治逻辑,指出了被“肉”化的动物与被物化的女性之遭遇的相似性。在男权制文化压迫女性的语境中,女性则被父权制从男性的需要的角度加以物化,她们具有完整人格的个体“人”的原有指涉也被迫缺席。[4]在小说中,托比和被宰杀的濒危动物的遭遇一样,原有的指涉被迫缺席,成为迎合男性需要的“物”,沦为弗蘭克泄欲的工具。
三、“男权制”社会下托比的生态女性意识的觉醒
加入园丁队伍的托比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以前,身处废市的托比涂指甲油,花精力护肤,陷入毒品掀起的狂欢里,在“秘密汉堡”每日都会吃两个汉堡……加入园丁队伍后,“花园一点也不像传闻言的那样……这有活泼的蝴蝶,附近有蜜蜂震动翅膀。”[1]“屋顶花园”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托比接受了园丁所倡导的素食主义,戒掉了肉类、每日只吃黄豆小食和甜甜圈、清洁生态厕所和为“生命之树”自然物材交易会包装蠕虫……通过对比托比在废市和屋顶花园的一系列行为来看,托比的生态意识不断觉醒,在屋顶花园这个大环境下渐渐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西方传统思维中,上帝即“男权制”的代表人物,上帝的形象和语言无一例外都是男性的。在小说中写到努埃拉告诉托比不要再剪短发了,女园丁都留长发,穿大口袋似的黑衣服。托比问及原因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是符合上帝的审美情趣。而在托比看来,女园丁努埃拉的行为方式早已受到了“男性”统治社会的熏陶,这里托比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无水的洪水暴发后,托比走出安诺优美容院回去找父亲留给她的来复枪正是托比女性意识彻底觉醒的表现,一方面托比不畏洪水所带来的瘟疫,带齐装备走出美容院去寻找能自卫的枪支,彰显出托比的女性智慧和勇气;另一方面,“男权”统治的大院不允许公民私藏枪支,托比的这一行为是对男权的公然反抗。所以小说中托比问努埃拉的话语及寻找来复枪自卫的行为都彰显了托比女性意识的觉醒。
四、“男权制”社会下托比的反抗
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自然孕育大地上的一切,女性也为人类孕育新的生命。女性同自然一样处于被统治的“他者”“边缘”“失语”地位,承受了沉重的压力。在这样的男权社会里,“女人要么仅仅是一个不具人格的对立物,要么就被动地屈服于男人的意志”。[6]在“二元论”中,女性处于感性、弱者的地位,而男性则是理性和智慧的代表。
小说中的托比恰恰与“二元论”下的传统女性不符,在小说中,托比一直在用“女性”的智慧去反抗男性带来的压迫,并与自然和自然中的动植物和谐相处。前面探讨了“父权”代表弗兰克对托比的压迫,而托比并没有像多拉一样坐以待毙,在亚当第一的鼓动下,她勇敢地伸脚踹了弗莱克并随亚当第一和游行队伍离开废市。加入了园丁队伍后,弗兰克找“屋顶花园”的托比复仇时,“托比看到一道闪光:是玻璃?弗兰克快要抓住她了:挡在他和她之间的只有蜂巢”;“蜜蜂倾巢而出,发出嗡嗡的怒吼,剑一般的朝弗莱克射去”。在这个小片段里,托比和自然中的蜜蜂联手击败了弗兰克,这一行为彰显了托比对于“父权”的反抗。而蜂巢也在这次战斗后元气大伤,这些正印证了生态女性主义中强调女性与自然有着天生的联系,女性同自然一样处于“他者”地位。托比的言行告诫人们女性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结合大自然来扭转这种局面,对抗“男权”势力。后来她教孩子们学习各种草本植物的知识,并在皮拉死后接替了皮拉的位置成為“夏娃第六”。无水的洪水暴发后,地球变得一片狼藉,人类也面临被灭绝的危险,托比则以安诺优为根据地,打造自己的亚腊拉(《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最后停靠的地方),最后还凭女性的智慧救下了瑞恩、阿曼达和吉米。
五、结语
陈秋华指出,阿特伍德的作品往往以女权主义、民族主义与生态主义三大主题之一为主,其他为次,相互交错融合,[5]《洪水之年》正是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相结合的佳作。本文从托比的角度出发,结合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探讨了“男权制”对托比的压迫,托比生态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托比的对“男权制”的反抗,从中可以发现女性与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女性和自然在“男权制”社会中都处于“他者的边缘地位”,女性可以结合自然的力量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小说里蕴含的生态危机,给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 · 阿特伍德.洪水之年[M].陈晓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2]吴琳.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与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Francoise d’Eaubonne.”Feminism or Death”,in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eds.New French Feminism:An Anthology.New York:Schocken Books,1981:64.
[4]韦清琦,李家銮.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交叠性研究思想的范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0,(02):111-120+150.
[5]陈秋华.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主义解读:表现、原因和出路[J].外国文学研究,2004,(02):56-62+171.
[6]纪秀明.阿特伍德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06):55-57.
[7]波伏娃.女性的秘密[M].晓宜,张亚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
宋淼淼,女,河南范县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