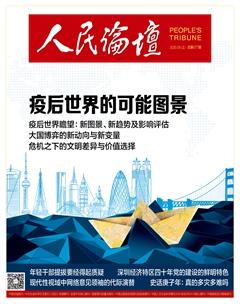“信息流行病”的产生、传播与治理
邓向阳

【关键词】“信息流行病” 传播机制 传播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新兴媒体的快速发展使信息量以指数函数的速度急剧增加,推动社会进入信息过载时代。这些过载的增量信息中,大量的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无用信息和有效信息交织在一起,鱼目混珠,皂白难分。尤其是那些虚假信息,因其天然的欺骗性、麻醉性、煽动性,更易于让人们接受、认同和扩散。相关研究表明,信息过载会引发“信息焦虑合并症”“信息疲劳综合症”“传播焦虑与恐慌”等“病症”,成为信息化时代如影随形的“信息病”。这些“信息病”具有潜伏性、感染性、传播性和可激发性,可因突发事件通过网络空间得到快速传播,从而形成具有流行性和破坏性的“信息流行病”。“信息流行病”带来的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容易导致群体极化和社会心态失衡,甚至掀起舆情风波,成为引发社会风险的巨大隐患。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流行病”造成的恐慌情绪,以及传播不正确的防疫方式,不仅造成巨大的信息资源浪费,还增加了社会防疫成本,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信息流行病”是信息化时代个体和社会负面情绪的传播学表现。因此,挖掘“信息流行病”的生成机理和传播规律,制定有效的传播治理措施,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信息流行病”的生成机理:信息过载和信息不确定性的叠加作用
信息过载的概念最早用于组织管理研究,后在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得到运用,并逐渐得到学界的广泛认识。信息过载是指人们的信息需求超过了个人或系统处理信息的能力,导致信息处理效率下降的现象。随着智能技术和信息化的推进,信息特性嵌入人们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全天候在线”获取信息成为普遍现象,信息过载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
当个人无法处理过载的社会信息时,信息不确定性及其风险也随之而来。不确定性是指人们事先不能准确知道某个事件或某个决策的结果。信息不确定性归因于信息不完全性的客观因素,以及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等主观因素。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人们难以认知未知信息,或者无法辨别真假信息,因而難以预测个人行为的风险。为了降低信息不确定性及风险,人们会选择去获取增量信息或筛选存量信息。然而,当信息处理能力低的所有个人都依赖于现代网络媒体来解决信息不确定性时,信息的平庸化(重复信息)和噪音化(虚假和无意义的信息)将更进一步加固信息的不确定性,从而形成信息过载和信息不确定性的恶性循环。
多重循环之后,焦虑、倦怠,甚至恐慌等消极情绪也随之产生。就社交媒体而言,有关报告显示,大多数用户感受到了社交媒体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受到信息环境影响丧失分析能力、不断搜索更多信息、倦怠焦虑与失眠状况加剧,或受到媒体影响产生负面情绪等。当人们因焦虑、恐慌而在网络上疯狂刷屏时,“信息病”已然形成。而且,这些“信息病”会通过可构建虚拟关系的媒体在人群内外得到扩散与传播,发展成为像流感一样可以传染和传播的“信息流行病”,并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呈爆发态势。例如,当专家确认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之后,人们因无法认知新型冠状病毒这个未知信息,试图通过网络媒体来确认。但是,人们发现获取的信息越多,越无法确认病毒的相关信息。因此,人们开始带有焦虑和恐慌情绪疯狂地在网络和社交平台刷屏和灌水,海量无用的、虚假的信息涌入人们头脑,潜伏的“信息流行病”也因此被激发。
“信息流行病”的传播机制:虚拟网络社交关系的连接
医学领域的流行病感染模型将研究对象分为易感者(Susceptible)和感染者(The Infected)两类。“信息流行病”同样存在感染者和易感者,感染者生产或传播“信息病毒”,易感者感染“信息病毒”。在现代网络社会,感染者通过媒体使用产生的事实和意见,以“信息留痕”的形式将“信息流行病毒”散播于信息环境之后,通过网络社交加速扩散和传播。
“信息流行病”在网络空间中进行扩散是个人出于信息需求参与传播导致的后果,当人们仅依靠自身无法解决信息过载问题时,会通过网络社交关系寻求解决。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将人际关系分为强连接关系、弱连接关系与无连接关系三种。强连接关系的特点是人们的相似性、认知平衡比较强,依赖强烈的情感因素进行维系。弱连接关系的特点是人们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较远的社会距离。在现代网络社会中,人们通过面对面传播、微信朋友圈、微信群传播等方式构成强连接关系,通过论坛、贴吧、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构成弱连接关系。在强连接关系中,因亲戚朋友的接近性,使得微信朋友圈、微信群中的虚假信息更难以辨别;在弱连接关系中,弱社交平台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通过公共议题,聚焦矛盾与冲突,并以热搜的方式不断抢占人们的注意力,传递“信息流行病”。因此,强连接关系和弱连接关系构成的复杂多元的社交关系,让“信息流行病”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产生“交叉感染”。
无论是强连接关系还是弱连接关系,“信息病毒”都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在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中扩散。美国新闻评论家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是媒体在人与现实环境之间插入的信息环境,它并非是客观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经过媒体加工筛选后的模拟环境,但人们往往忽略媒体的选择加工,而当作真实环境接受。媒体对异常事件、冲突事件的过度关注,无意中放大了客观世界中的负面情境,造成“拟态环境”不同程度的失真。本就具有传染性和情绪破坏性的“信息病毒”在这种失真的拟态环境中的扩散与传播就更加肆无忌惮。出于“搏眼球”与追逐流量的目的,媒体“脸谱化”“标题党”“贩卖焦虑或悲苦”、过度煽情等一系列行为大行其事,成为散播“信息流行病”的主要手段。据研究显示,构成网络热点事件的报道有72.22%以“标签化”报道形式出现,其中,72.31%是负面标签。这种简单化的归类弱化了受众认知,并且容易迎合商业逻辑,形成传播偏见,产生群体极化的隐患。例如,类似于《摩拜创始人套现15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这类文章曾引起“青年焦虑”大讨论,引发人们对于个人生活方式的反思,增强了人们对于“信息流行病”所产生的不良情绪的感知。
信息化时代,人们在公共媒体中失语的状态被改写,人们的情绪状态从“后台”走向“前台”,这也使“信息流行病”甚至以“可见”的方式在媒体的拟态环境中得到扩散和传播。人们一边感受不安,一边制造和传播焦虑。在网络社交关系中,许多意见领袖恶意营销、操纵舆论,掀起网络骂战,或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内容与歪曲的价值观,将焦虑、不安等“信息流行病”病源通过浏览、转发与评论的方式向和其有着虚拟社交关系的易感染群体蔓延。而且,许多媒体还将与其有着关系连接的人群作为“媒介商品”出售,采取“流量返现”的模式与利益挂钩,进一步推动“信息流行病”在网络社交关系中的扩散与传播。
“信息流行病”的治理模式:多主体的全过程协同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大众传播时代信息源单一、互动性低的局面。网络就像“无影灯”,政府若单凭封锁信息、屏蔽关键词等措施来阻止“信息流行病”的传播,不仅难以达到治理的目的,而且还会损害政府公信力,甚至加剧人们对于“知情权”与“表达权”被剥夺的恐慌,催产次生舆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善于学习和运用互联网。其中,最关键的是将“管制”思维转变为“治理”思维,打破传统“大家长式”的一元管理模式,搭建多主体、全过程的协同治理模式。
首先,加强信息透明公开,切断传染源。“信息流行病”因人们的信息处理需求与信息处理能力供给不平衡而产生,只要切断信息传染源,给人们提供已经处理过的真实信息,就可以降低人们处理信息的成本,实现需求和能力供给的均衡。当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传播渠道不畅通或者功能减弱时,集合行为中别有用心者就会利用人群的亢奋情绪和能量散布谣言,引发恐慌。根据奥尔波特流言流通量公式,流言的流通量与问题关联度、社会成员的不安感和环境的不确定性成正比。其中环境的不确定性指由于权威信息渠道不畅通或公信力缺失所导致的信息紊乱。在“信息流行病”日常生活中的潜伏期,政府与官方媒体应当树立服务意识,不断提高提供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硬消息”“硬新闻”的供给能力和效率,减少因信息不确定产生的负面情绪。在“信息流行病”突发公共事件时的急性发作期,政府保证信息透明公开,就能及時遏制谣言的传播,从源头上切断恐慌情绪的蔓延。
其次,主流媒体与市场化媒体分工协作,减少信息传播中的变异,净化信息环境。在全媒体传播格局中,形成了主流媒体与商业化媒体、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的结构分层。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同的媒体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职责。主流媒体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打造服务型媒体,以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为重点,传播社会理念,凝聚共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以《人民日报》等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较早介入疫情相关信息传播,并通过微信推文、短视频、漫画等形式对疫情情况进行报道。而市场化媒体也深入一线调查、采访,通过多渠道信源丰富了公众对于疫情一线真实情况的了解,这些报道的出现作为官方信源的及时补充,带领公众更加理性、客观面对疫情,同时也进一步促进官方疫情状况通报的透明化。当然,也应当防止某些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过于刻板,或者通过充满强烈冲突意味的仪式化报道来过分煽情,脱离了报道实际与初衷。总而言之,媒体在报道过程中要贴近实际,贴近人们的真实需求,用媒体专业素养与道德伦理防止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变异。
最后,个体层面提升媒体素养,提升信息处理能力,增强个人自身的免疫能力。媒介素养是信息化时代个人应当具备的媒体接近、信息处理与判断能力。面对超负荷的过载信息,人们在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上应当提升自觉,从控制信息数量与辨别信息质量两方面入手降低感知成本。对于过量信息确立优先级,有选择地接受与自身关联度较强的信息,提高获取有效信息的效率,避免因为被动地在信息潮中“随波逐流”耗费大量时间成本。增强信息质量辨别力方面,应当培养对于信息可靠性、真实性的质疑能力,了解媒体传播规律,多渠道、多角度评估信息可靠性,形成对传播内容的批判思考。同时,降低对于信息获取的“渠道依赖”,在利用媒介获取信息时,防止因算法推送机制造成的“信息茧房”与“意见固化”,减少因轻信或盲从虚假信息、片面信息带来的情感消耗。对于那些处理信息能力较低的“信息流行病”感染者,选择自我“隔离”,切断其他信息来源渠道,紧跟主流媒体,也是一个正确的行为选择。
“信息流行病”是与信息化时代相伴生的负面影响,信息总量的增加与社交关系的加入让传播治理与国家治理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网络环境。“信息流行病”的防治,关键是要立足人们的信息需求,从“管制”思维转变为“服务思维”,发挥多元媒体协同互补的优势,打造一个绿色生态的信息空间,培养有涵养、有理性、有水平的社会公民。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健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20AZD06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王娜、任婷:《移动社交网站中的信息过载与个性化推荐机制研究》,《情报杂志》,2015年第8期。
②陈世华、黄盛泉:《近亲不如远邻:网络时代人际关系新范式》,《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2期。
③仝鹏:《客观性原则下网络热点事件“标签化”传播负面影响研究》,《出版广角》,2016年第17期。
④牛静、常明芝:《社交媒体使用中的社会交往压力源与不持续使用意向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年第6期。
⑤刘鲁川、张冰倩、孙凯:《基于扎根理论的社交媒体用户焦虑情绪研究》,《情报资料工作》,2019年第5期。
责编/于洪清 美编/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