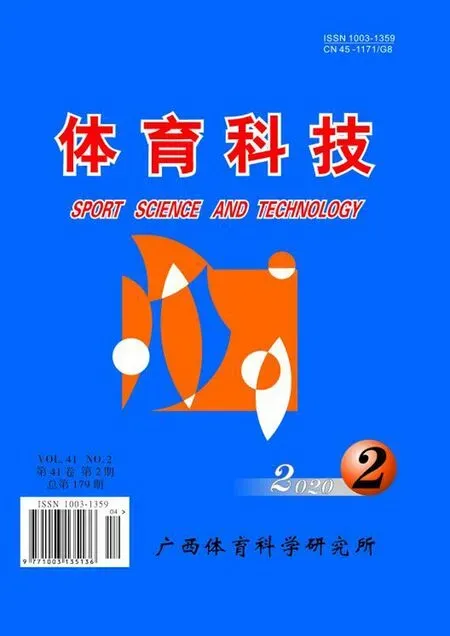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形成的双向实证研究*
谭伟平
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形成的双向实证研究*
谭伟平
(内江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四川 内江 641000)
对三峡巫文化的祭祀舞蹈与峨眉武术的动作内容,以及三峡巫文化灵魂迁徙与峨眉武术养生功法进行双向实证研究。探讨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文化渊源。“巫”“舞”“武”在原始状态下合一同源、差异发展、交融渗透,双方延伸的丰富内容在使用器械、形式展现等方面受诸多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印证了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交互式发展的人类学诊断规律。研究显示:原始人类的身体活动及图腾崇拜推动和发展了原始的宗教文化,三峡地区原始宗教祭祀文化丰富、传承和发展了原始体育活动,在巴蜀地区人类体育活动的开展促生出独具特色的峨眉武术文化;三峡巫文化的祭祀舞蹈与峨眉武术存在一定的同源性及相似性;峨眉武术吸收、传承了三峡巫术祭祀舞蹈内容和灵魂迁徙;峨眉武术对三峡巫文化宗教仪式舞蹈动作的丰富和灵魂迁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研究突破了以前考据和推理阶段,启发了鲜活的文化现实和研究领域。
三峡巫文化;祭祀舞蹈;峨眉武术;实证研究
峨眉武术作为三峡地区特色地域传统文化,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然而关于峨眉武术的起源问题,由于缺乏实证材料,形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格局,甚至有些专家对峨眉武术是否属于巴蜀地区土生土长的地域武术提出质疑。纵观峨眉武术文化的研究文献,几乎都是从资料记载等方面进行推理论证,实地调研的实物佐证研究较少,因此,形成的结论往往难以进行科学论证。除此之外,远古时代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因此,关于峨眉武术文化的文字记载,显然难以支撑原始峨眉武术的萌芽阶段。本文从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文化背景方面进行论述,探寻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的交融与发展情况,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实地调研,论证三峡巫文化祭祀舞蹈对峨眉武术动作萌芽的启发过程,以及利用三峡巫文化中的灵魂迁徙解释峨眉武术养生功的形成。通过讨论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之间的影响关系,进一步解读原始文化遗存,对峨眉武术的形成及源流提供新的认知及思考。
1 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文化的渊源
三峡巫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成时期可追溯到远古时代。长江之水浩浩荡荡贯穿四川盆地奔流向东,在渝东、鄂西地面衔接处切断巫山山脉,形成中外闻名的自然景观——长江三峡,其中巴文化与楚文化成为三峡巫文化的主要文化现象。巫溪县宁厂镇宝源山白鹿盐泉及珍贵药材的发现,为远古时代人类的繁衍及生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原始人类对自然景象的不解,由此产生图腾崇拜及系列神话传说,如“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炎帝神农尝百草”“巫溪盐水女神帮禹治水”等,原始人类的身体活动及思维方式,推动了原始宗教文化的发展。三峡地区作为巫文化的摇篮,在远古时期形成了“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巫文化思想,进而发展为巫教。巫教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鬼教、娘娘教及苗教等,后来鬼教逐渐演化成道教。
峨眉武术作为巴蜀地区特色的传统文化,受宗教仪式和宗法氛围的影响,形成了“佛”“道”文化为其精神核心,讲究以柔制刚、清静无为,文化底蕴深厚,对健身、养生都有着良好效果的特色武术文化。关于峨眉武术的起源说法较多,有“白猿起源说”“少林起源说”“巴蜀起源说”“三大起源说”“尼姑起源说”“道姑起源说”“佛道起源说”等。无论哪种起源学说,都表明峨眉武术与峨眉山具有密切的关系,与宗教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且属于巴蜀地域独具特色的武术文化。
通过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文化背景的对比可见,三峡巫文化作为原始知识分子的雏形,对三峡地区文化的推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峨眉山宗教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峨眉武术与三峡巫文化文化渊源同流,对峨眉山宗教文化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 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的交融与发展
2.1 巫舞与武术的同源及差异
巫、舞、武在原始状态下是合一的。祭祀文化作为三峡巫文化的主要内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针对不同的祭祀文化,有不同的祭祀舞蹈。而巫术中的舞蹈与武术在原始状态下是同源的。因此,舞蹈与武术也被称为民俗文化的“双壁”。舞武作为一种训练形式,虽然能够展现出一定的文化特征,但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舞蹈的艺术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其实用性占主导地位,因此武术与巫舞并没有分开。商朝的武舞多用于祭祀与庆典,当时人们经常跳武舞求雨、祭社稷。据文献记载:“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以达旦,前歌后舞,假于上下。”这种歌舞既有舞蹈的魅力,令士兵斗气昂扬,同时也有武术的攻防技击。由此可见,巫舞与武术关系密切,衍生同源。
巫舞与武术在原始状态下虽是同源的,但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巫舞与武术虽来源于生活,但巫舞是人体情感的表达,有开心庆祝的、忧伤沉郁的、祈祷保佑的等,表达的是人的追求与愿望,因此,它不完全是对生活动作的简单临摹。武术则是三峡居民在生活中总结的生存技巧,以攻防技击为基本属性。三峡地区高山耸立、丛林密布,猛兽较多,居民通过生活中与猛兽等的搏斗,总结出具有技击内涵的技巧动作,因此,武术体现出攻防进退、刚柔虚实的规律和技击内涵。
2.2 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的交融
武术作为民族生存和种族优化繁衍的原始重要手段,与巫文化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关于舞蹈、巫术、武术等的研究者在探索这些文化形态的萌芽及初期状况时,得到的材料几乎是原始人类生活的统一材料。有学者认为峨眉武术与三峡巫文化共同汇成了巴蜀人生活、娱乐及斗争的主旋律,具有一定的同源性并且交融发展。如三峡地区著名的东巴跳、端公舞等。东巴跳是在巫教信仰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民族武舞,有的学者认为其为舞蹈,有的认为其为武术,还有的则认为其即是舞蹈又是武术。随着社会发展和战事的需要,武术作为战争的重要技能被重视起来,而后作为一支独特的璀璨文化传承下来。其中,武术内功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名的拳派都有自己独立的内功体系,武术内功的主要内容就是气功,而气功在巫文化的灵魂迁徙论中得到重要体现。峨眉武术作为三峡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要元素,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当地人民的文化心理。同时,峨眉武术作为民族生存、种族优化的手段被三峡巫文化所吸收,使三峡巫文化的内容得以充实,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在历史岁月长河中不断影响、不断发展,成为三峡地区重要的特色文化。
3 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的双向实证研究
为了探寻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的关系,本文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峨眉武术在使用器具方面、身体形态动作方面进行研究,找出三峡巫文化对峨眉武术的影响,再通过峨眉武术中的动作与三峡巫文化中祭祀舞蹈的动作的对比,用三峡巫文化中的灵魂迁徙论来解释气功,找出其相似性,由此推断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的具体关系。
3.1 三峡巫文化中的器具与峨眉武术器材对照
三峡巫文化的祭祀文化中,除了身体形态动作之外,还包含了许多法器,这些法器的形态、功能、用法与峨眉武术有一定的相似性。

三峡巫文化祭祀种类较多,如跳端公、告阴状、化九龙水、请七仙姑、请桌子神、神兽舞等,每个祭祀的内容对应着不同的法器,法器的种类也十分丰富,有牛角、彩带、打神鞭、服装、刀、弓箭等。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崇拜,因此,巫文化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及神秘性。由于不同祭祀内容需要配以不同的法器,这些法器对后来峨眉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祭祀是假想有敌人或魔鬼的情况下,通过身体的动作进行对抗;而武术则是在社会实践中,通过不断的搏斗、厮杀,总结出来地具有技击含义的实用动作,因此二者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在器具使用方面也具有较多相似性。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生活的需要,有些器具不断地被改进、创新,成为现今峨眉武术独特的器材。总之,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在器具使用上具有紧密的联系。
3.2 三峡巫文化祭祀动作与峨眉武术动作对照

三峡巫文化在身体形态动作等方面也与峨眉武术的动作有相似之处,因篇幅限制,只列出其中部分动作进行对比。
通过上图的对比可以看出,三峡巫文化的祭祀动作与峨眉武术是相融发展的,巫术祭祀内容对峨眉武术的基本步法、攻防技击、器具使用、练功方法都有重要的影响。比如,三峡巫文化中的基本步法,涵盖弓步、马步、仆步、跳步等,这些步法仍然适用于峨眉武术;三峡巫文化中刀法的使用,涵盖劈、砍、撩、刺、缠头裹脑等动作;三峡巫文化祭祀动作中身法的灵活转变,对峨眉武术的闪转腾挪、灵活多变具有一定影响。此外,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的些许动作具有相似性和同源性,而且三峡巫文化的祭祀动作处处体现原始宗教的本职意蕴。可见,具有宗教仪式的祭祀动作与峨眉武术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密切关系。
3.3 峨眉武术与三峡巫文化的延伸及丰富内容
灵魂迁徙说是三峡巫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原始人类认为世间万物都具有灵魂,这种灵魂能够独立存在或者能够移入人、动物和物质对象的体内,而能够运行这些方法的对象只有巫师,驱鬼、招魂、降魂附体等都属于灵魂迁移的现象。采用灵魂迁徙论解释气功不难发现,气功被认为是一种追求长生或获取超自然能力的一种修炼方法,似乎这种修炼的方法与武术内功更为接近。据资料记载:道教在汉魏时期已经传入峨眉山,众道士居于洞穴修炼道术,把养生术作为一种修炼长生不老的手段,因其终极目标是追求今生今世得道成仙,因此,在道士们练习养生术的过程中加入“吐纳、导引、坐忘、心斋、守一”等内炼法门,使心灵与气息达到高度统一,最终达到“意与气合、气与神合”的境界。这种气功与武术融合,成为峨眉武术的一部分,即所谓的“峨眉武术养生功”[7]。峨眉武术与“气功”、“气功”与巫文化的这种交集关系无形之中使气功在三峡巫文化的依托下被峨眉武术所吸纳,可见峨眉武术是三峡巫文化的延伸,丰富了三峡巫文化的内容。
4 结论
原始人类的身体活动及图腾崇拜推动和发展了原始的宗教文化,三峡地区原始宗教的祭祀文化如东巴跳、端公舞等,丰富、传承和发展了原始体育活动,人类体育活动的开展在三峡地区促生出独具特色的峨眉武术文化。本文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三峡巫文化与峨眉武术动作组合进行对比,认为三峡巫文化的祭祀舞蹈与峨眉武术存在一定的同源性及相似性,具有巫术性质的祭祀舞蹈与峨眉武术动作相互交融发展,并赋予其原始的宗教文化。三峡巫文化促生了峨眉武术文化,峨眉武术的动作和独特的运动形式丰富和完善了原始宗教仪式舞蹈的外在表现形式。本研究突破了以前考据和推理阶段,启发了鲜活的文化现实和研究领域。
[2]邢程.大武术观视阈下峨眉武术发展现状及路径[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31(4):52-55.
[3]王亚慧,代凌江.试论峨眉武术的起源及对“白猿起源说”的质疑[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36(5):51-54.
[4]胜瑞东.巫术对传统武术套路影响的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2007(3):39-41.
[5]张扬.试论武术、舞蹈、巫术的交融与发展[J].大众文艺,2011(3):233-234.
[6]韩玉姬,王洪珅.峨眉武术养生文化初探[J].搏击·武术科学,2014,11(2):27-29.
[7]王校中,谭广鑫.武术演进过程中原始巫术的影响[J].体育学刊,2014,21(5):127-130.
Two-way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Wu Culture of Sanxia and Emei Martial Arts
TAN Weiping
(Neijiang Normal College, Neijiang 641000, Sichuan, China)
四川省社科联、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项目编号:TY2018305)。
谭伟平(1968—),本科,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训练。
———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