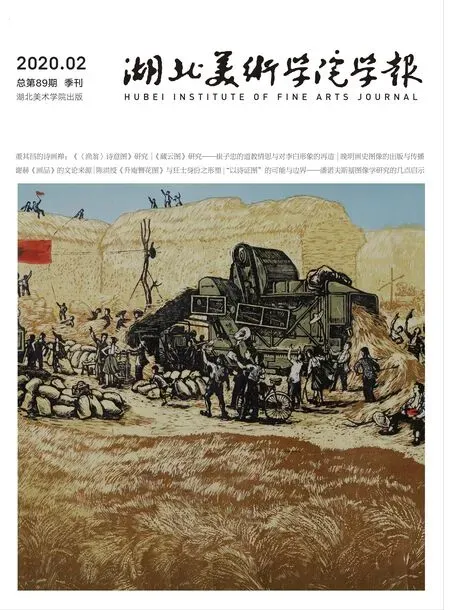《藏云图》研究
——崔子忠的道教情思与对李白形象的再造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 邢陆楠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崔子忠款《藏云图》轴,绢本设色,纵189 厘米,横50.2 厘米,为窄幅高轴。作者于画面左上自题:“丙寅五月五日,予为玄胤同宗大书李青莲藏云一图。图竟而烟生薮泽,气满平林,恍如巫山,复恍如地肺。昔人谓巫山之云,晴则如絮,幻则如人,终不及地肺。地肺之山云祖也,春峦峦不辨草木,行出足下,坐生袖中,旅行者不见前后。史称李青莲安车入地肺,负瓶瓿而贮浓云,归来散之卧内,日饮清泉卧白云,即此事也。崔子忠。”钤“丹仙骨”朱白文方印、“家住三城二水滨”朱文方印,起首钤“画心”朱文方印。右侧裱边处有两方梁清标的鉴藏印,分别是“苍岩”朱文方印、“棠村审定”白文方印。丙寅为明天启六年(1626 年),此作是目前所见崔子忠有纪年的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
图中上下皆为山石,岩体突出如瘤状物,画家以细密的横向墨线皴出山石质感,其上再以浓墨点苔;而在画心中部,占据画面近三分之一的是李白将要贮藏的白云,画家以水纹状线条勾出,循环往复,表现了云雾的轻盈飘忽及流动感。下方坡道上,李白正与二位仆从向白云行走,其中李白蜷腿坐于四轮圆盘车上,双手拱起搭在凭几之上,仰头目视白云,若有所思,一仆肩扛竹竿,上挂瓶瓿,左手指云,回首示意主人白云所处;另有一仆双肩背绳,绳系圆盘车,正躬身牵车而行。在中心人物的背后,可见山间垂下的瀑布,从顶峰处一直断断续续绵延至画面下方。作为此图所要表现的主体人物,李白的形象在画面中占比例很小,但画家通过一些视觉的营造技巧,将观者的目光拉至人物身上,如以较浓重的墨色表现处于上下两端的山石、树木,在此衬托之下,白云的淡与轻就显得很具说服力,而这团云雾的形状又由上至下进行缩回,直至末端形成了一个指向性的箭头,正对李白和两位仆从。
据崔子忠的题文可知,此图描绘的正是李白赴地肺山以瓶瓿贮藏浓云的传说,在这一传说中,李白贮云归来后又将所藏之云“散之卧内,日饮清泉卧白云”。然而,就目前所见有关李白的传说记载中并无“地肺藏云”一事,画家似乎通过绘画讲述了一个关于李白的罕见传说,而题文中所涉及的“地肺山”又具有明显的道教色彩。画家以此图赠“玄胤同宗”是否借此表达了更深层的意涵?这是否与画家本人的思想观念或信仰有关?本文通过分析画家题跋中所透露的信息、李白在明代世人心中的形象,以及崔子忠的信仰、交游等情况,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地肺山的道教色彩

藏云图轴 崔子忠
在《藏云图》的题文中,崔子忠提到了一处地理名称“地肺山”,他在文中是这样描述此山的:“烟生薮泽,气满平林,恍如巫山,复恍如地肺。昔人谓巫山之云,晴则如絮,幻则如人,终不及地肺。地肺之山云祖也,春峦峦不辨草木,行出足下,坐生袖中,旅行者不见前后。”按地肺山正是道教“洞天福地”体系中被列为“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一地。所谓洞天福地,简言之即是位于现世名山中的人间仙境,由神仙及真人所居住,若修道者居此修炼或请乞则可得道成仙。
就道教而言,其最核心的内容便是神仙信仰。有学者曾指出,“作为宗教来说,道教的情况复杂,前后不一,派别甚多,主张各别。但从总体上讲,服食丹药,追求长生不死和修炼成仙却是它思想的核心。”[1]其他如老庄哲学、符箓禁咒、斋仪修持、威仪戒律,或为文饰其教,或为迷信手段,多围绕这一核心思想展开。同时,道教认为求仙有术,想要得道成仙,需要勤修苦练,但由于术法或修炼手段的高低难易,以及阶级社会等级观念在神仙世界中的反映,仙界也派生出许多等级,早期一般将仙分为天仙、地仙、尸解仙,如:“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2]后期的神仙类型更加繁多,但基本不出上、中、下三个等级划分方式。其中等级略低的地仙,便是洞天福地的主要居住者。
作为道教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洞天福地实际包括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其内涵即在人类所栖居的现实空间中(即“大天世界”),并存着三十六所相对隔绝、大小不等的生活世界,以及七十二处特殊地域,这些洞天福地大多位于中国境内的大小名山之中或之间,且由于它们位于我们所处的空间中,因而与我们的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3]正是由于这种相对隔绝、隐蔽的神秘感,且在现实中可以到达的真实属性,使洞天福地成为了人与仙之间的沟通桥梁,也成为了修行者梦寐以求的修炼场所。①
据《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的“七十二福地”所记,“地肺山在茅山,有紫阳观,乃许长史宅”[4]。可知地肺山即位于今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县的茅山(又名句曲山)范围内;除此之外,地肺之所在另有终南山(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商山(位于陕西省商洛市)、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以及东南海里几种说法。如《史记》集解中的《括地志》云,“终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地肺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5]明人谢肇淛延续此说:“荆州济江西岸有地肺,洪潦常浮不没,其状若肺焉,故名。骆宾王吸金丹于地肺,即此也。或云终南山亦曰地肺,一云太一山。”[6]晋人皇甫谧撰《高士传》则言,四皓于“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共入商雒,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7]宋代僧人释赞宁在《东坡先生物类相感》中提及救穷草时,说它在“武当地肺山西角有大松树下生,不枯,日食三寸可以绝谷也”[8]。东南海里说则为“《玉环山舆地志》云:乐清东南海中有地肺山,一名未陋山,去岸百余里,周回五里,中无蛇虎,旧有居民,今空而湖田宛然疑此是也。”[9]
不论其具体地理方位如何,早期文献中关于地肺山的记载多与隐逸、长生不老等思想有关,而在洞天福地系统确立后,地肺则进一步与福地修仙的概念相结合了。据载,曾经居住在地肺山(茅山、商山、终南山)的隐士或者仙人包括四皓、凤纲、李常在、谢允、许长史(许谧)、陶弘景、彭君与王重阳等。在这几个人之中,四皓为避秦乱世而隐居商山,其余诸人除王重阳以外,则皆以肉身成仙后入山,凤纲“常采百草花,以水渍泥封之,自正月始尽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丸之,卒死者以此药内口中,皆立生纲长,服此药得寿数百岁不老,后入地肺山中仙去”[10]。李常在“少学道,人世世见之,计已四百岁而不老,每娶妇有儿乃去,去后三十余年,人见在地肺山”[11]。司马永祯在《天地宫府图》中提及第一福地时,有言“(地肺山)昔陶隐居幽栖之处,真人谢允治之”[12]。《云笈七谶》另有“彭君服之寿七百七十九岁后入地肺山去,不知所在”[13]。以上几位均可被视为地仙,而王重阳则略有不同,他是选择入终南地肺进行修行的道士,他在修道后舍妻弃子,且“故以猥贱语詈辱其子孙,其末后句云:相违地肺成欢乐,撞入南京便得真”[14],后更以地肺王重阳自称。
这一现象与福地概念的发展可以相互对应上,按福地与洞天是洞天福地学说的两大核心概念,但从现存文献考查,福地的概念出现较洞天更早,早期道经《道迹经》即谓:“句曲山(即地肺山)居月弗地,必度世,见太平。”《文选》载晋孙绰《游天台山赋》有“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之句,[15]葛洪《抱朴子》亦有言道:“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为此也。又按《仙经》可以精思合作仙药者,有华山、泰山……地肺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难,不但于中以合药也,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神必助之为福药。”[16]可见早期的福地或弗地、福庭便是具有度世太平、使人不死之功能的,后期道经如《南岳九真人传》则更关注于福地与修行之间的关系,“修道者若非其地,如植五谷于砂石之间,则不能成矣。虽有升飞之骨,当得福地灵墟,尔后可以变化。虽累德以为土地,积功以为羽翼,苟非其所,魔坏其功,兹道无由成矣”。文中将修道择地与农夫播殖相提并论,可见修道之人对于福地的重视程度。[3]因此,地肺山作为七十二福地之第一地,特指适合修炼的太平地域,可避兵灾大难,更可使人长生不老,同时它也是一些中级仙人——地仙的居住地,因而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并且附带有隐逸的寓意。
虽然尚未见到李白关于地肺山的直接描述,但是唐宋时期的其他诗人对于地肺是有诗文涉及的,如唐人温庭筠便有《地肺山春日》一首:“冉冉花明岸,涓涓水绕山。几时抛俗事,来共白云闲。”宋人陈深作《送刘梅溪游句曲》,对句曲也即地肺山的描述是:“天心桥畔行将老,地肺山中隐去休。半岭白云容可玩,一庵明月尚空留。”均对于山中白云有特别的描述,然而他们都是作为现实世界中的游客对山中云雾进行咏叹,能够藏纳地肺之云于瓶瓿中的李白显然超越了凡人的属性,他在其中究竟承担怎样的角色呢?
二、李白形象的仙化
作为《藏云图》的主要角色,在崔子忠的语境中,李白已然进入到了洞天福地的境界之中。按照前面的分析,能够进入地肺者或为地仙、或为修道者,而李白在现实世界中道教徒的身份,以及后人所赋予他的仙位皆可助他登临福地。
如前文所言,神仙有等级之别,在民间影响力较大的是天仙、地仙、尸解仙、水仙和鬼仙,其中地仙为肉体直接成仙者,由于无法升天,只能居住于地上的洞天福地之中,《仙术秘库》中说:“地仙者有神仙之才,无神仙之分。得长生不死,而作陆地游闲之神仙,为仙乘之中乘者。”[17]而尸解仙不能以肉体成仙,必须通过死亡进行转化,其形式多样,对应不同的死亡方式分别有有兵解、水解、火解等。在民间传说中,李白是通过水解的方式得以转化成仙的,南宋陈葆光在其《三洞群仙录》卷十五中有记:“《摭遗》子美后说李太白宿江上,于时高秋澄流,若万顷寒玉,太白见水月即曰:吾入水捉月矣。寻不得尸,说者云水解,此神仙之事也。”[18]可见在时人的认知中,李白的死亡是其水解成仙的途径。但同时,李白又符合“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的情况。在《三洞群仙录》卷十中,陈葆光又记载了一则李白成仙后与白居易之孙白龟年的一段对话,“李太白招之与语曰:吾自水解之后,放遁山水间,因思故乡西归嵩峰,中帝飞章上奏,见辟掌笺奏于此,今已百年矣……乃出书一卷遗之曰:读此可辨九天大地禽兽语言,汝更修阴德可作地仙也。”②从这段文字中可知,李白在水解成仙后被派放至嵩山掌笺,甚至可助人修行,从而具备了地仙居住洞天福地的属性。
在《东坡志林》中,苏轼也曾记录过一个关于李白的故事,“都下见有人携一纸文书,字则颜鲁公也,墨迹如未干,纸亦新键,其首两句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语亦非太白不能道也。”[19]这段趣闻在比苏轼略晚的赵令畤笔下则扩充地更为详细具体,“东坡先生在岭南言,元佑中有见李白酒肆中诵其近诗…少游尝手录其全篇。少游叙云:观顷在京师,有道人相访,风骨甚异,语论不凡,自云尝与物外诸公往还,口诵二篇,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白作也。”③李白之诗世人皆可传诵,在东坡面前读李诗并无特别,但关键之处在于这首诗苏轼之前从未见过,因为此诗乃李白死后成仙之新作,文中所言纸墨皆新、墨迹未干,以及某道士不久前从李那里得到,有人见李在酒肆中诵诗均意味着李白业已成仙,且时常往返人间传授逸诗,甚至还获得了正式的仙位——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此仙位得到了当时人的认可,如稍晚的阮阅记述:“元佑八年,东坡帅定武李方叔、王仲弓别于惠济,出示《南岳典宝东华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诗,曰此李真人作也。近有人于江上遇之得此,云即李太白也。”[20]南宋时期的道士白玉蟾也曾有云:“李白今为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白乐天今为蓬莱长仙主。”[21]
李白在死后被不断仙化,一方面与他生前就已经获得的“谪仙人”、“酒中仙”等称号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在现实世界中道教徒的身份有关,两者之间可谓互为驱动。关于李白诗歌中的神仙意向、他谪仙称号的获得、在诗歌中自我仙化的倾向以及求仙访道对于李白的影响,有许多学者都曾做过研究。如松浦友久就在其《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中指出,李白在被贺知章称呼为“谪仙人”后,便逐渐以“谪仙”自居,并且创作了表现其意图的“谪仙歌”;[22]李长之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中表示,道教的五大基本概念道、运、自然、贵生爱体和神仙都处处支配着李白的诗文创作,由此而言太白是一个忠实的道教徒是毫无疑问的。[23]罗宗强则进一步指出,李白所修炼的教派很可能即茅山上清派。[24]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知李白自幼便有求仙访道的行为倾向,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25]、“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26],因此结交了很多“道友”,如东岩子、元丹丘(丹丘生)、元演、紫阳先生、盖寰、高尊师、参寥子等。[23]35以“谪仙人”许之的贺知章也深信道教,二人初见便是在长安的紫极宫中,且李白能够供奉玄宗朝翰林,便得益于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女道士持盈法师)的推荐。而李白在天宝年间所作的两首诗歌《访道安陵遇盖还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与《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则可视为他正式入道的记录,在诗文中,李白提到:“安陵盖夫子,十岁与天通…为我草真箓,天人惭妙工。”[27]盖夫子即盖寰,他为李白造“真箓”的举动,实则是将李白纳入自己的道派,而其高尊师如贵也曾在齐州紫极宫(今山东济南)为李白授箓。修于初唐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对授道箓有明确的记载,按不同的等级需应传授不同的经箓,依次渐进,“参受经戒法箓,须依此次第名位,不得叨谬”。可见,传授者如果不按照被传授者的次第而错传,是有罪的[24],所以李白的两次受箓意味着他在教派中次第的晋升,也意味着中年以后的他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道士。
从凡间的一名道士进阶为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白在世人心中的形象经历了由凡入仙的过程,也由此产生了相应的故事、传说与绘画,如前文所引《南岳典宝东华李真人像》便是一例。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之中,有关李白的传说应当是最多的,这些故事传说有的出自其生平,如李白与酒(高力士脱靴、跨驴入淮阴县、醉写吓蛮书等);有的是基于其生平的演化,如李白与其他名贤的交往(春夜宴桃李园、竹溪六逸等);但其中内容形式最为丰富的当属讲述李白与仙有关的的传说。从李白作为太白星而诞生,到以“谪仙人”的风格作诗,直至他的死亡,也生发有“捉月”与“骑鲸”两个故事,而“骑鲸”又是在“捉月”的基础上产生的,更进一步将李白的形象仙化了。
就故事产生的年代早晚来看,酒类为先,同时期人杜甫即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这样的故事传诵;与仙化有关的传说则在李白去世后开始流传,传为柳宗元所撰的《龙城录》中便讲述有李白跨赤虬仙去的故事,而捉月与骑鲸说是李白死亡百余年才逐渐成型的,至早产生于唐末五代;基于李白生平所演化出的故事则略晚,元明时期为通俗文学所采纳。
明清时期,随着戏曲、小说的流行,关于李白的各类故事有了更加丰富的情节,有时甚至可以互相串联演绎,使李白成为了颇受欢迎的文学及绘画创作题材。从同期相对应的绘画作品来看,其中较为流行的画题为饮中八仙、醉酒、春夜宴桃李园与竹溪六逸,不仅历代皆有描绘,且数量较为集中,这些题目多注重表现李白的酒品与文人属性层面,这或与当时文人喜结社、好雅集有关。崔子忠显然对这一现象有所了解,虽然目前所见关于崔子忠的记载十分有限,但世人对他的“怪”与“异”却多有着墨,同时期人董其昌称他“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常见”[28]。清初人朱彝尊将崔子忠与陈洪绶二人并称,并点评道:“予少时得洪绶画辄惊喜,及观子忠所作,其人物怪伟略同,二子癖亦相似也。崇祯之季,京师号南陈北崔。”[29]乾隆时期的书画家方熏在评价崔、陈二人时,也说他们“僻古争奇,各出幽思”,并且“子忠人物外他画少见”[30]。可见崔子忠在人物画领域是有心僻古且力求险怪的,不满足于人物画的既定画风和题目,他在表现方式上追求与众不同,如以战笔作画,人物形体略作变形处理等,在题材上则追求新奇、高古,所作画题多出自道释、鬼神与新兴传说。
《藏云图》中所讲述的李白故事是世所罕见的,与同时期流行的雅集宴饮中李白颇具烟火气的形象不同,画家截取的是李白仙化的层面,在绘画性质上与“捉月图”和“骑鲸图”比较贴近,后者在明代也是传播较广的图像形式,不仅出现在了人们暑日纳凉的扇子上、客厅的屏风上④,且作为陪葬品出现在了淮安王镇的墓室中。在松浦先生看来,这类传说的魅力在于将李白诗歌的主要题材典型化,对“诗人李白”观念形态方面的认知基调予以可视化、形象化,从而构成了更为鲜明的印象,即李白的超凡脱俗、天才等因素由于他在长江采石矶饮酒、捉月入水溺死而轮廓鲜明。同时在世人眼中,这位天才诗人与他在自家宅中平凡衰老病死的结局不相适应,他应当在酒兴之际同江月融为一体,以保持永恒的生命。[22]306由此而言,传说正是诗人诗风与人生经历的象征,以此角度出发,则关于李白临终以及仙化的传说反映了后人对于李白的印象、评价和愿望。
在《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李白曾提到“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又“紫阳因大夸仙城,元侯闻之,乘兴将往。”[31]文中的紫阳先生胡氏,便是道教上清派的传人,在李白为紫阳所作《汉东紫阳先生碑铭》中,李指出了紫阳的师道传承,即以陶弘景为始的茅山派:“道始盛于三茅,波乎四许。华阳(中缺)陶隐居传升元子,升元子传体元,体元传贞一先生,贞一先生传天师李含光,李含光合契乎紫阳。”[32]除紫阳先生,李白还曾接触过上清派的司马永祯、吴筠与元丹丘,且曾受上清派的影响炼制内丹,这应是李白与茅山即地肺之所在最为直接的关联了。而将李白与地肺、藏云等意向相结合的崔子忠,实则是借助李白的形象传达了个人的认知与情思,背后所蕴藉的是他的道教情结与隐逸思想。
三、崔子忠的生平、交游与道教情思
关于崔子忠的研究目前比较有限,20 世纪70 年代,台北故宫博物院曾挑选晚明丁云鹏、吴彬、蓝瑛、陈洪绶和崔子忠五名画家的作品举办特展,首先对崔子忠的绘画有过一次汇总展览与出版。由于这些画家“盱衡斯世,能不为文(征明)、董(其昌)所覆盖而可以自开新生面者”,因此将他们命名为“晚明变形主义”(展览名称即“晚明变形主义画家作品展”),“名虽非旧,大抵可以概括其义矣”[33]。对于崔子忠作品的第二次全面汇集发生于2008 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南陈北崔——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陈洪绶、崔子忠书画特展》,悉数陈列新编三十卷《中国绘画全集》所收的崔子忠传世作品,几乎囊括了中国大陆的全部收藏,李维琨在图录文章中讨论了“南陈北崔”说的产生,以及清人对崔子忠的评述。[34]
1984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雅兰(Julia Andrews)以崔子忠道教题材作品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初步讨论了崔子忠与道教的关系[35]。2009 年,高居翰在其《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一书中以一节的篇幅介绍了崔子忠的绘画,同时提及了他作为道教徒的可能性[36]。另有青岛农业大学艺术学院的宋磊曾对崔子忠的祖籍进行过分析,认为他出身胶东崔氏,并对他与莱阳宋氏家族成员的关系有所涉及。[37]
崔子忠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母,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十分有限,大多围绕几个信息展开,分别是:侨居都门补顺天府学生员;游董其昌门下;莳花养鱼杳然遗世,兴至则解衣盘礴;一妻二女皆能点染设色;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购请,虽穷饿掉头弗顾;史可法当街赠马,崔氏卖马换酒宴客;宋应亨属人以千金为崔君寿,崔子忠拒受寿金;宋玫数求崔画不许,诱之邸舍,崔子忠不得已作画,后索取碎之;甲申入土室中匿,不出遂饿死等。⑤明清时期有关崔子忠的文献记载大多在这几条信息中相互引用、重叠,而崔子忠的友人王崇简、钱谦益,同时期人姜绍书、吴伟业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信息。
首先,王崇简在“都门三子传”中提到了崔子忠的出身与交游,“其先山东平度州人,嘉隆时有仕至显官者,子补荫留京师,遂家焉,即其祖也。家故饶,万历时上供珠玉诸珍货,率佥京师富民办纳,中官勒抑,费不赀,复不时与直,家以此中落。子忠为诸生,甚贫。于六经无不读,得诸戴礼者尤深。为文崛奥,动则千言……督学御史左光斗奇其才,置高等食饩。及数试而困,慨然弃去不复应试……先是子忠偕蒋生渔郎受业于宋公应(继)登之门”⑥。
由此可知,崔子忠祖上颇为显赫,可率佥京都富民办纳珠玉珍货,只是由于受宦官勒索,资金亏空而家道中落。崔子忠为顺天府诸生时,曾受御史左光斗的赏识,按王崇简与崔子忠同为顺天府学生,先后受知于左光斗,后来崔氏又与左光斗的弟子史可法结识,遂有当街卖马的故实。按左光斗与史可法左与史皆为东林党人,《藏云图》绘制时正值其覆灭,王崇简在崔子忠传中也提到了这一节点:“左公为阉竖陷诏狱,迨毙而归榇,人莫敢近。时史公可法与予皆诸生,受知于公。史公就视于狱,予哭于郊,几不测。子忠曰:‘二生何愚也,不能为魏邵之脱史弼于死,徒效郭亮、董班哭李固、杜乔何益耶?’士自四方来慕其人,多谢不见,人或尤之,笑曰:‘交游盛而朋党立,东汉之季可鉴也。’后果有以复社植党言者,其识力过人如此。”[38]2088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得知崔子忠并不好交游,也慎于结党、社,只是他的友人王崇简为复社一员,他的受业恩师也是山左大社的重要成员,他自己不免也加入了这一组织。据王氏记载,崔子忠受业于宋继登门下,与宋氏子弟多有往来,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之“崔秀才子忠”一节中也提到:“少为诸生,师事莱人宋继登。宋诸子及群从皆与同学,而玫及应亨尤厚善。”[39]宋氏为莱阳大族,而山左大社即莱阳士人为应援复社而成立,成立时间在崇祯二年前后。
据《民国莱阳县志》卷三之三记载:“山左大社九十一人,莱阳除继登父子,有左懋泰、宋珵、赵士骥、姜澜、宋璜……崔丹,实居十六七,栖霞、郝晋亦与斯盟而继澄为之冠。”[40]其中所列之人皆莱阳人氏,除宋氏外,姜氏、左氏均为当地大族,崔丹即崔子忠,位列最后。虽然身为社中一员,但崔子忠似乎仍试图减少与之有“利益往来”,宋应亨遣吏部之人送寿金被崔氏拒绝、宋玫请他作画也遭到回绝。
相比于社员的积极为政,崔子忠更倾向于平淡、闲逸的生活,并乐于隐居,甚至连绘画作品也不肯轻易许人:“人有欲得其画者,强之不可得,山斋佛壁则往往有焉。”[38]2086以至于其作品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存世不足20 件,且创作题材不外乎神仙道释(云中玉女、洛神、许旌阳升仙、李白藏云、扫象)、传说人物(长白仙踪)与儒林轶事(伏生授经、桐阴博古、云林洗桐、苏轼留带),这一现象与他避世隐居的思想是相吻合的。或许是看到东林党覆灭的惨状,以及个人对于党争的疑虑,崔子忠似乎更倾向于以温和的方式介入到现世当中,表现在绘画层面则是对于题材选择的稳定性与倾向性。崔子忠的作品题材颇为固定,他曾多次绘制的题材即“许旌阳升天图”,并且曾在自己的其他作品中提及过许旌阳的事迹,如在现藏上海博物馆的《云中玉女图》中有言:“如曰,许旌阳以五十旅行,虽多亦奚以为。” 许旌阳即六朝时人许逊(239-374 年),曾任旌阳令,因晋室纷乱而弃官东归,传说他于宁康二年举家飞天成仙,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典故的由来(台北“故宫”本即被崔氏命名为《云中鸡犬图》),其崇拜本为民间传说,后为道教之净明道所吸纳。该教派不仅奉许逊为祖师,且从儒家学说当中吸取了孝道一类的道德主体,自宋代以后逐渐成为民间流行的融合性宗教,其宗旨即“以忠孝为本,敬天崇道,济生度死为事”[41],认为恪守忠、孝即可得道修仙,因此又被称为净明忠孝道。“忠孝”本是儒家伦理纲常的核心,但净明道却将之转化为“仙道”的基础,这一理念使其成为明代最具活力的道教宗派,因之坚决地肯定各种儒家价值观,故对于儒家士子十分具有吸引力。⑦这种既能够兼顾儒家伦理道德,又可以修仙得道的主张与崔子忠的想法颇为契合。据各种史料文献所载,崔子忠一直流寓于北京,本名崔丹,或为怀念故乡,或为追求道法,他将名改为子忠以表忠孝之道,而其字道母,或亦出自宋人对于《道德经》的注解,“道有大小,真为道母,众人自道入真,真而后神。至人以神入真,却神返本,故曰:一定之器,真元大朴,真真真申言之者,不杂之谓也。”[42]
崔子忠虽然避免与宋氏子弟进行金钱上的往来,且将宋玫之画撕毁,但他并非一直拒绝为友人作画,据文献所示,崔氏曾为莱阳宋氏绘制过作品,但题材无非是“许旌阳移居图”或“扫象图”,朱彝尊认为崔子忠所画许旌阳如同龚开画鬼,并说“莱阳宋司臬玉叔曾示予《许旌阳移居图》,鬼物青红,备诸诡异之状,几与龚圣予争能”[43],又“扫象图”中具有“扫除着相”的意涵,崔氏以此图赠友或为警示意义。
在晚明绘画当中,避世修仙是一类颇为独特的主题,并在民众当中形成了一定的流行程度,相对于明代中期苏州的城市山林,这类题材的出现仿佛反映了时人正处于兵灾大难之中,亟须解脱之道。而崔子忠在这独特的主题之中,又赋予了画面超脱的景象,按子忠师承姜隐,此人曾于万历朝供奉内廷画院,以构景“萧疏寄情”为名,只是“凝远犹未足以尽其妙也”[44]。崔子忠在老师的基础上,于构图之上更为大胆,在处理布景时,他经常取窄而长的立轴布置山石、烟云,人物、事件则被缩小安排在画面中景的位置上,这几乎是崔子忠必用的手法,罕有例外,而这种若即若离的表现手法十分适用于超越现实的仙灵世界。并且,为了在人物画领域有所突破,崔子忠在常规题材创作时也会钻研创新,并在道释题材中加入现实的考虑,如吴伟业有言:“当时驾幸承天门,鸾旗日月陈金根。鸡鸣钟动双阙下,岿然不动如昆仑。崔生布衣怀纸笔,道冲驺哄金吾卒。仰见天街驯象来,归去沉吟思十日。”[45]生动地记录了崔子忠在銮驾承天门时,怀笔纸观察、记录大象的情景,以为其《扫象图》筹备素材。
同时期人的相关著述和现存的实物作品,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真实生动的崔子忠形象:他出生莱阳世家,文笔崛奥、画风奇古,为人不好交游却颇重情义,能够在东林覆灭之时与史可法、王崇简往来,后又因与莱阳宋氏交好而加入山左大社以应复社;内心怀揣儒家忠孝节义之思,却“数试而困,慨然弃去不复应试”,在避世隐居与忠孝之间为寻得一个平衡点,寄情于净明道的义理之中;作画好道释、传说题材,极少与人,且不为金钱所动,因此存世作品较少。这样耿直孤傲的崔子忠,在甲申之时走入土室饿死殉节,是合乎他的追求与品行的。
四、小结
《藏云图》为崔子忠的早年作品,此时的他已经显露出了对于道教题材的偏好,他在图中营造了一个“李白地肺藏云”的故事,将洞天福地之第一福地地肺山与尸解成仙的李白相结合。此图创作正值明朝天启年间,阉党横行,政治黑暗,而福地“过不逢兵戈之乱,不为豪强之侵,不近往来之冲”的属性正是世人所追求的美好愿景,李白身兼诗人、隐士、道士与仙人数重身份,在明末拥有广泛的社会认同,以此作赠人则具有得道求仙、避世隐逸,甚至长寿不老的多层意涵在其中。而崔子忠本人很有可能是道教净明道的追随者,在儒家忠孝与道家避世之中寻得平衡,反映在绘画作品之中,则是他对于道释类题材的偏好。同时,作为与陈洪绶并驾齐驱的人物画家,崔子忠在创作时力求僻古求新,能够在笔法、构图上大胆尝试,并在同类题材上进行突破。
注释:
①按洞天福地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其理论产生于东晋时期,至唐末五代达成最终形态。从现存文献来看,六朝时期陶弘景(456-536)的著述,唐代司马承祯(647-735)所编《天地宫府图》以及唐末五代杜光庭(850-933)编撰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可视为这一理论的三大重要发展阶段。后两部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了一套沿袭至今的中国名山系统,司马承祯与杜光庭有意识地将自然山水与道教乃至佛教相结合,强化了山就是神仙居所,也即道士们展开宗教活动场所的观念。
②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十,明正统道藏本,407 页。
③赵令畤《侯鲭录》卷第二,清知不足斋丛书本,58 页。
④图像记载见于:明人张岱《自为墓志铭》,“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程敏政《簋墩集》卷六十七、丁养浩《效唐集》卷四《太白骑鲸图》诗、章纶《章恭毂公集》卷六《李白骑鲸扇面》诗。
⑤这些叙述的原始文字出自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第十之“崔秀才子忠”,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4614 页。
⑥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八,清康熙二十八年王燕刻本,2086 页。王氏为于奕正、黄鼐与崔子忠三人作传,因三人皆“以志行闻”。
⑦净明道作为别具一格的整体出现于宋元时期,元人黄元吉编撰了《净明忠孝全书》,作为这一宗派的明确思想表述,强调儒家忠孝诚和正意等儒家价值。该教派在从元末一直持续至明,实际上“净明道”一词不见于诸如《明史》之类的官方材料中,但张宇初在其道教宗派史中却提到了它,而且它还出现于许多明代文人的著述中。净明一词的缺失可能说明该道派被政府官员认为是从属于正一道或全真教的道派。见于[英]崔瑞德、[ 美] 牟复礼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12 月,9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