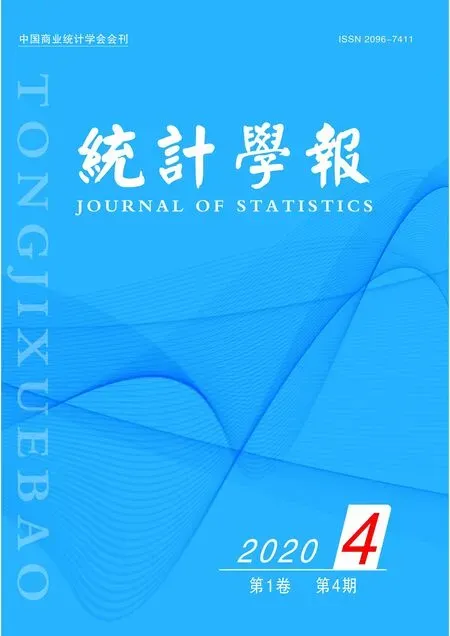收入不平等对中国收入代际流动的影响
孙 旭,魏嘉鑫,方逸茹,邢灵婉
(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收入不平等问题不断加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值为0.479,2008年升至最高值,为0.491,之后又逐渐回落,到2015年降至0.462,2016年又出现回升,2018年升至0.474。由此可见,中国基尼系数已经长期超过国际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的警戒线(0.4),收入不平等问题长期积累正在威胁公平、共享社会的建设。贫富状态在父代与子代间的持续和转换是我们观察社会公平程度的重要视角,理论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可能会通过多条路径影响收入的代际传递,一些面向欧美国家的经验研究也证实了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收入不平等影响中国代际流动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评估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层次影响。而且,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程度与欧美国家不同,故以我国为对象的经验研究有助于增加理论界对收入不平等影响代际流动问题的认识。
二、研究综述
(一)国外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代际流动的相关研究
关注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学者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从业者的小时工资报酬差距和年收入差距特别是家庭收入差距都在增大(Gottschalk and Danziger,2005;McCall and Percheski,2010)[1,2],且近40年来各州之间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等,使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美国民众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在世代间的持续存在倾向是否会加强的问题。一个较有说服力的理论假设是,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强化了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性,增加了个人成年后的收入与其原生家庭收入间的联系。Neckerman和Torche(2007)[3]发现,收入不平等加强了富裕家庭子女在教育等资源分配中的特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子代间的经济收入不平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用累积优势理论解释该观点,认为富人的子代经济背景产生的人力资本累积优势在其从儿童开始后的每个成长阶段都会加剧,具体而言,贫富家庭对儿童护理、教育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显著差异影响了子代后期获取经济成就的能力(DiPrete and Eirich,2006)[4]。
一些实证文献支持高度的经济不平等抑制代际流 动 性 假 设(Beller and Hout,2006;Mazumder and Levine,2002;Aaronson and Mazumder,2008;Wilkinson and Pickett,2010;Smeeding et al.,2011)[5-9]。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Alan Krueger在2012年一次公开演讲中强调,美国社会中存在“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这是一根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曲线的横轴是以基尼系数表示的社会不公平程度,纵轴为代际收入弹性,即父辈的收入水平对下一代收入水平的影响,用以说明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正在危害社会机会平等传统。
然而,也有学者的研究与高度的经济不平等抑制代际流动性的假设相矛盾。对于近40年来美国社会代际流动趋势的判断,Fertig(2003)[10]认为社会流动性不降反升,Mayer和 Lopoo(2005)[11]则认为是社会流动先降后升,Lee 和 Solon(2009)[12]、Chetty 等(2014)[13]和 Bloome(2015)[14]并不认为美国社会流动性出现了大变化。Downey(1995)[15]认为,即使考虑家庭对孩子教育等方面的投资,但投资和收益之间的真实关系并非呈线性变化,因此家庭经济差异也不会出现与代际收入流动性线性相关的情况。McLanahan(2004)[16]也认为,家庭经济背景差异可能会导致子代间的“分歧命运”,但由于国家、市场和家庭对儿童成长及就业机会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造成不平等和代际收入流动性之间的效应在理论上并不确定。Solon和Corak(2004)[17]发现,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可能会使政府为解决矛盾而增加对教育的公共投资,从而抵消家庭投资产生的机会不平等。
可见,为论证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国外学者们不但使用了不同的计量手段和建模方法,而且为增加变量的变异性以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学者们先后考虑了变量在跨时期上的变化(Mayer and Lopoo,2005;Lee and Solon,2009)[11,12]、在跨区域上的变化 (Treiman and Yip,1989;Corak,2016)[18,19]以及在同时跨时期和跨区域上的变化(Bloome,2015)[14],不断深入和扩展相关研究。
(二)国内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代际流动的相关研究
虽然我国代际流动研究起步较晚,但也有学者关注了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代际流动性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面。方鸣(2014)[20]通过分析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1989—2006年六轮七省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既估计了基尼系数对代际收入弹性影响的线性方程,也估计了代际弹性影响基尼系数的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显示代际收入弹性提高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会阻碍代际收入流动。周兴和张鹏(2015)[21]利用多类别logistic模型,通过处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数据,实证分析认为代际收入流动性差异扩大了城乡间收入差距。徐舒和李江(2015)[22]通过分析CHNS1989—2009年数据,利用工具变量分位回归方法对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代际收入流动性对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结果发现代际收入流动性差异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劳动者收入差异的35.3%可以用其解释。尹玉琳(2015)[23]计算了收入代际流动性对我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结论显示代际流动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70%,代际收入继承是影响我国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原因。
目前,国内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代际流动的研究比较少见,对于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停留在人力资本投资、健康、社会关系网络等微观和中观层面,对于宏观层面上居民收入差距的时期变异和地区变异产生的代际流动环境变化没有给予充分关注。为此,本文试图系统地探究中国社会背景下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流动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流动性相关研究进展。
三、收入不平等影响代际流动的路径和效应
(一)收入不平等影响代际流动的三个因素
要了解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就要了解个体经济地位如何在代际间持续,以及收入不平等如果影响继承性进而影响流动性。从技能内容上来说,不仅包括人力资本,还包括有助于获得经济收益的社会交往能力、文化素养和心理取向等,不管是与跨代相关的技能,还是在劳动力市场,或是在考虑家庭经济地位时的婚姻市场,所有可以获取经济回报的技能均可以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跨时间、地域或人口分组的收入流动性差异和变化可以由三个因素的变化来解释:技能的分布、技能在代际间的传递和流动强度、技能的回报率。收入不平等通过引起三个因素中的任一因素变化从而影响流动性。能够获得收入的各项技能在代际间的传递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定技能的分布及其在时间和空间的传递强度会因个体所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技能的相对特性在时空变化中得到了保持,但选择的回报率也会随社会环境变化而变化。
为直观说明由三个因素引起的代际流动性变化,接下来本文以木工技能为例来进行阐述。比较工业化生产全面扩展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可发现,虽然木匠所具备的技能是支撑社会生产生活活动的必须技能,但在工业化生产开始之后,由于机器生产成为可能以及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因此使得工匠所掌握木工技能由全面到部分细化,也使得木工技能在空间上的分布由相对均匀的分散到区域集聚,进而使得木工技能的平均回报率由于机器替代出现了大幅下降。传统手工技能相对稳定的子承父业路径,由于受到工业化的剧烈冲击,彻底改变了技能代际传递的内容和意愿,影响了技能的代际流动水平。
(二)收入不平等影响代际流动性的路径分析
虽然收入不平等降低代际流动性的假设在理论上占有一定优势,但由于不平等对收入代际流动可能存在复杂的多重抵消效应,因此不平等降低代际流动性的假设在一些经验性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支持。抵消效应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收入不平等对技能分布、技能传递及技能回报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效应,从而产生抵消效应。比如,对于某一给定技能,当收入不平等通过影响技能分布使代际流动性减少,相反又通过影响技能传递率使代际流动性增加时,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对流动性的影响不确定。二是考虑到获取收入技能的宽泛性,不平等可能会使不同的技能产生幅度差异较大甚至方向完全相反的影响。因此,仅讨论代际流动的单一路径至少是偏颇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不论是沿着单个技能路径还是跨越多个技能路径,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很可能都会出现抵消效应。Duncan(1966)[24]的路径分析原理为理解抵消效应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正式框架,并区分了传递因素和回报因素之间的效应判别。
变量i和j分别指子代收入和父代收入,父子收入的相关系数为ρij,其可以分解为不同来源技能集{q}的贡献率之和,即:

各项技能的贡献可以分解为技能传递率(ρqj)和回报率(αiq),其中,ρqj为子代特定技能q与父代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αiq为子代特定技能q的经济收益。若以教育作为技能q来说明公式(1)求和项中的ρqj和αiq,则传递率(ρqj)为父代收入与子代受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回报率(αiq)为子代教育-收入回报率,在子代收入预测方程中,即为子代受教育水平的标准化系数。
公式(1)将收入代际相关系数在传递率和回报率两个层面进行了分解,即代际收入相关性随着特定技能q与父代收入相关关系(传递性)的强弱及其与子代收入相关关系(回报性)的强弱而发生变化,从而子代收入与父代收入的相关系数会随着特定技能而发生变化。如果技能集{q}中只有单一技能,那么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将以单一路径体现;如果技能集{q}中包括多项技能,那么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将以多路径交叉方式体现。
除了技能的传递率和回报率之外,技能的分布也会影响流动性,其通过影响Duncan路径分析原理中的相关性和回归系数来影响流动性。首先,如果子代的技能分布相对父代的收入分布变得更为集中,那么子代技能分布与其父代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就会增加,进而增强技能的代际传递。在非标准化回归方程中,技能分布变化会引起代际收入弹性(βij)变化。非标准化系数下Duncan原理可以用式(2)表达:

其中,βqj为非标准化技能传递率,γiq为非标准化技能回报率,αiq和ρqj定义同前文,σi为父代收入变量的标准差,σj为子代收入变量的标准差,σq为子代技能变量的标准差。子代技能变量的分布(σq)会对非标准化技能传递率(βqj)和非标准化技能回报率(γiq)产生不同影响,根据式(2),当 σq增大时,会引起βqj变大,同时引起γiq变小。在分析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时,研究者往往将教育作为单一特定技能q讨论其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Mare,1980;Hout,1988;Breen,2011)[25-27]。
代际收入弹性也可表达为两项乘积,其中一项是代际收入相关系数,另一项为代际收入标准差的比值,即:

(三)收入不平等影响代际流动性的抵消效应
以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普通关注的“教育技能”来说明每种类型的抵消效果,能够有助于阐明这种模糊性的社会表现。
1.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性。本文分别从收入不平等影响技能分布、传递率和回报率三个方面,探究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原因。
第一,家庭的教育投资。与贫穷家庭相比,富裕家庭在子女教育的经济投资上占有显见优势。一方面,子女教育投资在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间的差距扩大,改变了子女的教育技能分布,造成子代教育技能差距扩大,进一步提高了教育技能传递率,使得富裕家庭子女继续保持高收入的机会增加,从而抑制收入的代际流动。另一方面,随着不平等的加剧,教育回报率由于教育技能改变而随之提高,从而使得高收入家庭子女获得更高收入回报。Alderson等(2005)[28]发现,教育投资预算在美国富裕家庭中的弹性比贫困家庭大很多,这些投资可以改变儿童学术技能的分配,使得一个富裕家庭的儿童在成年后仍保持富裕的机会增加。Reardon(2011)[29]也发现,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子女之间考试分数的差距在不平等问题加剧时期出现了上升。
第二,就业机会。当经济出现不景气时,较高的失业率会造成贫富差距扩大,进而加强收入的代际传承性。高收入家庭通常比低收入家庭拥有更发达、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富裕家庭子女更容易找到工作,特别是收入较高的工作。Savage(1997)[30]发现,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低收入群体在经济萧条时往往更难找到工作或更难升职,低收入群体更易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其收入水平常常徘徊在较低水平,决定了其子代长期处于不利的家庭经济背景下,影响了其子代人力资本的累积和收益。上升的教育回报率意味着教育经济价值的增加,而教育投资本身是父母收入的函数(Bloome and Western,2011)[31],往往会降低流动性。因此,假设不平等与以教育为中介的收入代际流动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是合理的。
2.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会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当存在外部力量时,会发生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情况。
第一,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当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时,Solon(2004)[17]发现家庭教育投资差异造成的子代教育技能差异可以通过政府再分配的变化来抵消。政府增加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缩小高收入家庭子女和低收入家庭子女之间的教育技能差异,从而减少子代收入对家庭收入的依赖,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Downey(1995)[15]提出了无差异技能存在的假设,收入家庭面临着下降的教育投资边际回报,收入产生的更多技能存在着天花板效应。Mayer和Lopoo(2005)[11]观察到,在收入不平等加剧初期,很多国家或地方政府都会增加儿童教育的再分配性公共支出。
第二,政府调控劳动力市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作用是收入不平等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又一重要外部力量。在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时,政府会通过制定相应政策来刺激企业增加工作岗位,降低失业率,如放松贷款条件、减税、免税等政策(Bondonio and Greenbaum,2007)[32]。这些措施降低了技能回报率,从而促进了代际收入流动。
3.收入不平等变化不会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如果两种效应抵消,就会出现虽然收入不平等变化但代际收入流动性并不受其影响的情况。例如,对于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Breen(2011)[27]、Hout和 Janus(2011)[33]发现子代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所处的宏观社会经济背景的相关性相对稳定,甚至下降,这就可以用政府投资和家庭私人投资两种相反力量的相互抵消加以解释。另外,对于市场经济本身周期性产生的失业问题,由于存在市场和政府两种调控力量,故可能会产生抵销效应,最终代际收入流动性不变。
另外,在不平等程度变化的同时,除教育、劳动力市场以外,一些重要的变化也在发生,如人口变化。Martin(2006)[34]发现,单亲母亲家庭比例的上升会导致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由于稳定的家庭结构状态破坏,使儿童被迫处于家庭收入差距较大的环境之中,导致重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过程变弱。DiPrete和Eirich(2006)[4]观察到,来自中产阶级背景的儿童如果由父母一方抚养,更有可能向下流动。
总之,尽管许多研究认为高度不平等会抑制代际流动性(Gosta,2004;Wilkinson and Pickett,2010)[35,8],但从前文的路径分析中可发现,不平等也可能会对代际流动性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或者不会引起代际流动性变化。在塑造子代经济机会方面,政府、市场和家庭的复杂交互作用使得代际流动变化的理论结果不确定。路径分析认为,不论是父母和子女收入连接的任一单一路径还是多条路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都可能会引起代际收入流动下降、上升或不变,具体影响结论需要经验证据的支持。
四、实证策略与计量模型
大多数关于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研究都以如下简单线性回归模型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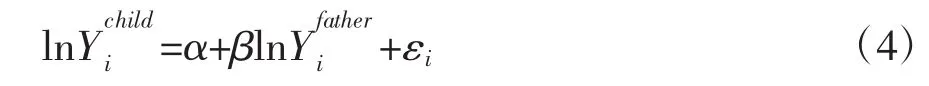
Bloome(2015)[14]为分析美国社会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同时考虑了时期和州两个层面上的情况,不但可以增加统计检验的效力,还可以使我们捕捉到重要的链接不平等与流动性的宏观因素的影响,包括流动变化过程中的公共投资政策、水平等因素的变化。跟随他的研究思路,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在年代和省份两个层面上检验中国社会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效应。为推进实证分析,本文在回归模型(4)的基础上设计了三个计量回归模型:简单交互项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系数模型。
(一)简单交互项模型
模型(4)的设定意味着所有个体i的代际收入弹性相同。通过在模型(4)中增加个体特征,特别是引入父代收入和年份-省份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的交互项,分析时间空间经济不平等宏观环境差异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对于在t时间s省份中观测到的子代个体i的收入,简单交互模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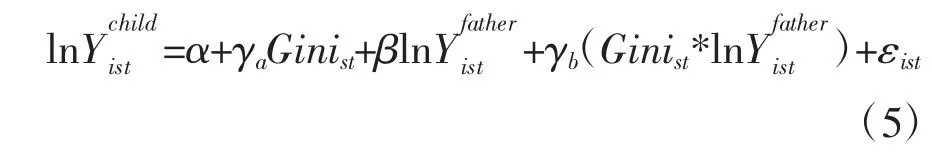
其中,γa测度的是时空不平等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γb测度的是收入不平等程度与父代收入的交互作用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反映了收入不平等通过影响父代收入的代际传递作用对子代收入产生的影响,揭示了父代和子代收入之间的关系是否取决于孩子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不平等。如果γb显著为正,则说明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会使父子收入之间的关联性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下降;如果γb显著为负,则说明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会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如果γb不显著,则说明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没有样本统计显著性。
(二)固定效应模型
简单交互模型汇集了变量在包含不同年份、不同省区的个体间的变化,用以估计均一的参数集。一个可替代的设定是区分年份或省区内的变化,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如下:

其中,μs和ut分别表示省份的子代收入效应和年份的子代收入效应。
(三)随机系数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通过部分合并简单交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的变量,成为了二者的组合。随机系数模型的设定除了包括代表年份和省区的收入效应特征外,还包括了年份和省区的随机误差成分。误差成分的作用是,允许在年份-省区特定时有不同的收入弹性预测值,同时也设定在年份-省区特定时有不同的截距值。随机系数模型(Random Coefficient Model)如下:


根据式(7c),代际收入弹性(βst)在年份和省份上异质,是平均斜率(β0)及年份-省份基尼系数和随机误差成分(vst)的函数。随机误差成分(vst)表达了不能由模型中包含的测量方法获得的弹性的变化。式(7b)中截距项(αst)的设定相类似,是平均截距(α0)及年份-省份基尼系数和随机误差成分(μst)的函数。随机误差成分(μst)代表模型未观测到的影响子代收入的其他因素。模型允许截距和斜率的随机误差成分μst和vst共同变化。γb反映了收入不平等对收入代际流动的影响。
将式(7a)、(7b)和(7c)合并后的模型如下:

本文实证部分汇报了简单交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系数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实证结论虽然大多不依赖模型选择,但随机系数模型(7)的结果更值得关注。首先,随机系数模型的设定考虑了代际收入弹性在年份和省份间的异质性,更符合现实情况;其次,βst是年份-省份组内和组间估计量的加权平均值,属于Stein(1956)[37]类型的收缩估计量(Optimal shrinkage estimator),更有利于降低参数估计的均方误差(MSE),从而增加参数估计的精度。
现有的三个模型没有包括除父亲收入和基尼系数以外的控制变量,为避免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实证分析中还检验了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主要控制变量包括父子年龄及其受教育程度。
五、数据、样本与变量间的基本关系
(一)样本和父子收入的基本信息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数据开展实证分析。CHNS公布了10轮调查数据,依次为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9年、2011年和2015年。该调查先选取了广西、贵州、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苏、辽宁和山东9个省(自治区)54个县(市)共约4 400户居民,2011年后加入了北京、上海和重庆3个直辖市,2015年又加入了云南、浙江、陕西3个省区。CHNS数据库具有如下三个优势:(1)跨越时期较长,从1989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已有10个年度的调查数据,可以用来反映中国2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变迁特征;(2)覆盖的空间范围较大,包含了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15个省(区),这些省区拥有超过我国半数以上的人口;(3)调查信息较为丰富,调查手段比较可靠。对于代际流动研究而言,CHNS数据库以户主为核心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家庭关系信息,如配偶、父母、子女、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等,使我们能够获得所有以父代为户主的配对、以共同居住的子代为户主的配对和以共同居住但子代和父代都不是户主的配对。
本文使用了CHNS提供的经年份价格指数平减后的时期可比收入数据。考虑到在实证模型中将父代收入作为表征子代所在家庭经济背景的变量,本文选取父母收入较高的一方作为父代收入水平。本文将子代的年龄限定在18~40岁之间,父代年龄不大于60岁,同时在实证模型中将子代年龄、子代和父代的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去除缺失值后,共收集到有效父子两代匹配数据5 937条,由于1989年数据的有效样本量过少,故本文分析的样本数据来自CHNS后九轮调查。收入及控制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见表1。

表1 收入及控制变量的均值

(续表1)
(二)基尼系数与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散点图
基尼系数是被广泛用于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其数值介于0和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本文利用CHNS收入数据计算了各省各调查年份的基尼系数,设某省有收入样本x1,x2,…,xn,且 x1≤x2≤…≤xn,x¯为收入均值,则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表2是各省份历年基尼系数的估算结果。

表2 各省份历年基尼系数的估算结果

图1 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与代际收入弹性之间的散点图
用父子两代匹配数据分别建立年份-省区层面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各省区各调查年代际收入弹性系数估计值。图1为基尼系数与代际收入弹性的散点图,显现了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收入流动性之间在年份-省份层面上的基本变化特征。由图1可见,收入不平等与收入代际弹性之间没有显示出任何相关关系,表现出了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流动性无影响的特点。
六、模型估计结果及结论
(一)模型参数的实证结果
本文利用简单交互模型公式(5)、固定效应模型公式(6)和随机系数模型公式(7)拟合年份-省份层面数据,重要参数的估计结果与模型的拟合情况见表3。
在表3中,模型1和2为简单带交互项的OLS模型估计结果,模型3和4为固定效应模型(仅利用省份和年份的组内变化,确保未观测的地区和时间效应不会对不平等-流动性关系的估计产生偏差)估计结果,模型5和6为随机系数模型(在截距随机变化的同时,允许代际收入弹性随省份和年份随机变化)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3和5只考虑了子代收入受到的父代收入及宏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模型2、4和6加入了必要控制变量的影响。
(二)结果讨论
由表3可见,在各模型中父代对数收入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模型中加入基尼系数变量后,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存在收入的代际关联性。父代对数收入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在简单交互模型中没加入控制变量时为0.6,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下降为0.46;固定效应模型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值非常低,只有0.2;随机系数模型的估计结果接近简单交互模型,在不加入控制变量时接近0.45,在加入控制变量后降为0.37。根据估计结果,可见父代收入之间10%的差距持续到子代之间还存在4%左右。
基尼系数前回归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并不统一,具体而言:在简单交互模型中,在没加入控制变量时基尼系数前回归参数显著不为零,且数值很大,达到了0.573 5;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加入控制变量后的随机系数模型下,回归参数的估计值均为负。虽然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回归参数在10%的水平下为显著非零,但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的随机系数模型中回归参数估计值非常小,因此不能准确地从统计角度判断基尼系数对子代对数收入的影响效应。
对于简单交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系数模型的估计结果,我们最关注的是模型中父代对数收入与基尼系数交乘项前的系数γb。从表3可见,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系数模型中γb的估计值均为正,但从数值上来看,包括简单交互模型在内的γb的估计值都非常小,在统计上不认为和零有显著差异。这说明,虽然累积优势理论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恶化的外部环境能够通过影响子代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加强子代收入与父代收入之间的关联性,但CHNS现有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年份-省份层面上的宏观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几乎不会影响收入水平的代际传递效应。也就是说,在父代间的收入差距向子代传递时,并没有出现由于宏观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而进一步加剧的情况。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在提高的同时已经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从收入的代际传递角度来看,父代之间10%的收入差距在我们的估计中将至少有4%持续到子代。如果以基尼系数的数值作为不平等程度标准,当基尼系数从0.479增加到0.491时,意味着虽然不平等程度增加了2.5%,如果γb的估计值为正且显著不为零,那么父代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将随之放大为2.75%γb+4%。需要注意的是,基尼系数作为不平等程度的测量指标,其数值的大小和不平等程度之间不是线性对应的,联合国将0.4作为国家和地区不平等程度的警戒线,在此标准下当基尼系数从0.479升到0.491时,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倍数就扩大到15.2%,此时父代之间10%的收入差距传递到子代将由2.75%γb+4%的差距提高到16.72%γb+4%。
当前的实证结论并不支持累积优势理论,意味着根据前面的影响路径分析,在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宏观环境下,教育、劳动力市场或其他影响技能分布、技能传递率及技能回报率的因素之间可能发生了影响子代收入获得的抵消效应,有待进一步检验。
——基于人力资本传递机制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基于反向社会化理论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