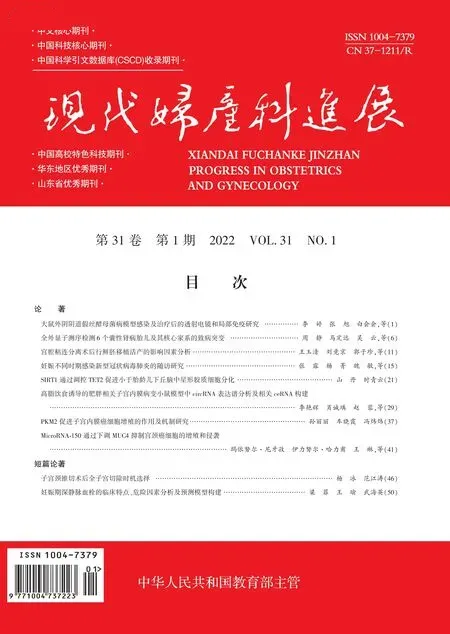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与子代心血管疾病关系研究进展
王 昊,胡 蓉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 200001)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ypertensivedisordersofpregnancy,HDP)包括子痫前期-子痫、慢性高血压、慢性高血压并发子痫前期、妊娠期高血压,是一种妊娠期特有疾病,可伴有全身多脏器功能障碍(如肾功能不全、肝损害、神经系统及血液系统并发症等),严重者可出现抽搐、昏迷甚至母婴死亡,其发病率约为5%~12%,是影响孕产妇和围产儿健康及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正常妊娠女性相比,HDP患者及子代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显著增加,研究HDP与子代心血管疾病间的关系及发病机制,对于防治HDP相关的子代心血管系统疾病,降低子代心血管系统疾病发生风险有重要意义。
1 HDP与子代心脏发育异常
1.1 心室重塑HDP可能通过影响子代血压以外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子代心室结构的发育,导致子代心室肥大等病理变化的出现。Aye等研究显示,宫内暴露于HDP的子代右心室舒张末期血流速度减慢,这种变化持续至出生后3个月,并出现了右心室的肥大,并且这种变化与子代血压水平无关[1]。HDP的青春期甚至成年子代同样会出现心室的结构变化。一项对7~12岁HDP子代随访5年的研究显示,这些子代的左心室体积与正常妊娠子代并无明显差异,但该研究样本量较少,年龄跨度较大,可能受到多种混杂因素的影响。2016年英国的一项纳入了1万余例平均年龄17岁HDP子代的研究显示,虽然暴露于HDP的子代心脏超声显示左心室体积没有明显改变,但相对室壁厚度(舒张期左心室后壁厚度与左心室内径之比)较正常妊娠子代明显增加,并且子痫前期患者的子代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较正常妊娠子代明显下降,但心功能并没有明显下降,这表明HDP可导致子代左心室发生向心性重塑[2]。动物实验研究也表明,HDP子代心室组织Gata4、Gata6及P300等基因表达增加,这些基因参与心肌细胞的分化、心室的发育、心室的肥大等过程,能使心室胶原成分异常增加,增加心室的质量,导致心室结构的重塑及心室的肥大[3]。
1.2 心脏结构异常 罹患HDP的孕妇子代患先天性心脏病的风险较正常孕妇子代升高了8倍,主要表现为房间隔缺损及室间隔缺损等分流型心脏病。一项挪威的研究表明,子痫前期的子代患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风险是正常妊娠子代的1.3倍,其中早发型子痫前期的子代患房室间隔缺损的风险是正常妊娠子代的13.5倍[4],这证实了HDP对于子代心脏的结构发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子代先天性心脏病与血管生成相关因子不平衡有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子代脐带血及母亲孕期血清中sFLT1水平上升及PIGF水平下降,先心病子代的心室组织中也出现了sFLT1及VEGF表达水平升高[5],而既往研究显示PIGF及FLT1参与了胎儿心血管发育及功能的调节。子痫前期等HDP被认为与胎盘浅着床、子宫螺旋动脉重铸不足等血管生成障碍相关,患有HDP的孕妇血清中血管生成相关因子也出现了和前述类似的改变。暴露于HDP的胎儿可能受到失平衡的血管生成相关因子的影响,导致心脏结构异常的发生率上升,也可能是HDP与子代先天性心脏病具有类似的发病机制,从而表现出类似的血管生成相关因子变化。
这种血管生成因子的变化产生的原因,目前还未得到完全阐释,可能是子代本身基因改变造成,也可能是胎盘局部缺氧等病理变化造成,这些变化如何在产后持续对子代造成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阐明。
2 HDP与子代高血压
HDP会影响子代的血压水平,增加子代高血压风险。一项英国的大型母婴队列研究中(6619例)妊娠期间患有慢性高血压、妊娠期高血压或子痫前期妇女的后代在7岁时的平均血压高于正常血压,收缩压分别高出1.67mmHg、1.98mmHg和1.22mmHg,并且这种差异持续至子代18岁依然存在,且没有明显的增强或减弱[6]。一项随访60年的出生队列研究显示,HDP子代罹患高血压的风险是正常子代的1.3倍,重度子痫前期则是1.5倍[7],这些研究结果提示了母亲的子痫前期(preeclampsia,PE)可能影响子代的平均血压,并且这种影响可持续至成年,增加子代高血压风险。
人类的血压受到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如肥胖、性别、年龄、不良生活习惯等,但一项印度的研究显示,子痫前期子代的收缩压升高在排除了出生体重、出生孕周、性别及母亲的BMI等影响因素后依旧存在,但舒张压没有明显差异[8]。另一项系统性综述显示,暴露于子痫前期的儿童及青少年血压较正常人群有所增加,其中收缩压约上升了2.39mmHg,舒张压约上升了1.35mmHg。女性舒张压的上升比男性更加显著,分别为1.69mmHg及0.67mmHg,这与既往许多研究中提到的女性在面临宫内不良环境时所展现的性别保护机制相悖,仍需更多深入的研究证实。年龄似乎也不是这一改变的关键因素,子痫前期母亲的孩子在10岁以前与10岁以后,其血压升高的水平没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9]。这些研究提示,HDP可能是通过增加子代的基础血压水平,而不是增加其危险因素,导致子代罹患高血压的风险上升。
基因表达改变、共同生活环境和宫内编程效应可能是HDP导致子代高血压风险增加的潜在机制。HDP的发生也受到遗传因素的调节,在子痫前期的发生中,遗传因素约占54%,这种遗传因素可传递给子代影响其心血管的功能,导致高血压等疾病发生率上升。
表观遗传在子代心血管疾病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Agtr1a基因表达生成血管生成素II受体I型(angiotensinIItype1receptor,AT1R),宫内缺氧的子代中其启动子中CpG岛甲基化水平下降,使得AT1R表达上升,增加血管紧张度进而增加高血压的发生[10]。宫内生长受限的子代Peg3、Snrpn、Kcnq1等基因甲基化水平也发生了改变,这些基因表达的改变可影响肾脏的发育导致子代高血压的发生,但这种影响不会再延续到第二代[11]。
HDP可通过使血管加压素受体(AVPreceptor1a,AVPR1a),催产素受体(OXTreceptor,OXTR)及蛋白激酶Cβ(proteinkinaseCisoformβ,PKCβ)的启动子甲基化而下调其表达,影响脐血管对血管加压素及催产素的敏感性[12],所以HDP可能改变子代相关基因的甲基化水平影响其表达水平,进而影响血管内皮功能及肾脏结构发育,导致高血压发生风险增加。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axis,HPAaxis)是调节机体血压及心血管活动的重要中枢,11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2型(11β-hydroxysteroiddehydrogenasetype2,11β-HSD2)能将皮质醇转变成无活性状态,其表达于胎盘滋养细胞中,可使胎儿免受母体高浓度皮质激素的损害。子痫前期患者胎盘组织中11β-HSD2含量较正常妊娠下降,这使得胎儿暴露于高皮质激素的环境中,HPA轴的发育和功能受到影响,导致HPA轴的失调从而增加子代罹患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风险。研究显示,子痫前期后代在青春期时血液中的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仍高于正常妊娠子代,这表明HDP可影响子代HPA轴的功能,并且这种影响可持续至成年时期[13]。
其他激素,如睾酮,可能参与子痫前期对于子代心血管的负面影响,子痫前期可导致母体睾酮水平上调[14],这可影响子代内皮功能,导致子代低出生体重和高血压。
此外,研究显示,在孕34周前暴露于子痫前期的子代的收缩期血压、舒张期血压、平均血压较正常子代均有所上升[15],但只有孕29周后出生的子痫前期后代在出生后1周出现了血压升高,在孕28周前出生子代没有发生相同的变化[16]。这可能是由于小于28孕周的子痫前期子代通常伴随疾病更多,需更多的生命支持,可能会掩盖子痫前期的升血压效应,并且这些孕妇通常会在产前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这也会使得子代血压升高,掩盖子痫前期对子代血压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子痫前期对于子代血压的影响仅在一定孕周后才会出现,28周以前的子代血压也许是受到其他因素的调控,如相关基因的表达等。这项研究仅统计了子代出生后一周的血压情况,对于这种现象是否长期存在还需进一步研究,以及HDP对于子代血压等影响是否与发病起始孕周相关也需进一步研究。
3 HDP与子代血脂异常
胎儿大部分的脂质来源于母体,仅有小部分为自身合成,母体血液中的各种脂质可以通过胎盘的转运进入胎儿,影响胎儿的血脂水平,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通常伴有脂质代谢的异常,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总胆固醇(totalcholesterol,TC)、LDL-c、VLDL-c均有所上升,但目前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对于子代血脂水平的影响仍有较大的争议。
Rodie等[17]研究显示,子痫前期子代脐血中的TC、TG及TC/HDL-C比值升高,HDL-C水平无明显差异,但子痫前期母亲仅有TC较正常妊娠有明显上升,母体和胎儿的血TC,TG及HDL-C水平并无明显相关性,这表明子痫前期对于胎儿血脂水平的影响并不是通过增加母体血脂水平来实现,可能是由于胎盘转运功能变化或不良宫内环境使胎儿应激所导致的。而另一项研究则显示,子痫前期子代的脐血中不仅出现了TG及TC升高,同时伴有HDL-C及apoA-I水平下降[18],由于子痫前期被认为是一种胎盘源性疾病,这种变化也可能反映了胎盘功能的障碍。
Hessami等[19]研究显示,妊娠期高血压及子痫前期的妊娠女性血清TG升高与子宫动脉搏动指数(uterinearterypulsatilityindex,UtA-PI)异常相关,HDP子代脐血中TG升高则与脐动脉搏动指数(umbilicalarteriespulsatilityindices,UA-PI)相关,这些研究提示HDP子代的血脂异常可能与子宫及胎盘的血流灌注、胎盘功能改变相关。
HDP对于子代脂质代谢的影响可能是持久存在的。研究显示,暴露于子痫前期的5~8岁儿童总胆固醇高于正常儿童,而甘油三酯、LDL等在两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20],但其作用机制未被阐明,成年子代的血脂水平变化也有待进一步研究。亦有研究显示,HDP对子代脂质水平并无明显影响,由于血脂水平受到饮食等各种因素影响,关于HDP对于子代脂质代谢的影响的研究尚少,许多研究结果之间还有着相互矛盾之处,二者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其对于子代血脂水平的长期影响的机制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母体血清中的甘油三酯需要被胎盘微绒毛上的脂蛋白脂肪酶(lipoproteinlipase,LPL)或内皮脂酶(endotheliallipase,EL)等分解后再经由脂肪酸转运蛋白转运至胎儿体内,母血中的胆固醇一般经由LDL、VLDL、HDL等脂蛋白转运至胎盘,再经由合体滋养层细胞表达的LDL受体、VLDL受体等转运至胎儿体内。Murata等[21]实验显示,子痫前期患者胎盘组织中LDL受体及VLDL受体的表达下降,脂肪酸转运蛋白(fattyacidtransportprotein,FATP)中的FATP1和FATP4在子痫前期胎盘中表达明显降低,并导致胎儿血液中不饱和脂肪酸水平降低,但这些脂质相关转运蛋白的表达下调似乎与胎儿脐血中甘油三酯等血脂水平的升高不符,也可能HDP通过降低胎儿体重,减少脂质的利用或其他机制使得脐血的血脂水平升高。沈虹等[22-23]研究则发现,重度子痫前期患者胎盘组织中LPL表达水平较正常妊娠组升高,而EL表达水平却较正常妊娠组有所下调,但该项研究仅研究了重度子痫前期患者的胎盘组织,这也许提示了不同的HDP通过不同方式影响胎儿的血脂水平变化。
4 HDP与子代脑卒中及冠心病
心脑血管疾病通常受到血脂、血压等的影响,HDP可能通过影响后者进一步增加脑卒中及冠心病的风险,也可能是独立作用于脑卒中及冠心病的危险因素。Kajantie等[7]研究发现,暴露于HDP的子代在成年后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升高了1.9倍,其中出血性脑卒中风险增高2倍,血栓性脑卒中风险升高了1.8倍,并且这种风险的增加与孕周和出生体重没有明显关联,潜在机制可能包括大脑血管紊乱,也可能是由于脑部发育减缓或大脑生长受损导致的“大脑保留”反应。同时,该项研究指出HDP与子代冠心病间没有明显关联。也有动物实验显示,暴露于HDP的成年子代发生脑卒中时,大脑的受损区域明显大于正常子代,同时伴有一氧化氮合酶及内皮素表达的上调及急性血管反应的增强[24],但目前相关研究较少,二者之间的关联及具体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5 总 结
综上所述,在不良的宫内环境及出生后的生活环境共同作用下,HDP可造成子代先天性心脏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增加,影响子代心血管健康,因此应重视子痫前期等HDP对子代的远期影响。但目前研究尚不够透彻,部分研究还存在互相矛盾之处,其中的分子机制并不清楚。进一步的研究有助于在更早期对子痫前期子代进行健康干预,降低其心血管疾病风险,制定完善的子痫前期子代出生后的随访、管理及干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