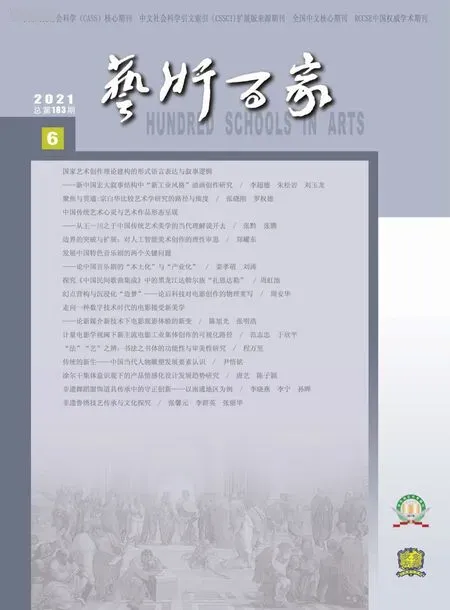音乐与诗歌的缱绻∗
——评《音乐文化与盛唐诗歌研究》
黄道玉,曾智安
(1.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2.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柏红秀教授的最新力作《音乐文化与盛唐诗歌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她在《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音乐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之后对学术界的又一非凡贡献,为“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成果。《研究》以独特的研究路径还原音乐与唐诗的创作互动,聚焦并剖析盛唐音乐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从文学本体出发创造新的学术命题,并且用“竭泽而渔”的研究态度全面展现音乐与诗歌的缱绻盛景,是诗歌研究的全新尝试和成功典范。
音乐和诗歌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艺术,都是抒发人类感情的美好途径,具有共通性。从《诗三百》孔子皆能“弦歌之”,到乐府诗“声依永,律和声”,到唐诗“旗亭赌唱”,无不展现出音乐与诗歌的亲密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盛唐的音乐文化以其百花齐放、姿态繁盛而著称。盛唐社会安定富足,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擅长谱曲和打羯鼓。由于统治者对音乐文化建设非常重视,优秀乐人、乐工大量出现,盛唐音乐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盛唐诗人储光羲在《长安道》一诗中写道:“西行一千里,暝色生寒树。暗闻歌吹声,知是长安路。”[1]1417盛唐不仅是音乐文化的繁盛时代,同时也是诗歌创作繁荣的年代,涌现出众多杰出诗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生活在这音乐的盛世里,盛唐诗人也大多喜爱音乐,精通音律,比如王维“性娴音律,妙能琵琶”[2]1331,李白擅弹古琴。
201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音乐文学研究专家柏红秀教授撰写的《研究》[3],此书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笔者有幸拜读,感慨柏教授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和开拓,沉浸其中不忍释卷。《研究》以盛唐作为断代,在考察盛唐音乐文化活动的基础上探讨它对于盛唐诗歌发展的具体影响。《研究》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对音乐文化与盛唐诗歌的整体考察,先是依空间将盛唐音乐文化分为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两种类型,对它们分别作具体详实的考察,然后考察音乐文化对盛唐诗歌创作及内容的整体影响;下篇为音乐文化与盛唐诗歌的个案研究,重点关注名曲、名家、名篇,从音乐文化视角对盛唐音乐名曲《破阵乐》,盛唐诗坛名家如王维、杜甫和元德秀,盛唐诗歌名篇《江南逢李龟年》等进行深度考察,对学界常见的问题作全新的探索,对学界忽略的唐代诗歌问题进行突出强调,对学界陈陈相因的误解予以澄清。《研究》对于音乐文化和盛唐诗歌的研究非常精彩,为唐诗研究创新提供了范本。
一、独特的研究路径:还原音乐与唐诗的创作互动
当前,唐代诗歌研究存在方法雷同和结论陈旧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于诗歌本质的理解过于陈旧,以及对于“文学本体”的理解过于狭隘。柏教授受到任半塘先生《唐艺学》的启发,找到研究唐诗全新的路径,锁定音乐文化与唐诗进行研究。柏红秀教授深刻认识到:“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静态的文本存在,文本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它的文本从来都不是像铁板那样一成不变,它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被孕育出来的,曾有过丰富的发展过程,最后才呈现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模样。”[3]自序因此她转向考察诗歌丰富的生成过程,并且深挖生成过程背后特定的时代风貌和文化根源。盛唐音乐文化对于盛唐诗歌的生成、审美和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音乐和诗歌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的关注,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是从诗歌入乐、乐器乐人入诗、乐人唱诗、唐诗的音乐性等角度出发,很少从音乐机构变化的根源、音乐的雅俗流变、音乐的地理空间变化等角度对音乐与诗歌的深层次关系进行研究。
柏教授的开山之作《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4]侧重研究了唐代宫廷音乐文化,从机构建制、宫廷乐人、宫廷音乐种类等方面,厘清了唐代宫廷音乐文艺中的各种关系,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后,柏教授转向音乐文化与唐代诗歌的交叉研究,除继续关注宫廷音乐之外,还着重考察唐代民间音乐的发展以及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密切关系。柏教授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更加热情地投入到更细致的断代研究中,依空间将盛唐音乐文化分为宫廷音乐和民间音乐两种类型,分别作具体详实的考察,探索盛唐音乐文化对诗歌创作及内容的整体影响,出版了《研究》。[5]柏教授通过还原音乐与诗歌的创作互动,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研究路径,对唐诗的研究甚至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明确的研究焦点:剖析盛唐音乐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经济富庶,商业繁荣,人民饱含激越的情怀,诗歌和音乐都绽放出无比的光彩。而盛唐阶段音乐更值得关注,因为它不但是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而且还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前后变化过程。唐代诗乐密切相联,特征鲜明,处于巅峰状态,因此盛唐音乐不但对此后音乐发展格局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诗歌发展影响深远。大多数研究者都把唐代音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却忽视了唐代不同时期的音乐文化差异和诗歌创作的差异。《研究》选择盛唐这一特殊的断代音乐文化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考察盛唐音乐文化的发展变化轨迹,揭示它对当时诗歌创作及内容形成的具体影响,为诗歌的精细化研究做了非常成功的尝试。
《研究》发现盛唐音乐文化呈现出几个新的特征:一是宫廷音乐机构的增设以及雅俗乐表演职能的分工有力促进了宫廷音乐的繁荣。二是盛唐以前音乐发展的惯性以及雅俗观念和朝廷管束等造成了民间音乐前期的沉寂。三是统治者的喜好及朝廷推行的激励措施推动了民间音乐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全社会宴乐之风的兴盛。诗歌入乐在宴会上传唱成为时人评价诗歌艺术水平高下的一个新标准,士人因此热衷投入其中,从而带动了盛唐诗歌创作的繁荣;盛唐雅乐歌辞的创作队伍构成变得单一。四是俗乐歌辞创作队伍结构变得丰富。五是文士们参与歌辞创作的方式发生了改变。随后,她进一步研究这些变化对于盛唐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并有新的收获:一是盛唐音乐诗歌不但数量增多,而且在内容上还出现了新的变化;二是盛唐诗人更加关注俗乐活动而非雅乐,更加留意当时而非前朝的俗乐活动,更加留意地方俗乐而非宫廷音乐,并且对南方音乐和胡乐的描写有所增多;三是乐器诗成为音乐诗中醒目的部分,除了传统的乐器琴以外,对琵琶和筝的描写极多;四是对俗乐审美风格的描写增多,已不再如以前那样概括和宽泛,转而走向具体和丰富,比如涉及的“悲”,就具体包括“愁”“怨”“哀”“苦”等;五是乐人诗数量较之初唐有所增多,描写的乐人包括前朝乐人、宫廷乐人和权要家庭乐人,但是这些诗篇所占的比例并不多,盛唐诗篇主要描写的是各地方的民间乐人,其中涉及胡乐人,然而这方面的作品并不多见。此时乐人诗所描写的内容,不但有他们的音乐活动,还涉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气质。在描写音乐活动时,细致到他们表演时的动作神情、整体过程以及取得的表演效果等,而且描写时运用的艺术手法变得更加多样和丰富。在描写乐人的精神气质时作者发现,诗人对于乐人所怀有的情感虽然有些与往昔相同,比如赞美之意和知音之情等,但是却将赞美之意及知音之情落到了实处,依据具体的情况而抒发。除此之外,还增加了深切的同情以及对社会的批判讽刺等内容。这些内容新鲜,观点新颖,令人耳目一新。正是因为研究焦点明确,她的研究才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结论才更有说服力。
三、创新的学术命题:揭示文学本体的真正内涵
在研究唐诗的过程中,柏红秀教授一直思考的问题是“诗歌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诗歌研究?如何进行唐代诗歌的研究?”她认识到文学研究必须回归文学本体,而文学本体曾经一度被狭隘地认为只是文学作品本身,对于诗歌来讲就只是它的题材内容与形式审美等。柏红秀教授认为文学的本体应该包含文学发展的过程以及内在的规律。“当文学依赖自身而非理论家来传达这一重要功能时,它更易撼动人心。”[6]107文学的产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当中孕育出来的,就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而言,音乐是这个土壤中关键的因素之一。因此,要解决诗歌的相关学术争端问题,对音乐文化作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研究》大胆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学术命题。著作的下篇就是学术命题的创新呈现及其解答。比如在考察王维的诗歌广受欢迎并入乐演唱的原因时,《研究》通过对盛唐音乐文化的分析,指出盛唐歌辞在“风骨”和“声律”上并求。进而结合王维的音乐才华、社会活动及诗篇特点,发现它们恰好与盛唐音乐文化高度契合。在考察杜甫在乐人诗方面所作的贡献时《研究》指出,杜甫在乐人诗方面所作的大力开拓既与他个人的创作努力相关,也与整个时代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相关,乐人诗是在盛唐音乐文化这片沃土上开出来的鲜花,对后世乐人诗尤其是中晚唐乐人诗的发展影响深远。在考察元德秀诗歌创作时《研究》指出,在雅乐衰弱、俗乐兴盛而歌辞创作需求骤增的情况下,在文士与乐人的关系仍然相对疏远的情况下,元德秀坚守儒家音乐思想,强调歌辞创作的重要性,主动参与到歌辞创作中来,一方面改造宫廷雅乐歌辞,一方面创作民间古老歌辞。创作时用自然质朴的语言直接地表达内心的真挚情感,这种情感包含着创作者对国家君王的忠诚和对社会百姓的关爱,体现“民间和政治的双重内涵”[7]146。以他在当时文坛上具有的巨大影响力,此举无疑带动更多唐代文人投身其中,从而打破先前歌辞由乐工创作或选诗入乐,而文人只是被动参与的局面,不仅大大扩充了歌辞创作队伍,还为歌辞创作提供了高雅范式。在对《江南逢李龟年》作者进行考辩时,《研究》结合唐代梨园设置与管理的历史,证实李龟年实为盛唐著名的京城市井乐人,该诗作者应是杜甫。李龟年并没有做过梨园弟子,也没有担任过曲师,南宋胡仔之所以会对《江南逢李龟年》的作者一事产生质疑,是因为宋人对唐代梨园及梨园弟子等历史的普遍误解,故而他的质疑本身并无科学性可言,根本无须反驳。这些学术命题的创新都是建立在柏教授对盛唐音乐和诗歌的详细梳理基础之上的,也反映了她对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
四、宏毅的研究态度:全面展现音乐与诗歌的缱绻
柏教授继承任半塘先生的治学方法,从文献收集、整理和细读,注重实证,全面梳理唐代的音乐文化(包括音乐机构、音乐制度、音乐活动等)到考察唐代音乐文化活动对唐代诗歌活动的影响(包括唐代诗歌的创作、传播、接受以及相关学术问题的争鸣等),柏教授认为学术研究应该秉持“大禹治水式的宏毅治学精神”,因此学者须要“占有和阅读那个时代的全部文献,进而全身心地贴近整个过往的文化历史,最终在海量的文献中用勤奋和智慧梳理出与文学活动最密切相连的内在逻辑,唯此才可以对文学的发生过程作出细致详实的揭示,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更富有成效也更具有价值,从而为当下的学术事业作出更有力的推动”[3]自序。
柏教授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全唐文》《全唐诗》《唐会要》《通典》及唐宋各类野史笔记等第一手唐代文献史料基础上进行的,每一个论断都有厚实的史料来佐证。敏感的学术感知力令柏教授能够从复杂的文献史料和丰富的文化现象中提炼出核心学术问题,进而挖出问题的本质,进行严密有力的论证。如在考察盛唐宫廷音乐建制时,具体指出太常寺在雅乐方面有四次建制;在探讨统治者的态度时明确指出唐玄宗登基之初曾经通过禁止女乐和胡乐来表达自己尊崇雅乐的态度;在宫廷音乐机构这一章节,详细地考察盛唐太常寺、教坊和梨园各自发展的具体情况;等等。在考察音乐发展与社会的关系时,《研究》指出:“盛唐后期,宫廷音乐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这与当时国家的安定富庶强大导致唐玄宗生出了与民同乐的心有关。”[3]52《研究》以大量细致的史料作为佐证,比如在论证太常寺乐工的选拔时,举了多个例证:“再如段师,他是一名寺庙僧侣,因为擅长琵琶而入宫表演”,“再如念奴,她也是长安青楼乐人,因为擅唱而被唐玄宗召入宫中表演”[3]54。这些论证史料丰富,分析缜密,所得结论客观科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五、结语
《研究》在介绍中国古代诗乐的悠远关系以及唐代诗与乐、诗与歌之间的密切关联基础上,从独特的研究路径还原音乐与唐诗的创作互动,聚焦并剖析盛唐音乐对诗歌创作的影响,通过揭示文学本体的真正内涵以产生新的学术命题,以宏毅的研究态度全面展现了音乐与诗歌缱绻盛景。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只有在融合历史、文化、文学等多重因素的前提下,才能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柏红秀教授的研究之路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借鉴。
——《乐府歌辞述论》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