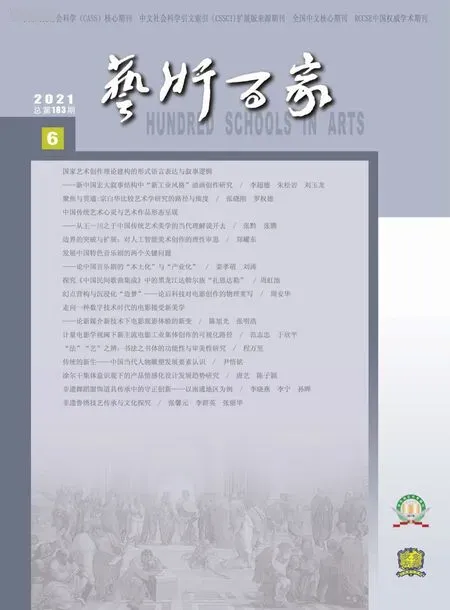论《清河书画舫》的体例创新∗
刘 义
(南京艺术学院 离退休工作处,江苏 南京 210013)
作为书画著录,《清河书画舫》因征引和摘录其他文献内容较多一直备受诟病,进而责其体例之非。其实,《清河书画舫》在体例编写方面颇多探索,不乏创格:组织架构上以时代为序,以人为纲,以作品为目,纲举目张,层次清晰;内容上鉴定与收藏并重,赏评与考据并存,既继承了以人论书、以人论画的史传叙述方式,又创造了以作品为中心这一“书画清赏展玩的新体”,特别是征引文献与己论相结合的叙述方式实属创格。是书以“附录”互证互见,以“补遗”前后呼应,叙论结合,语不虚出,实属古代书画著录体例之卓优者。
清人顾复认为,李嗣真《画录》有名无实,难以取信;《宣和书画谱》不辨“真伪优劣”;《米氏二史》与《东观余论》“少而无伦次”;《云烟过眼录》只记藏家,鉴评略胜于无;《铁网珊瑚》《郁氏书画题跋记》《孙氏书画钞》以及顾氏《笔记》皆有偏废,“无诗题者不录”;《铭心绝品》《严氏书画记》与《南阳书画表》皆“仅存人名而已”[1]序言。顾氏所论虽短短数语,却也一语中的,由此可见“编书难而立例尤难”。同为书画著录,著者不同则撰述之目的不同,内容亦会有所侧重:书画史家注重人物传论,鉴藏家注重书画作品,目录家注重体例,考据家注重文献,评论家注重风格流派与品第高下。书画著录体例不仅与作者编撰动机相关,更为编撰内容所支配,但无疑作者的学养和能力才是关键的决定性因素。
张丑(1577—1644),晚明著名书画鉴藏家,著有《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清河书画表》《南阳法书名画表》等。其中《清河书画舫》近30万字,著录各类书画家数百人,书画作品近千件,以“史”之体例记述鉴藏闻见,遍引诸书,加以赏评,以成己见。是书以时代为序,以人为纲,以作品为目,鉴定与收藏并重,赏评与考据并存,巧妙规避了以上顾氏所言诸书之弊,既继承了以人论书、以人论画的史传叙述方式,又突出了明代以作品为中心的鉴藏特点,其体例不仅超越了前朝和同时期的书画著作,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以时代为序、以人为纲、以作品为目的组织结构
中国古代书画著作的体例门目众多,各种组织架构优劣互现。有以收藏家为目录者,如周密《云烟过眼录》,著录了43位收藏家藏品,主要记载作者、名称、印记、题跋及传承,后附简明鉴别和论断等。其意首在记录藏品,征信天下,优点在于检录方便,一目了然。《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皆仿此例。有以品格为纲者,如《古画品录》《圣朝名画评》《益州名画录》《古今书评》等,以赏析品评为能事,以品第高下为标准,或设上品、中品、下品,或列能品、妙品、神品、逸品,论风格气韵、笔墨神采,间有人物小传,多粗疏简略。有以书画作品内容聚为一类的,如《珊瑚木难》《铁网珊瑚》等,全文照录书画作品的款识和题跋,汇而成书。余绍宋评价这种著录说:“其弊也,不讲考证,不重鉴赏,而徒以钞胥为能。于是著录之书几于汗牛充栋,而芜杂遂不可问矣。”[2]448对于鉴赏家来说,其论如是,但其文献保存与资料汇集的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其他诸如以书画作品形制区分者,如卷、轴、册页、屏等,其分类意义不大。
张丑以司马迁的史观意识,吸收了《历代名画记》《宣和书画谱》等以人物为中心的著录理念,将书画家放在不同的时代风貌和社会背景下加以记述,这种社会关照与历史把握方式显然要比一般的书画鉴赏著录取意要高。《米元章书画史》虽然只是笔记体的书画著录书籍,但却以“史”命名,其意甚明。《清河书画舫》以时代为序,依次著录自三国钟繇至明代仇英等书画名家87人,附录44人,记述作品近千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清河书画舫》可以看作是以书画家为中心、以书画作品为主要内容的一种书画通史。以时为序、以人为纲、以作品为目的组织架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网链,纲举目张,结构清晰,相较直接记录作品的著录体书画著录更为科学和严谨。
《清河书画舫》以人物为纲,这些“人物”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目录本身直接署名的书画家,一类是附在目录之后的书画家,还有一类是在论述具体书画时直接涉及的书画家。第三种所涉及的人物主要是在论述具体书画作品时发生和提及的,并非因时因人而设,也没有特定规律。如贯休名下涉及人物23名,之所以出现这些书画家,是因为作者此间插录了韩朝延出示书画和严持泰携示书画的记载;赵子昂《摹周穆王八骏》“在王元美家”,李嵩《服田图》则为“项氏藏”。
著录书画作品是《清河书画舫》最为主要的内容。如李成名下之述录作品多达十余幅。对于这些书画作品,《清河书画舫》对其形制、内容、题跋、藏家等信息多有记载,有时对书画还加以赏评,并作出真伪鉴定。如其记李成《寒林图》曰:“太师文公家藏,用笔神妙,意度清奇,有宰相吕大防、范纯仁、宗伯判、陈仪郎、李公麟、苏轼同观,执笔轼也。”[3]卷六张丑认为“此幅兼有魏了翁跋书题识”,评为“神品上上”[3]卷六。又如黄庭坚《头陀赞》,张丑定为其为“真迹,神品上上”。《清河书画舫》不仅录其原文,对其后济南张谦受益父、邹立诚、王穉登题识也全文照录,并记其获此帖为之作诗云,后张丑又为之展观重志。[3]卷九《清河书画舫》书画家名下所列的作品名目,有时与著录正文并不相符。其有目无文者,正文书画家名下计有56条目,有文无目的情况更多,或有作者非所亲见及引自他文者,多不入目。仅以王维为例,其有文无目者就有《山阴图》《精能图》《袁安卧雪图》《辟支佛》《沧洲图》《寒林》《雪霁捕鱼图》。[3]卷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或是传抄之误,或是作者未来得及修订之失。
二、融史传、鉴赏、著录于一体的汇编风格
书画著作的编次体例是作者书画史观和体系认识的总体反映,要深入了解其内在逻辑、论述关系及实现途径,必须对文本内容上的叙述体例进行深入研究。张丑不满《宣和书画谱》“大账簿式”的著录,故其著画史、画品、赏鉴兼具,呈现明显的“汇编”风格。《清河书画舫》以人为纲,以作品为目,虽然名家有大小,内容有多少,但其叙述的内在逻辑与结构板块还是比较一致的。
(一)“人物史”——为书画家立传
在书画演进发展的历史中衡量和把握人物,为书画家作传,言其生平,叙其师承,评其艺,述其作,有利于后人对其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如何为书画家立传,是对著者书画“史学”“史识”“史见”和“史胆”的重大考验。《清河书画舫》所载书画家,张丑多为其立传,并着重突出鉴赏“本色”。
第一种是不惜笔墨,亲自操刀者。如其言李唐云:“字晞古,河阳三城人。建炎间,与马远、夏珪同为画院待诏,赐金带。善画人物山水,笔意不凡,尤工画牛,得戴嵩遗法。所制《长夏江寺图》卷,古雅雄伟,今在吴郡朱氏。前有高宗御题,后有‘开封赵与懃印’,真笔,妙品上上。如马远《松泉图》、夏珪《溪山无尽图》名迹,然皆不能及之,固宜前人称许云。又见尊生斋收《桃林纵牧》小幅,亦晞古作,不知者谓为戴嵩,殊可笑也。”[3]卷十在李唐传中,张丑除了主要撰述其生平、师承、画法特点和作品内容外,还加入“画迹辨伪”项,突出其重在鉴藏的“本色”。不仅详记《长夏江寺图》形制,更赏其“古雅雄伟”,亦将尊生斋所收《桃林纵牧》定为李唐所作。第二种是言简意赅、寥寥数语者。如其为刘松年作传云:“御前待诏刘松年,画师张敦礼。工为人物、山水,种种臻妙,名过于师。黄氏藏其着色《听琴图》一,秀润清雅,墨法精奇,后有复斋、杨维祯等七诗,杜东原鉴定。真迹也。”[3]卷十张丑所作刘松年之传,无丝毫闲言赘语,仅仅26字道破其师承、擅长和水准。从张丑所作之传来看,传统书画家传的内容被淡化,更为显眼的是其鉴赏、鉴定和收藏的内容——对《听琴图》的介绍。不仅评其画“秀润清雅,墨法精奇”,还介绍其题有七诗及具体藏家。第三种是直接借用、“不添枝叶”者。对于有些书画家,张丑往往直接引用其他文献内容,不予更改和增补。如《清河书画舫》卷十,直接引《画继》内容为江参立传云:“江参字贯道,江南人,长于山水,形貌清癯,嗜香茶以为生。初以叶少蕴左丞荐于宇文湖州季蒙,矜其能。有飞泉怪石五幅,图一本。笔墨学董源,而豪放过之。”[3]卷十又如《清河书画舫》卷三、卷九补遗部分,直接引《宣和画谱》之内容为王维、李公麟立传;《清河书画舫》卷三补遗部分,直接引《宣和书谱》之内容为虞世南立传。第四种是虽有借用,但仍多方加以补充者。对于一些早有传记的书画大家,张丑多直接引用原文,但有时又嫌不足,往往又征引其他诸多文献,加以补充和完善。如王羲之,《清河书画舫》首先引《宣和书谱》内容叙其生平,录其书目;其后又引《书史会要》《古赤牍》《陶贞白集》《字源》《尺牍清裁》《墨池遗事》《书史会要》《艺苑巵言》等语言其笔,赞其艺,述其事;再引《东坡题跋》《白云先生书诀》《山谷题跋》《米氏书史》《宝晋英光集》《米氏书史》《辨诬录》《海岳名言》等语论其笔法,言其印信,述其真伪。此之种种,可算是一种隐晦的增补式立传,具有百科全书式的汇编性质。
《清河书画舫》并不为所有书画家立传,对于一些作者不喜,或是不太知名,以及距张丑时代较近的书画家,多不予立传,而是更关注其书画作品。其中,书画不太知名者如秦观、苏舜钦、文天祥,张丑不喜者如马远、夏珪等皆未有立传。有明一代,即使像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一样的书画大家,《清河书画舫》也未予立传。这些时代距离较近的书画家,虽然未有立传,但他们在书画史上应有的地位,《清河书画舫》都予以了足够的认可。
(二)“书画舫”——书画清赏展玩的新体
黄庭坚《戏赠米元章》诗云:“万里风帆水著天,麝煤鼠尾过年年。沧江尽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书画船”是米芾江湖畅游的交通工具,更是他书画活动的自由场所。他在这里研墨弄笔,纵情书画;赏书品画,神游物外;书画交游,易购佳品,鉴定真伪。是编以“书画舫”命名,取“米家书画船”之意甚明。《清河书画舫》正是这样一艘满载书画名迹的自由之舟,供人清赏展玩、书画娱乐。张丑是一位书画著录大家,也是一位书画鉴赏大家,《清河书画舫》体现出浓厚的“鉴赏本色”:以鉴赏语言赏鉴事。余绍宋将《清河书画舫》列为鉴赏类书画书籍,想来也是有鉴于此。
人物开篇具有鉴赏之“本色”。以书画家为单元进行文本关照,其首选真迹引入主体人物,并多伴有赏评和真伪鉴定之语。如“赵构”首段云:“思陵锐意学书,多历年所,故其书楷法清逸,行草浑成,无不臻妙。吾家旧藏《御书徽宗集序》一卷,前后虽有残缺,而字宗虞禇,实为希世奇宝。先府君博雅好古,目力过人,生平宝爱三代九螭白玉玦及此卷,至仙游时,以授长兄伯含,永为传家清玩。”[3]卷十张丑先是肯定赵构“楷法清逸,行草浑成,无不臻妙”,进而介绍其兄家藏之《御书徽宗集序》,虽有残缺,仍不失为“希世之宝”。又如“赵伯驹”首段云:“江阴葛维善旧藏赵千里《明皇幸蜀图》,绢本,重着色。虽小幅甚妙,秀雅超群,绝无皴法。都玄敬先辈载之《寓意编》,今转属太原王氏矣。近改作高头短卷。或云此图千里摹思训之作,固是甲观。”[3]卷十此段文字不仅介绍了《明皇幸蜀图》的质地、藏家,还介绍了流传轨迹和形制变化,并赏其“小幅甚妙,秀雅超群”,“固是甲观”。此种以真迹介绍、赏评和鉴定为主要内容的“开端模式”具有典型的“鉴赏本色”,与一般书画史以时代风貌或人物生平介绍开篇大相径庭。
文本内容凸显鉴赏之本色。
一是书画家与书画赏评之语俯拾皆是。如其评唐人景审《临黄庭经》墨迹,“其字颇带行体,与世传石本稍异,韵致楚楚可爱”[3]卷二;评蔡君谟《茶录》,“小楷精谨,纸墨如新,故文征仲太史极称赏之。北宋四名家书法,君谟称首,此真可宝者矣”[3]卷七;评米元晖“画品凌跨而翁”,其《湖山烟雨图》卷“纵横变幻,神化无穷”[3]卷十;评王叔明《阜斋图》,“皴法简淡,落笔尤古”[3]卷十一;评《鹤林图》,“虽萧疏小笔而逸趣无涯,真仙品也”[3]卷十一。张丑的赏评往往只为寥寥数语,但言简意赅,品评得当。吴士余认为《清河书画舫》“对名家名作兼有评论,内容系统丰富,论述精当,著录准确,是收藏家及鉴赏家的重要参考书”[4]733-734。
二是书画流传与真伪鉴定之例较为常见。如《清河书画舫》卷二记王羲之《官奴帖》之流传:米芾《宝章待访录》所记二本,真迹在王寔处,模本在王仲修家,真迹今在檇李项氏;又定吴中王氏所藏王羲之《袁生帖》、释怀素《梦游天姥吟》、王维《雪溪图》、李成《寒林平野图》、徐熙《柳穿鱼图》“皆宋秘府物,并神品也”[3]卷二。
三是书画交流活动时有体现。既有文人间的书画交游,也有友人间的赏玩;既有逞富斗强之举,也有书画交易之流。这些活动多为张丑亲身经历,是研究明代晚期书画活动的重要文献。《清河书画舫》所载王羲之名下书画交流活动有两次,一为“周敏仲携示逸少《行穰帖》一卷”,张丑定为“唐人硬黄临本”;一为“新都吴延之市书画”,“尝夸示王逸少《画像赞》《胡母帖》、虞世南临《乐毅论》、唐元宗《鹡鸰颂》、李成《寒林图》、米元章《海岱楼》卷,俱属赝本”[3]卷二。李公麟名下所载书画交流活动更多,此中仅举一例。乙卯春有客用钱三十万余购得李公麟《九歌图》,邀张丑往观,“其卷高头连幅,描法极细,然笔则未古也”[3]卷八。张丑不顾,大笑而去。
四是注重总结书画鉴定方法,虽少而精。张丑对书画鉴定有独特的心得和体验,这些方法虽只是只言片语,但直到今天依然精致有效。虽是一家之言,却不乏真知灼见。《清河书画舫》有时也征引其他文献,如卷二引《洞天清录》一文,介绍北纸、南纸、硬黄纸的区别,及其在书画鉴定中如何运用,可谓用心良苦。
(三)著录之体——书画名迹的实录
张丑曾讥《宣和书画谱》仅记书画名目,乃当时之“大账簿”,“无当与品题”[5]卷八。后世目录学家亦多持此见。《清河书画舫》受明人“好题跋、喜抄书”风气的影响,对一些书画名迹不仅记其形制、内容、印记、藏家、传承,对有些名品后题识、跋语等也往往全文照录。如卷八李公麟名下之《三清图》《维摩经相》《华严变相》《阳关图》所记甚详,《九歌图》《慈孝故实图》《君臣故实图》等题跋皆全文实录。[3]卷八《清河书画舫》对书画作品内容、材质、印记、流传、题跋等进行详细记录,显示出较强的专业性,极富书画史价值和鉴定价值。
《清河书画舫》对书画名迹作品本身的“印迹”变化保持高度敏感,只要事关真伪,就不吝笔墨。如李成《茂林远岫》真迹,不仅记其“在项氏,向若冰等有跋,乃文寿承鉴定也”,还特别指出,“近复得阅成画,为人拆去,别购补之,故‘封’字印不全云”[3]卷六。向若冰跋语的丢失、“封”字印的残缺,对《茂林远岫图》本身来说是一次重大变故,对其真伪鉴定有着至为关键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一记载,后人恐怕再难弄清其中的玄妙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有些书画名迹上的印章,《清河书画舫》不仅录其文字,还仿其形制,刻印于所录内容之后。《清河书画舫》此类印记看似简单,却非常难得,对于后世考察藏家之印章及书画之流传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参考意义。
三、“附录”——“互证互见”的人物图谱
正如前文所述,《清河书画舫》以人为纲,在目录所列书画家之后有时会“附录”其他书画家。“附录”书画家与“目录”书画家之间并没有所谓的附属关系。一般来说,“附录”书画家的分量要轻一些,著录的内容也相对少一些。但不管是在人物关系、画作题材,还是绘画风格上,他们之间往往有着不容忽视的“互证互见”关系。《清河书画舫》以“附录”形式构建书画史的人物谱系,重点突出,层次分明,详略得当,有利于整个书画史的清晰展现。
书画家之间的“附录”之间有着特定的逻辑联系。
一种联系主要是人物之间的关系。如唐太宗名下附录唐玄宗,二者为父子关系。赵孟頫名下附录管道升,二人为夫妻关系。艳艳名下附录李清照,所录作品一为绘画,一为法书,但二人同为女性画家。又如李成名下附录许道宁,《画继》认为:“宋人画山水者,例宗李成笔法。许道宁得成之气,李宗成得成之形,翟院深得成之风,后世所有成画,多此三人为之。”[3]卷六由此可见二人师承之渊源。像《清河书画舫》这样按照人物关系来编排著录书画家,在书画史著作中并不多见,但这一著录体例有利于读者更为深入把握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好理解书画史。
另一种联系主要是作品题材或风格相近。如吴道子名下附录之卢楞伽,从著录内容来看,吴道子名下为《南岳图》《送子天王图》《洪崖仙图》《水月观音变相》《天龙八部图》,卢楞伽名下为《过海罗汉图》《维摩像》[3]卷四,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二人画作皆作道释题材。又如韩干名下附录胡瓌和东丹王,三人擅画犬马,各有所长。黄筌名下附录徐熙,虽画风不同,但二人同为花鸟画家。郭熙名下附录燕文贵,二人同为山水画家,郭熙画作清峭秀劲,燕文贵画作清逸可爱,画风相近而异。按照绘画作品的题材和风格进行“附录”式编排,是对现有书画著作体例的一种突破。这种编排模式有利于加强作家和作品之间的横向比较和纵向联系,对研究绘画发展规律和演进轨迹有一定借鉴意义。
还有一种联系主要是作品藏家之间的关系。作为书画收藏大家,张丑对许多书画名迹的来源去处了然于胸,故而能由此及彼,以书画作品的藏家或来源关系作附录叙述。
也许有人会认为《清河书画舫》将一些比较重要的书画家作为“附录人物”不甚合理,如周文矩附于李煜名下,徐熙附于黄筌名下,文徵明附于沈周名下。客观来说,周文矩在绘画史上的影响确实比李煜要大。但鉴于二者君臣之身份,以及李煜在政治和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种附录无可厚非。徐熙与黄筌同为花鸟画家,画法各有特色,著录作品数量相当,艺术影响也同样深远。但作为个人,相比徐熙质朴简练的“水墨淡彩”,张丑更喜欢浓丽工致的“写生”,黄筌的花鸟更符合他的审美趣味。另外,将文徵明附于沈周名下,主要是鉴于二人师承流派之关系,作者并没有在书中就他们的画史地位进行直接排序和比较。
不可否认,《清河书画舫》也有一些附录比较随意,如顾恺之名下附“晋人画《张茂先女史箴图》、宗少文《秋山图》、王洽《泼墨山水》、唐人《捕鱼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赵令穰《江乡雪意图》、赵伯骕《桃源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不管是从时代因素、人物关系、作品题材还是画家风格上,都很难发现这些画之间的联系,让人莫名其妙。这种不合时宜的附录是对原有编排体例的一种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著作内在的逻辑关联,显示作者对书画家及其作品的定位、统筹和认知能力的不足。由于是编所见均源于抄本,作者可能未来得及整理和修订,就将其抄录而流传开来。
四、“补遗”——“前后呼应”的续录
《清河书画舫》各卷之后皆有“补遗”一节,专门对正文中已列记的书画家及其作品进行资料补充和完善。“补遗”的内在体例与正文高度吻合,具有前后呼应的特点,内容丰富,体量巨大,是《清河书画舫》重要组成部分。从成书过程来看,《清河书画舫》有“初稿本”和“修订本”,具有“补遗”内容者均系“修订本”。《清河书画舫》初稿完成后不久,就在朋友间传抄流传开来。张丑后期修订并非仅是增加“补遗”,研究时应当尽量避免将正文和“补遗”区别对待。
从“补遗”内容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正文所载书画家生平、作品及其艺术等作进一步补充,此类内容最多。如卷三后“补遗”,分别对陶弘景、智永禅师、李世民、虞世南、阎立本、陆柬之、孙虔礼、王维等八人的生平进行了补充。其中,对李世民、虞世南、王维的介绍尤为丰富和具体。从全文来看,“补遗”类书画作品合计多达一百多件。仅以王维为例,其所补充著录的绘画作品有《辋川图》《江干雪意图》《袁安卧雪图》《辟支佛》《沧洲图》《寒林》《雪蕉》《雪霁捕鱼图》[3]卷三,与正文著录作品几乎相当。
二是直接增添书画家及其书画作品,或是书画见闻。如卷二“补遗”增录画家有赵干、郑虔、张璪、林藻四人,附录作品7件。又引《云烟过眼录》载“乔达之篑成仲山所藏”书画。卷五“补遗”增录《五公手札》,并介绍李纲之生平;又增录吴彩鸾、詹鸾及其作品等。卷七“补遗”增录陆游及其自书诗一卷十七首,其《大圣乐词稿》为张丑所藏。卷九“补遗”增录文天祥及其书法《木鸡集序》等。
三是“补遗”与正文内容有别,或提出新见等。如卷三“补遗”载展子虔《游春图》云:“前有宋徽宗瘦金书御题,双龙小玺,‘政和’‘宣和’等印及贾似道‘悦生’葫芦图书,曲脚‘封’字方印。至元时,其题识者三人:冯子振、赵岩、张珪也。而宋濓亦尝奉旨和诗在其右,皆绝品云。”[3]卷三“补遗”所载印章与正文同,但题识少了董其昌。又正文云《游春图》“近归犹子诞嘉”,并称其“十美具焉”;但“补遗”又记其为“韩存良太史藏”,且言“其布景与《云烟过眼录》中所记不同”。一般而言,“补遗”要晚于正文,但展子虔《春游图》又是张维芑购自于韩氏,未审何故。
张丑有时也会在“补遗”中提出新的看法。如卷三载:“孙虔礼字过庭,见陈子昂撰墓志。《宣和书谱》云‘孙过庭字虔礼’,甚谬。”[3]卷三在他看来,《宣和书谱》将孙虔礼的名和字搞颠倒了。陈子昂乃孙虔礼同时人,所撰墓志当属可信。又如卷十一言及自己“品画以精细为先”,对“宋元云山不甚留意”;又云“阅书必求上古所无”,感慨“蓄无唐人书者,有志欲购,亡高赀也”[3]卷十一。
五、文献征引与摘录——资料汇编利用的“集大成手”
征引是指因著录内容的需要,对其他文献进行数句或整段的引用;摘录是指与著录内容无关,而直接对其他文献进行选择性的摘抄或抄录。《清河书画舫》征引和摘录书画文献的情况非常突出,从比重和分量来看,约占全书之半。为此,该书也受到一些评论家批评,认为其仅是向书画古籍中寻生活,缺乏创见,“加稗贩耳”。实际上,该书文献摘录内容较少,相较其30多万字的巨著来说微乎其微。而作为“主力军”的文献征引与著录内容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全篇有机组成部分。今天看来,这些“征引和摘录”不仅保存了大量书画古籍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书画史料,具有补益书画史的作用。此外,对已有文献进行合理征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学术重复的一种有效规避。《清河书画舫》在这方面的探索值得肯定。作为一种体例及叙述方式的创新,只是它的“尝试”和“示范”没有被真正理解,研究者对此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包容。
《清河书画舫》的文献征引和摘录主要有广泛性、兼容性、集中性、规范性四大特点。“广泛性”是指引用文献种类多,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据统计,该书征引文献书籍近百种,既有广为人知的书画要籍,也有一些不太知名的书画著作,甚至有些文献今已不传。彭元瑞言其“特向项子京加稗贩耳”[2]548,其论甚谬。从征引文献的内容来看,有书画家的生平逸事、师承流派、书画特点、艺术风格等,也有书画作品的形制、内容、印记、流传和辨伪等。对于一些篇幅不长、流传不广,而对鉴藏书画却有重要意义的书画著录,《清河书画舫》有时会予以摘录。如卷七全文载录文嘉《严氏书画记》,卷一摘录《云烟过眼录》“兰坡赵都承与懃所藏书画”,其他诸如《米氏书史》《米氏画史》《宝晋英光集》等也有摘录。
“兼容性”是指将征引文献与编撰内容进行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征引内容与张丑撰述内容一起构成了李煜在书画史上的完整形象,每一条征引文献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可或缺,相互之间不能分割。又如李煜《重屏图》,张丑撰言曰:“旧藏汝阴王明清家,图中正坐者为南唐李中主也,此图与周文矩同作。”其后又引《寓意编》云:“李后主《重屏图》,后有宋人书白乐天及荆公诗、元滕玉霄词,杨仪部藏。杨致仕回,问之,则已赠京师人矣。”前者介绍了《重屏图》藏家、画面内容,并强调其为李煜和周文矩共同创作;后者则介绍其题跋及收藏情况。二者前后呼应,互为补充。
“集中性”是指大量征引各种文献,对某一具体“论题”展开全面论述。“论题”既可以是某种具体的意见或观点,可以是书画家的生平、艺术风格,也可以是具体的书画作品等。如《清河书画舫》卷二著录王羲之《东方朔画像赞》,张丑首言其创作缘由、递藏经过、著录文献及艺术价值等,又记其曾见“赵子昂有临本并跋,亦见韩太史家”,“较之真迹不差毫发”。其后引《山谷题跋》三条,一评其字,二评其摹本,三论其“为吴通微笔”。张丑认为《米氏书史》载之确然,黄庭坚故为“好奇之论也”。其后又引《米氏书史》叙其流传,与此前撰文相映照。
至于其他“论题”,特定观点如“无李论”“墨戏”等,书画家生平如王羲之、吴道子、米芾、李公麟等,书画家风格如李成、苏轼、黄庭坚、赵孟頫、黄公望等,都是广泛征引文献进行集中论述。
“规范性”是指按照文献合理使用规则进行征引。从全书来看,《清河书画舫》所有征引文献均注明出处、来源、作者等。一般多是在引文后直接注明所引书籍,也有时在论述中加以说明。索引资料注明出处和来源,今天看来似乎寻常,但在同时期的书画著录中还难以见到,体现撰者画史观念的进步和学术规范的自律。彭元瑞曾批评《清河书画舫》“人己之说不辨”[2]548,实乃不知之论。众所周知,不管是篇首引语,还是中间插言,只要是张丑撰文,原书在具体内容后皆注“丑言”二字;征引文献后又皆注明出处,“人己之说不辨”绝无可能。只是后人在传抄和刊刻时,删去了原先标明的己见,只低一格排版,容易造成误解而已。另外,张丑在征引文献时,同一“论题”,所引各书,基本以时代为序排列,“画史方法清晰、科学,使读者一目了然”[6]57,“青父之书最晚出,一时服其精当”[7]1。诚哉,严诚所言。
六、结语
《清河书画舫》为书画家立传,多载书画名迹,是名副其实的“书画舫”;品书论画,辨别真伪,颇具画品、画鉴特色。结构上,是书以时代为序、以人为纲,以作品为目,脉络清晰,条理分明;篇章上,以“附录”绘构完整书画家图谱,以“补遗”增添后续见闻,虽有断续之弊,却也前后呼应。《清河书画舫》“征引”与“摘录”虽多受质疑,但其往往与著述内容共为一体,不仅颇具文献价值,其详注所出,刻意规避学术重复,亦凸显学术态度之严谨。《清河书画舫》作为明代后期书画清赏展玩的著录新体,其创格应当受到更多关注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