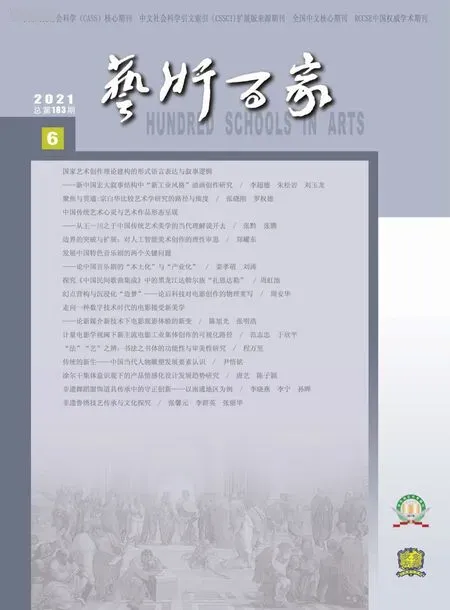非对象性美学的建构与艺术学理论知识的有效增长∗
——评赵奎英等著《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
李鹿鸣,程相占
(1.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2.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文化的转型,新的艺术类型的不断涌现,以往的美学理论在面对社会现实的变化、当代艺术实践的发展与审美领域的扩张时,越来越力不从心,于是,重建一种更具整合性、更富有解释力的美学理论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要想重建美学基本理论,我们就要在反思以往的美学理论存在哪些问题的同时,以此为基础和起点,提出一种能突破或超越以往美学理论局限的新美学理论或新美学观念,来回应当前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赵奎英教授主持完成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正是立足于当前美学研究与审美实践领域的新问题、新变化,借鉴吸收当代中西方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上述问题作出的总体回应。
一、从对象性美学到非对象性美学
《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首先梳理了中西方美学发展历程,并指出当今中西方美学界共同出现了一种“审美”转向,美学家们不再追问美的本质,也不再将美学简单地等同为艺术哲学,将眼光仅仅局限在艺术作品之上,而是将人类生存和文化实践所有领域的审美活动都纳入到美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当代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不是刻意追求标新立异,抛弃以往的观点主张从头重来,而是立足当下,参照中西方美学研究所取得的共同进展,并将其与当前的社会文化现实和审美活动实践领域的变化相结合。因此,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第一步就是将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然而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将审美活动确立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美学对象方面的重建工作大功告成,因为一旦我们将人类全部的审美活动都纳入考量范畴,便会发现按照以往对“审美”这一概念的理解来重建美学理论,既不能真正回应当前美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也无法真正超越以往的美学理论的局限。
现如今,我们对“审美”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受德国美学家鲍姆嘉滕的影响。1750年,鲍姆嘉滕在《美学》一书中正式为美学这门学科命名,并确立了美学的研究对象。在鲍姆嘉滕看来,“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1]13,“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1]18,换言之,美学就是“审美学”(aesthetics)、“感性学”,即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然而正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鲍姆嘉滕的这一定义以认识论对象性思维为前提,将审美活动当作对象性活动,单方面突出了主体的作用,而且它将感性认识与身体分离开来,只关注视、听这样的“高级”感官和心理活动。由此可见,鲍姆嘉滕虽然提出了“感性学”这一名称,但在他看来,“感性学”研究的并不是人类全部的感性活动(或审美活动)。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依循鲍姆嘉滕的定义,只是简单地返回到鲍姆嘉滕的“感性学”,那么以往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日常生活审美、各类环境审美、生态审美以及当代具有高度介入性的艺术实践等,便依然无法得到较为充分的解释。
除此之外,这种对于“审美”的理解还存在另外一个弊端,以此为依据建立起来的美学理论无法肩负起价值批判的作用。“一种理想的美学基本理论,不仅仅是解释性或分析性的,不仅仅是能够对已经出现的审美现象进行解释,肯定其合理性存在,或仅仅对其进行分析,帮助人们对它进行理解,而且也应是批评性、批判性和构成性的,亦即它能帮助人们对某种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做出审美评价和审美判断,发现其优点或问题,并对那些存在着问题的方面进行批判,引导、促进或构成一种健康的审美活动实践。”[2]14然而鲍姆嘉滕将美的根源归结于审美主体,并强调感性认识的“完善”,这多少体现了他的价值立场——纯粹的、理性的、存在于思想和认识层面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美,他因而也就相对贬低了外在于主体的自然的价值。在此之后,康德进一步界定了“审美”这一概念,使其更具有分离性和纯粹性,由此导致的后果如当代环境美学家和生态美学家所谴责的那样,这种“审美”的概念预设了主客体关系框架,并赋予审美主体以主导地位,因而具有主客体分离的二元论特征与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它不仅使得人们难以恰当地欣赏自然,这种观念甚至还要为当今的生态危机负有部分责任。
因此,正如本书所言,简单地返回到鲍姆嘉滕的“感性学”并不能真正实现当代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要想重建美学基本理论,首先要做的就是超越以往美学理论所秉持的认识论对象性思维。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分析、当代的现象学存在论哲学和具身认知科学都是对这种对象性思维的超越,它们都要求人们关注生活世界,重视生活现象与情境化的行动,而强调介入性、剧场性的当代艺术则通过打破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清晰划分,挑战了对象性美学的主张。有鉴于此,本书指出,上述观点与实践都可以作为重建美学基本理论的资源,用以超越以往的对象性美学。
此外本书还进一步指出,重建美学基本理论不仅仅是内在于美学自身的发展需求,它还是美学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于当前社会现实的回应,因此美学基本理论的建构本身也包含了一定的价值指向。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根本的生存关系,然而两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生态危机大大恶化了这一关系,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就此而言,当美学将关注的目光对准人类的整个生活世界的时候,人类也必须以秉持非对象性思维的生态审美观为指导。有鉴于此,本书提出了当代重建美学基本理论的目标,即构建一种非对象性的美学,这种美学要求我们在研究具体的美学问题时,综合运用语言分析、现象学存在论哲学、具身认知科学的方法,吸收当代艺术实践在打破主客体二分方面的探索,借鉴当代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研究的成果,以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重建一种以生态审美为指向、以艺术审美为依托、以生活世界为基底、注重身体诸知觉的、既具有理论解释性又具有文化批判性和实践构成性的美学基本理论”[2]15,而这种重建是对于作为“感性学”的美学的更高层次的复归。
二、非对象性美学对艺术学理论的意义
只有当这种非对象性的美学摈弃了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开始以一种情境化的、生态性的思维把握美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观念,并将人类生存和文化实践所有领域的审美活动都作为其研究对象时,美学才真正走出了“美学即艺术哲学”的误区。美学与艺术哲学关系的这一重要变化,使艺术不再是美学唯一的研究对象,美学因而拥有了更广阔的领地。而美学与艺术关系的这一变化,也为专门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产生提供了助力。
(一)艺术学理论的相对边界之确定
在我国,艺术学于2011年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学科门类之一,原先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升为一级学科,并更名为艺术学理论。至此,艺术学实现了学科建制层面的独立,但如果我们从具体研究的层面来看,艺术学理论的边界仍是不确定的,艺术学理论与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门类艺术学之间的关系仍是错综复杂的。然而一门学科的知识有效增长的前提是相对明确这门学科的边界,有了相对的边界,才能确立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相关研究才能有的放矢。但我们知道,边界不是绝对固定的,边界也不是单方面的,它总是相对于双方、甚至多方而言的,而《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一书提出的非对象性美学通过将人类的全部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为美学这门学科确立了相对边界,而这也就相对划定了艺术学理论的领地。当美学不再是艺术哲学的同义词时,以往的艺术哲学便成了一个居间领域,成为在美学与艺术学之间游动的东西。它既可以是美学的一部分,也可以由艺术学理论接管过来,成为艺术学理论的一个领域。由此,艺术学理论研究能够在艺术哲学的引导下,对总体艺术进行哲学思考,而这可以进一步深化、丰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有益于艺术学理论知识的有效增长。
(二)艺术学理论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式的革新
非对象性美学对于艺术学理论的另一个启发则在于,它的建构理念为艺术学理论借鉴吸收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指明了方向。非对象性美学对于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方面以当前美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为立足点,总结吸收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和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这四种当今美学具体形态研究和重建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它向上汲取现象学存在论哲学和具身认知科学的观点,向下以当代艺术实践和当代学者对具体门类艺术审美特征的阐释为研究基础,从而兼顾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建构理念。而如前所述,现如今艺术学已经获得了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并与美学和门类艺术学相区分,但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可能彻底割断。艺术(学)理论具有某种居间性,它之上有美学,它之下有艺术史和各门艺术理论,这种居间性固然使得其领地容易被美学以及艺术史、各门艺术理论所侵蚀,然而这也是其优势所在:一方面,它“在美学和各门艺术理论及其艺术史之间,可以将哲学和美学关于艺术的资源引入艺术各个领域,对艺术的分析和解释提供更具理论性的观念和方法”[3];另一方面,它能够“把具体艺术部门的各种现象及其特殊问题带入更高的理论层面,去激励艺术理论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甚至去叩响哲学殿堂的大门”[3]。就其前者而言,非对象性美学的建构理念能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革新艺术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式,从而促使艺术学理论知识有效增长,而这种影响又突出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非对象性美学对于“审美”以及审美活动的理解能够更新艺术学理论对于其研究对象的认识。艺术学理论不仅是“艺术研究”,而且是“艺术研究的研究”,所以它“不仅仅是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还以对艺术的各种研究作为对象,以艺术学的各级学科本身作为研究对象”[4]。就此而言,艺术在艺术学理论中处于中心地位。然而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艺术却是值得探讨的,对艺术这一概念的理解将塑造艺术学理论的面貌,影响艺术学理论的推进。而非对象性美学将审美活动确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指出审美活动不仅仅存在于艺术领域之内,而且还广泛存在于人类生存和文化实践的所有领域。这种划定一方面如前所述,明晰了美学和艺术学理论在研究对象方面的相对边界;另一方面,非对象性美学通过将审美活动确立为研究对象,完成了美学的“去艺术中心化”,丰富了我们对于艺术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就艺术的内涵而言,当我们以对象性美学为依据理解艺术时,就会将艺术当作客观存在的实体来研究,而非对象性美学通过强调审美活动的动态性、生成性与整体性,揭示艺术不是孤立存在的客体。因此,我们不能将艺术的内涵局限于作为“物”的艺术品的有形边界之内,艺术的内涵还要根据艺术与其他审美活动之间,以及艺术与环境、生活、身体、文化语境等之间的关系来界定,这样一来,艺术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便被打通了。就艺术的外延而言,当我们将非对象性美学对于审美活动和生活世界的关注引入到艺术学理论之中的时候,尽管艺术仍然是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但是艺术的集合已和此前大不相同。当我们研究艺术的时候,不应当还将目光仅仅局限于西方主流艺术、“美的艺术”、精英艺术,而应当同时关注通俗艺术、日常生活艺术、环境艺术、身体艺术、民间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等,而这种外延的扩展能够拓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从而丰富我们对于艺术学理论基本问题的阐释。
其次,非对象性美学所秉持的超越主客二分的非对象性思维能够为艺术学理论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正如《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一书中所指出的,“‘对象美学’秉持的是主客二分的二元论立场,它的要害在于忽视了审美活动的时间性、空间性、情境性、在场性、关系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特征,割裂了主体与客体,审美与生活、社会、伦理等的密切关联”[2]439。而非对象性美学对于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不是一种美学的具体形态研究,而是一种理念的变革,是在美学领域对于认识论对象性思维的超越,它在吸收现象学存在论哲学与具身认知科学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以揭示在以往的美学研究中对象性的思维模式所遮蔽之物。这种去蔽作用对于艺术学理论而言同样有效,因为这种思维模式不仅深刻影响了以往的美学,而且也支配着艺术学理论。当我们在研究艺术学理论的时候,往往会凸显传统艺术作品中的物化、对象化特征,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将非对象性美学的理念引入到艺术学理论研究之中,则可以看到艺术活动与广大的审美活动一样,都存在于一个审美场域之中。作为“物”的艺术作品与艺术作品中的“物”看似是预先存在的、确定的客体,但它们实际上并非孤立存在、有待观审的对象,而是一种存在者整体,一种有可能激发审美经验的审美“缘素”。同样,参与到艺术审美中的人也不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而是有可能启动艺术的“缘发”结构。对于艺术的审美经验也同样是一种审美“缘素”和审美“缘构”在审美场域中的遭遇,这种遭遇不是艺术家或审美者站在艺术作品之外,静观作为对象的艺术作品,而是一种“具身行动”,是“处在世界中的身体对整个情境做出的一种直接的综合的审美反应”[2]56。理论的本义是观看或观赏,它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视角,理论的变革就是通过视角的转换,看到以往未曾看到的东西,而非对象性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引领我们以非对象性的思维把握艺术学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从而促使艺术学理论知识有效增长。
(三)对于艺术现象的再诠释
非对象性美学的建构除了借鉴吸收哲学、认知科学领域的思想资源,还广泛关注艺术与审美经验的世界,关注现实中各个具体门类艺术的审美特征。这种建构思路正对应于艺术(学)理论居间性的第二方面。《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在建构非对象性美学的过程中,除了借鉴了生态美学、生活美学等美学具体形态的主张,以及哲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它还吸收了卡尔松、梅洛-庞蒂、柏林特、秦勇等对于建筑、绘画、文学、音乐、电影等门类艺术审美特征的阐释,并将一些打破主客体二分思维模式的当代艺术实践纳入考量。所有的理论都不是凭空搭建的空中楼阁,不是抽象概念发起的空洞的推演游戏,理论的构建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现象,并提出一种价值立场,以恰当地评判这些现象;理论的革新也不是在头脑中凭空产生的,它也必定要从现象中来。而非对象性美学这种自下而上的重建方式能够为艺术学理论建构一套非对象性的话语指明方向,艺术学理论知识的有效增长有赖于我们在汲取美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观点的同时,将目光对准各种艺术实践以及门类艺术学。
总而言之,《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一书对于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不仅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具有推进作用,而且该书提出的建构非对象性美学的主张超越了以往美学研究所秉持的认识论对象性思维,在观念上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因此它所能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了美学这一领域。非对象性美学的建构理念与建构方法对于艺术学理论这样的美学相邻学科同样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如果我们能以此为思想资源建构艺术学理论,那么也能促使艺术学理论知识的有效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