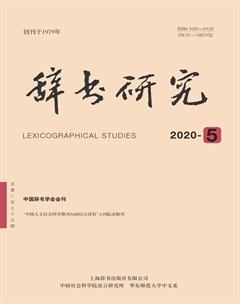“你”字前夜的“尔”与“汝”



摘 要 文章主要考察“你”行用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尔”“汝”的使用情况,认为“尔”“汝”有地域之别: 南朝口语说“汝”,“尔”已经是个文言词,完全退出了口语。北朝口语说“汝”,也说“尔”;“汝”是北朝通行的第二人称代词,相当于通语,“尔”带有地域色彩,较“汝”更为鄙俗。“尔”读音分化以后,产生新的书写形式“你”。“你”以北朝为出口,走出中古,迈向唐代,再次与“汝”展开竞争,最终成为汉语第二人称代词的唯一形式。
关键词 尔 汝 口语 地域 北朝
一、 问题与语料
(一) 提出问题
邓军(2008)调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尔”“汝”的句法功能已经无甚差别,据此本文不再探讨它们在南北朝的格位差异。在南北朝文献中,“尔”“汝”往往并用,如果二者没有语法、语义、语体上的区别,那么正如何大安(1993)所指出的,“毫无差异的两个同一指称的代名词并存的现象,是很奇怪的”,因此“尔汝在中古时期,应该有些细微的分别”。何先生的考察结论是,“尔汝似乎有着语境上的不同: 尔字古雅庄严,汝字平易无文”,“尔容易出现在较文雅、较庄重的场合,汝则否”,“中古时期尔汝的分别是在风格上的,前者庄重文雅,后者平易近人”;但是进一步观察语料,可以看到大量与上述观点相反的例证,因此何先生的结论还可推敲。本文旨在进一步调查“尔”“汝”在南北朝的使用情况,以窥其差别到底表现在何处。
(二) 语料說明
人称代词在会话中使用得最为频繁,因而本文以会话材料为核心语料;某些书信、家诫,甚至诏敕,口吻辞气一“如面谈”,可以看作“类会话”。会话和“类会话”材料尤以史书为富,所以南北朝史书(包括《隋书》《南史》《北史》)是本文重点调查的文献。
1. 应剔除的两类例子
a. 剔除史书所引用或承袭前代文献中的“尔”“汝”例
《魏书·张普惠传》:“《书》曰: ‘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非其人,惟尔弗任。”
此例明引《尚书》。
《宋书·乐志二》:“尔公尔侯,鸣玉华殿。”
此例暗引《诗经》。
《宋书·五行志》:“魏齐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有鼠从穴出,语曰: ‘王周南,尔以某日死。”
此例实据曹丕《列异传》。
《宋书·五行志》:“晋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 ‘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
此例引用东晋民歌。
b. 剔除史书所载异域材料中的“尔”“汝”例
《南齐书·东南夷传·扶南国》:“十余年,蔓少子长袭杀旃,以刃镵旃腹曰: ‘汝昔杀我兄,今为父兄报汝。”
此类例子情况比较复杂,姑且也排除在外。
2. 统计时应调整的例子
《魏书·岛夷刘裕传》:“子业曰: ‘若不从,当杀汝三子。”
《南史·贼臣传·侯景》:“裨将斛律光尤之,绍宗曰: ‘吾战多矣,未见此贼之难也。尔其当之。”
前例出《魏书》,但恐怕不能看作北魏用例;后例出《南史》,但慕容绍宗是北朝人,也不能算作南朝之例。本文如有涉及这种情况的例子,仍然依据说话人的身份归属于北朝或南朝。
3. 史书会话的“作者”及时代
史书所记人物会话,其生成方式有几种可能: 一是说话人言谈的实录,二是史书作者在言谈实录的基础上加以改易,三是史书作者的拟作。因此史书会话的“作者”就有三种可能: 说话人、史书作者+说话人、史书作者。这三种情况应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较难甄别,因此只能依据便于处理的方式来分析判断,否则简直无从使用这些语料。
一般说来,史书所载的对话——普通读者仅凭自身语感即能意识到浅俗鄙俚的——往往是说话人言语的实录,即使所记时代和作者时代不一致的史书也是如此。太田辰夫(1988/1991)指出北朝汉儿言语“只不过在《北齐书》《北史》《隋书》等史书中有极片断的传述。这些书籍都是在唐代编纂的,尽管如此,好像还没有必要把这些书里面记录的语言下限推到唐代。它们都是用当时的资料而在后来编写的,即使编纂时表达有所改动,也只限于把口语的表达改成文语的场合,把文语的表达改成口语的情形极少有”,这个观察和判断是很准确的。汪维辉(2000/2017)也指出“一般说来,史书中的对话部分也是比较接近当时人的语言的,因为史家在描述人物时往往有意识地注意到语言的个性化和真实性。……就一般情况而言,史书中出现的那些俗语俗词,大多是保存前代的原貌,较少出自后人的改写”。笔者曾考察《资治通鉴》与所据史料之间异文所体现的文白差异[1],确实如上述学者所说,改雅为俗的情况几乎未见于《资治通鉴》,也就是说,《资治通鉴》中那些口语片段都是沿用前代史料,那么判断这些片段的时代,就不必泥于北宋,反而看作原始年代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由此,正如太田先生所言,《北齐书》《北史》《隋书》所记载的“汉儿言语”可以看作是北齐周隋时代的语言现象。
哪些会话片段完全非说话人之语而是史书作者虚拟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无从判断;但有些地方,是可以断定的。《魏书·节义传·朱长生》:“(高车主阿伏至罗)夺长生等献物,囚之丛石之中,兵胁之曰: ‘汝能为我臣则活,如其不降,杀汝!长生与于提瞋厉声责之曰: ‘岂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宁为魏鬼,不为汝臣!”高车兵非能汉语,“汝能为我臣则活,如其不降,杀汝”之语当是史书编者拟写。《梁书·诸夷传》:“见观世音语云: ‘汝缘未尽,若得活,可作沙门。”这显然也不会是说话人的真实言语,只能出于虚构。此外,《魏书》所记孝文帝元宏之前的鲜卑君臣的会话也不可能是实录。
鉴于此,本文在利用南北朝史书材料时,主要使用当朝人物纪传中的语料;以会话为基本材料,以“类会话”为次要材料,以其他为辅助材料;除了上述几类应剔除的材料外,本文从权将某断代史中所出现的“尔”“汝”的时代均定于史书记述年代,同时充分认识史书材料的复杂性。在举例时,为了便于对比及说明问题,也略举文言性的例子。
4. 中古译经“尔”“汝”的性质
南北朝译经数量庞大,其中颇多对话,理应作为考察当时“尔”“汝”的重要语料;不过中古译经在“尔”“汝”使用上似乎有其特殊性。
从东汉译经开始,第二人称代词就习用“汝”,“尔”大约仅见于《修行本起经》《成具光明定意经》,共5例。
据曾亮(2007)统计,三国译经中“尔”的用例远少于“汝”(43: 934),只有康僧会译经中“尔”多于“汝”(210: 54)。众所周知,康僧会译经的语言务求典雅,“尔”用例较多应是习用文言词的结果。据龙国富(2013),《妙法莲华经》只用“汝”“汝等”,无一例“尔”。进一步抽查7部南朝译经,也可发现几乎一律用“汝”,详见表1。
据萧红(2010)统计,北朝4部译经也基本用“汝”,详见表2。
由此看来,东汉南北朝译经用“汝”应是一种沿袭已久、固化了的用词习惯。
朱庆之(2012)考察东汉译经第一人称代词后指出“这种新型的文体为后来的译经普遍采用,就是日后成熟的‘译经体的雏形”[3]。那么东汉译经第二人称代词基本用“汝”日后也成“译经体”,对称用“汝”成为一种固定的翻译模式,为魏晋南北朝译经所沿袭;换句话说,东汉译经中的第二人称代词“汝”是当时口语的反映,而南北朝译经中的“汝”就未必完全体现实际口语,反而可能是一种程式化的翻译用语,这和译经中大量使用的“彼”并不反映口语是一样的。(汪维辉2017)基于此,本文就不再调查南北朝译经。
二、 南朝的“尔”“汝”
本节所调查的南朝文献以史书为主[4],《宋书》《南齐书》是主要材料,《梁书》《陈书》及《南史》增补部分作为参证。除史书外,《周氏冥通记》也是重点调查对象。
(一) 《宋书》《南齐书》中的“尔”“汝”
1. “尔”的用例[5]
(1) 尚书符征西府曰: ……或能因罪立绩,终不尔欺,斩裾射玦,唯功是与。
(2) 修之自州主簿迁司徒从事中郎,文帝谓曰:“卿曾祖昔为王导丞相中郎,卿今又为王弘中郎,可谓不忝尔祖矣。”
(3) 闲居无事,为《庭诰》之文。……曰:“……吾年居秋方,虑先草木,故遽以未闻,诰尔在庭。……此固少壮之废,尔其戒之。……此亦持德之管龠,尔其谨哉。”
(4) 滍水诸蛮因险为寇,雍州刺史随王诞遣使说之曰:“顷威怀所被,覃自遐远,顺化者宠禄,逆命者无遗,此亦尔所知也。”
(5)甲寅,策相国齐公曰:“……锡兹玄土,苴以白茅,定尔邦家……其祗服朕命,经纬乾坤,宏亮洪业,茂昭尔大德,阐扬我高祖之休命。”
(6) 见一乌漆棺,敬则曰:“尔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进。吾富贵,当改葬尔。”
(7) 僧虔宋世尝有书诫子曰:“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各在尔身己切,岂复关吾邪?”
2. “汝”的用例
(8) 以锦囊盛高祖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食,便欲残害我儿子!”
(9) 元凶入弒,事变仓卒,旧将罗训、徐罕皆望风屈附,天与不暇被甲,执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战。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为?”天与骂曰:“殿下常来,云何实时方作此语。只汝是贼。”
(10) 潘淑妃抱持浚,泣涕谓曰:“汝始咒诅事发,犹冀刻己思愆,何意忽藏严道育耶?上责汝深,至我叩头乞恩,意永不释。今日用活何为,可送藥来,当先自取尽,不忍见汝祸败。”
(11) 三年,建康民陈文绍上书曰:“……诞见符至,大怒,唤饶入交问: ‘汝欲死邪?诉台求解。饶即答: ‘官比不听通家信,消息断绝。若是姊为启闻,所不知。诞因问饶: ‘汝那得入台?饶被问,依实启答。既出,诞主衣庄庆、画师王强语饶: ‘汝今年败,汝姊误汝。官云小人辈敢持台家逼我。”
(12) 诞于城上授函表,倩庆之为送,庆之曰:“我奉诏讨贼,不得为汝送表。汝必欲归死朝廷,自应开门遣使,吾为汝送护之。”
(13) 上既杀休仁,虑人情惊动,与诸方镇及诸大臣诏曰:“……休仁又说休佑云: ‘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许为家,从来颇得此力。但试用,看有验不?……及在房内见诸妓妾,恒语: ‘我去不知朝夕见底,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乱人耳。”
(14) 每见钱,辄曰:“我昔时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
(15) 敬则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关汝小子!”
(16) 上敕之曰:“吾前后有敕,非复一两过,道诸王不得作乖体格服饰,汝何意都不忆吾敕邪?……”又曰:“汝比在都,读学不就,年转成长。吾日冀汝美,勿得敕如风过耳,使吾失气。”
3. 分析和推论
调查《宋书》《南齐书》“尔”“汝”例,可以看到几个现象:
1) 从用例数量看,“尔”远少于“汝”(37: 235)。
2) 从分布看,“尔”主要用于策、符、诏等公文,即使用于诗、赋、书信,也是在正式场合下使用的;用于自然会话和“类会话”的数量极少。“汝”则大量用于日常会话,即使用于诏敕书信,它们也都属于“类会话”。
3) 从发话者或受话者的身份看,“汝”的使用是很灵活的,既有上级对下级、地位尊贵者对卑下者,也不乏相反的情况,地位相等者同样可用“汝”。
例(11)发话者为竟陵王刘诞,时任司空,受话者(即“汝”之所指)为陈饶,时任司空府史,这是上级称下属为“汝”。例(12)沈庆之称竟陵王刘诞为“汝”,这是位卑者称位尊者。也不乏对地位相等者称“汝”的情况,如例(13)刘休仁称刘休佑为“汝”。
4) 从语体风格看,“尔”所在的语句往往典雅正统,“汝”所在的语句基本上明白如话。
对于这一点,还有若干旁证可以进一步明之:
第一,“降辞”中称呼周子良除了用“尔”以外,还多处用“卿”(偶尔用“君”)。以“卿”称周子良一方面显示仙真与凡人间的阶级性,另一方面也表现谈话的正式意味。
第二,观察“汝”的使用场合,例(36)出于“冥通”记录之前的《周子良传》,发话者为周子良,“汝”指其弟周子平。例(37)也出于《周子良传》,发话者为周子良的姨母,“汝”指周子良。由此可见,周子良及其姨母的日常口语应说“汝”而非“尔”。例(38)开头周真人称“尔”,但当周子良回答错误,周真人“勃然”詈为“谬滥”后就称之为“汝”,这显然是生气时顾不得用词雅驯冲口而出的口语。
第三,《真诰》与《周氏冥通记》相类,《真诰》“仙真降诰”中“尔”“汝”并用,应该与书成众手、文辞未经整饬有关;对于这些所谓“仙真降诰”的词句,陶弘景在整理时是不会改动的(这从陶弘景校订《真诰》文字的方式亦可见一斑)。《周氏冥通记》情况不同,它实际上只经陶弘景一人之手,王家葵(2019)认为“《周氏冥通记》中的那些降辞,一定是经陶弘景篡改,或根本就是陶弘景编造出来的”,从仙真言谈第二人称代词一律用“尔”的情形来看,确实存在刻意编排的痕迹。
第四,《宋书·颜延之传》所载《庭诰》是长辈对家中晚辈的诰谕,其中称呼受诰者均为“尔”,如“诰尔在庭”“尔其戒之”“尔其谨哉”,用“尔”是为了特定的语用需求——凸显长幼尊卑之别,《周氏冥通记》的情况显然与此相同。
综上所述,《周氏冥通记》第二人称代词“尔”的数量远超“汝”并不是真实口语的反映,应是在语用需求促发下的刻意遣辞。萧红(2010)依据“在南朝一些文献如《周氏冥通记》中,‘尔出现了逆转,超过了‘汝”的情况,认为“南方文献中‘尔潜在的发展劲头更强”,恐非事实。
(四) 小结
综上所述,南朝口语第二人称代词说“汝”,“尔”已经完全书面化。梅祖麟(2011)认为“汝”在南北朝时是江东方言,从现存材料看,“汝”恐未必局限于方言;不过南朝口语只说“汝”不说“尔”应是事实。据《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现代汉语方言中唯闽语说“汝”[7],汪维辉(2018)指出这是闽语的特征词。闽语中的“汝”应该就是南朝口语的孑遗。
三、 北朝的“尔”“汝”
(一) 《魏书》中的“尔”“汝”
1. “尔”的用例
如同南朝史书,“尔”在《魏书》中也用于策、诏等公文,例不赘举;除此以外,还有些例子值得注意:
(40) 禎告诸蛮曰:“尔乡里作贼如此,合死以不?”蛮等皆叩头曰:“合万死。”
(41) 每以鲠气正辞,为北海王详所忿,面责忠曰:“我忧在前见尔死,不忧尔见我死时也。”
(42) 及彪之抗冲,冲谓彪曰:“尔如狗耳,为人所嗾。”
(43) 此人具以报,崇摄庆宾问曰:“尔弟逃亡,何故妄认他尸?”
(44) 主簿杨僧覆先行晓喻,诸氐忿曰:“我留刺史,尔送出也!”
2. “汝”的用例
(45) 坦傲佷凶粗,从叔安丰王延明责之曰:“汝凶悖性与身而长,昔有宋东海王袆志性凡劣,时人号曰‘驴王。我熟观汝所作,亦恐不免驴号。”
(46) 此人自称:“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违!”
(47) 景乃谓衍曰:“确与威方频隔岸见骂,云: ‘天子自与汝和,我终不置汝!我今便不敢去,若召此二人入城者,吾当解围。”
(二) 《北齐书》《周书》《隋书》及《北史》增补史料中的“尔”“汝”
1. “尔”的用例
《北齐书》中频见“尔”,何大安(1993)已经注意到“北齐使用尔的特别多”,如:
(48) 光禄少卿元子乾攘臂击之,谓腾曰:“语尔高王,元家儿拳正如此。”
(49) 京再诉,王使监厨苍头薛丰洛杖之,曰:“更诉,当杀尔。”……京闻之,置刀于盘,冒言进食。王怒曰:“我未索食,尔何据[遽]来!”
(50) 武成践祚,逼后淫乱,云:“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帝横刀诟曰:“尔杀我女,我何不杀尔儿!”
(51) 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谁是尔叔?敢唤我作叔!”
(52) 文宣尝见之,怒,使以马鞭击其额,血被面,曰:“尔反时当以此骨吓汉。”
(53) 景曰:“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
(54) 后责纮曰:“尔与纥奚舍乐同事我兄,舍乐死,尔何为不死?”
(55) 天保二年,从驾至晋阳,于宫门外骂元韶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即知死也,然尔亦讵得几时!”
(56) 帝大怒,召德政谓之曰:“闻尔病,我为尔针。”
(57) 并与诸勋冑约:“行酒至愔等,我各劝双杯,彼必致辞。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尔辈即捉。”
(58) 先是童谣曰……“羊羊吃野草,不吃野草远我道,不远打尔脑。”
(59) 猛父母兄弟皆在山东,尔朱京缠欲投高祖,谓猛曰:“王以尔父兄皆在山东,每怀不信,尔若不走,今夜必当杀尔,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从。京缠曰:“我今亦欲去,尔从我不?”猛又不从。京缠乃举槊曰:“尔不从,我必刺尔。”猛乃从之。去城五十余里,即背京缠复归尔朱。及兆败,乃归高祖。高祖问曰:“尔朱京缠将尔投我,尔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陈服事之理,不可贰心。高祖曰:“尔莫惧,服事人法须如此。”
(60) 雄按槊不及明月者丈余,曰:“惜尔不得杀,但生将尔见天子。”
(61) 穆乃以策抶太祖,因大骂曰:“尔曹主何在?尔独住此!”
(62) 齐神武使谓城中曰:“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
(63) 太祖抚掌曰:“我解尔意,欲激我耳。”
(64) 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骂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
(65) 昂奋头曰:“来,与尔开国公!”
(66) 文襄匿暹,为之请,神武曰:“我为尔不杀,然须与苦手。”
(67) 邢子才云:“尔妇疾,或问实耶?”业兴曰:“尔大痴!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谁检看?”
(68) 开皇中,有司奏智积将葬尉太妃,帝曰:“昔几杀我。我有同生二弟,并倚妇家势,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 ‘尔既瞋我,不可与尔角瞋。并云: ‘阿兄止倚头额。时有医师边隐逐势,言我后百日当病癫。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谓我曰: ‘尔二弟大剧,不能爱兄。”
2. “汝”的用例
(69) 有郑氏者,叡母之从母姊妹之女,戏语叡曰:“汝是我姨儿,何因倒亲游氏?”
(70) 帝以众人意未协,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龙,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终,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
(71) 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颈,骂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谁教汝?”
(72) 胜适与齐神武相遇,因字呼之曰:“贺六浑,贺拔破胡必杀汝也。”
(73) 太祖喜曰:“事平之日,当赏汝佳口。”
(74) 强练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贵贱。”
(75) 臻住城南,讷住城东,臻尝欲寻讷,谓从者曰:“汝知刘仪同家乎?”从者不知寻讷,谓臻还家,答曰:“知。”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门,臻尚未悟,谓至讷家。乃据鞍大呼曰:“刘仪同可出矣。”其子迎门,臻惊曰:“此汝亦来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于是顾盼,久之乃悟,叱从者曰:“汝大无意,吾欲造刘讷耳。”
(76) 曾至彭城王浟宅,谓其母尔朱曰:“忆汝辱我母婿时,向何由可耐。”
(77) 周文大窘而走,曰:“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邪?”
(三) 分析和推论(四)
1. “尔”“汝”皆用于北朝口语
“尔”在北朝的使用情况与南朝截然不同,它仍然频繁用于北朝人口头。“汝”也是北朝口语。
“尔”“汝”均用于口语性非常鲜明的语句。可以看以下例子:
尔乡里作贼如此,合死以不?
谁是尔叔?敢唤我作叔!
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爾!
尔大痴!
汝取一只箭折之。
谁向汝道耶?
汝既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是河水之河?
这样的语句,读者仅凭语感或者直觉即可知道,这就是当时口语;若一定要说“尔”或“汝”是文言,实在不合情理。
“尔”所在句子多用口语成分,“尔”与之并现,如:
我忧在前见尔死。
“在”做时间介词虽然先秦已见[8],但行用开来大概是在中古;介宾结构“在前”处于中心成分“见尔死”前。可以相信,句中的“在前”应是当时口语。
我会杀尔妇。
“会”做副词表示终究、总归,是中古新兴成分,也是当时口语。
尔反时当以此骨吓汉。
“吓”表(使)害怕,“汉”为北朝少数民族贵族对汉族人的贱称,均为当时口语。
在上述句子中,“尔”与这些口语性很强的成分共存并用,可推想“尔”的语体性质也应与这些成分一致。北朝史书中的这些“尔”与南朝史书中“尔其图之”“善修尔略”“以庇尔躬”“尔实冠群后”这样文言意味浓烈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
“汝”在否定句中做宾语均置于谓语动词后,如:
天子自与汝和,我终不置汝。
厍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
柳士镇(1992)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否定句代词宾语后置的词序在口语中已经基本定型”,“如果说此期汉语中‘主语+动词+代词宾语的词序已经基本确立的话,那么主要应当指否定句中代词宾语的位置,而且限于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载籍之中”,这实际意味着否定句代词宾语后置就是当时的口语表现。在上引二例中,“汝”在否定句中做宾语均在谓语动词后,充分说明了“汝”必定是当时的口语词。
“汝”可居于领位,且“尔”“汝”做领位时后可加“之”,如:
汝父如龙,汝兄如虎。
吾今取汝头。
朝廷不治,实尔之罪。
尔之罪恶,人神所弃。
尔之罪状,计不容诛。
汝之过失,已备积于前。
汝之官位,当复及吾。
“汝”在先秦汉语一般不处于领位(做定语)。据漆权(1984),《史记》30例“汝”中有7例处于领位;据庄正容(1984)、冯春田(1992)、邓军(2003)、程亚恒(2007)、曾亮(2007),汉魏以来“汝”处于领位越来越普遍,这是“汝”在后世发展的重要表现。据周法高(1959)、魏培泉(2004),汉代以来,“尔”“汝”处于领位时后面可以加“之”,这也是先秦汉语不曾出现的新变化[9]。这些发展变化应该在口语中最先出现,然后记录于书面语。换句话说,这些发展变化反映了实际口语。北朝文献中“汝”居领位已有不少例子;“尔”“汝”居于领位时,固以后不加“之”为常,但也不乏加“之”之例,上文已引。这些不符先秦文言语法的“尔”“汝”,应该具有口语基础。
综上所述,北朝口语中“尔”“汝”并用应是不争的事实。
2. “尔”“汝”在北朝的差异
在一个共时共域的口语系统中几乎不可能同时使用两个完全等同的第二人称代词(王力1958/1980),既然“尔”“汝”并用于北朝口语,那么它们必然有所差异。
魏培泉(2004)论及“尔”“汝”时认为,“尔”这个词“应该一直保存在一些方言中”,“大概一直保存在山东、河北一带”。这一观点虽然大抵属于推论,但颇能给人以启发。据上文所引“尔”在南朝文献和北朝文献中的分布推断,“尔”在南北朝时确实仅存留于北方口语。由此不妨提出一种假说: “汝”是北朝通行的第二人称代词,相当于通语;“尔”可能带有更鲜明的地域色彩及更鄙俗的语体色彩,在特定语境中往往具有一种对受话者表示轻蔑、鄙视的语用效果。
北朝“尔”“汝”之别,以下一些材料或能说明一二:
《十六国春秋·前秦录》:
大呼曰:“杀君贼姚苌,出来![吾]与汝决之!何为枉害无辜!”[10]
《魏书·临渭氐苻健传》改作:
登每围苌营,四面大哭,哀声动人,大呼曰:“杀君贼姚苌,出来!吾与尔决!何为枉害无辜!”
在《十六国春秋》中,苻登指称“杀君贼姚苌”用“汝”;但魏收编纂《魏书》袭用《十六国春秋》这段材料时,将“汝”改作“尔”,其改易动机应该就是为了起到轻贱姚苌的效果。由此可以推测,在北魏口语中,“尔”显然比“汝”更能传达出一种轻视的语用效果。
《北齐书·高昂传》:
追者见其从奴持金带,问昂所在,奴示之。昂奋头曰:“来,与尔开国公!”
《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四年》改作:
追者见其从奴持金带,问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奋头曰:“来,与汝开国公!”
《资治通鉴》参用前代史文常常以文言改易史文中比较口语化的词句,在司马光时代,口语中第二人称代词已是“你”,“汝”成为文言词。在《资治通鉴》编修者看来,《北齐书》中的这个“尔”显然太不雅驯,因此改作最习用的文言词“汝”。
北魏孝文帝元宏积极倡导学汉语、说汉语,《魏书》所记载的他的言谈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尔”“汝”性质的差异。通过调查发现,元宏言谈对话一律说“汝”,无一例“尔”。可以推想,元宏所学所说的汉语必定是当时通语,如果《魏书》所载诸例是真实记录的话,“汝”的性质就很明显了。
《周书·晋荡公护传》记载了北齐以护母阎姬名义写给宇文护的书信,在这封信中,指称宇文护通篇用“汝”。这封信虽然是以母亲口吻写给儿子,多叙家常,语言通俗(特别是第二段),但毕竟是在两国以之为筹码进行利益交换的特殊情况下写成,指称宇文护的第二人称代词显然应稍显正式而不宜过于鄙俗,因此通篇用“汝”而无一例“尔”,由此也略可窥见“尔”“汝”之异。
《宋书·臧质传》记载臧质在盱眙阵前与拓跋焘书,信中对拓跋焘极尽诋斥嘲讽之事,指称拓跋焘一律用“尔”。上文已述,南朝说“汝”,“尔”已是文言词,但此信出于南人之手,且语言并不典丽,何以一律用“尔”?原因应该在于: 指称对象是北朝人,故用北朝之语,“尔”并非南朝口语。之所以用“尔”不用“汝”,恐怕不是因为这种嘲诋语境只用“尔”,而是“尔”更为鄙俗,可以起到轻视拓跋焘的作用。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成立,那么说明当时南朝人对北方的“尔”的用法是很清楚的。
不过,北朝史书中还能见到“尔”“汝”用在同一句子或同一会话情境的情况:
临刑,太宗谓之曰:“终不令绝汝种也,将宥尔一子。”(《魏书·封懿传》)
世宗谓之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北齐书·赵郡王琛传》)
既而大悦,谓公主曰:“李敏何官?”对曰:“一白丁耳。”上因谓敏曰:“今授汝仪同。”敏不答。上曰:“不满尔意邪?今授汝开府。”(《隋书·李穆传》)
一句话中表达同一人称同时使用几个不同代词,这在古代文献中并不罕见。漆权(1984)、魏培泉(2004)、汪维辉(2016,2017)均谈及这种情况。王力(1958/1980)指出“如果在同一部书里,特别是在同一篇文章里,甚至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时用‘吾和‘我(或同时用‘吾和‘予等),或者同时用‘汝‘尔,就不能归结于时代不同和作者不同。如果说毫无分别的两个人称代词在一种语言中(口语中)同时存在,并且经常同时出现,那是不能想象的”。
就上引同时使用“尔”“汝”的例子看,这应是书面语避复以修辞,是人为的产物,并非自然口语的反映。
(四) 小结
北朝口语既说“汝”,也说“尔”,前者大约是通语,后者有地域色彩,大约是方俗语。梅祖麟(2011)认为“北人所说的河北方言第二人称不用‘汝而用‘尔、‘你”,“从南北朝开始,汉语的河北、江东两大方言已经产生基本分歧,其一便是人称代词‘你/汝”,可能还不够准确。南北朝时期,大江南北之口语均应以“汝”为通语,只是在北方的方言俗语中仍然保留“尔”。
四、 走出中古: 第二人称代词“你”的“北朝出口”假说
呂叔湘、江蓝生(1985)推测“‘尔的语音跟读音在南北朝时已经分化了”[11],并认为语音跟读音分歧之后,在字形上加“亻”作“你(儞)”以示分别,这是很有道理的[12]。北朝史书记录了若干“你”的用例,吕叔湘、江蓝生(1985)列举详备,兹不赘。
由于缺乏资料,“尔”在南北朝时口语音跟读书音到底有何不同不得而知。不过据《广韵》的记载推测,当时分化后的读书音跟口语音的差异应该不大。“尔”古为泥母字,《广韵·纸韵》儿氏切:“尔,汝也。”日母纸韵上声,这应是分化出来的读书音;又《止韵》乃里切:“伱(你),秦人呼旁人之称。”泥母止韵上声,这是保留了古读[13]。日母、泥母关系密切,章太炎有“娘日归泥”说[14],因此,“尔”之口语音跟读书音的差异可能就在韵母微变。
太田辰夫(1988/1991)分析有关用例中说话者的身份,认为“你”是北朝的“汉儿言语”。据太田先生的分析,“汉儿言语”是当时非常土俗的口语。《广韵》释“你”为“秦人呼旁人之称”,这一记载当前有所承,如果所记准确的话,“你”至少在南北朝晚期唐代初期应属关陇(秦)方言[15]。由此看来,“尔”既存于北朝的方言土语,还保留了古读[16]。
由于“尔”读书音和口语音分化,为了相区别,读书音的记录形式仍作“尔”,口语音的记录形式则调整为“你”[17],“尔”“你”可以看作一个词因文白异读衍生出的不同的书写形式。不过这是专业研究者的定性,就普通人的语感和认识而言,“尔”“你”就是两个不同的词[18]。进一步推测,这两个“词”的语体性质应该也有差异,前者大抵用于文言,后者乃是口语词。这样的话,北朝的“尔”其实可以分为两类:“尔1”读儿氏切,用于书面,完全是文言词;“尔2”,又写作“你”,读乃里切,用于口语,是当时的方俗语词。如以下《北齐书》二例:
其祗顺往册,保弼皇家,用终尔休德,对扬我太祖之显命。
帝谓愔曰:“王元景是尔博士,尔语皆元景所教。”
前例中的“尔”应是“尔1”,后例中的“尔”就是“尔2(你)”。
汉魏以来,“尔”实际上已经式微,处于退出历史舞台的十字路口;不过“尔2(你)”作为一种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面临特定的历史契机可能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隋唐定都长安,关陇方言成为统一政治体中的强势方言,属于该方言的成分自然可能扩散开来,摆脱地域性,进入通语。在此背景下,原本兼具社团方言和地域方言两种性质的“尔2(你)”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作为强势方言的一分子,向其他区域扩散,逐渐脱离“汉儿”与关陇,终于走出中古并重新与“汝”开展竞争,(吴福祥1995)最终成为汉语第二人称代词的唯一形式。
冯春田(1992)说:“至于为什么汉以后处于劣势的‘尔取代了‘汝(女)而成为后来的‘你,或者说作这种变化的动因主要是什么,还不很清楚。”[19]现在看来,有以下几个因素促成了这种变化:
一是“尔”在北朝发生口语音跟读书音的分化,并为口语音创制了新字形“你”,“你”作为“语言新质”始终存留于一定人群、一定区域的口语。
二是北朝统一南朝,隋唐王朝首都所在的关陇地区的方言占有强势地位,为“你”的扩散创造了条件。
三是“你”作为一定意义上的“语言新质”,并裹挟强势方言之势,较有活力;而“汝”行用多年,逐步成为旧成分。
如果“尔”在北朝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它可能就随汉魏以来的衰微之势逐步退出口语;如果不是北朝完成统一从而使关陇方言成为隋唐强势方言,那么“你”可能始终是个方言成分。从这个意义而言,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你(尔)”就是经由北朝这个“出口”走出中古,迈向隋唐的。
阎步克(2017)曾论及北朝这个历史“出口”:
中古时代,是经由北朝而走出中古、走向隋唐盛世的;对魏晋南北朝这个政治低谷,北朝构成了它的“历史出口”。
从汉语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汉民族共同语至唐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不少重要的或具有分期意义的语言现象。北朝至唐代(或唐代中期)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历史阶段,那么唐代汉语之所以发生重大变化,是否也与“北朝出口”有关?也就是说,中古汉语之所以走出中古,汉语史到了唐代之所以进入近代汉语,是否和北朝汉语变化具有紧密的因果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说,目前所见到的唐代的一些重要语言现象,其实早已产生或萌芽于北朝,它们在易代之际通过北朝这个“出口”进入唐代,从而进一步发展。这一假说是否成立,除了“你”以外是否还有例子以证成之[20],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附 注
[1]拙文《基于文白对比的中古史书与〈资治通鉴〉相应部分比较研究》,未刊稿。
[2]《百喻经》的情况值得注意。从纵向看,“尔”固然远少于“汝”;但从横向看,《百喻经》“尔”例又远多于其他译经。“尔”“汝”几乎1∶5的比例是很特别的。那么是否说明南朝口语也说“尔”,只是不及“汝”普遍呢?恐怕不然。据汪维辉(2010,2011),《百喻经》的语言并不全然是当时口语,例如表达悬挂义词,《百喻经》用“悬”而不说“挂”,表愚笨义,《百喻经》不说“痴”而多用“愚”,这说明《百喻经》仍不乏文言成分,第二人称代词用“尔”应该也是同样的情况。不过,口语色彩明显的《百喻经》为什么多用“尔”(当然是相对而言),与东汉以来形成的几乎不用“尔”的传统(详下文)相悖,其中原因何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引者按:“新型的文体”是指第一人称代词基本用“我”的译经文献。
[4]本文中“南朝”“北朝”既是时代概念,也是区域概念。
[5]包含“尔等”等表示复数的形式,统计“汝”时也是如此。
[6]例(38)、例(39)既用“汝”,也用“尔”,这并不能说明口语里也说“尔”,反而是一种书面避复的现象,参看第三节。
[7]梅祖麟(2011)認为吴语苏州、桐庐、黄岩、常山及赣语黎川、南城、南昌、高安方言中的第二人称代词本字都是“汝”。
[8]如《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9]王力(1958/1980,1989)也指出“在上古时代,领位不加‘之字……到了后代,才有加‘之字的”,不过举的例子都是唐以后的。
[10]《太平御览》卷一二二引。
[11]“语音”应指口语音,“读音”应指读书音。
[12]冯春田(2000)认为未必是语音发生分歧加“亻”旁以示区别,“六朝以至唐五代时期俗字盛行,这些俗字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原字基础上增加某一偏旁。因此,‘你的出现,可能就是六朝以后这样潮流的产物”。向熹(2010)认为“尔”“你”字形分化以后,语音才分化。
[13]李荣(1997)认为“‘尔字分化出‘你字,在字形上是加人旁,在字音上是日母转变为泥母”。
[14]也有学者认为应该调整为日母归泥。王力先生认为“日母和泥母,读音只是相近,而不是相同”。无论如何,日母、泥母读音是非常接近的。
[15]这只是依据《广韵》所记而言,实际上“你”的使用区域应该不限于关陇,但肯定在北方。
[16]方言土语保留古读,这在汉语史上是常见的现象。
[17]一词因文白异读改变书写形式的例子在汉语史上也不少见,往往是文读音保留通行的规范的书写形式,而白读音新创一个书写形式。
[18]“搅”和“搞”就是一词因文白异读而衍生的两个书写形式(承蒙边田钢博士惠告),但普通人往往将它们看作两个不同的词。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
[19]确切地说,应该是“‘尔成为后来的‘你然后取代了‘汝(女)”。
[20]第三人称代词“他”、表兄长义之“哥”、表追逐义的“趁”、表交换义的“博”等均可能与此有关。
参考文献
1. 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8.
2. 程亚恒.《吴越春秋》中的人称代词研究.安顺学院学报,2007(2).
3. 邓军.论三国时期代词“汝”和“尔”的格.兰州大学学报,2003(3).
4. 邓军.魏晋南北朝代词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 冯春田.魏晋南北朝某些语法问题探究.∥程湘清主编.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山东: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6.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7. 何大安.语词的脉络、阶级与体式——中古代词尔、汝、卿的用法与异同.∥王叔岷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王叔岷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台北: 大安出版社,1993.
8. 李荣.汉语方言里当“你”讲的“尔”(上).方言,1997(2).
9. 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 龙国富.《妙法莲华经》语法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11.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 学林出版社,1985.
12. 梅祖麟.江东方言的“汝”字(>苏州“倷”)及其相关问题.∥《东方语言学》编委会,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编.东方语言学(第九辑).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13. 漆权.《史记》中的人称代词.∥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十二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14. 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8/1991.
15. 汪维辉.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中国语文,1998(2).
16. 汪维辉.《周氏冥通记》词汇研究.∥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第一辑).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17. 汪维辉.六世纪汉语词汇的南北差异——以《齐民要术》与《周氏冥通记》为例.中国语文,2007(2).
18. 汪维辉.《百喻经》与《世说新语》词汇比较研究(上).∥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十辑).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19. 汪维辉.《百喻经》与《世说新语》词汇比较研究(下).∥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十一辑).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20. 汪维辉.有关《临济录》语言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汉語史研究所编.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十一辑).成都: 巴蜀书社,2016.
21. 汪维辉.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8.
22. 汪维辉,秋谷裕幸.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现状和历史.∥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汉语史学报(第十七辑).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23. 王家葵.《周氏冥通记》析疑.文史,2019(1).
24.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 中华书局,1958/1980.
25. 王力.汉语语法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9.
26. 魏培泉.汉魏六朝称代词研究.∥“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编.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甲种之六).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04.
27.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长沙: 岳麓书社,1995.
28. 向熹.简明汉语史(修订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29. 萧红.六世纪汉语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南北差异——以《齐民要术》和《周氏冥通记》为例.长江学术,2010(4).
30.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31. 曾亮.三国汉译佛经代词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2. 真大成.基于文白对比的中古史书与《资治通鉴》相应部分比较研究.未刊稿.
33. 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9.
34. 朱庆之.上古汉语“吾”“予”“余”等第一人称代词在口语中消失的时代.中国语文,2012(3).
35. 庄正容.《世说新语》中的人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4(4).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杭州 310028)
(责任编辑 马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