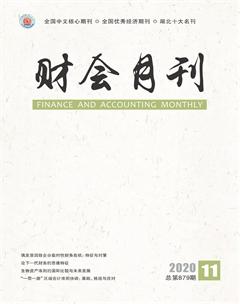反腐败能够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粘性吗
车嘉丽 温飞扬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的反腐败力度空前提升, 经过数年的治理, 已取得显著成效, 反腐败的经济后果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 基于此, 从反腐败对高管薪酬契约这一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视角, 探讨反腐败能否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粘性, 结果表明, 反腐败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粘性、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根据产权性质分组的研究发现, 反腐败对企业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在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中更加显著。
【关键词】反腐败;薪酬粘性;企业高管;产权性质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0)11-0028-8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的反腐败力度空前提升, 经过数年的治理, 已取得显著成效。 然而, 也有一些学者存在不同观点, 认为反腐败可能会使经济下行、企业绩效下降。 在此大背景下, 反腐败的经济后果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 现有文献较多研究的是反腐败对国家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 仅较少文献涉及反腐败对于企业微观行为的作用。 因此, 探讨反腐败这一宏观因素究竟会对企业的微观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高管薪酬粘性指的是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水平的不对称变化现象, 主要原因是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 为了降低代理成本,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实施了基于公司业绩的高管薪酬契约, 建立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钩的薪酬政策, 业绩升、薪酬升, 业绩降、薪酬降。 这种薪酬政策实施后, 若公司业绩上升, 高管的薪酬也会“水涨船高”; 若公司业绩下降, 高管可能会出于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对自身职业声誉、社会地位的考虑, 通过自身的权力影响治理层决策, 使其制定出对管理層有利的薪酬方案, 不愿意接受降薪的惩罚。 由此, 高管薪酬会出现“奖优不惩劣”的粘性特征, 这无疑会损害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并带来代理成本。 因此, 高管的薪酬粘性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代理问题。
已有的研究发现, 反腐败能够影响企业微观经济行为: 首先, 反腐败能够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 为企业带来更加积极的市场反应; 其次, 反腐败的开展能够通过净化企业的内外部环境来提升公司治理的水平, 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最后, 反腐败力度的增加可以降低高管的在职消费水平, 并能够增加高管的业绩—薪酬敏感度。 那么在公司治理环境得到优化后, 高管的薪酬粘性水平是否也会降低呢?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作为业绩的衡量标准, 并利用十八大召开的时间(2012年)、每年全国职务犯罪立案数、每年全国职务犯罪立案人数以及每年立案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数作为衡量反腐败的指标, 通过实证方法来检验反腐败是否能够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粘性。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根据企业不同的产权性质对全样本进行分组, 探讨在不同的产权背景下, 反腐败影响企业高管的薪酬粘性程度是否存在差异, 为我国反腐败的实施效果提供实证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反腐败相关研究。 从2012年开始, 我国反腐败力度大大增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满意的比例由2012年的75%增长至2016年的92.9%。 反腐败对宏观经济以及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首先, 反腐败能够对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汪锋等[1] 发现, 持续性反腐可以降低总体腐败程度, 提高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保证国家长期发展的驱动力, 从而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 其次, 反腐败能够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降低企业代理成本。 由于政治生态得到净化, 违规成本大幅增加, 反腐败开展后公司的行贿和高管的寻租行为显著下降, 业务招待费也随之下降。 反腐败还能促进企业加强研发[2] , 促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3] , 同时还可以通过优化投资效率来提升企业绩效水平[4] 。 最后, 反腐败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和财务决策也存在影响。 学者们发现, 由于反腐败后官员违规的成本大幅上升, 其包庇违规行为的动力有所减弱[5] ; 此外, 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提升, 盈余管理水平下降[6] 。
2. 薪酬粘性相关研究。 薪酬粘性指的是高管业绩—薪酬的非对称性变化现象, 企业业绩上升时高管的薪酬增幅大于业绩下降时的薪酬降幅, 即出现“奖优不惩劣”的现象。 国外学者最先发现了高管的薪酬存在粘性。 Gaver等[7] 通过对美国上市公司的研究, 发现样本企业的高管在企业业绩增加时能获得一定的奖金, 在企业业绩下降时却不会受到丝毫的惩罚。 国内方面, 最早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的文献可以追溯到2009年。 陈修德等[8]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薪酬粘性产生的原因可以通过委托代理理论、归因理论、双因素理论进行解释。 首先, 由于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企业在制定基于业绩的高管薪酬契约后, 在业绩上升时, 作为对高管的奖励, 高管薪酬会随之上升; 然而在业绩下降时, 高管可能会出于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对自身职业声誉、社会地位的考虑, 通过自身的权力影响治理层的决策, 使其制定出对管理层有利的薪酬方案, 不愿意接受降薪的惩罚, 从而出现薪酬粘性[9] 。 其次, 根据双因素理论, 在高管薪酬契约中, 货币性薪酬属于保健因素, 得到满足后无法产生激励作用, 若得不到满足则会对高管个人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因此, 为了使高管感到“合意”并保持对高管的激励, 当公司的业绩下降时, 治理层通常不会立刻降低高管的薪酬[10] 。 最后, 根据归因理论, 当公司的业绩上升时, 管理层会把经营的成功归结于自身的努力, 股东财富也会随之增加, 因此加薪可能更容易获得治理层和董事会的批准; 然而, 当公司的业绩下降时, 管理层会把经营的失败归结于经济环境的变化、成本费用的上升等外部原因, 降薪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阻力[10] , 从而出现薪酬粘性。
3. 反腐败与高管薪酬粘性。 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 高管与治理层之间的效用函数并不完全一致, 在实施了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契约后, 高管出于“自利”和对声誉、未来职业生涯的考虑, 他们通常不愿因业绩下降而降低自身薪酬[9] 。 反腐败对企业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机制实现。
(1)反腐败加强了对高管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减少了高管对薪酬契约制定过程的干预, 更好地发挥了薪酬契约的作用, 从而有效地降低了高管的薪酬粘性。 出现高管薪酬粘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管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高管权力过大, 甚至自身可参与薪酬的制定, 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11] 。 高文亮等[12] 研究发现, 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比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具有更高薪酬粘性。 公司内部人的在职贪腐与非法政商关系营建可以强化其对公司的控制, 而政商勾结又会弱化外部治理机制的监督作用; 同时, 公司内部人为了避免外部监督, 在制度选择上也会倾向于选择能强化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机制[6] 。 因此, 腐败会加剧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从而进一步加剧高管的薪酬粘性。 而反腐败的开展加强了对高管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企业高管的违规成本显著提高。
刘冠君等[13] 指出, 惩治力度加大形成的高压反腐局面会增加官员腐败行为的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 能够对遏制腐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党的十八大以后, 在国企方面, 各级党委加强了对所属国企的巡视力度, 派驻工作小组进入企业进行巡视、巡察, 实现了对中管企业的巡视全覆盖; 审计部门也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工作, 高管的在职消费等灰色收入得到有效抑制。 2015年,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开始实施, 明确进一步推进国企薪酬制度改革, 逐步构建起薪酬增长与经济效益、业绩考核相联系的激励约束机制。 这些举措都能对国企高管权力形成制约和监督, 高管不合理的收入得到遏制。
在民企方面, 反腐败营造了良好的经营大环境, 增加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风险[3] , 有助于企业将精力从寻租活动转回至企业的生产经营[4] , 并促使媒体、公众和投资者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 这些举措都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对高管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有利于缓解“内部人控制”现象, 抑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 减少高管对薪酬契约制定过程的干预, 更好地发挥薪酬契约的作用, 从而能有效地降低高管的薪酬粘性。
(2)反腐败遏制了政府官员的政治寻租现象, 使高管的在职消费等薪酬形式大幅减少, 当企业业绩下降时, 高管不能再通过维持政商关系使自身薪酬保持粘性。 由于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 政府部门仍然掌握着诸如信贷融资、事项审批、税收优惠等企业发展所需的必要资源。 反腐败开展之前, 对政府官员的外部监督相对弱化, 这为某些官员的政治寻租提供了便利, 也使得企业高管必须通过积极寻求政治关联以获得企业经营发展的必要条件。 研究发现, 企业在业务招待方面的投入能显著提高公司的成长性[14] , 因此企业不得不通过给予高管较大幅度的在职消费等薪酬形式来维护与政府之间的关系[15] 。
在这种背景下, 当企业的业绩上升时, 高管理所当然地会获得包括更多在职消费在内的丰厚薪酬, 但利用这种方式取得的业绩并不能很好地体现高管努力经营的结果, 这无疑会弱化薪酬激励的效果。 当企业的业绩下降时, 由于高管仍需要这方面的花费来维持政商关系, 在职消费并不能随之减少, 这可能使得高管的薪酬继续维持在先前的水平, 从而出现粘性的特征。 同时, 由于高管通过政治寻租来获得业绩提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在此期间内高管的薪酬也可能不降反升, 持续出现粘性现象。 反腐败开展之后, 我国的政商环境得到了大幅净化, 降低了企业高管通过不合理的在职消费寻求政治关联的可能性。
研究发现, 反腐败可以通过压缩寻租空间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 使企业内部及市场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16] 。 要想提升业绩, 高管必须把工作重心转向提升公司产品质量、提高创新能力等公司主业上来[2] 。 只有这样, 当企业业绩上升时, 高管薪酬才真正体现的是其努力工作的程度; 当企业业绩下降时, 由于在职消费等薪酬形式大幅减少, 高管不能再通过维持政商关系等名义和借口使自身薪酬保持粘性, 必须接受降薪的惩罚。 因此, 从外部治理来看, 反腐败对于增强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降低薪酬粘性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
假设1: 反腐败能夠抑制我国企业高管的薪酬粘性。
4. 产权性质、反腐败与高管薪酬粘性。 股权分置改革以来, 我国国企逐步建立健全了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实行基于企业业绩的高管薪酬体系。 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国企除了要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往往还有其他目标如保障就业、灾害救济等, 这会降低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10] , 并导致更高程度的薪酬粘性。 同时, 由于国企的委托代理问题更为突出, 因此相对于民企, 国企的高管薪酬粘性水平更高[17] 。 由于反腐败的开展会导致国企高管隐性福利(例如在职消费等)较以往有所减少, 为了更好地激励高管, 国企治理层可能会倾向于推进实施各种薪酬激励方案, 这会使国企高管的薪酬粘性水平下降。 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 国企高管大多由政府部门直接任命; 由于预期效应的存在, 在反腐败信息流出后, 国企高管预计到反腐败的开展而主动降低薪酬以规避风险, 因此反腐败对于国企高管的约束力更强。 此外, 民企具有相对市场化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这使得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18] 。 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民企本身就具有相对完善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因此本文预期民企的薪酬粘性在反腐败之后的变化效应不会太明显。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权限划分, 我国国企可以分为中央控股国企(简称“央企”)以及地方国企。 由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 央企的规模和影响力较大, 因此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 例如, 早在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就颁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 明确将以年薪激励方式对中央直属企业高层管理者进行考核, 并逐步引入长期激励机制。 由此可见, 央企已建立较为完善的薪酬体系, 且其高管面临的监管更为严格, 从而缓解了中央控股国企高管的内部人控制等代理问题, 抑制了薪酬粘性问题的产生; 而地方国企规模较小, 当地政府对地方国企的依赖性更大, 在反腐败开展之前受到的监管也较少, 因此存在更为严重的代理问题。 已有的研究发现, 地方国企的薪酬粘性比央企的薪酬粘性更大[19] 。 十八大以后, 反腐败对地方国企的监管显著加强, 一批地方国企高管被发现存在违纪违规问题。 因此, 本文预计反腐败对于地方国企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
假设2: 反腐败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国企中。
假设3: 相较于央企, 反腐败对地方国企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10 ~ 2017年沪深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并根据证监会2012版行业分类, 剔除了金融业、ST类企业以及样本期间数据存在缺失值的样本。 反腐败数据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 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同时, 为了减少和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水平上的双侧缩尾。 最终得到13572个研究样本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本文主要使用Stata和Exc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2. 变量定义。
(1)高管薪酬。 本文选取上市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三位高管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并以其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作为高管薪酬的衡量标准。
(2)公司业绩。 衡量公司业绩的指标包括ROA、ROE、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等。 这些指标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更能反映出高管的努力程度, 且大部分上市公司均以此作为评价高管绩效并确定其薪酬水平的标准。 因此, 本文采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作为衡量公司业绩的指标。
(3)反腐败。 目前, 学者们对于我国反腐败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式, 分别为虚拟变量法和连续变量法。 在样本期间(2010 ~ 2017年), 还有其他事件(如2015年开始实施的央企高管“限薪令”、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也可能会对高管薪酬产生一定影响。 为了尽量避免其他因素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首先借鉴党力等[2] 、陈胜蓝等[20] 对反腐败的衡量方法, 采用虚拟变量来衡量反腐败。 以中共十八大闭幕的时间(2012年12月)为分界点, 十八大闭幕以后代表高压态势的反腐败背景。 由于反腐败从部署到实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对企业发挥微观作用, 因此设定: 若样本时间位于2013年及以后,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在进行分组检验时, 主要采用虚拟变量法来衡量反腐败。 同时, 为了进一步减少内生性问题、体现我国反腐败的治理作用, 本文借鉴党力等[2] 、王健忠等[21] 、刘建秋等[22] 对反腐败的衡量方法, 通过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数、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职务犯罪人数以及人民检察院立案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数来衡量每年的反腐败强度。 参考以往的研究文献, 其余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3. 模型设计。 本文借鉴方军雄[10] 提出的高管薪酬粘性模型, 运用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 该模型以公司业绩(Lndnp)作为自变量、高管薪酬(Lnpay)为因变量, 检验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粘性水平。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反腐败因素(Anti2、Anti3、Anti4)作为调节变量, 用来验证反腐败对高管的薪酬粘性是否存在抑制作用。 此外, 两个模型均控制了行业和年度的影响, 同时也控制了公司个体固定效应以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模型(1)中, 当公司业绩上升(Down=0)时, 高管薪酬变动的幅度为α1; 而当公司业绩下降(Down=1)时, 高管薪酬变动的幅度为α1+α2。 若α1/(α1+α2)的值大于1, 则说明在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上涨的幅度大于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下降的幅度, 即高管薪酬存在粘性。 反之, 则说明高管薪酬不存在粘性。 根据理论推导, 本文预计在反腐败开展后(Anti1=1),α1/(α1+α2)的值会比反腐败开展前(Anti1=0)有所下降, 即高管薪酬粘性下降。
模型(2)中加入了反腐败(Anti2、Anti3、Anti4)与模型(1)其他主要变量的交乘项。 当公司业绩上升(Down=0)时, 高管薪酬变动的幅度为β1; 而当公司业绩下降(Down=1)时, 高管薪酬变动的幅度为β1+β4; 若β2显著为负, 说明高管薪酬存在粘性; 若交乘項Lndnpi,t×Antii,t×Downi,t的系数β4显著为正, 则说明反腐败对高管的薪酬粘性存在抑制作用。
四、实证分析
根据样本期间(2010 ~ 2017年)全国职务犯罪的立案情况(见表2), 在我国反腐败开展后, 无论是全国职务犯罪立案数、立案人数, 还是县处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立案数, 均比反腐败开展之前有所增长。 2014年、2015年两年的职务犯罪立案数均超过40000件; 其中, 2014年全国职务犯罪立案数达到41487件, 远远高于2010年的32909件。 这充分表明我国的反腐败力度不断得到加强, 并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
1. 描述性统计。 表3报告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3可知,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上市公司利润状况的差异较大。 样本数据中有36.9%的公司业绩较上一年出现了下降的现象。 在公司治理方面, 国企所占比例达到37.3%,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为 36.10%, 73.8%的样本出现了两职分离的情况, 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为 37.2%, 满足了证监会对独立董事至少要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占三分之一的要求。
2. 相关性检验。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系数分析(见表4)。 除极个别系数外,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 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变量间自相关问题。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有较高的敏感性, 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契约得到较好的执行。 另外, 高管薪酬与产权性质、股权结构、公司规模等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说明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有很多, 这也与已有的文献一致, 因此本文对此进行控制。 在2012年反腐败加强后, 上市公司的业绩得到了提高, 并且两者在1%的水平上显著, 这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 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也随着得到了提升。 这初步验证反腐败能够增强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 从而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
3. 多元回归分析。
(1)全样本。 为验证反腐败与高管薪酬粘性的关系, 本文首先以十八大召开的时间(Anti1)对全样本进行区分, 并代入模型(1)中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5中列1、列2所示。 结果表明, 在样本期间内, Lndnp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契约已经得到了建立; 然而, 在样本期间内, Lndnp×Down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的特征, 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特别是从经济意义上看,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Anti1=0), 样本公司在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上涨幅度是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下降幅度的1.30倍[0.060/(0.060-0.014)]; 而在十八大召开之后(Anti1=1), 样本公司在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上涨幅度是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下降幅度的1.17倍[0.074/(0.074-0.011)]。 这表明虽然十八大召开之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仍然存在粘性, 但是较十八大召开之前有所下降。
然后, 本文分别将Anti2、Anti3、Anti4代入模型(2)中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5的列3、列4、列5所示。 结果表明, 在样本期间内, Lndnp×Down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存在粘性的特征; 而Lndnp×Anti×Down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反腐败的开展抑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粘性。 因此, 无论采用何种衡量方法, 均能证明反腐败对于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 假设1得到验证。
(2)区分产权性质。 表6的结果显示, 在开展反腐败之前, 国企高管在业绩上升时薪酬上涨幅度是业绩下降时薪酬下降幅度的1.38倍[0.076/(0.076-0.021)], 而民企高管在业绩上升时薪酬上涨幅度是业绩下降时薪酬下降幅度的1.26倍[0.043/(0.043-0.009)], 国企高管的薪酬粘性高于民企高管, 这与既有研究文献的结论一致。 在开展反腐败之后, 国企高管在业绩上升时薪酬上涨幅度是业绩下降时薪酬下降幅度的1.00倍[0.063/(0.063-0.000)],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几乎同步变动, 且Lndnp×Down的回归系数不再显著; 民企高管在业绩上升时薪酬上涨幅度是业绩下降时薪酬下降幅度的1.35倍[0.077/(0.077-0.020)], 且Lndnp×Down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 说明民企高管薪酬在反腐败开展之后仍然存在一定的粘性特征。 因此, 反腐败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中, 假设2得到验证。
(3)区分国有资产管理权限。 本文进一步将样本中的国企分为央企以及地方国企, 并代入模型(1)中进行回归检验。 表7的结果显示, 在反腐败开展前后, 央企中Lndnp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Lndnp×Down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 但不具有显著性, 说明央企高管基于業绩的薪酬契约已得到较好的执行, 薪酬业绩敏感性高, 高管薪酬粘性水平较低。 对于地方国企而言, 在反腐败开展之前, Lndnp×Down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其高管薪酬存在粘性; 而在反腐败开展之后, Lndnp×Down的系数由负转正, 且不再具有显著性, 说明反腐败对地方国企高管的薪酬粘性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 假设3得到验证。
4.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以上市公司董事高管监事前三名薪酬之和作为高管薪酬的替代变量, 代入模型(1)和模型(2)进行重新检验。 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Anti1=0), 样本企业高管在业绩上升时薪酬上涨幅度是业绩下降时薪酬下降幅度的1.29倍[0.062/(0.062-0.013)]; 在十八大召开之后(Anti1=1), 样本企业高管在业绩上升时薪酬上涨幅度是业绩下降时薪酬下降幅度的1.13倍[0.074/(0.074-0.009)], Lndn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 Lndnp×Dow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而Lndnp×Anti×Down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与前述回归的检验结果一致。 在产权性质的分组回归中, 也得到与前述回归一致的结论。 由此可知, 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均再次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反腐败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以及不同的产权性质下反腐败对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 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基于大样本数据研究高管的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发现我国企业的高管薪酬仍然存在“奖优不惩劣”的粘性特征。 第二, 引入反腐败这一外部因素, 检验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是否对企业高管的薪酬粘性存在抑制作用, 结果表明反腐败的开展能够显著抑制高管的薪酬粘性水平, 发挥微观治理作用。 第三, 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 进一步研究反腐败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高管薪酬粘性的调节作用, 按照产权性质对全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发现, 反腐败对企业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中。
2. 启示。 根据实证研究结论, 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行了绩效工资体系, 以业绩为基础确定高管的薪酬水平; 但大多数企业的高管薪酬还是存在着粘性现象, 这不利于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契约的实施, 治理层应通过完善外部治理和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来抑制高管薪酬粘性。 第二, 反腐败不仅能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起到积极作用, 还能够影响企业的微观行为。 反腐败对于优化公司的治理、 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和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一定的作用, 这也为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 第三, 反腐败对企业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国企中, 这说明反腐败对深化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 1 ] 汪锋,姚树洁,曲光俊.反腐促进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理论机制[ J].经济研究,2018(1):65 ~ 80.
[ 2 ] 党力,杨瑞龙,杨继东.反腐败与企业创新:基于政治关联的解释[ J].中国工业经济,2015(7):146 ~ 160.
[ 3 ] 李追阳.反腐败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J].财经论丛,2018(9):66 ~ 75.
[ 4 ] 钟覃琳,陆正飞,袁淳.反腐败、企业绩效及其渠道效应——基于中共十八大的反腐建设的研究[ J].金融研究,2016(9):161 ~ 176.
[ 5 ] Zhang Jian. Public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rraud: Evidence from the recent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6(2):1 ~ 22.
[ 6 ] 王茂斌,孔东民.反腐败与中国公司治理优化:一个准自然实验[ J].金融研究,2016(8):159 ~ 174.
[ 7 ] Gaver J., Gaver K..The relation between nonrecurring accounting transactions and CEO cash compensation[ J].Accounting Review,1998
(2):235 ~ 253.
[ 8 ] 陈修德,彭玉莲,吴小节.中国上市公司CEO薪酬粘性的特征研究[ J].管理科学,2014(3):61 ~ 74.
[ 9 ] Jensen M., K. Murphy. Performance pay and top-management incentive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225 ~ 264.
[10] 方军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存在粘性吗?[ J].经济研究,2009(3):110 ~ 124.
[11] 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J].管理世界,2007(7):111 ~ 119.
[12] 高文亮,罗宏,程培先.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 J].经济经纬,2011(6):82 ~ 86.
[13] 刘冠君,朱立恒.遏制腐败需提升腐败惩治力度[ J].科学社会主义,2015(5):103 ~ 108.
[14] 黄玖立,李坤望.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 J].经济研究,2013(6):71 ~ 84.
[15] 谢获宝,惠丽丽.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有效激励还是隐性腐败——基于市场化改革进程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J].华东经济管
理,2014(11):1 ~ 5.
[16] 应千伟,刘劲松,张怡.反腐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共十八大后反腐风暴的证据[ J].世界经济文汇,2016(3):42 ~ 63.
[17] 孙丽,杨丽萍.所有权性质与高管薪酬业绩粘性[ 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123 ~ 131.
[18] 陈胜蓝,卢锐.股权分置改革、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J].金融研究,2012(10):180 ~ 192.
[19] 孫惠.不同政府控制层级下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 J].财会月刊,2012(26):9 ~ 11.
[20] 陈胜蓝,马慧.反腐败与审计定价[ J].会计研究,2018(6):12 ~ 18.
[21] 王健忠,高明华.反腐败、企业家能力与企业创新[ J].经济管理,2017(6):36 ~ 52.
[22] 刘建秋,盛开.反腐败、高管责任基调与企业价值[ J].商业研究,2019(7):100 ~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