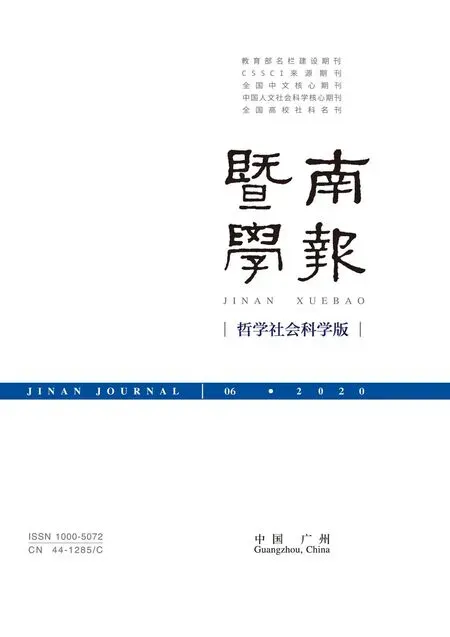《商君书》源流考
黄 效
《商君书》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之一,本应该和其他各类先秦的典籍一样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汉代以后直到清朝之前,学界对《商君书》的研究一直相对较少,以致此书的许多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厘清。一些学者如张觉(1)张觉:《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第一册)前言,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等人虽然对它在历朝历代的流传作过梳理,但对于《汉志》法家类《商君》与兵权谋家《公孙鞅》之间的关系,《商君书》的成书、篇数的变动、开始亡佚的时间等问题,现代学界少有详细的探讨,因此这些基本的问题还存在较大疑问。笔者为此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并试作梳理如下。
一、《商君书》的历代著录情况
对《商君书》的记载和征引,最早见于《韩非子》。《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内储说上》谓:“公孙鞅曰:‘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2)(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1、225页。此句见于今本《商君书·靳令》。
到了汉代,《淮南子》曾提到过《商君书》中《启塞》篇,所谓“启”者,与“开”字同(3)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24页。。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提到过《商君》一书,(4)(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5页。《商君列传》中对《商君书》的内容也多有化用,其在末尾云:“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18页。刘向在《新序》中对商鞅的事迹多有论及,在《善谋》篇中更有对《更法》篇的大幅引用。(6)(西汉)刘向:《新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143页。《汉书·艺文志》法家类:“《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云:“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又兵权谋家类:“《公孙鞅》二十七篇。”另外,《汉志》农家类中载:“《神农》二十篇。”颜师古注曰:‘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7)以上诸条详情参见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236、190页。由此可见,汉时商君学说实广泛涉及法、兵、农诸领域,汉后的著录主要见于法家一类。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目录学著作多已失传,所以今天能见到有关《商君书》的著录比较少。《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引《诸葛亮集》谓刘备在遗诏中叮嘱刘禅云:“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8)(晋)陈寿:《百纳本二十四史·三国志》(第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44页。将《商君书》和诸子及兵书《六韬》并列。魏时郑默著《中经》,后晋人荀勖因之而作《中经新薄》,将《汉志》中的“七分法”变为“四分法”,并将《汉志》中诸子、兵书、术数等并为乙部,又将诸子分为“古诸子”和“近世诸子”两类,故此时若《商君书》被收录,应该是被列入乙部,至于是被列入乙部中的“古诸子”还是“兵书”类,还是两者都有,由于文献缺失不得而知。《晋书·庾峻列传》:“唯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9)(唐)房乔:《百纳本二十四史·晋书》(第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67页。可见时人或对《商君书》较为熟悉。刘宋时王俭撰有《七志》,其体例仿《汉志》,设有“诸子志”和“军兵志”等七类,汉时商鞅著作分属法家类和兵权谋家类,由于文献失传,不知王氏是否收录或将其归属何类。梁时阮孝绪又撰有《七录》,复将诸子与兵书合为“子兵”一类,故若此时《商君书》被阮氏收录,其应入列“子兵”一类,具体情况也由于文献失传不得而知。又梁庾仲容《子抄》法家类:“《商子》五卷。”(10)(南宋)高似孙:《子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由上述可知,虽然此时能见到对《商君书》的著录较少,但是也一直有流传。
隋唐时期,《隋书·经籍志》法家类谓:“《商君书》五卷。秦相卫鞅撰。”(11)(唐)魏征:《百纳本二十四史·隋书》(第1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61页。其书名沿用《三国志》中裴松之注的记载,卷数则和《子抄》相同,但也只有卷数而并未言及篇数,因此五卷本《商君书》到底有多少篇仍然是疑问。另外,《群书治要》中辑录了《六法》《修权》《定分》三篇,并谓其来自《商君子》(12)(唐)魏征:《宛委别藏丛书·群书治要》(第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46—1853页。。而大概介于《隋志》和《唐志》之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谓:“《商君书》三卷。”(13)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6页。可见,《商君书》大概在唐朝时已经流传到了海外,并且在卷数上和《子抄》《隋志》的五卷本有差异。无独有偶,马总《意林》谓:“《商君书》四卷。”(14)(唐)马总:《意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6页。并对《商君书》的内容有所摘引,其卷数亦不同于《子抄》和《隋志》,可见“五卷”并非隋唐时固定卷数。此外,《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选注》《长短经》等俱有对《商君书》的征引,且均来自“商君书”,可见隋唐时《商君书》主要以“商君书”一名行世。五代刘昫《旧唐书》谓:“《商子》五卷,商鞅撰。”(15)(五代)刘昫等:《百纳本二十四史·旧唐书》(第1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54页。将《商君书》又称为“商子”,五代以后,《商君书》则主要以“商子”一名行世。
宋时,欧阳修所编的《新唐书》谓:“《商君书》五卷。”注云:“商鞅,或作《商子》。”(16)(北宋)欧阳修等:《百纳本二十四史·新唐书》(第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09页。《崇文总目》:“《商子》五卷。商鞅撰。”(17)(北宋)王尧臣等撰,(清)钱东垣等辑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一)·崇文总目》(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5页。《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商子》五卷,战国时公孙鞅撰……今是书具存共二十六篇,本二十九篇,今三篇亡。”(18)(南宋)陈骙等撰,赵士炜辑考:《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一)·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0页。《艺芸书舍本郡斋读书志》:“《商子》五卷,右秦公孙鞅撰。……鞅封于商,故以名其书,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19)(南宋)晁公武撰,(南宋)姚应绩编:《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二)·艺芸书舍本郡斋读书志》(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2页。《直斋书录解题》:“《商子》五卷,秦相卫公孙鞅撰,或称商君者,其封邑也。《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亡其一。”(20)(南宋)陈振孙:《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一)·直斋书录解题》(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64页。由上可知,宋时《商君书》主要被称为“商子”,且篇数已由《汉志》法家类的二十九篇减少到了二十六篇,《直斋书录解题》谓南宋时又佚一篇,故宋末时实仅存二十五篇而已。《遂初堂书目》:“《商子》。”(21)(南宋)尤袤:《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一)·遂初堂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88页。未标卷数作者,并将其归入杂家类,不知何据。另《黄氏日钞》:“《商子》者,公孙鞅之书也。始于《墾》章,督民耕战,其文烦碎不可以句,至今开卷于千载之下,犹为心目紊乱,况当时身披其祸者乎!”(22)(南宋)黄震:《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黄氏日抄》(卷五十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26页。今本《商君书》以《更法》为第一章,《墾令》为第二章,黄氏所称其始于《墾》章,不知其所据何本。除了以上著作之外,《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古今考》《事类备要》《玉海》等众多类书也多有对《商君书》进行征引。
金元时期,元脱脱《宋史·艺文志》谓:“《商子》五卷。卫公孙鞅撰。”(23)(元)脱脱等:《百纳本二十四史·宋史》(第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413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商子》五卷。”(24)(元)马端临:《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三)·文献通考·经籍考》(三九),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7页。此外,元时《韵府群玉》等对《商君书》亦有较多的征引。
明时,《文渊阁书目》谓:“《商子》,一部一册,阙。”(25)(明)杨士奇等:《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文渊阁书目》(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7页。《秘阁书目》:“《商子》一。”(26)(明)钱溥录:《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秘阁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23页。《万卷堂书目》官制类:“《商子》一册。”(27)(明)朱睦:《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万卷堂书目》(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8页。《晁氏宝文堂书目》:“《商子》。”(28)(明)晁瑮:《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晁氏宝文堂书目》(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27页。《脈望馆书目》:“《商子》一本,又四本。”(29)(明)赵琦美:《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四)·脈望馆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43页。《世善堂藏书目录》:“《商子》五卷。”(30)(明)陈第:《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五)·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页。《玄赏斋书目》:“《商子》。”(31)(明)董其昌:《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五)·玄赏斋书目》(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3页。《澹生堂藏书目》:“《商子》一册,五卷。范氏丛书本,汉魏丛书本、廿子全书本。”(32)(明)祈承:《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五)·澹生堂藏书目》(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3页。《徐氏家藏书目》:“《商子》五卷,鞅。”(33)(明)徐:《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五)·徐氏家藏书目》(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1页。《笠译堂书目》:“《商子》一册。”(34)(明)王道口:《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五)·笠译堂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5页。《国史经籍志》:“《商君书》五卷,汉十九篇,今亡三篇。”(35)(明)焦竑撰:《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五)·国史经籍志》(卷四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28页。(笔者按,《汉志》法家类《商君》二十九篇,此处“十九”当为 “二十九”,脱漏一个“二”字。)纵观明人的著录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有些著作不录作者、卷数、篇数,只是列个书名而已;而有些虽列册数,但篇数、作者都无,且以一册本居多。第二,在归类上出现了新的现象,《万卷堂书目》把《商君书》列入“官制”类,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第三,《澹生堂藏书目》出现了版本的记载,这在历史上也属首次。另外,《诸子辨》:“《商子》五卷,秦公孙鞅撰。……予家藏本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36)(明)宋濂:《诸子辨》,北京:朴社出版社1926年版,第29页。《少室山房笔丛》:“二《商子》。一《商鞅》二十九篇;一《商子逸书》亦号‘商子’。”(37)(明)胡应麟:《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22页。此处所谓的《商子逸书》应是指《宋史·艺文志》中载的“商孝逸《商子新书》三卷”(38)(元)脱脱等:《百纳本二十四史(第20册)·宋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414页。一书,而不是在明代另外出现了一部关于商鞅学说的著作。此外《问奇类林》《山堂肆考》《丹铅总录》等对《商君书》亦有征引。
清时,《四库提要》云:“《商子》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读书志》则云,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读书志》成于绍兴二十一年,既云已阙三篇,《书录解题》成于宋末乃反较晁本多二篇。”(39)(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48页。《皕宋楼藏书志》兵家类:“《商子》五卷,明天一阁刊本,秦商鞅撰;《商子》五卷,严可均手抄本,秦商鞅撰。”(40)(清)陆心源:《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七)· 皕宋楼藏书志》(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67页。著录了两个版本,并将其归为兵家类。《善本书室藏书志》:“《商子》五卷,明刊本。秦商君公孙鞅著,明钱塘冯观晋叔点评。《汉志》称《商君》,《隋志》始称《商子》,皆载二十九篇。今篇目二十有六,与晁氏《读书志》合,而第二十六、二十一两篇已有目无书。元刊外有范钦本、秦四麟本,此为吾乡冯氏评本,前附《史记·商君传》及嘉靖已末小海道人冯观自序。天启丙寅,观之孙贽始序而刊行,觐有廉访使者木印,其评点皆尚笔气文法,而其间错误不能句读者,或圈以隔之,竖以斥之,与乾隆时西吴严万里枝本往往多合。”(41)(清)丁丙:《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九)·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80页。《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与之类似:“《商子》五卷,旧抄本。《汉志》称商君,《隋志》始称《商子》,皆载二十九篇。今篇目二十有六,与晁氏《读书志》合,而第二十六、二十一两篇已有目无书,此邑人冯知十所录,以宋本校过。卷首有彦渊冯知十《读书记》二。朱记。”(42)(清)瞿镛:《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5页。《抱经楼藏书志》:“《商子》五卷,明天一阁刊本,顾王霖旧藏,秦商鞅撰。”(43)(清)沈德寿:《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十二)·抱经楼藏书志》(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5页。《艺风藏书续记》:“《商子》一卷。”(44)(清)缪荃孙:《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十四)·艺风藏书续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1页。《郑堂读书记补逸》:“《商子》五卷,范氏二十种奇书本。……是今本较陈氏时又亡其一篇。而中间阙字甚多,以口代之,是书首末二篇,俱称孝公问,公孙鞅答,使商君自著,安得在孝公后著书,及称其谥,此必其徒所追述,而附合者所亦不免。故其间之事,有《史记》所不载云。”(45)(清)周中孚:《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十五)·郑堂读书记补逸》(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3页。《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商子》五卷。……汉志二十九篇,宋佚其三,今有录无书者又二篇。”(46)(清)马国翰:《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十五)·玉函山房藏书簿录》(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1页。由上可知,清人对《商君书》的作者、篇数和版本出处等情况考究得比较多,对文本的真伪、句读情况等也多有关注,各种信息的记录比较完整和详细。就其卷数而言,除了“五卷”本外,还有“一卷”本,而篇数则在清时又亡一篇,故今仅余二十四篇,现行本《商君书》就是承清人二十四篇而来。
二、《商君书》的成书及《商君》与《公孙鞅》的关系
在上文中我们大致梳理了《商君书》在历朝历代的著录情况,但是对于它的成书问题,历代文献却鲜有提及。《韩非子》只谓“家藏管、商之法”,这里的“法”到底是指书还是指法律条文,已不可考。故那时到底有没有一本《商君书》在流行,则不得而知,但它应该至迟在西汉初年已经成书。因为《史记·秦本纪》在论述商鞅变法时谓“其事在商君语中”(47)(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5页。,这里的“商君”二字固然有可能指商鞅本人而非指书,但通观全文,指人的用法与《秦本纪》的行文风格不符。《秦本纪》在论述商鞅变法时“商君”二字只使用了两次,除了在这里用了一次外,后面介绍他的封号时又用了一次,说他“号商君”,其余提到商鞅时一律作“卫鞅”或“鞅”。结合后来《汉志》谓“《商君》二十九篇”,可知西汉时《商君书》被称为“商君”,故《本纪》中的“商君”应是指书无疑。又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说他曾读《开塞》《耕战》书,考之今本《商君书》,即有《农战》《开塞》两篇,但“耕战”与“农战”虽然词意相近,用字却有别。故司马迁所见,未必就是后来的《商君书》,《商君书》此时可能尚未有固定的版本。而对《商君书》完整著录者最早见于《汉志》,《汉志》是在刘向等人所编的《别录》的基础上删补而来的,刘向等人曾对当时的书籍进行过大规模的整理,现传书籍的许多篇章目录都是由他们删订增补而来的,故《商君书》可能直到刘向时才有固定的版本。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志》法家类中有《商君》二十九篇,而兵权谋家类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两者不仅书名不同,而且篇数也有差异。那么,这两者是否是同一书,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后来的《商君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古今学者多有人认为《汉志》中的《商君》与《公孙鞅》是同一著作,如王时润认为今传本《商君书》或为兵权谋家类的《公孙鞅》:
今案《汉书·艺文志·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而兵权谋十三家中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公孙鞅》即《商君》,窃疑法家与兵家所载实即一书。惟篇目多寡微不同耳,然据陈振孙《书录解题》所称则宋本《商君书》亦止二十七篇,今本二十六篇。加入《立法》(笔者按,应为《六法》)适符二十七篇之数。安知非《商君》原书如是。(48)王时润:《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商君书斠诠五卷》(第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58—59页。
此外,汉学家Robin D.S.Yates(中文名:叶山)也认为《公孙鞅》与《商君书》应该是同一书。(49)Robin D.S.Yates, “New Light on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Texts: Notes on Their Nature and Evolution, and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pecialization in Warring States China”.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74, Livr.4/5,1988,pp.211-248.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它们并非同一书,如管庆祺转引孙星衍语谓:
《汉书·艺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隋唐志》并无少阙。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存二十六篇,南宋始亡其三。宋本陈振孙《书录解题》又亡其一,本朝《四库简明目录》亡其二。《刑约》《御盗》亡,存其目。则现行世止二十有四篇耳。《治要》有《立法》一篇犹在。唐时孙乃云,第二十七篇并亡其目,则与宋存廿六篇之数不合。其未考之寀本矣。《艺文志·兵家》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王应麟《考证》并无说,当是别人。(50)(周)商鞅撰:(清)伦明录,(清)严可均校:《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商子五卷》(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608页。
其意谓现传本《商君书》与兵权谋家类的《公孙鞅》并非同一书,《公孙鞅》的作者当另有其人。今考王氏《汉书艺文志考证》一书,并未对《公孙鞅》有任何论述,确是没有说它是哪个人的著作。而清人章学诚谓:“若兵书之《公孙鞅》二十七篇与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号虽异,而实为一人,亦当著是否一书也。”(51)(清)姚振宗:《二十五史补编·汉书艺文志条理》(第二册),上海:开明书店版1937年版,第130页。其意谓两者的作者是同一人,但不知其书是否为同一书。姚振宗针对章氏的观点谓:“一在法家,一在兵家,家数既殊,篇数亦异,又何用著其是否一书也。”(52)(清)姚振宗:《二十五史补编·汉书艺文志条理》(第二册),上海:开明书店版1937年版,第130页。其意谓两者非常明显不是同一书。顾实谓:“兵权谋家《公孙鞅》二十七篇,盖非同书。”(53)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张舜徽谓:“今观《商君书》中《算地》《赏刑》《画策》《战法》诸篇中论兵之语,至为精要,知其沉研于此道者深矣。《汉志》著录之二十七篇,不必皆其手著,而散亡亦早,故已不见于《隋志》。”(54)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其虽不明说,但他应该认为兵权谋家的《公孙鞅》与法家的《商君》是不同的著作。然以上众说亦只是简单地说同异,至于其中的原委则没有详细的论证。
笔者认为,随着兵权谋家《公孙鞅》的失传,其真实情况已无法直接去考证,但通过《汉志》的著录体例,我们或可作一些合理的推测。《汉志·兵权谋家》:“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班固注云:“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55)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今计其十三家实为二百七十二篇,多十三篇;省略诸家共计三百六十九篇,多十篇。刘奉世谓:“‘种’当作‘重’,‘九’下又脱一‘篇’字。”顾实对此表示认同。(56)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陶宪曾谓:“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三百五十九篇重者,盖《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笔者按,‘九篇’当为‘九书’),其全书收入儒道纵横杂各家,又择其中言兵权谋者,重入于此。”(57)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陶氏的说法也未必准确,因为此处所收之书按其总的篇数看,明显不是“择其中言兵权谋者,重入于此”,而是将整本著作都收录其中,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篇。如果篇数不同,按照后文的著录体例也不可能会省略。由此可知,班固之所以会省去九家者,盖因其书和其他各家中出现的著作完全重合,故省略不著。其所省略诸书,也并没有完全是谈论军事的著作,它们只是部分地包括了军事的内容,如《管子》《孙卿子》之类。其省略不著者,也就意味着它们与之前出现的著作内容重复,否则便不能省略。故无论内容是否全部谈论军事,或是否与之前出现的著作内容重复,《汉志》都有可能著录,应该说这样的取舍标准也符合当时学术的生态特点。因为汉人虽然把学术分为九流十家,但事实上那时各派的学术是呈开放性存在的,许多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而转益多师,如陈良、告子之流。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据传也曾向道家的老子问学。所以在诸子百家之中,许多人的思想是很难用某一家思想去概括的,而应该兼具多家思想特色。故为了真实反映这种学术生态特点,《汉志》在对各家著作分类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不同的流派中著录那些思想兼具多派特色的著作。而商鞅本人的思想恰好也具有多方面特点,所以有关商鞅的著作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中出现,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事。孙德谦在《汉书艺文志举例》中将此称为“互著例”,并谓:
今考之班《志》,儒家有《景子》《公孙尼子》《孟子》,而杂家有亦有《公孙尼》,兵家亦有《景子》《孟子》,道家有《伊尹》《鬻子》《力牧》《孙子》,而小说家亦有《伊尹》《鬻子》,兵家亦有《力牧》《孙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子》《公孙鞅》,纵横家有《庞煖》,而兵家亦有《庞煖》,杂家有《伍子胥》《尉缭》《吴子》,而兵家亦有《伍子胥》《尉缭》《吴起》,小说家有《师旷》,而兵家亦有《师旷》。此其重复互见。班氏虽于六略中以其分析太甚,或有称省者(说见前)。然于诸家之学术兼通,仍不废互著之例。(58)(清)孙德谦:《二十五史补编·汉书艺文志举例》(第二册),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版,第11页。
故《汉志》法家之《商君》与兵权谋家之《公孙鞅》其实都应该是与商鞅有关的学说,只不过因为从不同的学术路数分类,所以把它们归属不同的门类。
至于其中篇数的差异,则可能和《公孙鞅》的出现或整理者的不同有关。对于《公孙鞅》的出现,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汉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多种商鞅的著作,其中便存在《商君》和《公孙鞅》这两部;第二种情况是两者早在汉初张良、韩信第一次整理兵书时就已经产生;最后一种情况是这两者直到刘向校书时才产生。目前看来,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从目前所见的文献来看,无论《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著作,都是一人一部的居多。他们的著作,虽然作者不一,成书时间也较长,但其要么是在未成书以前以单篇流传,要么是在成书之后以不同的版本流传,但事实上仍然是同一部著作,而非多部,《商君书》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
至于第二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汉志》载:

故事实上在汉初,张良、韩信就已经开始在各家有关军事的著作中删取三十五家作为定本。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家著作极多,而且情况十分复杂,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固然会涉及军事方面的内容,也会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张良、韩信作为权谋家和军事家,其所考虑的首先应该是富国强兵,故有关富国强兵的著作肯定会在他们“删取”的范围之内,至于这部著作是否完整和书中篇章出现的先后,则未必会是他们优先考虑的目标。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战争频繁、兼并激烈的年代,其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所以他的著作与富国强兵无涉的内容可能极少,故可能正是在这个时候,张良、韩信从有关商鞅的著作或直接从《商君》中选取了大部分篇章,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编成了《公孙鞅》。其之所以没有继续沿用“商君”的名号而把它改为“公孙鞅”,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因为《公孙鞅》的篇数和《商君》有差异,文本也经过一定的整理,为了和原来的《商君》区别开来,故将其名为“公孙鞅”;二是可能因为汉初刚推翻暴秦,而秦国的残暴一定程度上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汉人对此还耿耿于怀,故将其著作直接以名字而非爵位来命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文中提到,《史记》中已经出现了一部叫《商君》的著作。故后来刘向等人重校群书时,刘向所据的可能是《商君》,而任宏所据的可能是《公孙鞅》,底本不同,所以两者有篇数上的差异,但是本质上它们同属一书,只不过是篇数有异。

而从目前出土文献的情况看,哪怕是同一篇文献,两者的内容、章数、段落次序、语句,甚至句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如郭店楚简中的《缁衣》和《礼记·缁衣》篇的情况。简本《缁衣》是战国时期的文献,传本《缁衣》是经汉人整理过的文献,两者从其内容上看显然是同一篇文献,但其中的遣词造句、篇章句序、行文详略等都存在极大的差异。此外,清华简《蟋蟀》与《唐风·蟋蟀》篇的情况也应与之类似。”(61)关于这两篇文献之间的关系详情,参见黄效:《清华简〈蟋蟀〉再议》,《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所以,西汉之前没有经过统一整理的文献,即使是同一文献,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可能是十分巨大的。刘向之前的文献基本没有一个固定的版本,也可能没有固定的次序、章数,甚至句子和内容也可能被传播、整理者润色。“故对于《商君》与《公孙鞅》的区别,非常有可能是由于刘向与任宏在校书时的取向有所不同造成的。”今本《商君书》虽然从属法家类著作,但其中有“兵”字的便有21篇,有“战”字的便有18篇,两者相加除去重复,其涉及军事的就占22篇,几乎覆盖了全书。这还不算间接谈治乱的篇章,如果算入的话,除了《六法》一篇外,几乎全书都与国家间的争霸存亡有关。故按照以上对兵权谋家著录标准的分析看,其完全够格列入兵权谋家类,也完全可能会被张良、韩信选取。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兵权谋家《公孙鞅》与法家《商君》在篇数上差了两篇,其文本情况也可能有诸多差异,这也是它在《汉志》中重复被著录的原因,但其中的内容应该绝大部分是重合的,而且应该同属一书。
三、《商君书》的书名和篇数问题
除了上述的成书及《商君》与《公孙鞅》的关系问题之外,《商君书》的书名及其篇数的变化同样有待理清。我们在上文中提到,《商君书》一开始并非称为“商君书”,《史记》称为“商君”,《汉志》称为“商君”和“公孙鞅”,但到了三国时期,刘备将其称为“商君书”,这是“商君书”一名出现的最早记载。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口中的《商君书》并非归入其所称的“诸子”一类,而是将之和诸子及《六韬》这部兵书并列,故其所见的《商君书》或许不是汉时法家类的《商君》,因为法家类的著作亦属诸子中的一种,没有必要单独列出,其和《六韬》这部兵书并列,则其属于兵书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故刘备所见的《商君书》可能就是《汉志》中兵权谋家类的《公孙鞅》。
此外,南北朝时期梁人庾仲容《子抄》法家类谓“《商子》五卷”,这是“商子”一名出现的最早记载,故清人《善本书室藏书志》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谓《隋志》始称“商子”的说法并不准确。上文已提到,目录学在魏晋南北朝有了新的发展,晋人荀勖因魏人郑默《中经》作《中经新薄》,将刘向班固等人的“七分法”变为“四分法”,经、子观念在目录学中得到加强,故在魏晋以后,《汉志》法家类的《商君》可能就逐渐变成了《商子》。我们知道,在“七分法”变为“四分法”的过程中,兵书与诸子常被合为一类,那么在这些合并的过程中,法家的《商君》与兵权谋家的《公孙鞅》有没有受到影响而被重新整合了呢?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唐初魏征等人所编的《群书治要》的情况,我们或许可以作一些合理的推测。上文中我们提到的《群书治要》中辑录了《商君书》中的三篇,并称之为“商君子”。笔者认为,《群书治要》辑录的三篇,极有可能是来自与商鞅有关的两种著作。因为从书名而言,“商君子”的书名,更像是为了行文简洁而将“商君书”和“商子”这两种书名合称。详细理由如下:第一,如果不是两书的合称,那么前代已有关于商鞅著作的书名诸如“商君”“公孙鞅”“商君书”“商子”之类,其在辑录时直接沿用前面的称法即可,又何必另造一书名叫“商君子”,既拗口也显得多余。第二,这三篇文章应该都是与《商君书》有关的著作,同属魏晋南北朝后目录学上的乙部或丙部,这实际上是后世的子类。而且我们上文已经分析,《商君》和《公孙鞅》应该多有重合之处,所以这三篇文章可能同出自这两本书,或其中的某些篇章如《修权》和《定分》共见于这两本书,只有《六法》一篇不同而已,故为了行文简洁而将其合称。第三,《群书治要》中所辑录的《六法》一文,其引文在《修权》篇之前,但今本《商君书·修权》篇前并未缺佚,其《定分》一篇和今本《定分》篇也有数十字的差异,故这两篇也有可能来自与今本《商君书》不同的书籍。第四,对于《商君》和《公孙鞅》何时被整合的问题,有可能是在魏晋南北朝目录学发生变化之时,也有可能是在唐初之时。因为两者的重复程度较大,所以后人是非常有可能再次对两者进行删并的,并将其称为“商君子”,后世学者不明就里,故又将“商君子”改称为先前已有的“商君书”或“商子”,以致两书的源流混淆模糊了。第五,根据我们上文的分析,今本《商君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和军事有关,只有少数篇章及佚篇《六法》与军事无涉,这或许也说明今本《商君书》或是混合了商鞅兵、法两类的著作,或主要传承了兵权谋家《公孙鞅》二十七篇的作品。故《商君书》书名的变化,或许反映了此书的源流情况。
而对于《商君书》的篇数问题,《汉志》法家类著录《商君》二十九篇、兵家类《公孙鞅》二十七篇,但《子抄》时变篇为卷,已从之前的二十九篇或二十七篇变成了五卷,且兵家类《公孙鞅》已不见著录,只有法家类的《商子》,《隋志》《见在书目》《意林》等著录又分别出现“五卷本”“四卷本”和“三卷本”,但亦无具体篇数,故清人《善本书室藏书志》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谓《隋志》所载的“五卷本”为“二十九篇”的说法并不准确。至南宋时目录学著作才出现具体篇数的记载,但已剩二十六篇。南宋末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又亡一篇,故南宋末年实余二十五篇,清时又亡一篇,今仅剩二十四篇而已。需要澄清的是,马端临《文献通考》谓:“《周氏涉笔》曰:‘陈氏曰,《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62)(元)马端临:《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三)·文献通考·经籍考》(三九),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7页。这里《周氏涉笔》中所称的“陈氏”云云,当是指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今考武英殿聚珍版《直斋书录解题》,其所记为“今二十六”篇,非“二十八篇”,上文已有引用,不知周氏所据为何本。后四库馆臣(6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48页。、王时润(64)王时润:《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商君书斠诠五卷》(第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58—59页。、蒋伯潜(65)蒋伯潜:《诸子通考》,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361页。、梁启超(66)梁启超:《饮冰室专集(四十八)·汉书艺文志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0页。等亦有类似的论述,他们的说法应该都是误引《周氏涉笔》所致,如武英殿聚珍版《直斋书录解题》无误,则四库馆臣、王氏、蒋氏、梁氏于此处实为以讹传讹之说而已。
那么南北朝以后的“五卷本”“四卷本”“三卷本”的《商君书》到底有多少篇呢?又是从何时开始亡佚的呢?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清人丁丙、瞿镛认为《隋志》所载五卷本就是二十九篇,但并不准确(说见上文)。当然,历史上主流意见还是认为《商君书》应该有二十九篇,但也有人认为只有二十七篇或二十六篇。二十七篇者如清人孙星衍、王时润(说见上文第二部分的引文),二十六篇者如明人黄之寀,其谓:
《汉书艺文志》录《商君》二十九篇,《正义》云《商君书》五卷,《馆阁书目》,今是书具存共二十六篇,三篇亡。剑今考此本目具二十六篇同,唯中一亡篇失其目,更亡《刑约》一篇,则所亡止二篇也。岂三篇亡之说,二字伪作三与?剑叟记。(67)(周)商鞅撰,(明)黄之寀校,(清)吴广霈校并跋:《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商子全书五卷》(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我们目前见到的五卷本《商君书》为二十六篇,其中第十六篇《刑约》有目无文,而第二十一篇本来目与文并亡,但清人又根据明时施氏本补出其篇目为“御盗”。故现在实知的有二十六篇,其中两篇为有目无文之作。但是后人又据唐《群书治要》辑录出《六法》一篇,故今已知的篇数为二十七篇,黄氏二十六篇的说法和实际情况不符。另外,《馆阁书目》所说的亡三篇应该是相对《汉志》的二十九篇而言,而不是说二十六篇中又亡了三篇,黄氏此处应该是会错了意,故疑“三”为“二”。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晋书·庾峻传》中出现了“六蝎”一词,其不见于今本《商君书》,唐李商隐亦曾作有《虱赋》与《蝎赋》,清人徐炯谓:“晋《庾峻传》:‘唯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然则‘六虱’‘六蝎’并出商君之书,义山所以赋此二物也。”(68)(唐)李商隐、(清)徐炯笺注:《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李义山文集笺注》(卷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1页。清钱熙祚据此怀疑《商君书》中另有一篇关于“六蝎”的佚文:“今检《靳令》《弱民》二篇,并有六虱而无六蝎,岂蝎误为虱耶?抑逸篇中别有六蝎之文耶?”(69)(周)商鞅:《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商子五卷》(第三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钱氏的推测不无道理,但根据后世中出现的引文情况,“六蝎”一词属《晋书》误引的可能性较大。唐杜牧在《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一文中谓:“彼商鞅者,能耕能战能行其法,秦基为强,曰:‘彼仁义,虱官也,可以置之。’”(70)(唐)杜牧:《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樊川集》(卷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62页。而《商君书》中谈到“虱”的一共有两处,其中《去强》篇以“岁”“食”“美”“好”“志”“行”为“六虱”,(71)周立昇等:《商子汇校汇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155页。《靳令》篇又谓“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72)周立昇等:《商子汇校汇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426页。杜氏之语,虽不见于今本《商君书》,但其意当出自《靳令》篇,因为《靳令》篇已明确将“仁义”列为“六虱”之一,杜牧可能只是取其意而已。又五代时期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引《商君书》谓“锴按,《商子》曰:‘有敢剟定法令者死。’”(73)(五代)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0页。“臣锴曰,《商子》论兵曰:‘怨如钜铁。’”(74)(五代)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1页。今本《商君书·弱民》篇即有论楚国之兵谓“宛鉅铁釶”(75)周立昇等:《商子汇校汇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687页。,故徐锴此处所引的“怨”或应作“宛”。由杜牧和徐锴的情况可知,古人在引用古书时未必是一字不漏地引用,而是取意的可能性较大。故《晋书·庾峻传》中的“六蝎”或为错引“六虱”所致。故考古今佚文,其实不能有超出二十七篇者,至于它实际的篇数情况,则由于文献缺乏不得而知。
而对于《商君书》是从何时开始亡佚的问题,亦有南宋和五代两种说法。上文提到的孙星衍就认为隋唐时期《商君书》并未缺佚,其缺佚当自南宋时始。朱师辙则认为:“魏征《群书治要》引《商子·修权》(笔者按,当为《商君子·修权》)篇前有《六法》篇,宋本已无此篇。知唐时《商君书》尚完全,诸篇之失当在唐末五季之乱矣。”(76)朱师辙:《子藏·法家部·商君书卷·商君书解诂五卷附录二卷》(第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325—326页。其认为缺佚当在五代时,比孙氏的南宋说要早。但以上说法或都有待商榷,因为据笔者搜罗,宋廖莹中在《东雅堂昌黎集注》中谓:“诸本‘虱’作‘风’,今从唐杭荆公洪谢本云:‘《商君》二十六篇,大抵以仁义礼乐为虱官,曰:“六虱成俗,兵必大败。”’”(77)(唐)韩愈、撰,(南宋)廖瑩中注,(明)徐时泰编:《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东雅堂昌黎集注》(卷六),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1页。后经朱熹考异,把“杭荆公洪谢”改为“杭谢公里谢”,(78)(唐)韩愈、撰.(南宋)朱熹考异,(南宋)王伯大音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652册)·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传一卷》(卷六),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但对其前缀“唐”字并无改动,而此处的“唐”字应是指唐时人之意。廖莹中本人为南宋时的藏书家、刻书家,其所记当有所本;朱熹为一代文宗,见识也应广博,其两人对此并无异议,故《商君书》在唐时可能已是二十六篇,而不必等到五代或南宋之后。又我们虽然知道杭谢公为唐时人,但已经不知其具体生活在唐代何时。但韩愈本为唐朝中后期人物,而其生活的时间不可能早于韩愈,故其为唐代后期人物无疑。因此,我们推测五卷本《商君书》的缺佚时间应该在韩愈之后、五代之前的唐代末年。至此,我们对《商君书》的书名、篇数及何时开始亡佚的问题也大致作了梳理。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就历代的著录情况而言,虽然各代能见到著录的资料的多少有异,但《商君书》的源流是清晰的。应该在韩非之前就已经有商鞅学说的出现,否则《韩非子》中的说法就无从谈起,其成书则应该至迟在西汉初年或秦朝时期,其有固定的版本,则可能要等到刘向校书之后。《汉志》中出现了两种与商鞅有关的著作,一为法家类二十九篇的《商君》,另一个为兵权谋家类二十七篇的《公孙鞅》,而根据汉代对书籍的整理情况、《汉志》的著录体例、刘向校书时的情况和今本《商君书》的内容特点,我们对《公孙鞅》一书的缘起作了探讨,并认为虽然兵权谋家《公孙鞅》与法家《商君》在篇数上差了两篇,其文本情况也可能有诸多差异,但其中的内容应该绝大部分是重合的,其之所以会被重复著录,可能是由于两者的版本不同。而就其书名的流变而言,《汉志》法家类称之为“商君”,兵权谋家类称之为“公孙鞅”,三国时刘备称之为“商君书”,南北朝时“商君书”和“商子”都有,《群书治要》中又出现了混合两者的“商君子”,唐代主要以“商君书”一名行世,五代后又主要以“商子”为主,其书名凡数变。“商子”的出现可能和经、子学术的分化以及目录学中分类方法发生了变化有关。《商君书》的篇章内容也可能在魏晋南北朝目录学发生变化之时或在唐初之时重新经过整合。而就其篇章数目而言,《汉志》法家类著录为“二十九篇”,兵家类著录“二十七篇”,南北朝时期为“五卷”,隋唐时有“五卷”、“四卷”、“三卷”本,明时又有“一册”和“一卷”本,南宋晁公武时存二十六篇,后至陈振孙时又亡一篇,清时又亡一篇,最终余二十四篇而已。根据一些新材料,我们把《商君书》开始缺佚的时间推测为韩愈之后的唐代末期。我们后来虽然发现了一些佚文,但属于古人误引的可能性较大。而就其分类而言,《汉志》将其列为法家和兵权谋家,其后主要被列为法家,但宋时又曾被列为杂家,明时又曾被列为官制类,清时又曾被列为兵家。至此,我们就对《商君书》的源流情况大致作了一个梳理。
由《商君书》的源流情况我们也可以略窥先秦古书流传的崖略。《商君书》本来应该是战国时期的文献,但是由于当时古书多以单篇流传,而且《商君书》中的许多篇章产生较晚,所以《商君书》的成书可能相对较晚,而从汉代的情况来看,其可能晚至刘向时才有固定的版本。那么在拥有固定版本之前,《商君书》的内容是否一成不变呢?这恐怕未必,因为单从书的篇名来看,《淮南子》所称的《启塞》,司马迁所称的《耕战》,都未见于今本《商君书》,今本《商君书》将《启塞》变成了《开塞》,将《耕战》变成了《农战》。既然篇名可以改变,那么内容也未必不可改变,但是无论是“启塞”还是“开塞”,“耕战”还是“农战”,它们的意思大概一致。当然其他篇章也可能产生完全不一致的改变,这点由于文献的失传我们已无法辨别。那么在有了固定版本以后是否也会发生改变呢?我们知道,《商君书》在汉时不称“商君书”,而是称为“商君”,据《汉志》所载有二十九篇,但是汉代以后《商君书》的书名和篇数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它的内容也是否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不是不可能的,《群书治要》中《定分》篇的内容和传世本中《定分》篇的内容就不尽相同,证明唐时它的文本内容仍然处在变化之中,只是这种变化的幅度可能比拥有固定版本之前要相对小一些而已。这就给我们以下启示:第一,我们在对古代一些文献进行研究时,必须承认文本的内容可能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而且这种变化应该并不拘于某一朝代。第二,我们在处理古代文献,特别是先秦文献时,不能轻易根据个别的字词就认为它是真,或伪,这种做法在当今学界颇为流行,而应该综合多方证据进行判断。像上面我们所举的“耕战”与“农战”一词一样,虽然“耕战”一词可能出现得晚些,但是它的意思和“农战”甚为接近,司马迁用“耕战”来代替“农战”可能只是想把它变得更为通俗而已,这点在司马迁的《史记》那里是常有的事,而非涉及内容的真伪性,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考察《商君书》源流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