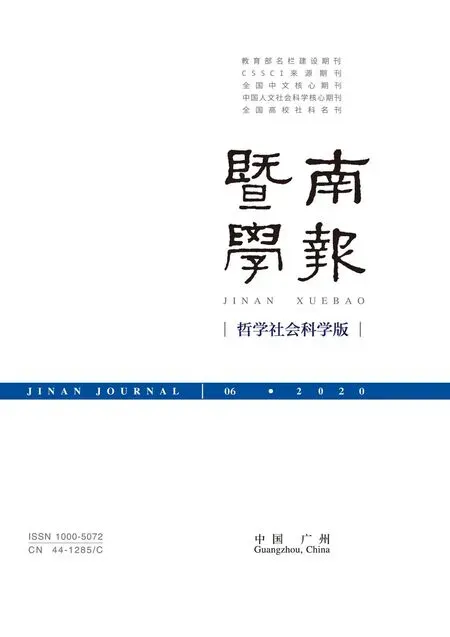商鞅及早期法家的学术批评
——以《商君书》与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为中心
高华平
法家是先秦诸子重要的学派之一。对于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吴起、商鞅等人的思想特点及成因,学术界已做过多方面的探讨,并取得过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这些研究似乎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他们并未将吴起、商鞅的思想与当时思想界业已存在的诸子百家之学结合起来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讨论,以见出早期法家思想与当时诸子百家思想之间相互吸收与批评、继承与扬弃的复杂关系。有鉴于此,笔者在此尝试以《商君书》的解读为基础,围绕商鞅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互动关系,从先秦学术批评史的角度,对以商鞅为代表的早期法家思想家与当时诸子百家思想的继承和批评关系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考察,以期更准确和更深入地揭示先秦法家思想的演变轨迹及其内在思想史的深层原因。
一、先秦早期法家思想的特点
对于先秦法家思想,学术界通常将其划分为尚法派、尚术派、尚势派和法、术、势综合派。尚法派以商鞅为代表,尚术派以申不害为代表,尚势派以慎到为代表,法、术、势综合派则以战国末期的韩非为代表。先秦法家的创始人,前人或以为是“撰次诸国法,著《法经》”的李悝,或以为是最早实行“变法”的吴起,或以为是在秦国成功实行“变法”的商鞅,(1)于先秦法家之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李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彊兵。”《晋书·刑法志》曰:“律文起自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故世多以李悝为先秦法家之创始人。近人蒙文通则曰:“法家之学,莫先商鞅。”(见蒙文通:《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01页)但李悝仅“撰次诸国法”而“著《法经》”,商鞅之生卒年及“变法”年代皆晚于另一位法家思想家吴起,故笔者认为先秦法家的开山祖应为吴起。(参见高华平:《先秦诸子与楚国诸子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186页。)似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李悝、吴起、商鞅都属于先秦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应该代表了先秦早期法家思想的特点。
李悝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为“《李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彊兵。”但这二十二篇书早已亡佚,后人已无从据以讨论李悝的思想。后世学者据以探讨李悝思想的基本资料,一是《晋书·刑法志》所谓“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云云;二是《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汉书·艺文志》儒家类又有“《李克》七篇”,班固自注:“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史记·货殖列传》亦曰:“当魏文侯时,李克尽地力之教。”以往学者皆认为(李)悝、(李)克乃“一声之转”,殆即一人。从这些有限的材料来看,李悝应是从儒家学派脱胎而来的,他虽著有《法经》和“尽地力之教”等“积极一面的经济政策”(2)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页。,但在法家理论方面却并没有多少建树。
吴起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杂家类”有“《吴子》一篇”,前人多以其“颇似吴起”,认为应属吴起的论政之文,可惜其书早亡,无得据以而论其思想。(3)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又有“《吴起》四十八篇”。《韩非子·五蠹》曰:“今境内言兵,藏孙(武)吴(起)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之。”《汉书·艺文志》的“《吴起》四十八篇”原在《兵书略》,应该就是“世俗所称”的《吴起兵法》了。《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有“《吴起兵法》一卷,【魏】贾诩注”。但《宋史·艺文志》著录此书,已变成了“《吴子》三卷”。学者们考证认为,唐人所见的《吴子兵法》一卷,并非《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的“《吴起》四十八篇”;而《宋史·艺文志》中的“《吴子》三卷”,今存六篇,“辞意浮浅,已非原书”(4)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郭沫若猜测:“或者今存《吴子》即是此书,被后人由一篇分而为六篇的吧。”(5)郭沫若:《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72页。客观地讲,这些看法多属臆测。可以肯定的只是,吴起传世的似主要为“兵家”著作而不是法家思想。
商鞅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为“《商君》二十九篇”。班固自注:“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商君书》五卷”,两《唐志》以后多称“《商子》五卷”。今传本《商君书》为五卷二十六篇,较《汉书·艺文志》少三篇,且《刑约》一篇有目无篇、第二十一篇并目亦亡,实存二十四篇。对于今传本《商君书》哪些篇属于商鞅自著,学术界仍存在较多争议。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先秦无私家著述”,“周秦诸子之书,不皆出自己之手,大率由其门生故吏或时人之服膺其说者、裒录其言论行事以为之。(此)上古书通例。”(6)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故不能因此而怀疑诸子著作与诸子本人学术思想的关系。在今存《商君书》二十四篇中,《更法》“称(秦)孝公之谥”,当“是法家者流掇拾鞅余论以成是编”;“《徕民》一篇,时势多非商君时事”,“在廿四篇中最为不伦”,“非商君意也”。故总体而言,《商君书》“其书即非商君自撰,要为近古,不失商君之意与其时事者也。”(7)蒋礼鸿:《叙》,《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张林祥的《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章“《商君书》各篇的作者和作时”,对该书与商鞅的关系有详细讨论,亦可参考。同时,笔者认为,即使《商君书》中那些可能属于商君后学所作的各篇,其思想亦只是对商鞅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故不能排除在商鞅思想研究资料之外。《荀子·议兵》曰:“秦之卫鞅,世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汉书·刑法志》曰:“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功,垂著篇籍。”《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亦著录有“《公孙鞅》二十七篇”。商鞅之兵书与传世本《商君书》的关系虽不可得而详,然“今观《商君书》中《算地》《赏刑》《画策》《战法》诸篇中论兵之语,至为精要,知其沉研此道者深矣”(8)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由此可见,商鞅的法家思想是和其兵法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其法家思想同时也是一种军政思想。
综观现存有关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思想资料,我们不难看出,先秦早期法家的思想似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首先,先秦早期法家思想皆源于儒家,与儒家思想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李克》七篇”,班固谓李克为“子夏弟子”。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虽后人颇疑此说中诸人年辈失序,(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9页。但李克(李悝)之学源于儒家则应无疑。《史记·吴起列传》说吴起曾学于曾子(《吕氏春秋·当染》同),《汉书·儒林传》则说他“受业于子夏之伦”;刘向 《别录》云《春秋左传》的传授系统为:“左丘明传曾申,申授卫人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10)刘向、刘歆撰,姚振宗辑录:《七略别录佚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皆可见吴起之学与儒家思想之关系。传世本《吴子·图国》曰:“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战国策·魏策一》《史记·吴起列传》亦皆载有吴起对魏侯“魏国之宝”乃“在德不在险”之说。可见,吴起“自然也是在初期儒家的影响中陶冶出来的人”,儒家思想的色彩是十分明显的。商鞅,虽说《史记·商君列传》说他“少好刑名之学”,似与儒家没有关系,但由他初说秦孝公“变法”所言皆为“礼法”来看,正如郭沫若所云:“他也是魏文、武二侯时代儒家气息十分浓厚的空气中培养出来的人物,他的思想无疑也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11)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248页。
其次,先秦早期法家的立论宗旨皆为富国强兵,故他们制定的法律政令多涉“兵法”,实施的法令亦皆带有战时法令的性质。《汉书·艺文志》在“《李子》三十二篇”之下班固注曰:“相魏文侯,富国强兵。”《汉书·食货志》则云李悝“著《法经》”、行“尽地力之教”的目的,皆在“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显然他实行的法令乃是针对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礼让”特殊时局而提出的,故带有战时法令的性质。同样,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亦是“要在强兵”。《商君书》明确定位当时的社会为:“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开塞》)因此,他提出的“画策”是“壹言”、“壹刑”、“壹教”和“兵战”之法,其目的乃在于使“民听于上”——“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战法》)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如在儒家著录“《李克》七篇”、在法家著录“《李子》三十二篇”一样,除在《诸子略》“法家类”著录“《商君》二十九篇”之外,于《兵书略》又著录了“《公孙鞅》二十七篇”。这种情况的出现,虽可能是因为刘向校“诸子”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时,两部分都有商鞅之书,故二人都做了著录,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似也正好说明,商鞅、吴起等早期法家制定和实行的法令实多属“兵法”,带有战时法令的性质。
再次,先秦早期法家思想常以治乱、虚实、强弱、贫富诸范畴论当时治国方略,肯定和提倡能增强国家实力、使国家走向治强的主张,而否弃和批评将导致国家政治混乱和贫弱败亡的思想。李悝的《法经》和“尽地力之教”固然是要使“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国以富强”。吴起谓魏武侯“山河之固”乃“在德不在险”,则是对以魏武侯为代表的以“山河之固”为实、以“德”“义”为虚的传统虚实观的否定,他认为山河的“险固”其实是虚而不可靠的,只有“德”“义”这种“软实力”才是实在的、可靠的。《商君书·农战》曰:“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又曰:“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商君书·慎法》曰:“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事而诵虚词。”皆以治乱、虚实、强弱、贫富诸范畴论当时政治社会和道德学术,进一步凸显了先秦早期法家重实力、图富强、强本抑末等思想特点。
二、《商君书》学术批评的主要指向
先秦早期法家对当时的各种政治思想和学术主张,皆以治乱、虚实、强弱、贫富诸范畴加以评判,肯定和提倡其中有利于富国强兵、增强国家实力的思想观点,而否定和扬弃了其中可能导致国家贫弱的思想因素。《汉书·艺文志》曰: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汉书·艺文志》的这段文字,虽然并非是就先秦早期法家的思想特点而发,也并非是论法家的学术批评的,但它说法家的优点在于“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即相当于是说法家的这一思想乃是吸收了先秦儒家的“礼”学思想而来的;而法家的缺点所谓“无教化,去仁爱”,则等于说它是否定了先秦儒家的礼义教化、摒弃了先秦儒家的仁义道德的。而很显然,这里的“仁义”、“礼制”、“教化”,不论是为法家所肯定或否弃,都是先秦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这既说明了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叙说”先秦法家完全是从儒家立场出发的,是儒家的批评视角也说明先秦法家主要是以儒家思想来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的。它肯定与否定、吸收与摒弃的,主要是先秦儒家的“仁义”、“礼制”和“教化”思想。以商鞅为代表的先秦早期法家思想都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商君书》中对先秦诸子百家展开学术批评的主要对象或目标,也是指向当时儒家的思想和行为的。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一个以“法”名家的学派,法家之“法”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为“变法”之“法”,即法度、法式或制度;二为刑赏之“法”,而且主要为“刑”。正因此,商鞅法家思想的内容也不外乎“因时变法”和保障法令制度统一的“壹言”、“壹刑”、“壹教”和“重刑”等思想主张。而且,它还对可能妨害法家思想的各种思想观点和行为予以了明确而坚决的反对,甚至欲以法律的手段加以禁止。如《商君书·更法》曰:“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这是主张“因时而变法”。同书《赏刑》曰:“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这是主张“壹言”、“壹刑”、“壹教”。《商君书·外内》篇曰:“故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淫道必塞,为辩知者不贵,游宦者不任,文学私名不显……以此遇敌,是以百石之弩射飘叶也,何不陷之有哉?”这则是对各种可能危害“法治”的思想行为坚决的否定和批判。
但是,如果我们对《商君书》中所反对和否定的各种“违法”思想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商君书》所批判和否定的思想观点和行为,如果从学派的归属来看,其实主要是针对先秦的儒家思想和言行的。如上文商鞅对反对“变法”者的批评,表面看来虽是对所谓“拘礼”和“守法”者的批评,但实际却是应该看作对儒家思想态度的批评的。因为儒家的孔子即是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并力求恢复三代的礼乐制度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孟子也说:“今之乐犹古之乐”(《孟子·梁惠王下》)。这都有“道不变,礼乐亦不变”的意思。但《商君书·开塞》却说:“法古则后于时,修今者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商鞅此处虽未明确说明自己是针对谁而发的,但由“周不法商,夏不法虞”,明显与孔孟“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相对立,故可知商鞅对反对“变法”和固守旧礼者的批评与否定,主要乃是针对当时的孔孟儒家的。
又如,《商君书·外内》反对所谓“必塞”、“不贵”和“不显”的“淫道”、“辩知”、“游宦”和“文学”等,虽然商鞅也未说明这些都属于儒家的思想和行为,但如果结合《商君书》全书来看,则其所要“禁塞”的“辩知”、“游宦”和“文学”等“淫道”,其实仍主要是属于先秦儒家的思想观点和行为的。《商君书·说民》曰:“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弱民》篇略同)同篇又说:“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举,奸之鼠也。”则其所谓“淫道”,乃是“淫佚之道”的意思,具体而言,即是所谓“礼、乐”。而又因为战国时代“礼乐”的主要提倡者是儒家,其内容则是由《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而来的“礼教”和“乐教”,故商鞅此处“必塞”的所谓“淫道”,其实就是指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而所谓“辩慧”“慈仁”“任举”之类,亦同样应该属于儒家的思想行为无疑。
“慈仁”属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自不待言。“任举”,蒋礼鸿以为当作“任誉”,并引《商君书·赏刑》和《韩非子·六反》以为证,说:“盖任为任侠,誉为名誉”——“任誉”即“任侠致声誉”(12)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页。。清人陈澧认为“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国时侠烈之风,盖出于此。”(13)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4页。故近代学者多以此“侠”乃是指“墨”而言,以法家批评“任侠”,即批评墨家的思想作风(《韩非子·显学》批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指儒、墨)的。但我认为,此处的“任誉”之“任”既非“任侠”,“任誉”一词更不是“任侠而致声誉”的意思。《说文解字·人部》:“任,保也。从人,壬声。”段玉裁注:“按上文云:‘保,养也。’此云‘任,保也。’二篆不相属者。‘保’之义,《尚书》所谓保抱也。任之训保,则保引申之义,如今言保举是也。”这说明,“任”之义应是“保举”,而所谓“任誉”,本即“任举”,即相互保举。相互保举者一定是以智辩巧言互相吹捧,激扬名声,以致声誉,故可谓之“任誉”。而不管是作“任举”还是“任誉”,似乎都和所谓“任侠”没有关系,不可能是所谓墨家的“任侠而致声誉”,而应该只会和儒家的好《诗》《书》及“文学”和“辩智”有关。退一步讲,即使“任誉”或“任举”的“任”是指“任侠”,在当时“任侠”的也不一定就是墨家,而很可能就是儒家。如《韩非子·显学》篇说的“子张氏之儒”,就很有一些勇武的精神,“言议谈说无以异于墨子”,“已经是更和墨家接近了”;但“他们尽管有些相似,在精神上(与墨家又)必然有绝对不能混同的地方”,所以他们仍然是儒家。(14)郭沫若:《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7—100页。故《商君书·说民》此处批评“任举”的理论指向,同样是针对当时儒家的思想和行为的。从今传本《商君书》来看,商鞅最为反对或批评最为激烈的,乃是所谓“五民”。《商君书·垦令》有曰: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此处所谓“褊急之民”,指气量狭小之民;因气量狭小,故斤斤计较、好与人争斗。“很刚之民”,指不听众指令的强有力的民众(参见《说文解字》)。“怠惰之民”、“费资之民”、“巧谀恶心之民”,应该是指“好学问”、为“博闻、辩慧、游居之事”而“恶农”的“辟淫游惰之民”。但在此“五民”中,“褊急之民”和“很刚之民”,似都与儒家有关,至少与“好学问”、习《诗》《书》的“辩慧”有关。《左传》昭公六年载“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郑铸刑书则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尽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似乎民众的“争”“斗”之心产生于法家自身的颁布法律;但这只是因为“持法最重名例,故法家必与名家相依”的缘故;(15)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但如果从儒家与刑名或法家的联系来看,则民之“争”“斗”之心形成的最根本原因,未必不是由于其“好学问”、习《诗》《书》及求“正名而开启智慧”的结果。《商君书·垦令》在下文接着又说:“农愚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可知“好学问”而“知”,是一切危害国家法令行为的根源。故商鞅此处对“好争”、“好讼”的“褊急之民”和“很刚之民”的拒斥与反对,不可能只是针对其“征于书”的“争心”,而更应该是针对引起其“争”“讼”之“心”的源头——“博学”和“辩慧”,即针对儒家的思想和行为的。
同样,商鞅“五民”中的“怠惰之民”、“费资之民”、“巧谀恶心之民”,亦皆是指“好学问”“习《诗》《书》”的儒家思想和行为,或至少主要是针对儒家的思想和行为的。《垦令》曾说:“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下文接着说:“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农战》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国之危也。”又说:“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以言相高也……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在商鞅看来,“贵学问”、“务学《诗》《书》”之民,一定是怠惰于农,外交谀上,空费国家粟帛钱财的无用之民,是应该坚决地批判和反对的;而这样的人十有八九又都是儒家人士。这就说明,《商君书》中所谓“五民”主要都是属于儒家的;商鞅所拒斥和反对的主要乃是先秦儒家的思想和行为。
当然,《商君书》中对“五民”也有不同说法。《商君书·算地》曰:“夫治国舍势而任谈说,(16)案:原文作“说说”,陶鸿庆曰:“上‘说’字当作‘谈’字。”此据以改。则身修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这是将“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合称“五民”;且这里的“五民”似乎儒、道、工、商都有,不独为儒家。但如果考虑到商鞅此处立论的出发点,仍在于“任谈说,则身修而功寡”上面,则仍不难看出,他对所谓“五民”的否定和排斥,重点其实仍是针对儒家的思想和行为的。因为这里“五民”所以托身之资,说到底仍不外乎儒家的“贵学问”、“务《诗》《书》”及由此而来的“辩慧”;只有具备了这些“士之资”,他们才会“轻其君”、“非其上”或“议其上”而“轻其禁”以“徙居”或“游居”。故《商君书》又有所谓“六虱”之说。《商君书·靳令》曰: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虱”繁体作“蝨”,《说文解字·虫部》:“蝨,齧(同书《齿部》:‘齧,噬也。从齿,声。’)人虫。从虫,卂声。”可引申指害人虫。“六虱”即“六种害人虫”。但此处所列“六虱”,文中却称“国有十二者”,与“六虱”之数目不符。《商君书·去强》既曰:“农、商、官三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弱民》篇同(17)学术界的研究多认为《商君书》中的《说民》《弱民》二篇,实“为《去彊》篇之注”。《弱民》言“三官生六虱”与《去彊》篇同。参见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2—161页。)又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同书《赏刑》曰:“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则不仅数目不一,所谓“虱”的内容亦互有异同。故近人蒋礼鸿注《靳令》曰:“此言十二者,而中间所列凡九事。《农战》《去彊》《赏刑》三篇并有其文,名目或同或异,数目或十或八,或不举数。盖六者乃汪中所谓虚数,必斠而一之,则非矣。”(18)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9页。而历代学者于“三官者生六虱”之“岁、食、美、好、志、行”所指争讼不止。我认为,在“岁、食、美、好、志、行”六者之中,尽管其确切含义难以确指,但“岁、“食”属“食货”之事,后四者则属价值范畴,且多出于儒家则应属无疑;而所谓“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或“礼、乐、《诗》《书》善、修、孝弟(悌)廉、辩”诸范畴,除“非兵”、“羞战”主要应出于墨子的“非攻”之说外,其余显然皆属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商君书》对所谓“六虱”的批评和否定,其批评的目标始终主要都是针对先秦儒家的。
不仅如此,即使是《商君书》中正面论证其极端重刑观的“刑用于将过”、“刑九赏一”、“以刑去刑”等思想主张,其实也是隐含着对儒家思想观点的反驳与批判的。《商君书·说民》论述其“行刑重轻”的观点说:
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彊;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商君书》这里的立论目的,当然是为论证其“行刑重其轻者”之必要。他认为,只有“重其轻者”,才可能使“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即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真正实现“天下大治”。但他同时也并没有忘记对当时社会流行的“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的量刑原则予以反驳与批评,使他的这篇文章做到有“破”有“立”,立论和驳论结合。他认为“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根本起不到法律的威慑作用,结果只能是“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虽然使用了刑罚,但各种犯罪行为(“事”)仍然会不断出现,不仅会导致社会的“乱”,更会使国家衰弱(“国削”)。而在当时那个属于“儒墨显学”的时代,商鞅所批评与反驳的“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的观点,无疑主要是应该针对儒家所主张的法治原则的。《尚书·立政》记周公之言曰:“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孔传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罚,不轻不重。”)这说明儒家自其奉以为“圣人”的文、武、周公以来,即已有施刑“不轻不重”的主张。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不要随便使用刑戮,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为政》《颜渊》《子路》等)如果一定要用刑杀,则应“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即遵循执法公正和量刑公平的原则。《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
孔子相卫,弟子子皋为狱吏,刖人足,所跀者守门……夜半,子皋问跀危曰:“吾不能亏主之法令而亲跀子之足,是子报仇之时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于子?”跀危曰:“吾断足也,固吾罪当之,不可奈何。然公子之方狱之治臣也,公倾侧法令,先后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悦而德公也。”
孔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
孔子这里所说的“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正是上文《尚书·立政》篇中的所谓“不轻不重”之意;而孔子弟子子皋行刑跀危时不仅要做到客观上“不轻不重”的“公平”,更有主观上有“轻其重者”的“不忍”。而这些,既是与商鞅法家思想家的主张针锋相对的,应该是当时社会主流的法律思想。商鞅要论证其“行刑重其轻者”思想观点的合理性与正确性,自然不能不对与之相反的观点进行反驳,也就不能不对持这种观点的儒家思想行为给予重点的批评了。
三、商鞅对道、墨、名、法等诸子学派的批评与继承
商鞅除了对属于当时“显学”的儒家思想和学说进行重点的批评之外,对当时道、墨、名、法等诸子学派的思想也给予了相应的批评和继承。
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一点学术界的讨论可以说已相当充分。稷下“黄老学派”因有兼采阴阳、儒、道、名、法的特点,故或被人称为“黄老道家”,或被人称之为“稷下法家”、“道法家”或“法道家”,等等,即可看出法家与道家关系的密切与复杂。
从现有文献来看,在中国先秦思想中有意识地将法家思想与道家思想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当属法家的商鞅。商鞅之前的李悝、吴起等人,儒家思想成分较多,在法家思想理论方面的建构又少,故基本未涉及道家思想。商鞅是先秦法家历史上第一位有理论建设自觉的思想家,故他对当时儒、道各家思想都有借鉴与吸收。上文引郭沫若说:“他(指商鞅——引者)的思想无疑也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已可见出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商君书》又屡言应使民“愚”、“朴”、“无知”等,则显然又带有道家“愚民”和“反朴归真”等思想的特点。《商君书·垦令》曰“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这是其“愚民”观点。同书《农战》曰:“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智)虑”;《禁使》曰:“故遗贤去知(智),治之数也”,等等。这又是“民朴”、“不淫”和“遗贤去知(智)”之说。而这些都明显是先秦道家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如《老子》中就曾提倡“愚”,曰:“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第3章),“见素抱朴”,“众人皆以,而我独顽似鄙”(第19章、第20章)。又曰:“返朴归真”,“去甚、去奢、去泰”(第28、29章),等等。上文我们曾说商鞅批评当时社会的仁爱、礼智、举贤任能之风是针对先秦儒家的;但从思想源头上来看,《商君书》对儒家仁义礼智、贤德辩慧的批评,其实很多都是沿袭道家老子的观点。《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第38章)又说:“绝圣弃智,民利百信;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3章)商鞅对儒家仁、义、礼、智的批评,显然与老子对仁、义、礼、智和“辩慧”的否定态度一脉相承。《老子》还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第81章)“不尚贤,使民不争。”(第3章)等等。而《商君书》中对儒家“美、好、志、行”和“善、辩、孝、廉”等善行贤德的批评,显然也正是对老子否弃“美”、“辩”、智、“博”等“不尚贤”观点的继承。所不同的只是,道家《老子》主要是从道家的“道德”标准出发,反对仁、义、礼、智和“美言”、“善”、“辩”、“知”、“博”之类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即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18章)。而商鞅则更主要是从实用功利的立场出发,认为这些将影响国家的“壹言”、“壹教”,影响国家引导人民抟力于农战,并最终影响法家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因此,商鞅同时又对道家的某些思想和行为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如《老子》曾明确地说:“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57章)这是对“法令”和法家之“法”的直接否定,认为“法令”不仅不能导致社会的安定,相反还会使社会上滋生更多的违法行为。因此,这里甚至可以说是包含了某种要求取消“法令”之意。但《商君书·错法》却曰:
臣闻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
在商鞅看来,“法令”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必须制定和实施。这不仅是认为“法令”乃“治国之本”,是“民利”所赖,而且,“法令”应越繁越详越好。只有“法令”十分严密和烦苛,人们的一举一动才都有章可循,也才能使人民微小的过错都不遗漏而受到惩处。这样,就能通过“刑用于将过”,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故《商君书·说民》曰:
法繁则刑繁,刑繁则刑省。(19)此两句原作“法繁则刑繁,法繁则刑省”。蒋礼鸿曰:“‘法繁则刑省’疑当作‘刑繁则刑省’。‘刑繁’即下文‘行刑重其轻者’,‘则刑省’即‘则重者无从至。其定刑繁,则其用刑也省,是所谓以刑去刑也。’”(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页。)
这样,商鞅通过“法繁”、“刑繁”、“刑省”三者关系的论证,否定了老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观点,也可以说实现了对道家老子学术思想的批评。
商鞅同时也有对先秦墨家思想的继承和批评。
作为法家思想家的商鞅,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对墨子“法仪”、“法度”的重视。《墨子·法仪》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故百工从事,皆有法度。”(《群书治要》引)此即表明墨子对于所谓“法仪”、“法度”,即“法”的重视。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受墨家重视“法仪”、“法度”思想的影响,但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重视的已不是“百工从事”的规矩方圆等“法仪”,而是专指“治国之法”。他说:“国之所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商君书·修权》)“故有明主忠臣产于今世而欲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法。”(《商君书·慎法》)即应是对墨家“重法仪”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但商鞅所尚的“法”,不仅不是墨子所谓“百工之规矩”,亦非其以为“治法”的“法天”及所谓“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的“天志”(《墨子·法仪》),而且他还对这种以“爱利”、“仁义”为内容的所谓“天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种所谓的“法治”实是“释法度而任辩慧,后功力而进仁义”(《商君书·慎法》);而“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商君书·画策》),从根本上走上了“法治”的反面。
商鞅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是:“民之生(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故可以说:“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同上,《赏刑》)“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同上,《君臣》)但在商鞅以前的诸子学派中,儒家的孔子基本不论人性,只是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早期道家的老子、杨朱也不见直接论“性”之文,只是老子认为宇宙的创生乃“道生之,德育之,物形之,势成之”(第51章)的过程,“因此,老子的道德论,亦即老子的性命论”;“他对于道与德的规定,亦即他是他对人性的规定”。(20)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06、307—308页。而又因为这种所谓“性”,“是自然的朴素的,乃所谓‘德’之显现”,故“可以称为性超善恶论”,“亦可以说是一种绝对的性善论”(2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65—266页。。从现有文献来看,商鞅之前的先秦诸子与之有相类似的人性论观点的,似只有墨子。《墨子·尚贤下》曰:
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王引之曰:“‘安’犹‘乃’也”)生生。
墨子此处并未明言普遍的人性如何,但他说“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云云,则无疑已包含“士君子”之“性”乃趋利避害、好逸恶劳之意。“天下之士君子”之德性自当高于一般民萌及愚贱不肖者,他们之“本性”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民萌”及愚贱不肖者之本性趋利避害、好逸恶劳则更不待言。故墨子一书处处皆以“利”为言,其对“义”的定义亦为“义利也”(《墨子·经说下》)。对世上的一切事物皆以功利权衡之曰:“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同上,《亲士》)而现实社会纷乱争斗的根源,亦由于人的自私自利之本性使然。《墨子·兼爱上》曰: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
墨子又将这种自私自利的“私爱”称为“别”,以与“爱人若爱其身”的“兼爱”相对。
很显然,墨子这种以人的本性为趋利避害、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了商鞅对人之本性的认识的,成为了他提出以“刑赏”之“二柄”治国的“法治”主张的理论根据。《商君书·算地》篇既说:“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又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这正是从人之好逸恶劳、追求名利的本性出发,提出“壹于农战”的治国方略的。同时,《商君书》所谓“壹言”、“壹教”思想观点的提出,亦当是受墨子有感于当时“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且人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因而提出“尚同”主张的影响。上文言商鞅批判儒家的礼乐繁饰,其基本观点也应该来自墨子“节用”、“非乐”等崇尚功利实用的立场。
但商鞅又并非全盘照搬墨家的思想观点,他对墨子本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核心价值和好辩、“外交”等行为,都给予了明确的批评。
上文已经指出,商鞅对“兼爱”、“尚贤”、“非攻”、“辩慧”、“外交”等思想观点的批评,其中很大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针对当时儒家的;但无可避讳的是,其中也有很多批评是针对当时的墨家,或至少是包括了当时的墨家思想的。如墨子因“兼爱”而“非攻”、“非战”,但《商君书》则针锋相对地主张“强兵辟土”,主张使全民“壹于农战”,“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赏刑》)而《商君书·靳令》则径将“非兵”、“羞战”与仁义、礼乐等合称为“六虱”,并予以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先秦时期的“贤”概念,本应兼指德行、才能皆优者,如《尚书·大禹谟》:“野无遗贤,万邦咸宁。”这里的“贤”,即指德、才兼优者,但“贤”有时也偏指德行或才能。《周礼·地官·乡大夫》曰:“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郑玄注:“贤者,有德行者。”即偏指德行。《谷梁传》文公六年:“使仁者佐贤者。”范宁注:“贤者,多才也。”则偏指才能(大体而儒、道所谓“贤”偏于德,而墨、法所谓“贤”偏于才)。先秦典籍中又多以“贤”、“不肖”对举者。如《商君书·修权》曰:“不以法论智、能、贤、不肖者惟尧”;《荀子·儒效》曰:“身不肖而诬贤,是犹伛身而好升高也。”这里的“贤”都是与“不肖”相对的。而“不肖”的“肖”,《说文解字·肉部》曰:“肖,骨肉相似也。从肉,小声。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骨肉相似者,谓此人与彼人骨肉状貌略同也。”《说文解字》云“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乃是“释经传之言不肖,此引申之义也。”即是说,“不肖”的本义是“不似其先人之骨肉状貌”,但后来多用其“引申之义”,指无如其先人的德才,故与“贤”相对而言。商鞅对于所谓才德并不一般地反对。《商君书·画策》曰:“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肯定了“明主”“举贤”的意义。但他对“举贤与能”的所谓“尚贤”之弊端却更为关注。《商君书·慎法》曰:“夫举贤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诈。”这说明,商鞅之所以否定“举贤能”的“尚贤”,主要乃是因为评判“贤能”的标准和方式并非客观的审核名实或客观的法则,而在于道德或舆论的“善正”;而这种道德或舆论“善正”评价的基础,则是“朋党”众口一词的臧否,其最终的结果可能并非“尚贤”论者所期待的“贤能”得以选拔任用,反而是“使污吏有资以成其奸险,(使)小人有资而施其巧诈”。商鞅这里对“任贤能”思想主张的否定,无疑也是对墨家“上(尚)贤”思想观点的否定与学术批评。
先秦有“好辩”之风,墨家从墨子开始就是“尚辩”的。《墨子·耕柱》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这里的“辩”实际已是“将‘辩’的辩别、认识、论辩含义概括而成的一门学问”(22)张晓芒:《先秦诸子的论辩思想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而墨子的“谈辩”超出了当时诸子的地方还不在此,而在于他第一个提出了“辩”的原则和标准,即所谓“三表法”。《墨子·非命上》曰:
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言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辩不可得而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墨子在这里虽然同时以“本之者”、“原察者”和“发以为刑政”而“观之者”为“三表”,但其中最重要的,却无疑应该是所谓“本之者”,即“古者圣王之事”。故《墨子》书中动必以尧、舜、禹、汤、文、武为说,足见他的确是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底了。而这种动辄以“古者圣王之事”为言的辩说原则与标准,则说明墨子的思想中是存在强烈的“尚古”意识或“尚古”情结的。
《商君书》虽然也常举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为言,(23)在现存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商君书》是第一个将伏羲、神农、黄帝与尧舜、禹汤、文武并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商鞅可谓先秦“黄老学派”(或至少是先秦“黄老法家”)的先驱。似乎也给人以“尚古”的印象,但《商君书》援引“古者圣王”的目的,却似乎并非要“本之古者圣王之事”;恰恰相反,它只是为了说明自古以来即没有永恒不变之法,“古者圣王”皆是“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因此,如果要以“古者圣王”为法的话,那么,也只能是以“古者圣王”因时变法的精神为楷模,而不是固守他们的成法。而从某种意义讲,商鞅援引“古者圣王”以为例,不仅不是墨子的“尚古”,而恰恰是对墨子“本之古者圣王之事”的一种批评和否定。
商鞅对于他之前的名家思想也有吸收和批评。《汉书·艺文志》著录名家著作,始于“《邓析》二篇”。(班固自注:“与子产并时”)后代的研究一般认为“邓析的年代略前于孔子”(24)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今存《邓析子》一书“不类先秦古书”,应属于伪书之列。(25)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91页。自邓析始先秦的名家思想大致可分为偏向逻辑学意义上的、知识论意义上的“名”学和偏于伦理学、政治意义上的“名”学两个路向。前者(不论是与“名称相关的概念论”,还是作为“论辩拔技巧手段”的“辩学”)是后者(即伦理学、政治意义上的“名学”)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联系环节。(26)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1页。根据《吕氏春秋·离谓》《淫辞》及《左传》定九年经注等记载,邓析的思想无疑是十分重视“名”的,故他在作有属于“制名定律”的《竹刑》的同时,又以“善辩”闻名。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荀子·非十二子》所谓“好治怪说,玩琦辞者”。这说明他应该同时是逻辑学或知识论意义上与伦理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名家先驱。但必须承认,即使是在邓析时代或邓析本人那里,偏于逻辑学、知识论意义上与伦理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名”或名家,二者之间既是互相联系,也是互相冲突的。这种联系在于逻辑学、知识论意义上的“名”或“名学”是伦理学、政治上的“名”或“名学”的基础或前提,因为不论是纯粹论辩的“辩学”,还是政治伦理的“正名”,都必须以“与名称相关的概念论”为基础。这种矛盾冲突一是“与名称相关的概念论”要实现“名”“实”的相符(“相副”),就必须充分揭露“名”“实”之间的矛盾,有可能走向“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怪说”或诡辩,故《礼记·王制》曰:“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二是偏于伦理的、政治上的“名”的理解上,因为“名”既可以理解为区分等级的礼仪制度“名位”(《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即此义),也可以理解为与法律政令相关的“刑名”或“形名”之类;但“礼”与“法”既有一致性,即都强调上下等级制度的分明;但也存在冲突——“礼”为“礼治”之本,属于“礼治”时代,“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而“法”为“法治”之本,属于“法治”时代,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汉书·艺文志》)
《商君书》中“名”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名声、名誉、名利和功名,二是指伦理、政治意义上的“名位”或“名分”。而这种伦理、政治意义上的“名位”或“名分”,殆又可分为指“礼”或伦理意义上的“名位”和指与“法”相对的、属政治意义上的“名分”二义。《商君书·君臣》曰:“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这里的两个“名”都是指“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是“名位”的意思。《商君书·定分》曰:“今法令不明,名分不定(27)原作“其名不定”,蒋礼鸿曰:“‘其名’当作‘名分’。”今据以改。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6页。,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这里的“名分”与“法令”对举,表明“名分”即指“法令”,是法令制度及其规定。故近人吕思勉曰:“名、法二字,古每连称,则法家与名家,关系亦极密也。”(28)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2页。
《商君书》在如上意义上使用“名”概念,说明它与当时的名家思想是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的。它对此前已有的名家思想是采取了既有批评也有吸收、继承的态度的。它继承了名家思想与“礼”、“法”相联系的指向上下等级制度和法令制度的“名”之意义,提出了“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的主张,而对“烦言饰辞而无实用”的“谈说”“辩慧”“辩说”“私议”等“名辩”则给予了坚决的批判和否定。
我们在上文曾经指出,《商君书》对“辩慧”“辩知”“谈说”“私议”的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是因为这些思想和行为的根源乃由于“学《诗》《书》或“贵学问”而来,所以其主要矛头是针对儒家思想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不论是儒、墨在道德评价领域的“贤”、“善”、“辩慧”,还是道、法、形名各家在政治和法律领域关于法令与“名分”的讨论,都必须借助逻辑学或概念论的形式来进行。而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名家“名辩”的范围。因此,《商君书》对“辩慧”“辩知”“谈说”“私议”的批判和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对名家“名辩”思想行为的批评和否定。
《商君书》对“辩慧”“辩知”“谈说”“私议”等的学术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这些“名辩”乃“烦言饰辞而无实用”,“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此贫国弱兵之道也”。(《商君书·农战》)道德的说教不论多么美好,辩说的言辞不论多么巧妙,都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故应该禁止。其二,这些“名辩”即使属于政治或法律领域,也是属于“违法”的言论,同样应该予以禁止和否定。《商君书·定分》曰: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
《商君书·定分》篇所述“百人逐兔”的故事,亦见于先秦典籍《慎子》《尹文子》等。前人对此多从“立法明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上加以解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我看来,《商君书·定分》篇中的这段文字,其意蕴尚不止于此,它同时也是对当时名家“名辩”的批评和否定。因为“百人逐兔”之事之所以发生,并非是由于完全没有“法令”可依,而主要的只是因为“法令不明,名分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商君书·定分》)。这种情况,即是《礼记·王制》所说的“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可以说,要防止“百人逐兔”事件的发生,不仅需要“立法明分”,而且更需要使天下人不能“私议”已经形成于上的“法令”。故《商君书·定分》接着说:“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即不是将“名分不定”界定在“立法”的环节,而是明确地将其界定在“立法”(“为法”)之后的——这一阶段主要属于法令的实施或执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还仍然在“自议”“私议”或“辩慧”着“名”“法”的内容或价值的言行,这即使在儒家那里亦是不被允许的,故有所谓“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之说。《商君书·说民》曰:“辩慧,乱之赞也”;同书《修权》曰:“先王知自议私誉之不可任也。”这也是从“名辩”之“乱名实”或“乱法”的角度来加以批评和否定的。
商鞅是先秦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对于他之前的法家思想无疑也是有所继承和扬弃的。《晋书·刑法志》曰:“(李)悝撰次诸国法,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商鞅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可见商鞅对此前法家思想的接受。《商君书·更法》云:“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里是引“郭偃之法”以为自己“变法”的根据。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曰:“韦昭注:‘郭偃,晋大夫偃也’。又曰:‘卜偃,晋掌卜大夫郭偃也。’《春秋左氏传》皆作卜偃,无作郭偃者。其人则献公、文公间人。《左传》《国语》无此(引郭偃)二语。法,盖言之可以为法者也。”《商君书》此处所引郭偃既远在晋献公、晋文公(公元明636—前628年)在位之时,其言也并无涉及“名法”的内容,所可肯定的,只是商鞅对此前法家人物和思想是奉为楷模和准则的。今传本《商君书·禁使》曰:“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悬绳之数也。”其似乎已提出了法家的“势”“术”(“数”)学说,而这一学说的提出,也应该不是商鞅的凭空创造,应该包含了对此前法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只是前人多认为《商君书》中的这些篇章,应该不是商鞅本人所作,而是商鞅后学所作,因此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要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
除此之外,《商君书》对农家的重农思想也有明显的批评和继承。《商君书》明显吸收了农家的重农思想。《史记·商君书》裴骃《集解》引刘向《新序》既曰:“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策以富强,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云云,《商君书·垦令》《农战》《赏刑》等篇又都有使民“壹之农”的观点。故近人蒙文通认为“兵、农、纵横统为法家”,而有“李悝、商鞅又农家流欤”之说(29)蒙文通:《法家流变考》,《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85页。!但由于《商君书》本是极为重视礼法和名位的,故商鞅虽然没有谈到农家的“君臣并耕而食”之说,但仍不难想象他应该是和此后法家的韩非一样,对农家的这一观点是持坚决的批判和否定态度的。(30)高华平:《客观的总结与辩证地扬弃——韩非对先秦诸子的批判和继承》,《诸子学刊》编委会编《诸子学刊》(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至于商鞅对先秦诸子中的阴阳、纵横、杂、小说等学派的学术批评,则此数派或形成时代较晚,或其与法家思想关系太远,《商君书》中基本没有涉及,我们的讨论亦暂付之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