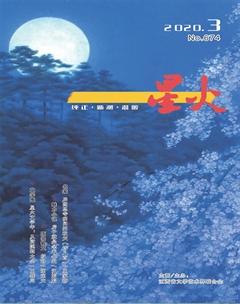我的孤独是一瓶啤酒
曾剑,湖北红安人,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现当代文学创作方向在读研究生。1990年3月入伍。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解放军文艺》等发表中短篇小说三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小说集《玉龙湖》《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等。多部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入选多种小说年度选本;获多种军内外文学奖项;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协会员,辽宁文学院签约作家。
我是在地铁里发现忘记带手机的。地铁人多,我等了两趟,第三趟才挤上去。人贴人,身体歪斜,无法直立。我努力抽出手,去摸裤兜,探寻手机,这是我上地铁后的习惯动作。手在我身上摸,却遭到一个女人的白眼,她认为我在骚扰她。我委屈,但凡有一丝空隙,我不会触碰这个半老徐娘。我不理她,继续探寻,隔着一只别人的胳膊,我摸到了我自己。裤兜在,手机没了。冷汗从脊背渗出。我劝自己别着急,要冷静。我努力回想,手机应该没丢,它可能就在我宿舍卫生间的盥洗池上。我用吉列剃刀剃须时,喜欢听手机里的钢琴曲。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在京城某培训机构学习,时间半年,发结业证。我们住在此地,每天坐地铁到彼地上课。今天是专业课,从下午到晚上。我离不开手机。我在下一站下车,然后回返。
我进到我的宿舍,手机果然在。我拿起手机往外走。保洁员李大姐出现在楼道里,她说,今天怎么啦?半道回来好几个。我问谁回来了。他说,你们班长也回来了,还有那个漂亮的白雪歌。
李大姐,年近五十,外来的农民工。从她的脸上,能看见生活的沧桑,也能透过她生活的沧桑,窥见她昔日曾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女人。可惜男人在外当包工头,有钱了,就跟她离了。女儿上大学。她独自闯荡京城,挣养老钱。
班长名叫鲍春光,他和白雪歌是这个班上我最在意的两个人。鲍春光是我们中的精英,佼佼者,他专业方面的成就,令我仰视。
白雪歌是班花。
我想,他们也许是一起去上学了。我没理保洁大姐,继续前行。我从她身边走过时,她甩给我一个笑,那笑诡秘,像是向我暗示什么。我没理她。我不喜欢这种笑。她的声音追着我的背影而来:他还搂着她,我从窗户里看见的,他们往秀水湾去了。
秀水湾是一片河湾,属于古运河。河还是那条河,岸也是古时那条岸,物是人非。古人作古,今人在此游玩,寻乐,看风景。河岸柳树成荫,树林里有一个星级酒店,名为“风雅颂大酒店”。有一次,我们在秀水湾散步。鲍春光说他喜欢白雪歌。我说,你喜欢,你们去私会吧。白雪歌说,好呀,班长,我们去风雅颂吧。说着,脸竟然红了,羞涩地笑了。她不是一个泼辣的女孩,她很少开这样的玩笑。她常常是笑而不语。那天她的表情,表明她对班长是有感觉的,至少在意他。我且当作玩笑,一笑而过。现在看来,他们双双去了秀水湾,是要把这种玩笑变成现实。
班长鲍春光是我最好的哥们。如果男人也有闺蜜的话,他应该算得上我的闺蜜。白雪歌长得白净,瘦削,弱不禁风,有时,真不知道她怎么在这个行业里打拼。事实上,她的业绩一直很好,有人说,这得益于她林黛玉式的体态和美貌,她不乏客户关照。
在这个班,我单爱林黛玉式的白雪歌,是暗恋。
现在,我最在乎的两个人,成双入对地去了同一个地方,我的腿就迈不动了,似乎被人抽了筋。我一下子没了去上课的情绪。我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屁股跌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凝望着我的床。床上有两个人,一对男女,赤身裸体,仿佛我的床是一片海,他们像两条在浪花里翻腾的白条鱼。他们鏖战正酣。那个男人背对着我。他臀部肌肉绷紧,松开,再绷紧。那个女人的脸,从他左肩处露出来,朝向我。她处于那种迷离状态,醉眼朦胧,那眼里只有虛幻。她显然没看清我,因为她没有惊慌,没有叫喊,没有停止他们的翻腾,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向着他们预定的目标挺进。
那个男人就是鲍春光,她身下的那个女人是白雪歌。
我被眼前幻景击中,脑子近乎无意识状态。我扶着椅子,努力不让自己跌倒。我嘴张得大大的,惊骇使我发出惊叫,我只觉得有一把锋利的刀在我心口划过。我脑子里出现了流氓、无耻字眼,我知道,他们正在寻欢,这是一定的,只不过不是在我的床上,他们在风雅颂大酒店,那客床软如水浪。这种猜测那么真实,像刀一样让我疼痛。
我脑袋膨胀,似乎就要炸开,血液在体内飞速地奔涌。说不清是想象那对男女寻欢而产生的激情,还是怒火,我不知道。我感到我的整个身体,也像脑袋一样就要炸开。
我很小的时候没了母亲,父亲为了我们的生活,在外做工,是哥哥把我带大的。哥哥上学去了,就留下我一个人。我常常坐在门前的石凳上,看落日,等哥哥。那时候,我是多么孤单。我害怕孤单。记得有一次,哥哥他们的老师拖堂了,他回来时,天像墨水一样黑,我在阴郁的夜风里等哥哥,只有惧怕陪伴着我。那一次,我已不仅仅是孤单,而是孤独了。当哥哥的身影在黑暗里,像一截黑色木头移动时,我向他奔过去。我一直在眼里打转的眼泪,不可抑制地奔涌出来。我喊道,哥哥,我也要去上学。第二天,哥哥上学带上了我。有时他让我在教室外玩石子,有时他把我带进教室,让我悄悄地坐在他身边。
我依赖哥哥,这成为我生活中一个很深的印记。我脆弱、敏感,不喜欢孤单。我害怕孤单,我不知道是孤单对我的伤害太深,还是哥哥给我的爱太多,我无法摆脱。这使得我在特殊环境下,即便对身边比较熟的男性,也常常会滋生一种依赖,就像我小时候依赖哥哥。而这次,班长鲍春光,从培训班开学至今,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他其实比我小三岁,但他比我成熟,内心比我强大,办事滴水不漏。我们行业里的精英,偶尔会在经验交流会上遇见。我和鲍春光多年以前就认识。三年前,我们在北京某基地培训三月,那时候,我们每天午后沿人造湖散步,成为好友。这次相聚京城,多年的朋友成兄弟。
因为每天要坐地铁到异地上课,第一次课前,我对鲍春光说,我们一起去上课吧。他说,好呀,我们一起走。于是我们这对兄弟,除一起去上课,还常常在秀水湾散步。我们谈论专业,谈论我们爱看的书,也谈论我们的爱情。当然,我们谈论爱情时,不是谈论我俩,而是我们心中各自喜欢的女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白雪歌。我们谈论白雪歌时,毫不避讳我们内心的爱慕。
那是我们快乐的单身时光。
突然有一天,我们不谈论白雪歌了,白雪歌变成我俩心中五彩斑斓的肥皂泡,她时刻在我们眼前飘浮着,我们却都不敢伸手去触碰。
一个周末之夜,鲍春光请我喝酒。我问,就我俩?他点头。以往我们喝酒的时候,会多找几个人,尤其白雪歌,从未缺席。
那个酒馆幽静,舒适,有着浪漫的气息,适合情侣。我们两个男人坐在那里,有些不自在。要是换成鲍春光与白雪歌,或我与白雪歌,会更有情调。
我们不喝白酒。我自带了一瓶红酒。酒不但没使我们的情绪松懈下来,似乎更紧张了。鲍春光的语气是严肃的,他说,咱们这个班,快两个月了,故事慢慢多起来。你知道我说的故事是什么吧?都成对了。我说,嗯,我知道。他说,不羡慕他们。我说,不羡慕。他说,抛家舍业,对不住老婆孩子。他说到老婆孩子时,我突然想哭。我想家。
鲍春光打扮时髦,我以为他是个很前卫的人,原来他很传统。他说,就算不考虑对不对得起家人,如果故事结局不圆满,就是事故,是绵延不尽的烦恼。我们是知识分子,不说是尖端人才,也是人才。自毁前程,到时后悔都没得药吃。
我说是。我们碰杯。他接着说,我知道你喜欢白雪歌,我也喜欢,实话实说,白雪歌不是最漂亮的,但最有女人味。别看她温和,其实有着女人的野性,野玫瑰似的,充满着强烈的诱惑力,却也浑身是刺,碰不得的。
酒精使我亢奋,胆大。我说,我喜欢白雪歌。
我看見鲍春光的脸突然冷下来。我不知道他的脸为何突然冷了,或许是门口的风,因为这个时候,小酒馆进来一个人,门打开的那一刻,一股冷风扑来。
门关上之后,鲍春光的脸色转暖。他举起酒杯,说,来,兄弟,喝。我干了,你随意。
我没有随意,这不是我的风格,我也干了。两人喝得就都有些高。
鲍春光伸手抹了一把眼睛,好像有泪,其实没有。他说,忍忍吧,很多事,忍忍也就过去了。多少当官者,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他这话我明白,他是那么喜欢白雪歌,又是那么压抑自己。我感到,他是在劝说我的同时,劝说着他自己。
鲍春光说得有理,我虽不是官,但也是一个蓝领,参加这次集训后,回到原单位,或许能成为白领,这是多少员工望穿双眼的事啊。
我敬鲍春光,我说,兄弟,你说得对。我叫他兄弟,不叫班长。我说,可我的确喜欢白雪歌。鲍春光说,白雪歌不是你的菜,就算你费很大的劲,得到了,也是麻烦,无尽的烦恼。男人最重要的不是女人,是事业、前途、家庭。
我低头不语。
我说,你不是也喜欢她。他说,喜欢呀。他说,喜欢的东西多了,你都想得到?可能吗?埋在心里,默默地欣赏,不是很好么?半年时间,忍忍也就过去了,何况中间还有两个节日,可以回家的。
鲍春光的话有道理,我压抑着内心的爱恋。
昨天晚饭后,我们漫步秀水湾,鲍春光对我说,我俩的关系太近,我们没有必要总在一起。他这句话让我郁闷了一个晚上。我也没想清他所指,他是说我们不必一起去上课吗?他在原单位虽然是副职,是副处级领导。当领导的人,常常话不明说,让身边的人去悟。我没悟透。下午上课前,我决定自己走,我怕孤单,但我更珍惜尊严。
现在回想,昨天他跟我说我们没有必要总在一起,今天,他就这样带着白雪歌玩失踪,原来这是个阴谋。
我打开窗。我劝说自己:这只是我的猜想,是幻觉。也许他们到了培训班,正在上课呢。我往培训班赶。今天的我有些怪,平时他们俩要是离得近,我心里就不舒服,有一股细微的妒嫉之火,沿着幽暗的心壁往上爬,而此刻,我是多么希望他们成双成对坐在教室里。然而,没有。我通过教室后门的窗玻璃,看清了这一切。我们班的其他同学都在,没有他俩。
我逃离教室,在寂静的走廊里往外走。阳光从窗玻璃照进来,尘埃在光柱里翻舞,鲍春光与白雪歌这两只“白条鱼”在我的臆想里翻腾、翻腾。
我喜欢班长,视他为兄弟。我暗恋白雪歌。但现在,我的兄弟,正和我暗恋的女人,在风雅颂的床上,像两只白条鱼样翻腾。回想那个夜晚,鲍春光在小酒馆对我说的话,都是谎言。他欺骗了我。我全部的热情,我的喜欢和暗恋,此刻都转化成了恨,就像柔和的水,突然结了冰。
我走出校园,像一个丢了魂魄的夜游神,漫步在大街上。车来车往,川流不息,但街道看上去并不拥堵,街道上的天空空旷而纯净。我看见白亮的太阳开始西移,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就在人行道上,向着太阳的方向行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不累,也不渴,只是有些困,很想找个地方睡一觉。我像是梦游。
我看到很大的一个河坝,河里有水,河边树木林立。天很蓝,水流清澈。沿河坝走了百十步,进入到河坝公园。公园里,有宽一些的水泥环道,有林间小路。我不喜欢热闹,选择林间小路,这里幽静。小路在浓密的树林里向前延伸,伸向一个土坡。那个土坡上有一个突起的土堆,像我遥远乡村里的一座坟茔静卧在那里。我突然有一丝恐惧。一个女子从林子里钻出,惊吓了我,她让我想起《聊斋》。我正要退身而回,她冲我嫣然一笑,那笑很美,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我就走不动了。我无法抗拒。惊骇和惧怕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因为我并不相信世间有什么狐狸精。此刻,在我看来很美的这个年轻女子,或者说独身妇人,也许也是因为郁闷,被人抛弃,或像我一样,被人欺骗,误撞到这儿来;或者她是要用这种寂寞的散步,冲淡她失落的情绪,如我。我这么胡乱猜测着,便有一种与她搭讪的欲望。我向她问了一声好,她回我一声你好。话就接上了。我们像一对老熟人。路旁有石头,那看似天然的石头,像是随意地生长在林子里,其实是故意摆放在那里的雕琢之物。那天不是太冷,暖阳高照,我们就坐在石头上。穿透枝叶的阳光,像银元落在我们身上。我觉得可笑,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打招呼,就坐在那里,像一对恋人。但我没把我的笑表露出来。她倒大方,比我放得开。我们问对方做什么工作,不是试探,而是出于礼貌,无话找话。我感觉到她没跟我话实话,我也就没把我的职业告诉她。我说,我是个诗人,但不以写诗为生,我做生意,与文化有关,体制外。她显然也感觉到我没同她说实话,没再问,装作信任我。她扯着嘴角一笑,那笑有点冷,事实上,很妩媚。她说,咱们到“林中咖啡屋”喝杯咖啡吧,我请你。
我跟着她,沿着林中小路往前走,路旁树木高大,枝叶更繁密,我觉得我们正在走向一片原始森林。密林深处,果然就见一间小木屋,屋里典雅别致。我们靠窗,相对而坐。我平时喝茶,很少喝咖啡。咖啡让我很兴奋,像喝了酒似的,眼神迷离。她说,我们可以喝点酒。我说,好吧。因为咖啡和这个女人,并没让我忘却鲍春光和白雪歌,幻觉里的两只“白条鱼”依然在我脑子里翻腾。此刻,我需要酒。也许只有酒,才能平复我心。
我跟着她走。我们穿过咖啡厅的后长廊,进到另一间小木屋。小木屋里有一只木板梯。我跟着她下了木板梯,是地下室,像军营里的防空洞,入口小,里面的空间突然变大。灯光炫目,以粉红为主色调。诱惑人的灯光,压抑的气氛,带给我陌生、不安,并且因了这陌生和不安,滋生出亢奋。有一个穿着超短裙的女人,在台上跳钢管舞。那钢管舞不是我在电视里看的那么火爆,她跳得很轻,很柔,很优雅。她的腰身轻轻扯动她的短裙,她臂部的纹身便若隐若现。那是一朵鲜红的牡丹,裙裾拽起,落下,那牡丹花就如同瞬间绽放,凋谢。她越发勾人。她不像别的舞者那么浓妆艳抹。她甚至连口红都没打。她的美击中了我。那是一种既能迷倒男人,也能迷倒女人的美,因为我看见带我进来的这个女人,眼光落在她的身上时,怔在那里,居然忘记招呼我。
女人回过神,我们落座。我要了一瓶啤酒。我不是酒吧的常客,对啤酒品牌不太了解,对那繁杂冗长的英文字母不感兴趣,依價格而已。她给自己点了一杯鸡尾酒。灯光和鸡尾酒映衬,光的阴影残酷地剥离了她化妆品装扮的美,加深了她脸上的褶痕,这显然不是我所希望的陪酒女。这时,一位戴着黑色文胸,穿着肉色连袜裤,看起来像没穿裤子的年轻女孩来到我身边。她声如燕语,说,哥,我是北影(北京电影学院)的,没课时出来兼职,挣点学费,要不要陪你喝一杯。我说可以。我想用她挤走眼前这个女人,但我瞬间退缩了。我不常泡酒吧,每年要去几次的。这些陪酒女特别能喝,点的酒还贵,她所有的酒水,都得她陪的这个男人给她买单,一个时辰,没两千块下不来。我不想就这么花掉两千块。
我随即改口说我不用她陪。女孩说,不喝酒也行,哥也可以把我带出去,去你的地,或我的公寓,明早散,两千块。我说,我没这个意思。
我今夜失落,也可能会堕落,但还没堕落到要带一个女孩出去过夜的程度。
女孩不走,眼前这个女人看出了我的尴尬,右手一扬,说,不用了,今天我陪哥。那个女孩低首含笑,说,好的姐。
她们好像很熟。她像是这里的常客。
女孩走了,她的背影让我想起她刚才所言“北影”,我当然知道那是她给自己贴上去的一个虚假标签。
我们坐着听音乐,看钢管舞表演。那个优雅的舞者下去了,换上一位外国女人。我对面的女人介绍说,她来自乌克兰。她黑眼圈,长睫毛,身上银光闪闪,像鱼的鳞片。我不喜欢这类女人,她与我脑子里偶尔闪现的妖精形象无异。
我干了我那杯啤酒,准备离开,带我来的那个女人又给我要了一瓶。她说,今天不是我陪你,是你陪我,我消费。
我一个男人,怎么能要女人消费?
她把一千块钱递给服务生,说,先拿着,一会儿算。
我说,你也不像富婆。她说,你也不是“小鲜肉”呀。我们相视一笑,似乎一下子就亲近了。这是幽默的力量,也是酒的力量。
坐了一会,钢管舞者下去了,换上乐队演奏。她说,上包间吧。她指了指我们身后。我才知道,我们身后有很多包间。那包间的帘子拉得严实,我以为是装饰,服务员拉帘进去送餐时,我才看见里面坐着男女。
里面很安全。她说。她说到安全,我就知道里面不干净,或许可以行苟且之事。可眼前这个女人,不是我要与之苟且的那种。只因为她买单,吃人嘴软,我顺从了她。我们进到角落里的那个包房,离小舞台远,不过这不重要,那个优雅的钢管舞者,已经表演过了。
我们闲聊。她谈她的生意,我谈我的文化产业,依然在编造着谎言,彼此心知肚明,不揭穿,要不谈什么呀。我不胜酒力,五瓶之后,已是醉醺醺的。幸存的那点意识告诉我,不能再喝了,但当她再递过来一瓶时,我却对自己说,喝,干嘛不喝,不就是买醉来了么?
女人先是坐在我对面,现在,她坐到我身边来。包房的门帘像一道轻纱,两块厚布,女人把它们都拉上了,包房便成了一个独立隐秘的空间。除了桌上那只散发着粉红微光的电蜡烛,再无光亮。包间里的氛围的确适合男女相会。她坐到我身边来,但并没搂抱我。她是女性,要矜持。出于礼貌,我搂抱了她。当她把嘴唇送过来时,我没有拒绝。我迎了上去,吻了她。不是轻描淡写地吻,是舌吻,但这并未诱发我的激情。我说过,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途中,她曾把她的手伸进我的下腹,我用我的手捉住了它,我有我的底线。我不想与一个刚认识的、没有一点情感的女人,在肉体上欢娱,我觉得那样没意思。我曾一度把她想象成白雪歌,但她不是,差别挺大的,我没能够完成我的想象。
我只是亲吻她,逢场作戏。之后,我去了趟卫生间,回来我就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女人还守在我身边。我看了看表,已经午夜11点。我喟叹酒吧的时间真好打发,再愁苦的一天,在这儿瞬间就过去了,难怪那么多人愿意泡在酒吧。
她依偎在我身旁。我以为她早就走了。
结了账,她递给我五百块钱。我不要。她说,买单剩下的钱,我点的啤酒并不贵。我说,我不能要你的钱,你这是侮辱我。她说,别这么说,这是你应该得到的,看来你今天不开心,跟谁过不去,也别跟钱过不去呀。
我就收下了。钱在我口袋里,像一只刺猬,让我不适。
还剩一瓶啤酒没开,可以退的,但我没让退。那天的我,就是有些怪。我想带走那瓶啤酒,服务生竟然同意了。
我把那瓶啤酒装进双肩包。
我们出了酒吧,穿过长廊,走过咖啡馆。林子里的路灯灭了,地灯还亮着,光打在小路两旁的树枝上,青翠欲滴。酒真是个好东西啊,我现在除了疲惫,困倦,不再那么焦虑了。
出了公园门,我们各奔东西。好奇心驱使,我冲她背影问,你叫什么?她无声。我说,加个微信吧。她说,不用吧。她淡然一笑,没有笑声,月光下,她洁白的牙告诉我她笑了。她说,以后在林中小路上,你或许还能碰到我。如果碰见了,别装作不认识,咱们进去喝一杯。
她的话像一团夜雾笼罩着我。
我现在回想买醉的时刻,回想那个吻,差点呕吐。幸亏只是个吻。
路旁的灯光朦胧,我一直像在梦里。我“滴滴”了一辆车,它把我送到住所。我行走在院子里,夜风让我清醒许多。夜风抚慰着忧伤的我。夜风使忧伤中的我更加忧伤,它让我想起鲍春光和白雪歌。我已经不仅仅是忧伤了,无比的失落带着伤痛袭来,还有懊悔。我们住在栖园。栖园的一切才是美好的,真实的,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活。我不应该去公园,更不应该去酒吧,不应该跟她接吻。
没有什么能让我的心平息下来,没有什么能浇灭我内心的嫉妒之火,酒没能够,那个吻,更没能够。
栖园里有了微弱的光亮。那是月亮钻出了云层,给门前的银杏披上一层银灰色的光。那是栖园最大的两棵银杏树,修长秀美,静立在我们窗外两三丈远的地方,像一对情侣。我曾暗中把它们比作白雪歌和我,现在看来,它们更像鲍春光和白雪歌。栖园的那边,是一条河。河水流淌,发出轻微的幽咽。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
我上楼。我没乘电梯,那种温和而悠长的“叮咚”,会惊醒梦中人。我走步行楼梯。我的脚步迈得很轻,像我少年时学走太空步。
无数条微信发过来,铃声像屋檐下的水滴,清脆悦耳,不紧不慢。经夜风的吹拂,我的头脑略微清醒。我意识到我外出匆忙,忘记打开移动网络,微信处于死亡状态,回来之后,WLAN自动连接,信息排着队跳出来。
是鲍春光的:
你在哪儿,到处找你。白雪歌病了,高烧。同學们都在这儿呢。秀水湾东面的仁和医院;
下午准备上课前,她给我发了微信,说她身体不舒服,我过去一看,她发着高烧。把我吓坏了,我就扶着她直接来了医院;
晚上下课后,同学们都来了。你没来,我也给你发了微信,以为你看到了;
听他们说你也没去上课;
行了,太晚了,你别过来了。我们留下两个人陪她,输完液就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吧;
对了,把电话号码发过来,我们总用微信交流,居然没有你新的电话;
…………
我在夜的微光中冲出住所,冲向秀水湾,冲过风雅颂大酒店。我看到黑暗中那红色的“仁和”二字。我冲进大门,我冲进急诊室。
白雪歌半卧在病床上,手上挂着吊瓶。她旁边,围坐着我的同学们。鲍春光见我来了,站起身,迎过来。他一脸惊喜,问我,你到哪里去了,也不回个信。
鲍春光的表情,和他急促焦急的语调,让白雪歌笑了。她说,班长对你是真好啊,简直掺杂了爱的成分。他虽然在这里照顾我,却一直担心你。她努力地挤出笑。笑得无力,憔悴,却真诚,令人动容。
我说,他对你才是真好。
我又说,这个时候你还开玩笑。
她说,不笑,难道哭不成。她说着,一阵咳嗽。
鲍春光急忙给她拿水。之后,他推了一下我的肩,我跟着他走出病房,来到走廊里。他问我,同学们说你也没去上课,你到底上哪儿了?没出什么事吧?
我说我来了个朋友,在外面吃了个饭。我极力掩饰自己,但我冰冷而颤抖的语调,将我内心的担忧、懊悔,甚至后怕,暴露无遗。
你不会撒谎,他淡然一笑说。
我说,是的,我不会撒谎。我还是实话实说吧。保洁大姐说,你搂着白雪歌出去了,向着秀水湾来了,我以为你和白雪歌去了“风雅颂”……他打断了我的话,他显然知道我想说什么。他说,你怎么这么想?他在我的肩上重重地擂了一拳,说,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谈情说爱的。我不让你做的事,我也不会去做,更不会瞒着你去做。我们是兄弟。
他说着,攥着我的手,攥得紧紧的。他说,别想太多,我们都好好学习,拿个结业证,运气好的话,回去能换个好工作。
我们回到白雪歌身边。我将背轻轻靠在椅子上,仰望星空。我没看到星空,白炽灯像太阳一样悬挂于头顶。
屋子里闷热。靠近鲍春光的窗台上有几瓶饮料,他递给我一瓶。他说,你累了,喝点。我摆手。我说,我有,我有的。
我拿出双肩包里的啤酒,找到两只一次性纸杯。我咬掉瓶盖,倒了两杯啤酒,一杯递给鲍春光,一杯留给我自己。孤独像一杯啤酒,我一饮而尽。我眼角有了泪。也许它不是眼泪,是我喝得太急,啤酒直接从眼角涌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