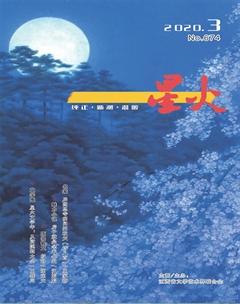“只有一棵苍黑的树上还挂着几个鲜红的柿子”
陈离
第一次读王家新的诗是什么时候,已经记不清了—那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也许是三十年前,或者是更久远的某个时间。那时候我还是个文学青年,还没有开始学习写诗,甚至也不知道诗歌是什么,但却喜欢阅读诗歌,喜欢阅读诗歌所带来的有时沉醉有时迷茫、有时欢喜有时痛苦、有时悲哀有时激越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学体验。后来我在大学讲台上和年轻的朋友讲授中国新诗,因为教学工作的需要,我读过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也可说不计其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选择王家新作为我重点关注的中国诗人之一,试图通过他的诗歌,他的诗学随笔,以及他的诗歌翻译,观察中国新诗的发展态势,也作为观察“时代的精神状况”的一个窗口,其中的原因,也实在一时难以厘清。我常常被所读到的他的诗歌“击中”,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他的文字有一种迷人的气息,让人沉陷其中难以自拔,也是一个原因。我想最为重要的,还是他的诗歌的“高度及物”吧—我从他的诗歌里能够读到来自心灵世界的信息,那些发生在人的灵魂深处的重大心灵情节,那些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的世界上的重要事件,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密切联接,都会在他的诗歌里以某种方式得到体现。总而言之,我从一位诗人写下的文字里读到了他的“体验”“承受”(可能是无比痛苦的)和“担当”(可能是十分艰难的)—我理解的大诗人,应该也必然具有这样的品质。
见到诗人本人,却是很晚的事。那是去年的暮春或者初夏,他应邀来我任教的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我和几位在读的研究生一起去机场接他。这是与诗人的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最初印象”很重要。我后来不时地回到那个时间节点:2019年6月的某一天的下午,我和几位年轻的朋友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诗人。我的“最初印象”是:这是一个朴素的人!是的,“朴素”,这就是我见到他时想到的第一个词。他看上去是太朴素了,也许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加朴素。他的衣着打扮,他的言行举止,他的随身携带的小小的行李箱,他的带着浓重的鄂西北口音的普通话,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朴素—它们根本不符合我对一位大诗人的想象吗?或者正符合我对一个大诗人的想象……我们见了面,打了招呼,走出机场大厅,他对我和一起来接他的研究生说:“你们等我一下,我要抽支烟……”
他抽的烟,他抽烟的动作,也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站在他身边等他,不知道当时在场的几位研究生同学是怎样想的,我在他的朴素之外,还从他站在飞机场大楼边上抽烟的形象里,读到了“忧郁”和“沉思”。我们见到的,是一位朴素的、总是在“忧郁”地“沉思”的诗人—我这样说,真是毫无新意可言,难道不是所有可以真正称得上是诗人的人,都应该这样吗?我们期待着见到能真正称得上是诗人的人,但现实却总是让我们失望,尤其是让正在读诗和正在写诗的青年失望。我们面前的这位诗人,因为其超出想象的“朴素”,却一下子让我们感到无比亲近,仿佛一下子可以毫无阻碍和毫无距离地交流起来。我知道同行的几位青年,心里都有许多话,要和仰慕已久的诗人倾诉。我知道他们都读过他的许多诗,也许是他已经发表的所有的诗,以及他所有的诗学随笔(《人与世界的相遇》《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这样的书名,多么亲切,又多么具有一种引领的力量),以及他所有的诗歌翻译(他翻译的策兰、阿赫玛托娃,以及曼德尔施塔姆)。
因为写下了所有这一切,他才成为一个诗人,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必须首先是一个诗人,他才能够写出他写下的所有的诗—到底是先有诗人,还是先有诗,这是一个难题,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是我们在讨论一个诗人的时候,不讨论他的诗是不可能的。何况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诗人”,而是几乎将一生所有的时间都贡献给了诗,一生都在为诗歌工作。他为中国新诗贡献了不少名作,《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塔可夫斯基的树》《回答》,等等—那确实是名作,对中国新诗稍有研究的人,都不可能不知晓。一个以诗歌为一生的志业的人,一辈子能写出一首这样的诗就足够了,而他却写出了那么多好诗,影响了那么多人,而且在我看来,一定会传之久远。
在一篇短文里,要讨论太多他的诗作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应该暂且把那几首最有名的诗先放到一边,它们太有名了,已经被谈论得太多,无论诗人自己的意愿如何,它们确乎已经进入了文学史(我们知道诗人自己很讨厌“进入文学史”这样的说法)。我们还是看看诗人最新的作品,《后园恩寺胡同的秋天》(诗八首)。
你喜欢这样的诗吗?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诗,你的“最初印象”是什么?我的回答依然是“朴素”,甚至有些“平常”,一点也不晦涩,更谈不上“先锋”,是吗?—但就是这样“朴素”而又“平常”的诗,如果用心去读,它们却会用一种特别强劲的力量,深深地击中你。你甚至觉察不出自己什么时候被击中,什么地方被击中,为什么被击中。它们让你百感交集,然后引领你思考,这一切的一切,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他叙述的调子有些低沉,他所有的沉思,都用一种缓慢而从容的声音表达出来。这是来自生活的诗,这里有一个人在生活中的百感交集。但是它们又仿佛来自生活之外,来自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仿佛我们在尘世之内,听到了一种来自天外的声音。就像我和诗人短暂的接触所得到的印象,他就在你身边,是一个朴素的人,那么亲切那么平常,但是突然地,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也许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时候,他又进入了一个没有人知道,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他的诗歌的“秘密”吗?这是所有伟大的诗歌的秘密吗?
这是诗人王家新的《诗八首》。除了题目,诗的内容和风格,也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穆旦—是的,是诗人穆旦的晚年,是诗人穆旦在晚年写下的那些中国新诗史上不朽的杰作。但是和穆旦那首著名的以深刻地思考与表达青春和爱情的《诗八首》不同,王家新的这组诗写得最多的季节是秋天和冬天,这是典型的“晚期风格”。有人不喜欢这样的诗吗?也许。因为这样的诗太沉重了,诗艺上没有表现出多少“探索性”,有些“简单”和“直接”(真是这样吗?),其中有一種“姿态”,多少有些说教的意味;而且,你看,诗人有点不知道节制,他的诗里出现了太多的“我”,太多地写到了疼痛,他甚至写到了“有点让人想哭”(《在冬日的颐和园》)……不喜欢他的诗的人当然可以说出自己不喜欢的理由,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却被这样的诗强烈地吸引。在我看来,它们是这样的诗:初读仿佛很容易被忽略过去,因为其“朴素”和“平常”(或者换一个词,沈从文先生喜欢用的“家常”),但诗中总有一种东西吸引你,逼迫你停下匆促而纷乱的思绪,去仔细感受、体会和思索诗人用这样分行的文字所表达出的一切。时代的风云变幻,无常的世事,不测的“命运”,难解的生命之谜,必然会引起一个置身其中的诗人内心的波澜起伏。他从日常生活和普通的事物上面,看到了“时间”,看到了“时间”所带走和留下的,看到了那些我们也曾看到,以及那些我们不曾看到的一切;听到了那些我们也曾听见,以及那些我们不曾听见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诗。
我们很容易从这样的诗里读出诗人的不安和无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一个诗人面对世界和时代的诚实的表达。在我看来,他的诗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是因为他的不安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不安,他的无力,正是我们内心深处时时感受到的无力。当然还有我们常常隐而不宣的忧伤,迷茫,痛苦,以及愤怒,更多的人将这些深藏于内心,诗人却呈现出来,而且是诗艺的表达,看上去不动声色,隐忍和克制处处可见,却在不经意的时候引起我们内心深处剧烈的电闪雷鸣。
于是我们总是在他的诗里看见一只鸟在飞,一只燕子,一只喜鹊,一只斑鸠,一只布谷,一只鸽子,一只夜莺……或者一只我们根本叫不出名字的鸟,从我们的童年飞来,飞过我们的窗口,然后在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之后,在夜晚的天空发出一声令人心惊的啼鸣。我们听见了,但是我们装着没有听见,仿佛这样就可以对我们心中的不安视而不见。但是诗人总是不停地提醒我们那只鸟的存在,而且希望它“飞得更低一些”,当整个世界都在“朝深渊里坠”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
在这一组诗里,诗人写得更多的还不是鸟,而是树。在这八首短诗里,有好几首诗中都出现了树的形象。各种各样的树,银杏树,白蜡树,黄栌树,梧桐树,松树,柳树,一棵不知名的老树……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棵柿子树(这一次,它没有生长在海边,而是生长在山上),在秋天快要过去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在“路边灌木丛中的小浆果早已熄灭”,在“脚下的落叶,一片焦枯……”之时,只有那棵躯干“苍黑”的老柿子树上,还挂着几个“鲜红的柿子”,突然出现在行路的人面前(《秋末》)—我们会被这样的诗击中么?也许一些特别追求诗的“技艺”的人,会以为这样的诗有点过于“直白”了?至少我不这样看。我喜欢这样无比朴素而又无比深沉的诗。在经历过无数次的风吹雨打之后,在一再地感受到“无人能够继承卡夫卡的痛苦”(这无疑是一种“更深的痛苦”)(《重读<卡夫卡传>》)之后,一棵老树依然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出对于“生命的感谢”(《三月之诗—给陈育虹》),面对这样的一棵“生命之树”,我们能不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引领的力量么?
据说诗坛是个是非之地。我虽然不是诗人,也对发生在诗坛上的诸多争议略知一二。诗人也会受到这些争议的困扰么?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关于“先锋”“学院”与“口语”,关于“中国气派”与“伪奥登风”。但是在我看来,可能许多这一类的“问题”本来都不是问题,或者说是假问题—关键是,你必须写出令人信服的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诗(而不是小圈子里的自我欣赏和相互吹捧)。事情仿佛是这样:曾经指向穆旦的批评也指向了王家新。有人批评他的写作是“面向西方”,他的诗表达的是“二手经验”,诸如此类。我不知道这种批评的根据是什么。以我对他的诗歌的长期阅读,和与诗人为期不长的近距离接触,在我看来,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诗人写下的所有的诗,其“本色”和“底色”,都是非常“中国”的。他朴素的衣着,终生难改的楚地口音,略有些黝黑的肤色,风尘仆仆的面容,以及总是带着一丝拂之难去的愁思的神情,都让人感觉到他曾经是也一直是那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并对脚下的土地魂牵梦萦念念难忘的中国孩子。他在诗歌中流下的所有泪水,都与那片土地息息相关,尽管他在诗里一再地写到哈姆雷特,卡夫卡,里尔克,策兰,尽管此刻他可能正走在巴黎或倫敦的街头。也许正是这样,他才能够写出那么多“又热烈又恬静,又朴素又深刻,又温柔又骄傲,又微妙又率直”的读来让人百感交集的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