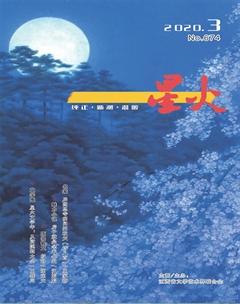房间里的森林
杨小卫,武汉人。曾当过小职员、图书馆管理员,现为自由职业者。有小说发表于《山花》《湖南文学》《野草》《广西文学》等刊。
一
语言是奇妙的玩意,无论怎么搭配似乎都能自圆其说,不过—房间里的……森林?这到底是什么鬼?
要我说,这不是什么鬼,这或许恰恰就是真相。
每当外出关上房门时,随着门锁“嗒”的一响,身后的空房间似也“呵”地发出一声叹息。起初我并不清楚那是什么。
那天回家时,我发现桌上有只蟑螂,它察觉到动静马上警惕地瞪着我,触须警告般地摆动着,仿佛它是这里的主人而我是入侵者。我们对峙了三四秒,当我抄起一个酒瓶扑过去时它迅速地溜了。房间里有蟑螂并不奇怪,让我惊讶的是它主人般的架势。或许它一整天都在这儿,也或许它好多天都在这儿,那么在它眼里这房间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无法从蟑螂的角度去看问题,但我想它不会认为这是个房间。
另有一次,在厨房的水池下发生了一场搏斗:一只苍蝇陷在蛛网里,苍蝇激烈地挣扎而蜘蛛沉稳地一点点困死对手。最后我用鞋底帮它们解决了问题。哦,即便在市中心四十层的高楼上,也会上演原始森林里的一幕,我当时想。房间与森林,这隐隐的联系其实并非首次出现,但它究竟起于何时我却早已经忘记。
还有一次,我回家时发现金鱼从鱼缸里蹦到了地板上—我实在不明白它是如何蹦出来的。金鱼在地板上游动,碰到落地柜时轻巧地拐弯并轻轻跃起,地板是干的表明它离开水已有段时间,但它的姿态看起来是欢快的。当我把它放回鱼缸后它却很快就翻了肚子。它在地板上到底待了多久?如果不回到鱼缸它是否更快乐?在它眼里这房间究竟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也无法从金鱼的角度去打量这世界。
我想到了森林,那闷热,那森森的树木与棕色的缓慢流动的水。也许金鱼更了解这房间的真相?
外出关上房门时,身后的空房间依旧轻轻发出叹息声。它在伸展,这毫无疑问。
然而这终究是可笑的—这只是个睡觉的地方而已,不管它是房间还是森林都无关紧要,所谓真相其实也毫无用处。
我也从不觉得自己是在森林里睡觉,除了偶尔的几个片刻之外。
二
我的工作是電影院引座员。我一个人住。我每天下午两点离家凌晨两点回家。
在影院里,我时常打量那些观众,我发现当影片无聊时他们的反应最有意思:这时很少有人会抽身离去,相反为了对得起自己的钱,他们会抓住一切机会大笑大叫以给自己找些乐子。这当然有些可笑,但如果我是观众是否也会和他们一样呢?我这么琢磨时总是摇摇头。
我对看电影也颇有些腻烦。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让自己被虚幻的影像弄得或哭或笑,这事想来终究有些奇怪。有次我对老余这么说了,他却只是一笑。
凌晨的街道像沙漠而白天它像河流。我从不抬头看月亮因为我知道它就是那样。无论什么季节我在空气中只嗅到干燥,道路上布满了乱影宛如一张大网,我甚至也无法想象旁边静静的房子里住着人—关于凌晨的街道我只能说这么多因为我对它并不熟悉,有时走在另一条路上我也察觉不出它与原来的路有什么区别。
凌晨两点其实还很热闹,路上有行人和车,有岛屿般的夜间营业的超市—它的灯光不像火而像一块冰。我脚步匆匆,从那些声音那些光里仍然只嗅到干燥。
有一次我进入夜间的超市,它的空旷与洁净出乎我的意料,与白天相比,那些货品仿佛有了特殊的光亮。我不由得放轻了脚步,仿佛走在中世纪的宫殿里。
这里有着一种薄薄的湿润的气息。我在货架前尽量拖延着不忍离去,结果除了方便面外,我又买了饼干、咖啡、口香糖及一包茶叶。
然而当我白天再来这里时,它却普普通通与所谓的宫殿没有半点相似—
夜里的房间是另一个房间,这似乎理所当然。
我和老余是中学同学,如今他在电影院旁边经营一家冷饮店,每天下班后我都去他那儿喝杯冷饮或只要杯冰水。晚上没有多少顾客,我们时常默然相坐看着窗外,并非找不到话题而是这样更舒服。
我们都爱看中央七套的农业节目。老余常说他要办个养殖场,去山里过喝泉水吃土灶饭呼吸新鲜空气的日子。我觉得他只是说说而已—老挂在嘴上的理想大多也就终结在嘴上了。而且这理想也明显不靠谱—若真有那么一个“山里”恐怕早就成了旅游地,不会让他办什么养殖场。
我们总在夜里一点半分手,然后他往东我往西。我们从来没谈过对半夜街道的感受。老余其实是个充满斗志的人,他需要的是钱、成功以及更多的女人,他可不会理会什么“凌晨两点的沙漠”。
三
我熟悉凌晨两到三点的所有电视节目。这正是欧洲联赛的黄金时间,那些豪门对决我几乎从不错过。我时常在沙发上悄然睡去又被一阵阵欢呼声惊醒,如此反复直到天明。
夜里的房间才是我的房间。当我打开灯时它呈现出熟悉的味道,有时从这味道中我能嗅到白天的痕迹。白天的空房间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呢?从那一丝残留的味道里我无法找到明确的线索。有人说房子如长年不住人便会自行垮掉,我深深地相信这一点—是的,空寂的房间会一点点生长,直到砖块水泥再也束缚不住它。
我已很少再想到森林,相反我变得有些小心翼翼,每次外出锁好门后,我总觉得不放心,于是又打开门再进去看看,有时甚至反复数次。房间里并没有值钱的东西,我不知道自己何以变得如此。
我也很少再听到背后房间的叹息,我想这应是听力出了问题。有一次回家后我没开灯,在黑暗中我准确地陷落在沙发上。房间里十分寂静仍保留着白天的味道,我回想着那声叹息而它果真就隐隐响了起来。这时我突然变得有些慌乱,然后猛地一下跳起来打开了灯。时至今日我也无法解释当时的举动。
电影院位于城市的最繁华处。我曾用老地图、老照片来比对以确定它的前身—那应该是一家国营的酒楼。而更早的资料表明一百多年前这里曾是红灯区,路面以青石铺就,两旁满是精致的木质小楼。而再往前追溯便已无人知晓。
追根溯源对城市人来说总是困难的。
据说乡人更了解事物的本源和真相,他们种下树苗,看着它们长大,然后砍倒树木来做家具,以后每当看到桌子或柜子他们就会想起当初的树苗如何长成大树—对事物的每一个环节都如此清楚,他们于是更接近真相,他们的内心于是也更安定。
然而我怀疑,真相真来自于对每一个环节的了解?或许真相并不依附于事物本身?或许真相只来自于片时的闪念,如空房间的叹息令人突然想起森林?
有时我想象自己来到乡间,栽下树苗然后看着树苗长大,然后将它们砍倒做成家具。这一过程或许至少需要十年。十年的乡间生活将会令我的内心变得更加安定?或许将是更加的疑虑?
我没有答案。
四
此时我独自生活已经超过一年,这让老余十分操心,“你不能再这样了,你必须得找个女人,要不我看不下去。”他说。
于是一个女人便出现在我生活中。我们在一场麻将中相识,她坐在下家我坐在上家。这牌局是安排好的,但我并不在乎—女人是如何认识的并不重要,关键是得让人知道你有女人。是的,我想事情就是如此。
牌局散后我送她回家。这是个小个子女人,圆脸配黄短发,一路上她毫不拘束地叽叽喳喳,竭力显得如少女般活泼。送到时她母亲候在阳台上偷偷地打量我,据说对我的评价是:“嗯,还行,个子不矮。”
后来我对小个子女友说这不公平,“哪有这样的,要看的话就面对面看呵。”“好了,以后会让你们面对面的。”她说。
小个子女友令房间热闹起来,它不再是森林也不再叹息。也不再有深幽复杂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争抢卫生间的忙乱、衣裤鞋袜的乱放以及热播剧令人难耐的对白,房间也因此有了另一种味道,如同尿撒在沙漠上。房间究竟是喜欢一个住客还是两个住客呢?出于直觉,我觉得它是喜欢一个住客的。
晚上回来时我突然变得有些不适应,房间里有另一个人它似乎就萎缩了,仿佛需要腾出另外的空间。女友正在熟睡,我必须轻手轻脚。我不再有收看欧洲联赛的心情也不再吃零食,却反而习惯于坐在黑暗中抽支烟。烟头一闪一闪如同某种信号。我抚摸着墙壁突然感觉到与房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房间里有另一个人才令我发觉这一点。
有次做爱时我告诉女友:“这房间里有树叶的味道。”她却只是喉嚨里咕噜了几声,也不知听清没有。
女友爱看金鱼吃食的场面,时常看得兴致盎然。“真有意思,”有一次她说,“我家原来也有金鱼,我一点都不爱看,可不知怎么就爱看你这儿的金鱼。”我对此只能撇撇嘴。
那天她投食过多把两条金鱼给胀死了。我正心情烦闷,于是和她大吵一架,然后就分了手。房间也即刻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
五
我又开始自己做饭。我拿手的是番茄炒蛋、焖土豆和炒青菜。我不吃肉,这并非因为有什么禁忌而只是怕麻烦。
焖土豆的过程总有国画般的清素之意,与之相比番茄炒蛋与炒青菜都稍嫌混浊:土豆削皮切成小块再滤一遍水,油烧至七分热下锅翻炒,随即加水放适量的盐,待熟后加少量醋及葱花便即起锅。这样的一盘焖土豆我有时可以白口吃完。有时我想做些改进,比如加些酱油味精之类,但那味道却总不如原来的好。
在某次聚会上,我自告奋勇做了盘焖土豆。那是在一幢新房子里,厨房里的一切都闪闪发光散发着新鲜的味道,窗外阳光下的花园看起来也非常新鲜。我心情愉快动作迅捷。几乎是下意识地,在起锅前我少许加了一点酱油、味精与蒜泥,结果这盘菜大获成功,连我自己也觉得比平时的土豆好吃得多。
然而在家里,当我如法炮制时它却并不那么好吃。或许在这个房间里,焖土豆只能加一点盐及一点醋。
我仍然下午两点离家,凌晨两点回家。晚上睡不着时我忽然开始写小说。我写得很慢,仿佛那些句子需要用力地拽出来。短短几千字的小说我用了二十天才写完。
打印出来后我去邮局寄稿。邮局的门面早已出租,邮寄业务改在了背街的小房间里。
柜台里光线很暗且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我注意到她仔细看了投寄地址并抬头看了看我,看得出来她很想找人说说话但结果却是更加沉默。“六块二毛。”在信件称重后她终于说出四个字。
这个下午我大概是她唯一的顾客。
那之后我时常想起那黑洞洞的房间,我想它的味道以及女工作人员的沉默已附着在了信件上—此刻它们或许正握在一位编辑的手中,而那些文字也将因此呈现出另一番意味。
我对此深信不疑。
六
老余突然结婚了。
婚后老余去了外地,那冷饮店他转手给了一位亲戚打理。每天下班后我仍然去那儿喝杯饮料或冰水。
我仍然每星期去一次超市。几乎所有的超市小票我都保留着,它们总会让我想起一些被时间掩盖的细节。有时它们也令我很苦恼,比如某次我发现自己竟然买过儿童面霜和纸尿裤,我想破脑袋也想不起买它们的理由,最后只得把那小票撕了。
久而久之这些小票四处散落,桌上柜子里抽屉里购物袋里全都是。在某些夜晚我依靠阅读这些小票才能入睡。相比于虚构的小说,这些小票似乎更虚幻也更适于睡前阅读。
有时醒来,我发现手中的小票长出了细密的黄色绒毛,而且湿淋淋的几可拧出水来。我把它们摊平,轻轻地刮掉绒毛,然后用夹子挂在阳台上晾干,有时竟会晾上一整排。对面的邻居肯定会疑惑这究竟是什么新奇的玩意。
七
有些观众很容易让人记住,比如特别闹的特别漂亮的或特别孤独的。
那个女孩第一次来时我就记住了她,因为她是独自一人。在黑暗中看不清脸,只看清她穿的是一件暗红格子短大衣。
第二次来时她仍是独自一人也仍穿着这件衣服。那是午夜场,有近一半的座位空着。我在她旁边坐下时她并没什么表示。那是部喜剧片,但她始终都没有笑。结束后,她默默地离去似乎根本没留意到我。
然而后来相遇时,她却忽然对我一笑。那是在渡轮上。我问她怎么认出我的,她说是因为你的声音还有那种……味道。我问什么味道,她仰头想想说:“有点像……唉我形容不出来。”
我们的交谈忽然顺畅起来。我问她为何总是独自来看电影,她说我失眠,在电影院里才能有点睡意。我笑说怪不得你看喜剧也没反应呢。
不久后她又独自来看午夜场,散场后我送她回家。她住在江边的老房子里,窗外可见明亮的工地与乌黑的江面,轮船的灯光正缓缓滑过犹如一个低沉的音符。她告诉我,这里房租便宜交通也方便,“不过也住不长了,这里可能马上要被拆掉。”
房间里的陈设非常简单,桌、椅、床以及梳妆台而已。梳妆台上散落着几张超市小票,我告诉她我有保留超市小票的习惯,“知道么,这些小票都保留下来以后就是一本日记。”我说。她看着我含义不清地笑了笑。
我们在黑暗中拥抱抚摸。我说这房间的味道与我的房间有点像。“是树林的味道。”她说。“是森林。”我说。她嗯了一声像是轻轻的叹息。
我们倒在那张略嫌狭窄的床上。我的胳膊搭着旁边的梳妆台,在她高高低低的呻吟声中,我下意识地把一张小票握在了手中。
早上醒来时,我发现手中握着的却是一片枯叶,它颜色焦黄已经断成了两截。我轻轻叫了一声,她忙问怎么了。我把枯叶团在手中说没什么。
我原准备留着这叶子,但回家后却翻遍口袋也找不着,我想肯定是遗失在路上了。
那之后,她再也没来过电影院。不久后那老房子也拆掉了。我不知她去了哪里。
八
我换了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远离了凌晨两点的街道。
我的三餐与作息时间都已恢复正常,图书馆的安静也让我觉得很适应。那些读者也都是很安静的人,他们大多神情忧郁,身上有着失败者特有的涩涩味道。我时常觉得自己也是他们之中一员。图书馆其实就是为失败者准备的,每当看到意气风发者走进图书馆,我就知道他走错了地方。
自换了工作后有一个问题总困扰着我:究竟哪种人更好—是电影院里那些俗气的观众,还是这些安静文雅却明显更不快乐的读者呢?我觉得那答案在潜意识里。
我能感受到房间的变化,它不再像森林而只是像一棵树,树枝光秃气息清冷仿佛冬天。有时夜里醒来,我穿戴整齐走到门外。
我侧耳细听,但身后的空房间依然寂静无声。
在深夜的超市里我接到了小个子女友的电话—在分手后她又找了个银行职员,听起来就比我强得多。
“看看,得亏和你分手了,要不哪能找这么好的。”她炫耀道。
“这么晚打电话来就为刺激我?”
“你呀,别把人都想得和你一样,我是让你努力点,也去找个好的。”
“没那可能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没哪个女人比得上你。”
“这话我可真爱听,再多说两句。”
“唉,伤心欲绝,说不下去了。”
“去你的吧,算了不跟你废话了。”
挂断电话,我继续流连在货架前。那薄薄的湿润气息已倏忽远去。
九
我的金鱼还剩下最后一条。我为它买回最贵的全价饲料并隔两天就换次水,为防它跳出来我还在鱼缸上加装了网罩。这金鱼看起来很悠闲,似乎并不觉得孤独。金鱼眼中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或许它看我们就如同我们看它一样?看着这条又孤独又悠闲的金鱼,我很有些疑惑。
金鱼曾在地板上游泳,这段录像我存在手机里,但某一天它突然消失了。这其实也无关紧要,想起那天的情形我觉得它清晰如昨,根本无需录像来证明。
老余果真辦起了一家养鸡场,他打来电话详细说明了地址并说你来看看吧,这里一个院子就有一幢别墅那么大,这里的空气纯得会让你发晕的,这里的夜里有很多萤火虫你还根本没见过萤火虫吧……
我沉默不语,我想问“那儿有女人吗?”但始终开不了口。一个总是衣冠楚楚的人却真的去山里办起了养鸡场,我对这事还有点上不来实感。我想老余养鸡时是什么样子?或许仍然穿着一身正装?
我承认我对老余并不了解。
每个月初,我翻动挂历打量着后面的日子,它们不会有什么不同这令我感到很心安。
偶尔我重新回到电影院,虽已离开一年多,但我仍能熟练地找到座位。此刻我也是一名俗气的观众,即使那电影并不好笑我也与观众一起大笑。是的,做个俗气的人也并没什么不好,我想多数人最后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金鱼被网罩碰掉了一只眼睛,我取下网罩后它终于从鱼缸中跳了出来,那天回来后我发现它已死在了地板上。它不会在地板上游泳,它眼中的房间与上一条眼中的不同,当然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我不再养金鱼,鱼缸中很快便装满了书籍、牙签、方便面、饼干以及绿豆、小米等等。
没有金鱼的房间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十
火车车厢像一片平原,慵懒杂乱而且开阔。人们在这里也如在平原上,大声地说话随便地吃东西大大咧咧地玩游戏。
我的邻座正一手托着手机一手抠着脚,他看得相当投入不时嘿嘿地笑出声来。
我也在看手机,但几乎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窗外是一条小河,那水光就如同一片剪影。这时是八点多钟,仅仅驶离那座城市两个小时,我已觉得四周非常的陌生。
我和邻座忽然开始交谈。我提到了近郊一新开发小区里闹鬼的传闻,他一拍大腿,“咳,你还别不信,这些事真说不清,我跟你说件真事,我亲身经历的一点不掺假。我十岁那年—大概还不到十岁吧,有天夜里起夜,卫生间里有块镜子,我边撒尿边朝镜子看,就见镜子里面还有个人,穿白衣服,没看清是衬衫还是啥,脸也晃晃悠悠的,我当时一下吓傻了,哇哇地哭,可爸妈过来后镜子里又啥也没有了。我后来一直记得这个,我真就不相信那是眼花……”
他的故事吸引了旁边的旅客,有人马上就接上了话:“你这可能是幻觉。我说一个,那才真的一点水分没有。那年夏天,我们一帮人在外地搞工程,天热,晚上我们都上房顶睡觉。那天在上面看着电视,正有点迷迷糊糊的,忽然见一老乡坐我旁边。这老乡是我同学,一直留在老家没出来,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我和他就说了会儿话,问他怎么出来了,又说既来了就留下来一块干吧。他说还有事,只坐一会儿就走。我拉他手说了一会儿话,他就走了。过两天就有消息来,说是这老乡头几天就得病死了。这可把我们吓住了,他来那天不只我一人看见,旁边人全看见了,我还拉着他手说话呢。你说这事咋解释?谁又说得清……”
这时聚拢的旅客越来越多,对于这话题看来人人都有些故事。无形中我的位置已被挪到了外围。正好这时我也到了站。我下车时他们对灵异事件的讨论还正热烈。
这是邻省的一座小县城,之所以在此下车是因为我的钱只够到这里。
夜里十点多钟,正是夜市热闹时。我溜达了一会儿,在街边吃了碗酸辣粉,然后随便找了家小旅店。
房间的地板上有残留的淡黄色污迹,床单有很浓的洗衣粉味,卫生间的镜子上有层雾显然很久没擦过。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倒在床上抽烟看电视。
我想起了父亲,二十多年前,父亲总是在节假日独自去旅行。他没有目的地,去火车站赶上哪趟车就上哪趟—他管这旅行方式叫“瞎撞”。父亲旅行时什么也不带,总是空手去空手回,所以即便住在工厂的宿舍区里也少有人知道他的这一癖好。那时我曾问他哪个地方最好玩,父亲说其实都一样没什么好玩的。
后来父亲进入销售部整天跑外地,列车时刻表也记得滚瓜烂熟,任何时候去火车站他都知道最近的那趟车将要去哪儿。他的旅行再不可能是无目的的,这“瞎撞”的癖好也就无形中被终止。
现在我也开始了这样的旅行。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自然的。管它去哪儿呢,随便逛逛就行—这样的念头我想人人都有。
我掐灭烟,出门去了楼下的网吧。坐了四五个小时的火车来此却只是打游戏,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凌晨三点回旅店睡了一觉。醒来后我便去火车站搭上了返程的火车。
仅仅相隔一天,房间的气息已有些混浊,或许它也和我一样逃开日常的轨道去打了个盹。我打开窗子通风,同时想起这房间最初的样子—那时它光秃秃的什么也沒有,粗糙的水泥地面上还留着一摊尿迹。
这幢楼同样的房间有一百多个,如今它们肯定已拥有各自的真相—我不相信每个房间都是一片森林。
然而这终究也无关紧要,房间只是房间,我们进入房间睡觉起床然后离开,所谓真相其实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
所谓真相其实一钱不值。
电梯平稳地向地面滑落。我嘴里仍有酸辣粉的味道,但那小县城却已如相隔十年。我抬头看着显示板不禁又想到了老余,他现在在干什么?正西装笔挺地满山跑着捡鸡蛋?不知为何这画面竟突然显得十分真实。我想下个假期一定得去看看他。
在渡轮上,我又碰到了那女孩。“我上个月去过两次影院,可都没见到你。”她说。我告诉她我已经换了工作。接下来我们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都转头盯着江面。船上颇有些游客,面对着这条大江他们非常兴奋,一边不断地拍照一边四处指指点点,有人甚至吟诵起了诗句。我和她不禁相视一笑。是的这些游客很值得羡慕,他们做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我知道她肯定也这么想。
下船后她带我去了她的住处。
她的新住处仍然离江边不远,也仍然极简单,床、桌、椅以及梳妆台而已。窗外是小湖,有人正沿着湖慢跑。
我们看着窗外。她突然轻声说道:“你闻到了么?这房间里也有森林的味道—”我看着她,然后搂过她来,用吻封住了她余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