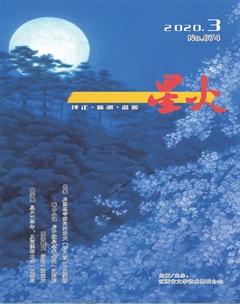后圆恩寺胡同的秋天(诗八首)
王家新,诗人、批评家、翻译家,1957年生于湖北丹江口,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诗集《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未完成的诗》《塔可夫斯基的树》《重写一首旧诗》《未来的记忆》《旁注之诗》,诗论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为凤凰找寻栖所》《雪的款待》《在你的晚脸前》《黄昏或黎明的诗人》《翻译的辨认》《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1941年夏天的火星》,翻译集《保罗·策兰诗文选》《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没有英雄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等。另有《当代欧美诗选》《20世纪外国诗人论诗》《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中外现代诗歌导读》《新诗“精魂”的追寻:穆旦研究新探》等编著数十种。
后圆恩寺胡同的秋天
从茅盾故居出来
“嗖”的一声
一辆自行车从我的身边窜过去了
是一位穿校服的少年
安静、寂寥的古老胡同
没有任何人,好像是
我自己的前生或来世与我擦身而过
我看着他起身蹬车,只那么几下
消失在小巷尽头……
青灰的墙。墙角
垃圾桶和上锁的三轮车……
两棵高出屋顶的老树
以黝黑的枝干、满树青黄的叶子
问候着我们生命中的
又一个秋天
我们家的兔子
我们家本来有两只兔子,
一只死了之后,另一只活到现在。
我最爱我们家的兔子,
是在它抖抖地吃生菜叶的时候。
我们已把它养了四年多,
我每天出去给它买吃的。
我一走近它,它就趴到铁栏杆上,
激动地向我张望。
孤独吗?但是我们也看不出
它有什么悲哀。
只是有时早上起来发现
它把干草梗掀得满地板都是!
我们能做的,只是蹲下来,
轻轻地、久久地
抚摸它抽动的后背和大耳朵……
但是我们家的兔子从来不叫,
它只是有时在用前爪给自己挠痒痒时
会发出几声“嘟”“嘟”。
我惊异世上还有如此安静的造物!
我给它、也为我自己
放上了巴赫。
但现在,我却有点怕见到它。
经常在夜半醒来后,当我起床,
打开灯的开关穿过房间
去厨房找水喝,我看到它
仍在那里蹲着,甚或站立着
静静地望向落地窗外……
它怎么不睡觉?
它在等待着什么把它带走?!
篁岭一日
—给陈离和他的学生们
我们在雨后的黄昏入住
在第二天的雨雾中离开
我们不是思想家,甚至也还不是诗人
如有可能,那就化为
这些在屋檐下来回飞翔的燕子
我听见了它们无声的鸣叫
我们在山道上散步,一会儿下雨
一会儿起雾,一会儿霞光
闪射在我们的额头上
而在满山的雨瀑声中
我更爱这墨色的屋瓦、赭红的砖墙
和小巷中撑伞的寻梦人了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从风尘仆仆的
人世,到这山上,我们知道了
什么是一个人的感激和自由
我们在夜晚读诗,每个字念下去
都应和着这高山上的安静
我们住在“添丁巷”的一座小楼上
但在“担水巷”的低矮门口
留下了我们最孩子气的合影
如今我已回来数日,眼前仍是青山流云
一条带着哗哗水响的小巷
和雨后窗玻璃上最晶瑩的雨珠
“我听见一个声音……”
“我听见一个声音,一只鸟的声音,
这声音对我讲话……”
—“顾城在德国或维也纳的开场白
总是这样”,顾彬回忆说。
是,在伦敦时他也这样,我在场。
那只鸟,好像是为了他的演讲,
从波恩飞到了英国。
那只鸟在飞,在我们的童年
我也曾听到它的声音。
那只鸟还在飞,但我们都不再可能
说出它的名字。
那只鸟在飞,在鬼进城的时候,
它曾和蝙蝠一起飞撞进我们的胡同……
那只鸟还在飞,一会儿是卡夫卡的乌鸦,
一会儿是山东下放农场上空的百灵……
那只鸟在飞,它不飞,
整个世界都会朝深渊里坠……
那只鸟还在飞—当你飞过激流岛,
请飞得低一些吧,请哀悼
你的永远沉默了的诗人。
秋末
秋天到来我们才感到自己植物学的贫乏。
银杏树谁都知道,但是其他那些
也变成彩色的树呢?是枫树还是槭树?
一周前我在锣鼓巷看见几棵满树黄叶的老树,
我以为是黄栌树,
但他们告诉我叫“白蜡树”。
……秋末,我们攀上北京西山。
曾是一片苍翠的世界,现在一片褐灰,
愈来愈接近岩石的颜色。
霜降过后,除了几株还挂着红黄圆叶的黄栌,
满山杂树的叶子都已落尽。
而我们静静地走在山路上,好像也不是
看红叶来的(我们来看什么?)
路边灌木丛中的小浆果早已熄灭,
脚下的落叶,一片焦枯……
只有一棵苍黑的树上还挂着几个鲜红的柿子,
它们让人仰望,但却够不着—
好像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
能拥有的最后的果实。
伦勃朗晚年自画像
伦敦,国家艺术馆。
两幅伦勃朗自画像,一张是年轻时的,
自信地面对着世界;
一张是六十三岁时的,
但那似乎已是另一个人。
他在望着什么?
—这已是很多年前的一次参观了。
今天,当我从外地归来,
踩着一路干燥的落叶,疲惫地
回到我的书桌前,
你晚年的那幅自画像,
好像从幽暗的光中释放,
出现在了我面对的墙壁上—
平和,而又锐利、深邃
睿智,但又带着审视
好像是从你的调色板上调头
你的目光,径直向我投来
而我接受了这样的注视,
好像是从一个什么大梦中醒来;
好像我多走了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与这样的目光相遇;
好像我已可以去死……
我接受了这样的注视。
我知道,它就为我准备。
我接受了这样的注视,既然
它出现在了这样一个秋天。
在冬日的颐和园
1
如果,在巴黎的街巷
也能出现这一棵松树,在冬日
依然葱茏的松树
(我们谈到了策兰)
如果,那条陷入冰川纪的石船
也能够起航
如果
在我家从一楼到五楼的昏暗楼道里
每天也能涌上一阵初雪的
清凉的气息
如果,……
2
这是十二月,我们
在半结冰的昆明湖边上行走
谈话中有穿堂风
有瑟瑟抖动的荻花,也有
来自天空的石头
下午的黄金般的光打在冰面上
有点让人想哭
而芦苇,一枝北方的凛冽
而垂柳,它们在各自想着
自己的心事
3
但是,我们还是走吧
我已无力注视
远山变暗的剪影
(石拱桥上,残雪,
词的一角湿润)
我们来了一趟
我们能否再来?
会来,那些溜冰的孩子会来
(当气温降至零下……)
那些冬天的小燕子会来
会来,一个雪人会来,被废黜的
盲眼王子会来
会来,愿你也会再来—
从你还遥远的晚年赶来
雪中吟
1
白茫茫耀眼、落雪的冰湖
一串還未走到湖心
又折回的脚印
好像那就是我未能完成的一首诗
开始是想试一试,后来每一步
都伴随着恐惧
2
似乎雀鸟比我们更喜欢雪天
路过一个小公园
在一棵高高的白杨树上
我看到一群叽叽喳喳的喜鹊
有八只
我把这张照片放在朋友圈里
有人说:“在你诗中还有一只”
是的,我都忘了,但它就在那里
我有一颗石头之心
也有一颗喜鹊之心
我有一颗喜鹊之心
只是它已很难找到它的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