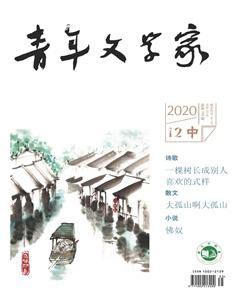析纪德“道德三部曲”中主人公的三重人格
方晓梅 宋敏生
摘 要: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道德三部曲”(《背德者》《窄门》《田园交响曲》)中主人公的性格各异,人生经历也各不相同,但三部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均以悲剧告终。本文通过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论来分析三部小说中主人公的人格特征,包括米歇尔的本我、阿莉莎的超我和牧师的自我,旨在挖掘造成悲剧结局的深层原因,探索隐藏在文本背后作家深邃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纪德;三重人格;创作心理
作者简介:方晓梅(1995-),女,汉,河南信阳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硕士在读;宋敏生(1977-),男汉,湖北黄冈人,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法语文学与翻译专业博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5--05
引言: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说,他将人格分成三个部分:本我(伊底)、自我和超我。本我(伊底)处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它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包含人类的最基本需求,遵从快乐原则,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为目的。弗洛伊德认为,“伊底当然不知道价值,善恶和道德。与唯乐原则有密切关系的经济的或数量的因素支配了它的各种历程。它所有唯一的内容,据我们的观点看来,就是力求发泄的本能冲动。”[1]58-59 自我处于人格结构的中层,起到警戒线的作用,阻止本我进入意识层面,遵从现实的原则,将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欲望压制到无意识层中,并且在社会规范的许可范围内满足自身的需求。“这个系统针对着外界,介入了知觉,而且当活动时还产生了意识的现象。它是整座机器的感觉器官,它不但接受外在的刺激,也感受内心的兴奋。我们尽可承认自我是伊底的这样一个部分,这部分可因和外界接近而受其影响,又可为感受刺激的目的服务而使机体不受损害,其功用有类于环绕于活的物质的周围的外层。它与外界的这个关系尤其是自我的特点。自我以外界的消息供给伊底,从而挽救了它,不然,倘若伊底力求满足其本能而完全不顾强大的外力,便难免于灭亡了。”[2]59-69 超我处于人格结构的最上层,它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既可以抑制本我的冲动又可以对自我实行监督。超我遵从唯美原则和至善原则,它包括两个重要部分:一为自我理想,是要求自己的行为符合自己理想的标准;二为良心,是规定自己的行为免于犯错的限制。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文学批评中也得到广泛应用。文学批评围绕作品、作家和读者展开,而精神分析批评关注的焦点在于作家,具体来说,即是通过分析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语言、行为模式等揭示作家的创作进程和心理动态。通常,我们把《田园交响曲》、《背德者》和《窄门》并置起来,称之为纪德的“道德三部曲”或“爱情三部曲”。我们发现,作家在这三部作品中呈现出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人物形象,但人物在人格结构上又相互关联。李建琪运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论分析纪德《田园交响曲》里面的牧师的人格结构,指出牧师在“超我”和“本我”的两难境地中利用宗教教义自欺欺人以求“自我”的平衡。景春雨在《安德烈·纪德“道德三部曲”中的“自我与上帝”评析》一文中,提出米歇尔的非道德主义、阿莉莎的禁欲主义和牧师的虚伪自欺。纪德为何写作这一“道德”或“爱情”系列?他有什么隐秘的创作心理?我们将通过文本细读,运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分析这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人格,进而揭开纪德的创作动机。
一、《背德者》中米歇尔的“本我”
在《背德者》中,起初是主人公米歇尔在蜜月旅行期间患上肺结核病,妻子玛丝琳陪伴在侧并予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后来,米歇尔的身体逐渐好转甚至完全康复,但玛丝琳由于被丈夫传染也染上了肺结核病。医生建议玛丝琳去阿尔卑斯山上疗养,因为那里的空气清新,有助于身体康复。米歇尔对此建议之所以非常赞同,是因为他自己也很想在这样的地方度过整个冬天。在阿尔卑斯山待上一段时间之后,玛丝琳的身体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没有完全痊愈,但是米歇尔却以高山上的清新空气已经对玛丝琳完全发挥作用为借口说服对方下山前往意大利,这其实是因为米歇尔已经对高山上的生活厌倦至极,现下他自己非常向往南方的融融春光,所以他才不顾妻子的病体,带着妻子南下。一踏上意大利的土地,米歇尔就感觉到:“我的所有欲望一齐爆发。爱的巨大积蓄把我胀大,它从我肉体的深处冲上头脑,使我的思绪也轻狂起来。”[3]90相较于高山上苍郁的落叶松和冷衫,意大利秀美轻盈的繁茂草木使米歇尔感觉到生命的气息,能够激发他的欲望,使其具有无限的活力。当意大利的天气变得潮湿阴晦无法再让米歇尔感觉到生命的气息时,他又带着妻子继续南下。尽管每到一处,米歇尔都会精心准备,像似再也不会离开此地,实际上他感觉有魔鬼在驱赶着他继续前行。这只魔鬼实则是米歇尔对强者的渴望和对弱者的毁灭。在继续南下的途中,米歇尔在大自然中汲取力量,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具有旺盛的精力与活力;同时,玛丝琳的身体在频繁易地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得到调养反而日渐衰微。米歇尔表面上是为妻子的身体着想才去寻找气候温暖的地方,其实他是在本能欲望的驱使下满足自身的快乐。
“由于何等荒唐谬误,何等一意孤行,何等刚愎自用,我援引我在比斯克拉康复的事例,不但自己确信,还极力劝她相信她需要更充足的阳光和温暖啊?……其实,巴勒莫海湾的气候已经转暖,相当宜人;玛丝琳挺喜欢那个地方,如果住下去,她也许能……然而,我能自主选择我的意愿吗?能自主决定我的渴望吗?”[4]94
通过上面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米歇尔并没有从妻子健康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让自己的本我占据人格结构的上风,完全听凭本我欲望的支配,而不考虑现实的因素,从而以牺牲妻子的健康为代价。在米歇尔看来,“强者自有强烈的快乐,而弱者适于文弱的快乐,容易受强烈快乐的伤害。玛丝琳呢,有一点微不足道的乐趣,她就要陶醉;欢乐再强烈一点,她反倒禁不住了。她所说的幸福,不过是我所称的安宁,而我恰恰不愿意,也不能够安常处顺。”[5]92 相较而言,玛丝琳更喜欢温和静态的生活,而米歇尔更喜欢强烈动态的生活。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脚步,而是让自己始终处于运动的状态,到各地去感受和体验生活,让自身的欲望得到满足。除了不停地南下,他时常抛开病重的妻子,而是跑出去和下层的民众接触,他或是与妓女鬼混,或是對长相俊美的马车夫又亲又抱,要么是融入到码头的工人或是流浪汉的群体中,甚至主动与阿拉伯人挤到一起过夜,因为这些人身上体现出原始的野性特质。
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中,本我按照快乐原则行事,是原始的人,不受任何道德规范和社会原则的限制。这一点在米歇尔身上展露无遗,他完全不受社会等级制度或是道德规范的影响,乐于与下层群众为伍,或是为偷盗的人隐瞒事实的真相,哪怕受害人是自己也无所谓,因为和这样的人群待在一起 ,他的本能欲望就能得到最彻底地释放。正如米歇尔所说:“我模糊地意识到文化、礼仪和道德所掩盖、掩藏和遏制的完好的财富,而这种模糊的意识在我身上日益增强。于是我觉得,我生来的使命就为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发现;我分外热衷于这种探幽索隐,并知道探索者为此必须从自身摈弃排除文化、礼仪和道德。”[6]89也就是说,米歇尔不仅放纵自身的本我,抛开自我,而且力图挖掘人的真实本性。用玛丝琳的话来说,米歇尔总是让人们暴露某种恶癖才会心满意足。而米歇尔则认为,“人的最恶劣的本能才是最坦率的。”[7]95此处,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米歇尔在为人的本能欲望寻求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在玛丝琳去世后,米歇尔说道:
“老实说,令我恐慌的是我依然年轻;我时常感到自己的真正生活尚未开始。现在把我从这里带走,赋予我生存的意义吧,我自己再也找不到了。我解脱了,可能如此;然而这又算什么呢?我有了这种无处使用的自由,日子反倒更难过。请相信,这并不是说我对自己的罪行厌恶了,如果你们乐于这样称呼我的行为的话;不过,我还应当向自己证明我没有僭越我的权利。”[8]102
此处,尽管米歇尔依然维护本我欲望的合理性,但是没有了作为丈夫的责任和义务,他无法再找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本我欲望的无限释放使他经历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二、《窄门》中阿莉莎的“超我”
阿莉莎和杰罗姆虽然是表姐弟关系,但是两人相互爱慕已久,感情深厚。当阿莉莎发现妹妹朱丽叶也喜欢杰罗姆时,阿莉莎的超我战胜了本我,选择牺牲自己的幸福,让杰罗姆娶朱丽叶为妻,成全妹妹的幸福,体现了超我的至善原则。杰罗姆明确表示自己爱的人是阿莉莎并且不会娶朱丽叶为妻,后来朱丽叶另嫁他人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阿莉莎也并没有和心爱的杰罗姆在一起。
“在他和上帝之间,惟独有 我这个障碍。如果像他对我讲的那样,他对我的爱当初也许使他倾向于上帝,那么事到如今,这种爱就成为他的阻碍了。他总恋着我,心中只有我,而我成为他崇拜的偶像,也就阻碍他在美德的路上大步前进。我们二人必须有一个先行达到那种境界;可是我的心太懦弱,无望克服爱情,上帝啊,那就允许我,赋予我力量,好去教他不再爱我吧;我牺牲自己的功德,将他无限美好的功德献给您……”[9]206
此时,阿莉莎的超我依然占据上风,因为通向上帝的路是一条窄路,容不下两个人并肩前行,她认为自己是杰罗姆通往上帝道路上的阻碍,为了帮助自己心爱的人到达上帝那里,阿莉莎再一次选择牺牲自己的尘世幸福,再一次压制自己的本我欲望,拒绝与杰罗姆结婚,这里再一次体现出的是超我的至善原则。同时超我的唯美原则在阿莉莎身上也有所体现:“不,杰罗姆,我们的美德,不是极力追求来世的报偿:我们的爱情也不是寻求回报。受苦图报的念头,对于天生高尚的心灵是一种伤害。美德并不是高尚心灵的一件装饰品:不是的,而是心灵美的一种表现形式。”[10]204《窄门》中的阿莉莎为了追求上帝的爱德,选择了极端禁欲的生活,因为她错误地理解了上帝的法则,认为爱德与爱情是相互对立存在的,“她将人的灵魂与身体视为完全对立的两个范畴,只有禁绝由欲望带来的感性快乐,对身体加以折磨才能使灵魂变得更加纯洁,最终进入天国以实现永生。”[11] 这不仅让杰罗姆饱受不能与心爱之人结合的痛苦,而且也让她自己在痛苦中不断挣扎直至死亡。事实上,阿莉莎放弃了本我追求的肉体爱情,选择超我所追求的精神恋爱,前者是真实存在并且触手可及;而后者却是虚无缥缈的、无法触及的。
在阿莉莎的人格结构中,超我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压制她去满足本能的欲望,其自然本性受到极端压制,结果是阿莉莎饱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一步步迈向死亡。但是,超我又并不是只会给人带来痛苦。阿莉莎在日记中写到,“不错,超过人世欢乐,越过一切痛苦,我感觉到了这种无与伦比的欢乐。我达不到的岩顶,我知道有个名称:幸福……我也明白,如果不追求这种幸福,我便虚度此生……”[12]217 海涅曾将禁欲主义视为基督教培育的一朵花,“这朵花绝不难看,只是鬼气森然,看它一眼甚至会在我们心灵深处引起一阵恐怖的快感,就象是从痛苦中滋生出来的那种痉挛性的甘美的感觉似的。在这点上,这朵花正是基督教最适合的象征,基督教最可怕的魅力正好是在痛苦的极乐之中。”[13] 可以说,超我压制本我使阿莉莎感到无比痛苦,同时,超我对至善和唯美的追求也使其因自身的美德和完美理想的实现而感到快乐。所以,超我本身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在阿莉莎身上,她的痛苦则来源于超我的過度压制本我,意图消灭人的最基本、最自然的欲求。
三、《田园交响曲》中牧师的“自我”
在盲女失去唯一的亲人后,牧师将其领回家中悉心照顾,并为盲女量身定制方案教授其知识。起初,牧师是以上帝爱德的名义来照顾和开化盲女,他的亡羊比喻认为:“一个人如有一百只羊,走失一只,他不是要将九十九只羊丢在山上,去寻找那只迷途的羊吗?”[14]233对牧师来说,盲女即是走失的那只羊。因此,即使自己家境困难,牧师也没有放弃盲女,而且相较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牧师对盲女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是牧师人格结构中超我的体现。另外,考虑到现实的因素,牧师的自我也在发挥着作用:“我最好离开她,觉得同她单独关在小教堂里毕竟不妥,一来要敬重这个圣地,二来也怕惹起非议—尽管平常我根本不理睬那些流言蜚语,但这又牵连到她,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了。”[15]242 牧师的自我遵从现实的原则,由于担心近距离的相处有损盲女的名声,所以他在与盲女的相处过程中会刻意避嫌。
在后来与盲女热特律德的朝夕相处中,牧师对热特律德的情感发生了变化。当盲女拒绝牧师教她弹琴而接受牧师儿子雅克的指导时,牧师对儿子产生了嫉妒之心。为了防止热特律德爱上年轻英俊的雅克,牧师以父亲的名义要求雅克远离盲女,实际上此时两人的父子关系已经演变成情敌关系,牧师不过是以父亲的权威赶走自己在爱情上的竞争对手。为了让雅克淡化对热特律德的感情,牧师将盲女送到德· 拉· M小姐处生活,但他仍然以牧师的名义去与盲女见面。牧师的一系列行为反映出的是他的本我欲望,这种本我欲望不遵从任何的道德规范和现实原则,体现在牧师身上就是他在已婚的状态下爱上了盲女,并且为了将盲女占为己有,他剥夺了儿子雅克的爱情。
但是,造成这场爱情悲剧的真正原因要归咎于牧师的自我在调控本我欲望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冲突中选择了自欺欺人的手段。也就是说,牧师利用上帝爱德的外衣掩盖了自己对于热特律德的自然情欲。牧师一直自欺地认为他对盲女的爱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这里面没有任何违禁的成分,“因为我相信爱情是该受谴责的,我认为一切该受谴责的事使人心情沉重,我心情不感觉沉重,也就不相信这是爱情了。”[16]66而牧师之所以没有负罪感,实则是因为他在解读《圣经》时只选择迎合自己的内容,他认为《福音书》中并没有任何命令、威吓、禁戒,禁令来自于解经人对《圣经》的误读。从这里可以看出,牧师在有意通过《圣经》的解读来模糊上帝的爱德和世俗爱欲之间的界限,并以此来获得心理安慰。另外,盲女之所以不知道她与牧师的爱情是一种罪,也在于牧师在谈论《圣经》时有意避开“罪”的部分,导致盲女因为无知而陷入对牧师的爱情中。最终,牧师在上帝爱德的掩护下实现了自身情欲的满足,与盲女完成了精神与肉体的结合。当盲女复明后,她看到了上帝的诫令,也就看到了自身的罪,选择通过自杀的方式来赎罪,留给牧师的只剩下如荒漠的心。
四、纪德的内心世界
纪德的作品甫一问世,读者就试图从他的作品中窥探作家本人的生活,而纪德本人却说:“我无论写哪部书,也从来没有全部投入进去,最急切要我处理的主题,很快就往我自身的另一个极端发展了。别人不易画出我思想的轨迹;这种弧线仅能在我的文风中显露出来,一般人是看不见的。假如谁在我最新的作品中,以为终于抓住了与我相似的人物,那他就错了:与我差异最大的,总是我最新的产物。”[17]450在弗洛伊德看来,作家与其他人一样有着本能的冲动,作家写作就是通过社会许可的方法是去发泄自身的欲望。在纪德的朋友热昂看来,纪德是天生的道德家,强迫自己不道德,举棋不定和谨小慎微的处事方式使他长时间处于一个改变的边缘,但从没有屈服于改变。那么对于纪德来说,他是拿自己笔下的人物做实验,让他们代替自己去行动去改变,去探索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因此,纪德每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只能反映纪德的一个侧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纪德通过作品塑造了一个潜在的自己。宋敏生指出:“写作是纪德的生存方式。他的生活与创作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他将自己多彩的生活和对生活的思考写进作品,通过作品中自己形象代言人来尝试每一种极端生活的可能性。”[18]
从纪德的“道德三部曲”来看,前一部作品总是对后一部作品 的否定,也就是说他在作品中建立一种存在的可能性,继而推翻这种可能性,然后又重新建造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对纪德的评价:“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人相比,纪德都更具有对比性。他就像性格多变的普罗透斯一样,一直在改变他的态度,他为了能撞击出闪亮的火花,不知疲倦地在两个极端活动。所以他的作品呈现出永不间断的对话,信仰一直反抗着怀疑,禁欲一直反抗着对生命的热爱,戒律一直反抗着对自由的渴望。”[19]
事实上,在纪德的作品中,除了作品与作品间的对话以外,每一部作品本身就有对自身否定的部分。纪德曾说:“我喜欢每本书里都含有自我否定的部分,自我消灭的部分。”[20]11具体而言,《背德者》包含有对个人主义的批评,《窄门》包含有对神秘主义的批判,《田园交响曲》则是包含有对人的虚伪性的批判,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纪德“道德三部曲”都以悲剧结尾。深究其根:首先,纪德从小接受的宗教教育使其养成时常自省的习惯,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日记,如《窄门》和《田园交响曲》,这也是因为日记更有利于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因此,纪德的作品体现出反思性的特征;其次,正如盛澄华指出的那样,“纪德对他每一件作品最大的关心,不在是否这作品能得到一时的成功,而是如何使它能持久。这‘永远的今日‘永远的青春正是纪德在艺术上最高的企图与理想。而为达到这目的,对于艺术品思想价值相对性的重视与认识,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21]8 就拿《田园交响曲》这一部作品来说,纪德固然有对牧师的虚伪性的批判,但这绝非是作家全部的写作目的,這部作品真正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对简单的道德判断的超越,而意在揭示人性的复杂,《背德者》和《窄门》各自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吴晓东在《田园交响曲》的序言中写到,“纪德认为每个人的生活当是由两种相反的力所构成。这两种力的相互排斥、挣扎,才形成一切生命的源泉。所以,在艺术中我们有想象与现实的对立,在意识中有思想与行动的分歧,在社会中即形成个人与集团的抗衡,在恋爱中即形成情与欲的冲突。因此他的作品所表现的常是一大片战场,在那里上帝与恶魔作着永远不断的角逐。”[22]5-6从这里可以看出,纪德是在通过探索自我,从而探索普遍人性的复杂性。
纪德将自身的复杂性归因于遗传:“在我的生活中,什么也不持久,什么也不坚定,什么也不可靠。我与自己时而相像,时而不同;不管多么陌生的人,我也敢发誓能够接近。我年已三十,还不知道自己是吝啬还是大方,是简朴还是奢侈……或者说,我感到自己突然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我的命运就是在这种摇摆中完成。为什么我要虚假地模仿自己,给我的生活制造一种虚假的统一呢?我能在运动中找到平衡。两种迥异的生活方式在我身上相交叉,我忍受的这种复杂性、这些矛盾,通过我的遗传可以得到解释。”[23]351纪德的父亲来自温暖的南方,性格温和宽容,热爱大自然,情感丰富,但可惜英年早逝。纪德的教育重任落到母亲头上。她来自寒冷的北方,性格刻板保守,做事循规蹈矩,是十足的清教教徒。因此,纪德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成长,禁欲主义成为他生命的底色。
美国心理学家,环境决定论者毕生认为,“人的行为、人的全部组织都好像一套待动的机器,这架机器只有傻乎乎地 等待着环境和训练给他指令,以决定动作的发展和方向。”[24]47张佐邦在《文艺心理学》中表示环境虽然对人的个性气质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他认为在毕生的观点里,人成为环境的奴隶,完全丧失人的主体能动性。张佐邦认为,“人是永远也不会像机器那么‘乖的,在人的机体中,有一种通过‘集体无意识积淀而来的先天的主动创造欲,这种创造欲常常表现为对任何支配意志的反抗的本能。”[25]47从纪德的自我虚构作品《如果种子不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性格中的反叛特征,这与他母亲对他实行的严格教育不无关系。当外在的压力越大时,人所产生的反抗力也越大。纪德生活环境和家庭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努力挣脱宗教思想的束缚,探索自我,解放自我,从更深层次来讲,他是在作品中通过理想的人探索普遍的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人存在的问题。
纪德突破禁欲主义的禁锢,大胆追求身体的解放,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的朋友热昂和王尔德的影响,热昂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认为,纪德在我这里寻找他本人缺少的东西:某种动力,活力,力量,健康,直率,还有,我承认,满足自己欲望的勇气。”[26]223 如果说热昂给了纪德满足自己欲望的勇气,那么纪德从王尔德那里得到的就不只是勇气,还有对自己伦理观的肯定。除此之外,纪德在1896年就曾贪婪地阅读过朋友亨利·阿尔贝发表的一篇主要讨论尼采思想的长文一一“道德主义的危险”,并且和作者讨论。1898年,纪德读了亨利·利什唐贝热的《尼采的哲学》,文章中透彻而详细地论述了尼采的整个创作。读完这篇文章后,他写信给德鲁安:“尼采把我逼疯了。他为什么存在?我会疯狂地想当尼采。我嫉妒他一一发现了我最秘密的思想。”[27]169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尼采的思想对纪德的自我解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和王尔德一样提供给纪德的是满足自身欲望的信心和勇气。
纪德的文学观也指引了他的精神追求。他在《论那喀索斯》中宣扬自己的文学观,认为真理是散落在世界各处的,是散落在万事万物中的,那么艺术家的使命就是去不断搜集飘散在各处的真理,而真理又是不能穷尽的。因此,艺术家永远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袁筱一在《违背道德的人》这部作品的导读部分这样解读纪德的文学使命:“如果说文字是对真实的探索,是对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与真实生活的有限性相反,这种探索却是永无止境的。”[28]
结语:
虽然纪德总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提取素材,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并非真实的纪德,而是纪德通过艺术的手法创造的理想的人,作家真实的自我则隐藏在这些理想的人物背后。通过弗洛伊德三重人格结构学说分析“道德三部曲”,我们可以对纪德的创作心理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探索自我,在作品中实现自身的欲望,同时也是通过作品来反思自我。纪德在《背德者》和《窄门》中将主人公推向极端最终导致他们走向毁灭,在《田园交响曲》中主人公实现了灵肉的完美结合,然而最终也是走向死亡,这似乎是在暗示作家自身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灵肉冲突和矛盾。纪德从个人的内心世界出发,实则是为了揭示包括自身在内的普遍的人性的复杂性。虽然现实中的人内心不一定经历着纪德如此强烈的 灵肉冲突,但是作为社会中的人,难以逃脱社会的道德规范束缚,而人自身动物性的一面势必会与社会规范产生冲突。换言之,人的灵性和动物性之间的冲突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故而,纪德的“道德三部曲”揭示了人的存在困境和真理。
参考文献:
[1][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3][4][5][6] [7][8][9][10][12]纪德:《背德者·窄门》[M].李玉民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1]景春雨:《安德烈·纪德“道德三部曲”中的“自我与上帝”评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6(03).
[13]海涅:《論浪漫派》[M].张玉书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
[14][15][16][20][21][22][法]安德烈·纪德:《田园交响曲》[M].马振骋译,上海:上海出版社,2011.
[17][23][法]纪德:《纪德日纪》[M].李玉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18]宋敏生:《纪德的“那喀索斯情结”与自我追寻》,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276-277.
[19][法]安德烈·纪德:《窄门》[M].陈诗雨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2
[24][25]张佐邦:《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6][27][英]艾伦·谢里登:《安德烈·纪德一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伟大人物》[M].刘乃银译,2003.
[28]纪德:《违背道德的人》[M].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