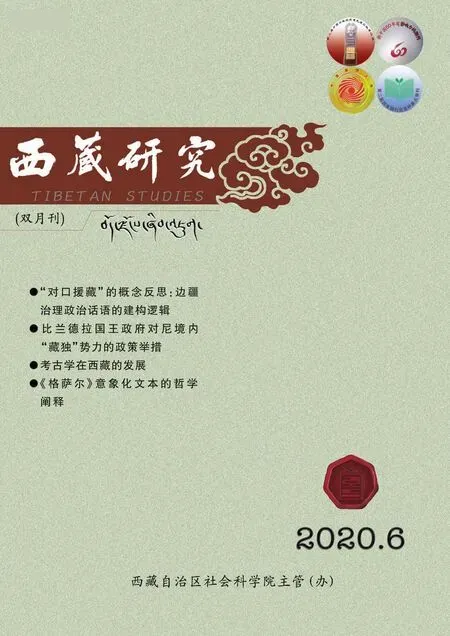《格萨尔》意象化文本的哲学阐释
丹珍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近20年来,随着世界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深入,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1)即《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研究受到世界关注。对民间口头文学、史诗传承、史诗学的理论探讨,尤其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活形态口传史诗珍贵价值的发掘和研究,开始进入深度性考察分析和学理性研究阶段。对史诗观念、史诗传统的认知,以及史诗的研究范式,正悄然发生变化。诺布旺丹新著《诗性智慧与智态化叙事传统:格萨尔传承类型的再发现》正是在此学术语境下出版的一部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著者通过对《格萨尔》史诗书写艺人丹增扎巴的叙事文本、艺人成长语境的深度追踪研究,将丹增扎巴的创作称为“智态化叙事”文本。所谓“智态化叙事”,就是在传统《格萨尔》史诗传承类型如神授类型、圆光类型、掘藏类型、顿悟类型、吟诵类型等基础上,重新对史诗传承类型进行的解构与建构,并以分层化分析发现的一种新的《格萨尔》史诗叙事形态。著者认为,丹增扎巴的叙事文本及其创作形态属于掘藏史诗中的“意念掘藏类”[1]38,他的文本与神授艺人的说唱文本、吟诵艺人的说唱文本以及其他掘藏文本都不同,丹增扎巴的史诗故事习得,并不是传统的口耳相传,亦没有特定的说唱地点或表演性活动,而是以书写方式进行的文本演述,属于《格萨尔》艺人个体生命的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这种叙事文本,是以象征主义手法和超世俗叙事视角对民间叙事的独特演绎,是《格萨尔》史诗从口头走向书面、从诗性走向智性、从世俗性走向神圣性的一种过渡性的特殊文本形态。本文认为作者研究丹增扎巴文本的叙事特质,即是阐释其“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艺人“想象性类概念”建构的英雄世界和民族“根隐喻”智慧的融合演绎。
《格萨尔》史诗的“活形态”特征,当代传承的新实践、新话语,意味着学者在田野的新发现和所谓“活鱼要在水中看”的学术实践。同时,学者于书斋中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理性思考与科学分析更加重要。附录部分是著者走进田野,对几位著名的《格萨尔》艺人(丹增扎巴、昂仁、格日尖参等)以及青海果洛本土《格萨尔》专家诺尔德的田野访谈日志。附录一是著者对丹增扎巴、老艺人昂仁(已去世)、著名掘藏艺人格日尖参(已去世)、果洛本土《格萨尔》专家诺尔德的访谈录,真实记录了史诗艺人的世俗生活与创作实践,可圈可点和不可忽视的是其丰富的信息量与材料的启发性。附录二是作者提供的佛教伏藏经典目录和《伏藏宝典》经卷目录。附录三是《格萨尔》伏藏本部分的文本目录。这些原始资料,为今后交流中进一步完善《格萨尔》史诗叙事形态研究敞开了新的话语空间。
一、“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

有天夜里,我梦见一座小小的山丘,很多人在绕着它转,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山的一面,有一扇门,进入这扇门之后,发现这是一个堆放着很多书籍的三层楼的房子。人们边瞻仰边向前行进,然后爬上了三楼。我好奇地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地方,他们无言以对……我拿起一只装有书稿的破损的皮箱。其中有三部长条书,后一部有些破损。前面两部上面写道:《世界格萨尔大王传白红片光——一百一十八部故事大纲》。当时我顿悟,所谓白光代表妙音女神,红光代表文殊菩萨。我所要写的《格萨尔》应该就是源于他们的无尽智慧(是他们在护佑我取《格萨尔》伏藏)。当我从头阅读时发现,先是叙述关于董氏八弟子(将士)攻取八大吉祥宗的故事大纲,并且每个大纲都以八吉祥图案镶饰 ……第二天,这八部故事的名称和大纲我都记得很清楚。为了感激神的恩典,我立即向神进行了供奉,并写下了一首小诗,此后又写了一篇名为《八大宗大纲阐释》的文章。从此,我便有了写大纲的习惯。
后来有天夜里,我梦见七个佩戴黑盔甲的男人在地上给我铺了一张虎皮,赠给我褐色披风,还有一对乐器,对我说:请你立即把这个乐器吹响八次。八大宗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扩写[1]119。
梦,在丹增扎巴的创作中成为间接启发或激活其潜意识故事原型的重要方式,并会对梦中的语言进行自我转喻。“神话思维”“诗性智慧”一脉相承,“以己度物”的传统类比式隐喻思维,是神话思维以象表意的直觉领悟,不能用科学理性来分析衡量其所具有的思维特质。这种“以已度物”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往往是创作者从自己的角度、个人化的心态去体验事物感悟生命和解释客观现象。如同人类学家弗雷泽研究提炼出的相似律,“以已度物”是“秘索思”(Mythos),而非“逻格斯”(Logos),更不是“赛因斯”(Science)(3)“秘索思”(Mythos):神话故事;“逻格斯”(Logos):逻辑推理;“赛因斯”(Science):科学理性,即一个建立在词源考证基础上,解释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理论元概念。。丹增扎巴对自己无比痴迷的英雄故事加以个人想象,并不断丰富和完善,把情感寄托幻化于外物,以自身为标准来推想和类比外物,是“将心比心”的思维方式。这种“以己度物”的主体性体验,也是他对自己所生活环境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和宗教氛围的文化心理感受,是对民族英雄叙事的信仰化、神圣化。
一个民间艺人的创作才华,从来离不开其生长的本土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丹增扎巴生活在海拔3800米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这里是全国降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坐落着藏族人心目中的“年宝玉则”神山(意为“神圣的松耳石之巅”),这里草地丰美,牛羊肥壮,景色宜人,从小生活在这宽阔、恬静的草原上,全然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只有日出日落、岁月交替和无尽的遐想神思。对于丹增扎巴来说,草原、天空、神山、圣湖,都是他奇思妙想的灵感来源和驰骋想象的创作语境。雪域高原本就传诵着说不完的英雄故事,如奔流的江河从未断流,延续至今。神奇的大自然为《格萨尔》艺人插上了诗意的翅膀,把远古的神话时空、金戈铁马、战争硝烟与和平女神的容颜都带到了他眼前的生活中,开启了其诗性智慧,激活了其潜意识灵感。
著者将丹增扎巴对史诗本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置于其成长的自然生态环境、民间传统文化中,勾勒出其故事结构形态的参照物和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写作视角,以及创造性的艺术神话思维形式。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理文化空间中,自然与文化、主体性的体验模仿与理解感悟等有机地融合在了丹增扎巴“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中。
二、“想象性类概念”建构的英雄世界
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其著名的人类学哲学著作《新科学》中,将“诗性智慧”作为想象的审美共通感,阐释了人类的理解想象力是如何根植于个体生命以及与他者的融通中。在他看来,人类与生俱来就有非凡的想象力,诗性智慧就是凭生动的想象力来创造的,以直观方式对生命本质进行关照的。诗性智慧代表着人类的想象力、创造性以及生存品质的整体性与超越性。人类的想象、直觉和感性自诞生起就深深打上了族群文化诗性智慧的烙印。希腊神话流传千年,伟大的荷马就是希腊人不羁的想象力、绮丽的神幻思维创造出的英雄人物。
从“神话思维”到“诗性智慧”,丹增扎巴的“智态化叙事”文本以“想象性类概念”建构了他的英雄世界。著者在书中分析:“其创作演述看似是一种书面化的创作,实则是一种口头传统在另一种方式下的演绎;其文本中出现的各种人物、场景、主题、故事范型等诸多事项,看似是故事情节的一般性展现,实则是一种对现象世界在另一种视角下的观察和解读,倾注了艺人的生命意识……将现实与理想、战争与和平、慈悲与无情融为一体,在创作过程中,心灵的激情自由穿梭于虚实、空灵、古今、时空之间。他的文本不仅仅是简单的叙述英雄故事的史诗,而是一种在‘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意象化世界之旅中演绎出来的‘精神图谱’”[1]6。这个“心游万仞”的意象化世界演绎出来的“精神图谱”,是诗性智慧不同于实用理性智慧的感性智慧,而个体情感的寂静“观想”,心思旷达,简单质朴,也是藏族诗歌的传统,是藏族诗性智慧与西方诗性智慧的显著不同点,“观想”传统把想象力带入特定的生命情景中,既是对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缅怀,也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更是对生命本体精神的一种绵密传承。
作为“智态化”掘藏艺人,丹增扎巴眼中的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意象世界两部分。他通过观察现象世界认知、解读潜藏于其后的意象世界或意义世界,也就是把无数个偶然或必然的现实事项视为蕴涵或象征某种意象世界的“信息流”。这种“信息流”又通过现实生活或经验世界中的某种自认或人为的现象,抑或在梦境幻觉中出现的某种符号、文字、意象等象征性符号呈现……“信息流符码”在他的世界中随时会出现,甚至一件很普通的事项,在他看来也具有某种神秘意义,代表和象征着《格萨尔》故事的某个片段或主题……史诗故事的习得完全属于一种个体的神秘心理性体验。[1]41
丹增扎巴意象世界“个体的神秘心理性体验”,即为诗性智慧的“想象性类概念”。作为观照史诗世界的特殊方法,其核心的艺术思维方式便是想象、幻想。诗性智慧是想象和创造的智慧,也是超验的智慧。我们不能不认同人类所有创造活动都首先从想象出发,进而开拓到一切领域,特别是宏大史诗叙事的发生或创作更需要超强想象力。“古代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社会制度、宇宙观等的起源,都是古人运用诗性智慧对于世界的想象与创造。”[3]通常我们会将“类比推理”称为现代思维方式类型之一,其实早在人类原始神话思维阶段,这种认知方式就已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一种能力。诗性智慧之于一个当代《格萨尔》艺人的想象力,又是怎样的相映生辉?我们可从本书附录部分,看丹增扎巴观照《格萨尔》史诗世界的方法:
在书写时,一旦开始提笔书写,一句句、一段段故事相继涌入脑海,并不是整个故事在霎那间显现在脑海。有时,若干个故事情节同时蜂拥而至,让人不知道应该先捕捉哪一个好。有时,一些意象顷刻间涌入脑海又在霎那间消失。我怀疑,这是不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能够自由驾驭(自己意念中出现的),有时,虽然在心里显现了一些信息符码,但若想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又显得很模糊。在任何嘈杂喧闹的地方都不能静下来写作……
每当我开始写《格萨尔》故事时,首先要念诵《七句祈祷文》和《格萨尔祷告文》,将自己的心置于世俗的杂念之上,与格萨尔、莲花生等智慧之心融为一体。然后,矫正自己的道德信念,发善愿。开始写正文时,一心将所显现的内容付之于笔端,还要寻找叙述善事的段落,停笔歇息(因为我个人认为,在叙述一个美好事物的段落处停笔,办事会很顺利圆满,反之,做事不利)。在完成之后,又要这样发愿:书写格萨尔上师传记所带来的功德,将消除世界上一切疾病、饥饿和战争,让佛教有情众生之事业弘扬光大!总之,神授故事是由于自己曾经得到(莲花生)嘱托和发愿,而今对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及其本质有了感悟,自己的智慧之门得到开启,并从中涌现出宝藏之波涛而创作出的……[1]113-114
如果艺人的智慧之门已经开启,那么,书写的史诗故事内容自会从其意念想象世界中显现,并汹涌而来。丹增扎巴的文本《杰瓦益西宁布传记》,是一部关于《格萨尔》岭部落支系——直家族弟子的前世生平业绩。关于这个故事的缘起,丹增扎巴称自己是直家族某个弟子的转世,“转世”直接使个体生命的某种情感、情结与史诗故事人物有了必然联系。艺人自述:有一年去拉萨朝圣,来到唐古拉山附近一个叫盐水品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个盐湖。有天夜里,他梦见一座神山,山上有个据说是藏珠喇嘛乌坚的修行洞,两边流淌着潺潺溪水。旁边有一城堡,只剩下残垣断壁,在他的想象中,此地正是史诗中岭国三十员大将之一的直噶德的城堡遗迹。次日,他就激动地写下了《直噶德赞词》。
无论是梦的媒介或是神的启示,诗人、创作者总能通达无限的想象力花园。丹增扎巴“自认为是直家族弟子的转世”,这个强烈的自我心理暗示也是其想象力和梦境的引线或动机之一。梦中浮现的所谓家族的以往记忆,那些潜意识中隐匿的故事人物、主题、情境等,其实都是在强调创作者个体生命与自然环境、宇宙万物的沟通与交流,是艺术本性的“灵韵”显现与情感互动的彼此印证。《格萨尔》艺人这种前世今生的“想象性类概念”,打破并重组了通常的所谓空间与时间的结构,创作主体是以个体生命为内核,感受心灵和自然的原始性、隐喻性,于是来自本源的诗性、梦幻性和自由灵活的想象力皆成为其文本创作的“情感脚本”,使其创作表现出生命的情感性和具象性的一体化、史诗故事与生命情感的同一性。高阔的疆域总为善于诗性思维的民族创造了信仰的蓝天,想象力让神灵和梦幻由此布满诗意,丹增扎巴的英雄世界由此建构。
三、 民族“根隐喻”智慧的融合演绎
大千世界,万物环环相扣,皆有自然的相似性与各种辩证联系,这是隐喻之所以存在的理据。亚里士多德说,诗歌是隐喻的语言,诗歌使用隐喻最多,一个字面背后还有另一个隐含本质的根源意义。美国哲学家派帕(Stephen C.Pepper)1942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隐喻理论——根隐喻(root metaphor)。派帕的根隐喻理论,本质、直白、清晰地浸透着哲学对立统一辩证的原初运思,致力于说明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和观察世界的(4)派帕观察到“我们对不同类型、形式、范畴、语类等的注意力是根据事物的相似性来陈述的,这些概念逻辑上来自相似性的根隐喻。”他观察到人们往往是用他们具备的基本常识和现实经验去理解其他领域的概念。人类的世界观总有一些互相联系的中心范畴,而这些中心范畴来自根隐喻,或原型,或概念。。俄裔著名诗学家、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借助失语症的研究,确认了隐喻与相似性的直接联系,认为隐喻是表达相似性“最凝练的方式”。根隐喻的哲学思维阐释了人类的概念系统本质上都是隐喻式。隐喻不仅存在于我们表面语言的使用中,还存在于我们思想与文本的创作实践中,隐藏在人们思维系统中的“根隐喻”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深层核心概念。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世界早期的认识,并且对我们日常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与生俱来凭借原型、潜能、直观、想象,拥有了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推理或玄学思辨。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隐喻”和“转喻”已经成为《诗学》的核心概念。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对隐喻研究的多学科突破,隐喻有了更丰富深刻的表达方式,“根隐喻”可称为一个民族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的基础。如果我们把藏传佛教文化作为阐释与丹增扎巴世界观、创作观互相联系的“根隐喻”中心范畴,我们就能看到,诗性的本质特征就是隐喻和想象,他的文本创作图式,以诗性智慧的形象思维将“原始智”特点的“伏藏”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文本叙事的结构模式上,显示了创作主体在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中与格萨尔史诗千丝万缕的自然链接,具有从认识论和哲学思维角度的合法性阐释。即“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在藏传佛教文化对待事物的一种特殊视角下,表现为创作图式与主体性神话思维、想象性类概念和民族“根隐喻”的融合演绎,阐释了关于生命哲学的意象化文本,传承并建构了《格萨尔》史诗的智态化叙事,通过根隐喻的映射体会传达史诗世界的故事内涵。
著者诺布旺丹对《格萨尔》伏藏文本有过较长时期的关注与研究,其博士论文为《伏藏史诗论》。这一前期积累和认真准备给予本书的写作以极大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条件。附录部分,有一段作者对果洛本土《格萨尔》专家诺尔德的访谈,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伏藏史诗的“智态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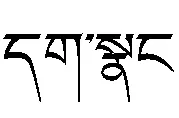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根隐喻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在语言和文化的衍变中,根隐喻永远不变地使人与自然万物间建立了人类精神心理中最原始的关联域。根隐喻和隐喻思维链接着人类古老生活的宗教、仪式、巫术、习俗和基本信仰,不仅是史诗存在传承的根基、史诗语言创作的构成方式,也是史诗文化的基本构成方式。从隐喻思维来看,物质的世界即是一个圣物的世界,也是一个事物的世界,任何事物、动物、植物或者颜色等都可能具有隐喻性或符号功能,它自身也同样隐含着一种表意程序,一种特别陈述,隐含着一个意义场或自然—文化的关联域。正像每个句子或本文的构成包含着一系列的语词。一个实际的仪式程序也并不只涉及一种象征物,而是依序波及一系列的象征物。“人类古老的生活形式由于具有一种象征性,由于对事物符号化的理解,人类的活动才变成了文化活动,其生活形式才成为文化形式。在某些传承了神话与仪礼之遗风的习俗中,事物的符号性与行为的象征性,不仅净化了行为的粗蛮性,而且增添了文化意义,甚至具有某种诗意”[5]。
不难看出,作为一种体验、情感方式、信仰和理论范畴,原始智是根隐喻的哲理性思维结构,其实亦存在于各民族文化早期的精神心理内核中。瑞士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医师荣格以科学的态度,从古代神话、传说和宗教中,来理解人类的幻想和梦境,他的原型理论、集体潜意识概念,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他说,“在我看来,宗教是一种特殊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符合于religio一词的原始用法。religio意味着对某些充满活力的要素的细致而小心的体察。这些要素被想象为各种‘力’(Powers)——灵气、魔鬼、神祇、法则、观念、理想等。无论人们以什么名称去命名这些要素,它们在人们眼中始终是一些强大、危险、有益的足以对之仔细体察的东西,或者始终是一些伟大、美丽、有意义的足以对之虔心崇拜和爱戴的东西。在日常的口头语言中,人们往往说那些热情专注于某一追求的人对自己的事业几乎是一种‘宗教式的献身’。例如,威廉·詹姆斯就曾经说,通常,科学家并没有任何教义,但他们却具有‘虔诚的气质’”[6]。当然这里的“宗教”不是指宗教的教条,而是建立在对某种具有“神秘”性质的体验及其在意识中引起的变化的忠诚、信赖和相信之上,一种主体的体验意识特有的态度。通过这种视角所体悟到的现象世界,便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理想的意义世界,是诗性思维不可或缺的哲理审美境界,并成为文本“文学性”直观而具体的表述。
丹增扎巴的创作文本明显呈现出两种文化系统的创作印记。首先是故事的原型文化形态,其次是故事的再生文化形态。两种认知形态既是《格萨尔》史诗英雄叙事中的始元本真,又是史诗故事的演绎或再创作形态。口头文学的“活态传承”与民间文学的“文学维度”两者相结合,既是“以己度物”的主体性体验下英雄故事的文学创作,也是“想象性类概念”认识的宗教化、信仰化的英雄叙事。实际上更是对史诗艺人所生活的部落民族所共有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观念的隐喻和阐释。这种根隐喻的融合性演绎思维,使得人们把存在的东西看作喻体去意指那些不存在的或无形的喻意。一切存在的,只是一种象征。壮丽的隐喻、动人的故事,才是诗歌的生命。在这种思维状态下,著者认为,“智态化”文本艺人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些已证悟佛性、彻悟事物本质和“原始智”大智慧思维者。
四、结语
20世纪末,劳里·航柯在对西方史诗的研究中发现,史诗的范例是多样的,其预言21世纪对史诗的研究将会更加多元化。《诗性智慧与智态化叙事传统》一书,是作者对自己多年积累的《格萨尔》伏藏史诗资料的再度整理与研究思考,是通过对田野调查、文献资料和艺人手稿的归纳分析,针对《格萨尔》史诗个体记忆形态的发现与反思,是一次对《格萨尔》史诗理论与实践的跨学科探索。丹增扎巴的叙事文本是藏传佛教文化的民族“根隐喻”智慧对待事物的一种在特殊视角下产生的特殊文本,并非本雅明焦虑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如上文所述,丹增扎巴的文本创作图式以诗性智慧的形象思维,将“原始智”特点的“伏藏”以“潜文本”的方式“隐潜”在文本叙事的结构模式中,显示了创作主体在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与《格萨尔》史诗千丝万缕的自然链接,即“以己度物”的主体性神话思维,在想象性类概念和民族“根隐喻”的融合演绎基础上,阐释了关于生命哲学的意象化文本,建构并传承了《格萨尔》史诗的智态化叙事。
对丹增扎巴文本“创作图式”的分析和归纳,可以拓展《格萨尔》史诗研究领域的学术潜力。所论“智态化叙事传统”的象征主义手法和超世俗的叙事视角,在民间叙事中的独特演绎,是对史诗传承类型的重新发现与建构。这种所谓特殊的叙事文类,早已存在却从未被深入研究与真正命名。著者视野开阔,文献翔实,其学术性和探索性对当下相对薄弱的《格萨尔》学科建设和史诗理论研究以及学术范式的转换,具有开创性意义。新的学术思考点和方法论的启示意义,为《格萨尔》史诗学的“国际对话”与学术互鉴,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